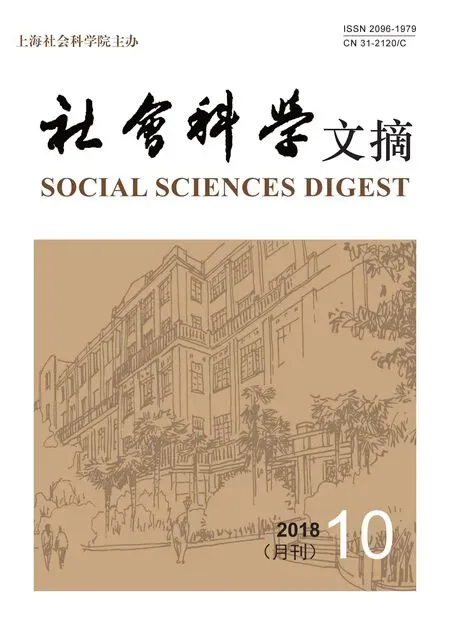中国当代作家的海外传播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碰撞之后,便陷入现代民族国家的“主权”“生产力”和“文化”焦虑之中。这些“现代性焦虑”渐次得到缓释的过程,基本也是一个新型现代民族国家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历程。1912年中华民国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先后缓和了“主权焦虑”(但直到现在仍有诸如台湾等遗留问题)。随着中国经济总值达到世界第二并不断拉近与美国的距离,“生产力焦虑”也得到了很大缓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代中国的文化焦虑:在世界范围内,文化影响力处于严重滞后的局面,和经济影响力形成一种“不对称性”现象。
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两次大的西学东渐之后,似乎没有输出什么被世界普遍认可的价值观、社会思想或人文精神。因此,国际社会流传着英国政治家撒切尔夫人的一种说法:中国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因为中国没有足以影响世界的思想体系。当代中国文化影响力的生成,首先不同于经济增长,其次也不同于国内文化发展。文化影响力的生成要有起码的国家耐心,坚持以质取胜,避免低标准的数量扩张和虚假繁荣,杜绝无实效的文化“面子”工程,否则极有可能出现花钱不讨好、自欺欺人的尴尬传播局面。文化创造从来就是一种心灵艺术,而内心的认同与接受来不得半点勉强。如何让当代中国文化从海外的客观“传播”走向真正的内心“接受”,我们需要从国家行为到民间交流各个层面的探索与研究。本文拟通过对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以来部分典型作家、作品海外传播的考察,希望能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一种参照。
政治的美学转化
60多年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大致经历了一个政治淡化、美学凸显、边缘影响力不断加强的演变过程。当代文学及其海外传播的源流关系决定了其发展史基本也吻合国内当代文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总体特征是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对外传播。“冷战”的基本格局决定了这一时期的海外传播主要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阵营及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间展开。社会主义阵营出于互相声援、资本主义阵营出于“认识敌人”的需要,都由国家对文学作品进行有组织、有规模的译介,这导致明确的政治意识形态目的性取代了文学本身的审美追求。中外文学交流方式是有组织的,文学译介则是泛政治化并且深受政治关系的影响,导致这一时期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并非文学的审美力量。从海外传播的角度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外文化“输出”和影响最大的阶段,恐怕正好是“文化大革命”带给世界的震惊。
第二阶段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基本特征是政治与美学的混生发展。这是中国当代文学最为激烈变化的时期,虽然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始终会受到国内和海外各类“混杂性”因素的影响,但这一时期当代文学整体上由“意识形态化”的海外传播开始转向政治与美学“混生”的传播期:即社会学式的“传声筒”中开始听到一些文学审美的声音;“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传播主体阵营在这一阶段开始分化;在传播的方式与渠道上更多表现出从本土到海外的趋势;译介作品类型与速度上从单调滞后到多元同步;最重要的是对作品的阅读开始有了从政治到艺术的审美转变,虽然这种转型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完全结束。
第三阶段是21世纪以来,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变得更加常态化和多元化。21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经历了前期“意识形态化”“混杂性”阶段后,进入到文学的常态与“多元化”时期。当然这也可能是最为复杂的阶段——它既没有断绝早期意识形态的阐释角度,也深受后期全球化商业操作的影响;既受国内文学发展的深刻制约,也受译介国本身的政治影响和文化筛选;既有自发的作家、作品译介,也有国家力量参与的文化翻译工程。和第一阶段形成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大传播阵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在同样形成了欧美与东亚文化圈两个传播中心,却褪去了很多政治色彩。这些转变说明,当代文学正在悄然从边缘处生长出一种缓慢、温和,但更容易让世界认同和接受的传播力量。
当代作家海外接受的基本特征
统计分析20世纪以来大约430位中国作家的海外传播资料(英语为主)之后,笔者发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存在鲜明差异性的同时,也确实有如下一些最基本的特点和规律:
首先,当代文学的海外接受整体上很边缘化,影响力十分有限。即使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或者其他国际文学大奖,于大局不会有实质性的影响,只是会较好地带动作家本人的海外接受状况。但国内媒体或者学界在短时间内的集中讨论,非常容易给人造成“虚胖”的繁荣印象。
其次,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在地理特征方面会形成两个中心圈。一个是发达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德国、英国、美国等;另一个是东亚文化圈国家,如韩国、日本、越南等。相应的会形成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另一个基本的翻译规律,即只要在英、法、德三个语种获得成功的作品,也很容易在其他语种获得更大范围的传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英语往往并非是翻译最早、最多的语种,法语、日语,甚至近年来越南语和韩语呈现后来居上之势。在这一总体格局中,作家又会形成各自的传播特点。比如莫言、余华在越南的译介,莫言因翻译家同时也是汉学家,研究就会更突出一些,余华的作品则呈现出“翻译先行、研究滞后”的特征。即使是同一个作家的作品在不同国家表现也会很不一样。
再次,作品“被禁”、电影改编以及海外获奖这些具有强烈“吸睛”“聚光”效应的影响因素,虽然对某些作家作品的海外译介的确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从长远来看,真正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创作本身。实力作家的作品往往会持续被译介,数量多,语种多,再版多,评论多,获奖机率也多。我们需要明白,翻译只是流通环节中最重要的因素,而能否创造出优秀的文化作品才是制约当代中国文化能否“走出去”的关键所在。没有好作品却花力气硬推出去,只会沦落为被嘲笑的对象。这也是为什么强调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要从“传播”努力向“接受”转换的根本原因。
民族性与人类性的世界写作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与实力相近的作家相比,其决定性优势可能在于:其海外传播的各项关键因素几乎没有短板。比如莫言、余华、苏童的作品都属于海外译介和接受较好的,但莫言作品的民族性和本土性更浓郁。贾平凹、王安忆和莫言相比,虽然实力相当,但他们作品的海外译介数量和影响则落后了很多。莫言、贾平凹、阎连科都属于乡土风格,作品中的现代主义、批判性因素也很明显,甚至都有被批判或被查禁的作品,但贾平凹在翻译、海外获奖与影响方面有欠缺,阎连科的海内外接受比莫言、贾平凹甚至晚了10年以上。这些既是作家海外传播的差异所在,也是莫言海外传播的特长所在。
莫言作品更多的是以本土性、民族性的写作特征获得了海外传播的成功。《红高粱》是莫言最早被译介到海外并获得声誉的作品,其中浓烈的本土性、民族性内容,艺术上大胆新颖的创造性,使莫言在海外的传播从开始就显示出某种大气磅礴的成熟。莫言是从电影改编中获益的当代作家。他后期的《酒国》《丰乳肥臀》等作品并没有被改编成电影,但在国外和《红高粱》相比却似乎反响更好。这说明电影改编及海外获奖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作家的经典化程度。良好而稳定的翻译者,是影响中国当代作家和作品海外传播的关键因素。一般来说,兼具翻译家、学者和作家三重身份的译者是最理想的人选。莫言的许多译者正好符合这一特点。
余华作品海外传播的成功,主要源于他以一种极简化的写作方式表达了人类性的主题。余华小说极简化的语言风格和人类性的主题内容,使其更容易克服翻译和接受的障碍。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电影《活着》获奖,对其小说的海外传播是否有直接影响,但余华的小说从1994年起确实开始有了更多的外译。余华的海外奖项不论是从数量还是分量上讲,都似乎超过了国内奖项,作品经典化程度很高。苏童的海外获奖不多,但其海外接受状况,并不比莫言和余华逊色。苏童的海外传播也许正好说明:作家经典化和海外获奖之间并不一定存在必然的关系,一个作家的地位归根到底是由其作品质量决定的。余华、苏童、莫言都首先通过代表作获得海外市场的认可;海外市场首先从英、德、法三大语种获得成功译介,然后很快地带动更多语种的翻译传播;三人每个语种都会拥有比较稳定的优秀译者,比如葛浩文、马悦然等。
古典与现代中国经验的阻碍
贾平凹作品具有典雅与粗俗并存的特点,小说内容和语言上多有古典志怪、传奇、笔记、话本小说传统的余韵。他是一位能够将古典文学资源和现代社会转型融汇贯通,对中国城乡变迁、世态百相加以生发刻画的重要作家。其外译作品,越南语多达14种,其次为俄语10种,以下依次为日语6种,英语6种,法语3种,韩语、德语各2种。2013年,胡宗锋、罗宾已经将英文版《废都》译出,但迟迟未得出版。2016年由葛浩文翻译的英文版《废都》(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出版)上市,不论是国内还是海外,《废都》都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传播个案。
如果说贾平凹作品的海外传播难度主要体现在如何翻越乡土与古典方面,那么王安忆作品的海外传播难度则主要表现为中国经验与细节的缓慢感知方面。王安忆的译作以英语和法语居多,但语种并不是很多。从1981年《中国文学》(北京)译介《小院琐记》起,其英文译作包括各类短篇小说在内大约近30篇。法语查到的有《长恨歌》以及“三恋”等6部。其他还有越南语和韩语版《长恨歌》,也有少量的德语和日语翻译。王安忆的海外传播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期如英文版《小鲍庄》《流逝》和“三恋”等,后期以《长恨歌》为代表,该作也是我们考察王安忆海外传播的首选作品。王安忆的作品不容易进去,所以会影响到她的海外接受效果。
“胀破”的光焰与世俗的呈现
阎连科创作的成功应该得益于他对常规的“胀破”——不论是国内影响还是海外译介。他的崛起与争议无论是文学的还是非文学的,国内或是海外,在当下中国都有标本意义。阎连科在20世纪90年代末“胀破”常规的写作方式后,其整体的写作风格不断向“极端”“敏感”发展,在题材、语言、文体甚至写作理论方面都有表现,最终形成了一种令人“惊骇”的文学效果。法语对于阎连科作品外译有特殊的“发动机”作用,法国比基埃出版社截至2015年一共翻译了阎连科的8部作品。英语世界的阎连科译本数量虽不多,但影响可能更大。一般来说,其英文译作都有英、美、澳大利亚三国的版本。第一次把阎连科带到英语世界的是蓝诗玲(Julia Lovell)翻译的《为人民服务》(2007),之后辛迪·卡特(Cindy Carter)翻译的《丁庄梦》(2010)进一步扩大了阎连科的接受。罗鹏(Cgrlos Rojas)翻译的《受活》(2012)真正确立了他在英语世界中作为一个作家的地位。《受活》在一些小语种国家的传播接受显然好于“被禁”的《丁庄梦》,这应该是基于《受活》的艺术性而非意识形态。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作家们还得继续忍受海外来自政治意识形态彬彬有礼的高傲目光。
毕飞宇译作也都集中在21世纪以来。从克洛德·巴彦(Claude Payen)2003年翻译《青衣》算起,至2015年,单行本已经不下20个语种,其中法语已有6个单行本,基本包括了毕飞宇最为重要的几部小说。其他语种的翻译包括3个荷兰语译本,2个意大利语译本,2个西班牙语译本以及1个德语译本。毕飞宇作品的英译整体上较晚,1995年葛浩文译介了其短篇小说《祖宗》,收到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集《毛主席看了会不高兴》之中。但毕飞宇真正被英语世界所关注,应该是2010年《玉米》获得了第四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Man Asian Literary),之后迅速就有了3个长篇小说的英文单行本。毕飞宇的海外传播也存在“转译”现象:比如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德语等,早期都是从法语译本里转译的。
结语
中国当代文学正在不断历史化和国际化。在这样一个整体格局中去观察莫言、余华、贾平凹、王安忆、阎连科、毕飞宇等当代文学创作及其研究,也许我们正处于某个巨大的历史转折点上。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犹如地壳深处渐渐积聚能量的岩浆,终于在2012年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形式“胀破”喷发:媒体大面积的报道讨论;迅速成为2013年国内十大学术热点之一;各类文章、课题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许多文学期刊以各种方式给予关注,参与人员突然变得异常丰富起来。长期以来,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研究以一种模糊的形式游离于当代文学、翻译学、比较文学、海外汉学(或中国学)、传播学等相关学科之间。天然的“跨界”性让它的国际化问题在每个领域都沦落为边缘话题或附属演练对象,一定程度上耗散了它本应该深入探查的许多问题,形成了在各领域都一直存在却始终难成气候的研究局面。
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研究,从近两年涌现的大量文章、编著以及课题来看,显然是持续发展的局面。其热情固然令人高兴,诸如复制性、平面化等问题却也值得警惕。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会带来材料、视野、方法以及结论方面的新拓展,如何将“域外”材料和国内批评、研究以及文学史写作有效地结合起来,凸显当代文学不同于其他相关学科海外传播的研究特色就成为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视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就要努力摸索、探讨、建立起一套更为专业、有效的研究经验和方法,要有能力真正打通国内和海外的相关资料,这绝非“外语”+“当代文学”那么简单的事。
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的兴起,让国内学者有机会将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的语境里,从而发现一个非常不同于固有印象的文学“风景”。它是一个研究领域,也是一种研究视角,更是一种研究方法。在初始阶段有必要加强典型个案研究,注重资料性和学术性相结合,“嵌入”自己的研究心得,努力形成一种对话式的专业研究。资料的总量是客观和固定的,如何在补白的同时提高对资料的利用率,写出不可复制的专业意见才是关键。其未来基本的发展应该是:各归其所,和而不同,形成交叉融合的研究局面。即“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理应成为当代文学重要的研究内容,同时兼顾海外汉学、翻译学、比较文学等学科的方法与成果。这一原则同样也适用于其他涉及海外传播的学科,比如电影、美术、音乐、哲学等。这不仅是对当代文学,也是对其他相关学科提出的共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