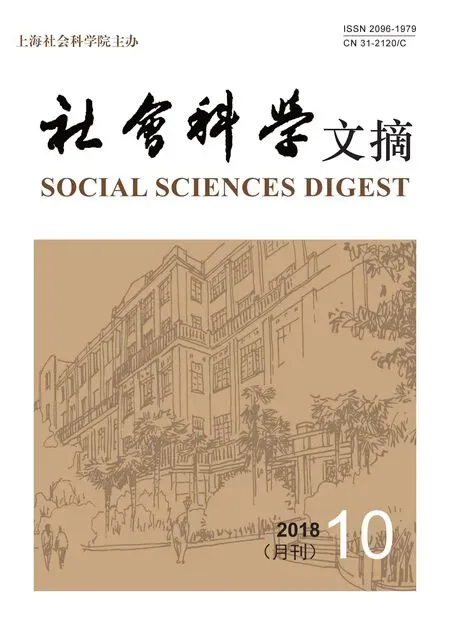女性艺术家的成长:论《奥兰多》中的异质空间建构
作为具有鲜明的性别意识的现代小说大师,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的创作始终关注女性的精神发展,尤其执着于女性艺术家的成长这一核心主题。1924年后,伍尔夫为贵族出身的女作家薇塔·萨克维尔-韦斯特(Vita Sackville-West,1892—1962)所深深吸引,终至在1928年完成了长篇小说《奥兰多:一部传记》(Orlando: A Biography),使其成为献给密友的一封炽热的“情书”。《奥兰多》以薇塔的身份、家世等为原型,虚构了主人公奥兰多在长达四个世纪的岁月中由男性变为女性的奇幻历史。通过冲破地域、种族与性别壁垒的跨界想象,伍尔夫虚构了一个女性的浮士德在异质空间中深入“生活”、探究“真相”的求索过程,设计了奥兰多从16世纪的都铎王朝到1928年爱德华七世统治时期近400年的生命之途,暗合了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博士上天入地、穿越古今的探索之旅。
和浮士德一样,奥兰多从个人情感的“小世界”步入开阔的“大世界”,由西方来到东方,勘破了逸乐、社交与政客生涯的浮华与虚妄,最终在创造性的事业中获得了自我满足与实现。只不过浮士德的创造性事业是在18世纪启蒙背景下的变沧海为桑田,而奥兰多则是在艺术创造的天地中获得了成功。由此,伍尔夫向男性大师与经典表达了敬意,同时又特别关注了女性艺术家的困境与脱困之途,通过三重异质空间的建构,实现了对浮士德式自我实现的女性主义修正。
地域跨界:“重要的是旅程而不是目的地”
《奥兰多》中的第一重异质空间,是通过主人公跨越地理疆域的旅行而得以拓展的。
旅行不仅意味着物理空间的变换,同时隐含着流动性、冒险性、自由身份、经济实力等文化要素,古往今来更多是属于男性的特权。《浮士德》中,中世纪的江湖术士浮士德与魔鬼靡菲斯特击节赌赛、遨游世界前曾豪迈声言:“我觉得有勇气,到世界上去闯一趟,去承担人间的祸福,去跟暴风雨奋战,在沉舟的碎裂声中毫不沮丧。”然而,作为稳定性、依附性与私人空间之象征的女性,与“闯世界”的功业几乎无缘。在反思女性艺术家的创作困境时,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特别指出了简·奥斯丁封闭的闺秀生活对她小说空间想象力的束缚,认为是地理和阅历上的局限性,使她的写作不得不沦为司各特所说的“两寸象牙微雕”,并感叹夏洛蒂·勃朗特“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她的天赋,如果不仅仅耗费在寂寞地眺望远方的田野上,将会有多么大的收获,只要让她有机会去体验、交往和旅行”。所以伍尔夫尽管看到了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和独立的经济地位的重要性,又辩证地指出:“我想到给人拒之门外有多么不愉快;转念一想,给人关在门里可能更糟。”她强调了通过旅行开拓人生、锤炼思想对于艺术家成长的关键意义。
伍尔夫本人即热爱旅行,除了希腊、意大利、法国、德国、葡萄牙、西班牙等地,还曾先后于1906和1910年两次漫游土耳其。简·莫里斯在《与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道旅行》一著中认为,伍尔夫的大部分作品均可被视为独具特色的旅行文学,并与逃离的主题紧密相连。如在《远航》中,伍尔夫使蕾切尔借助前往南美的航程,逃离庸常狭隘的生活轨道,在打破身体所受的空间局限和心灵所受的秩序规约后获得了灵魂的自由。《达洛维夫人》中,具有流浪艺术家的气质、不肯与世俗妥协的彼得·沃尔什选择前往印度,以逃离英国中产阶级的虚伪矫饰;热爱莎士比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老兵赛普蒂默斯更是决绝地以跳楼而死逃避了“权威”人士对其命运的操控和尊严的践踏。到了与《一间自己的房间》几乎同时问世的《奥兰多》中,主人公的地域跨界包含了在都市与田园、西方与东方之间穿行的漫长旅程。通过异质空间的建构,女性身体与心灵的自由得以舒展,由此领略殊异的风景,体味别样的人生,在丰富的收获中激发艺术创造的灵感冲动。
1925年是伍尔夫与薇塔之间关系十分亲密的“蜜月期”。现实中,她对薇塔刚强的个性、神秘的气质以及作为艺术家的成功称羡不已。小说中,她则通过旅行想象,使奥兰多体验了有限人生的多个侧面,由此获得了艺术创造的无限潜能:“奥兰多现在召唤的,可能是那个砍断套在黑鬼骷髅头上绳索的少年;也可能是又把骷髅头栓好吊起的少年、坐在山坡上的少年、看到诗人的少年、向女王呈上玫瑰水碗的少年;或者她在召唤那个爱上萨莎的青年、廷臣、大使、军人、旅行者;或许是那女子、吉普赛人、娴雅的贵妇、隐修士、热爱生活的少女、文人的女恩主……”伍尔夫的爱侄昆汀·贝尔认为,《奥兰多》是“弗吉尼娅最理想化的创造物,他/她就是照她自己所爱的样子塑造的”。由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女性先后赢得部分与完全选举权的时代语境下,伍尔夫以浪漫主义的笔法塑造了通过地域跨界以实现梦想的女性艺术家形象。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教育法案的改革,英国女性更是获得了伍尔夫当年可望而不可得的接受高等教育的珍贵权利,一代知识女性开始生成,女性由静态的私人空间向动态的公共空间的流动性愈益增强,一大批优秀的女诗人、小说家、戏剧家也脱颖而出。无怪女性文学研究专家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在1999年推出的修订版《她们自己的文学》中欣喜地写道:“随着当代流动性的增长,游记写作的盛行,英国女作家已经抛弃了奥斯丁那小小的两寸宽的象牙,而展示了从中东延伸到南极的国际画面。”由此看来,在通过旅行跨界以谋求精神成长这一层面上,《奥兰多》不仅具有先行的意义,也以鲜明的女性立场实现了与以《浮士德》为代表的传统旅行文学的对话。
种族跨界:“扬帆驶向吉普赛人”
《奥兰多》中的跨界书写还体现为对种族藩篱的跨越:既包括身为男子的奥兰多对神秘冷艳、桀骜不驯的俄国公主萨莎那独特的异国情调的迷恋,及其在此基础上对俄罗斯莽原与冻土的向往;更体现为身为女子的奥兰多对吉普赛人生活的向往,以至于即便在回到英国之后,吉普赛营地也始终为其提供了秘密的精神滋养。
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吉普赛人大约在公元10世纪左右从印度旁遮普一带向欧陆迁徙。居无定所的生活方式,使这一生活在大篷车上的民族在部分西方人眼中成为兼具“美”与“恶”的双生花,既神秘浪漫、自由奔放,同时又因占卜、行乞与歌舞表演等独特的求生手段而受到歧视与迫害,长期以来吸引了众多西方作家与艺术家的关注。吉普赛人自由而散漫的生活态度与循规蹈矩的英国中产阶级文明格格不入,但又为不堪清规戒律负累的现代人提供了缅怀逝去的乡村文明、对抗工业化与机械化的冰冷世界的一个出口,因而使得吉普赛营地在不少作家艺术家的心目中成为逃离功利主义的现代文明渊薮的世外桃源。如深受伍尔夫赞誉的女作家乔治·艾略特的小说《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吉普赛营地成为桀骜不驯的小玛姬想象中摆脱刻板的淑女角色对其热情天性的扭曲、投奔自由的一块飞地;自身亦拥有西班牙吉普赛人血统的薇塔的两部小说《遗产》(Heritage,1919)和《挑战》(Challenge,1923)中也有对吉普赛人的突出描写。前辈作家与闺中密友对吉普赛人的热情影响了伍尔夫,使她将女性艺术家突破传统禁忌、寻求自我实现的梦想与这一流浪民族的自由生活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由于薇塔与身为外交官的丈夫哈罗德·尼克尔森曾在君士坦丁堡生活过很长时间,伍尔夫于是将她心爱的主人公投奔吉普赛营地的背景设置在了君士坦丁堡。
热爱写诗的奥兰多从孩提时代起,即怀揣着心爱的《大橡树》诗稿。被任命为大英帝国驻土耳其苏丹国家全权大使后,他不得不锦衣华服地整日周旋在达官贵胄们中间,虚费光阴。他的烦恼,正是浮士德怀才不遇、只能为封建小朝廷的淫逸君臣作法取乐时的烦恼,亦恰似歌德本人在魏玛公国度过的十年御用文人生涯的写真。因此,公务闲暇时分,吉普赛人的自由世界便成为奥兰多的心灵寄托:“在使馆时,她常从阳台上眺望这些山脉,渴望到那里去。那里是她一直向往的地方,对喜欢沉思的人来说,那里可以给予思想充分的滋养。……不再需要盖章或签署文件,不再需要描摹花饰,不再需要拜访什么人。”而由于在反叛主流生活方式与价值规约方面的相通性,“那些吉普赛人似乎视她为自己人”。
与此同时,吉普赛人模糊的性别意识,更是动摇了主流文化中僵化的二元对立性别模式,吉普赛人的另类世界于是成为女性追求性别平等的异质空间。这就是奥兰多“在革命前就与他们保持了秘密联络”的原因,也是她在弃绝了显赫的大使与男性身份之后毅然投奔的新世界:“在一棵高大的无花果树的暗影中,一位骑驴的吉普赛老人在等她。他还牵了另一头带辔头的驴,奥兰多抬腿跨了上去。就这样,在一条瘦狗的护卫和一个吉普赛人的陪伴下,大不列颠驻苏丹国朝廷的大使,骑驴离开了君士坦丁堡。”而在她以女性之躯回到英国,面临着男权社会对其头衔、财产、地位的剥夺,同时在所谓“时代精神”的驱迫下勉力成为一个柔弱的贵妇之后,吉普赛人蔑视世俗财富与名望、以天地为庐、拥抱整个世界的豁达胸襟,更是成为她反思不同的人生价值的宝贵参照。在回国的船上,奥兰多“觉得,无论上岸意味着何等舒适、富裕、出人头地和地位显赫,但如果这意味着循规蹈矩、奴役、欺骗,意味着拒绝她的爱情、束缚她的手脚、闭紧她的嘴巴,限制她的言语,她宁肯调转船头,再次扬帆驶向吉普赛人”。因此,吉普赛营地构成了伍尔夫为女性艺术家的成长所开拓的对抗性别压迫的又一重异质空间。
性别跨界:“获得了双重收获”
在《奥兰多》中,主人公最神奇的跨界是冲破性别间的对峙与壁垒,即在担任大使期间,君士坦丁堡发生了土耳其人推翻苏丹的暴动,奥兰多再度昏睡七天七夜后变成了女人。这一奇妙的构思呼应了人类始祖“双性同体”的圆融特征,集中表达了人类对两性和谐互补的理想境界的向往。
作为在英国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团体“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中熏陶出来的作家,伍尔夫高度重视情感与智性的均衡协作对于艺术创造的意义,曾在罗杰·弗莱逝世后为他举办的纪念画展上,特别谈及她的这位密友与精神导师身上所具有的“两种不同品质——他的理性与情感”的统一。弗莱身上情感与智性和谐协作的品格,在伍尔夫看来是一种完美的人格力量,也是自己努力要通过作品加以传递的信念。与此同时,“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亦使圈中艺术家们无论男女,大都能在同性恋或双性恋的自由选择中践行“双性同体”,集情感与智性于一身,并在各自的领域中迸发出惊人的创造力,薇塔即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而对伍尔夫这一自小即因同母异父兄长的侵犯而遭受性别创伤、成长期又因受教育权利被剥夺而深感不满的女性来说,渴望通过异装或变性幻想以分享男性世界的特权,更是成为十分自然的心理逻辑。
因此,她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提出,与肉体的和谐相对应,头脑中的两性同样应该和谐:“我不揣浅陋,勾勒了一幅灵魂的轮廓,令我们每个人,都受两种力量制约,一种是男性的,一种是女性的;在男性的头脑中,男人支配女人,在女性的头脑中,女人支配男人。正常的和适意的存在状态是,两人情意相投,和睦地生活在一起。”伍尔夫认为,“任何创造性行为,都必须有男性与女性之间心灵的某种协同。相反还必须相成。头脑必须四下里敞开,这才能让我们感觉,作家在完整地传达他的经验。必须自由自在,必须心气平和”。此所谓“头脑中的联姻”。
这一“头脑中的联姻”,在《奥兰多》中,即形象化作主人公神奇变性的超现实主义构思,将两性间的互补关系进一步浓缩为对同一个人身上理性与直觉、情感与智性彼此中和的境界的追求。由此,伍尔夫揭示了诗人的艺术获得成功的奥秘所在。
甫一踏上英国的国土,奥兰多即以换位思考的亲身体验,获得了检视文化、习俗与法律不公的可能性。当年的奥兰多难以理解萨莎无情的爽约,曾无比伤心地指责了她的欺骗背叛和水性杨花;成为女人的奥兰多则在一种新的角度下理解了萨莎的不辞而别,并拥有了与其他女性的秘密情谊。
为了写好从1586年即已开始的诗歌《大橡树》,“她”决意深入生活,通过频频换装而在两性角色之间自由穿行:“她的性别变化之频繁,是那些只穿一类服装的人所无法想象的。毫无疑问,她用这种办法获得了双重收获。生活的乐趣增加了,生活的阅历扩大了。”随着视野的打开,奥兰多不仅通过换位思考呈现了两性看待事物的不同视角,更以丰富的阅历赢得了诗神的青睐,与伟大的诗人产生了共鸣。奥兰多进而领悟了人性中更加复杂而普遍的现象,即“每个人身上,都发生从一性向另一性摇摆的情况,往往只是服装显示了男性或女性的外表,而内里的性别则恰恰与外表相反”。由于单一性别总存在缺陷,双性互补的必要性由此获得呈现。“双性同体”的理想人格结构使得奥兰头脑中的双性可以平等对话,平衡互补,既以男性之躯经历了如浮士德般的漫漫历险,又以女儿之身寻求并拥有了“生活和恋人”;不仅以结婚生子体现出身体的创造力,更以传世之作《大橡树》表达了精神的创造力。由此,小说纪念了伍尔夫对薇塔的爱,凝聚了作家“关于对立性别的理想结合物的观念”,表明经受过多次性别创伤的伍尔夫,呼吁女性克服自身的怨愤,以开阔的胸襟和双性的视野,突破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追求整合性别差异的人性理想。可见,性别跨界以获得双性的互补、思想与情感的兼容,是伍尔夫为女性艺术家的成长构建的又一重异质空间。
结语
综上,作为一部与既有文学传统、与男性大师的经典具有对话性的女性成长小说,《奥兰多》通过跨越地理、种族与性别疆界的三重异质空间的建构,探索了女性艺术家精神成长的可能性,以奇幻的乌托邦想象让女性挣脱了历史的压制与时空的局限,获得了发声的权利。作为伍尔夫唯一的一部未受死亡阴影笼罩的小说,《奥兰多》可以被视为一部具有预言性质的女性版本的《浮士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