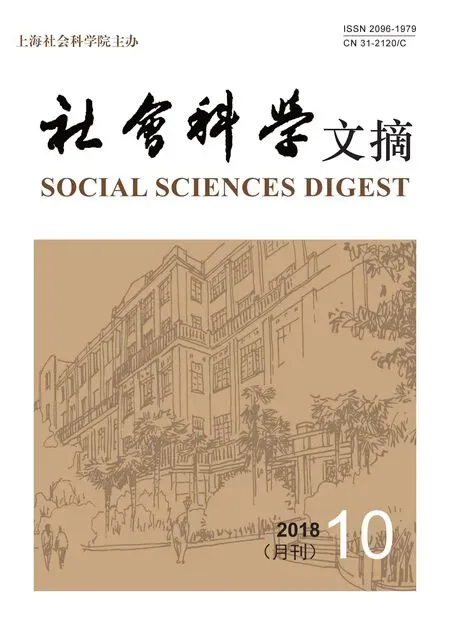二世纪至十一世纪北族前国家时期的社会组织
本文所说的北族,指分布在汉族居住区以北的诸少数民族,东至东北与朝鲜半岛,西至羌区及蒙古草原西部;本文所涉及的北族,最早的是东汉的羌人,最晚的是辽代的女真人,大体而言,时间跨度自2世纪至11世纪;本文所说的前国家,指这些少数民族既不是某一政权的统治民族,也未成为其他政权所属编户齐民的时期。本文的研究主旨是,讨论北族在没有进入国家管理体制时其所通行的社会组织的状况,并尝试对之进行类型的归纳和规律的总结。北族建立本族政权之后的史事与其成为其他政权属民时期的史事,皆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因这一时期的北族社会组织恐怕已经受到国家体制的改造,不再具有原生性和典型性。
一
关于北族前国家社会组织的比较详细的史料,最早见于范晔《后汉书》卷87《西羌传》对尚未建立自己国家的羌人社会组织的记载。东汉羌人最大规模的社会组织,中原史家称之为“种”,其首领称“酋豪”。从理论上讲,“种”由同一始祖的子孙后代组成。由于始祖诸子后裔发展的不均衡性,强大的支系会从原本的“种”中分离出去独立发展,另立自己的首领,此即“强则分种为酋豪”。尽管为同一始祖的后裔,在裂变为不同的“种”之后,彼此间即不再存在特殊关系,各自独立发展,此即“子孙分别,各自为种”。在各个“种”竞争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衰落的、弱小的“种”无法自保,即依附于强大的“种”,成为其依附部落,即“附落”,此即“弱则为人附落”。在“种”之上,不存在稳定的社会组织,此即“不立君臣,无相长一”。故《后汉书·西羌传》称羌人共150种,都是以“种”为统计单位,亦可以证明羌人不存在“种”之上的社会组织。
在经历“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的裂变与聚变之后,“种”逐渐分化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由同一始祖的后裔构成的种,也是原生形态的种,可称单一型种;另一种类型则包涵种和其领导下的“附落”,即由若干个单一型种合并而成,可称复合型种。羌人独立种共89个,“附落”共52个,可见单一型的种占多数,但势力皆较弱,复合型种虽然比较少,但都是强大的种。因复合型种内部包涵不同的“种人”,故也被称为“杂种”。复合型种如果衰落也会成为其他种的“附落”,这种“附落”也称“杂种”。也就是说,“附落”也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个是单一型,史书通称“附落”;一个是复合型,史书也称“杂种”。
可与《后汉书·西羌传》所载羌人社会组织状况相参证的是王沈《魏书》所载乌桓人的社会组织状况。王沈使用的概念与范晔略有差异,王沈笔下的“族类”,内涵等同于范晔笔下的“种”。“族类”或“种”的首领,王沈称“大人”,范晔称“酋豪”。王沈记载的“族类”之下的乌桓社会组织“邑落”,显然相当于范晔所说的羌人的“附落”,而其首领即“小帅”。透过《魏书》、《后汉书》所用概念的差异可以发现,活动于公元二三世纪的羌人和乌桓人的社会组织是极其相似的。
羌人堪称高原、高山河谷游牧民族的代表。自甘陇河湟的羌人至西南夷的夷、羌、氐诸族,最大规模的社会组织都是包涵部落的复合型种,而这些民族的生计类型多与羌人类似,也就是说,高原、高山河谷游牧民族的前国家社会组织通常是“种”、“部落”两级。
乌桓人则是丘陵森林草原游牧民族的代表。由乌桓、鲜卑的情况可以推断,丘陵森林草原游牧民族的前国家社会组织通常也是“种”、“部落”两级。关于正北方典型草原游牧民族的社会组织,《晋书》卷97《匈奴传》记载:“北狄以部落为类,其入居塞者……凡十九种,皆有部落,不相杂错。”亦体现着“种”下为“部落”的结构,则“以部落为类”,只能是以部落构成类的意思。由此可证,北方草原民族前国家社会组织通常也是“种”、“部落”两级。
《晋书》卷3《武帝纪》咸宁三年:“西北杂虏及鲜卑、匈奴、五溪蛮夷、东夷三国前后千余辈,各帅种人部落内附。”证明西北、西南、东北诸族以及典型的游牧民族匈奴、鲜卑各部,最重要的社会组织都是两级:种、部落。种下辖的部落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依附部落,即“附落”;一类是本种的宗族组织,即“种人”,也是种的首领所属的部落,其部人都是种的首领的同宗,因此也称“宗族”、“宗种”。可见,中古北族通行的前国家社会组织是种、部落二级制。
从《晋书·匈奴传》的记载来看,19种内“皆有部落”,说明草原民族最大规模的社会组织是复合型种,这是草原民族与羌人社会组织的最大区别,羌人的种仍以单一型居多。《后汉书·西羌传》反映的是东汉时期羌人的情况,《晋书·匈奴传》反映的是晋代草原民族的情况,时代有早晚之别。另外,《晋书》反映的是匈奴帝国瓦解之后的情况,经历过草原帝国的草原民族显然经历了更多的裂变与聚变。无论是从时代先后还是从其演进过程来看,都可以证明《晋书》所载草原民族的社会组织是《后汉书》所载羌人社会组织的下一发展阶段。也就是说,北方民族规模最大的社会组织种,经历着由单一型向复合型的演进。
如果我们引入文化人类学的概念进行描述,一个单一型种就是一个父系继嗣群,而复合型种则包括若干个父系继嗣群;单一型种尚保有亲属谱系,其成员彼此间认同这种真实的或想象的亲属关系,而复合型种内部的亲属关系已经相当复杂。
二
关于复合型种的进一步演进,我们首先以拓跋鲜卑为例。《魏书》卷113《官氏志》记:“至献帝时,七分国人,使诸兄弟各摄领之,乃分其氏。自后兼并他国,各有本部,部中别族,为内姓焉。”献帝的改革内容主要是三项。其一,自统本种,命自己的兄弟分别统率7个附落。估计献帝改革以前,拓跋鲜卑应是保留附落原有的统治结构,只是满足于征收贡赋,而此次改革却是将附落首领皆更换为拓跋氏的亲属。其二,给予附落和拓跋本种同等的地位,应该还构建了一种想象的亲属关系,认为本种与附落皆出自同一始祖,故规定“与帝室为十姓,百世不通婚”。通过这种改革将原来的本种和附落整合为一体。其三,承认7个原附落与本种共为8部的现状,但想象为已经裂变为8个单一型种,此后8个部皆可以拥有自己的附落,即“兼并他国,各有本部,部中别族”,所谓“本部”,即8个部的本种;所谓“部中别族”,即依附于8个部的附落。改革之后的拓跋鲜卑社会组织演变为三级,最大规模的社会组织是八氏十姓组成的集团,下面才是原有的两级社会组织——种、部落。
献帝的改革与种的自然裂变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自然裂变之后的各种,虽出于同一个母体,但裂变后彼此间不存在隶属关系,原母体瓦解,新生成的各种独立发展,在这种状况下,社会组织始终维持两级制;献帝改革后的拓跋鲜卑不仅保留了原母体,甚至是强化了拓跋宗族对各种的统辖关系,母体内部的凝聚力得到加强,其社会组织演进为三级。经历此改革之后,拓跋鲜卑成为种之上的社会组织,这是人为构建的种之上的社会组织,已经开始挣脱血缘关系的束缚,向早期国家演进了。
突厥是与拓跋鲜卑类似的另一个例证。《旧唐书》卷104《哥舒翰传》有记载:“哥舒翰,突骑施首领哥舒部落之裔也。蕃人多以部落称姓,因以为氏。”北方民族本无姓,受汉族姓氏制度影响,才以部落号为姓,因为只有部落才是北方民族的宗族组织,是血缘组织,其上的种以及类似于拓跋鲜卑在种之上构建起来的另一级社会组织,都已经不是血缘组织了。“北狄以部落为类”也是对此现象的描述。可以说,北方民族一姓就是一个部落,就是一个单系继嗣群、一个宗族,这是北方民族最基本的社会组织。
拓跋鲜卑和突厥代表着北族前国家社会组织演进的一种模式,通过加强对附落的控制,不是通过裂变而是通过聚变的形式,人为制造出一个新的种,原来的本种与附落则被改造为新的种的内部支系,这些支系又可以拥有自己的附落,由此形成新的种-支系(原来的本种和附落)-附落(新接纳的附落)三级社会组织。
复合型种的演进,另一种模式是诸种通过联合的方式生成更高级的社会组织,兹举两例。
鲜卑檀石槐,“为庭於高柳北三百馀里弹汗山啜仇水上,东西部大人皆归焉”,建立起鲜卑诸种联盟。此后的轲比能“本小种鲜卑,以勇健,断法平端,不贪财物,众推以为大人”,出身于一个小种的轲比能,通过与檀石槐类似的途径,建立起鲜卑诸种的联盟。学界传统称檀石槐、轲比能建立的联盟为部落联盟,揆诸史籍,恐怕是不准确的。
回纥的出现,《新唐书》卷217上《回鹘传上》:“韦纥乃并仆骨、同罗、拔野古叛去,自为俟斤,称回纥。”韦纥、仆骨、同罗、拔野古不仅见于回鹘15种,亦见于《隋书》卷84《铁勒传》所载铁勒诸种,即铁勒的几个种联合反抗突厥处罗可汗,形成一个种之上的集团,推举了自己的可汗,并确定集团名号为回纥,由此发展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
综上,复合型种的演进主要有两种模式,如拓跋鲜卑、突厥,可称为衍生型;如檀石槐、轲比能、回纥,可称为联合型,其社会组织最终皆由两级发展为三级,至此已走到国家形成的前夜了。复合型种衍生发展的典型例子还可以举出契丹、女真。
女真人最大的特点是一种一姓,其下的部落皆同姓,因此才要对种内各部作进一步区分。《金史·完颜勖传》记载“凡部族,既曰某部,复曰某水之某,又曰某乡某村,以别识之”,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金史·宗室表》:“金人初起完颜十二部,其后皆以部为氏,史臣记录有称宗室者,有称完颜者。称完颜者亦有二焉,有同姓完颜,盖疏族,若石土门、迪古乃是也;有异姓完颜,盖部人,若欢都是也。”“宗室”、“同姓”即“种人”,“异姓”即附落、“部落”。
通常情况下,种之下的部落都是血缘组织。也有无亲属关系者联合为一部的例子。如柔然。但这种情况是极为罕见的。一般来说,部落仅有裂变、没有聚变。单一型种实际就是一个独立的部落,就其内部结构而言,二者并无本质的不同,因此,单一型种也是仅有裂变、没有聚变。单一型种或者复合型种中的宗种部落,导致裂变的主要原因是权力继承,以及对资源的再分配,特别是对牧场的再分配。在资源充分的情况下,种与部落的裂变总是倾向于达到最大限度。
种的裂变的最大限度也受制于人口基数。大体上说,单一型种的平均人口,东北诸族为2000户、北方草原诸族为3000户,西南民族的数字介于二者之间,最少的是羌人。由此来看,弁韩、辰韩“大国四五千家,小国六七百家”,可能正是单一型人口的上下限。换言之,少于六七百家的单一型种很难生存,这是下限;达到四五千家的单一型种则面临裂变,或是向三级社会组织演进,这是上限。
由于是“弱则为人附落”,复合型种内部每个“附落”的人口数字可能是远远低于本种部落的。由契丹人的情况推测,本种与“附落”之间的人口比例,大体在1∶1至1∶2之间,可能这是本种得以控制附落的正常比例。超出这种比例的话,要么意味着复合型种的裂变,要么意味着复合型种演进为三级组织。
结语
中古北族步入国家形态以前,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是宗族组织,也就是父系继嗣群。宗族首领往往习惯由同一家族产生,但却并不存在明确的继承原则,首领威权不足即导致宗族的裂变。在自然资源相对于人口显得过剩的地区,宗族组织倾向于最大限度的裂变,这也是更好地利用自然资源的最佳方式。当人口相对于自然资源显得过剩时,宗族组织之间自然因对资源的竞争而形成对抗,这种外在的压力迫使宗族组织扩大规模、彼此吞并。弱小宗族无法保持独立,只有被迫或自愿地依附某一强大的宗族才能生存下去,这就是《汉书》卷87《西羌传》说的“弱则为人附落”。强大的宗族组织规模越来越大,内部构成也越来越复杂。简单地说,是以强大宗族为核心,控制一些弱小宗族,形成一个宗族群,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复合型种。史书称这样的强大宗族为“宗种”、“种人”、“宗族”等,称其控制下的宗族为“附落”、“部落”,当然,这两种宗族组织史书中也皆称之为“部落”。这种宗族群成为凌驾于宗族之上的新的社会组织,并逐渐成为中古北族通行的社会组织。
中古北族除羌人以外,其他民族最大规模的社会组织可能皆以宗族群为主。换言之,北族前国家时代最普遍的社会组织可能是两级制,即宗族群下辖宗族的模式。
控制力和威权不足导致的宗族“强则分种为酋豪”的裂变,与资源和人口压力导致的“弱则为人附落”的聚变,成为中古北族社会组织变迁的主旋律。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埃文思·普里查德对非洲努尔人的研究表明,努尔人宗族组织的演变是以裂变为主,不存在明显的聚变趋势,这可能是努尔人始终停留在前国家社会的最重要原因。中古北族则存在比较明显的聚变趋势,这是其向国家演进的内在动力。
宗族群的进一步发展至少可以分为衍生型、联合型两种类型。宗族群的衍生型发展,第一步是主导宗族群的宗族,即“宗种”,以自己首领的兄弟子侄取代依附宗族即“附落”的原首领,将控制变为统治。为完成这一转变,一方面要利用宗族的传统,将本不同源的“宗种”和各“附落”想象为出自同源的裂变,另一方面则要发明起源神话,以证实这种想象的裂变,以此为依据,打造出包涵若干“宗种”的宗族群。这种新型的宗族群我们可以称之为宗种群。第二步,宗种群下的每一“宗种”都通过吸纳或征服拥有自己的“附落”。至此,社会组织发展为三级制,宗种群(种)-宗族群(支系)-宗族(附落)。
宗族群的联合型发展,往往是几个宗族自愿形成联盟,并由最强大的宗族中推举产生联盟的首领,由此发展出社会组织的三级制,联盟-宗族群-宗族。衍生型的典型个案是拓跋鲜卑,联合型的典型个案是契丹八部。
不论是衍生型三级社会组织还是联合型三级社会组织,经历进一步的改造都可以形成早期国家,但其也皆是不稳定的社会组织,首领威权不足时即宣告瓦解。最典型的个案是鲜卑檀石槐建立的大联盟,王沈《魏书》有记载:“檀石槐年四十五死,子和连代立。和连材力不及父,而贪淫,断法不平,众叛者半。灵帝末年数为寇钞,攻北地,北地庶人善弩射者射中和连,和连即死。其子骞曼小,兄子魁头代立。魁头既立后,骞曼长大,与魁头争国,众遂离散。”三级社会组织要么向早期国家演进,要么退回到二级社会组织,这种不稳定性导致其具有明显的过渡时期的特点,是由前国家形态向早期国家演进的过渡时期。由此看来,草原民族前国家形态下最典型的社会组织是两级制,宗族群-宗族。明白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史料中一些特殊概念的内涵可能是研究北族社会史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