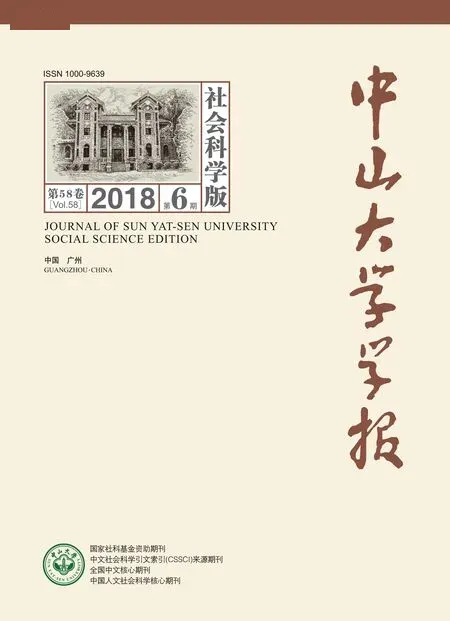帝国以前的罗马城*
——从聚落到都城的考古学观察
周 繁 文
罗马地处亚平宁半岛中部的第勒尼安海岸、阿布鲁佐亚平宁山脉和台伯河之间,分布在帕拉蒂诺山、坎匹多伊奥山、奎里那勒山、维米那勒山、切利奥山、埃文蒂诺山和俄斯奎里诺山之间,建城后历任王政时代、共和国时代、早期罗马帝国时代的都城。卡匹托利尼山和帕拉蒂诺山一带自青铜时代至今都是城市的中心区域。罗马的城市模式在环地中海城市体系中独具特色,尤其是它的延续性之长、重叠性之强,在同时代的欧亚大陆极其少见。本文从考古学视角观察罗马从聚落到都城的变迁过程,进而讨论它的空间演化形式和动因,分析罗马城在形成和扩散中的空间结构形成、重组及变革模式,并尝试概括罗马城历史空间与城市界线的关系,以及最终成为地中海中心城市的复杂机制。
一、石器时代的意大利中部
(一)考古学分期和年代序列
旧石器时代早期,今罗马西北的托利马皮埃特拉便有古人类活动迹象。旧石器时代中期,今罗马东南的奇尔切奥山和阿尼奥河流域都是尼安德特人的活动范围,后一地点发现所谓的萨科帕斯托勒人①M.Cary and H.H.Scullard, A History of Rome: Down to the Reign of Constantine, London and Bastingstoke: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The Third Edition, 1975, p.7.。
公元前6000年左右,拉齐奥地区进入新石器时代。此时,贝壳戳印纹陶器文化(Impressed Wares,前5600—前5200)流行于环第勒尼安海岸,萨索文化(Sasso,前5500—前4400)流行于意大利中部西海岸,这两种文化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拉齐奥地区并存。
新石器中期,约公元前5000—前4300年,今托斯卡纳到拉齐奥一带近海岸处兴起棕彩陶器文化(Brown Painted-Incised)。大致与此同时,意大利中部和南部都被赛拉达尔托文化(Serra D’Alto,前4700—前4000)控制。公元前4500年,意大利中北部还出现了利波里文化。
新石器晚期,利波里文化的晚期类型在拉齐奥地区一直延续至公元前3000年。大致同时期的狄安娜—贝亚维斯特文化(Diana-Bellavista)则广泛存在于意大利中部和南部[注]Caroline Malone, The Italian Neolithic: A Synthesisi of Research, 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 2003, Vol.17, No.32, pp.242-243,p.258,pp.258-261.。
总体来说,整个新石器时代,流行于不同地区的几支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影响着拉齐奥地区,时间和空间上互有交错(见图1)。

图1 亚平宁半岛及周边岛屿新石器时代主要考古学文化分布示意图
(二)居住形态和空间布局
新石器早期,拉齐奥地区的主要栖居形态是洞穴和露天,视地貌类型的不同而定。前者主要分布在海岸地区[注]John Robb, The Early Medditeranea Vill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76.,如维纳斯山洞穴(图2:5),自公元前6000年就开始使用,发现有贝壳戳印纹陶器和生活痕迹[注]F. Delpino and M.A.Fugazzola Delpino, La “facie” di Monte Venere nell'ambito della cultura del Sasso, Atti della XXVI Riunione Scientifica, 1987, pp.671-680.。内陆地区的居址则是近河或环湖的房屋建筑,遗迹包括疑似棚屋(hut)或小屋(capanne)的基址、沟渠、柱洞、灰坑、生活遗迹、人工制品以及垃圾堆④Caroline Malone, The Italian Neolithic: A Synthesisi of Research, 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 2003, Vol.17, No.32, pp.242-243,p.258,pp.258-261.。这一时期的相关发现不多,只见到与家庭生活相关的遗迹,居址间的关系也不十分明确。
新石器中期,拉齐奥的材料较少,因此扩大到意大利中部来观察,仍延续着前一阶段的两种栖居形态⑤Caroline Malone, The Italian Neolithic: A Synthesisi of Research, 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 2003, Vol.17, No.32, pp.242-243,p.258,pp.258-261.。
洞穴遗址中出现了空间的功能区分,部分遗址明显不属于日常居住的性质,而与信仰行为或经济活动相关。亚平宁山脉的高地洞穴遗址如皮齐奥尼洞、阿布鲁佐的博洛尼亚(图2:27)[注]A.M.Radmilli et al., Recenti scavi nella Grotta dei Piccioni di Bolognano (PS) e riesame dei scheletrici umani proenienti dai circoli, Atti della Società Toscana di Scienze Naturali, 1978, Vol.85, pp.175-198.以及托斯卡纳的切托纳山,洞内堆积似与信仰活动相关。意大利中西部的地下洞穴,如贝拉洞(图2:12)[注]Guerreschi et al., Grotta Bella(TR), Una sequenze stratigrafica dal neolitico inferiore all’età imperiale, I livelli presitorici, Bullettino di Paletnologia, 1992, 83(1), pp.143-227.、翁布里亚的皮亚纳洞(图2:7)[注]L.Passeri, Ritrovamenti preistorici nei Pozzi della Piana(Umbria), Rivista di Scienze Preistoriche, 1970, Vol.25, pp.225-251.、拉塔伊亚洞(图2:8)[注]R.D.Whitehouse, Underground Religion: Cults and Culture in Prehistoric Italy, Accordia Specialist studies on Italy, 1992, Vol.1, pp.27-28.、撒尔特亚诺(图2:9)、托斯卡纳阿夏诺的拉·洛米塔[注]R.Peroni, La Romita di Asciano, Riparo sottoroccia utilizzato dalla età neolitica alla barbarica, Bulletino di Paletnologia Italiana, 1962-63, Vol.72, pp.251-442.和拉齐奥的帕特里兹—萨索·弗巴拉洞(图2:1)等,发现有畜牧和狩猎活动的遗存以及与信仰相关的堆积。
近河和环湖仍然是内陆栖居的选址原则,出土遗迹仍多与生活有关。近河型聚落包括阿布鲁佐的卡蒂尼亚诺(图2:24)和莫利塞的玛乌罗山(图2:33)[注]G.W.Barker, A Mediterranean Valley: Landscape Archaeology and Annales History in the Biferno Valley, in G. Barker ed., The Biferno Valley Survey: The Archaeological and Geomorphological Record, Vol.2,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5.。卡蒂尼亚诺发现有五个半圆形建筑基址,环绕着石壁炉、窖穴、灶,包括带半圆间的长方形棚屋,约5×10平方米[注]Grifoni Cremonesi and C.Tozzi, Il neolitico dell’Abruzzo, Atti della XXVI Riunione Scientifica, 1987, pp.239-252.。环湖型聚落包括萨包迪亚湖区的赛特维拉·迪·圭多尼亚(图2:29)、拉·波特(图2:31)[注]A.P.Anzidei, Il processo di Neolizzazione nel Lazio centro-Meridionale, Atti della XXVI Riunione Scientifica, 1987, pp.173-185.。布拉齐阿诺湖区的拉·玛摩尔塔(图2:4)发现了湖泥中保存着的木桩和连接结构[注]M.A.Fuggazzola Delpino et al., La Marmotta (Anguillara Sabazia, Roma), Scavi 1979, Unabitato perilacustre di età neolitica, Bullettino di Paletnologia Italiana, 1993, 48(new series), pp.181-342.。
这个时期的建筑既有土木结构,也有土石混合结构。托斯卡纳的皮恩扎(图2:10)遗址发现有木骨泥墙(wattle and daub)结构,以及用粘土粘结的圆形卵石堆[注]G.Calvi Rezia, Pienza (Siena): ipotesi di una fascia cronologica parallela alla fase culturale e ceramiche graffite, Preistoria Alpina, 1977, Vol.13, pp.216-221; G.Calvi Rezia, La ceramica impressa di Pienza (Toscana) e quella di Basi in Corsica, Rivista Scienze Preistoriche, 1980, Vol.35, pp.323-333.。托尔·维加塔遗址则为粘土和干砌石墙(未用灰泥)建筑[注]R.Grifoni Cremonesi, Il Neolitico nell’Italia centrale e in Sardinia, in A.Guidi and M.Piperno, eds., Italia Preistorica, Bari:Laterza, 1992, p. 311.。

图2 意大利中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示意图
新石器晚期,意大利中部的东海岸出现环壕聚落。关于壕沟的作用,存在象征界限、防御设施、圈卫牧群、集水、排水、停尸处等多种解释[注]John Robb, The Early Medditeranea Village, p.93-94.。
阿布鲁佐的利波里遗址(图2:22)地处河流阶地,壕沟的围合面积约300×120平方米,壕沟约宽7米、深5米。聚落内部区分出生活空间和埋葬空间,共发现50余座半地穴式棚屋,3—5座为一组,有居室葬的现象。其他的利波里文化聚落,如圣安吉罗城遗址(图2:19)也发现有环壕,佛萨切西亚和塞尔瓦的圣玛利亚(图2:16)聚落内的房址规模存在差异。托尔托雷托的匹亚纳齐奥(图2:17)有超过80个成排分布的半地穴式棚屋房址,直径约1.2—5米不等。帕特尔诺(图2:23)、蒂涅罗山和波波利的圣卡里斯托遗址(图2:25)都发现有壁炉遗迹和火烧面,其中圣卡里斯托斯遗址的环壕形态较特殊,平面为长方形。翁布里亚的诺奇亚(图2:13)发现有棚屋基址和家庭生活垃圾。少数遗址中出现了专门的手工业区域,如赛迪丰蒂的一些棚屋与粘土开采有关,托尔·斯帕卡塔(图2:30)遗址发现有与黑曜石制作有关的踩踏面[注]Caroline Malone, The Italian Neolithic: A Synthesisi of Research, 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 2003, Vol.17, No.32, p.261.。
如果壕沟在当时代表着界线,那么新石器晚期的聚落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单个聚落的规模更大,空间的功能分区更明显,生活、埋葬和手工业区域,且在同一聚落内存在房址规模间的差异。
二、青铜时代的罗马:聚落成型
(一)考古学分期和年代序列
约公元前3000—前2300年为“铜石并用时代”或“红铜时代”。约公元前2300年左右,亚平宁半岛逐渐进入青铜时代,大致分为三期:早期(前2300—前1700)、中期(前1700—前1325/1300)、晚期(前1325/1300—前950/925)[注]Francesca Fulminante, The Urbanisation of Rome and Latium Vetus: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Archaic Er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26-27,pp.67-69,pp.69-70.。
拉齐奥地区的相关发现较少,未能构建起系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仅知从青铜时代中期起,意大利中北部的考古学文化持续南下对这里产生重要的影响,先是亚平宁文化,而后是“先维拉诺瓦文化”。
约公元前15世纪,半岛从北边的博洛尼亚到南边的阿普利亚都被亚平宁文化(Apennine Culture)所控制。这支考古学文化以小型聚落、土葬墓、装饰性陶器为特色[注]T.J.Cornell, The Beginnings of Rome: Italy and Rome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unic War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48.。亚平宁文化晚期(公元前13—前12世纪),爱琴海迈锡尼文化的陶器到达意大利中部[注]Gary Forsythe, A Critical History of Early Rome: From Prehistory to the First Punic War,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21.。
公元前1150—前1000年,在原亚平宁文化的范围内出现了骨灰瓮火葬墓地,也出现了新的陶器形制和装饰风格,以及小提琴弓形扣针、单拱形扣针、曲背刀、直背刮刀、曲背刮刀等新的青铜器类型,均属于“先维拉诺瓦文化”(Proto-Villanovan Culture)。关于这支文化的来源,学界尚存在亚平宁文化和意大利北部波河河谷的灰泥土文化(Terramare Culture)两说。至于其去向,则普遍认为与铁器时代的维拉诺瓦文化有关[注]R.Ross Holloway, 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Rome and Latium, pp.14-17; Gary Forsythe, A Critical History of Early Rome: From Prehistory to the First Punic War, pp.12-25.。
(二)聚落形态和空间布局
青铜时代早期在罗马的圣奥莫波诺一带可能有一个低地遗址。但稳定的聚落应该是从青铜时代中期开始。阿尔贝托·卡泽拉认为此时罗马的聚落应当只局限在卡匹托利姆(卡匹托利尼峰南部),规模不超过1公顷,人口约为200人。但安德烈·卡兰蒂尼认为由于罗马是重叠型城市,前代遗址被后代破坏的现象很常见,所以很有可能此时的聚落已经包括整座卡匹托利尼峰,占地约7—8公顷⑥Francesca Fulminante, The Urbanisation of Rome and Latium Vetus: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Archaic Er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26-27,pp.67-69,pp.69-70.。青铜时代晚期,原先卡匹托利尼峰的聚落可能扩展到了帕拉蒂诺山⑦Francesca Fulminante, The Urbanisation of Rome and Latium Vetus: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Archaic Er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26-27,pp.67-69,pp.69-70.,也有学者认为应该也包括北边的山谷(即广场谷)[注]A.P.Anzidei etc., Roma e il Lazio dall’età della pietra alla formazione della città, Roma: Quasar,1985; R.Peroni, Introduzione alla protostoria italiana, Roma-Bari: Laterza,1994.。到公元前12—前10世纪,卡匹托利尼峰的聚落已占地约14公顷,帕拉蒂诺山的聚落可能约占23公顷。卡兰蒂尼认为此时的奎里纳勒山也有人居住[注]Francesca Fulminante, The Urbanisation of Rome and Latium Vetus: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Archaic Era, pp.70-72.。
整个青铜时代,以卡匹托利尼峰为中心的聚落逐步壮大,帕拉蒂诺山及其北边的山谷也先后被纳入聚落内。但由于考古学证据的匮乏[注]近代的工程建设和法西斯的发掘计划都忽视前罗马时期的遗址,造成大量考古学材料的丢失。,对这一时期聚落的具体形态和空间布局尚不甚清楚。
三、铁器时代早期的罗马:聚落扩大与融合
(一)考古学分期和年代序列
公元前10世纪,在先维拉诺瓦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维拉诺瓦文化,分布在意大利的北部和中部,包括两个主要类型:北方类型,在博洛尼亚周围;南方类型,在托斯卡纳和北拉丁地区[注]M.Cary and H.H.Scullard, A History of Rome: Down to the Reign of Constantine, pp.7-13.。
公元前9世纪,拉丁和阿勒巴诺山区分布着拉齐奥文化[注]Ⅰ、Ⅱ期才是铁器时代,Ⅲ期以后已属于东方化时代或称王政时代。。在这支考古学文化的分期问题上,学界存在较大争议,主要包括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乔万尼·平扎—J.C.迈瑞尔的分期体系,也是最主流的观点。平扎以广场谷和俄斯奎利诺山墓葬群为基础,综合墓葬形制、随葬陶器和铜扣针的演变,以及希腊式器物及仿制品的出现与否,将拉齐奥文化分为早晚两期,其下又再细分[注]Giovanni Pinza, Le civiltà primitive del Lazio, Bullettino della Commissione Archeologica Comunale di Roma, 1898,vol.26, p.157; Gary Forsythe, A Critical History of Early Rome: From Prehistory to the First Punic War, p.37.。迈瑞尔基本延续了平扎的分期,仅将Ⅲ期以公元前740年为界细分,并对Ⅳ期各段的年代界限略有调整,对不同期段的考古学文化特征的认识也略有不同[注]J.C. Meyer, Pre-Republican Rome: An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and Chronological Relations 1000-500 B.C., in: Analecta Romana Instituti Danici, Supplementum XI, 1983, pp.9-60.。

表1 拉齐奥文化的分期体系
第二种观点是赫尔曼·穆勒—卡培和雷纳托·佩罗尼的分期体系[注]R.Ross Holloway, 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Rome and Latium,pp.40-42,pp.47-50.。他们以葬具和铜扣针为标准器,将广场和俄斯奎利诺山墓葬群分为四期。但安娜·玛利亚·比埃蒂·瑟斯提埃利认为地位、性别、年龄等因素都综合影响着随葬品,因此穆勒—卡培等学者所谓的不同期别实际上可能是同一时期的不同人群。
第三种观点是埃纳·耶尔斯塔德的分期体系。耶尔斯塔德将随葬的希腊式陶器作为标准,根据其形制演变将两处墓葬群分成了三期⑧R.Ross Holloway, 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Rome and Latium,pp.40-42,pp.47-50.。他的分期虽然存在较多争议,采信的人也并不多,却不容忽略,尤其是他注意到拉丁地区与意大利南部的希腊殖民地所出的希腊式陶器在变化轨迹上有同步的趋势,似说明希腊文化对拉丁地区的影响变得明显。
(二)聚落形态和空间布局
铁器时代早期的意大利中部,一些小型山顶村落开始融合形成大型的中心聚落,在埃特鲁利亚南部尤其表现明显。拉丁地区虽未发现如此清晰的演进链条,似乎也有类似的过程,在拉齐奥文化时期,这里的聚落明显增多、规模增大,从Ⅱ期开始,墓葬和随葬品的数量也显著增加[注]Christopher Smith, Early and Archaic Rome, in Jon Coulston and Hazel Dodge, ed., Ancient Rome: The Archaeology of the Eternal C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18-19.。约在拉齐奥文化ⅡB段,之前被分散的独立村落占据的遗址上出现了集中型聚落,但具体布局不清,只知道有大量集中的棚屋,并无证据表明有空间规划或正式的组织[注]T.J.Cornell, The Beginnings of Rome: Italy and Rome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unic Wars, p.92-97,p.50,p.48,pp.60-63.。但同时期的阿勒巴诺山区依然保持小型的分散聚落,并未观察到类似的人口增长趋势③T.J.Cornell, The Beginnings of Rome: Italy and Rome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unic Wars, p.92-97,p.50,p.48,pp.60-63.。(见图3)
至于罗马所在地,在拉齐奥文化Ⅰ期,罗马广场和俄斯奎利诺山皆发现有以火葬墓为主的墓葬群④T.J.Cornell, The Beginnings of Rome: Italy and Rome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unic Wars, p.92-97,p.50,p.48,pp.60-63.。到拉齐奥文化IIA期,康奈尔等学者认为此时罗马主要的居住区在帕拉蒂诺山,面积不到20公顷[注]Pierre Gros e Mario Torelli, Storia dell’urbanistica: il mondo romano, Roma-Bari: Laterza, 1998; T.J.Cornell, La Prima Roma, in Andrea Giardina, a cura di, Roma Antica, Bari: Editori Laterza, 2000.,罗马广场的墓地可能属于帕拉蒂诺山聚落。弗兰切丝卡·弗勒米南特则认为仍是在卡匹托利尼峰和帕拉蒂诺山,只是朝奎里纳勒山和俄斯奎利诺山的方向有所扩展。拉齐奥文化IIB期,两个主要的聚落区向东北方向扩展。卡匹托利尼峰—奎里纳勒峰(奎里纳勒山东北部)聚落可能有

图3 罗马时代的意大利语族分布示意图(约前450—前400年)(据T.J.Cornell, The Beginnings of Rome: Italy and Rome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unic Wars, Map2, p.42重制)
54公顷。帕拉蒂诺山聚落可能有37公顷,假如包括俄斯奎利诺山墓葬群的话可能达到60公顷[注]Francesca Fulminante, The Urbanisation of Rome and Latium Vetus: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Archaic Era, pp.72-77.。但学界对此仍未达成共识。
这一时期的罗马聚落大体呈现高地居住、低地埋葬的特征,结合地貌特征对空间进行了功能区分。目前聚落的整体形态和具体布局仍不清晰,但从规模上看,能观察到发生了明显的扩张,这也可能意味着若干分散聚落的融合。
四、王政时代的罗马:城市初创期
(一)城市起源理论
至少在奥古斯都时代就已流传着公元前753年罗慕路斯建城的传说⑦T.J.Cornell, The Beginnings of Rome: Italy and Rome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unic Wars, p.92-97,p.50,p.48,pp.60-63.。不过各种文献中对建城的具体年代存在争议:公元前3世纪的埃拉托斯特内记载为公元前1184年[注]F.Jacoby, Die Fragmente der Griechischen Historiker, Leiden: Brill, 2004: p.241, F.1, F.45; p.566,F.60.,西西里历史学家提密欧认为当在公元前814年②F.Jacoby, Die Fragmente der Griechischen Historiker, Leiden: Brill, 2004: p.241, F.1, F.45; p.566,F.60.,罗马历史学家如法比奥·皮托雷、秦齐奥·阿里门托和卡托内·伊勒·钱索勒等人都认为是公元前8世纪。
但从考古学的角度,建城的起始时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们对“建城”行为的定义。总结以往的研究,关于罗马城起源的理论主要有如下三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城市”是革新性的突变,与短时性的营造行为有关,将修建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设施如广场或城墙视为建城的标志。耶尔斯塔德认为罗马广场开始铺设地板即是“城市化”的象征,也即公元前575年左右[注]Einar Gjerstad, Early Rome, 6 vols, Lund,1953-1963.。但他对绝对年代的认识与最新研究成果之间存在偏差,按照今天的分期,假如用“广场开始铺设地板”作为标志,那么年代应当在公元前7世纪。而卡兰蒂尼则将建城的行为指向帕拉蒂诺山东北坡发现的墙址,他认为这道建成于公元前8世纪后半期的设施,可以解释为具有防御功能,也可解释为出于自觉性政治行为而营造的空间分隔界限[注]Andrea Carandini, Le mura del Palatino:nuova fonte sulla Roma di età regia, Bollettino di archeologia,1992,16-18, pp.1-18.。这背后隐含的是界限内外空间有别的共识,以及调动资源建成这道围墙的权力生成。
第二种观点以穆勒—卡培为代表,更倾向于用渐进的发展过程取代“城市革命”的理论,也就是说并不存在短时间的、突然的建城行为,罗马城应当是逐渐从帕拉蒂诺山的原始居住中心发展而来的,在铁器时代扩展到其他山丘。
第三种观点则强调“城邦”而非“城市”的概念,将对整体空间的规划以及建筑技术的发展视为其形成的标志。蒂姆·康奈尔从罗马城的考古学材料着手,指出这个过程应当发生在公元前625年前后十年[注]T.J.Cornell, La Prima Roma, in Andrea Giardina, a cura di, Roma Antica, p.100.。
不同的理论模式将会对考古材料产生不同的解释。本文赞同蒂姆·康奈尔的界定标准,假如将“建城”视为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那么它应当对应着社会组织和制度的深层次变革,而整体规划的实施,显然代表着广泛空间内的唯一权力中心。但是,就作为建筑群体组合的“城市”而言,罗马所在地自史前以来就有人类连续居住,并非全新修建的城市,因此旧的聚落并不能够即时被完全取代。也就是说,罗马城的建成应当是“二元结构性”的:权力空间和公共空间的短时性革新,私人空间的渐进式发展。
(二)考古学角度的观察
1、王政时代早期
相当于东方化时代早期(拉齐奥文化ⅢB期到ⅣB期早段),时间大致从公元前8世纪到前7世纪末。帕拉蒂诺山上出现第一道墙,奎里纳勒山、维米那勒山、俄斯奎利诺山的墓地仍继续使用,但切利奥山被占用的迹象不明显,推测此时罗马扩张到了275公顷,如果不包括切利奥山则是210公顷[注]Francesca Fulminante, The Urbanisation of Rome and Latium Vetus: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Archaic Era, pp.80-82.。
公元前7世纪中期,位于后来罗马广场神圣大道和图密善骑马雕塑一带的棚屋群被毁,形成了粗糙的踩踏面,这就是最早的广场露天区。大约公元前625年,广场谷的沼泽被排干,修建了大型的下水道体系[注]Frontinus, De Aqui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1925, 111; Ashby, The Acqueducts of Rome, London, 1935, p.46; Strabo, The Geography, 5.8,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liny, the Elder, Naturalis Historia, 36.10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va Margareta Steinby, a cura di, Lexicon Topographicum Urbis Romae(后文缩写为LTUR), Vol.Ⅰ, Roma: Quasar, 1993-2008, pp.288-290;,填充土石并铺设地板,周围逐渐集中了维斯塔神庙、议会等建筑[注]Einar Gjerstad, Early Rome, Vol.III, pp.217-223; F.Coarelli, Il Foro Romano, Vol.Ⅰ, Roma: Quaser, 1983, pp.119-130, 161-199; Gary Forsythe, A Critical History of Early Rome: From Prehistory to the First Punic War, pp.87-88.。大致同时,出现了石结构、陶瓦屋顶的房屋。帕拉蒂诺山类似的建筑年代为前6世纪早期[注]T.J.Cornell, The Beginnings of Rome: Italy and Rome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unic Wars, pp.92-97.。
公元前7世纪后半期,帕拉蒂诺山东北部的城墙被毁,局部被墓葬打破(可能是人牲),似乎与城墙废弃的仪式有关。约前625—前600年,第二道新墙建于旧墙之上。弗尔米南特认为,帕拉蒂诺山城墙的象征意义更甚于实际功能。卡兰蒂尼认为帕拉蒂诺山的土墙与罗慕路斯所建之城有关。帕拉蒂诺山东北角发现了十字交叉的道路(公元前8世纪末到前7世纪初)以及两座东方化时代的建筑(沿用到帝国早期,其中一座是后来的维特勒元老院)[注]Francesca Fulminante, The Urbanisation of Rome and Latium Vetus: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Archaic Era, pp.83-95,p.96,pp.80-82,pp.83-95.。
这些建筑活动有四个明显的特征:一是以广场为中心的政治-宗教建筑群、以坎匹多伊奥山为中心的宗教建筑群、以帕拉蒂诺山为中心的政治建筑群、帕拉蒂诺山西南山谷的公共活动建筑群、台伯河东岸的商业建筑群成型,在较为广阔的区域内结合地形对空间进行了功能的整合和划分。二是广场作为最具象征意义的区域,同时兼具世俗—神圣双重功能。三是具有政治、宗教和象征意义的区域均是“近尊”,即是毗邻离当时权力中心者的活动区域。在空间位置上,将城市的中心等同于权力的中心。四是建筑类型的转变。自公元前7世纪中期开始,土木结构的棚屋逐渐被木梁、陶瓦的砖石房屋取代。建筑类型和技术的转变很可能受到来自腓尼基和希腊的影响[注]Gary Forsythe, A Critical History of Early Rome: From Prehistory to the First Punic War, p.86、p.91,p.92,p.88.。
这个过程中,城市中心区成型,公共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在一定空间内出现了整体规划的迹象,表明存在着这个空间具有主导权的统治阶层,以及认同这种权力的共同体④Gary Forsythe, A Critical History of Early Rome: From Prehistory to the First Punic War, p.86、p.91,p.92,p.88.。
2、王政时代晚期
相当于东方化时代晚期(拉齐奥文化IVB期晚段)到古风时代,即前7世纪末到前6世纪末⑤Francesca Fulminante, The Urbanisation of Rome and Latium Vetus: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Archaic Era, pp.83-95,p.96,pp.80-82,pp.83-95.。切利奥山被占据,罗马的面积扩展到了约310—320公顷(不含埃文蒂诺山)⑥Francesca Fulminante, The Urbanisation of Rome and Latium Vetus: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Archaic Era, pp.83-95,p.96,pp.80-82,pp.83-95.。
这个时期的建筑活动主要包括:桥梁、码头等基础设施的修建;广场上修建了王宫建筑群、维斯塔中庭⑦Gary Forsythe, A Critical History of Early Rome: From Prehistory to the First Punic War, p.86、p.91,p.92,p.88.;卡匹托利尼山成为天神朱庇特神庙(即至高无上朱庇特神庙)等主要宗教建筑的所在[注]Charles Gates, Ancient Cities: The Archaeology of Urban Lif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d Egypt, Greece, and Ro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second edition, 2011, pp.329-331.;帕拉蒂诺山西南的山谷被辟为赛马等竞技活动的场所,商业活动逐渐集中在台伯河东岸的牛广场和油广场;公元前6世纪中期以后,帕拉蒂诺山修建了第三道墙,在约前530年部分并入私人住宅⑨Francesca Fulminante, The Urbanisation of Rome and Latium Vetus: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Archaic Era, pp.83-95,p.96,pp.80-82,pp.83-95.;公元前6世纪,塞尔维奥·图里奥在防守薄弱的罗马东北部平地修建城墙,并与其他山丘原有的防御设施[注]公元前6世纪的城墙修建之前的防御工事,遗迹在今阿拉克埃利的圣玛利亚教堂和祖国祭坛。相连接,即最早的塞维鲁城墙[注]即塞尔维奥·图里奥划分的四区,包括苏布拉纳、俄斯奎里纳、科里纳和帕拉蒂纳。。
五、共和国时期的罗马:变革与定型
公元前509年,共和国诞生[注]宫秀华:《罗马:从共和走向帝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15页。。与新的政治体制相适应,王政时代的政治中心区几乎完全重建,王宫建筑群被改造成包括维斯塔神庙、家神与宅神神庙、玛尔斯与俄普斯圣所、神圣王室(即后来的公共别墅)在内的公共祭祀中心[注]Filippo Coarelli, Il Foro Romano, pp.56-78.。罗马广场成为公共政治、经济和宗教中心[注]E.Gjerstad, Legends and Facts of Early Roman History, Lund,1962, p.33.。
公元前5世纪,由于平贵斗争和领土危机,罗马城的建筑活动基本停滞。公元前4世纪初,高卢人入侵罗马。传统记载认为高卢人烧毁了大部分与城市历史相关的古老文献,可能有所夸大。但相关的考古发掘与文献不甚符合,年代较早的和公元前4世纪的重要建筑(如王宫和大量神庙)并未发现火灾后的修缮或重建痕迹[注]Filippo Coarelli, Guide Archeologiche: Roma, Milano: Mondadori Electa S.p.A., 2008, pp.7-16.。高卢人撤出罗马后不久,执政官重建并延长了塞维鲁城墙[注]F.Coarelli, Guide Archeologiche: Roma, pp.20-24; A.Giovagnoli, Le Porte di Roma, Roma: Edizioni del Pasquino,1973.。
公元前3世纪亚平宁半岛统一后,罗马城的建筑活动恢复,坎匹多利奥山和帕拉蒂诺山修建了大型公共建筑,大量神庙被修复或重建,营筑阿庇亚大道和阿庇亚渠等基础设施。最突出的变革是,希腊艺术家来到罗马,创作了大部分建筑和广场中的雕塑,罗马逐渐成为地中海世界的文化中心。
公元前2—前1世纪是罗马城的定型期。共和国统一地中海世界后,大批人口涌入。对都城规划来说,一方面是实用性的增强,产生平民居住区,出现多层公寓以及配套的基础设施。新的实用建筑和基础设施如港口和仓库等也应激增的城市供应需求而涌现。另一方面则是纪念性的凸显,蜂拥而入的中下层平民需要寻求政治依靠,相应地,贵族家族则以大型公共建筑来作为自身威望的表现,以此吸纳更多的依附者来获取政治资源,在罗马广场、坎匹多伊奥山和战神原,贵族竞相营造柱廊、园林和神庙等各种公共建筑,也使这些区域逐渐被“纪念化”[注]F.Coarelli, Guide Archeologiche: Roma, pp.8-11.(见图4)。

图4 4世纪的罗马城区遗址平面示意图
共和国末期到帝国时期的主要考古遗迹:1.三城门 2.拉威尔娜门 3.青铜门 4.纳维亚门 5.卡佩纳门 6.卡厄利蒙塔纳门 7.奎尔奎图拉纳门 8.俄斯奎里诺门 9.维米那勒门 10.科里纳门 11.奎里那勒门 12.健康门 13.桑库斯门14.泉之门 15.卡尔蒙塔门 16.江河门 17.凯旋门 18.科尔涅里亚门 19.弗拉米尼奥门 20.平齐奥门 21.盐路门 22.诺曼图姆门 23.“封闭门” 24.提布尔门 25.普拉俄涅斯特门 26.阿西纳里亚门 27.麦特罗维亚门 28.拉丁纳门 29.阿匹亚门 30.阿尔德阿门 31.奥斯提恩塞门 32.波尔图恩瑟门 33.奥勒留门 34.塞提米阿纳门 35.卡匹托利姆 36.阿克斯峰 37.罗马广场 38.马森兹奥会堂 39.维纳斯与罗马神庙 40.凯撒广场 41.奥古斯都广场 42.和平神庙 43.过渡广场 44.图拉真广场 45.奥古斯都府与阿波罗神庙 46.提比略府 47.弗拉维宫与奥古斯塔那宫 48.塞维鲁府 49.埃里奥伽巴洛神庙 50.斗兽场 51.大竞技营 52.克劳狄奥神庙 53.新精锐骑兵营 54.宫廷角斗场 55.塞索尔里姆宫 56.爱莲娜浴场 57.瓦里乌斯马戏场 58.圣克莱蒙特教堂的密特拉神殿 59.金屋 60.提多浴场 61.图拉真浴场 62.“七室” 63.莉维亚围廊 64.莉维亚市场 65.麦切纳斯庄园 66.亚历山大·塞维鲁水神殿(“马里奥胜利纪念碑”) 67.“医疗者密涅瓦神庙”(利齐尼阿尼庄园的大厅) 68.塞拉匹斯神庙 69.康士坦丁浴场 70.戴克里先浴场 71.撒路斯提奥庄园 72.禁军营73.克劳狄奥拱门与维尔勾渠 74.哈德良时期的多层公寓 75.太阳神庙 76.葡萄牙拱门 77.路库路斯庄园 78.马塞留剧场 79.阿波罗神庙与贝罗娜神庙 80.弗拉米尼奥马戏场 81.屋大维娅围廊 82.菲利普围廊 83.海神神庙 84.旧米农奇奥围廊(阿根廷广场) 85.米农奇奥小麦围廊 86.巴勒伯剧场与柱廊 87.庞培剧场与围廊 88.哈德良火葬堆 89.赛车场 90.塔兰托 91.阿格里帕浴场 92.万神殿 93.朱利亚选举围廊 94.伊西斯与塞拉匹斯神庙 95.神圣围廊 96.图密善体育场 97.图密善音乐厅 98.尼禄浴场 99.玛提蒂娅神庙 100.哈德良神庙 101.马可·奥勒留纪功柱 102.安东尼诺·皮奥火葬堆与纪功柱 103.马可·奥勒留火葬堆 104.和平祭坛 105.奥古斯都日晷 106.奥古斯都陵墓 107.油广场108.圣奥莫波诺区 109.牛广场 110.大马戏场 111.狄安娜神庙与密涅瓦神庙 112.苏拉浴场 113.圣普利斯卡教堂的密特拉神殿 114.德齐奥浴场 115.卡拉卡拉浴场 116.市场码头 117.艾米利亚围廊 118.加尔巴仓库 119.萝丽娅仓库120.特斯塔奇奥山 121.盖伊奥·切斯提奥金字塔 122.波尔图恩瑟门居住区 123.俄利奥颇利斯城的朱庇特神点 124.法尔涅瑟宅邸 125.卡里古拉马戏场 126.罗慕路斯喷泉 127.梵蒂冈墓地 128.哈德良陵墓 129.席匹奥涅墓
结 语
(一)城市空间结构演变
在罗马从聚落到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其空间演化方式可以用斯梅尔斯所说的“城市物质形态演变的双重过程”来概括,即内部重组和向外扩展的过程,分别以替代和扩散的方式形成新的城市形态结构[注]A.E.Smailes, The Geography of Towns, London: Hutchinson,1966.。替代过程包括物质性的,也包括功能性的,在城市核心区尤其表现明显。
1、内部空间重组
坎匹多伊奥山的卡匹托利尼峰是罗马城所在范围最早出现聚落的区域,自青铜时代中期到铁器时代规模逐渐增长,公元前8世纪也即王政时代开始,修建了最早的至高无上朱庇特神庙(三主神神庙)[注]S.B.Platner, The Topography and Monuments of Ancient Rome, ed. 2, Boston, 1929, pp.297-302; LTUR III, pp.144-153; F.Coarelli, Guide Archeologiche: Roma,pp.48-50.。这个最早的居住区域被神化,从此成为宗教中心区,到帝国时期并将之作为国家祭祀中心。
帕拉蒂诺山聚落出现的时间稍晚于卡匹托利尼聚落,可能由于此处离台伯河更近、山顶也更开阔,取水、交通和贸易都更为便利,也能容纳更多的人口,逐渐成为中心聚落。在拉齐奥文化ⅢB期出现了第一道土墙,后被拆毁,IVA2期又修筑了第二道。弗勒米南特根据第一道墙废弃后不久被墓葬打破的现象,认为墙的仪式意义更重于现实意义[注]Francesca Fulminante, The Urbanisation of Rome and Latium Vetus: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Archaic Era, pp.83-95.。在公元前7世纪,第三道凝灰岩墙的修建被蒂姆·康奈尔等学者认为是政治性的界线。也许这意味着墙内外产生了阶层的分化。共和国时期,帕拉蒂诺山被贵族们的宅邸所占据。帝国早期,这里基本成为皇帝宅邸和宫殿的专属区域[注]F.Coarelli, Guide Archeologiche: Roma, pp.214-253.。这是一个“尊化”的过程。
广场谷早期是沼泽地,到铁器时代成为墓葬群,可能属于附近山上的聚落。王政时代晚期,也即公元前7世纪,这里被改造成政治宗教中心,修建了王宫(性质存在争议)和维斯塔中庭等建筑。共和国时期根据政治制度的需求,将其转型成为公共的政治宗教中心[注]S.B.Platner, The Topography and Monuments of Ancient Rome, pp.230-237; F.Coarelli, Guide Archeologiche: Roma, pp.56-111.。从凯撒到奥古斯都时期,又经历了新一轮基于政治需求的转型,在周围增建帝国广场群,成为了显示皇帝权威的政治中枢区[注]S.B.Platner, The Topography and Monuments of Ancient Rome,pp.220-223, 225-229, 237-245, 386-388; F.Coarelli, Guide Archeologiche: Roma, pp.113-140,145-147.。
由此可见,罗马城的核心区域是自青铜时代以来传统的人类活动区,因地形和环境不同,开发时间不同,产生功能分化,在王政时代普遍发生物质性的替代,共和国时期、帝国早期大致保留原来的物理格局,对空间作物质性或功能性的替代。最古老的居住区域最终成为神圣世界,次古老的居住区域则成为世俗世界的权力顶端,原有的政治中枢区随着政治制度的变迁而调整(见图5)。罗马城之所以具有超强的层累性和延续性,和这种内部空间的适应性重组和调整不无关系。

图5 罗马城中心区域沿革表
2、对外空间扩散
罗马城的内部核心区域在不断被替代的同时,对外则是逐渐扩散的过程。根据弗兰切丝卡的意见,约在公元前9世纪(拉齐奥文化ⅡB期),奎里纳勒山、俄斯奎利诺山分别被作为卡匹托利尼峰聚落、帕拉蒂诺山聚落的墓葬群[注]Francesca Fulminante, The Urbanisation of Rome and Latium Vetus: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Archaic Era, 2014: pp.72-77.。扩散的主要方向是东北方向的山丘。公元前6世纪塞维鲁修建城墙时,将卡匹托利尼峰、帕拉蒂诺山、奎里纳勒山、俄斯奎利诺山、维米那勒山、切利奥山和埃文蒂诺山北部都包括在内。埃文蒂诺山南部、平齐奥山直到克劳狄奥时期才划到神圣边界内[注]LTUR IV, pp.96-105.。进入罗马城“界线”内的先后顺序也影响了各个区域的建筑功能和类型。
最早进入“罗马城”范围的是俄斯奎利诺山和奎里纳勒山。俄斯奎利诺山西部是按照垂直原则分布的平民和贵族居住区(平民在低地,贵族在高地),东部从墓地变为共和国时期的贵族区再到帝国时期的皇帝别墅区。山上年代较早的神庙有平民化的特征,还有一些外来神祗神庙。公共纪念物较少,实用建筑较多。奎里纳勒山东部是平民区,北边是皇帝宅邸,也有重要的希腊——罗马神系神庙和近东宗教神庙[注]F.Coarelli, Guide Archeologiche: Roma, pp.214-253.。
公元前6世纪才进入罗马城范围的维米那勒山、切利奥山和埃文蒂诺山北部。由于早期都在“界线”以外,因此有大量的外来宗教神庙,共和国时期都以居住区为主,埃文蒂诺山由于临近台伯河,平民特色尤其突出。到帝国时期,埃文蒂诺山逐渐成为贵族聚居区,切利奥山由于紧邻帕拉蒂诺山,山顶成为皇帝专门的居住区,西边的低地是平民区[注]F.Coarelli, Guide Archeologiche: Roma, pp.203-213、 pp.240-253, pp.254-257, pp.318-349.。
第三批次进入“界线”内的是平齐奥山与战神原北部。这里较少重要的公共建筑和宗教建筑,共和国时期遍布墓葬和贵族别墅,帝国早期是重要的居住区②F.Coarelli, Guide Archeologiche: Roma, pp.203-213、 pp.240-253, pp.254-257, pp.318-349.。
而3世纪以前,战神原南部、埃文蒂诺山南部平原和河对岸都一直在界线外。战神原南部在共和国时期已有部分公共建筑,到帝国时期成为公共娱乐和休闲区。埃文蒂诺山南部平原一直承担商业中心和交通中心的功能。河对岸则有大量社会中下层,不过高地依然被贵族占据③F.Coarelli, Guide Archeologiche: Roma, pp.203-213、 pp.240-253, pp.254-257, pp.318-349.。
纵观罗马城的整个扩散过程,明显表现出先高地后低地的特征,从山丘向谷地、平原逐渐扩散,或可称之为“水流式扩散”。而在从共和国到帝国早期的城市发展过程中,也有一个明显的“等级驱逐”或“等级挤压”的行为,皇帝占用了帕拉蒂诺山及其周边的俄斯奎利诺山东部、奎里纳勒山北部和切利奥山,贵族则逐渐搬离到更远的其他山顶,而平民从原本生活的埃文蒂诺山搬离,居住在各山之间的谷地或河对岸的平原。但唯一不变的区域是台伯河东岸,从铁器时代起一直是商业和运输的中心地带。
(二)城市空间演化模式和动力
从史前时代到铁器时代早期的发展轨迹看来,罗马从人口稀少的非中心区域,逐渐发展成一个重要的居住中心,它的崛起与地理环境以及在半岛的商贸交流网络中的位置息息相关,尤其是地处从埃特鲁利亚到坎帕尼亚地区必经之路。坎帕尼亚地区有古希腊人最早在半岛建立的殖民地,而埃特鲁利亚地区也由于富含矿产受到地中海东部商业人群的瞩目,因而成为半岛上较早发展起来的地区。这两地的交流最早以罗马东南约20公里的阿勒巴诺山区为中转。铁器时代开始,罗马取代阿勒巴诺山区成为半岛南北交流的中点[注]Christopher Smith, Early and Archaic Rome, in Jon Coulston and Hazel Dodge, ed., Ancient Rome: The Archaeology of the Eternal City, pp.18-19.,或许因为阿勒巴诺山区是复合火山,罗马的地质条件稳定,而且恰好位于台伯河拐弯口,更少遭受洪涝灾害,距海又较近,才得到发展的机会,出现大型中心聚落,并于公元前7世纪建城。可见在罗马的建城和壮大过程中,商业贸易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与罗马城的发展过程类似,环地中海地区的大部分城市都是从旧有的聚落发展而来,虽进入城市形态的时间先后不一,但城市的沿用时间往往很长。就地中海北部、欧洲南部而言,爱琴海地区明显早于亚平宁地区,在迈锡尼时代(前1600—前1200)就已普遍建城。雅典的建城模式是爱琴海以及大希腊地区(magna graecia)的代表。约公元前4000年左右,卫城山上就有人类居住。迈锡尼时代在此修建城墙、宫殿。此后城市逐渐向山下扩散,形成上城(卫城)和下城的格局。公元前6世纪起,上城由政治核心区逐渐成为宗教中心,相继修建了雅典娜祭坛、帕台农神庙、伊瑞克提翁神庙和尼基神庙等。下城则以世俗职能为主,政治中心在广场。到罗马帝国时期,雅典城成为地方城市,在政治核心区加入了与元首制度相关的建筑元素[注]John M.Camp, The Archaeology of Athen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综合比较罗马城和以雅典城为代表的地中海北部城市,可发现扩散方式基本一致,都是先高地后低地,在此过程中,建筑实体和地形一般保持不变,但城市内部进行与各个城市的等级、制度和功能等相关的空间结构和功能重组及变革。罗马城最终之所以成为地中海的中心城市,与罗马的崛起是双向性的相互作用,罗马城在地中海城市序列里的地位随着罗马人的称霸而抬升,地域空间格局的重组和变革也因而比其他城市更加剧烈,根据上文的分析,这是由地理环境、商业贸易、交通条件、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和军事实力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并最终成为造就罗马城具有高度层累性和延续性的复杂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