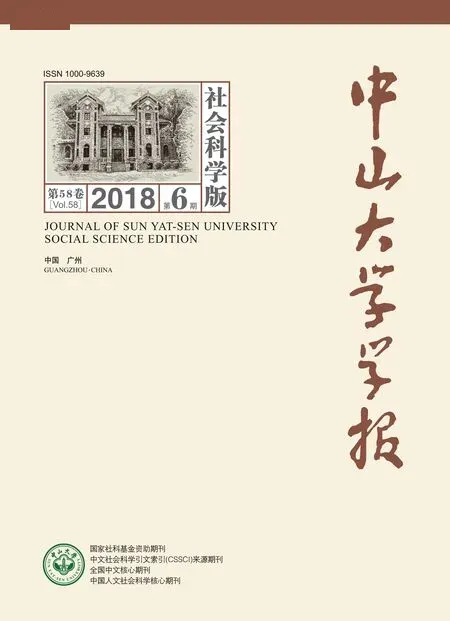汉赋为“学”论*
易 闻 晓
自来对于汉赋特别是汉大赋存在认识的偏差,汉人论赋以《诗》学为本,否定大赋的丽藻夸饰,影响深远。现代以来又以魏晋“文学自觉”遮蔽汉赋的“文学”本质,而且“文学”主情的观念并不适合赋体,例如刘勰批评大赋不本比兴,在来自西方的“四分法”里也找不到赋的位置。汉大赋的堆砌名物、堆垛繁难也一直受到自古迄今的批评。实际上赋体本于学问,其作为“辞章”的“文学”特点,就在于名物和描写的“丽藻”铺陈,最为突出地彰显了汉字书写的文体特性。
一、子学的流衍
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体裁中,辞赋尤其是大赋最资学问,兹以汉大赋为论,足为代表。大赋盛于两汉,汉代经学昌明,蔚起学风,包括辞章的各种著述都根于学问之深。不仅时代风气使然,对于词章之学,也深受往代学术浸被。清章学诚《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第十五论曰:
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虽其文逐声韵,旨存比兴,而深探本原,实能自成一子之学,与夫专门之书,初无差别。①章学诚撰,王重民注:《校雠通义通解》,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16页。
实际上屈《骚》在《诗》外别立一体,宋赋承之,去情叙物,开启汉赋,赋不本《诗》,向有确论。明末钱澄之《停云轩赋序》从《诗》《骚》流变推论,但认为至《骚》则“赋之名遂离诗以孤行”②钱澄之:《钱澄之全集·田间文集》,合肥:黄山书社,1998年,第290页。。晚清姚华《论文后编》亦本《诗》六义之赋,然谓“未尝独名一体”,而“楚隔中原,未亲风雅,故屈原之作,独守乡风,不受桎梏,自成闳肆,于诗为别调,于赋为滥觞”③姚华:《弗堂类稿》论著甲,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28—30页。。清程廷祚《骚赋论》则谓“宋玉以瑰伟之才,崛起骚人之后,奋其雄夸,乃与《雅》《颂》抗衡,而分裂其土壤,由是词人之赋兴焉”④程廷祚:《青溪集》卷3,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66—67页。。这是“赋家者流”的本源问题,必先简略说明。
章氏之说主要在于赋“出入战国诸子”的推论,由此确指赋为“一子之学”的本质属性。其中“排比谐隐”,汉大赋承之为寡,不作申论。首先是《庄》《列》寓言的影响。《庄子·寓言》谓“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日出,和以天倪”[注]郭庆藩:《庄子集释》,《诸子集成》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407,407—408,474—475页。,寓言就是假托之言,重言是“耆艾之谈”,所以尊重。成玄英疏:“巵,酒器也……夫巵满则倾,巵空则仰,空满任物,倾仰随人,无心之言,即巵言也。是以不言,言而无系倾仰,乃合于自然之分也。又解‘巵’支也。支离其言,言无的当,故谓之巵言耳。”②郭庆藩:《庄子集释》,《诸子集成》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407,407—408,474—475页。“巵言”无定,义通支离。《庄子·天下》又说:“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巵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成玄英疏:“谬,虚也。悠,远也。荒唐,广大也。恣纵,犹放任也。觭,不偶也。”③郭庆藩:《庄子集释》,《诸子集成》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407,407—408,474—475页。究之寓言、巵言都是不着边际、曼衍无当的谈说,俱非 “庄语”,重言也是假托之言,本质上与寓言不异。因为一本正经而不见信,所以恣纵不傥,并无偏私执著。这确实是《庄子》谈说的特点,《列子》亦然。《庄子》中如鸿蒙、云将、河伯、海若之谈,都是寓言,而且如《逍遥游》整篇就是一个大寓言,其中又套着若干小的寓言,甚至毋宁说整个《庄子》一部书都是寓言,属于假托之辞,指向虚无的境域。先秦诸子中寓言多见,但大都夹在文中,职在说理,如《韩非子·说林上》的涸泽之蛇就是这样,说明故弄玄虚的欺骗。《庄子》这种寓言的谈说方式与屈《骚》具有相通之处,对汉赋当有深刻影响。班固《离骚序》谓《骚》“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扬雄,骋极文辞,好而悲之,自谓不能及也”[注]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9—50页。。这固然不是寓言,但“多称……虚无”的假托无征与寓言相类,考虑到南方文化的共性,庄、屈也许具有某些共通的“浪漫”气质,这在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中有概略的描述[注]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惟荆楚之地,僻处南方。故老子之书,其说杳冥而深远。及庄、列之徒承之,其旨远,其义隐,其为文也,纵而后反,寓实于虚,肆以荒唐憰怪之词,渊乎其有思,茫乎其不可测矣。屈平之文,音涉哀思,矢耿介,慕灵修,芳草美人,托词喻物,志洁行芳,符于二《南》之比兴。而叙事纪游,遗尘超物,荒唐谲怪,复与庄、列相同。南方之文此其选矣。”(程千帆:《文论十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1页),后世亦以《庄》《骚》并列[注]韩愈《进学解》:“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910页)。宋玉去情叙物,承《骚》之虚,假设问对,直开汉赋。如《高唐赋》写“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鱼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王曰“试为寡人赋之”,“盖假设其事”。汉大赋则如枚乘《七发》假托楚太子与吴客,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假托子虚、乌有与亡是公,扬雄《长杨赋》假托子墨客卿与翰林主人,张衡二京赋假托凭虚公子与安处先生,都与《庄子》寓言“假托外人论说”同功。大赋的假设问对,主要在于夸饰,以物为主,旨归铺陈;《庄子》及诸子寓言则以事为主,义归说理。但是《庄子》的寓言谈说与大赋铺陈的“凭虚”夸饰具有相通之处,二者都出于荒唐谬悠、漫无端崖的想象,这是精神气质的深层相通。
其次是“苏张纵横之体”。战国策的写作特点,当然在于人物生动、辞藻丰赡等方面,但最主要的还是“恢廓声势”,运用结构相同的语句,一顺排比,气势恢弘。例如《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注]刘向集录:《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78页。为了说动人主,必须危言耸听,正好夸夸其谈,滔滔不绝。汉大赋的写作也具有恢张扬厉的特点,只是出于物类铺陈和形容描写的需要。大赋大题包容如《上林赋》《西京赋》,凡上林、西京题下之物,包括山水土石草木鱼虫鸟兽,靡不铺写,具有极为广阔的铺陈空间,因此需要名物的堆垛。例如《子虚赋》“其北则有阴林,其树楩柟豫章,桂椒木兰,檗离朱杨,樝棃梬栗,橘柚芬芳”,四字一顺,铺陈名物,鳞次栉比;又如《上林赋》“汩乎混流,顺阿而下,赴隘陿之口,触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汩濦漂疾,悠远长怀,寂漻无声,肆乎永归”一段,中间一个五字句用作散语说明,两个三字句提起气势,其余都是四字句,都在形容水势,滚滚而来,源源不断,明显可以感受到战国纵横家铺张扬厉的精神气势。
再次是“《吕览》类辑之义”。《吕氏春秋》有“八览”,其中《有始》篇论“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泽有九薮,风有八等,水有六川”。例如九塞:“大汾、冥阸、荆阮、方城、殽、井陉、令疵、句注、居庸。”又如八风:“东北曰炎风,东方曰滔风,东南曰熏风,南方曰巨风,西南曰凄风,西方曰飂风,西北曰厉风,北方曰寒风。”[注]高诱注:《吕氏春秋》,《诸子集成》本,第124—126页。这真是知识的类聚,与汉大赋如相如《子虚赋》“其树楩柟豫章,桂椒木兰……”的名物堆砌十分相似,只是前者意在博览,后者凭虚夸饰,并资博识,可知汉大赋本于学问的体制特点。
二、辞章的学养
先秦学术对汉赋的影响,当然包括《诗》《书》等,但诸书在汉代被尊为儒家经典,经学对汉赋的影响比先秦子学更为直接。经义要求辞赋创作有讽喻的功用,但经学对于词章的影响主要在于崇学的风气以及作家所具有的经学学养,与先秦子学一起灌注于自《骚》衍流的汉赋创作中,使之具有“学”的特征,这不尽合乎现代关于“文学”的定义。“文学”当然首先是“语言的艺术”,但必须具备情感和形象两大要素。汉大赋去情叙物,并不合乎这一标准;而且在西方文学的“四分法”里,中国的赋找不到位置。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书写下来就是文字的艺术。相对于多音节的拼音文字来说,汉字象形表意,不纯粹是语音的忠实记录。在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看来,语言符号是语音和思想的结合,语音传达思想,思想和声音之间形成“自然的唯一真正的纽带”,而在表意的文字系统中,“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表示,而这个符号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体系的典范例子就是汉字”[注][瑞士]索绪尔著,高名凯译,岑麟祥、叶蜚声校注:《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0—51页。。事实上,汉字必然是汉语的记录,否则就不配文字的资格,因而汉字的表达必与汉语语音相关,只是汉字象形表意,具有表音之外的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而且单音独字便于灵活的组合,造就无数奇丽的辞藻。中国文学成于汉字的运用,其最为基本的素质就是“字本位”的组合,辞藻乃是中国文学的根基,“辞章”的观念取决于此。惟其如此,中国古代的文体学总是统合各种应用文体如奏、疏、序、议,几乎一切汉字的书写都具有“文言”的讲究。如果我们愿意套用当世习用的“文学”称谓,这些文体由于汉字使用的语言之美,完全可以称之为“文学”。当然辞赋、诗词、骈文等最具文采,遂被习惯视为“辞章”的代表,而辞、词的文体称名本身就彰显文学作为“辞章”的本质。
大赋凭虚夸饰,恢张扬厉,征材聚事,都体现为辞藻的铺陈,基于作者的广博知识和深厚学养。汉代经学之盛彰显崇学的时代风气,这个时代的学术在校书、修史和文字等方面凌轹后世。虽经秦始皇焚书之劫,但在民间藏匿不少,及汉发掘所献,京师传之,遂有“古文”之学。辞赋创作夸饰铺陈,搜罗奇字,当存古文之遗,又复今文之异。《汉书·艺文志》说:
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注]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20—1721,2841,2821,3514,4225页。
对于学童试六体,要求“通知古今文字”,学者辞人就更需博通了。著名赋家中如司马相如、扬雄及班固都自己撰有字书,不仅对于国家“正字”作出了贡献,而且为他们自己的辞赋创作奠定了基础。辞赋创作实际上就是字词的运用,汉大赋的繁复名物、繁难僻字、大量异体字,来源于古、今及六国文字的复杂性,未正复字的存在、“书同文”的不彻底,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的遗存,反而成为赋家选字、堆砌名物、排比形容的文字渊薮。元祝尧《古赋辨体》卷4谓“自楚《骚》已多用连绵字及双字,长卿赋用之尤多,至子云好奇字,人每载酒从问焉,故赋中全喜用奇字,十句而八九矣”[注]祝尧:《古赋辨体》卷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60—761页。,联绵字因声异形,字形繁复,并奇字之用正是资于文字来源的复杂性。司马相如《凡将篇》残文38字:“乌喙桔梗□芫华,款冬贝母木蘖委。苓草芍药桂漏卢,蜚廉萑菌□荈诧。白敛白芷□菖蒲,芒消□莞椒茱萸。”[注]金国永:《司马相如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24页。这实际上就是以字存物,既是字书,也是名物的类聚,借用一定的句式和押韵,便于记诵,即使不是专为作赋所撰,也给作赋的名物铺陈带来了方便。若《子虚赋》的名物铺陈,也是博物的堆积罗列,仅此就具有博物的厚重,借助四言句式的排比气势,却不觉滞窒,例如“其卑湿则生藏莨蒹葭,东蔷雕胡,莲藕觚卢、菴闾轩于”,纷至沓来,鱼贯而出,恰好充当夸饰的铺陈。
汉赋作家的学问修养当然不限于小学。东方朔自谓从13岁到19岁学《诗》《书》、兵法,诵四十四万言⑤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20—1721,2841,2821,3514,4225页。;王褒“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⑥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20—1721,2841,2821,3514,4225页。;扬雄“少而好学……博览无所不见”⑦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20—1721,2841,2821,3514,4225页。,班固子承父业,“永平中为郎,典校秘书,专笃志于博学⑧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20—1721,2841,2821,3514,4225页。,“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注]范晔:《后汉书》,第1330页。;张衡“少善属文,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艺……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注]范晔:《后汉书》,第1897,1953,1954—1972页。。马融是郑玄之师,少从京兆挚恂游学,“博通经籍”②范晔:《后汉书》,第1897,1953,1954—1972页。,注群经及《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作为博通大儒,“融既博览典雅,精核数术,又性好音律,能鼓琴吹笛”[注]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249,22,119,119,120页。,安帝时滞留东观十年,桓帝时重在东观著述④范晔:《后汉书》,第1897,1953,1954—1972页。。刘跃进认为东观校书活动影响了“辞赋创作所追求的实录风格”“及其繁缛壮丽的文学风貌”[注]刘跃进:《东观著作的学术活动及其文学影响研究》,《文学遗产》2004年第1期。,总体上说汉大赋的演变可谓由虚转实。刘熙载《赋概》云:“相如一切文,皆善于架虚行危。其赋既会造出奇怪,又会撇入窅冥,所谓‘似不从人间来者’此也。”[注]刘熙载:《艺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92页。至扬雄倔强,既以学者从事,执于讽谏,其赋如《长杨赋》质实不繁,去相如凭虚甚远。东汉愈益征实,如班固方正,论赋坚持《诗》学讽喻立场,《两都赋序》本诸“先臣之旧式、国家之遗美”⑦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249,22,119,119,120页。,然如《东都赋》“发鲸鱼,铿华钟,登玉辂,乘时龙”云云,也必定凭虚夸饰,舍此无以为赋[注]参易闻晓:《汉赋“凭虚”论》,《文艺研究》2012年第12期。。倒是校书、修史所得的博学用于辞章的创制,乃能发为“繁缛壮丽”的凭虚铺陈,学问是汉赋的根基,也成就汉赋为“学”的品格。
三、博物的取资
学问之于汉大赋,就是“辞章”的铺陈,首先在于博物的取用。汉大赋名物广涉历史、典制、人事、传说、宫室、器物、天文、地理,及飞走鳞甲、卉木蔬果等类,相与构成庞大的知识结构,反映汉赋的博物学倾向。汉大赋容纳名物极多,是由于题目苞览,长篇巨制,具有广阔的铺陈空间,需要广博的名物充实其中。赋题不同,如《子虚赋》写云梦泽,并《上林赋》,凡其中山水、土石、草木、鸟兽,类聚众多;京都则如扬雄《西都赋》、张衡《西京赋》,乃至宫殿、苑囿、人物、车马、仪仗、玩好,糜不铺写至极。又往往展开上下左右的空间铺写,若《子虚赋》“其中有山焉,其山则……其土则……其石则……其东则有……其南则有……其高燥则生……其埤湿则生……其西则有……其中则有……其北则有……其上则有……其下则有……”,各类名物充实其中,构成十分广阔的空间铺陈。具体铺陈如“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坿,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瑉昆吾,瑊玏玄厉,碝石碔砆”云云。丹,朱砂,或指赤土;青,指黑土。《管子·地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注]戴望:《管子校正》,《诸子集成》本,第382页。《尔雅·释宫》:“墙谓之垩。”郭璞注:“白饰墙也。”[注]郭璞注,邢昺疏:《尔雅注疏》,《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6页。雌黄与雄黄相对而称,可药用,具有奇特的讲究。《本草纲目·金石部》:“生山之阴,故曰雌黄。《土宿本草》云:‘阳石气未足者为雌,已足者为雄,相距五百年而结为石。造化有夫妇之道,故曰雌雄。’《别录》曰:‘雌黄……与雄黄同山生。’”[注]李时珍:《本草纲目》第2册,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8年,第69,70页。《本草》引《仙经》云:“(雌黄)无单服法,惟以合丹砂、雄黄,飞炼为丹尔。”李时珍:《本草纲目》第2册,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8年,第69,70页。坿,音附。《文选》本赋李善注引苏林曰:“白坿,白石英也。”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249,22,119,119,120页。《说文·玉部》:“玫,火齐,玫瑰也,一曰石之美者。”[注]许慎:《说文解字》,第13页。《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本赋裴骃集解引《汉书音义》曰:“琳,球也。珉,石次玉者。”[注]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005,3005页。《文选》本赋李善注:“昆吾,山名也,出美金。《尸子》曰:‘昆吾之金。’”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249,22,119,119,120页。其山产金,即以山名代之。《山海经·中山经》:“(葛山)下多瑊石。”郭璞注:“瑊石,劲石似玉也。”[注]郭璞注,郝懿行笺疏,沈海波校点:《山海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10页。碝,《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本赋裴骃集解引徐广曰:“石似玉。”《文选》本赋李善注引张揖曰:“碔砆,赤地白采,葱茏白黑不分。”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249,22,119,119,120页。总上两句,前句写土10种,后句写石8种,各有来历,可见名物之富、闻识之博。
明谢榛《四溟诗话》卷2谓“汉人作赋,必读万卷书,以养胸次,《离骚》为主,《山海经》《舆地志》《尔雅》诸书为辅,又必精于六书,识所从来,自能作用”[注]谢榛:《四溟诗话》卷2,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75页。。读书“以养胸次”,也在博学的积备。当然除了上述诸书,汉人作赋所资者,也还包括《诗》《书》《老》《庄》等,语词名物多取于典籍,而不是我们现代这样来源于生活的口语,后者不能算作博学的修养。再以《子虚赋》并《上林赋》为例看其名物对《离骚》和《山海经》的取用,以见谢榛所言不虚。取于《离骚》植物类如江蓠、辟芷,本“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蕙茝,本“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茝”;神物类如玉鸾,本“鸣玉鸾之啾啾”;望舒,本“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鸩鸟,本“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并神话地名如县圃,本“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又如飞龙,则本《九歌·湘君》“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取于《山海经》者,动物类则如白虎,《西山经》谓“鸟鼠同穴之山,其上多白虎”[注]郭璞注,郝懿行笺疏,沈海波校点:《山海经》,第80,399,269,91,234页。;玄豹,《海内经》谓“幽都之山,其上有……玄豹”③郭璞注,郝懿行笺疏,沈海波校点:《山海经》,第80,399,269,91,234页。;蛩蛩,《海外北经》谓“(北海)有素兽焉,状如马,名曰蛩蛩”④郭璞注,郝懿行笺疏,沈海波校点:《山海经》,第80,399,269,91,234页。;鵁,《北山经》谓“(蔓联山)有鸟焉,群居而朋飞,其毛如雌雉,名曰鵁”⑤郭璞注,郝懿行笺疏,沈海波校点:《山海经》,第80,399,269,91,234页。;蛫,《中山经》谓“(即公之山)有兽焉,其状如龟而白身赤首,其名曰蛫”⑥郭璞注,郝懿行笺疏,沈海波校点:《山海经》,第80,399,269,91,234页。。
汉大赋的名物铺陈不是按实求之,而是出于凭虚夸饰的目的,在想象的空间充当丽藻的功用,这是赋体作为“辞章”的本质,那么名物的取用就必需广致多方,在典籍中搜罗殊方奇异以为夸饰,较之实录的文体指向实际的物事,更加需要作者的博学。左思《三都赋序》谓相如、扬雄等赋,“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侈言无验,虽丽非经”[注]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74页。,《上林赋》中有些植物取于《离骚》,本为楚地所生,却移到了关中,在赋家铺陈之时,出于类聚名物的需要而取之四方。左思自己写三都赋,也一样侈言神怪,如《吴都赋》“长鲸吞航,修鲵吐浪,跃龙腾蛇,鲛鲻琵琶”,《蜀都赋》“汩若汤谷之扬涛,沛若蒙汜之涌波”,岂必如《序》所云“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再如扬雄《羽猎赋》叙写从上所见,具体描写如“撞鸿钟,建九旒,六白虎,载灵舆,蚩尤并毂,蒙公先驱……霹雳列缺,吐火施鞭……飞廉云师,吸嚊潚率,鳞罗布烈,攒以龙翰”云云,却凑会神物,极尽夸诞。这要求作者博览群籍,具备博物的闻见,藉以达到自我炫耀并竦动览者的效果。
四、字词的繁难
大赋铺陈,一在名物的直接呈现,二在形容词的叠复描写。大赋名物需要之多,在于名物作为对象的呈现,借助散语一顺铺陈,形成名物的堆积,例如张衡《西京赋》“其中则有鼋鼍巨鳖,鳣鲤鱮鲖,鲔鲵鲿鲨……鸟则鹔鹴鸹鸨,鴐鹅鸿鶤……不可胜论”,这是散体大赋铺陈的典型句式,以四字为读,四字中或以双音节奏固定二字为一个名物,或者一字一物,堆砌呈现,间不容发。那么名物的广取,在某种角度上看就是多识字,《西京赋》罗列鱼类和鸟类之字,乃见识字为多、闻见为博。汉语初多单音命物,物乃有名,因以单字代之,故有“名字”,一字对应一名,一名指代一物,必多识字,才能博知名物。现代双音词为多,例如指称猪的种类,都用双音叠加修饰,就组合成“大猪、小猪、公猪、母猪、野猪、白毛猪、黑毛猪”等等双音或多音词,但不堪取为赋的铺陈、充当博识的表现。拙作《相如盛览问对赋》写上古黔中夷民猎猪,“幼曰豵,大曰豜,肥以豨,毫者豲,豥蹄白,余者黔,豱头而短,豯未及年,豟硕而壮,豶获可阉”[注]易闻晓:《相如盛览问对赋》,《会山堂初集》,济南:齐鲁书社,2015年,第61页。,“豶”是未阉割的公猪,颇觉物类之众。
赋家的铺陈,尤其需要不常见的奇异名物,相对应的字也就生僻繁难,赋家适可炫耀博学。例如《上林赋》“其兽则麒麟角端,騊駼橐驼,蛩蛩驒騱,駃騠驴驘”云云。《史记·匈奴传》“其奇畜则橐駞、驴、驘、駃騠、騊駼、驒騱”[注]司马迁:《史记》,第2879页。。《尔雅·释畜》:“騊駼马。”郭璞注引《山海经》:“北海有兽,状如马,名騊駼,色青。”[注]郭璞注,邢昺疏:《尔雅注疏》,第334页。《汉书·扬雄传》扬雄作《解嘲》云:“今大汉左东海,右渠搜,前番禺,后陶涂,东南一尉,西北一候。”陶涂,如淳注谓“小国也”。颜师古曰:“騊駼马出北海上。今此云后陶涂,则是北方国名也。本国出马,因以为名。”[注]班固:《汉书》,第3568页。《诗·鲁颂·駉》:“薄言駉者,有驒有骆。”《说文·马部》:“驒,驒騱,野马也,从马,单声。”[注]许慎:《说文解字》,第202页。并本赋“騕褭”等,率皆异物,若都是平常之物,殊难起到夸饰的效果。又如《七发》“鳱鴠”,二字并翰韵,本叠韵联绵,当是因其鸣声得名。《说文》“鴠,渴鴠也。”段玉裁注:“《月令》作‘曷旦’,《坊记》作‘盇旦’。郑云:‘夜鸣求旦之鸟。’《方言》作‘鴠’、‘鹖鴠’,《广志》作‘侃旦’,皆一语之转。”[注]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50页。这些不同的字都是因声异字,字无定型,益滋繁难。
大赋形容词的叠复描写,情况益加复杂,或以《骚》语长句铺陈。《离骚》以句中虚字连接更多的字词形成复杂结构的长句,并以句尾虚字加强情感的表达和咏叹的效果,实质上乃是借助虚字以使散语长句成为韵语[注]参易闻晓:《“赋亡”:铺陈的丧失》,《文学评论》2015年第3期。,较之《诗》四言,具有容纳名物和形容词的更大空间。例如“杂申椒与菌桂兮”,“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与”连接两个名物;“心犹豫而狐疑兮”,“曾歔欷余郁邑兮”,“而”连接两个形容词,“余”起到了连接前后的结构作用,虚用为连词。汉大赋中如扬雄《甘泉赋》用《离骚》十之八九,是比较特殊的现象,赋文“咸翠盖而鸾旗”,长句中虚字连接两个名物,“飞蒙茸而走陆梁”,“声駍隐以陆离兮”,则连接两个形容词。但大赋多四字句一顺铺陈,名物铺陈已见上述。汉大赋中堆砌形容词最多的莫过于《上林赋》一段:
沸乎暴怒,洶涌彭湃,滭弗宓汨,偪侧泌瀄,横流逆折,转腾潎洌,滂濞沆溉,穹隆云桡,宛潬胶盭,踰波趋浥,涖涖下濑,批岩冲拥,奔扬滞沛,临坻注壑,瀺灂霣坠,沈沈隐隐,砰磅訇礚,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驰波跳沫,汨濦漂疾。
这一段形容词的堆砌描写不仅在汉大赋中具有普遍性,而且考察其组合的方式及其祖述与被祖述的转写,可以反映辞赋语词的历时性演变,具有典型的阐发意义,让我们看到汉赋为“学”具体落实于“字本位”的真实情形。在这些语词中,仅“瀺灂”出宋玉《高唐赋》;“彭湃”,“滂濞”“砰磅”,都是宋玉《风赋》“淜滂”因声异形的转写;“滭弗”是《诗·大雅·瞻卬》《诗·小雅·采菽》“觱沸”的异形。其余都首见本赋,在缺乏此前文献支持的情况下,暂定其为相如临文所用。没有人会否定司马相如在汉代以至整个中国赋史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他的创作开启了汉大赋的模式,而且他是语词创造的大师,引导后人的递相祖述,也许正是由于相如“赋圣”在前,后人祖述因便,但自造语词,此风既开,亦必影响后人。
这些词在字的组合上具有声、韵、调的联系,或无声韵联系而以同义、近义并列,借助语句中双音节的作用和后人祖述固定为词;有声韵联系的词则多因声异形,往往繁复叠出。“彭湃、滂濞、砰磅”,并“滭弗、宓汨、沆溉”为双声联绵;“洶涌、宓汩、偪侧、泌瀄、潎冽、穹隆、宛潬、湁潗”为叠韵联绵;“汨濦”是入声并用;“沆溉、瀺灂、胶盭”无声韵系联;“暴怒、转腾、漂疾”近义组合,或以后代祖述成为习语,或临时组合而未成常式。兹分析这些语词的组字和后人祖述及其转音易形,显示汉赋语词的纷繁复杂:

“滭弗”为“觱沸”的仍音转写,《诗》之《大雅·瞻卬》《小雅·采菽》并有“觱沸槛泉”语。《说文·水部》:“沸,滭沸,滥泉。”⑥许慎:《说文解字》,第231,232,229页。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涌出之貌。”[注]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武汉:武汉市古籍书店,1983年,第626页。“滭”,上古帮母质韵,“弗”,帮母物韵。“滭弗”在本赋又转作“咇茀”,义为香气发散,以发出义转为形容香气,字亦随之变形,故从“口”从“艸”。“宓汨”,李善注引司马彪谓“(水)去疾也”⑧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23—124,265,266,70,123,123,265,123,123页。。“宓”,上古并《广韵》明母质部,“汨”,上古并《广韵》明母锡部。
“洶涌”,李善注引司马彪谓“(水)跳起也”⑨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23—124,265,266,70,123,123,265,123,123页。。宋玉《高唐赋》“濞洶洶其无声兮”,扬雄《羽猎赋》、左思《吴都赋》祖之,李善注引《说文》谓“洶洶,涌也”⑩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23—124,265,266,70,123,123,265,123,123页。。“洶”本“涌”义,双声同义并用。汉语造字,本其韵初有二字,赋家以同韵的语感并用,并以双音节固定为一词,后人祖述,遂成习用联绵,嵇康《琴赋》祖之,至今习用。“偪侧”,叠韵同义组合。“偪”,上古帮母职部,《广韵》未变。“侧”,上古庄母职部,《广韵》未变。《说文》无“偪”字,同“逼”,本字为“畐”。《方言》:“偪,满也。”[注]扬雄撰,郭璞注:《方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1页。“侧”义狭窄。《释名·释姿容》:“侧,偪也。”[注]刘熙:《释名》,《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页。《荀子·解蔽》:“处一危之,其荣满侧。”杨倞注:“侧谓迫侧,亦充满之义。”[注]王先谦:《荀子集解》,《诸子集成》本,第266页。张衡《西京賦》作“偪仄”,傅毅《舞赋》“逼迫”,也是近义并列。“泌瀄”,近韵连用,汉晋赋罕见祖述。“泌”,上古帮母职部,《广韵》毗必切,变为并母,《说文·水部》谓“侠流也”许慎:《说文解字》,第231,232,229页。,《玉篇》作“狭流”[注]顾野王:《大广益会玉篇》,第89页。。“瀄”,《广韵》阻瑟切,庄母栉韵,质部。瀄”音同“栉”,上古庄母质部。“潎洌”,叠韵联绵,《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本赋司马贞索引引薛林谓“流轻疾也”[注]司马迁:《史记》,第3019页。,嵇康《琴赋》、潘岳《秋兴赋》祖之。“潎”“洌”上古并月部,《广韵》并薛韵,“薛”本在上古月部。“穹隆”,李善注引郭璞谓“起回窊也”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23—124,265,266,70,123,123,265,123,123页。扬雄《甘泉赋》、孙绰《游天台山赋》祖之,扬雄《羽猎赋》“三军芒然,穷冘阏与”,“穷冘”盖其转音变形。“宛潬”,李善注引司马彪谓“展转也”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23—124,265,266,70,123,123,265,123,123页。。“宛”,上古影母元部,《广韵》於阮切,影母阮韵;“潬”,《集韵》上演切,禅母狝韵。二字并元部,近韵连用。本赋“象舆婉僤于西清”,“婉僤”为“宛潬”易形,形容山势如象舆蜿蜒相接,亦避重,李善注谓“动貌也”[注]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25,252,255,124,124,124,265,124,123,123,124页。;马融《長笛賦》易为“虫”旁,转作“蜿蟺”,形容吹笛声,李善注谓“盘屈摇动貎”②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25,252,255,124,124,124,265,124,123,123,124页。;嵇康《琴赋》“蟺”形容水流,李善注谓“展转也”③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25,252,255,124,124,124,265,124,123,123,124页。。“湁潗”,一作“湁湒”,后人罕用。李善注引三国魏周成《襍字》曰:“水沸貌也。”④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25,252,255,124,124,124,265,124,123,123,124页。“湁”,《广韵》丑入切,彻母缉韵。《说文·水部》:“湁,湁湒……从水,拾声。”[注]许慎:《说文解字》,第230,227,230页。“拾”,上古禅母缉部。“潗”,《广韵》子入切,精母缉韵,《广韵》子入切的字如“咠”,上古清母缉韵,二字叠韵。凡上联绵之字,或双声,或叠韵。比较特殊的是“汨濦”,李善注引司马彪谓“水声也”⑥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25,252,255,124,124,124,265,124,123,123,124页。,二字入声并用,在赋家用字组词,也是普遍的现象。“汨”已见上文,上古并《广韵》明母锡韵。《说文·水部》:“濦,水,出颍川阳城少室山,东入颖。从水,声。”⑦许慎:《说文解字》,第230,227,230页。李善注引韦昭谓“许及切”⑧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25,252,255,124,124,124,265,124,123,123,124页。,当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本赋作“”,字当从此。许及切之字如“吸”,上古并《广韵》晓母缉韵。
“瀺灂”出宋玉《髙唐赋》“巨石溺溺之瀺灂兮”,李善注引《埤苍》谓“水流声貌”⑨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25,252,255,124,124,124,265,124,123,123,124页。,二字单用本无声韵联系,以同义并用。张衡《南都赋》、潘岳《闲居赋》、《西征赋》转相祖述。本赋李善注引《字林》谓“小水声也”⑩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25,252,255,124,124,124,265,124,123,123,124页。,“瀺”单用也是此义。“灂”,上古崇母药部,《广韵》士角切,崇母觉韵,《说文》训“小水声”许慎:《说文解字》,第230,227,230页。。“瀺”“灂”并可作为名物的所指,并用成为形容词。
“沆溉”连义并用。“沆”,大水,水流貌。“溉”,灌注,洗涤。李善注引司马彪曰:“沆溉,徐流也。”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25,252,255,124,124,124,265,124,123,123,124页。“胶盭”,李善注引司马彪曰:“胶盭,邪屈也。”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25,252,255,124,124,124,265,124,123,123,124页。“胶”,胶着,扰乱。“盭”,同“戾”,乖戾。二字连用,形容水流扰乱而不直行。左思《吴都赋》写房舍“东西胶葛,南北峥嵘”,“胶葛”另组词,与“胶盭”具有意义关联。“訇礚”拟声连用,李善注引司马彪谓“水声也”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25,252,255,124,124,124,265,124,123,123,124页。,成公绥《啸赋》祖之。枚乘《七发》“訇隠匈磕”,第一、二、四字并拟水声,本赋略取其二,组合成形容词。潘岳《藉田賦》“鼓鞞硡隠以砰礚”,“硡隠”状鼓声,为“訇隠”的转写,而另组“砰礚”,可见临文组词之实。“暴怒、转腾、漂疾”近义组合,常语不假分析。晚清郑知同《说文新附考》“湲”字按语云:
郑珍为晚清道咸间贵州著名诗人和文字学家,知同为郑珍子,亦如其父谨守许、郑。《说文》不收辞赋复字,然辞赋语词孳乳繁复,正是名物铺陈和描写形容之需,非如经籍谨守家法。辞章家用字造词,随用随写,音形义因仍转复,这是辞赋字词孳乳的主要来源,实际上是“自屈宋滥觞”,汉赋承之,已经“繁滋复赘”,不待晋人,也不尽“吻合六书”。其所出者,或“南楚晚出方言”,而汉赋本之屈《骚》宋赋,则用字造词递相祖述,因仍展转,或取六国文字之遗。究之必须识字之多、闻见之博,才能满足大赋的丽藻堆积、完成空前绝后的大赋创制,博得“一子之学”的名声,以迥然不同于六朝述情赋和现代“文学”的面目彰显自己为“学”的突出特征。
——评杜朝晖《敦煌文献名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