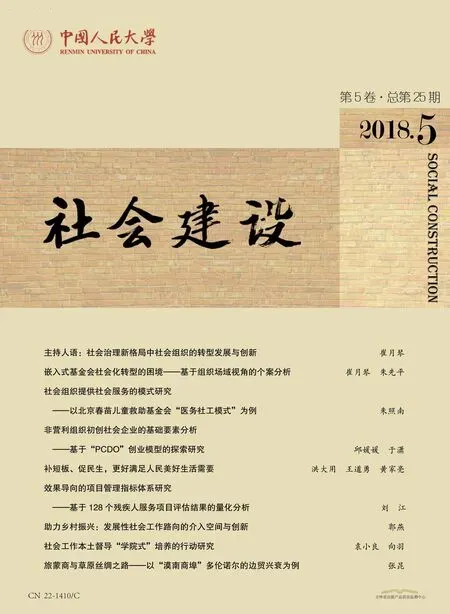旅蒙商与草原丝绸之路
——以“漠南商埠”多伦诺尔的边贸兴衰为例
张 昆
一、写在前面:认识旅蒙商
旅蒙商,是旅蒙行商的简称,又称边商。指明清年间活动在内外蒙古、新疆兼及东北三省(以蒙古地区为主)的大号商店和小本商贩,是蒙汉经济联系和中俄通商贸易活动的中介人群。①牛国祯、梁学成:《张库商道及旅蒙商述略》,《河北大学学报》,1988(2)。本文意指由中原内地往返蒙古地区从事边疆民族贸易的商人、商号和商帮的总称。它兴起于明朝中期,发展于清初,到清朝中后期进入了全盛时期,大部分为晋商,也有部分来自河北、北京、天津、陕西、甘肃、宁夏和青海等地的汉族及回族商人。旅蒙商最初在蒙地是以肩挑扁担流动的形式出现并发展起来的,因此蒙古人将他们称之为“damnagurqin”,汉音译为“丹门沁”。在东部地区,因为他们携带贩卖的货物主要是日常所需的针头线脑等,所以也叫“杂货郎”,也就是东北人所说的“萨胡勒”。而在西部地区,一般是来自山西榆林、神木、府谷等地的商贩,越过边境跟蒙古人进行贸易,所以也叫“边客”。旅蒙商人根据游牧经济生产的特点,往往在春夏之交,载货车运送商品到蒙古牧民营地,经营销售货物,这种经营方式也称“出拨子”。
有关旅蒙商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史学领域,探讨的角度也各有侧重。部分学者以大型旅蒙商号为基础,对其经营方式和组织情况进行了分析,较具代表性的莫过于20世纪80年代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著的《旅蒙商大盛魁》①内蒙古自治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著:《旅蒙商大盛魁(内部发行)》,1984。,该书通过上、下两篇内容,详尽地记述了清代至民国初年内蒙古地区最大的旅蒙商号——大盛魁的内部组织和营业状况,比如其分支机构总号和小号,以及印票业务、日用百货业务、牲畜业务、皮毛和药材业务等。此外,于军、双梅、扎木苏②于军、双梅、扎木苏:《大盛魁对呼和浩特经济建设的启示》,《北方经济》,2012(11)。等从经营特色和经营经验等方面进行了探讨,进而将其纳入到对地区经济建设的启示讨论框架中。还有一些学者从旅蒙商对地方经济产生的影响展开论述,具体包括正面和负面影响两方面,比如李学诚③李学诚:《旅蒙商与内蒙古西部地区经济——文化变迁》,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邢野④邢野:《旅蒙商的反思》,《草原》,2008(3)。等人,前者总结了旅蒙商对内蒙古地区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具体包括增强了西部地区与内地经济的联系、促进了民族团结等,后者则从旅蒙商深入草原地区开展贸易的欺诈行为、对资源的破坏性掠夺、走私生意及他们的不幸婚姻等方面反思了旅蒙商经济行为中产生的诸多负面影响。而牛国祯、梁学成⑤牛国祯、梁学诚:《张库商道及旅蒙商述略》,《河北大学学报》,1988(2)。、陈东升⑥陈东升:《清代旅蒙商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1990(3)。等人则以时间为基本脉络对旅蒙商的发展历程进行了详尽梳理,但他们大多都是对清代活跃在漠南、漠北草原上整个旅蒙商的情况作一大致描述,而将视角集中在某一特定的点,全面分析当地旅蒙商的成长历程并且反思其历史作用的研究目前还非常少。
基于此,本文将选取清代漠南草原上旅蒙商云集、商号林立的贸易重镇多伦诺尔为个案,结合田野调查获得的档案及史料,通过对其兴起、兴盛以及衰落三个历史阶段的边区贸易情况展开论述,并在此基础上反思多伦旅蒙商对民族区域经济及文化发展所起的作用,以期对牧区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一种参考的视角。
二、来自草原的暖风:多伦旅蒙商的肇始
多伦诺尔,为蒙语表述,汉译“七个湖泊”,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南部,河北省北部的两省交界处。其地理位置东接河北围场,南连独石口,西邻正蓝旗,东北与赤峰克什克腾旗接壤。经纬位置为东经116°15′,北纬42°15′,总面积3773平方公里,人口约10.5万,素有“滦河之源”、“京北后花园”之称,依托环京津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区位优势明显,是内蒙古自治区距离北京最近的旗县。民族成分包括蒙、汉、回、满等,因此基于我国华北与北方民族地区毗邻的地缘优势,自古成为沟通蒙古高原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重要门户与兵家争夺的战略要地,也是旅蒙商到内蒙古草原活动较早的地方。
提及多伦旅蒙商的肇始,还得将时间拉回到明朝中期。当时,一些来自山西、河北等地的商人,以同乡或同业结成团体,在长城沿边城镇开展互市贸易,当时被称之为“边商”。由于他们的艰辛努力,蒙汉、南北经济的贸易市场,逐步从边关转移到了内蒙古境内,这可以看作是旅蒙商的萌芽。他们的到来给蒙古牧民带来不少好处,比如内地商人给牧民带来了生活所需的物品,同时也可以借此把他们富余的牲畜和畜产品交换出去,扩大销路,促进蒙古经济的发展,这就使世代以游牧生计为生的草原游牧民,在日常生产生活中所需要的粮食、布帛、器皿等物品和一部分劳动工具,开始完全依赖内地商贾的供应。
而清王朝建立之初,为了加强其对蒙古的统治地位,防止蒙古权贵再度武力内侵,采取了限制蒙古社会经济发展的封禁政策,不允许汉族农民到蒙古地区开垦移住,也不允许蒙古各旗之间越界放牧联系。特别是对进入蒙古地区的汉族商人,除了课以苛刻的捐税外,还规定了种种严厉繁琐的法律,限制蒙汉之间直接的经济贸易联系。更不准蒙古王公、台吉和牧民自由进入长城以内地区的“互市”进行商品贸易,同时清政府派兵驻守在长城及蒙汉接壤的沿边通道,以阻绝蒙汉联系的交通。这些禁令的实施,虽然在政治上实现了对蒙古的控制,但在经济上,导致的结果是蒙古社会经济生活完全依赖于清政府的安排,处于十分封闭的境况,因而对其社会发展极为不利。
当时,政府只允许在长城沿线的张家口、归化以及青海西宁等几处较大的贸易据点,由少数汉族和回族商人,在地方官吏的监督控制下,进行有限的以物易物贸易交换。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交换的商品,无论是品种还是数量,都十分有限,远远不能满足蒙古社会发展的需要。因而,居住分散的牧民渴望中原内地的商人深入草原地区,“不惜多用一两头牛羊,使其交换”到他们所需的各种日用品。特别是蒙古封建王公贵族,拥有大量牲畜、皮毛等财富,更加迫切需要各种奢侈品来满足他们及其家人日常生活的物质需要。地方经济发展和牧民物质需要的推拉作用呼唤着旅蒙商的到来。正在此时,机遇降临了。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五月,为缓和清朝与内外蒙古的关系,加强对喀尔喀蒙古的管理,维护各部的团结及西、北边疆的安定,巩固边防,康熙在多伦诺尔召见内蒙古四十八家王公贵族,举行盛宴并加封赏赐,史称“多伦诺尔会盟”。期间,到会的蒙古王公和喇嘛上层人士,一致向康熙提出请求:放宽对内地旅蒙商人到塞北蒙古高原进行经济交流、商业贸易活动的限制,派遣商人来多伦诺尔进行常年大宗贸易,允许中原内地商人到蒙古地区进行贸易。他们认为,只限于一年一次蒙古封建主派遣贡使商队,远道跋涉到北京或者清廷指定的城市进行贸易交换活动,远远不能满足蒙古广大牧民对各种生活日用物品的需求。
因此,借着来自草原的“暖风”,为笼络蒙古各部王公和上层喇嘛宗教领袖人物,康熙表示,自此允许内地商贾出长城塞外,进入蒙古高原地区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在多伦诺尔开设市场。这一决定,不仅受到蒙古王公贵族和喇嘛领袖的感激,也得到了希望深入草原开展贸易的中原商人的一致拥护。由此,清政府首先在内蒙古地区设立了五路驿路,即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和杀虎口驿路,被称为南路或西路驿路。后来,清政府又在漠北地区建立了北路驿路,其一,由四子部落境内出发,途径47站到达乌里雅苏台①乌里雅苏台:今蒙古国扎布汗省省会扎布哈朗特。,再由此经14站到达科布多②科布多:今蒙古国科布多省会。;其二,从塞尔乌苏出发,途径包括库伦③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在内的26站,到达终点恰克图。④钟志祥:《“漠南商埠”多伦诺尔》,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第50-51页。
这些驿路的开通,将蒙古高原与中原内地紧密联系起来,正如波兹德涅耶夫所说:“中国与东北蒙古之间几乎所有的贸易都取决于比较直捷而方便的通过多伦诺尔的大路。”①[俄]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卷二)》,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这为多伦诺尔及其周边地区的商业贸易发展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清政府派遣京城的鼎恒升、大利号、聚长城、庆德正等八大商号的“龙票商人”,到多伦诺尔设立店面,开设分号,由当时专门掌管蒙古、新疆、西藏各地少数民族事务的机关——理藩院颁发“龙票”②“龙票”:也称印票,是大清以政府名义发给商人的一种信符证件,上面记载商号的字号,经营的货物品名、数量,并附有用满、蒙、汉三种文字注明的,保护商人生命财产的条文。另据相关史料,“龙票”不仅是经商执照,实质也是一种专利证件,不是每家旅蒙商都能请领得到,而是特别发给极少数几家商号。。据当地几位年老商人描述,“八大商号”均由山西商人开设。清代《万泉县志》③何修,冯文瑞纂:《万泉县志》(石印本),民国七年。上也有这样的记载:“八家商人者,皆山右(及山西)人。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自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交易,皆八家主之。”由此可知,早在明末清初时,在张家口一带从事蒙古民族贸易的这八家商号,就已经在市场上占据了重要地位。因而会盟之时,康熙自然会选择这些商号派往多伦,使其成为在此生根发芽的首批“龙票商”。
三、旅蒙商的蜜月:“漠南商埠”如何兴盛
自此,康熙派往多伦诺尔的京城“八大商号”即“龙票商”拉开了多伦商业集镇快速形成的帷幕。之后,来自直隶④直隶:即今河北。、西北、山东等地的大批商人相继到来,在多伦纷纷设立商号。多伦的商人包括坐商和行商两种类型。坐商是在多伦建立铺面和仓库,从事批发零售的商人群体,比如上节内容所提到的八家“龙票商”。而行商是指,从多伦市场上批发货物,运载到草原牧区进行销售,或者从外地进货运到多伦,将货物存放在熟悉的商号中委托其代为批发的一些商人。这两类商人虽在经营方式、资本势力方面略有差别,但二者的共同特点都是借助于草原牧民地理闭塞,市场广阔的巨额商机,开展“出草地”经营,深入漠南漠北草原牧区,与牧民进行以物易物的贸易交换,从中赚取差价。
他们大多从多伦诺尔用牛车、骆驼将货物运到草原各旗王府、寺庙和牧民的居住点附近,支起帐篷进行贸易,因此这种买卖方式也被称为“账房买卖”。对于资本雄厚的大商号而言,他们“出草地”时,一般会派遣一名精通蒙古语、通晓商业知识,并与所去地方王公贵族、上层喇嘛较为熟悉,又被牧民所信任的掌柜,率领若干员工深入牧区,在适当的地点搭建帐篷进行贸易,方便附近牧民前来购买所需的生活用品,同时出售牲畜和畜产品。而行商一般都做“无本买卖”,通过他们在多伦较为熟悉,并且固定的关系和供货商号,从“供垫”商铺赊出货物运到牧区零售,待货物出售完毕,再回到多伦诺尔提货,提货时将上次赊欠的货款结清。如此一来,双方在长期的贸易关系中建立了比较稳固的信任关系。以下诗歌将当时“出草地”商人的沿途景象及其内心感受描绘的淋漓尽致:
马嘶风壮出边城,
千里川原一望平。
白日鼯鼪跳客路,
斜阳驼马走荒城。
遥岑影与云天合,
极塞光分沙水明。
大地渺如江海阔,
远来车骑若帆轻。
由此可以看出,旅蒙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深入草原,辛勤往返于牧区和内地之间,开展贸易的艰辛与不易。“边城”、“荒城”、“极塞”、“渺如江海阔”等词汇揭示了他们对于边塞草原地广人稀与路途遥远的内心感受,而“远来车骑若帆轻”又描述了“出草地”商人牛马车队的络绎不绝。无论是坐商还是行商,他们用货物换取的牲畜并不及时赶回,而是选择分散在牧民家饲养,毛、奶等畜产品归牧民所有,繁殖的仔畜归行商或商号。部分商号还在牧区建立了自己的牧场,雇人为其放牧,商牧兼营。
这些行商和坐商“出草地”一般按季节出发,远程可以到达外蒙古和恰克图等地,春去秋回,每年一次。而到察哈尔和锡林郭勒盟地区的,则多按牧区生产季节、宗教庆典、祭祀活动和民族民间节日的不同时间,一年往返两到三次,大多在春节过后气候变暖时出发,农历六月返回,准备好货物后再次出发,到天气变冷时返回。而资本雄厚的坐商多在草原上设立分号。据公元1935年日本佐藤晴雄统计,多伦诺尔“出草地”行销于锡林郭勒盟北部各旗的商号有几十家之多。比如设在东乌珠穆沁旗的德隆泉、四盛昌、凝远合、兴隆瑞、世兴永、义兴魁;贝子庙的商号复兴振、永兴源、义兴魁;阿巴嘎贝勒府的义和长、义兴魁,以及西浩特旗、东苏尼特札萨克王府、西苏尼特札萨克王府等地的商号均属此类。
早期的多伦诺尔商业,按行业划分为四大行,即畜、皮、斗、货。畜业,是专门从事牲畜交易的行业,主要把从蒙古草原上收印票账得来的牛、羊、马、驼等各种牲畜赶到多伦诺尔,再销售到全国各地。皮业,是经销牲畜皮毛的行业,一些山西、直隶的皮毛匠春来冬归,为牧民和商人制毡、熟皮、裁剪缝制皮袄皮裤、制作靴子。斗业,是经销米、面粮食的行业。而货业,即指经销布匹、茶叶、日用百货等货物的行业。康熙允许内地商人进入蒙古高原从事商业贸易活动之后,很快,在十三行基础上,又逐步细分出细皮行、老山羊皮行、黑皮行、青盐行、米粟行、黑白铁行、运输行等行业。可以说,多伦商人的贸易,经营品种和范围十分丰富,从绸缎到五谷杂酒,凡蒙古人日常生活用品、消费品无所不备,无所不销,当时从锡林郭勒盟各旗运送到多伦诺尔的皮毛等,除供应本地需要,大多运销张家口、山西、天津等地,当地的各种货行则充当了内外贸易的交流纽带。
原内蒙古自治区商业厅1957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清光绪年间(公元1821-1908年),多伦诺尔的商业行业多达63个,商号4000多家,殷实商号3000多家,其中包括绸缎、布匹、皮毛、牲畜、珍珠、玉翠、烟、茶、百货、保险及钱行、当行等商行。①钟志祥:《“漠南商埠”多伦诺尔》,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第105页。发展到民国18年(公元1929年),商行种类进而增加到了300多个。根据《多伦县志》的记载,将这些商行的名称及行业类别统计如下:
银钱行13家:源顺昌、裕和魁、合盛魁、晋川达、聚得正、聚源厚、万兴成、信义银行、天兴顺、兴顺昌、广和长、福巨公、春发成
银行4家: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兴业银行、殖边银行
牲畜交易行3家:天顺店、巨元店、义盛店
生皮行20家:合顺永、德隆昌、同源达、裕和庆、同合义、大义中、大顺玉、裕兴德、亿生恒、宝华兴、德和恒、瑞德厚、振盛元、义顺德、聚兴皮房、义和公、巨发皮房、双盛德、源远长、长德元
白皮行8家:信泰元、信和诚、合义兴、双成、吉星皮房、正兴皮房、信记、天顺美
马尾铺1家:义成和
皮袄铺6家:永泰泉、复盛元、德元永、恒庆隆、英顺魁、四合源
皮鞋皮靴铺12家:万庆魁、恒心德、庆盛鞋铺、魁集义、黄庆、万庆德、恒祥魁、合兴靴铺、兴隆茂、巨义鞋铺、三顺永、庆盛享
毛庄11家:兴记毛庄、兴泰新、聚兴毛庄、聚丰恒、泰昌洋行、仁和洋行、福利洋行、互利洋行、成记洋行、平和洋行、广德兴
毡铺7家:永兴元、德胜利、茂盛德、福兴魁、华积祥、义兴源、德日成裕
毡帽行3家:德盛元、聚成玉、隆茂公
铜铺4家:裕合永、兴隆瑞、大成裕、庆盛德
铁匠铺8家:享泰德、和合元、万盛炉、永生炉、复和炉、福源炉、顺和隆、万庆炉
绸缎庄32家:聚兴长、祥发号、谦益号、义丰永、天兴顺、兴泰享、聚庆成、德源兴、源复兴、永庆丰、协成祥、同盛兴、大成元、王庆公、义丰和、复巨成、恒昌永、德和仁、永茂昌、庆兴公、德和昌、恒祥德、茂盛通、聚顺兴、恒盛裕、义和祥、天彰裕、三义成、长胜通、德巨祥、志成号、双和魁
布庄8家:兴顺成、义利成、宗祥号、义兴成、三义兴、恒德玉、同盛魁、广源成
新衣铺2家:维恒公、瑞兴成
茶叶行和茶食庄23家:乾享泰、永陞元、福记、天庆大、德茂长、崇义厚、源裕生、玉隆元、福泰魁、德泰魁、明盛高、万兴德、聚和元、崇茂涌元记、元盛昌、宏顺德、宏顺公、义兴居、福庆魁、独成玉、源福享、广元、富新昌
粮店13家:聚锦店、益昌店、庆盛店、大合店、义和店、裕盛店、天元店、义庆店、福泉店、世合店、聚隆店、敬业享、德顺店
面铺19家:广裕兴、四成店、涌兴店、复兴店、广兴盛、永发德、聚记、丰盛享、四合隆、永记、兴华新、合成店、永和恒、聚生泰、义兴公、德新店、庆德源、聚德源、协庆昌
木材行及木匠铺15家:德盛隆、德发成、德元魁、义盛兴、双盛泰、德润店、永兴泰、天森公、三庄德、三义德、同生义、永泰玉、公兴木局、天元森、聚成木铺
杂货铺15家:元兴魁、亿泰和、福和魁、天义魁、义元昌、晋忻长、永茂裕、恒盛和、天顺昌、广巨成、源德发、裕兴成、长盛豫、林长胜、长盛公
烧锅(白酒行)4家:广义店、金源涌、兴隆泉、德兴泉
肉铺3家:兴和成、义合德、义合公
洋货店2家:德茂隆、亿和裕
青盐行4家:德隆店、义和堂、庆成涌、万兴玉
醋油铺4家:元兴涌、荣源永、四合泉、万庆泉
饭庄4家:永和楼、万德圆、万成馆、裕香园
蜡烛店2家:义顺永、裕和永
煤油庄2家:生钰庄、长胜通
麻绳铺2家:静和成、天玉永
点心铺1家:思巨和
药铺4家:广顺李、义元成、德长魁、天叶吉
书局2家:北大书局、大兴书局
货栈4家:万顺增、公合栈、光昌栈、记兴栈
外商贸易2家:祥茂裕、庆昌合
旗商36家:德隆泉、万成魁、复兴振、恒裕、四盛昌、兴明魁、聚盛魁、德成玉、凝远合、源裕公、义兴魁、裕和兴、义和长、同德和、源裕隆、天顺义、庆昌号、万盛成、万义魁、敬兴魁、德顺魁、玉德盛、北义成、裕德长、义成元、世成西、聚合义、裕顺魁、福兴顺、义顺魁、世发隆、大兴昌、广盛荣、裕德永、隆泰昌①钟志祥:《“漠南商埠”多伦诺尔》,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第107-109页。
从上述统计来看,旗商有36家之多。“旗商”,是专门从事蒙古旗民买卖的商号。而绸缎庄、茶叶行以及生皮行所占比例也较大,可见中原汉人和蒙古牧民进行交易的主要商品种类为绸缎、茶叶、牲畜及畜产品,其中绸缎主要以河南曲绸、山东曲绸、苏杭绸和山东茧绸为主。皮鞋、粮店、杂货店、木材行和木匠铺次之,这也表明由于交换贸易的带动,多伦各类手工业也开始兴盛起来。而银钱行和银行的出现,则说明经过长期的贸易交换,他们已经从最初的以物易物交易发展为现金交易方式了,因此需要具备专门处理货币兑换和流通的金融机构。
其实,为跻身多伦诺尔市场经商贸易,早在19世纪中叶,一些俄国人就开始对多伦诺尔进行商务考察。清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古伯察、神甫秦噶哔一行对多伦诺尔的商业和宗教情况进行了了解,而后清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俄国涅尔琴斯克商人布金兄弟装备一支商队也来到此地进行了考察。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和十九年(公元1893年),拥有蒙古文学博士学位和蒙古文学教授头衔的俄国学者阿·马·波兹德涅耶夫先后两次在多伦诺尔进行了考察,并在其《蒙古及蒙古人》一书中,对多伦诺尔的商业、贸易、手工业、商业运输、关税、寺庙等情况,做了较为详细的调查记述。而后来的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6年),俄籍布里亚特蒙古人嘉木沙郎·也·马耶夫带领商队到多伦诺尔开展贸易活动,并多次到多伦诺尔考察和旅行,不久美、英、德、日等外国商人开始竞相在多伦诺尔开设洋行,经商贸易,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将多伦诺尔列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商业城市”。其中,主要有美国的美丰洋行、怡和洋行,俄国的联行洋行、金林洋行、雷福肯公司等。他们在多伦高价收购,垄断市场,大力推销洋货,如洋布、洋油(即上述统计中提及的煤油)、纸烟等。
再加上康熙、雍正年间,统治者先后从国库拨重金,支持喇嘛庙汇宗寺和善因寺的修建,使多伦诺尔很快成为整个蒙古地区的政治、宗教中心,由此围绕庙会的商业贸易也随之出现。据《锡林郭勒盟商业志》②锡林郭勒盟商业志编著委员会:《锡林郭勒盟商业志》,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5。记述:“寺庙经营的商业极为广泛,有解典库、店舍、铺席、酒馆、茶馆、金银器具、手工业,并常有贩运走私。”每年正月初六到正月初八、农历六月初一到十五、七月初七到十八,都要举行三次大型法会,后来逐渐演变为宗教、娱乐以及物资交流的草原盛会。庙会期间,漠南、漠北的蒙古王公贵族、草原牧民可以与上海、北京、天津、张家口等周边旗县的商号,甚至美、英、日等外国商人进行牛、马、皮毛、铜银器皿及金玉锦绣、日用杂货等商品的交流互换。
到清末,在蒙古高原进行贸易的旅蒙商达到高峰,可以说完全沉浸在了“蜜月”一般的繁盛状态中。而多伦诺尔这时也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漠南商埠”,“外番贸易络绎于此,而中外之货亦毕集”,“商贾骈集,泉货流通”①张鹏翮:《奉使俄罗斯日记》,神州国光社,民国29年再版。,很快发展成为草原上物资交流的贸易中心,以及沟通漠南漠北蒙古与内地经济交流的交通枢纽。贸易范围也日渐广阔,一方面连接当时的归化②归化:今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张家口、库伦、乌里雅苏台、恰克图③恰克图:今属俄罗斯、蒙古两国。俄罗斯境内仍名恰克图,蒙古国境内则改名为阿尔丹布拉克。等民族贸易城市,另一方面,辐射海拉尔、经棚、赤峰、乌丹、围场、丰镇等地广袤的草原零售市场。他们以多伦诺尔为中心相继开辟了多条赴草原贸易的商道:
1. 多伦诺尔——苏尼特草原——外蒙古库伦——恰克图
2. 多伦诺尔——乌珠穆沁草原——巴尔虎旗——呼伦贝尔草原
3. 多伦诺尔——乌珠穆沁草原——外蒙古车臣部
4. 多伦诺尔——赤峰——通辽——卜奎(齐齐哈尔)

图1 清代民国时期多伦诺尔市场辐射图
随着多伦诺尔商业中心地位的确立,许多商铺、商号进入草原的同时不断向多伦诺尔周边地区扩张和辐射,包括经棚、赤峰、乌丹、围场等周边的小集镇。聚集在多伦进行交易的药商远至云南和贵州等地,而上海和香港的马贩也赶到这里进行交易,使多伦进一步成为国内最大的药材、牲畜和马市之一。在这里集散的农畜产品,远销张家口,部分皮张、毛类运往天津等地,牛皮则销往东北地区。经棚、赤峰等周边城镇的农产品及加工成品也由此转运到张家口进行售卖。正如日本学者剑虹生所言,“多伦诺尔市街之地位,远至库伦,近入东蒙古,当中蒙贸易之冲,欲观将来蒙古贸易之发展,无过于此地也”。①转引自:钟志祥:《“漠南商埠”多伦诺尔》,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第110页。
四、悲情岁月:多伦旅蒙商的衰落
多伦旅蒙商,由“漠南商埠”多伦诺尔出发,驰骋于广阔草原的劲商队伍,终于在走过了整个清王朝的兴盛岁月之后,于20世纪初,步入了商业的寒冬,逐步走向衰落。民国肇始,辛亥革命爆发,外蒙古分裂势力于1924年宣布独立。再加上19世纪末,《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陆路通商章程》等条约的签订,沙皇俄国获得了在中国边界和内地自由经商,甚至在张家口、库伦等中国任何地方开设商店和行栈,享受免税优惠等特权,其商业活动迅速向我国西北地区扩张,形成了以库伦、科布多、乌力雅苏台为中心的商业运输网络,最终控制了从新疆到蒙古以至东北的经济命脉。
由此,旅蒙商在外蒙古的经商环境不断恶化,他们的处境受到外部压力和内部税收的束缚,已无力与外商竞争。外蒙古王公贵族赊欠旅蒙商货款拖延不付,甚至所欠高利贷的债权也被认为无效。与此同时,因通往内蒙古各主要驿站、路口捐税的征收,转运至多伦的牲畜和生活用品受到限制等,旅居库伦等地的多伦旅蒙商活动备受约束。民国9年(公元1920年),蒙古车臣汗桑贝司(子)地方发生变乱,多伦商人损失严重。《多伦商会档案》记载,旅蒙商乞求还债的禀文充满悲声,旅蒙商损失甚大。据多伦档案馆现存一份统计资料显示:这一年多伦商人在桑贝子地方损失财产285005两。②数据来源:据多伦档案馆相关数据整理。另据不完全统计,同年,在桑贝子地方,义盛公等16家多伦商号数十万财产被抢劫;巨和长号在达赖贝司损失财产8100两;四合隆号在达赖贝司损失财产14305两……③数据来源:据多伦档案馆相关数据整理。
民国初年,多伦又陷入了战乱频繁局面,由于多伦诺尔地处南北交通枢纽的重要位置,过往、驻扎军队较多,其军需供应不足,就需要就地自筹军饷,向当地借款借粮、摊派柴草,但他们大多都是有借无还。比如,民国13年(公元1924年)十二月,察东镇守使署为垫发淮军四五两个月的军饷,向多伦县商会借款10000元之后就再无踪影。迫于供应兵差,多伦商会只能随时印刷商票藉以周转,最终积成百万巨债。加上一些军阀军纪不严,对当地商人强征、强派粮款,使多伦商民面临较大损失,多伦诺尔商业几近陷于停顿。
自此,内忧外患使得前来多伦诺尔朝拜的漠北民众急剧减少。民国十四年(1925年),政府又停止了对汇宗寺的经济支持,这样,自清朝以来一直对喇嘛教采取扶持政策,得益于庙会带动旅蒙商经济繁荣的有利条件也消失了,市场需求量开始大幅下降。多伦的政治、宗教中心地位已名存实亡,进而使其商业贸易受到了极大冲击。最终,因政治、宗教、经济等多重原因,雄踞于草原上几百年的“漠南商埠”,及由此出发进入边疆开展贸易的旅蒙商从此日渐陨落了。
五、尾声:关于多伦旅蒙商的反思
历经300多年的兴衰历程,多伦旅蒙商在中国民族贸易史上写下了凝重的一页。这既是一部促进民族经济、文化、宗教交流发展的文明史,也是一部旅蒙商人辛勤谋生的奋斗史。站在历史的长河中,反思多伦旅蒙商的作用和意义。首先在于旅蒙商依托其重要的商业地理位置,通过对周边城镇、草原边陲重镇,甚至南方城市和国外城市的市场辐射,实现了草原游牧经济与内地农耕经济的互补。多伦旅蒙商的经营几百年经久不衰,从根本上讲,是由于农牧两种生产方式相互补充的需要,尤其是牧业经济对农业经济的依赖。他们不远千里,越过长城,携带牧区所需的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深入草地,不仅满足了牧民对内地农产品、手工业产品的需要,而且对牧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扩大了牧区牲畜和畜产品的销路,做到互通有无。进而使当地畜牧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得到了提高,人们的商品意识也大大增强,形成商业、手工业、农业等多元化经济结构,比如一部分兼营手工业的旅蒙商将中原地区的酿酒、榨油、制碱、制笔、制毡、制衣及熟皮子、擀毡子等技术教授给牧民,促进了草原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使牧民开始从单一、粗放的游牧经济生产经营中分化出来,到城镇从事畜牧产品加工业,运输业、采捞盐业、经营采矿业及商业等。其次互通有无的经济关系也促进了内地经济的发展。从明末马市开放以来,尤其是清代旅蒙贸易兴盛之后,蒙古草原地区成为内地手工业产品、农产品销售的广阔市场,每年有成万匹粗布和几十万箱砖茶销往牧区,大大刺激了江南地区棉纺织业、茶叶种植及加工业的发展与繁荣。因此可以说,江南地区棉纺织业、种植业等行业的兴盛和发展与草原市场的开发有必然联系。由多伦旅蒙商开通的贯穿东西南北的多条商道,也自然成为“草原丝绸之路”贸易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旅蒙商在蒙古草原的活动,又进一步促进了内地汉文化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交流。旅蒙商在贸易交流中学会了蒙古语言,了解了蒙古人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同时又将其他民族文化带到了草原,丰富了蒙古牧民的生活,改变了牧民常年以放牧为主的单一生活。许多旅蒙商不仅“习蒙语、行蒙俗”,且“入蒙籍、娶蒙媳”,与蒙古族融为一体,客观上起到了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旅蒙商的商贸活动也带动了草原城镇的发展和边疆的开发。以外蒙古的库伦为例,从有关旅蒙商的档案中发现,除官署衙门和寺庙等建筑外,其余基本都是旅蒙商的店铺。可以说,没有旅蒙商的活动,库伦也未必有今天的规模与地位。本是屯兵要地的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也因旅蒙商的活动增加了经济发展的活力。而恰克图则更是因为旅蒙商的贸易活动形成了重要的边贸市场。多伦诺尔、锡林浩特、海拉尔等北部城市,也因此逐步形成了草原牧区的经济中心,可以说借助多伦旅蒙商到来的有利契机,一些大中草原城镇也开始迅速崛起。
然而,当我们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应看到其不足。比如旅蒙商在对蒙贸易交换中,长期严重的不等价交换和高利贷剥削,使蒙古牧民的财富大量流失。加之旅蒙商每年秋天到牧区收账时,对收购的牲畜挑选极其苛刻,这使牧区牲畜的质量提升受到影响,对牧业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同时,在与蒙古人持续的商品贸易活动中,旅蒙商队伍的不断壮大也带动了许多内地居民移居草原,他们将农耕技术和农耕文化传播到蒙古地区,导致牧区草原被大量开垦,农耕面积不断扩大,蒙古人的游牧生产受到了来自农业社会的冲击,从而使农耕生产方式和游牧生产方式展开了持续不断地碰撞和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