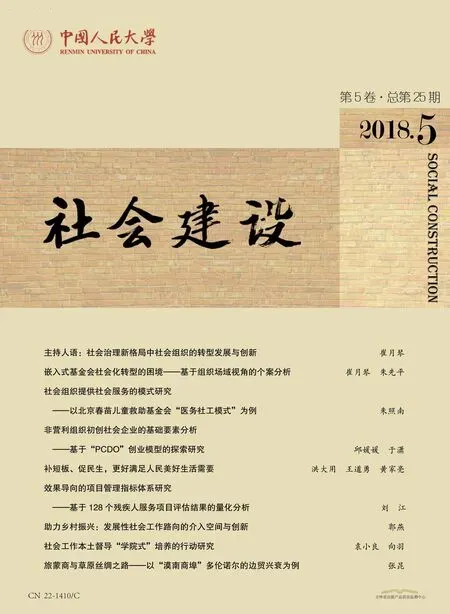社会工作本土督导“学院式”培养的行动研究*
袁小良 向羽
一、引言
督导(supervision)是一种借助互动过程进行专业训练的方法,是由机构指定的资深工作者(督导者)对机构内的新进工作者或学生(受督导者),藉由个别或团体的定期或持续的互动方式,传授专业服务的知识与技术,以增进被督导者的专业技巧,充分发挥其所能,以确保机构政策的实践,并提升案主服务的品质①黄源协:《社会工作管理(第三版)》,台北:双叶书廊有限公司,2015,第464-465页。。始于1878年的社会工作督导(social work supervisor)在社会工作领域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140年来,社会工作督导特征随着社会时代的变化而有所不同②徐明心:《社会工作督导的渊源:历史检示(The roots of social work supervision:An historical review)》,邹学银译,《中国社会工作》,1998(5)。,“发展及维持高水平的社会工作实务”是其始终不变的精神内核③香港社会工作者注册局:《社会工作督导指引》,2009。。作为社工人才梯队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工作督导无论是在整合理论与实务、发展专业自主与自我能力,还是在培养专业意识与专业价值观、提升服务素质与管理能力等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亦被视为社会工作对社会主要贡献之一④Kadushin, A., &Harkness, D. Supervision in social work.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近20年来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工作督导在实务上存在大量的缺口外,研究也非常薄弱。①李晓凤、黄巧文、马瑞民:《社会工作督导的历史演进及其经验启示——以美国、中国深圳社会工作督导实务为例》,《社会工作与管理》,2015(6)。张洪英②张洪英:《中国社会工作督导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以1998—2015年CNKI期刊论文为样本》,《社会工作与管理》,2017(4)。指出,针对社会工作督导的论文总计约86篇,数量极低,核心期刊论文仅有6篇,且研究以经验研究为主,主要聚焦于现状与改善、理论应用以及境外经验引介等关键议题,行动与研究之间存在着“断裂”的现象,尤其是中国本土督导培养模式方面的研究更是薄弱。
作为珠三角社会工作发展的后起之秀,X市2009年被列为第二批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城市,2013年被确定为首批全国社会工作服务标准化建设示范地区,在2006-2018年期间X市无论是机构的数量还是社会工作者考试通过(从业)人数均获得了飞速的增长。③民政部:《2018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mzyw/201506/20150600832371.shtml然而,在社会工作超高速发展的同时,X市的社会工作督导并未有获得同步的发展,成为社会工作行业发展的薄弱环节。为应对“督导荒”,X市于2014年采用“学院式”模式展开启动社会工作本土督导培养。“学院式”是政府透过项目购买,由承担机构以项目运作的方式,透过招募学员、聘请师资、设计课程、组织考核等途径培养本土督导人才。本文试图通过对X市的经验研究回答“学院式”本土督导培养模式的过程是怎样的、能否实现培养本土督导的目标等本土督导培养模式中的核心问题,并尝试弥补督导研究中行动与实践的断裂。
二、研究方法
笔者及所在研究团队是X市2014至2016年“学院式”培训的组织和参与者之一,在实践的过程中面临一系列的困惑:“学院式”本土督导培养模式的过程是怎样?如何通过“学院式”的方法培养本土的社会工作督导?“学院式”督导培养模式能否满足行业的需求?这种模式有哪些经验?又会遇到怎样的挑战?上述种种困惑一直萦绕于心。笔者及所在研究团队一方面既要作为实践者推动培训课程,另一方面又要作为研究者回应实践的困扰,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成为解答上述困扰相对契合的方法。
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由美国Kurt Lewin及Stephen M. Corey等人在20世纪40年代所倡导,在50年代盛极一时,随后60年代远播欧洲,被英国的L. Stenhouse、J.Elliott、W.F.Carr以及澳洲的S.Grundy、S.Kemmis的完善修正,推动了行动研究在80年代在美国、英国以及澳洲等地区的盛行。④McTaggart, R.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7.总的来看,行动研究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研究方法⑤袁振国:《教育研究方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第6页。,它强调社会情境中的实践者“行动”与“研究”相结合,为了加深对改善社会的合理及正义或增进实践,而进行的一种协同、自我反省的研究形式,以求得专业的成长与进步,而研究的过程中,实践者采取质疑和批评的态度,不断的反思。⑥Atweh, B., Kemmis, S.,& Weeks, P. (Eds.)Action research in practice.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行动研究实施的设计,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行动研究过程模式,例如Lewin的螺旋循环模式、Kemmis和Elliott的模式、Eubbtt的可回复性历程模式、McNiff的衍生性螺旋循环模式、Somekh的自然螺旋模式等。总的来看,不同模式之间大同小异,一个典型的行动研究基本的元素包括:第一阶段的计划(Plan)、行动(Action)、观察(observe)、反思(reflect)、第二阶段修改计划(Revised Plan)这五个核心元素。①Dan MacIsaac.An Introduction to Action Research,http://www.phy.nau.edu/~danmac/actionrsch.html

图1 行动研究的典型模型
以行动研究的典型模式为研究框架,X市2014至2016年的督导培训可以被视为一个“行动”,2014年的督导培训为其第一阶段,在项目执行近一年里,依次经历了项目计划、项目投标与项目实施(学员招募、组织教师、预约场地、现场授课、课程评估等),项目观察与项目总结(反思);2015年为督导培训的第二阶段,根据第一阶段的反思和不足,第二阶段的培训课程在课程体系和课程考核有所调整,其他诸如学员招募、课程分类、授课教师等基本延续;2016年为督导培训的第三阶段,受制于项目预算的缩减,这一阶段的培训课程受到一定的压缩,实务督导的课程整个体系基本是2015年的延续。
笔者及研究团队2014至2016年既作为整个培训项目行动实践者,参与X市“学院式”社会工作督导培训实施每一个环节,同时又作为研究者,在每阶段课程结束时对参与督导课程学员进行半结构深度访谈,了解学员对整个课程的反馈。在尊重学员自愿参与的前提下,基于立意抽样原则,综合考虑学员的性别、工作年限、职务、服务领域、所在机构规模等要素,向潜在的研究参与者发出邀请,在每一期培训课程结束后进行面对面访谈。访谈主题包括:学员报读督导班的原因和经历;学员对督导培训班的总结和反思;学员的督导/被督导经历,及其对督导的理解等。2014年至2016年,笔者及研究团队陆续共成功访谈了17名学员,每人访谈时长约2小时左右,累计整理逐字稿253123字。本文试图从学员“局内人”的角度描述“学院式”社会工作本土督导培养过程,并对其形成的经验、遇到怎样的挑战等问题进行总结和反思。

图表 2 研究参与者基本情况
三、“学院式”本土督导培训体系
与本土督导的“广州模式”一样①本土督导的“广州模式”是指本土督导人才培养以项目化方式运作,由承办方邀请相关老师,以“学院课程制”方式对督导学员进行课程培训与实习练习,最终根据学员表现取得相应的督导资格,该模式以广州市的做法最为典型。见张莉萍、韦晓冬:《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实践:督导人才培养研究报告——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X市“学院式”本土督导培训由X市民政局出资通过政府购买,中标的Y高校以项目运作的方式,透过招募学员、聘请师资、设计课程、组织考核等途径培养本土督导人才。
(一)课程目标
承接方Y高校历年关于项目的总结报告均指出,该课程目标旨在“开展全市社会工作督导专业人才关于督导工作的方法、技巧等专业知识培训。通过社工督导培训提升学员对社会工作的认识,掌握社会工作管理技能和督导技能,强化落实社会工作政策措施的能力,带动全市社工作的健康发展。”
由于是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在历年的招标需求文件中,均对督导培训课程的内容、人数、课时等指标做出一定的要求(如图表3)。

图表 3 2014-2016年X市社会工作督导培养项目预算及指标
(二)课程体系
在课程体系设计方面,三年的课程大纲体系和内容基本参照高校社会工作督导课程,每一年略有微调。
2014年,承接方的总结报告指出,鉴于社会工作督导三项功能①Kadushin, A., &Harkness, D. Supervision in social work.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2.,设计了“社会工作行政督导课程”和“社会工作实务督导课程”两个平行班,让前者发挥督导的“行政功能”,而后者发挥“教育功能”和“支持功能”,前者针对社会工作相关专业背景以及在政府部门等担任行政社会工作角色的学员参加,后者则只限社会工作专业及在职社会工作者参加。两项课程的课时均为90小时或以上,没有社会专业学历之学员无法参加社会工作实务课程,但持有社会工作专业学历的同工可修读两项课程,总课时超过180小时。
社会工作行政督导班的课程内容,主要是社会服务机构行政管理、督导理论和督导技巧;社会工作实务督导的课程内容,主要是社会工作方法、社会工作理论以及督导理论和技巧。这两个班级的任课教师“清一色”由香港、澳门的资深社会工作者担任。这两个课程为周末开班,课程之间相隔两个月,整个课程在一年内能完成。学员通过课程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1)出勤率达到课程总时数的70%;2)完成所有的小组或个人作业;3)通过课程闭卷考试。
2015年,课程体系在延续中有所调整。具体来看,延续了之前行政督导班与实务督导班的分类和对象、培训大纲和内容、授课师资以及授课方式;在此基础上,压缩了行政督导班的课程时数,同时强化了实务督导班的要求,例如增加了机构推荐实习和实习答辩的环节。也即,实务督导学员需要在出勤率达标的基础上,参加笔试考试,在通过笔试的基础上通过机构推荐以及本市社协的筛选,才有资格进入实习,在完成实习要求(实习时间不少于168小时,同时必须完成个案、小组及活动的其中2项及1项行政项目)的基础上,还需要通过答辩委员会组织的口头答辩(如表4),如此才能够获得督导资格。

图表 4 X市2015年本土实务督导课程体系
2016年,受购买金额的调整,这一年完全取消了行政督导班设置,实务督导班的课程课时有一定的压缩,整个课程体系完全沿袭了2015年实务督导班的课程设计体系、课程内容、授课师资和考核方式等。
(三)结业学员
课程推出时,X市尚未有实务督导相关配套政策和设计,每期课程均受到行业的“热捧”,课程前期参与者“场场爆满”,但是到课程后期,通过者“寥寥无几”。
2014年,参与实务督导课程大致85人左右,行政督导课程大致70人左右。然而整个一年的课程结束后,最终仅有19名学员顺利通过考核,其中10位来自实务督导班,通过率约12%;9位来自行政督导班,通过率约13%。
2015年,参与实务督导班66人,在本课程内出勤率高于80%的学员,且参与并通过期末考试(>60分),机构同意推荐实习,并获得主办方和珠海市社工协会的遴选,最终完成实习,且在实习总分通过(个人平均分>60分)的学员为14人,通过率为21%。
2016年参与实务督导班63人,在本课程内出勤率高于80%的学员,且参与并通过期末考试(>60分),机构同意推荐实习,并获得主办方和X市社工协会的遴选,最终完成实习,且在实习通过答辩(个人平均分>60分)的学员为21人,通过率为33%。
四、“学院式”本土督导培养面临的挑战
(一)参与学员的经历参差不齐,影响其对课程内容的学习和理解。
“社会工作督导即为专业,从人力资源管理角度看,就应有其专精的教育与训练过程,而非只要资深就能担任”①徐雅惠,张英阵:《风险管理下的社会工作督导》,《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刊》,2016(2)。。要成为社会工作督导并不容易,“督导者必须接受过充分的专业教育,以及有丰富的实务工作经验,尤其对督导知识和技术应有深入的认识”②黄源协:《社会工作管理(第三版)》,台北:双叶书廊有限公司,2015,第464-465页。。为了应对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指标要求,该项培训计划对参与人员的资格筛选并不严格,每期参与督导培训班的人数皆在60人以上,参与者的来源具有较高的异质性,专业素养参差不齐。三年的督导课程学员既有来自服务机构的社工,也有政府单位、社会团体的职员以及部分高校教师。尽管执行方和X市社工协会每年均会对课程报名学员按照课程最低标准“一刀切”进行筛选(例如至少2年的社会服务经历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每一年参与课程的学员无论在专业、社会证书、工作年限、职位、服务领域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这种差异影响到学员对课程内容的学习和理解。
我知道协会那边说是有一定的分类:刚刚入行的社工,两年以上的社工,也有总干事级别的,但是好像我没有看到内容上有多大的区别,因为毕竟我们做的时间不一样,我们所接触的东西,我们的需求都是不一样的。(P-13)
对学员的分类,就像刚刚讲的,又是科班出身,又做过实务,然后现在大概到什么年限,这一类人,授课的难度或可能偏重侧重点是什么,然后剩下的是非科班出身,可能社会经验比较多,但对社工的认识比较少,他可能是有其他的长处,那么需要给他补的是社工的什么东西,可能他不需要那么多的沟通,他可能不用社工的方式但他其实还是很懂看人。(P-17)
(二)课程体系定位模糊
就课程体系设计来讲,学员认为督导班整体的课程体系设计应该“真正地去站在用户的角度,从学员的角度做这种精心的设计”(P-3),但是现有的课程体系“不接地气”,“确实是比较散,比较乱,而且真的是没有针对我们的学员”(P-3)。学员的访谈显示,整个课程体系因为学员的对社会工作知识掌握的差异,导致课程体系在“基础知识普及”以及“督导能力提升”两者之间摇摆不定。对于非社工专业或在社会工作服务经验不足的学员来讲,督导培训课程的课程目标设置太高,整个课程就成为“社会工作基础知识普及”;对于在社会工作有一定积累的学员看来,这样的课程设计无法回应学员对提升督导能力的期待,整个督导培训沦为简单的“扫盲班”或复习。
在课程设计里,我感觉到就是更倾向于这些基础的知识的掌握。其实我不是社工专业的,对于我来说可能是要学很多的东西,但是真正的要到实践中去我就会发现其实后来老师说的东西都是我们平时工作中基本要掌握的东西。(P-11)
我一直不太清楚整个督导培养的目标是什么,课程的培养目标是知道这种知识,还是具备这种能力能够成为一个督导,这个是两个概念。现在我觉得督导班是社工扫盲班,因为很多来参加的人,其实第一个非科班出身,然后第二个他没什么社工工作经验,然后第三个,有的只是刚刚考了证而已,那如果像这样的一些人学完课程就能够成为督导,这是值得反思的?……整个课程设计不接地气,其实光看他的课程名字,我觉得还是蛮吸引的,然后一来听课程,就觉得已经是香港老掉牙的东西,还拿过来讲。(P-6)
关于实务课程的内容是挺充实的,那种概况性会比较多一点,但是在安排课程上可能就只有一两节课,讲的不是很能够展开,里面很多想听我们想探讨的内容没有机会展开。……内容上面对我自己来说是相当于是一种复习。(P-15)
如何培养社会工作督导?社会工作督导培训的目标是什么?培训的内容是什么?不单是X市参与培训的学员感到“疑惑”“混乱”,培训主办方对此的认知也不清楚。
(三)培训教师体系“水土不服”
三年督导课程的授课教师,均是“清一色”来自港澳地区在社会工作领域近20年左右的社工或老师授课。从学员的角度来看,听港澳老师讲课喜忧参半。有学员认为港澳的老师案例和实践比较多“我还是希望请香港那边的,香港那边毕竟案例比较多,做的时间比较长嘛,或者澳门也行啊,实战比较丰富,反而国内社工这一块也就七八年、十年的事情,……真的实践比较少一点,可能理论派多一点。”(P-1)“我发现课程努力请一些有二三十年经验的老社工来,我觉得这个很好,让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对这个行业的情怀,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P-13)。然而,也有一部分学员指出港澳老师“不接地气”,对X市缺乏了解,希望听到更多本土老师的声音: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本身语言有欠缺,第二个他们不接地气,就是有一些办法不能直接搬到大陆来做,对吧,就是上课的话,我就是来帮助你的学生,因为我是有这个能力的,但是你对我们的学生并不了解。(P-3)
不要请香港那边的。因为他们讲的有些是不适合这边的。他们香港有的政策什么的,跟我们本土这边是不一样。可能他讲的有的东西,在他们那边是很好的。其实在这边不是很适用这样子。(P-9)
就我个人来说,特别是在之前我是做农村项目的,那我肯定是愿意去听像张和清老师这样的课,但是我在接触香港老师的时候,反而我告诉她的事情会比较多一些。(P-13)
(四)课程内容脱离实际
尽管承办方围绕价值观、知识、技巧三个层面设计课程内容,对学员来说,整体课程无论是整体设计抑或课程内容涉及的案例仍旧过于“理论”,缺少与在地的联系和情境;对学员来说,技巧的部分与学员的实践有一定距离,学员也认为比较偏理论。
第一,是它的内容是非常的香港化,在过往,在深圳,在广州,我们临近的区,做督导培训,虽然说会是有香港的,但一定是本土化的。……你请来的老师非常优秀,但是他们在讲的内容和方式几乎是没有考虑到内地国情,他们所有的案例教学完全就是照搬香港教材,几乎和本土没有任何联系,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的话,至少说不管你老师的背景是什么,但是你应该针对你学员的情况,他们的经验和水平,可能还有你们本身的课程目标,他应该是要去做教学的调整,整个课程体系的设计,和他的这个课程开发。第二,课程里边理论的东西非常多,实操部分比较少,实操的部分也都是用理论的方式来讲的。(P-6)
另外,对学员来说,在课程内容层面,他们希望在课程中可以结合一些本土的信息或实践,课程内容能够回应机构或学员其所处的发展阶段。港澳老师虽然经验、资历略胜一筹,在授课过程中受制于语言(粤语)以及彼此文化制度的差异,对学员来说,在理解上存在障碍,在实践上可借鉴的有限,从而造成一定的脱节。
对设置的课程内容来说,记不起来全部的,只能说课程中有的有用,有的有一些脱节。(P-9)
还有制度的障碍,因为我们的制度跟港澳的不一样,所以他讲的有些不是很实用的,香港澳门很多东西很完善。但是,这几年,大陆特别是珠三角的社工,发展得很快,有些社工机构已经很完善了。他们再来讲更好,而且沟通没障碍。(P-10)
给我们上课的时候,我感觉在国家政策的掌握和我们社会工作和政府的这些关系方面,我们和香港存在很大的区别。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去学的话,香港的那些老师不会体会到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存在的那点难处。……我个人认为啊,专业知识,很多理论上的东西,和我们实际的操作还是会有一点点的距离。(P-11)
香港老师确实是很专业,但是我觉得香港老师来之前可能需要对我们相关的一些政策,项目啊,去了解一下,……培训内容可能就是要更加结合实际一些,我们一些社工机构还比较年轻,刚刚起步,顶多三五年的历史不算很长,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老师的课程讲的太过于深,太高大上的话,跟现在她们所需要的东西不符合。(P-4)
社会工作督导强调的是应用性与实践性。X市督导培训课程过于理论化,一方面导致参与学员接受困难,另一方面空谈的理论抽离于具体的实践情境,参与者并不能真正获得“督导的能力”。
(五)课程考核量化单一
三年的督导培训课程,在考核上遵循“宽进严出”的理念,设计了考勤、笔试、推荐、实习、答辩等考核模块,每一模块的考核形式相对量化和单一,例如2016年考核出勤率模块需要高于80%,且期末笔试需要大于60分,机构同意推荐并完成168小时的实习,实习答辩评委平均分需要大于60分。对学员来说,出席培训课程会面临一定的时间冲突,特别是对于绝大部分学员是在职,需要平衡工作与学习,对于部分作为机构核心负责人的学员来说,出席课程面临较大的难度;
课程是连续三个月,连续三个月这样子,学员会奔溃的。……大部分学员是在职的,在职的情况之下,如果你是一个月搞那么两天然后集中学习,或者说有时候分开一下,一个星期一天,相对来说还好安排一下,经常是一个星期还安排工作日两天的时候,而且关键还和其他培训有冲突的时候,我去这里还是去那里。(P-6)
对于笔试环节,非专业的学员认为理论理解有一定难度,并且即使考过也不能理解和应用;对于社会工作专业的学员来说,考试这种“一刀切”看似相对标准的方式,只是衡量督导能力的一种,而不能代表督导的综合能力。
考试,大多数都是理论知识,考试是过了,但是就是感觉在用的过程中就会一个是很遥远,另一个就是我真的不理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一味地只给我用理论去讲解,没有实实在在的案例去讲解分析是不可以的,那么我对这个东西的理解就真的是不到位的。因为我在工作的过程中,也只接触到了三个项目。(P-8)
考试培训这件事情,因为是一刀切嘛,反而你很难去选出真正的督导,有督导能力的人,因为你这个一刀切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在里面,其他地区的督导培养可能都不是这样子的,它会更多的可能不是培训班的考试,督导的考试可能有笔试和面试,甚至团体面试等等一系列的环节的,通过这样一些环节,去看这个人的综合能力,也就是说,成为督导的路径是多种的,不是只有一条考试的渠道,……考试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标准化的操作方法,可以看得到你比较基准的水平,但这可能是作为基础方法,只是其中之一,我个人觉得督导本身是非常个性化的事情。(P-6)
对于笔试后的实习,对学员来讲,需要平衡本职工作与实习任务的挑战。
实习的时间,确实是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边去完成这些实习的内容,在量或者是又想保质保量的话,就是确实挑战比较大。……自己本身也有工作,也有需要支持一下同事的这个事情,就很难做,又要回应外界对你这个项目或者你要公平啊,这个人你不能说他为了参加自己的实习,他工作都没有做完,一个项目里边你不做就我做,要么就是全都受影响。……本来参加这个训练的同事就是比较核心的同事,如果他的重心和精力不在他工作上的话,其实对工作都是挺大的一个伤害的。(P-17)
该项目督导培训计划虽然安排了“实习任务”,即要求参与学员回到原来的机构中担任“实习督导”,并完成指定的“实习任务”。但该过程如何观测?学员是否真正运用了“督导知识”?是否扮演了“督导角色”?是否锻炼了“督导技能”?不得而知。
学员参与了督导课程,部分还通过了最后的考核,但“通过培训考核”是否就意味着他们具备了督导的资格和能力?能够在具体的服务实践中扮演其“督导角色”?一方面,这种“学院式”的督导课程架空、抽离于现实情境,仅从理论、知识上教育学员“社会工作督导”,不能让参与者真正获得督导能力。另一方面,完成督导培训的学员是否有“扮演督导角色”的机会,继续锤炼督导技能?这需要通盘考虑。据研究者了解,在这批督导培训完成后,X市的服务项目督导仍然以“外聘督导”为主流。
五、本土督导培养何去何从
通过对X市三年本土社会工作督导“学院式”培养过程的行动研究发现,在学员筛选、课程目标体系设计、教师配备、课程内容、结果考核等均面临一定的挑战。
从督导培养过程来看,作为道德实践的社会工作督导理应发挥传承社会工作使命的角色,但是X市本土社工督导的实际培养过程中变成了流于程序的“训练有素的无能”(trained incapacity)。凡勃伦(Thorstein B Veblen)用此概念表示科层制中墨守成规的趋势,成员依赖既有的规章制度,并且以机械的、缺乏想象力的方式执行。默顿(Merton,Robert K.)则进一步指出科层制的效率只针对例行事务,因而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造成了刻板僵化、墨守成规,一旦特殊事件发生,既定条件改变,便反应迟钝,动作迟缓。X市三年“学院式”的本土实务督导培训,从项目投标-学员筛选-课程设计-教师授课-课程考核等过程中,看似“训练有素”殊不知最终却造成学生“训练无能”的结果。整个培训过程流于形成,奉行如保罗·弗莱雷所批评的“灌输式教育”(banking education),课程体系目标偏离,课程内容更多是向学生灌输知识和学生死记硬背知识,而学生存储的知识越多,其批判的意识就越弱;学生被灌输的越多,其创造力也就越低,越不能培养其作为世界改造者对世界进行干预而产生的批判意识。他们越是原原本本地接受强加于其身上的被动角色,就越是只能适应世界的现状,适应灌输给他们的对现实的不完整看法①保罗·弗莱雷:《被压迫者教育学》,顾建新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从督导培养的考核来看,X市三年的“学院式”本土实务督导培训考核途径单一,屏蔽了督导能力呈现的其它可能。Allan Brown & Iain Bourne认为,督导的养成主要受几个方面因素:家庭及学校的个人经验;专业实务工作经验;担任受督导者的经验;担任实习老师或督导的经验;工作和学习风格的发展,学习其实只是督导养成的因素之一。②Brown A G, Bourne I. The Social Work Supervisor: Supervision in Community, Day Care, and Residential Settings. Open University Press,1996.
基于对X市三年本土社会工作督导“学院式”培养过程的行动研究,笔者就中国本土督导培养模式的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社会工作本土督导培养应定位于道德实践的本质和使命传承。从本质上说,社会工作督导不仅是一种专业实践(professional practice),更是一种道德实践(moral practice)。③朱志强:《社会工作的本质:道德实践与政治实践》,载何国良、王思斌主编:《华人社会:社会工作本质的初探》,香港: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0,第89-94页。因此,作为社会工作人才梯队资深工作者的督导培养目标应定为于“有责任知道了解社会工作的传承,并对被督导者传达其中的意义。这种传承感不必得以技术性的方法表达,而可以以一种哲学的和实践的方式提供实务工作者的使命感。由此观点经验督导的实务工作者将获得激发,使其在工作上更有效力,也比较不会丧失信心、理想幻灭并感到孤立,以至于在社会工作专业主义中失去自尊”④Munson C E. Handbook of clinical social work supervision[M]// Handbook of clinical social work supervision /. Haworth Social Work Practice Press, 2002, P13-19.。
第二,社会工作本土督导培养要结合国际社会工作督导训练的标准和本土实务情境需要,厘定本土社会工作督导的能力结构,并开发相应培养课程体系。社会工作本土督导培养过程中,除了社会工作督导一般理论和模式外,更应注重探索社会工作督导理论和模式的本土化,充分考虑中国社会文化特性和社会工作服务情境,从中建立与发展出一套适合本土情境的督导方法与技巧;打破理论与实践、教育与实务落差,在教师与学生之间建立双向对话机制,发挥学员的主体性和批判反思性精神,推动构建包括个体脉络、机构脉络、社会大环境和国家政策制度脉络、国际专业话语脉络,以及物理场域脉络、文化脉络和知识体系脉络等在内的多元多重的本土社会工作督导脉络体系。⑤张洪英:《中国社会工作实习督导模式的发展——以山东济南为例》,香港理工大学博士论文,2011。
第三,社会工作本土督导培养应该建构起完整的体系。社会工作督导是社会工作实务教育中非常重要的环节,美国《社会工作百科全书》中提出:督导是社会工作专业的传统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将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与技术由训练有素的社会工作者传授给新的社会工作者或实习生。社会工作督导被认为是弥补教育与实务断裂(gap)的桥梁。因此,社会工作本土督导的培养理应构建衔接教育与实务的完整体系。其一,学校教育与在职训练体系贯通。帕蒂和奥斯汀提出要增强督导教育计划,包括“发展机会让学生深入、有内涵地体验督导者的角色”、“发展机会和要求,让学生通过标准化测试方法或其他方式评估自己的督导管理潜能”,即学校要提供特定的督导课程以协助学生获取日后成为督导者的必备的知识和发展技能①雷克斯·A·斯基德莫尔(Rex A.Skidmore):《社会工作行政-动态管理与人际关系》,张曙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233-247。。其二,培训教育与实践运用体系贯通。本土督导的培育应当结合“学院式”与“师徒式”两种模式的优点,既强调督导知识的传授,也强调不脱离实践情境的过程陪伴,在协同行动中建立督导者的能力。不单接受“督导课程培训”,更要打通“实践体系”,让参与督导培训的学员真正有机会参与督导实践。
第四,社会工作本土督导的培养应该注重持续性的过程。在研究者看来,加紧培育一支本土社会工作督导队伍无可厚非,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通过“学院式”快速催生一批所谓的“社会工作本土督导”有“急功近利”的嫌疑。社会工作本土督导的培育应当与社会服务发展一样保持“战略定力”,不要追求短时间内培育出多大规模的本土督导人才,而是严格把控参与者的数量与质量,精耕细作,持续培养。社会工作本土督导的培育不是凭借“一次性的培训班”来完成,而是一个持续性发展的过程。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完成“督导培训”获得“督导资格”并不意味着督导培育的终结,对督导者的持续性的进修、教育和培训也应构成一个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