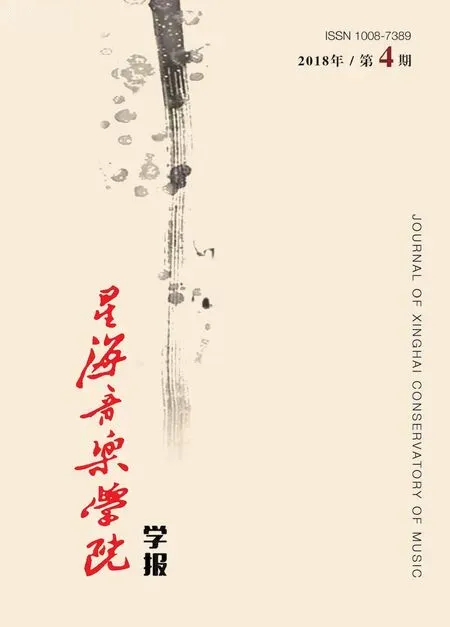读书笔记Ⅰ:“音乐的耳朵”与超生物性感官
——重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相关内容并及赵宋光人类学本体论思想讨论
韩锺恩
卡尔·马克思在其早年著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给出一个后来常常被相关学界同仁随意引述并误读释解的词语:“音乐的耳朵”。
引述释解者,主要在艺术学、美学、哲学乃至音乐学、音乐美学、音乐哲学等诸多研究。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写于法国巴黎,史称《巴黎手稿》(下文简称《手稿》)。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称:写于1844年4—8月,德文,第一次全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2年国际版第1部分第3卷[注][德]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3页。。
目前,据笔者所知的汉译文献者,主要有以下四种(按出版先后为序):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翻译,校订时参考其他文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根据刘丕坤译文校订,并承朱光潜、熊伟提意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3—181页。

4.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EconomicandPhilosophicalManuscripts),伊海宇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
在《手稿》中,从语言表述层面来说,其实,并没有“音乐的耳朵”这样一个术语,所呈现者,都是以否定方式进行修辞的陈述,比如:不辨音律的耳朵、没有音乐感的耳朵、不懂“音乐的耳朵”;而从理论论述层面来说,假如将其置放在整个上下文中间,即使以肯定方式进行修辞,其实,也只是哲学问题论述过程中的一个术语而已。因此,严格意义上说,“音乐的耳朵”在书中并非是有专属意义指向的概念。[注]按:在这里,有必要把术语和概念加以区分,参见王振复主编:《中国美学范畴史》第一卷中的有关叙述:术语是各门学科中具有约定俗成意义的专门用语;概念是一定事物与现象之特有属性的逻辑形式。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页。但是,却又切切实实构成了一个问题:究竟有没有这样一个有别于自然属性的“音乐的耳朵”?假如有的话,又是否可以扩至所有有别于自然属性的感官,并继续设问:这样一种有别于自然属性的艺术的感官,究竟是什么?
超生物性概念,出自赵宋光先生写于1975年的一篇文章(署名方耀),以《论从猿到人的过渡期》[注]方耀(赵宋光):《论从猿到人的过渡期》,《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6年第14卷第2期,第77—84页。关于此文,李泽厚:《试论人类起源(提纲)》(载《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9页)文注中提到,该提纲曾经于1974年与赵宋光先生多次讨论,并由赵宋光先生执笔成文,署名方耀发表。据赵宋光先生自己回忆:马克思并没有说人以外的物质是唯一的东西,他强调的核心还是人的活动。于是,在“生产力的核心是人的创新活动,是人的使用工具的活动”思想指导下,完成了《论从猿到人的过渡期》这篇文章。参见刘红庆:《耀世孤火——赵宋光中华音乐思想立美之旅》,济南:齐鲁书社,2011年,第75页。命题。这里,将此概念与感官一词相连缀:超生物性感官,再和马克思“音乐的耳朵”对应关联。
为了对“音乐的耳朵”这一术语有一个充分的理解以及相应的有效释解,这里,先辑录上述相关文本对这一术语的译释,以作为进一步诠释与讨论的基本依托。
《手稿》包括以下部分:
序言;
“第一手稿”:工资、资本的利润(包括资本、资本的利润、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和资本家的动机、资本的积累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四个部分)、地租、异化劳动;
“第二手稿”:私有财产的关系;
“第三手稿”:国民经济学中反映的私有财产的本质、共产主义、需要、生产和分工、货币、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注]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目录,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Ⅰ—Ⅱ页。
“音乐的耳朵”,这一术语出自“第三手稿”中的“共产主义”部分。
以下,仅辑录四个译本的相关陈述:
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注]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目录,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9页。
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注]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目录,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5—126页。
正如只有音乐才唤醒人的音乐感觉,对于不懂“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感觉)。[注]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节译),朱光潜译注,《美学》1980年第2期,第11页。
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伊海宇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第84—85页。
就翻译而言,四个译本基本上没有太大差异,然而,基于上述提问:究竟有没有这样一个有别于自然属性的“音乐的耳朵”?就必须进行文本还原,即将此相关陈述置放到其原本上下文中间去加以审视,以钩沉与考掘可能潜藏并隐义于其中的专属意义指向。限于篇幅以及不必要的简单重复,以下引述者,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本作为主体文本,在不发生重大歧义的情况下,其他译本不再赘录。
从原上下文来看,这一相关陈述是在讨论对象与人的对象之关系,进而牵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问题时,从对象与主体两个方面作出的判断。
因此,一方面,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也就是说,对象成了他自身。对象如何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眼睛对对象的感觉不同于耳朵,眼睛的对象不同于耳朵的对象。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就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成为它的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的独特方式。因此,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
另一方面,即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也就是说,它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自为地存在着那样对我存在,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注]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目录,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5—126页。
由此论述可以看到,这里的中心议题就是关于人的创造物的属性,以及这样的创造物对象与创造者(主体)之间的关系。因此,“音乐的耳朵”,从表面上看,似乎仅仅是上述哲学问题论述过程中的一个术语,而并非是有专属意义指向的概念。但深入一步,是否可以通过对相关哲学与美学问题的理解“音乐的耳朵”的意义指向。
1.主体与对象之间互为依存的相属关系。基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这一理论前提,充分强调:一切对象对人说来也就成为人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人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人的对象,甚至于对象成了人自身。这一互为依存的相属关系,仅在《手稿》其他译本中就有进一步的强调,比如刘丕坤译本,将“成为人的现实”译为“成为属人的现实”,将“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译为“成为人固有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8页。;再比如朱光潜译本,将“对象成了他自身”译为“人自己变成了对象”[注]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节译),朱光潜译注,《美学》1980年第2期,第10页。。核心的问题是,之所以主体创造者与对象创造物和合一体的规定性就在于: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里面丧失自身。[注]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目录,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5页。与此相应,只有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注]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目录,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4页。与此相反,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注]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目录,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7页。。
2.人的感官的自然属性,其差异十分明显,不容混淆。眼睛对形状,耳朵对声音,这是毋庸置疑的。需要讨论的是,眼睛与形状所必须通过的视,耳朵与声音所必须通过的听,也就是由既定感官所发出的特定动作行为;以及在属生物的感官与动作行为之后,有没有特殊的感官和异常的动作行为。《手稿》认为:不言而喻,人的眼睛和原始的、非人的眼睛得到的享受不同,人的耳朵和原始的耳朵得到的享受不同[注]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目录,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5页。。并由此进一步引发出相关感觉的结论: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注]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目录,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6页。。由此可见,在属人的范畴中间,属文化的与属艺术的,乃至具审美的,所有一切,都可能在其各自的活动过程中构成特殊的感官与异常的动作行为。折返回去,这一由既定感官所发出的特定动作行为,则就是一种超生物性感官,以及由此产生出的相应经验与目的。就像马克思所提到的那样,人以自己的全部感觉在自己创造进而属自己的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由此面对音乐,去听这样一种属文化的与属艺术的,甚至于具审美的声音创造物,所遭遇的问题:究竟是生长着一只仅仅能够听到一些声音的原始耳朵?还是生成出一只又能够听出什么样以及之所以是的声音的音乐耳朵?
3.在人造世界愈益成为人所面对的世界,进而成为人的世界,甚至于成为人自身的现实情势下,“音乐的耳朵”究竟是一个事实存在?还是一个概念存在?眼睛不可能经由看而接收乃至接受[注]为了对相关美学问题进行深度讨论,这里,有必要在事实乃至概念上对接收与接受做一个辨析,接收是一个纯粹动作,是被动的,可以没有主体姿态,是中性的,而接受则包含有一种行为方式的意味,是主动的,不能没有主体姿态,是偏性的,因此,置放一起合用,除了给出必要的区别与说明之外,应该要有进一步的意义规定,比如:接收感官与接受理念。声音,耳朵也不可能经由听而接收乃至接受形状,这是自然固有的,是属生物的感官本身的规定。依照波普尔三个世界的看法[注]波普尔在1972年出版的《客观知识》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即:把物理世界称作世界1,包括物理的对象和状态;把精神世界称作世界2,包括心理素质、意识状态、主观经验等;把世界3用来指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即思想内容的世界或客观意义上的观念的世界,或可能的思想客体的世界,包括客观的知识和客观的艺术作品。参见360词条: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604/18/1720781_215886230.shtml.,假如物质是世界1,精神是世界2,那么,包括艺术作品在内的人的创造物就是世界3。毫无疑问,这里所讨论的音乐与“音乐的耳朵”,同属世界3。更为复杂的问题是:“音乐的耳朵”究竟是一个无须事实依据的概念?还是一个无须概念证明的事实?[注]最近,笔者在跟学生上课讨论问题的时候,牵扯到事实与概念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往人们常常以客观与主观的相对方式去观照这对关系,笔者现在考虑,是不是可以以互存互动的方式去对其加以观照?概念即意识认定之事实,事实即感官确定之概念。进一步,本有的之所以能够通过精神创造去部分改变物质形态的那个原样的世界[注]世界0是我依据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的一个新的提法,参见韩锺恩在2015年11月27日《2015第10届交叉音乐学大会闭幕主持》中的有关叙事:声音本体→想象本体:无须上下文的本文,没有方位的原位,自有永有的绝对存在,之所以是的是——本体论承诺?在世界1(物质世界)、世界2(精神世界)、世界3(创造物世界)之前,是否还存在一个本有的世界0(之所以能够通过精神创造以部分改变物质形态的原样世界)?该会议议题:音乐中的想象,2015年11月27—29日,在上海音乐学院学术厅举行,会议由交叉音乐学学会、上海音乐学院主办,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承办,上海评弹团、上海数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海卓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大会网站、《音乐艺术》、中国音乐学网媒体支持,纳入2015上海音乐学院重大活动项目、第六届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术季系列活动。,又将置于何处?退一步,作为人的创造物的音乐与作为属人的超生物性感官的音乐耳朵,以及由此超生物性感官“音乐的耳朵”所产生的感性经验与存在目的,又将如何构成更加高端的互为依存的相属关系?
由上述问题聚焦,假设“音乐的耳朵”是有专属意义指向的一个特定概念,似乎有必要先进行一个去蔽,即“音乐的耳朵”并非仅仅是具有音乐感的耳朵。所谓对牛弹琴的喻示,即对一个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再美的音乐也是没有意义的。其实,这一释解本身就是对属人的感官的一种遮蔽。因为对牛也好,对没有音乐感的耳朵也好,终究不会把这种特殊的听当做一个专职,也不会把这个特殊的听感官当做一个专职器官,更不用说把这种通过特殊的听感官进行的特殊的听当做一个有专属意义指向的目的了。这里,类似视而不见(look but see not,在看,没看到)与听而不闻(listen but hear not,在听,没听到)的悖论式表述中所隐藏着的深刻涵义是值得充分关注的。
对此,如上所述赵宋光先生早在1970年代中就提出了一系列有关超生物性问题。出于对“人类学本体论”[注]人类学本体论是1960年代赵宋光先生与李泽厚先生所共同关注并经常讨论的问题,与此相关的命名还有:历史本体论、人类学历史本体论。赵宋光先生将人类学本体论视为马克思主义的隐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显义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马克思主义的隐义则是人类学本体论、关于人类历史的质料主义观点、工艺学的视角和方法。参见罗小平、冯长春编著:《乐之道——中国当代音乐美学名家访谈·第五章“学坛奇才——赵宋光”》,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年,第242页。问题的关注,出于对人类发生发展进程中由使用制造更新工具[注]参见罗小平、冯长春编著:《乐之道——中国当代音乐美学名家访谈·第五章“学坛奇才——赵宋光”》,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年,第213页。文中的“人类历史依托生产力发展的根本质料的隐秘内核”就是人类使用、制造、更新工具的持续能动创新活动。所焕发出来的智力智能智慧的关切,先生择取了一个有别于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所起到的质变作用的视角,深度审视并逐步描述处于从猿到人过渡期中间的多层级质变。与“音乐的耳朵”密切相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此过渡期中间,这个逐渐从猿到人演化衍变的族类,是如何通过使用创造更新工具来形成超生物的肢体、积累超生物的经验、实现超生物的目的的。
关于超生物的肢体,赵宋光先生从人种学和人文学的角度,把马克思关于工具作为人类肢体的延长、作为人的非有机的躯体、作为人的活动器官的哲学论述,做了进一步的阐发:经常化的使用工具的活动把大量天然物件用作工具,这些物件就成为他的天生肢体之外的肢体,它们突破了原有肢体为遗传所决定的生物局限性,例如,锋利的石椎能赛过利齿,挥舞粗硬的木棒能赛过强爪硬角迎击敌手,扔出去的石块能赛过飞奔的腿追逐猎物……它们客观上已成为这族类的“超生物的肢体”。形成中的人走出生物界,并不是开始于他的意识方面,而是开始于他的存在方面:在过渡期之初,尽管这个族类的脑量并没有超过猿,但由于他已具有一双以使用工具为专门职能的手,将大量不同质料、不同形状的自然物件,以多种多样的使用方式,化为他的“超生物肢体”,因而,这个族类的肢体存在已经是超生物的了。[注]方耀(赵宋光):《论从猿到人的过渡期》,《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6年第14卷第2期,第78页。这里,将“音乐的耳朵”作为超生物的肢体,[注]将“音乐的耳朵”作为超生物的肢体,赵宋光先生也有相关论述,参见赵宋光:《数在音乐表现手段中的意义》,《美学》1984年第5期,第179—199页。文中的有关叙述“以数理关系的形成逐渐暗示出音乐耳朵的人文意义:声音的三种基始侧度(强弱,长短,高低和音色作为音高和音量共同参与的复合侧度)→其量受到人的加工→量的规定与变化常常处在特定的比例关系之中→比例数量呈现为单纯的自然数→一方面作为人类理性在听觉审美对象中的淀积,另一方面也是人类审美听觉这种本质力量(音乐耳朵)成长发达的必经途径”。对此看法,笔者曾在《阅读赵宋光有关文论并由此引申》一文中,做了这样的提问:这种淀积仅仅是理性的吗?如果是的话,那么经验的积累又在哪一个环节?尤其是“音乐的耳朵”作为超生物性肢体的成型有没有反数学(单纯的自然数展现出复杂的质量关系)的历程?参见韩锺恩:《守望并诗意作业——韩锺恩音乐文集》,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222—223页。除了可能突破生物性遗传的局限之外,是否在相当程度上表明了人文进化的结果,即:在一般生存活动的一个普通器官之后,又成为文化生存活动的一个特定器官。这一个有别于自然属性的“音乐的耳朵”以及所发出的听动作乃至临响行为,在属人的范畴中间,已然成就为一个属文化的与属艺术的,乃至具审美的特殊感官与异常动作行为。
关于超生物的经验,赵宋光先生认为:随着工具的频繁运用,以及相应材料、形状、运用样态的愈益多样化,并以此作为原因,使各种各样形状、材料的工具以各种可能的样态活动起来(作为中介),从而造成周围事物发生愈益广阔而深刻的变化(作为结果),这样的因果链只有在具有超生物的肢体的人的活动中才能形成,进而反映在人的主观方面,便形成了超生物的经验;这种经验包括:对使用工具器官的技能,对工具性能的感知,对工具活动所引起的种种事物变化的感知,对动作样式和活动样态因果联系的感知,对活动样态和引起相应变化因果联系的感知。[注]参见方耀(赵宋光):《论从猿到人的过渡期》,《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6年4月第14卷第2期,第79页。案,就此问题,李泽厚:《人类起源提纲》(载《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1页)也有相应表述:通过这种以工具为中介的劳动活动,日益被揭示出来,成为其他生物族类所不可能获有的超生物的经验。由此关联同为超生物的经验的音乐审美经验,作为一种具有观照性的人文活动结果,就是通过这种活动结果来反观自身,除了有特定的感受对象音乐之外,也把自身作为一个特殊的感知对象,包括对“音乐的耳朵”的认知。很显然,这些活动以及相关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已然跨越了从体质人类学到文化人类学、从古人类学到哲学人本学的界限。
关于超生物的目的,赵宋光先生如是描写:形成中的人本有生物性的本能需要(例如食物,适宜的温度,免除危险等),起初,在他使用工具以满足生存需要的斗争中,本能需要的对象是他的“目的物”,使用工具仅仅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中介)”;但当这样的活动在他生存斗争中占优势以后,事情就变成:不通过某种“中介”,他就无从获得那些“目的物”,他的本能需要就无法得到满足,为了满足本能需要,他首先需要有“中介”……对于一个双手已有一定技能的族类,所需要的就是工具,于是,工具成了“目的物”,这是“超生物的目的物”。[注]方耀(赵宋光):《论从猿到人的过渡期》,《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6年第14卷第2期,第80页。一定意义上说,“音乐的耳朵”就是这样一个超生物的目的物,起初,声音作为载体,把人的情感表达与交流作为目的,人们通过接收去理解与诠释这样一种情感表达与交流,以至于接受这样一种表达与交流,并以此为音乐进行最初的命名;之后,随着声音功能的愈益进化和强化,其本身似乎也有了结构的意义,于是,出现了一种纯粹的生产和消费:人们需要一种只供感性愉悦的声音[注]就这样一种只供人的感性愉悦的声音,笔者曾经有一个类比,2001年10月22日,在讨论艺术问题的纯粹性时,突然迸出一个有点奇特的概念:时装音乐。我想,模特的衣服是穿在人身上的,但不是给人穿的,因为它是给人看的,完全地去功能性,彻底地无实用性,绝对地划时代性。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和仅仅给人看的衣服一样,仅仅给人听的声音才是满足人的纯粹听觉感官及其感性愉悦的音乐,这究竟是标示一种时尚文明?还是给出一个艺术承诺?或者就是先验存在?对此,似乎可以有这样一种肯定:艺术本身是一个东西,惟有通过直观的感性体验。那么,通过这样一种纯粹声音与纯粹聆听的对接,是否有可能呈现出部分意义来呢?;于是,不仅音乐成了这样一种只供人的感性愉悦的声音的最后方式,而且,“音乐的耳朵”自然也就成了接收乃至接受这样一种音乐并与之形成最最合适关系的超生物的目的物。
至此,专属于这样一种超生物的目的物——“音乐的耳朵”,其意义指向逐渐彰显。
就上述针对《手稿》中相关哲学美学问题的理解,与“音乐的耳朵”相关联,回应如下:
1.关于互为依存的相属关系,就像音乐中有什么样的声音就能够造就什么样的耳朵一样,反过来,有什么样的耳朵同样也就能够听出音乐中该有什么样的声音。
2.关于人的听感官属性,正因为有这样一个超生物的感官,才可能听出音乐中该有什么样的声音,也许,没有“音乐的耳朵”,可以听到所有的声音,却听不出作为音乐的声音。
3.关于“音乐的耳朵”的存在问题,这个非生物又超生物的存在,应该在哲学高度上予以确认,以使其作为一个理论前提,进入到艺术学乃至美学论域中间去发挥托底的作用。
由此关联以上赵宋光先生有关超生物的肢体、超生物的经验、超生物的目的论述,笔者以为,就现实意义层面的“音乐的耳朵”而言,不容忽视想像与想象[注]依据相关理论研究所见,想像与想象有不同所指,想像指依托经验的再生性想像,想象指不由自主的原生性想象。两文中的有关叙事:想像力(Eikasia):仅仅把表象的形式呈现给直观,主要作用在于再现所看到的事物的具体形象;想象力(Phantasia):在没有对象在场的情况下,从感觉材料中或者通过虚构或者通过抽象而形成形象。周凌霄《从康德的“想象力”到汉斯立克的“幻想力”》,上海音乐学院学士论文,2013年;2.周凌霄:《维柯艺术想象理论并及音乐想象相关问题研究》,上海音乐学院硕士论文,2016年。在其听动作乃至临响[注]临响(Living Soundscope)是笔者的一个原创叙辞,而且,有明确的音乐美学指向和归属,并给出如是定义:置身于音乐厅这样的特定场合,面对音乐作品这样的特定对象,通过临响这样的特定方式,再把在这样的特定条件下获得的(仅仅属于艺术的和审美的)感性直觉经验,通过可以叙述的方式进行特定的历史叙事和意义陈述。其简约表述:置身于音乐厅当中,把人通过音乐作品而获得的感性直觉经验,作为历史叙事与意义陈述的对象。参见韩锺恩:《临响,并音乐厅诞生——一份关于音乐美学叙辞档案的今典》,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编,《音乐文化》总第2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第392—393页。行为中,同样由中介物到目的物的结构转换,并以此成就一种超结构性结构的历史进程。
对此,仅就“音乐的耳朵”所牵扯到的经验性想像与先验性想象关系,以及由此关系成就的超结构性结构与听本体问题,作以下讨论:
1.听感官有没有可能在属艺术与具审美的范畴内[注]为了使这里的讨论更加充分有效,不再将属文化的问题纳入其中,依笔者看,所谓文化属性仅仅表明:这样一种音乐是人创造的;所谓艺术属性则表明:这是一种具人文性工艺结构的音乐作品;所谓美学属性则进一步表明:这样一种音乐仅仅满足人的纯粹感性愉悦;因此,这里的讨论不再牵扯什么是作为文化产物的音乐,而主要针对与围绕作为艺术作品的音乐与作为审美对象的音乐,以及作为纯粹形式的音乐。由连接性中介结构变成超结构性结构呢?如果生物性目的→超生物性目的→超生物性目的作为目的,其工艺学结构层次:自然躯体以及天生感官动作行为(始渡线)→使用工具并延长自然躯体再转换天生感官(中线)→制造工具并从中获得感性愉悦再生成价值环链(终渡线)[注]这里的工艺学结构层次,是根据赵宋光先生有关从猿到人过渡期历史描述范式设定的,参见罗小平、冯长春编著:《乐之道——中国当代音乐美学名家访谈·第五章“学坛奇才——赵宋光”》,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年,第216—217页。“始渡线”是前肢演变为使用工具的专职器官——手(这时期的“工具”是天然物件因人对它的使用而成立的),“中线”是族类群体间互相交流的有声信号因具有使用工具活动的心理内涵而演变为语言的萌芽,“终渡线”是把自然界的物件加工成为生产工具(制造工具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推进)。,那么,在超生物性目的作为目的的合目的性牵引下,通过艺术方式发出声音的合规律性的音乐(音乐之所以是艺术底线和审美边界),以及以此本体论作为依据的临响(想象的声音在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进程中)[注]参见韩锺恩:《天马行空再求教——庆贺赵宋光先生80华诞特别写作》,《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第17—18页。。
2.一方面是再生的经验性的声音想像,一方面是原生的先验性的声音想象。由此,在确认艺术中具有大量经验性想像的前提下,设问:有没有先验性的艺术想象?进一步设问:当想象中介在艺术中果然成为超结构性存在(类超生物的目的作为目的)的时候,这样一种先验性的艺术想象即艺术想象本体[注]之所以称其为想象本体,至少,有3个不可述说者:凭什么这样想象?难以预料会想象出一个什么东西来?之所以这样想象的理由?于是,只有想象之后所可能呈现的结果:想怎么想就怎么想,想什么像什么,想出来就是一个东西。是否可以就此确证?反过来,在先验性想象果然存在并为艺术想象提供可能性的基础上,在作为审美对象的各类艺术作品已然自足的情况下,设问:经验性的艺术想像对于审美主体的审美活动来说是否还有价值存在?
3.当人们面对完全陌生的属艺术的感性直觉对象,甚至于对所面对的感性直觉对象完全处于无经验状态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一种处于先验层面的艺术想象首先为人们提供一种对这些无经验的感性直觉对象进行想象的可能性。这种逼近先验层面的艺术想象,除了在理论上可能确证其存在条件之外,是否还可能在事实上确认其存在?音乐想象作为中介置于听感官与思意识之间实现不同结构间的功能衔接,当缺其不可时,想象中介是否就变成一个超结构性的存在?进一步,当此超结构性结构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结构的时候,是否就此确证想象本体的存在?
4.如果声音果然由传递或者传达他者表达与示意的中介物,逐渐变成仅供感性愉悦的纯粹目的物,那么,听感官有没有可能在属艺术与具审美的范畴内,也由一个仅仅作为听动作的中介物变成一个足以成就临响行为的目的物呢?假如没有这个有艺术属性的听对象与具审美性质的听感官及其行为动作,假如通过临响依然形不成这样一种有艺术属性与具审美性质的听感官事实[注]听感官事实是笔者近年来创用的一个仅限于艺术与审美范畴的具有专属意义指向的术语概念,仅从字面看,不难理解,就是通过听这个感官以及相应的听动作与临响行为所呈现的一个事实。或者说,就是通过听这个感官去接收且接受一个声音并由此获得一种感觉。然而,一旦将此置于特定的艺术学并美学论域中间,则仅从字面理解就远远不够了。就艺术学而言,就需要明确其听对象前提,即听什么样的声音?就美学而言,又需要明确其听感官及其听动作与临响行为前提,即依托什么去听这样一种声音?,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艺术的声音与非艺术的声音没有任何的差别?如果说,处于生存低端时段的人们依赖的是操作领先—言语镶嵌的范式,[注]这是赵宋光先生在推进幼儿数学教学过程中所发现的一条类规律的规则,参见罗小平、冯长春编著:《乐之道——中国当代音乐美学名家访谈·第五章“学坛奇才——赵宋光”》,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年,第217页。那么,在进入生存高端时段之后,人们是否能够在想象的介入并就此成就为超结构性结构之后,形成并依托一种操作—语言即时完形的范式?
5.如果说面对音乐的听是人的属自然的听本能通过听感官生成的超结构性结构,尤其当面对艺术音乐的听作为超结构性结构成为结构的时候,音乐作为艺术作品才得以起源,音乐作为审美对象才得以发生;那么,听本体作为无目的的合目的的存在,能不能通过意向去把握声音在听经验与听意识中的显现?一种有别于现实存在的意向存在?也就是,依托这一只立美在先[注]立美是赵宋光先生在音乐美学与教育学领域长期从事教学与研究后创用的一个特定概念,所谓立美在先,参见罗小平、冯长春编著:《乐之道——中国当代音乐美学名家访谈·第五章“学坛奇才——赵宋光”》,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年,第217页。把自然界的物件加工成为生产工具的活动,是以目标意识领先的,这目标已不是生物性的欲望对象,而是超生物的合目的形式:凭着先前使用工具活动所积累的经验,已经知道什么样的形式具有什么样的性能,为了使加工对象具有某种性能,应当使其具有某种形式。这就是“赋予形式”的历史实例。主体在赋予对象合目的形式的过程中,建立自身活动的另一些合目的形式,以保证加工劳动获得成功。至此,就形成了“对象立美”与“主体立美”互相依存的“立美”概念。的“音乐的耳朵”,通过临响去听那种属艺术的声音,并在临响过程中通过意向去显现具审美的意义。
回到《手稿》,依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任何人的创造物包括音乐,都只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在通常的、物质的工业中,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注]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目录,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7页。
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注]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目录,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7页。
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注]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目录,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7页。

与此相仿的表述,《手稿》如下所说,几乎可以看作是对黑格尔上述形象喻示的哲学注解或者人类学诠释: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注]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目录,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7页。
兴许,是出于纯粹逻辑意义上的考量,一个双向乃至互向的关系如是呈现出来:
音乐不仅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性存在,与此同时,音乐也通过人实现自己,并显示出音乐自身的本质力量。[注]关于音乐通过人实现自己并显示其本质力量的观点,参见韩锺恩:《对音乐分析的美学研究——并以“[Brahms Symphony No.1]何以给人美的感受、理解与判断”为个案》,《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第16页。
其中,特别值得关注并进一步可以研究的问题是:既然音乐通过人实现了自己,那么,音乐的本质力量是否并非像人们原先所认定的那样仅仅由人给予,应该说,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先在的,或者是一种自在之物的逻辑还原。[注]关于先在与自在之物的问题,显然,牵扯到哲学意义上的形而上本体与先验存在问题,对此,笔者曾经以这样一些叙辞加以表述:与生俱有的存在,惟其不可的存在,独一无二的存在,仅其自有的存在,自然而然的存在,无缘无故的存在,无须解释的存在,不由自主的存在,始终如一的存在,无中生有的存在;之所以是的是,一种以存在自身名义存在着的存在;自有,原在,本是;一种不由自主的自有存在,一种与生俱有的总有存在,一种始终如一的永有存在,一种独一无二的仅有存在,一种之所以是的本有存在;以及与音乐相关者:物自体,情本体,声常体,听元体,TMI(The Music Itself)。
由此,通过重读《手稿》并关联赵宋光人类学本体论思想,在弄清楚搞明白哲学问题的前提下,重新折返,回到艺术学乃至美学论域中间,似乎可以如是认定:
“音乐的耳朵”,从一个单纯接收普通声音并仅仅产生一般感觉的生物器官,到一个专门接受特殊声音并产生异常感觉的超生物性感官,离不开属艺术的听动作的发生与具审美的临响行为的介入。于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就是听感官事实的呈现:听与对音乐的听同一,就像胡塞尔所言:听不能与对声音的听相分离……这个“一个为我的内容的此在”是一个可以并且需要进一步现象学分析的实事。[注][德]埃德蒙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现象学和认识论研究”》,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420页。也就是说,作为感性动作行为的听与临响,和作为感性对象的声音,不仅不可分离,[注]依胡塞尔的说法,这个不可分离,就是一个无须再区分的双重的东西。参见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420页。而且,其根本的限定就在于:能够与艺术的听与审美的临响这样一个感性动作行为同一的感性对象,只能是作为音乐的声音。
因此,一定意义上说,比上述主体与对象之间互为依存的相属关系更进一步,作为音乐的声音与属艺术的听动作以及具审美的临响行为之间,还有一种更加高端的互为依存的相属关系,即一种互为依存的相生关系。有如马克思在论述劳动在人和自然关系中间所发挥的作用时所指出的那样: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注][德]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01—202页。
“音乐的耳朵”既是一个无须事实依据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无须概念证明的事实。因为只有在专属于艺术设定与专属于审美设入的声音,也就是作为音乐的声音这样一种仅有的感性对象的前提条件下,进一步,通过属艺术的听动作的发生与具审美的临响行为的介入,才可能成就之所以是的这一只“音乐的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