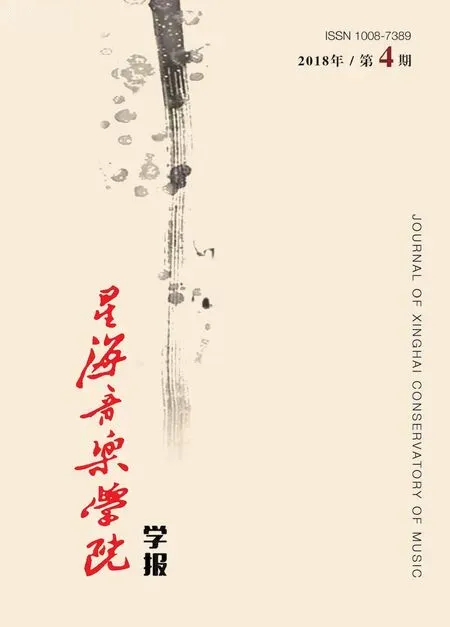1949年前敦煌乐舞研究的历史进程
刘文荣
1900年6月22日(时农历五月二十五日),举世震惊的敦煌藏经洞被意外发现,正如王圆箓墓志所铭:“又复苦口劝募,急力经营,以流水疏通三层沙洞,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明。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事也。”*敦煌市志编纂委员会编:《敦煌市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4年,第660页。藏经洞的发现,有五万多件六朝隋唐文书面世,时之学界为之震惊。1907年与1914年,已获东方语言学博士的英国人斯坦因带走敦煌文物文献共计34箱1万多件。1908年,法国法兰西学院教授伯希和博士运走5000余件。1910年,敦煌劫余写经含残卷八千余卷运往北京京师图书馆。1911年,日本人吉川小一郎、橘瑞超带走近600件。其中在斯坦因和伯希和带走的现今英藏和法藏敦煌遗书中即有古老的敦煌乐舞文献。
敦煌音乐文献中其历史价值至为珍贵者,莫如敦煌曲谱,今收伯希和氏3808号,即书写P.3808。敦煌舞蹈文献即如敦煌舞谱,至目前已发现的有今收S.5613、S.785、S.7111、S.5643和P.3501。其中最丰者,当为S.5643与P.3501两件,分属英藏与法藏。
自藏经洞文献的发见之起,对敦煌乐舞研究的发轫及至1949年前的研究过程,下以年代为据分而论之。
一
1909年,伯希和将敦煌带来的部分写卷在北京公布后,引起时之学界极大反响。最早有关敦煌著作遂之诞生,王仁俊发《敦煌石室真迹录》(1909)、罗振玉与蒋斧发《敦煌石室遗书》(1909)、罗振玉撰《鸣沙山石室秘录》(1909)。以上涉敦煌著作的撰写与出版,均是因为伯希和回京后邀请王仁俊、罗振玉、蒋斧等人观看了敦煌卷子,才有了三位学者对敦煌文献最早的记录。
伯希和归法国后,又陆续邮寄出一些法藏的敦煌文书照片。国内学者又据此着笔,撰成数种,即是第二时期敦煌文献的发表。如1910年12月着手著录,1911年,已入端方幕[注]1908年,刘师培由日本归国,谒晚清两江总督端方,此年,于南京入端方幕。1911年,随端方至天津,发《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文,事见方光华著:《刘师培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236页。的刘师培在《国粹学报》第7卷第1期发表《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即是对伯希和藏敦煌卷子所拍照片而写。如其文云:
法人伯希和于敦煌所得唐写本,其数至多。近阅其印片若干种,各为提要一首,以寓目后先为次。依类编集,俟诸异日。庚戌十二月,师培记。
刘师培之《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是伯希和于北京首次公布敦煌文献后第二年的有关敦煌文献著作。
1911年,孙毓修出《唐写本公牍契约考》,以斯坦因获敦煌契约文书为据,考唐敦煌社会生活诸事。正如其卷首所云:
光绪季年,有英人司泰音,游我新疆甘肃诸邑……司泰音[注]按:指斯坦因,英名Marc Aurel Stein,另可见文献有译“司泰音”,即如文献该处所指,又见译名“司坦囊”“司代诺”,今通译“斯坦因”。穷搜冥索,携之归国……中有唐时官私公牍契约墨迹十余通……(吾)取其文字稍完好者,更为之掇拾旧闻,证其阙略[注]孙毓修:《唐写本公牍契约考》,原载《东方杂志》,1911年第8卷第2号。后又集纂出版,即东方杂志社编:《考古学零简》,北京: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65页。。
但据伯希和返回法国所寄回敦煌卷子照片,国内学者主要研究者仍是罗振玉。罗氏于1910年汇编有《石室秘宝》以及稍后的《鸣沙石室》三书,即《鸣沙石室佚书》(1913)、《鸣沙石室佚书续编》(1917)、《鸣沙石室古籍丛残》(1917)。
1917年王国维撰《流沙坠简》[注]王国维:《流沙坠简》,《学术丛编》卷24,1917年。,主要据斯坦因得西北古简、法人沙畹所释并寄回罗振玉而写,以考释敦煌河西史地。
自20世纪初年藏经洞文献的发现,到20世纪第一个十年,主要是藏经洞文献的四散。自20世纪第一个十年伯希和等对敦煌文献的公布,到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主要是罗振玉等敦煌材料先睹与先据者的研究。对于敦煌乐舞文献,20世纪的前两个十年,仍是默默的“沉睡”着,不过是在由中国西部藏经洞中的“沉睡”到欧洲西部英、法等国国立图书馆中的“沉睡”,由中国“西部”到欧洲“西部”,其绝美的面庞仍处神秘面纱之下尚未引起人们关注。
二
罗振玉《鸣沙石室》系列三部书出版后,一直至20世纪20年代初仍主要为罗氏主笔敦煌文献研究。1923年起,罗振玉再出《莫高窟石室秘录》(1923)、《敦煌零拾》(1924)、《敦煌石室遗书》(1924)三种,蒋斧出《沙州文录》(1924),罗振玉出《敦煌石室碎金》[注]按:据罗琨、张永山的研究,《敦煌石室碎金》于1925年6—9月校对完成,见罗琨、张永山:《罗振玉评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46页。(1925)。
敦煌文献如此重要,以致陈寅恪为陈垣《敦煌劫馀录》撰序更是云:“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注]陈寅恪:《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03页。。可见敦煌藏经洞文书的发现与公布,学界察觉并估计出的巨大学术价值。但此时学界并未完全引起对音乐信息的关注。一则,与时之学人各自的学术着眼点及学术擅长有关;二则,与藏界和学界对敦煌文献资料的公布及相关内容的及时发现有关。
可喜的是,在20年代中期,在敦煌乐舞文献上,终于迎来了开篇之作。即1925年,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发表半农(刘复,下文统称“半农”)先生的《敦煌掇琐》[注]刘复:《敦煌掇琐》,1925年6月29日写于巴黎,后载《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3期,1925年10月28日。,其最早是以“舞谱”的定名抄录了藏经洞涉敦煌舞蹈方面的文献,使敦煌舞谱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半农记舞谱编入《敦煌掇琐》第四十六号,记有《遐方远》《南歌子》《南乡子》《浣溪沙》《双燕子》《凤归云》等谱,计五首《遐方远》谱、各三首《浣溪沙》谱和《风归云》谱、各一首《南歌子》谱、《南乡子》谱和《双燕子》谱,总共十四谱,即半农《舞谱》目录中所云之“残抄出者共十四谱”。[注]刘复:《敦煌掇琐》,《敦煌丛刊初集》(15),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229—236页。
半农所抄该十四谱所依文本是今编号P.3501的敦煌法藏卷子,该卷为长卷,亦为残卷,首无总录与开篇说明,文直起于《遐方远》词序,卷末残,至《凤归云》舞谱字,共计存六名十四谱。按该卷子脱字的状况,恐与受覆盖或与多卷相连粘贴有关。对原卷文字及卷面情形分析,原卷记谱当不止半农所记之十四谱,容后整理散佚比对再录。
半农为语音学者之外,亦工音乐,其作词的《教我如何不想她》为音乐界所熟知。正如周作人在《半农纪念》中所说:“他的专门是语音学,但他的兴趣很广博,文学美术他都喜欢,作诗,写字,照相,搜书,讲文法,谈音乐”[注]郁达夫等著,郭雨选编:《名人印象》,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6年,第212—213页。。半农亦著《从五音六律说到三百六十律》《十二等律的发明者朱载堉》等音乐学术论文,并采集民歌,为北京天坛等古乐器测音,建语音乐律实验室,在龙门、巩县发现著述乐舞造像等。正是他在音乐上的嗜好与功力,使他在法国抄录敦煌文献时最早发现了舞谱。鲁迅先生亦曾写有著名的《忆刘半农君》,使半农为更多的人所熟知,文中提及“他的(原文确)到法国留学……他回来时,我才知道他在外国抄古书”[注]鲁迅:《忆刘半农君》,《鲁迅杂文散文》,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0页。,即指半农在法国抄敦煌文献的工作。
半农的贡献在于对敦煌舞谱的定名、辑录与首次对外公布。关于敦煌舞谱的价值,他在《敦煌掇琐》中以《尚书》与《小唱》进行比较,言说:
照著沿袭的说法说,《尚书》当然比小唱重要到百倍以上:《尚书》当然是“大”,小唱当然是“小”。但切实一研究,一个古本《尚书》至多只能帮助我们在经解上得到一些小发明,几首小唱却也许能使我们在一时代的社会上、民俗上、文学上、语言上得到不少的新见解。如此说,所谓“小”、“大”,岂不是义得其反。[注]徐瑞岳:《刘半农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15页。
半农对敦煌舞谱有辑录,但无暇释录。半农自语通过他的努力,抄录资料为他人研究,并亦便于他人研究,其云:“但我总算是尽了一分愚力了。若然我这个见解不错,则我将这数年来留学余暇所抄录的敦煌文件发表,也就未必是‘妄祸枣梨’”。[注]徐瑞岳:《刘半农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15—116页。
蔡元培为《敦煌掇琐》作序,亦言“舞谱”事,云:“刘半农先生留法四年,于研究语音学的余暇,把巴黎国家图书馆中敦煌写本的杂文,都抄出来,分类排比,勒成此卷,就中如家宅图,可以见居室的布置;舞谱可见舞蹈的形式”。[注]高平叔:《蔡元培史学论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21页。蔡元培极力肯定半农的历史功绩。
半农留法,事法藏敦煌文献,王重民去英,事英藏敦煌文献。今查,英藏中亦有不少涉敦煌乐舞卷子,如S.3501《舞谱》、S.5643《舞谱》等。可惜王重民在1947年5月14日于上海《大公报》上公布《伦敦所见敦煌群书叙录》中没有进行采拣披露。后于1947年12月11日亦在上海《大公报》上公布《伦敦所见敦煌残卷叙录》中亦无披露。
自敦煌藏经洞文献的公布至20年代末,罗振玉一直是敦煌文献著录与研究的主要生力军。值得一提的是,受罗振玉门风熏陶的影响,罗振玉第四子罗福葆于1924年首出敦煌文献辑录成果《沙州文录补》,该著共收敦煌卷子55件,其中有英藏卷子13件。罗福葆该著对敦煌卷子的收录及资料公布非常重要,惜亦不见敦煌乐舞之原资料与对乐舞资料辑录公布之提醒。
20世纪20年代后期,敦煌文献研究的主力军渐有扩充,学术着力点由辑录到校录再到研究。1926年起,胡适因公到英国参加中英庚子赔款会议,期间在大英博物馆与巴黎国家图书馆寻找敦煌遗卷及禅宗史料。但胡先生更多的是关注了敦煌文献中的禅宗史料,遗憾的是没有对两家所藏敦煌乐舞文献引起重视并进行辑录研究。
1929年,向达发表《论唐代佛曲》,异常重视从敦煌的资料中寻觅龟兹琵琶七调及般涉宫调的原理,正如其云:
公元一千九百二十五年的夏天,我偶然翻阅《隋书·音乐志》,看到纪龟兹人苏祗婆(Suvajiva)传来琵琶七调的一段话,觉得其中所有相当于中国羽声的般赡调……那时不知是哪一位朋友远远地从云南寄了几期《澎湃》给我,在十三、十四两期中得读徐嘉瑞先生所著《敦煌发见佛曲俗文时代之推定》一文,因此我于南卓《羯鼓录》所纪诸佛曲调而外,知道还有许多有宫调的佛曲。罗叔言先生的《敦煌零拾》中收右俗文三篇,罗先生也漫然定名为佛曲。[注]向达:《论唐代佛曲》,原载《小说月报》,1929年第20卷第3号,后收入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重庆:重庆出版社出版,2009年。
20年代,像王国维、罗振玉、胡适等,敦煌学是时之学术大师们的前沿领域学科,敦煌学亦是前沿学术大师们的倾力主攻学科。
三
30年代起,敦煌研究的队伍再次扩大。1930年,胡适出《菏泽大师神会遗集》,开敦煌文献校录之先河。1930年,唐文播写《敦煌老子写卷“系师定河上真人章句”考》《巴黎所藏敦煌老子写卷校记》,攻敦煌经籍文献。
1930年起,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已学成归国的陈寅恪笔锋渐次移入敦煌学,率先提出“敦煌学”一词。陈氏“敦煌学”的提出,大有学科广厦新建之气概,此言一出,振聋发聩、不啻晨望云霓、贯顶金针。遂开旗得旨,后之学界“敦煌学”漫途晦涩研究之征程多始于此。伴随着“敦煌学”的提出,陈氏又发表《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注]陈寅恪:《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年第2本。(1930)、《〈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注]陈寅恪:《〈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清华学报》1932年第1期。(1932)、《敦煌本〈维摩诘经·问疾品〉演义书后》[注]陈寅恪:敦煌本〈维摩诘经·问疾品〉演义书后》,《清华周刊》1932年第9—10期合刊。(1932)等重要文章。倍感遗憾的是,陈先生亦无涉敦煌乐舞卷子。
可喜的是,1934年,王重民、向达至英法等国抄录敦煌卷子,并拍摄了三万余张的微缩胶片,为日后编纂《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次对法国国立图书馆等地抄录敦煌卷子的过程中,王重民、向达见到了敦煌曲谱的卷子,拍摄了P.3808的曲谱22张,拍摄了S.2607《浣溪沙》四首,S.2607《西江月》三首。拍了S.5643的舞谱5片。有《蓦山溪》舞谱、《南歌子》舞谱、《双燕子》舞谱、《三当》舞谱,其余舞谱名损。未见所拍S.5613的舞谱《南歌子》,未见所拍S.0785,未见所拍S.7111。
王重民亦拍摄了P.3501舞谱的图片,并命名为“大曲舞谱”。拍摄了《遐方远》《南歌子》《南乡子》《浣溪沙》、又《遐方远》、《双燕子》、前《遐方远》、又《浣溪沙》、《凤归云》等全部舞谱,今可见12胶片。另有见拍摄P.3128《曲子浣溪沙》三首,拍摄P.3821《曲子名浣溪沙》及又四首。有见P.3719的《尔雅》10片,未见所拍《浣溪沙》乐谱残谱。《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有“南歌子两页”,有P.3128曲子《浣溪沙》,未见所拍P.3137。
其《敦煌曲子词集》中收P.3137《南歌子》一首及残一首共两首,收S.2607《浣溪沙》及又三首、P.3128《曲子浣溪沙》及又两首、P.3821《浣溪沙》及又四首,共九首。《敦煌曲子词集》惜未收舞谱P.3501的《南歌子》及《浣溪沙》名,亦未收S.5643、S.5613的舞谱《南歌子》,未收P.3719的《浣溪沙》乐谱残谱。王重民此次对敦煌曲谱和舞谱的辑录是极为重要的,因为此前罗福苌译伯希和《巴黎图书馆敦煌书目》并未有载。虽然没有公开资料显示此时期王重民对其进行的研究,但是直到1950年,王重民才将其定为“曲子工尺谱”。
1934年,向达撰《唐代俗讲考》[注]向达:《唐代俗讲考》,《燕京学报》1934年第16期。,对“僧人之唱小曲”“寺院中的俗讲”等展开专论。1935年,向达在伦敦大英博物馆抄录敦煌卷子,两年后于1937年发表了《伦敦的敦煌俗文学》[注]向达:《伦敦的敦煌俗文学》,《新中华杂志》1937年第5卷。,并列录有关敦煌俗文学的卷子,如“季布歌”“禅门五更曲”“禅门十二时曲”等,无载曲谱。再逾两年后于1939年发表《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其中俗文学》。
1935年10月许国霖撰《敦煌石室写经题记》,同年发表于《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9卷第6期。该文主要是据时藏“京师图书馆”(后成“国立北平图书馆”的敦煌卷子而成)。敦煌乐舞字录多在经卷背面所写,正如其所云:“窃见卷内题记及背面杂文,多有关于学术之研究”,但可惜的是,其在辑录中并未发现涉乐舞卷子。
那么,敦煌藏经洞所出,斯伯二君并未带走仍藏在中国的琴谱卷子何在呢?
这在1935年《中央时事月报》的报道中有了答案。《中央时事月报》在1935年第4卷第48、49期中发表了以“中央图书馆”为署名单位的《德化李氏敦煌写本目录》,前言云:
甘肃敦煌千佛洞之建筑创于后魏……而自北宋初,经洞封闭,后世几不知吾国尚有如是之伟大宝藏。前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佛龛坍塌,秘册写本,乃稍稍流布于外,惟彼时人尚不甚措意。越七八载,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先后来游,见而大诧,以为希世瑰宝。于是智取利诱,择其精者,既捆裁归诸英法矣。朝野闻之,始颇惊悔。宣统二年(1910),学部咨甘肃有司,将洞中所遗留悉数运京,已仅存八千余卷,且多系佛经残帙,他书甚鲜,盖德化李木斋阁读盛铎氏藉其威何秋辇,彼时任甘省藩司之便,尽得斯伯两氏所余精品而朋分之。致学部所得,殆全糟粕,未几何氏旧藏,复归于李,然李氏则讳莫如深,从未出以示人,其内容究竞若何,外间固无从揣测也。今年春,李氏将有斥卖消息,乃印成目录一册,藉资号召,批览一过,佛经外,经史杂著,及契约历本等,有关史料者甚众。[注]中央图书馆:《德化李氏敦煌写本目录》,《中央时事月报》1935年第4卷第48—49期。
李氏敦煌写本目录中即载有“琴谱”一则,此等古代珍贵之乐谱,经藏经洞八百余年的封存,斯坦因、伯希和皆未带走,是当时所见敦煌乐舞谱中惟一在中国所劫余者,可惜当时“索值殊奢,国内学术机关多欲购不得,亡何传卒以八万元日金,畀诸异国”,遂流佚海外[注]关于此琴谱为舞谱,并其下落者,续文详披,此不繁赘。。
其实,早在是年8月份,胡适闻讯李盛铎出手所藏敦煌文献时,征询陈垣欲购买,陈垣认为多为佛经,且购资昂贵,姑可抵押。陈垣回信胡适云:
李氏所藏敦煌卷,据来目,除大部分佛经外,可取者不过三二十卷。普通写经,精者市价不过百元,次者更不值钱,来目索价太昂,购买殊不相宜。鄙意只可抵押,抵押之数,可以到贰万元。
故至12月份时,《中央时事月报》已登载披露,《德化李氏敦煌写本目录》记载之李盛铎所藏敦煌卷子已至日本,“琴谱”遂初落日本。
1935—1937年,姜亮夫自费往返于伦敦与法国之间,1936年3月入法国国家图书馆,12月写出《敦煌经籍校录》。1937年入大英博物馆,写《敦煌杂录》。1937年姜亮夫回国,由北京至上海后,恰逢日本侵占上海,姜亮夫所抄的敦煌文本在上海闸北毁于战火,千辛万苦辑录却终毁之一炬,令人无比惜痛。本以属国的文物掠于他国,已令学界痛惜,如今却辛苦亦要忍辱在国外抄录,更倍感月缺花残,毁玉锤珠。向达在英国抄录,受翟里斯种种为难,姜亮夫在法国拍摄敦煌卷子,每拍一张,需付费十四法郎。在这种情况下,千辛万苦历尽艰辛再由他国抄来,在本国因战火又遭焚毁,更感华亭鹤唳、捶胸顿足,无比惜叹。
姜亮夫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所拍敦煌卷子主要是涉及语言音韵方面,正如先生在自传中所言:“老友王重民在巴黎国民图书馆编伯希和弄去的敦煌经卷目录,约我摄制语言学部分的韵书卷子。于是,我又走上读欧洲所藏敦煌卷子的道路”[注]姜亮夫:《姜亮夫自传》,载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文献》一九八○年第四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第189页。。姜亮夫有没有抄录敦煌乐舞方面的卷子,先生著录中未见直接披露,从其他公开资料中亦无从知晓。但是先生在欧洲,面对流失中国之文物,是有极大兴趣,甚至是怀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去拍摄、去记录的。姜亮夫对流散在欧洲的敦煌卷子及其他文物近乎痴狂的研究欲望和态度从章太炎邀其西去,姜亮夫卖掉先前的旧文稿自付费去欧洲一事即能看出,“至巴黎后,我参观了许多博物馆及专藏中国艺术品的美术馆……参观是我进修的最好老师……这是真正科学的整理工作呀,于是我如疯似狂地抄录、摄影,忙得不亦乐乎……我还从巴黎到伦敦、罗马、柏林去寻找,除敦煌经卷外,把所得千余件青铜器、石刻、古书画的摄影记录等”[注]姜亮夫:《姜亮夫文录》,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9页。寄往中国。
姜亮夫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抄录敦煌文献时,即使见到了敦煌曲谱,即后编号为P.3808的曲谱卷子,可惜姜亮夫带回来的敦煌卷子多毁于战乱。姜先生在欧洲所摄敦煌卷子及其余书画照片等“写成一篇《欧洲访古录》寄给《国闻周报》(我当时不知大公报已南移,故此文寄天津后无下文,至今未觅得,又无底子可重录,可惜之至)”[注]姜亮夫:《姜亮夫自传》,载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文献》一九八○年第四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第189页。。回国后,碰巧抗日战争时期,“这时,我已知道我在沪、杭、苏州的书已损失(从法国带回来的书也在其中)”[注]姜亮夫:《姜亮夫自传》,载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文献》一九八○年第四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第189页。,现已无从知晓。
七七事变前夕,我绕道西伯利亚回到北京,不久,八一三事变爆发,我不得不逃难。逃难途中,随身携带的大批文物艺术制片损失几尽,仅仅剩下不到三百张敦煌制片。我非常珍惜这些制片,决心加以整理……于是,我第一步把所得的卷子,分类写出个总目,将按这个总目作研究。[注]姜亮夫:《我是怎样整理敦煌卷子的》,载《文史知识》编辑部编:《文史知识文库·文史专家谈治学》,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68页。
可惜,主要据此仅剩的制片整理出的《瀛涯敦煌韵辑总目叙录》中不见敦煌乐舞事。
王重民亦有将法英所藏敦煌资料丢失者,如其云:“敦煌出的《五更转》,约有廿来个写本,可惜我在巴黎和伦敦所抄的都丢了”。[注]原载《申报·文史周刊》1947年12月13日第3期,后收入王重民:《冷庐文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5页。
在中国学者去欧洲抄录敦煌卷子的同时,一位日本学者注意到了敦煌遗书,并痴醉于其中的乐舞文献,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来进行研究,这就是林谦三。1937年,日本音乐学者林谦三开始着手进行敦煌曲的研究,但系统的研究成果一直到1957年才在中国出版发行,即著名的《敦煌琵琶谱的解读研究》[注]按:由潘怀素翻译,于1957年9月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该书对我国20世纪50年代起敦煌音乐学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叶栋等我国前辈学者首先在该书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如叶栋所言:“关于三群定弦与谱字译音,林谦三氏作的研究,于人也有启发”[注]叶栋:《唐乐古谱译读》,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年,第6页。。
林谦三最早发表刊出的敦煌乐舞研究成果,是1938 年,林谦三与平出久雄在《月刊乐谱》联合发表了日文文章《琵琶古谱的研究——〈天平〉、〈敦煌〉试解》,后饶宗颐加以翻译,收入其《敦煌琵琶谱论文集》中。[注]《琵琶古谱之研究——〈天平〉、〈敦煌〉二谱试解》,见饶宗颐:《敦煌琵琶谱论文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1年,第1—35页。林、平一文,是将与《天平琵琶谱》的联系与比较进行的研究。《天平琵琶谱》载有《黄钟番假崇》一曲(图1),在其背《写经料纸纳受帐》上记有“天平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的抄本时间字样,即唐玄宗天宝六年(747)。该谱现存日本正仓院,谱式与敦煌琵琶谱类同,反映了唐乐琵琶谱的整体面貌,是现存唐乐古谱的最早记录者。

图1 日本天平琵琶谱
早在1932年主编《国剧丛刊》后任日本京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讲师的傅芸子,开始考察正仓院中国唐代遗物并关注中日文化的对比研究,其所撰《正仓院考古记》在国内较早并详细记录了该谱页面及林氏对其进行的相关研究:
又院藏古文书中,曾有人整理发现天平琵琶谱一叶……林谦三、平出久雄据敦煌琵琶谱及三五要录相互研究结果,因知此谱宫谱,与今日本雅乐所用之琵琶,完全同型。[注]傅芸子:《正仓院考古记》,东京:东京文求堂,昭和十六年(1941),第21页。
无独有偶,傅芸子亦十分关注敦煌学的研究,于1943年在《中央亚细亚》第2卷第4号上发表了《三十年来中国之敦煌学》的文章,言及:
有清光绪末年,戊戌庚子两年之间,在吾国政治上外交上,固有极大的变化;而在此两年之中,吾国学术上乃亦有极重要的资料,适亦在此际发见,影响所及,致使吾国学术上亦有极大的变化与开展。此两年的发见维何?……与夫光绪庚子(1900)甘肃敦煌千佛洞佛龛坍塌六朝唐五代古卷子之出现。不过两三年之间,乃有如此重要的,如此巨量的古代文物呈现于人间,近三十年来,吾国学术的进展能与前代截然划一新阶段者,实皆由于上述殷墟敦煌两地并其他各处古器物的发见所致,就中敦煌千佛洞所发见古卷子的关系,尤称钜要焉。[注]傅芸子:《三十年来中国之敦煌学》,《中央亚细亚》1943年第2卷第4期,第50页。
可见,敦煌卷子的发现在当时学术界引起的震惊以及傅芸子对其的重视。可惜30年代斯、伯藏敦煌乐舞卷子,并未引起国内学术界的足够重视,更无对其进行充足与专门的研究。
1938年,日人神田喜一郎编《敦煌秘籍留真》,在下卷第63号拍录P.3501敦煌舞谱影印一页,影印可见《南歌子》《浣溪沙》《遐方远》各舞谱。在《敦煌秘籍留真》中,神田喜一郎录舞谱影印图的同时,并述“舞谱 未详书名”字样,可见,当时敦煌舞谱的研究现状仍处有待研究的地步。下见日本昭和十三年(1938)京都影印暨铅印本的敦煌舞谱图。

图2《敦煌秘籍留真》中的影印敦煌舞谱[注]神田喜一郎:《敦煌秘籍留真》,《敦煌丛刊初集》(第1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5年,第241页。
1938年,是敦煌乐舞研究极为重要的一年。除神田氏的舞谱辑录外,在敦煌曲谱上,1938是年,林谦三与平出久雄将P.3808敦煌曲谱定名为之“敦煌琵琶谱”,目前在学术界基本持此定论。林先生亦将曲谱谱字音高记号做了释读,并译《水鼓子》为五线谱,将曲谱按字迹分为三组,对每组琵琶的定弦法做出了判断,如第二组定弦用谱字十五个,第三组定弦用谱字十四个,这是当时对敦煌曲谱所取得的最主要研究成果。今指敦煌曲谱主要是指P.3808(见图3)。

图3 P.3808敦煌曲谱中的《伊州》《水鼓子》等曲
另有P.3539二十谱字发现的过程,为1959年事,兹容续文详谈。
较之林谦三氏,国内学者对敦煌曲谱的研究起步稍晚。1940年,对敦煌乐谱研究极为重要的是,向达提出了P.3808的敦煌曲谱是为《敦煌唐人大曲谱》,这是继林谦三定名敦煌琵琶谱后中国学者最早为该谱定名的人,向达又在法国进行了专门的拍照。罗庸在西南联大授课时亦曾言向达所带回的敦煌曲谱事:“《曲谱》为向达自欧洲摄影带回者,存九调二十五谱,即《西江月》《倾杯乐》《伊州》《心事子》《水鼓子》《急胡相问》《长沙女引》《撒金沙》《营富》是也”[注]罗庸讲述,郑临川记录、徐希平整理:《罗庸西南联大授课录》,北京:北京出版社,2014年,第182页。。
在向达研究敦煌曲谱的前两年,敦煌舞谱方面的研究,亦得到了进展,主要发力者仍是罗庸。1938年12月,罗庸、叶玉华撰《唐人打令考》,认为P.3501舞谱是唐人打令谱,有商榷于半农《敦煌掇琐》之“舞谱”定名。罗、叶认为该谱是为唐人打令谱,对其研究的发现过程有详细的描述:
二十五年春(1936年),庸在北京大学讲文学史,至令词之起源,博涉旧说,鲜能当意。因忆刘半农先生所辑《敦煌掇琐》中有题名“舞谱”之残篇,其目皆令词恒调;意或可由此寻觅一新途径,以求得令词之由来。嗣检朱子语类,于第九十二卷中得“唐人俗舞谓之打令”条,因联想及于全唐诗所收酒令中,亦有“送摇招由”之目,张炎词源讴曲旨要中,亦有“南歌子两段慢二急三”之语,可资互证。[注]罗庸、叶玉华:《唐人打令考》,《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38年,第219页。
罗庸在该文中由谱到令进一步辟《敦煌舞谱释词》一节,专析“舞谱”字录,再次肯定舞谱乃唐人打令俗谱,其引《朱子语类》云:
唐人俗舞谓之打令,其状有四:曰招,曰摇,曰送,其一记不得。盖“招”则邀之意,“摇”则摇手呼唤之意,送者送酒之意。……舞时皆裹幞头,列坐饮酒,少刻起舞。有四句号云:“送摇招摇,三方一圆,分成四片,送在摇前”……据此,所谓瓦谜者,本打令舞容……非敦煌残谱,今人殆无从解此瓦谜耳 。[注]罗庸、叶玉华:《唐人打令考》,《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38年,第226页。
文后,罗庸并再言半农《敦煌掇琐》中舞谱残谱为打令谱,如其强调:“敦煌残谱藏巴黎图书馆,刘半农先生传录归国,刻入《敦煌掇琐》中。初未审其性质,拟名舞谱。今案各谱调名,皆唐五代令词,送摇诸目,亦与中山词话朱子语类合,其为打令谱子,当属无疑”[注]罗庸、叶玉华:《唐人打令考》,《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38年,第226—227页。,遂详解各词令及十三字目。
罗庸与其生叶玉华的《唐人打令考》,是《敦煌掇琐》录舞谱后第一篇关于P. 3501舞谱研究至深的学术论文,虽有部分观点值得商榷,但近八十个春秋已过,今读仍彰显其浓厚的学术含量。
1938年《唐人打令考》是1925年《敦煌掇琐》后在舞谱方面的研究,并仍是在《敦煌掇琐》舞谱介绍的基础之上展开的,亦即《敦煌掇琐》对时人打开了敦煌舞谱存在的视野,后之学者多汲氧于此,仅此一点,痛惜英年早逝寿终仅四十有三的刘复,其功实不可没。
1938年,注定是30年代敦煌乐舞研究的盛年,也是敦煌乐舞研究成果卓硕的一年。先是林谦三氏的敦煌曲谱研究开始成果发表之始,也是对敦煌舞谱录字展开研究之始,罗庸在敦煌舞谱“十三字目”的动作所示上展开的研究,穷籍索史,极见功力。是年,敦煌曲谱与舞谱研究,国外与国内各占一半,平分秋色。我国学者在敦煌舞谱方面的研究,显然早期走在世界前列,这与能早在1925年伯希和劫经后八年,半农《敦煌掇琐》中辑录敦煌舞谱有着重要的关系。
四
1942年,冒广生撰《疚斋词论》,亦立《敦煌舞谱释词》一节,专谈舞谱内字录的解释。并坦言由《掇琐》而知舞谱,且更受罗、叶《唐人打令考》文思的启发,如其文云:
往阅《敦煌掇琐》所载舞谱,辄思为释其词,以行箧携书无多,未敢下笔。自顷叶君玉华以所撰《唐人打令考》见寄,援引博洽,佳士也。《打令考》附此谱残卷,兼有释词。略贡所知,复于叶君。[注]冒广生:《疚斋词论》,载张璋等编纂:《历代词话续编》(上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319页。
文中冒先生对《唐人打令考》多有肯定者之外,对《舞谱》中字目亦发表了一些不同的见解,认为“与”乃“由”之残字;认为“令”非为小乐器,是“律录事所司之令”,提出了“据”当读“如”字、“约”是舞者自束其腰、“拽”谓声音等重要观点。
冒广生《疚斋词论》是《敦煌掇琐》《唐人打令考》后最重要的一篇敦煌舞谱研究的文章,也是敦煌舞谱研究第三大力作。从发表的时间(1925年、1938年、1942年)看,国人研究的间隔逐渐缩小。
1946年,向达发表《唐代俗讲考》[注]向达:《唐代俗讲考》,《国学季刊》1946年第6卷。,该文初稿发于1934年,时向达尚未访欧,是文的补善重发正是向达引用了其访欧后所见之英法藏敦煌文献材料,如其引文所言:“本文初稿曾刊《燕京学报》第十六期,其后获见英法所藏若干新材料,用将旧稿整理重写一过。一九四零年五月向达谨记于昆明。”[注]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8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294页。向达《唐代俗讲稿》文后的补录正是引用了新获见的材料,为1934年发表于《燕京学报》第16期文所不载,即《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而该附录之材料正是与P.3838敦煌曲谱正背共用之纸卷。文下向达有说明言:“此卷原本今藏巴黎,编号Pelliot 3808。案:唐明宗生于九月九日,因以此日为应圣节……正可为此卷证明”[注]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335页。。这就是今有多数文论作者细节不辨将敦煌曲谱的抄写时间引在933年9月9日的缘故,孰不知卷中卷背或有非同人同时所作之可能。事实上,依笔迹巡判,讲经文与曲谱确非同人所作,竟连曲谱亦为三人不同笔迹,曲谱的抄写或非一时之作,《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与同卷背曲谱的抄写更无同时作成可证。
1947年,自幼秉承家学的罗振玉第五子罗福颐在《岭南学报》发表了《敦煌石室稽古录》,详细记录英人斯坦因“调查之开始”“斯坦因氏取去古卷轴原委”“法国伯希和氏继取古卷轴之概略”“日本人购去古卷轴之约数”等敦煌古籍劫外情况[注]罗福颐:《敦煌石室稽古录》,北京:中国文化研究室,1947年。,备为详实,或第一次成目录性的敦煌遗书备录,惜未载乐舞谱之来龙去脉端详。
40年代,多数学者的敦煌研究是据半农的《敦煌掇琐》,如1946年周一良写《跋敦煌写本“海中有神龟”》[注]周一良:《跋敦煌写本“海中有神龟”》,《大公报文史周刊》1946年12月。,是据《敦煌掇琐》第一八所收伯希和二一二九号卷子而写。
再如1947年,与向达商榷“唐代俗讲”的关德栋,写《〈丑女缘起〉故事的根据》[注]关德栋:《〈丑女缘起〉故事的根据》,《中央日报·俗文学》第9期,1947年12月19日。,文首云:“在《敦煌掇琐》(刘半农先生编)里面,第一个给我们介绍了一篇比较完整的‘缘起’——《丑女缘起》”。[注]关德栋:《〈丑女缘起〉故事的根据》,载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81页。
另如1948年,周一良撰《敦煌写本杂抄考》[注]周一良:《敦煌写本杂抄考》,《燕京学报》1948年第35卷。,是据《敦煌掇琐》中辑第七七号所收伯希和二七二一号卷子而写。
《敦煌掇琐》最早收有敦煌舞谱,时鲜有人据《敦煌掇琐》中的敦煌舞谱而行考证者。据笔者考,周一良是半农《敦煌掇琐》收舞谱后对舞谱最早进行校录的人[注]按:1938年,罗庸只是针对《敦煌掇琐》P.3501舞谱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并未对刘复抄谱进行有针对性的校录。。周一良注意到,并据日人神田喜一郎之藏法国敦煌写本影印进行校注[注]按:周一良对日人神田喜一郎之《敦煌秘籍留真》有跋,题为《跋敦煌秘籍留真》,原刊《清华学报》1948年第15卷第1期。,认为刘复《掇琐》中舞谱“挼”字有误,即认为刘复将“接”一律误抄为“挼”字,如其文云:
书中[注]按:书指据神田喜一郎藏法国敦煌写本影印,择六十三种,于1938年在京都出版。所收之写本曾经发表或已为当代学者研究利用者刊缪补缺切韵,智骞楚词音,舞谱等。所景印虽只寥寥数行,偶亦有足据以订透写之误,祛学人之惑者。如六三号舞谱(伯希和三五O一号)即可以订正《敦煌掇琐》中透录之误数处。最重要者为写本“接”字,《掇琐》因形近一律误为“挼”,遂不可通矣。[注]见周一良著、钱文忠译:《唐代密宗》,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2年,第207页。
周一良介绍,神田氏该书“每种影印一二叶,有题记者兼存其题记。惜只鳞片羽,复不注明原存行数。足供谈书法源流者之考镜,而裨益于学术研究者无多”。因此,周一良认为是书不注明行数等原本详细情况,于研究者无益,但残卷有题记具有学术价值,即“唯其所收残卷之题记颇有值得注意者,在巴黎之写本未印行发表前,此书要亦为治敦煌之学者所不废也”[注]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第366页。。故周一良才有注意日人所影敦煌舞谱,才有对半农《敦煌掇琐》舞谱相比较的考证。然周氏所考或因仓促,其认为半农将“接”通抄为“挼”是为有错。半农有抄“挼”字并无有错,舞谱中既有接,又有“挼”。“接”“挼”并存,况以“挼”字为多,目前所审,“接”字的出现次数非常之少。如S.5643号《蓦山溪》舞谱有“舞舞 舞挼挼 挼 挼挼奇 送据 ”字样。 P.3501《遐方远》舞谱有“送送 挼挼挼 送 据据据 头头”的字样。《南歌子》舞谱有“舞挼 挼送挼 送送 奇送奇 奇据”字样等,多为“挼”字,非为“接”字。一如图4敦煌S.5643号舞谱所示。

图4 敦煌S.5643号舞谱
40年代除周一良后,亦多有学者研究敦煌文献,颇多为经籍卷子,如唐文播《巴黎所藏敦煌老子写本综考》(1944)[注]唐文播:《巴黎所藏敦煌老子写本综考》,《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4年第4期。、谏候《关于老子化胡的故事——跋巴黎藏敦煌卷子老子化胡经》(1946)[注]谏候:《关于老子化胡的故事——跋巴黎藏敦煌卷子老子化胡经》,《图书月刊》1946年第1卷第4期。、陈槃《敦煌唐咸通抄本三备残卷解题》(1948)[注]陈槃:《敦煌唐咸通抄本三备残卷解题》,《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8年第10期。。
1949年,王庆菽遍阅英法藏敦煌卷子抄本,并将部分重点拍了照片。王庆菽详细地查看了英法藏敦煌卷子,诚如其所云:
我请求将七千卷子遍阅一次,以便自己搜集所需要的俗讲,变文和通俗文学等等的资料。经过该室室长福尔敦(AS·Fulton)同意后,我开始由第一号看起……先将上半盒借给我,看完交还后,再借下半盒,如是一盒又一盒,不停止、不间断的看下去。[注]王庆菽:《敦煌文学论文集》,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3页。
并说到了卷子中的“诗、词、曲”内容,云:
卷子翻阅一遍后,知道共有六千九百八十号……我除将变文和笔记小说全部影印外,还影印了诗、词、曲、医药方、占算、日历、户口、田亩等全部,和一部分古籍及其他杂料。计共二百六十二卷,一千一百八十二张。[注]王庆菽:《敦煌文学论文集》,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4页。
关于对法国国立图书馆敦煌卷子的抄录,王庆菽亦是很顺利,并尽心做了编录:
查巴黎所藏敦煌卷子,共为五千五百九十号,所以王氏(笔者按:指王重民)也没有编完……我除了二千号卷子是西藏文不懂不看外,因未编号的卷子尚有九百余,所以很想遍阅一次……每日由工人取出卷子二、三十盒,待我阅毕,由杜乃扬[注]杜乃扬(Dolleaus Guignard),又译圭娜尔,法国汉学家,时任法国国立图书馆抄稿室负责管理敦煌文献的职员。在中法教育基金会的帮助下,杜乃扬女士1934年亦曾来北京图书馆作为馆员交换研修学习。参见栾景河、张俊义主编:MODERN CHINA:CULTURE AND DIPLOMACY(下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女士点收后,再取其他,由是卷子可源源不绝的参考了。[注]王庆菽:《敦煌文学论文集》,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5页。
对英法所藏敦煌卷子的抄录摄影,王庆菽回国后,于向达、王重民、周一良、启功、曾毅公等合作编纂为《敦煌变文集》。此印《敦煌变文集》卷第五中有收“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其背后正是敦煌乐谱。
结 语
1949年前的研究,正如陈寅恪所言“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国人以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责任感,不但首次提出了“敦煌学”这一新兴学科,并以罗振玉、陈寅恪、王国维、胡适、刘复、王重民、向达等时之国内最负盛名的学者,推动了一大批新成果的出现,树立了我国学者在世界敦煌学研究中的学术权威,奠定了国人在世界敦煌学术研究之林中的研究地位。特别是1949年前,敦煌舞谱的最早“昭示”,刘复的最早定名及最早辑录,罗庸、冒广生、周一良的接力研究,他们的每一篇论文、每一篇著作都是中国学者向世界展示的研究成果,都是以中国学者的身份对敦煌舞谱研究的推进,在学界引领世界敦煌舞谱研究的方向与进展,取得了极大的文化自信。
在敦煌曲谱的研究上,王重民早在1934年就于法国国立图书馆拍摄了P.3808的敦煌曲谱,后开启了向达等人的研究。1938年日本学者林谦三积极展开研究,在京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担任讲师的国人傅芸子亦引录林谦三的成果,并比较敦煌与日本太平琵琶谱,建立中日敦煌曲谱研究的对接。
1949年前敦煌曲谱的研究逐渐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确定了敦煌曲谱是为琵琶谱,更确言之,敦煌曲谱是燕乐半字谱记录的唐人琵琶谱,即以燕乐半字谱为记谱形式记录的琵琶演奏乐谱。敦煌曲谱音位谱的高度等问题的解决,使学界达成了广泛的共识。
1949年前敦煌乐舞的研究,扩展了敦煌学研究的学术视野,充实了敦煌学的研究体系,揭橥了定名、定器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引起了敦煌学界向对敦煌乐舞研究的关注,推动了国际敦煌乐舞学研究的不断发展。敦煌乐舞研究的良好起步,为1949年后敦煌曲谱的不断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来敦煌乐舞文献的研究朝着不断向前的深度和广度发展提供了学术视域和视角。
综观1949年前敦煌乐舞研究的历程,可以看出40余年诸多学者的经年努力,在研究成果上取得的傲人成绩,对学界作出的极大贡献。正是经历了敦煌乐舞研究在发轫阶段的良好开端,也为后继学者在研究上提供了良好的范例,奠定了敦煌乐舞世界性研究的基础。
1949年前敦煌乐舞的研究为推动敦煌乐舞研究破解更多的难题,从而对中国古代乐舞在记谱的形式以及记录记载方面的认识与研究,对中国古代乐舞史一系列问题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史敦宇艺术作品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