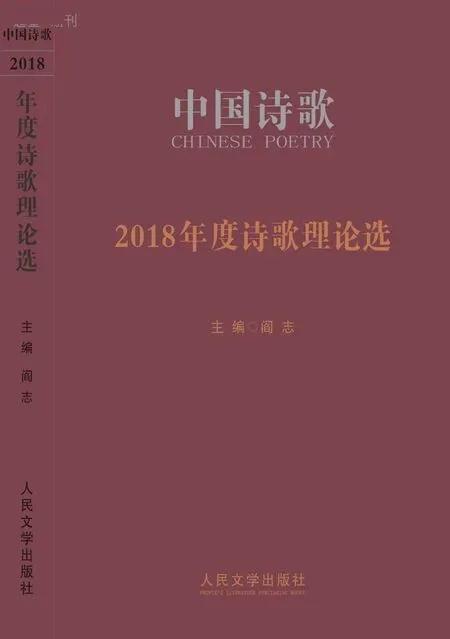论华兹华斯对汉语诗歌创作的影响
涂慧琴
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 是继莎士比亚和弥尔顿之后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 是英国浪漫主义的先驱, 英国“湖畔诗派” 的领袖。 18 世纪末, 他站在古典主义诗歌的对立面, 高举诗歌改革的旗帜, 勇于打破传统, 力求新颖自然。 他取“微贱的田园生活” (low and rustic life) 为诗歌题材;主张诗歌语言平民化、 生活化, 去矫饰堆砌求简单质朴; 摈弃传统的双行押韵体, 采用无韵诗体或歌谣体(韵脚是abab, 一三行八音节, 二四行六音节) (梁实秋: 《英国文学史》 第三卷,协志工业丛书, 1985 年版)。
20 世纪初, 华兹华斯及其诗歌作品陆续被介绍到我国, 不仅为中国现代诗歌打开了更加广阔的视野, 而且为其背离古代诗歌提供了语言和形式上的借鉴, 从而极大丰富了中国现代诗学内涵。 华兹华斯的诗学主张与黄遵宪、 梁启超等人倡导的“诗界革命” 和胡适倡导的“白话诗运动” 多有不谋而合之处, 并最终得到了中国新诗运动的回应。 然而, 一方面中国现代诗歌在特殊的历史场景中具有明显的现代性, 另一方面诗人们的血液早已被传统文化所侵染, 要彻底摆脱中国诗歌传统是不可能的, 因此, 中国现代诗歌以新的诗歌语言和形式阐释现代性的同时, 又具有相对独立的民族性, 这正是其独特性和丰富性所在。 那么,在此特殊的历史语境和文学语境中, 华兹华斯诗歌是如何对汉语诗歌产生影响的?
自然的语言
语言是诗歌的内部问题, 也是诗歌的本质体现。 大凡诗歌的革命, 基本上先从语言革命开始, 无论华兹华斯领导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运动, 还是我国“诗界革命” 和新诗“白话诗运动”,无不强调语言的变革。 为挣脱新古典主义的“诗歌辞藻” (poetic diction), 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 中主张, “这些诗的主要目的, 是在选择日常生活里的事件和情节, 自始至终竭力采用人们真正使用的语言加以叙述或描写, 同时又给它们以想象的光彩, 使平常的东西以不寻常的方式呈现在心灵面前; 最重要的是从这些事件和情节中真实地而非虚浮地探索我们的天性的根本规律” (W. Wordsworth: “Preface to Lyrical Ballads, 1802”, Stephen Gill, William Wordsworth The Major Work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596-597)。 他力主诗歌采用“人们真正使用的语言”,强调诗歌语言的朴素、 平淡却有力, 这是对统治当时英国诗坛的整齐、 刻板的英雄双韵体的有力抨击。 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的《抒情歌谣集》 掀起了英国浪漫主义思潮, 开启了现代英美诗语之风。
华兹华斯具有革命性的“自然” 诗歌语言观, 为中国新诗革命开辟了一种新的思路。 深受“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而作” 的儒家文学理念的影响, 晚清时期一些先进人士意识到要改变日益羸弱的中国, 需以诗和文学作为唤醒民众的工具,而中国传统诗歌无法承载新的知识, 表达新的思想, 沟通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情感。 因此, 梁启超等人提出“诗界革命” 的主张, 但他们的诗歌改革也只是在保存诗歌旧形式的前提下进行的, 诗歌的旧形式和新词语之间的矛盾必将导致这次改革的搁浅。 华兹华斯的诗作于1914 年由陆志韦译入我国后, 其纯净、美丽的诗歌语言呈现出的新境界, 给当时寻求病症的药方、 谋求出路的中国诗坛吹来了一股清新自由的海风。 在新诗理论建设和实践中付出了诸多的努力、 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的中国新文学革命的领袖人物胡适极力推崇华兹华斯的诗学语言观。 1919 年10月, 他在《谈新诗》 中曾引证华兹华斯的诗学语言观来说明自己的诗歌语言理论主张, “文学革命的运动, 不论古今中外, 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 一方面下手, 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 ……十八十九世纪法国嚣俄、 英国华次活(Wordsworth) 等人所提倡的文学改革, 是诗的语言文字的解放……这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活动, 也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 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 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 是不拘格律的。” (胡适: 《谈新诗》 ) 胡适从西方的文学革命中获得启示, 提出“诗体大解放” 的主张, 宣称“诗体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 一切打破: 有什么话, 说什么话;话怎么说, 就怎么说。 这样方才可有真正白话诗, 方才可以表现白话的文学可能性” (转引自谢冕: 《论中国新诗—— 〈中国新诗总系〉 总序》, 《中国新诗总系·第1 卷》, 姜涛分册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胡适的主张, 在当时中国诗坛是具有探索精神的, 是“五四” 时代精神的体现。 胡适、 陈独秀、俞平伯等为重建一种理想的诗歌秩序进行了诗歌创作尝试。
白话诗在尝试初期就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如白话的词汇贫乏、 白话诗缺乏美感等。 中国新诗运动提出的“白话诗” 虽说受华兹华斯“自然” 语言观的影响, 但并未像华兹华斯那样强调对“人们真正使用的语言加以叙述或描写”, “同时又给它们以想象的光彩”。 华兹华斯《迈克》 一诗写道, “……these fields, these hills/Which were his living Being, even more/Than his own Blood—what could they less? had laid/Strong hold on his affections, were to him/ A pleasurable feeling of blind love, / The pleasure which there is in life itself.” (……这些原野, 这些山岭/是他鲜活的生命, 甚至/比他的血液还要多——他们又怎会/不紧紧抓住他的心灵? 对于他/这是一种盲目的爱带来的愉悦, /这也是生活本身的愉悦。) ( W. Wordsworth: “Michael”, Stephen Gill, William Wordsworth The Major Work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226) 诗人对迈克与他赖以生存的原野和山岭的情感描写明朗而又深刻, 明朗在于他使用的朴素、 简洁、 自然的诗歌语言, 没有过多修饰的词藻, 深刻在于他使用平实的语言描述时, 赋予迈克和原野山岭的情感想象的光彩。 “罗斯金曾称华兹华斯是他那个时代诗坛上的伟大风景画家” (勃兰兑斯: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三分册·英国的自然主义》,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可以说他诗歌呈现出的画面感与他采用的诗歌语言是分不开的。周作人于1919 年11 月所作《画家》 一诗写道, “车外整天的秋雨, /靠窗望见许多圆笠, ——男的女的都在水田里, /赶忙着分种碧绿的稻秧。” (周作人: 《画家》, 《中国新诗总系·第1 卷》,姜涛分册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同样采用朴实、口语化的诗歌语言, 但《画家》 中耕种中的男女不如《迈克》中迈克的形象鲜明, 《画家》 中的“水田” 和“稻秧” 缺少《迈克》 中“原野” 和“山岭” 的灵秀, 它们与耕种者之间没有情感的互动, 只是冷淡的静物而已。 对新诗创作初期所缺乏的美的问题, 周作人提出“我只认抒情是诗的本分”, “经过许多时间, 我们才渐渐觉醒, 诗先要是诗, 然后才能说到白话不白话……” (转引自谢冕: 《论中国新诗—— 〈中国新诗总系〉 总序》, 《中国新诗总系·第1 卷》, 姜涛 分册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俞平伯则早在1919 年提出警示, “我们要紧记,做白话的诗, 不是专说白话。 白话诗和白话的分别, 骨子里是有的, 表面上却不很显明, 因为美感不是固定的, 自然的音节也不是拿机器来实验的” (转引自谢冕: 《论中国新诗—— 〈中国新诗总系〉 总序》, 《中国新诗总系·第1 卷》, 姜涛分册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虽则中国新诗在“白话诗” 尝试中存在着审美的偏差, 但华兹华斯的自然的诗歌语言观对其产生的深刻影响是不可否认的。 金东雷曾高度评价华兹华斯, 认为“他指给了我们一条文艺上的‘新的大道’。” (金东雷: 《英国文学史纲》, 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
平民的题材
华兹华斯取“微贱的田园生活” 为其诗歌题材。 他从语言、情感和形式方面解释了诗歌以田园生活为题材的必要性, 认为以田园生活为题材, 诗歌的语言更纯朴有力, 诗人对自然和人们的情感更易于表达, 对自然美的追求更能成为永恒的一部分。 他的以自然为主题的诗歌包括《致蝴蝶》 《先见》 《自然界万物之影响》 《黄水仙》 等, 其《序曲》 也含有大量的自然的描写。
华兹华斯对自然有其独特的认识, 他对自然的观察也是融入了个人的情感, 往往能与自然合二为一, 达到相融的境界。 如他本人所言, 诗人“比一般人具有更敏锐的感受性, 具有更多的热忱和温情, 他更了解人的本性, 而且有着更开阔的灵魂; ……他高兴观察宇宙现象中相似的热情和意志, 并且习惯于在没有找到它们的地方自己去创造” (W. Wordsworth: “Preface to Lyrical Ballads, 1802”, Stephen Gill, William Wordsworth The Major Work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603)。 他认为诗人观察宇宙万物比一般人更敏锐, 更热情, 并习惯创造热情和意志。 梁启超因此称其为“善观者”, 1900 年3 月1 日他在《慧观》 一文中写道: “无名之野花, 田夫刈之, 牧童蹈之, 而窝儿哲窝士于此中见造化之微妙焉。” (梁启超: 《慧观》, 《梁启超散文》, 鄢晓霞编选,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 梁启超高度评价了窝儿哲窝士(华兹华斯), 认为他能从普通人忽视的无名野花身上发现大自然的微妙之处, “微妙之处” 其实就是诗人所发现的大自然拥有的相似的热情和意志, 并与其合二为一。 无独有偶, 徐志摩在《征译诗启》 中说: “华茨华士见了地上的一棵小花, 止不住惊讶和赞美的热泪; 我们看了这样纯粹的艺术的结晶, 能不一般的惊讶与赞美?” (徐志摩: 《征译诗启》, 《徐志摩全集第六卷》, 梁实秋、 蒋复璁 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 年版) 这其实表明徐志摩在发现自然之美、 自然之微妙之处与华兹华斯有类似的感受。
徐志摩不仅在对自然万物的生命方面与华兹华斯有相同的感受, 还深受华兹华斯自然观的影响, 创作了许多关于自然美, 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诗歌。 徐志摩曾在华兹华斯读过的剑桥大学留学两年, 其间深受欧美浪漫主义的影响, 对华兹华斯欣赏有加, 认为他是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且认为他的不朽的诗歌多半来自对自然的吟诵, “你们知道宛茨渥士和雪莱他们不朽的诗歌,大都是在田野间、 海滩边、 树林里, 独自徘徊着像离魂病似的自言自语的成绩。” (徐志摩: 《话》, 《东方现代文选说明文选》,范仲文编, 东方文学社, 1933 年版) 华兹华斯笔下的自然富有灵性, 被赋予了神谕, 他借助诗歌, 再现了一个有独创性的大自然的形象, 对大自然做出了崭新的描绘, 这是在弥尔顿和汤姆森之间的那个时代中, 英国诗歌所缺失的部分(勃兰兑斯: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三分册·英国的自然主义》,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受华兹华斯《黄水仙》 影响, 徐志摩在十四行诗《云游》 中也勾画了一幅云在空际自在逍遥, 涧水在地面静静流淌的画面。
但华兹华斯与徐志摩不同的是, 前者能从自然中体会到自然对人类的爱, 并从中获得慰藉, 最终走出政治理想不得意的阴霾, 而后者往往在诗歌中寄寓了自己的爱情或理想, 渗透着淡淡的忧伤。 在《雪花的快乐》 中, 诗人将“我” 假设为“一朵雪花”, 在前两节赋予雪花独立、 自由的精神: “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 “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不去那冷寞的幽谷, /不去那凄清的山麓, /也不去荒街去惆怅——” (徐志摩: 《雪花的快乐》, 《新月派诗选》 修订版, 蓝棣之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年版) 在后两节将雪花男性化, 等着恋人“她” 来花园探望, 凭借身轻沾住她的衣裳, “贴近她柔波似的心胸——/消溶,消溶, 消溶——/融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 (同上) 显然, 雪花融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是自然与人和谐共处、 合二为一的隐喻,也是理想爱情的象征。 徐志摩的《康桥再会罢》 与华兹华斯的《自然景物的影响》 对自然的描写有异曲同工之妙, 前诗中“清风明月夜”、 “缦烂的云纹霞彩”、 “穆静腾辉的晚景”、 “清晨富丽的温柔”、 “缓和的钟声”、 “和悦宁静的环境”、 “圣洁欢乐的光阴” 等应和着后诗中“静静的夏夜”、 “柔波荡漾的湖水旁边”、 “远方的山峦”、 “星斗粲然”、 “橙红色晚霞”, 分别将诗人与自然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徐志摩在淡淡的忧伤离别情绪中, 又感到了一种力量, “但我如何能尽数, 总之此地/人天妙合, 虽徽如寸芥残垣, /亦不乏纯美精神; 流贯其间, 而此精神,正如宛茨宛士所谓/ ‘通我血液, 浃我心藏’, 有‘镇驯/矫饬之功’ ” (徐志摩: 《康桥再会罢》, 《新月派诗选》 修订版, 蓝棣之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面对离别的康桥, 心中虽有万千思绪, 但此刻诗人如华兹华斯一样, 感受到天人妙合带来的精神和力量。
朱湘曾翻译过华兹华斯的《迈克》, 在1927 年去美国留学前后创作的诗歌较多接受了外国诗歌的影响, 其中华兹华斯的田园诗话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然是朱湘诗歌的主题, “杨柳呀风里颠摇; /荷叶呀翠盖, /荷花呀人样娇娆。 /日落, /微波, /金丝闪动过小河。” (朱湘: 《采莲曲》, 《新月派诗选》 修订版, 蓝棣之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在朱湘笔端,自然万物与人宁静、 和谐相伴: “菡萏呀半开, /蜂蝶呀不许轻来, /绿水呀相伴, /清净呀不染尘埃。 /溪间/采莲, /水珠滑走过荷钱。 /拍紧, /拍轻, /桨声应答着歌声。” (同上) 诗人虽未明写人物, 但“采莲”、 “水珠滑走”、 “桨声” 和“歌声” 暗示了人物的出场, 于有声处展现了一幅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景象。这样的景象在《小河》 中也有同样的表达, “轻舟是桃色的游云, /舟子是披蓑的小鱼” (朱湘: 《小河》, 《新月派诗选》 修订版, 蓝棣之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长柳丝轻扇荷风, /绿纱下我卧看云天; /蓝澄澄海里无波, /徐飘过突兀的冰山。” (同上)
自由的情感
华兹华斯强调“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 (For all good poetry is the spontaneous overflow of powerful feelings) (W.Wordsworth: “Preface to Lyrical Ballads,1802”, Stephen Gill, William Wordsworth The Major Work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598)。 这种强调“情感” 的主张具有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和大胆的创造力, 它冲破了传统的古典主义诗歌的藩篱, 颠覆了一切以理性为衡量标准和评价尺度的真理。
华兹华斯关于“情感” 的诗学主张传入我国后, 立即触发了时代的感受。 1919 年, 田汉在《诗人与劳动问题》 一文中指出, 华滋渥斯(华兹华斯) 是主张“诗歌与其重形式, 宁重内容上情绪的空想的要素” 诗学观点的最重要的人(田汉: 《诗人与劳动问题》, 《少年中国》 1919 年第1 卷第8 期)。 闻一多主张诗歌典型化就要注重想象, 强调激情(葛桂录: 《中外文学交流史: 中国—英国卷》,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5 年版)。 郭沫若则用“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 和“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 来表达华兹华斯所说的“情感的自然流露”, 他指出“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 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 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 生底颤动, 灵底喊叫, 那便是真诗, 好诗, 便是我们人类底欢乐底源泉, 陶醉底美酿, 安慰底天国” (田汉、宗白华、 郭沫若: 《三叶集》, 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0 年版)。 因此, 在他个性解放的诗歌里让人能感受到他个人觉醒后向群体、向整个时代发出的呐喊声。 他在《女神》 中发出的呐喊、 凤凰再生的美妙歌声、 天狗要吞下日月的狂呼, 都是他在血泪和黑暗中喊出的自焚中的新生热情。 他声声的呐喊是其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 是一个清醒的自我对“你” 的呐喊, 对“他” 的呐喊,对“我们” 的呐喊, 是对自由发出的呐喊声: “我们自由呀! /我们自由呀! /一切的一, 自由呀! /一的一切, 自由呀! /自由便是你, 自由便是我! /自由便是“他”, 自由便是火!” (郭沫若: 《凤凰涅槃》, 《中国新诗总系·第1 卷》, 姜涛分册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华兹华斯认为诗歌的“情感” 可以给予动作和情节以重要性, 诗人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去探寻。 如《阿丽斯·费尔》 (陆志韦译为《贫儿行》 ) 中对纯真弱小女孩的同情和道德关怀,《我们是七个》 中天真的孩子对死亡观念的理解, 《宝贝羊羔》中小女孩的纯真善举, 《傻小子》 中母爱的伟大和普通人身上具有的同情感, 这些情感都是普通人身上具有的高贵品质, 是属于大自然的, 是一种自然的流露, 不属于习俗。 而诗人是善于发现普通人身上具有这些高贵品质、 情感的人, 具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慧眼。 在英国工业革命发展上升时期, 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致使英国整个乡村田园景象遭受破坏, 华兹华斯生活行走在乡村田园间, 看到的不再是斯宾塞笔下理想的、 浪漫的田园生活, 而是饱受生活艰辛却依然保持着纯真的人们。 他们有破产的牧羊人、乞丐、 傻子、 穷人……华兹华斯“创作的触角广及大众阶层的生活样态及情感体验, 呈现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照, 展现人道主义关怀” (邹建军、 覃莉: 《华兹华斯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学》,《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12 年第5 期)。 华兹华斯对这些善良的、 纯朴的、 大众阶层人们流露出的关爱之情是自然的, 发自内心的, 这表明了他具有的一种人道主义的立场。 华兹华斯许多优秀的诗作表达了他对穷苦大众的深切同情, 其最初被译入我国的代表诗作多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有关, 这与当时中国文学的价值取向相吻合。 陆志韦于1914 年3 月在《东吴》杂志1 期2 卷发表的译作《贫儿行》 (Alice Fell) 和《苏格兰南古墓》 (A Place of Burial in the South of Scotland)、 徐志摩于1922年翻译的《葛露水》 (Lucy Gray)、 贺麟和张荫麟等8 人于1925年翻译的《露西组诗》 第二首《威至威斯佳人处避地诗》 (“She dwelt among the untrodden ways” ) 及朱湘翻译的《迈克》 (Michael) 都是华兹华斯关于贫苦大众的优秀代表作品, 这些译作“与国内民生民情相似”, “符合了当时中国文学的主流价值取向” (同上)。 当时的汉语诗歌在表达劳苦大众生活疾苦方面,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胡适的寒风中奔走的人力车、 刘半农的穷苦的卖萝卜人和像卖炭翁那样艰辛劳作的铁匠、 沈玄庐《十五娘》 中十五娘夫妇、 刘大白《卖布谣》 中的哥哥嫂嫂等穷苦大众, 在穷困的生活中仍保持着勤劳善良的贫民本色, 诗人们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悲悯情怀。 徐志摩的《谁知道》 写道: “我在深夜里坐车回家, /一堆不相识的褴褛的他, 使着劲儿拉; /天上不明一颗星, /道上不见一只灯; /只那车灯的小火/袅着道儿上的土——/左一个颠簸, 右一个颠簸, /拉车的跨着他的蹒跚步。” (徐志摩: 《谁知道》, 《新月派诗选》修订版, 蓝棣之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深夜”、“车灯的小火”、 “颠簸” 和“蹒跚” 道出了车夫拉车的艰辛,“褴褛” 点明了车夫的生活窘境, “一堆” 则说明了贫穷车夫的普遍性, 诗人在此虽未直接表明自己对车夫的悲悯之情, 但这种情感渗透在字里行间。 在当时的社会, 诗人们普遍将目光投向了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 即使是强调“诗是贵族的” 的康白情,也不得不承认: “我们却仍旧不能不于诗上实写大多数人底生活, 仍旧不能不要使大多数的人都能了解, 以慰藉我们底感情。所以诗尽管是贵族的, 我们还是尽管要作平民底诗。” (康白情:《新诗底我见》, 《少年中国》 第1 卷9 期)
尽管华兹华斯认为诗歌的情感是一种自然的流露,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情感是泛滥的而无节制的。 他指出“凡有价值的诗, 不论题材如何不同, 都是由于作者具有非常的感受性, 而且又沉思了很久” (W. Wordsworth: “Preface to Lyrical Ballads,1802”, Stephen Gill, William Wordsworth The Major Work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598)。 他提出了“强烈情感” 和“沉思” 的关系, 实际上, 这是他对诗歌创作中感性和理性关系问题的思考。 这二者看起来是一对矛盾, 华兹华斯却辨证地看待了它们之间的关系, 继而指出, “因为我们的思想改变着和指导着我们的情感的不断流注, 我们的思想事实上是我们已往一切情感的代表; 我们思考这些代表的相互关系, 我们就发现什么是人们真正重要的东西; 如果我们重复和继续这个动作, 我们的情感就会和重要的题材联系起来。” (同上) 虽然深受西欧浪漫主义文学和华兹华斯诗学观点的影响, 新月派自诗歌活动的正式开始就打出了反对“伤感主义” 和“伪浪漫主义” 的旗帜。 闻一多对“顾影自怜”、 “无病呻吟” 和“多情的眼泪” 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在《死水》 的创作中明确提出了“理智节制情感” 的美学思想。 徐志摩看到了从卢梭的《忏悔录》 到哈代的一百七十年间, 人类冲动性的情感脱离了理性的挟制, 在《白朗宁夫人的情诗》 中指出情感应受理性的相当节制与调剂。 梁实秋也指出文学的力量在集中和节制, 节制就是以理智驾驭情感, 以理性节制想象。
早在二百多年前, 华兹华斯的诗学观念就撼摇了新古典主义诗歌的统治地位, 宣布了英国浪漫主义的到来。 华兹华斯那朴实清新、 口语化的诗歌语言, 自然的诗歌题材和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 都是使他成为伟大浪漫主义诗人的重要因素。 在20 世纪初期, 随着他的诗歌作品和诗学主张被介绍到我国, 他的诗歌对汉语诗歌, 特别是中国现代诗歌产生了深厚的影响。 他的诗歌启发了中国现代诗人在以诗救国的时代, 寻到了一条新的出路, 为中国新诗革命“白话诗” 的到来提供了理论借鉴, 是一种积极的探索精神的体现。 然而, 华兹华斯诗歌对汉语诗歌的影响不仅深厚而且深远, 即使是在汉语诗歌不断走向多元化的时代, 他的诗歌仍为许多中国诗歌爱好者所吟诵, 他的诗学主张仍被许多诗歌研究者所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