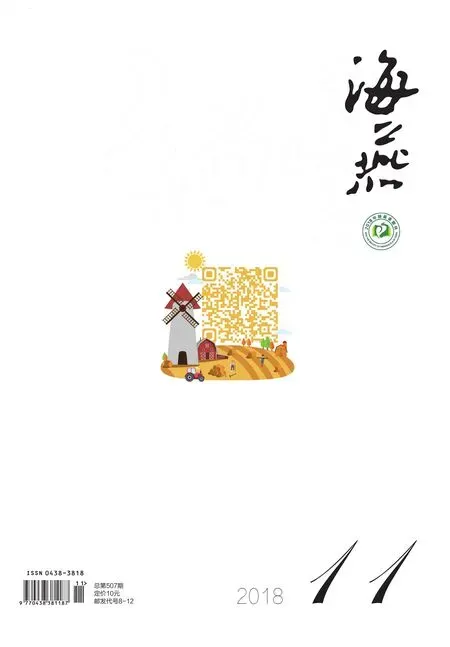罪的逍遥与正义的救赎
□张 宁
李轻松的长篇小说《跟孤独的人说说话》通过一起十年前的命案,引出一个家庭两兄弟的不同命运故事。其间的司法推理与心理悬疑带给我们的是关于正义、道德和人性的深层思考。在扑朔迷离的情节演绎中,每一位当事人都经历了令人唏嘘心灵的炼狱。罪与罚都不只是法律意义上的,欲望在爱的名义下充当了灵魂创伤的止痛剂,真正的自由只能来自正义的救赎。
一、罪与非罪
母亲带着双胞胎兄弟去看电影,回家的路上遇见醉汉殴打自己妻子,兄弟俩上前制止,醉汉抓过路边西瓜摊上的刀与两兄弟拼斗,结果混乱中醉汉被刺倒地身亡。弟弟向警方承认是自己刺的那一刀,后被判入狱十年。十年后,弟弟出狱,醉汉的妻子认为凶手是哥哥,于是要求重新侦查审理此案。最后真相大白,弟弟的确是替哥哥顶罪坐的牢,那一刀是哥哥刺的,但事实上致命的却不是那一刀。
读了这个故事,首先一个问题是:魏锋为什么心甘情愿去顶罪?
父母之所以决定让弟弟魏锋去顶罪,因为当时哥哥魏东已经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弟弟落榜了。懂事的魏锋觉得上不了大学也会成为家里的累赘,为了整个家庭的利益同意了这个决定。其实,从心理学上分析,魏锋的妥协还有一个深层原因,那就是他在内心深处不止一次地有过杀人的念头,尽管实际动手的是哥哥。
这就要说到有家暴行为的父亲,父亲经常殴打母亲和两个孩子,而母亲总是逆来顺受。兄弟两人都曾有过那样的一闪即逝的念头——反抗,杀了他!在谈起幼时经历时,魏锋说:“那一刻,我把心里的委屈都忘了,只有一个冲动,我真想杀了他!”这符合弗洛伊德的论断:“在童年形成的精神冲动的原料中,对父母爱一方恨一方是其中的主要成分,也是决定后来神经症症状的重要因素。”(弗洛伊德:《释梦》,孙名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60页。)所谓“弑父情结”在从小生活于家暴中的两兄弟心中,已经转化为了真实的暴力倾向。刑警苏宁问魏峰:“你在那个男人追打老婆的时候,也产生要杀死那个男人的冲动?”魏锋的答案是“有”。无论是魏东还是魏锋,当双胞胎的他们作为一个整体从局外进行反观的时候,是谁刺的那一刀并无太大分别,那是他们同样都有过的无数次的闪念。正因如此,当事情发生以后他们两个是都有负罪感的。
魏锋由于是心甘情愿去坐牢,所以也没有太多心理不平衡。魏锋用十年的监狱生活完成了弑父情结的自我救赎。从心理层面说,魏锋的入狱客观上起到了一种拯救的作用,以法之名、以捍卫正义的形式完成的自我的心灵拯救。魏东却在对罪的自责、愧疚与正义的拷问中煎熬了十年——对逝者的自责和对弟弟、家庭的愧疚,以及如何赎罪。魏东顺利读完大学,又留学日本,回国后成为公司高管、技术白领。然而,十年间,哥哥魏东始终都无法逃脱良心的谴责。被那起命案所困扰,加上张宝珍母女经常通过电子邮件、QQ、电话等不同途径对他进行报复性威胁和恐吓,魏东患上严重的抑郁症。看似逍遥法外的魏东,其实每天都在经历心灵的炼狱。那么第二个关键问题就是:魏东为什么始终无法坦然面对过去,并且最终崩溃?
二、爱与欲望
把魏东的情感历程剖析清楚,也就回答了前文留下的第二个问题。
哥哥魏东在故事中有三段恋情,分别是和麦穗、托娅和包小芸。这三位女性无论是从家庭出身、成长环境、教育背景到各自的性格、习惯、形象、气质都迥然不同。麦穗是魏东初恋女友,两个人可以说是青梅竹马,作为心理医生的麦穗温柔体贴,知书达理,处处为人着想,可以委屈自己成全别人,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型女子;托娅来自蒙古大草原,美丽活泼,单纯直爽,凡事由着自己性子来;包小芸是下岗工人的孩子,小学文化,内向孤僻。如果说魏东抛弃前女友麦穗而与托娅走进婚姻是喜新厌旧,那么在婚内与包小芸精神出轨则非常匪夷所思。
其实,这两次转变都和性有关。他放弃麦穗,是因为他发现自己不再是真正的男人,他不想在那份深沉的爱面前失去自尊,而恰恰是野性疯狂的托娅让她做回了男人。在严重的抑郁症的折磨下,自卑魏东一度失去了活下去的欲望,他有过许多次自杀的念头,为此他曾求助应召女郎,然而无济于事。毫无疑问,其抑郁症的根源就是“那件事”——是他而不是弟弟杀了那个醉汉,但受到法律惩罚的却是弟弟而不是自己。正如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斯维德里加依洛夫所说:“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不在这方面寻欢作乐,我也许会拿手枪自杀。”(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岳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548页。)魏东也正是在这本书的空白处写到:“几年前父母帮我逃脱了罪责,却给我的心灵戴上了枷锁,生不如死……”“那件事”也使他产生了弟弟出狱后会对他进行报复的妄想症,于是托娅和弟弟的正常交往在他看来都是充满暧昧,结果是他和托娅再也不能成功进入那种美妙的状态——他又一次濒临死亡。这个时候,电话情人包小芸出现了,两个人在虚拟时空极尽两性之缠绵,他似乎重新觅到一线生机。
对于魏东来说,麦穗是完美的,真实的,托娅介于真实与幻觉之间,包小芸则是想象中的存在。那么魏东移情的过程,其实就是他从真实堕入虚无的过程,也是他迷失自我、在幻象中自证的过程。弗洛伊德视性本能为人的一切行为的动机,“把人看作是一个性欲的存在”。(霍兰德:《后现代精神分析学》,载《外国文学》,1993年第2期。)如果说弗洛伊德的观点过于绝对,那么,至少性的力量让魏东做回了男人,更让其重新“活”了过来。
也就是说,魏东恰恰是和被他抛弃的麦穗之间的感情才是真正的爱情,因为内心深处的负罪感使他觉得无法面对近乎完美的麦穗,所以他和麦穗在一起时不会感到快乐;魏东和成为他妻子的托娅是爱与性两者参半,曾经欢喜,曾经甜蜜,但他越来越觉得托娅对不起自己——其实是他自己因为有罪而越来越自卑,于是将自己的负罪感转嫁给托娅,折磨托娅;而和从未发生性关系包小芸在一起却是为了欲望的满足,因为裸裎的灵魂萍水相逢,爱与不爱两不相欠,幻想之中没有现实的责任与压力,尽情放飞自我,任性逍遥。这种逍遥是通过幻想,甚至是通过性虐待实现的,不只是对托娅的性虐,魏东与包小芸的虚拟性关系也充斥着语言的性虐。他所追求的是折服受虐者的自由并化归己有,然而“性虐待狂者愈是热衷于把别人当作工具来对待,这自由就愈是逃离他”。(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496页。)因此,当魏东一次次发现终究要从幻想回到现实,他最终的结局只能是崩溃。
三、道德与自由
分析这部小说要回答的第三个问题是:完成救赎且已经自省的魏锋何以又重回炼狱爱上自己的嫂子?回答了这个问题,也就清楚了魏东是如何完成救赎的,以及这一救赎背后的深刻隐喻。
魏锋年少入狱,在监狱里有规律地作息,早睡晚起,锻炼身体,读书看报,反思人生。更重要的是,看似身体失去自由的与世隔绝的生活环境让他多了一份自然脱俗的心态,多了身体的羁绊却少了心灵的约束。书中这样描写他出狱那一刻的样子:“魏锋的眼睛是空洞的,没有托娅也没有魏东,而是仰着头看着天,又低下头看着地。”结合前后情节我们可以很容易判断出,其眼神的“空洞”绝不是呆滞、呆傻,而是一种超然。
魏锋出狱后接触的第一个异性是嫂子托娅,这个来自草原的女孩天真无邪、任性自我。从托娅的视角看,家教严苛的魏家就像一座监狱。那么在法律意义上无罪的魏锋从高墙内望向道德社会的时候,外面的世界又有多少真正的自由呢?此时的监狱不正是边沁眼中的“全景敞视建筑”吗?(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24页。)这也是魏锋爱上打铁的真正原因,在那个全景敞视的动物园中没有人会给他这个异类——坐过牢的人获得工作的机会,只有老铁匠对他没有世俗偏见,只有打铁才能让他找回生命的力量。表面看起来,一个刚走出被限制了人身自由的有形牢狱,一个来自无拘无束的大自然,可是这完全相反的生存环境却有着极为相似的特征:远离世俗生活、生命样态单纯,两个人同样毫无世故之心,同样走进了一个自由被限制的场域。因此,他们可以心有灵犀。
然而极度自卑和敏感的魏东将弟弟和妻子的投缘、谈得来视为一种挑衅,忍不住挖苦魏锋并折磨托娅,父母同样以道德之名站在魏东的一面,不觉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心理伴随着他在托娅面前再次成为性无能者,进而变本加厉地挖苦、折磨,如此恶性循环,直到终于将妻子和弟弟逼到了真正相爱的地步。对于魏锋和托娅而言,起初并无太多想法,在魏东的不断强化之下,两颗本来就极为相似的灵魂慢慢靠近,但事实上两人出于道德的考量,始终保持着克制。也许他们并不知道,感情上的事越是克制越是强烈。实际上,这种克制体现的是一种自由精神。一如康德所说,正是因为人是自由的,可以为自己确立法则,道德行为才成为可能。
这种自由,克制的能力,恰恰是魏东所丧失的或者不曾拥有的。他在和托娅热恋时的性活动中所感受到的以及和包小芸的虚拟恋情中所体验的,表面上看是自由,然而那其实是一种伪自由。当托娅作为野性与自由的象征出现在魏东的生活中,魏东眼前一亮、灵魂一震,爱上托娅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托娅包括托娅的马所代表的一切恰恰都是疗愈他抑郁心灵的良药——“从此,托娅和马将是他生命里的宝贝”。这就是托娅引领魏东和她在奔驰的骏马上以及露天的草地上做爱这一情节的象征意味。
然而,魏东并未真正享有这一自由,他只是在那些激情燃烧的瞬间出现了种种幻觉,他把这些幻觉视为自由。“所谓亲吻、柔情都不过是柔软的床上用品,只服从肉体生命的欢悦,只配用来擦洗人身上渗出的带有印刷油墨的涓涓鲜血,让肉体复归于其本己的自由”,进而“用自然性的肉体来证明自己的人性”。(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17页。)为了生命自由而作下恶,为了求得真实生命又进入虚无世界。所以魏东很快失去了托娅和他的马,也失去了他以为是自由的自由。至于他对包小芸的迷恋,无非是饮鸩止渴,他被欲望所控制,失去的恰恰是作为超越了动物性本能的人的自由。在小说结尾,只有当托娅心灰意冷决绝地和他解除婚姻,只有当他见到包小芸之后得知她作为当年被刺死的包福林之女,只有当他“死”过一次之后成为一无所有的流浪汉,魏东才真正觉醒,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
结语
萨特认为人的自由是被给定的,是不得不自由的自由。反过来,当一个人真的失去这种不得不自由的自由,也就失去了真正的人之为人的要素。通往自由的道路,也是正义的救赎之路;罪的逍遥无论怎样狂欢,终究指向心灵的炼狱。关于这部小说,其实还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另外几位人物也值得深入分析,如麦穗、包小芸,以及兄弟俩的父母魏子安和韩如梅、包小芸的母亲张宝珍,他们都是徘徊在正义与罪恶边缘的迷路者,无论是法律意义上的还是心灵意义上的。本文篇幅所限,不能赘述,留待后续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