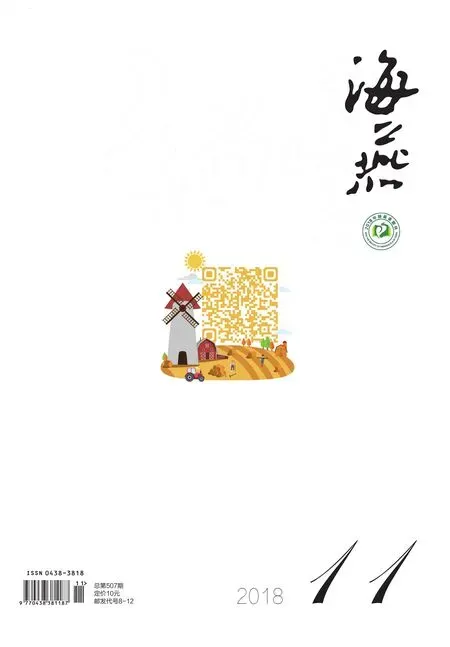在低处
□微雨含烟
一条身首异处的鱼
我认为身材矮小的婆婆
是个没有大力气的女人
当她把一条十斤重的鲢鱼,拦腰截断
我忽然对这个小小身体
有了敬畏之心
一条被分成两半的鱼
一半冻在婆婆家的冰箱
一半被我送给从不吃鱼的爸爸
父亲信佛,不杀生
不动荤,我不知道
那半条鱼在他那里
会不会得到超生。我只是依婆婆叮嘱送去
尽一尽心意。
这被强加的派送,是不是触犯了
某种戒律?我看到父亲
面对那半条鱼的表情
像秋天的树干对即将落下去的叶子们
那般无奈和自责
一条身首异处的鱼
在这样的秋天里,遥遥地
呼唤着自己的另一半,并把另一个自己
叫成悲秋。
在低处
低处的叶子们飞舞
仿佛永不再与树重合
许多人努力向上,试图离地面高一些
离光线近一些
使举起的手能攀到想要的事物
索求的太多,以至于
微笑是一件奢侈品
当我们顺着盘山路走到墓园
纷扰也随之退去
我们看到飞起来的柳絮和
凭吊亲人们的花环
以及那些随风起舞的纸蝴蝶
我们终将不能越过它
我们亲手点燃了
终将逝去的那些。
挽歌
母亲最后流下两行眼泪就撒手而去
我看过她一生里的几次哭泣
没有一次因为不舍
只有这最后的告别
无声地揪紧每一个人
病重而坚强的母亲
从不对我说她的痛
她说得最多的是“好些了”
当我抱着她的身体
当我抱着蜷在盒子里她的
没有烧碎的腿骨
她是安静的,轻的
两年了,当我在一场大风中
怀着莫名烦躁打开一首乐曲
母亲突然出现
没有任何言语,只有耳机里的水声
仿佛濯洗
她不胜针剂的紫色手臂
在风中轻轻挥着
那告别,那召唤,那看着我的
流泪的眼睛,让活着的我生出一丝羞愧
我有什么理由憎恨莫须有的虚无
三只桃子
三只桃子被我放在袋子里
一个小小的承诺(不经意的)
跟着我穿行于人群中
在最不可能的时候制造意外
或者找个理由见一见
人群中不被发现的另一个自己
三只桃子是干净的
甚至被人忽略,现在
它们中的两个
跟随你回到故乡,第三只在我的背包里
不知什么时候
会在内心里生根
长成枝繁叶茂的树,在我们经过的地方
随风摇动,目送我们远去。
穿过那片竹林
我们被竹林的纤细感染
江南风范的植物们
总归要守住它们的底线
关于白茶的故事
我们听到的只是其一
因为某种误会我们错过了
故事的另一种版本
当我们重新聚在一个屋檐下
黑夜已经架起屏障
它巨大的消音功能可以瓦解许多
看似坚强的事物
当虚无的蝉鸣响起来
没人愿意走进中心
看看究竟哪一只头上顶着桂冠
人群里的英雄,掩藏着标识
所有人都是自己的救赎
我们怀揣一个圆形的不被刺破的梦想
穿过竹林,我们踩在那叫作“影子”的上面
那在光照中存在的
不可握住的部分。
在冬天里行走
我们安静地在风里行走
像两个外地人,不时看一看路牌
一边看,一边把掉下来的围巾
重新围好
这座城太拥挤,人和车
都到了要溢出去的程度
当我们坐在车里,看着
屁股冒烟的车百无聊赖地
等拥堵散开,总会不自觉地想
立即跳下去,和风
挨得更近一些,于是又
有新的问题——
我们在风里行走,风会不会
觉得带着我们,是一种负担?
在寺庙听人说手相
一个和尚抓住我的手
“六月里会有贵人相助”
他仿佛知道了天机
我说没有多余的钱可付
他仍旧滔滔不绝攥着我的手讲。
他说了一堆好事之后,到底还是说到了钱字,
我看到他翻开的记录本上,善心者捐赠的钱数
我再次强调我的贫穷
并转身离开。即将迈出房门时
听到他大声说我额头带着光
那是爱情的光。我再也不能停留一秒
快步走到室外。
老树上密密麻麻的祈福布条
迎风飘动。我紧紧攥着手中的一条
不知将它系在树上
还是退回和尚手里
犹豫之中,看到一只喜鹊停在树上
它的翅膀扇动了几下
头转向我这边,仿佛被我手中的布条吸引
仿佛我攥着一条喜讯。
站在秋天里的人
那么多隐语,向这个秋天低头
好在这个季节,能低头的事物有很多
我们探讨迟钝与敏感的话题
以及一个事物的两面
连续一周的雨
令气温骤降,让人怀想高温里的环湖而行
会游泳的人在奔驰的车上念
一句古诗,而生在水边
却从未下过水的人
试图在句子中学会潜伏
风声经过沉甸甸的果实
我们想起关于果实的托付
于是站在果园里,面对打了农药的李子
远远地对它的外形加以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