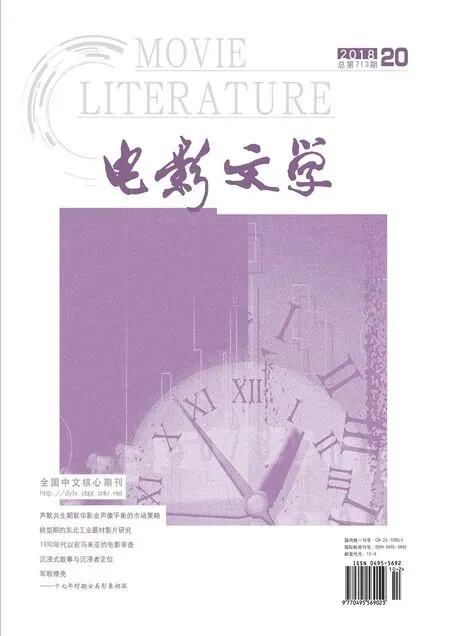《生存家族》中的末世逃亡与人类生存
王 梅
(大连外国语大学 比较文化研究基地、日本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44)
日本导演矢口史靖的最新电影《生存家族》于2017年2月在日本公映,并于2018年6月成功进入中国院线。电影以突如其来的电能消失为灾难背景设定,讲述了普通工薪阶层四口之家从东京逃亡至鹿儿岛的冒险故事。本文认为《生存家族》的成功之处在于题材新颖和视角独特。电影紧扣当下城市化发展脉搏,脑洞大开地将城市停电这一日常现象设置为无限期电能消失这一科技灾难。电影放弃宏观视角,而是以家庭视角切入。借助家庭成员的逃亡之旅,聚焦铃木一家的“城市病”,巧妙使用人物符号展示父权的消解与再建构。同时扫描日本社会,甚至是当下人类的生存群像,重新诠释城市与农村的共存关系。
一、聚焦“城市病”:科技灾难外壳下的家庭喜剧
电影第一幕向观众展示号称“不夜城”的东京夜景,铃木一家四口就居住在东京的高层公寓。父亲是爱岗敬业的上班族,在家里保持绝对父权。他对子女的教育不闻不问,只知训斥不知关心。母亲是贤惠能干的家庭主妇,熟练使用各种厨房电器,包揽所有家务。哥哥是大学生,平时总戴着耳机,基本不和家人交流;妹妹是高中生,无时无刻不拿着手机沉浸在社交圈里。兄妹俩一个喜欢吃快餐,一个严重挑食。
这是生活在东京的当代日本家庭实像,发达的科技、便利的电器、便捷的城市生活使得他们(其实也是银幕前的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患上了“城市病”。停电的前一晚,远在鹿儿岛的外公快递来了亲手打捞的新鲜活鱼。一家人对于食物的漠不关心甚至厌烦态度充分暴露了他们的病态。母亲总是购买超市处理好的食材,不敢动手杀鱼,于是向父亲求助,可父亲光顾看电视,连头也不回。妹妹极其厌恶乡下的一切,她说自己绝不吃那条鱼。哥哥只待在房间里摆弄电脑,压根儿不参与家庭事务。母亲只好暂时用保鲜膜把鱼包起来放到冰箱里。第二天,发现由于停电冰箱停止运转,母亲毫不犹豫地将鱼扔进垃圾桶。这里仍是导演预设的伏笔,城市人对待食物的傲慢态度,与停电之后逃难过程中由于食物匮乏而导致的饥饿状态形成鲜明对比。
当一家人逃亡至须磨水族馆时,看到一车车活鱼被工作人员烹饪成为海鲜大餐分发给路人。这时,一家人眼里流露出的再也不是厌恶,而是渴望,于是迫不及待地去排队。可是,偏偏刚刚排到,海鲜就分完了。再当他们继续逃亡至九州的乡下时,全家已经处于缺水少食的虚脱状态。看到田地里有一头猪,全家人出于本能、用尽最后的力气捉住这头猪。平时连鱼都不敢杀的城市人此时面对一头猪。从停电前的不情愿杀鱼,到停电后的不得不杀猪;从逃亡前的暴殄天物,到逃亡中的饥不择食。铃木一家的不幸遭遇和种种窘态全都充满喜剧笑料,同时也形成强烈的讽刺效果。
电影里毫无征兆的电能消失正是基于已经患上“城市病”的人物设定而设置,电影人物也只有经历大停电这样的城市灾难才能意识到自己的病态现状,并实现人物缺点的克服与人物弧光的完成。因此,科技灾难只是电影的外壳,其核心还是日本导演擅长的家庭叙事。《生存家族》采用暗示和未知的方式进行灾难设置。停电前,镜头给了妹妹手机“电量不足”的特写。这其实是一种预言,更是一种象征,即全球大停电已经进入倒计时。停电发生在半夜,父亲一觉醒来发现闹钟的电池失效,接着进一步发现家用电器全部失灵。同样,灾难的结束也是悄无声息。当停电已长达两年126天,全家人在鹿儿岛已经很习惯男耕女织式的原始生活时,还是父亲从睡梦中听到了闹钟的声音,紧接着发现路灯亮了。
矢口导演在接受采访时说道:“停电的瞬间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恢复也是未知,这种未知的状态有一种细思极恐的效果。”因此,一家人在发现停电的第一时间并未流露出过多担忧,只是由于家用电器失灵和公共交通瘫痪而感到不方便。不仅没有担忧,反而在停电的夜晚,还因欣赏到了久违的星空而获得了少有的家族认同感。而随着停电天数的增加,这种“未知的状态”逐渐升级为末世的恐惧。终于,在停电第七天,父亲决定带领妻儿逃离东京,投奔鹿儿岛的岳父。
电影不从政府如何应对灾难、科学家如何研究直至战胜灾难等方面做文章,只展示铃木一家从东京逃亡到鹿儿岛的所见所闻。电影自始至终也没有给出灾难发生和结束的具体原因。导演的用意非常明显,借助电能消失这一概念,让城市人回到没有手机和其他电器的原始状态,借助城市人的逃亡,最大限度地放大城市人的“城市病”。当“城市病”已被克服,城市人学会了在没有电能的农村丰衣足食时,灾难就会结束。而当观看电影的城市人也悟出这一点时,《生存家族》的启示和警醒意义就非同小可了。
二、逃亡之旅:父权的消解与再建构
作为一部成熟的商业电影,《生存家族》为每位家庭成员都量身订制了符号代码和城市伪装。父亲的假发象征虚假的父权,母亲的眼镜指向她口是心非的软弱性格。女儿的假睫毛与父亲的假发相对应,暗示父女俩的相似性,逃亡途中父女俩的愚蠢与无能是电影喜剧性的主要体现。手机则是儿子的城市伪装。逃离东京之初,他们并未发觉这是逃亡的开始,而是带着各自的城市伪装、怀着单车旅行的心情上路。
逃亡第九天的暴雨袭击是对铃木一家的第一次正面打击。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不仅夺走了一家人的装备和物资,而且迫使他们抛弃从城市带来的伪装。暴风雨吹掉了妹妹的假睫毛,摔碎了母亲的眼镜。哥哥以手机套为材料修补自行车轮胎,随后就毫不犹豫地丢掉了手机。三个人相继卸下城市伪装,表明恢复原始的状态。只有父亲的假发符号贯穿电影始终,因为假发除了具有城市伪装的意义,更是虚假父权的象征。电影临近结束时,大难不死的父亲重新获救后,他亲手丢掉了假发,意味着与过去的自己进行诀别。
逃亡第15天,铃木一家在高速公路上遇到另外一家四口。他们是野营爱好者,身着专业装备,享受野外生活。这与野外生存能力几乎为零的铃木一家形成鲜明的镜像对比。真正意义上的父权崩塌发生在逃亡第36天。父亲执意要去大阪,但等全家骑车来到大阪,才发觉这里也是人去楼空,一片狼藉。于是,妹妹摔掉自行车直指父亲的不是,哥哥随声附和,指出父亲只会虚张声势。在父亲准备摆出父权教训子女时,已经卸掉眼镜的母亲一改平日里充当父子关系润滑剂的软弱,终于说出了“你爸就是这副德行”的心里话。也正是母亲的这句斥责让父亲醒悟自己在家人眼中的样子,并不是自己有多厉害,而是家人一直在包容自己。
停电之前,这个家庭虽然表面和谐,但已经危机重重。夫妻间有隔阂,兄妹间无交流。而最大的问题是“父亲缺席”。1963年德国的社会心理学家亚历山大·米切利希出版了名为《没有父亲的社会》的学术专著。他指出随着城市化进程,现代社会不同于农业和手工业时代,父亲劳动的身姿逐渐在孩子面前消失。这使得孩子只能对父亲的存在抱以幻想,从而导致系列青少年问题的发生。
电影里的父亲仅仅满足于“养家糊口”这一现代社会父亲的基本职责,导致父子间沟通和交流的机会骤减,从而使父子间的关系逐渐疏远。高度的城市化更是加速了父子关系的疏离。工作以外的父亲不是在看电视,就是休息日在家睡一天。父亲和孩子连基本的交流都没有,更谈不上在共同劳动的过程中对孩子进行道德准则和生活实践的示范和指导。而野外逃亡的严苛环境加速了父权的瓦解。喝溪水拉肚子,钻木取火的失败。父亲越想树立父权,越适得其反。从这点来看,野营爱好家庭的父亲教会了兄妹俩野外生存的技能,实际上树立了“理想的父亲”这一典范。
逃亡第60天,精疲力竭的铃木一家被九州的农夫田中所救。在这里,经历了一段休养生息。面对田中的挽留,父亲不再一意孤行,而是就继续前行还是就此住下询问一家人的意见。再次上路时,父亲已经开始改变,从虚张声势的父亲转变为“理想的父亲”。铃木一家按照哥哥的地图前行时,发现被水流湍急的河流挡住了路。兄妹俩开始互相埋怨,父亲却走到河边开始动手收集木头编制简易木筏。父亲的行为对孩子起到了示范作用,真正实现了精神领袖的塑造。
父亲和哥哥跳下河推着载有自行车的木筏前行时,父亲不幸被河水冲走了,只留下父亲的假发。全家人将父亲的假发视为遗物,悲痛不已。父亲的离去对刚刚建立起的父权起到了巩固和升华的作用,使得哥哥作为父权的继任者带领母亲和妹妹继续前行。被冲到河流下游的父亲靠着之前哥哥在超市里找到的信号弹成功发出求援信号,这个信号恰好被已经坐上一辆蒸汽火车的母亲看到,最终全家人在火车上团圆。当母亲把假发交还给父亲的时候,父亲却把它抛向了窗外,实现了人物弧光的完成。
三、如何生存:城市与农村的共存性
矢口史靖的上一部电影《哪啊哪啊神去村》讲述的是高考落榜的失意青年因为一张印有美女头像的宣传手册而来到偏远山区从事林业工作的故事。男主人公经历了从几次试图逃离到逐渐感受到“神去村”的大自然魅力,到最终完全转变想法的过程。如果说《神去村》所展示的主题是现代文明与原始自然的碰撞,那么《生存家族》则跳出了这个二元对立,展示了现代人的生存途径,即城市与农村的共存与调和。
饥饿交加的城市人被农夫田中所救,吃饱了饭,洗上了澡。作为补偿,他们要帮田中捉回因电动闸门失灵而跑散的猪,还要拿起刀帮助田中杀猪。铃木一家发现虽然严重的物资缺乏使得城市人的生存成了问题,但农村仍是平静的生活。铃木一家与田中老人共同相处的一周时间是电影剧情发展的转折点,不仅是父权得以再建构的契机,也是彻底改变妹妹“重城市轻农村”这一价值观的过程。缺少了现代科技支持的城市无法继续提供生存所必需的条件,人们想要生存,就必须返回自然资源丰富的农村。
然而,《生存家族》的高明之处在于并非将城市与农村设置成为前者低级后者高级、前者需要后者来拯救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互相需要、互为依靠的关系。田中老人的儿子一家搬去了美国,留下老人独守乡下的老房子。田中老人现在身体尚且硬朗,生活上也能料理一切,但他的内心是孤独的。他把预备留给儿子一家的睡衣拿出来让铃木一家换上,并且间接流露出挽留铃木一家的意思。电影并非在说城市人只退回到原始社会,才能解决“城市病”的问题,而是强调两者的共存性。即城市文明需要农耕文化作为其后盾,农耕文化更加需要城市文明的补充与更新。
关于留下来还是继续逃亡的问题,矢口导演的处理方式很到位,他借母亲的视角审视这一问题。母亲在田中身上也看到了自己父亲的影子。自己的母亲去世后,父亲在鹿儿岛的渔村也成为一名独居老人。电影开头,寄来食物的父亲在电话里让女儿有空回来看看,但作为女儿的母亲也只是表面敷衍。最终,一家人在田中老人留恋的目光中再次启程上路。他们的目的已经不是被动逃离城市,而是主动投奔比九州更加偏远的鹿儿岛渔村。
最终,在停电第108天,逃亡第101天,铃木一家终于靠体能从东日本横穿至西日本,到达日本列岛的最西端,一家人互相扶持找到了正在海边钓鱼的外公。无数类似铃木一家的城市人来到小渔村,男性下海捕鱼,女性纺纱织布,过上了返璞归真的生活。渔村因为他们的到来而充满生机。
灾难结束后,铃木一家没有选择留在世外桃源的渔村,而是重新回到城市。一切看似照旧,但他们不再沉迷城市的便捷。父亲改为骑车上班,母亲开始操刀杀鱼,哥哥不再吃垃圾食品,妹妹满心期待美食。电影最后,一家人收到了逃亡时野营爱好家庭为他们拍摄的照片。电影定格在这张狼狈不堪的照片,似乎提醒着他们要居安思危,铭记那一段生死存亡的求生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