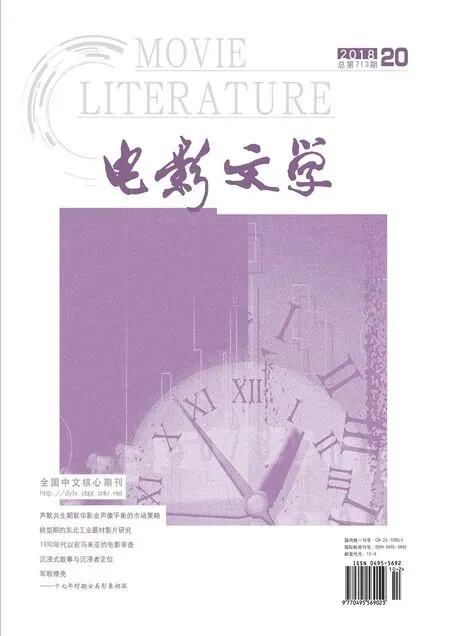引爆还是转移:电影《引爆者》的意识形态症候解读
孙 丽
(北京师范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北京 100875)
一、《引爆者》的叙事建构解读
作为典型的动作犯罪类型片,《引爆者》(常征导演,2017)的类型讲述在上映阶段并未能攫取受众市场的有效关注,其文本内容的丰富性及生产过程的妥协性也被大多数影评人及观众忽略。从犯罪-动作片的类型出发,《引爆者》在叙事逻辑、类型标准等方面有着不少漏洞,但若从社会学意义与现实主义方面分析,《引爆者》的故事文本实则突破了目前内地商业片的主流表达,这种突破在各种复杂力量的牵扯下却又是十分有限的。影片的叙事建构完成了一部标准流程的商业片,看似简单的情节铺陈通过运用意识形态修辞术对影片的叙事矛盾进行悄然置换。
电影最初通过一场矿难构建出赵旭东等普通矿工和煤矿老板李毅间的矛盾:通过展现煤矿资本运作过程中的黑暗内幕,人物冲突被指向劳资双方。在这一过程中司法系统则被矿主、受害家属绕过,矿工的生命、工作权益未能获得正当的保障,劳动者沦为资方的牺牲品。这一矛盾的设置推动作为唯一幸存者的赵旭东开始查明真相,试图寻求劳动者与资方间的问题解决方式,却导致主角赵旭东彻底卷入到矿主李毅与另一煤矿老板程飞的资本较量中,使得有待解决的劳资矛盾陷入无解的境遇。随着后续事件的发展,程飞暗害李毅,影片之前所建构的劳动者赵旭东与资方的矛盾随着李毅的死亡而消解,由于程飞绑架了赵旭东的爱人萧红,程飞与赵旭东之间的个人恩怨成为影片真正叙事意义上的冲突。
值得提及的是,在电影开场及高潮部分,赵旭东的独白讲述了其父通过求签对自己命运的预测:若子承父业做炮工,必有血光之灾。这些独白镜头多采用一种俯拍式的上帝视角,通过打光将人物置于强烈的明暗对比中,且辅以悲怆性的音乐背景,这一系列视听语言成功进行了意识形态缝合,将人物的遭遇指向“命运”。之后影片通过一系列情节自我确证了这种命运的暗示,把赵旭东遭遇的一系列不幸运用一种意识形态腹语术与命运的不可抗性相连,从而成功将赵旭东最后的反抗解释为一种与既定命运的对抗,彻底屏蔽了赵悲剧性命运的根本原因——劳资双方不平等的社会生产体系。情节发展至此,《引爆者》最初所构建并有待深入展开的劳资矛盾被置换为主角与反派间的个人恩怨,救人取代维权成为影片矛盾的解决方式。一部本来可以引导我们反思现行劳资关系、反思现行社会结构的影片,随着影片叙事焦点的转移,变成了孤胆英雄解救爱人与凶残犯罪分子进行较量的犯罪片。赵旭东个人的救人行为巧妙地让故事中的矛盾得到一种表面上的解决;主角也通过被塑造为犯罪分子魔爪下的受害者,从而模糊了其被资方剥夺了正当权利的劳动者身份。
二、“在场的缺席”的法律体系
在由“好人”赵旭东和“反派”程飞、李毅构成的主要人物关系中,警察徐峰是区别于两者之外的存在。作为矿难与李毅死亡案件的调查者,徐峰是法律体系和权力机关的人格化代表。然而在本片中,作为司法代表的徐峰却始终处于一种“在场的缺席”的状态。受害者赵旭东在接二连三的案件中从未把警察徐峰列入可以寻求帮助的对象中;加害者程飞、李毅间的私人冲突也不曾考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影片中有几处很有意思的台词设计,矿主李毅在爆炸事故发生后,曾多次提到“不要报官”,“报官”这种古代社会中的口语化表达,被李毅沿用至今,由此侧面印证了李毅对当代司法制度的陌生。在整个叙事层面上,警察体系是始终在场的,但缺席了现实层面对真正犯罪行为的制裁功能。主人公赵旭东在结尾处对徐峰高喊的“你他妈的只知道干我,他呢!”控诉了徐峰所代表的警察们对底层受害者保护的不力,除了对赵旭东这种弱势小人物的司法制裁外,徐峰对真正的犯罪分子程、徐二人无计可施。在《引爆者》中描述的存在于矿主与矿主间、矿主与工人间的司法体系始终是处于一种“在场的缺席”的状态,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射了影片中描述的煤矿再生产体系在真实社会中的运作情况。
另外,警察徐峰与“疑犯”赵旭东之间,还存在一种暧昧性的亲疏关系。徐峰作为刑警队长,与犯罪嫌疑人赵旭东是从小就认识的朋友,甚至徐峰会以“咱妈”称呼赵的母亲,这就构成了一种象征意义上的兄弟;徐峰给受伤的萧红输血的情节更是将两人指向一种血缘上的亲情联系。除此之外,作为警察与“罪犯”,徐峰与赵旭东间也有着复杂的恩怨情仇。在赵旭东的讲述中,徐峰当年正是因为破获自己私做炸药的案件,才成为刑警队长,赵旭东则因此锒铛入狱,留下案底。影片中,徐峰破案立功被数次暗示性地与出卖朋友联系起来:在赵旭东成为嫌疑人后,徐峰多次通过劝萧红“帮助”赵旭东,来对赵实施抓捕。
对于犯罪类型片来说,警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角色类型,“电影通过其塑造的警察形象和与警察建立联系的其他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之间的关系,以及叙述关涉违法犯罪事件中他们各自的行为表现,呈现出对我们所处社会的表达与想象”。《引爆者》中警察形象的塑造及其与众多人物间的关系呈现,侧面印证了由资方主导的生产体系的复杂性,而警察与众多人物关系的塑造,则展现了警察体系对犯罪行为监管的难度。影片的最后,徐峰制伏了程飞、赵旭东两人,警匪三人同处于一个画面内:代表受害者的赵旭东蜷缩在画面左侧;煤矿老板程飞躺在中央,占据了画面的绝对主体位置;警察徐峰则拿枪站在两人右侧,形成居高临下之势。三人的站位在画面中形成一个明显的三角构图,微微倾斜且处于抖动状态的镜头则暗示了这种三角关系的脆弱与不稳定性。
《引爆者》中,司法制度难以对煤矿运作体系进行有效监管与干预,李毅、程飞这些煤矿管理者及赵旭东、王三百这些体制的服从者们选择构建了一个“矿上的规矩”,并心照不宣地遵照着这一规矩行事。这种规矩以暴力性为主导,呈现出一种原始社会式的弱肉强食性生存法则。对于煤矿老板们来说,煤矿私人化的进行是通过暴力行为来扩张的,这种规矩亦导致了其自身的悲剧,甚至“非人化”的转变。金钱的桎梏使得程、李等人成为精确计算利益、不为情感驱使的“生意人”,为了争夺煤矿所有权,程飞失去了儿子程云,王毅则失掉了自己的性命,比这更为严重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都失去了“人”的资格。程飞等矿产老板所构建起的资本生产体系,使得赵旭东失去了正当的法律权益,从而诉诸非法的暴力行为为自己“讨一个说法”,而程飞、李毅也正是因为这种将法律排除在外的体系,失去亲人、人性,甚至自己的生命,同样与赵旭东陷入一种悲剧性的结局中。
三、不彻底的底层关怀倾向
《引爆者》涉及的内容表达实际上承担着一种表现社会真实的使命感,这也是影片被绝大多数观影者和电影市场所忽略的一点。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电影出现后,形成了一种表现社会真实的创作潮流。但在近年来,随着内地电影市场的蓬勃发展,影片的主流制作却始终没能突破电影意识形态化的宣教本质,尤其是以第五代导演作品为代表的影片,始终缺乏艺术表达真实的功能,因此立足于批判现实和平民化关照的电影在近年来一直处于空白状态。直到20世纪90年代第六代导演崛起开始,表现社会底层人物及弱势群体的一系列现实主义影片才重新以一种革命性的姿态出现,譬如《小武》(贾樟柯,1998)、《天注定》(贾樟柯,2003)、《安阳婴儿》(王超,2001)、《盲井》(李杨,2003)、《盲山》(李杨,2007)、《孔雀》(顾长卫,2005)、《钢的琴》(张猛,2011)等,这些影片均背离了居于绝对强势的主流价值观表达,几乎全部为现实主义题材,且客观上有同情弱势群体、反抗强权势力的倾向,在这些电影作品里,工农大众“积贫积弱的底层性和弱势群体成员的边缘性得到正视和体现”。
《引爆者》的文本涉及对当下社会现实的表达,将国产电影中鲜少提及的矿难题材与商业类型结合,不仅突破了小成本文艺片的局限,也突破了题材上的边缘性,与同为矿难题材的《盲井》相比,《引爆者》中涉及的死亡,终于通过一种巧妙的叙事手段与意识形态修辞,纳入主流社会允许呈现的死亡范围之内。但是,相较于《盲井》《盲山》《钢的琴》等影片来说,影片虽然涉及了当下社会现实表达的内容,这种表达却是不够彻底的,原因在于作为商业电影,《引爆者》面临着一种在真实社会表达与商业主义间的平衡与妥协。2000年前后出现的针对底层人民及现实社会表述的电影,多为作者电影色彩强烈的小成本文艺片,这类影片并不以商业发行作为影片创作的主要目的,从而能在反主流表述层面不考虑过多受众与商业因素的干预。《引爆者》的创作环境则要更加复杂,这也导致了其虽有批判性的创作理念,但这种批判精神却未能深入。
影片生产的年代与环境实际决定着影片的呈现方式与叙事结构。20世纪8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开始主导全球经济和政治结构,中国社会也“在国家权力结构的延续形式之下推动了激进的市场化过程,并在这一国家的政策主导之下,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积极参与者”。政府对市场化的推动使得私人资本出现,同时在政企分离的口号下,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含混过渡中,“大量国家资产‘合法地’和非法地转化为少数人的经济利益”。《引爆者》由华谊兄弟电影有限公司出品,北京二十一世纪威克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星世纪影业有限公司等10家公司联合出品,其中华谊兄弟电影有限公司为主要制作方与发行方。由民营资本为主要制作与发行方的《引爆者》,在内容表达方面由于受到不同方面的社会诉求牵扯,原有的对底层社会的关注度与社会批判力度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电影在大众文化传播领域的强势表现使其成为意识形态构建领域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反映现实的同时,电影也通过一种对影像的构建强化了某种现实逻辑。这种逻辑在商业影片身上呈现出一种以市场为主导的生产模式,并巧妙地把握着意识形态与商业主义间的平衡。
四、结 语
作为一种表象系统,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表现/再现的方式建立起一种想象性图景,并将个体询唤至其中,使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合法,或者说是“宿命”的位置,从而构造出一种主体的幻觉。《引爆者》最初展现了资本与劳动者间的矛盾关系,但最终这种关系被意识形态话语术悄悄替换为一种血亲复仇式的矛盾,并通过赵旭东个人的暴力行为得到一种想象式的解决,达到与主流社会的和解。这样的一种叙事设置成功地对赵旭东所存在的位置进行了合法性叙述,从而为“赵旭东们”在个人生存中遭遇的矛盾提供(想象性)了解决。这样来看,《引爆者》通过文本表达构建出的意识形态是十分成功的,它不但成功地隐蔽起自身,且让每个在其中照见自己主体形象的观者从中得到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