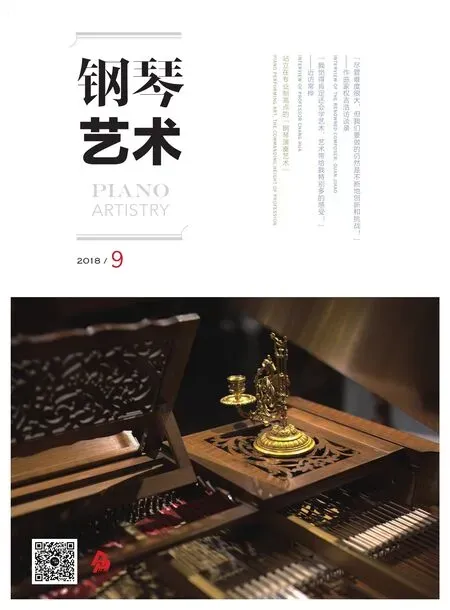创意的有机因素
文/ 赵穗康

(一)
1721献给马格瑞(Margrave)的《勃兰登堡协奏曲》(Brandenburg Concerto)实际上和勃兰登堡的马格瑞没有太大的关系。六首协奏曲是巴赫两年前应大选帝侯的小儿子、业余音乐家马格瑞侯爵的邀请所作。Brandenburg Concerto是巴赫从他平时在科滕(Cöthen)星期天晚间音乐会中整理出来的一套器乐作品。在他卑谦的献词里面,巴赫表示了希望为马格瑞侯爵效劳的意愿。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协奏曲的谱子闲置在马格瑞的图书馆里,一直到侯爵去世,从未被人过问。经过一番转折,最后落在柏林图书馆里(这里简称巴赫用于科滕星期天晚间音乐会的谱子为“CöthenConcerto”,巴赫给马格瑞候爵的版本为“BrandenburgConcerto”)。
当时的音乐创作是音乐生活的有机环境。科滕星期天晚间音乐会的内容相当松动,那是个随遇而“玩儿”的聚会(event),也是一个有机则变的音乐活动。因为这个原因,实际演出的CöthenConcerto,一直处于不断的修改调整之中,更不要说像《第五协奏曲》这样的作品,居然有13个出处之多。由于音乐条件和环境的变化,巴赫必须就地修改乐谱。巴赫不但自己在中提琴和羽键琴间充数,更是到处拉人,朋友、学生、儿子加上资助人一起参与。乐队的乐器数量常常随遇而“配”,有时甚至不惜改编乐谱。小型的室内乐可以有三把小提琴、三把中提琴和两把大提琴的组合,有的协奏曲自然而然发展到更大规模。有意思的是,一次,两位圆号演奏家来科滕过周末,巴赫绞尽脑汁,拼凑一个能与圆号平衡的乐队,尽管弦乐部分还是力不能及,但是结果就是有了Brandenburg Concerto(No.1)这样的“交响”作品,同样的原因,Brandenburg Concerto(No.5)也是“玩儿”出来的键盘协奏曲雏形。
1723年巴赫带着他的CöthenConcerto到莱比锡,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那里。在莱比锡的泰勒曼(Telemann)音乐会上,巴赫曾经改编、转换了很多自己的作品,其中包括CöthenConcerto。不仅如此,协奏曲的音乐甚至被巴赫用于在莱比锡写的康塔塔里。当时音乐家转抄、改编彼此的作品是常有的事情,巴赫去世之后,协奏曲的版本就成了问题。现在被认为最有权威的是彭泽尔(Christian Friedrich Penzel)的版本,因为彭泽尔版本是巴赫早期科滕手稿的抄本。年轻的彭泽尔在巴赫去世之后,承接了大师留下的很多事务。有趣的是,彭泽尔从来没有见过巴赫给马格瑞侯爵的版本。据说,彭泽尔的版本,是巴赫自己整理马格瑞版本时同时参考“旧版”转抄写成的版本。具体的故事现在谁都说不清楚,可是,巴赫自己的CöthenConcerto手稿却早已去向不知。
就像巴赫所有手稿一样,Brandenburg Concerto是他在纸上的“画音”,然而,美妙的视觉效果多少掩盖了当时繁忙的草率和生活琐碎的困境(巴赫前妻在1720年去世)。尽管如此,学者们还是觉得,Brandenburg Concerto是巴赫乐思不断发展的有机过程,也是大师对协奏曲的最终思考。因为这个原因,几乎没有机会演奏的“善本”CöthenConcerto是对活的音乐(Living music)的一种“失真”。但是,Brandenburg Concerto的手稿里面有多处笔误,再加上巴赫以后又对协奏曲修改不止,所有这一切都给力图考证是非的学者出了很大的难题。事实上,艺术家和音乐家的创造都是自己内在源泉的不断再生,对于一个创造者来说,不尽完善是自然而然的有机过程,只是作者辞世他去,原本有机的演变发展突然停止,被动的学者只好从时间的终点倒回过去,音乐学的理论试图明确无常理的常规,研究捉摸不定的有机,因为人类追求完善的本能,加上不可完善的沮丧,迫使我们无止境地寻求大师最终的定位。然而事实上,我们很难说清哪一个版本更为优胜,哪个版本是作曲家的最终“善本”,它们都是出之于作曲家的手笔,不管它们当时的起因是环境的限制还是艺术的追求,所有的手稿,都是作曲家艺术思考的不同角度,从个这角度,布鲁克纳(Bruckner)的音乐对于今天音乐学提出的挑战,无疑是个艺术哲学的课题。
(二)
Brandenburg Concerto(Op.1)第四乐章的音乐非常有趣。它由一个不断重复的小步舞曲(minuet)和夹在两个三重奏(trio)中的波兰舞曲(Polacca)组成。音乐的结构是A—B—A—C—A—D—A 的模式(CöthenConcerto中没有Polacca,是A1—B—A2—D—A3的结构)。第一个三重奏是三支双簧管和巴松管的对话,第二个三重奏是两个圆号和三支双簧管的交织。
第四乐章的Polacca典雅别致。指挥家里赫特(Richter)的诠释不偏不倚、无与伦比。里赫特没有卡拉扬现代工业的金属,也没有本真学究的极端理伦。他的音乐层次丰富,古朴悠然的轻巧诙谐的小步舞曲,在平衡雅致之中,趣味别致横生。两个管乐的三重奏性格决然不同,第一个三重奏里,两支双簧管和巴松的对话,是室内私密的促膝交心。第二个三重奏的性格完全不同,音乐在粗犷的号角声里,搅入三支双簧管的叫嚣欢欣,广场群舞的喧闹里面,可以听到男人炫技耀武的吼声,那是街市人气的沸沸扬扬和庆典狂欢的群众场面。夹在两个三重奏之间的Polacca更是别致新颖,那是小姐妹间的窃窃私语,拉着裙子文绉绉的调笑矫情—当然,所有这些都是一时听来的感觉,不是具体不变的音态场景。音乐的好处在于乐谱只是一个符号,不同音乐家的不同解释,重新不同的语言信息,给于听者完全不同的音响含义。
指挥家莱昂哈特(Gustav Leonhardt)的Polacca庄严肃穆,但是好像不是我所想象的那种轻盈古朴的舞步。他的三重奏对位交替奇特,一如平时整体有致的严谨风格。哈农考特(Harnoncourt)的Polacca速度缓慢,音乐性格和里赫特的完全不同。如果说里赫特的诠释注重主观个性,哈农考特则是更在客观的角度取胜。另一个是Archiv上Baumgartner的录音,那是里赫特冷静的那一面。I Musici的录音典雅清晰,有霍利格(Heinz Holliger)、布吕根(Frans Brüggen)、加拉蒂(Maria Teresa Garatti)这样的音乐家聚在一起,可以想象音乐的格调一定非凡。我也喜欢平诺克(Pinnock)的录音,他的Brandenburg Concerto是轻盈的类型,特别是他的Polacca,舞蹈的姿态正是我所想象的那种形状趣味。没有想到富勒(A.Fuller)在Smithsonian做的录音也是独具风格,他的Polacca是快速中的庄重。高伯曼(Goberman)与里赫特有相似之处。我向来喜欢霍格伍德(Christopher Hogwood)对巴洛克音乐的诠释,但是这里有点让我失望,他的舞步太快,缺乏古风的轮廓。马里纳(Neville Marriner)的第一次录音和霍格伍德一样,用的都是CöthenConcerto的谱子。马里纳在1981年的录音聚集了谢林(Szeryng)、朗帕尔(Rampal)、霍利格尔(Holliger)、马尔科姆(Malcolm)之类的大牌独奏音乐家,这次用的是BrandenburgConcerto的谱子,整个音乐效果好得出乎意料,一点没有通常大牌合作的凌乱感觉。卡萨尔斯(Casals)的录音又是一绝,古老的小步舞在他手里变成交响的宽广宏伟,那是卡萨尔斯惯有的悠长气息和拱门式的骨架结构。然而,卡萨尔斯的三重奏却又不乏谨慎之中的透彻清晰,其他中段的处理也是各有区分不同,可见卡萨尔斯有他“三明治”的总体设计。卡拉扬版本的演奏奇慢,光洁平整的音乐缺乏巴洛克的节奏感觉。想来他的立意在于宏大,但是结果却是宏而不大,空而无物,尽管三重奏有点特色,但是整体听来,总是觉得有点不伦不类的古怪。
记得昆德拉在他《被背叛的遗嘱》里指责伯恩斯坦对于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的歪曲。就这一具体的争议,我是倾向昆德拉的说法。但是,话又得说回来,从音乐的角度,这是一个艺术处理的角度问题。今天我们看到Big Four给爵士音乐提供了即兴音乐的可能,事实上,即兴的传统可以追溯西方音乐的源头,倒过来说,就是具有即兴传统的19世纪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音乐,今天也都已经成为历史。我想,即兴的创意是所有艺术的根本,如果我们能把创意从具体的技艺准则里面解放出来,也许其中的含义可以不再局限某个具体的框架标准。
这里,就以巴赫这段Polacca的姿态为例,在卡萨尔斯和平诺克之间,可以说是两个极端,甚至音符的时值都有可能不同。我想,如果我们真要追求“原本”,至少在巴赫音乐里面不大可能。不说BrandenburgConcerto有很多不同抄本,巴赫晚期《赋格的艺术》没有配器,每次看到《赋格的艺术》的唱片,总有一种好奇的冲动,想听音乐里面如何不同。今天我们听到的《赋格的艺术》,不说每个处理不同,就连配器都是不同搭配组合,巴赫给予今天的我们留下一个有机的悬念,音乐是个生的机会,什么模样都是可能,这才叫作Living music!
结 语
无论我们如何追求原汁原味,事实上,绝对的原本真实并不存在。原创不是一种能力,也不是具体不变的物体。原创是种心态,是个独特角度。演奏最终还是重创的艺术活动。所以,艺术家必须通过自己进入作品的内涵关系,由此创造的再现才有可能。
古钢琴家比尔森(Bilson)在康奈尔(Cornell)大学的讲座“Knowing The Score”里,强调的不是绝对“本真”,而是如何正确阅读乐谱。他说如果能够理解音乐家乐谱上的标记,也就能够跨越常规,创造更加直接的音响语言。古键琴家和古乐指挥莱昂哈特说过,如果真的要去刻意追求本真(Authentic),那就不免堕入迷宫失落,因为事实上,我们没有可能确定不变的“本真”。这话出自于一生追求“本真”音乐的莱昂哈特之口,思维的广度和含义的精深值得让人品味琢磨。
今天,古典音乐在“本真”问题上面纠缠不清。首先,“本真”的原意在于清洗时代隔层的误解和具体音乐作品的历史,然而,“本真”的理论一旦成为概括艺术作品的条条框框,学术的研究拐弯抹角局限艺术创作的有机不定,本末倒置的逻辑混乱就会出现。通过历史环境,梳理具体艺术作品上下文的工作非常重要,但这只是一个学术研究的工具,目的在于提供不同的角度,给予艺术创造更多选择的可能。“本真”好像是学术环境和现成备用的工具,不是创意有机的艺术主动。所谓的“本真”,只是不同角度的一种,不是固定绝对的标准。格伦·古尔德从来不为“本真”问题焦虑,但是他的音乐可以比“本真”的准则更为绝对,也可以比“浪漫”的随意更加自由。问题的根本在于,“本真”的教条最后成为学术“正统”的标准。然而,对于比尔森和莱昂哈特来说,他们追求的不是简单的“本真”,不是音乐学的研究,而是他们自己听到的音乐内在信息。
我想,音乐犹如生命,是生死并存的自然有机。就像爵士音乐一样,音乐里的即兴因素非常重要。无论是乐队作品还是个人独奏(也许这是我的夸张,一般公认乐队的演奏最难具有个性),无论多少次的演奏,无论多少雷同的曲目,演奏总有重新创造的余地。指挥家富特文格勒(Furtwängler)演奏贝多芬多次,没有一次绝对雷同相似。就我自己的经验而言,创作视觉艺术的过程也是如此,灵感不是最高级的固定标准,而是点滴细微的异样不同。作品完成之后,作者完全失控,作品的物象随即渐渐开始自己的生命旅途,最后“定型”的作品随着时间和环境变化。伦勃朗《夜巡》的名字是画面色彩变化之后所得,西斯廷教堂天顶壁画色彩“还原”之后,很多人不能接受米开朗琪罗当年色彩的“本真”。再说,观者听众的趣味认同也是随着时代在不断改变,很难想象我们如何用固定的“本真”标准衡量所有艺术。
一件视觉作品,一个音响艺术,观者和听众都是再度创作的参与者。原先乐谱上的音乐是一回事儿,重新体现的音响又是一回事儿,听众的反映感受更是另一回事儿。这里没有矛盾冲突,甚至没有学术间隔。我常在想,像哈农考特、加德纳(Gardiner)、平诺克和霍格伍德这类“本真”音乐家所演奏的音乐,尽管都用古乐器,同样主张忠于原作的“本真”理论,然而,不管这类理论具备多少历史价值,也不管这种努力解决多少具体的技术疑问,如果我们能够去掉表面的不同,“本真”复古的音乐,实际是个“借尸还魂”的艺术创新。“本真”的音乐通过“复古”,揭开一个我们当代的声音织体,那是一个全新的音响语态和口气,一个未来的音色情绪和精神环境。所谓追求“本真”的理由,其实是个旧瓶新酒的借口,就音乐趣味和音响效果而言,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对巴洛克音乐面目一新的特殊解释―感知的音乐本身最后总是超越音乐的学术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