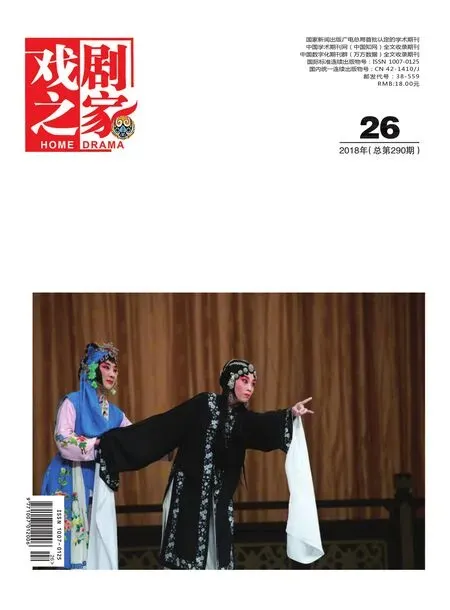他人即地狱
——《竹林中》的日本耻感文化探析
龚 仪
(湖北大学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2)
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力作《竹林中》,讲述了一件离奇的凶杀案。小说内容由七段供词构成,其中樵夫、云游僧、捕役和老媪作为证人,交代了案件环境和人物背景;多襄丸、真砂和金泽武宏是案件当事人,其供词承载了小说情节的高潮。这七个人对案件的描述莫衷一是,尤其是三个主角,提供了三种截然不同又自圆其说的供词,而三段供词又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供认武宏身上的刀是自己刺下的,但又拼命美化行为动机。这种令人费解的矛盾,或可通过支配日本国民行为的深层观念——耻感文化来解释。
一、日本耻感文化下的“竹林”悲剧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提出“耻感文化”这一概念。在与之对应的西方“罪感文化”中,人对于“罪”会产生负罪感,因而约束自己的行为;但以“耻”为基点的耻感文化对人的约束力来自于社会评价。
耻感文化的核心是“名誉”。本尼迪克特将日本对名誉的维护称作“对名誉的情理”,包括“维持各种纷繁复杂的礼节各得其所,能忍受痛苦,维护自己在专业或技能上的名声。……还要求消除毁谤和侮辱,……必要时要对毁谤者进行报复,或者自杀。”①由此可见维护名誉实质上包含了两个方面:获得荣誉、洗刷耻辱。虽然多襄丸三人各执一词,但通过将三人划分为施暴者(多襄丸)和受害者(武宏夫妇)两种角色,就可以根据他们的主要动机,看出他们对于耻感文化这两个方面的诠释。
(一)追求荣誉
多襄丸供认他强奸了真砂,但不是出于色欲,而是真心想娶她。他嘲笑武宏的贪婪,又美化自己的色欲,因为他知道出于欲望而犯错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而后他又强调自己是在和武宏公平决斗后才杀死对方。在日本封建时期严格的等级制度下,一个强盗敢正面挑战甚至杀死一个武士,这一“壮举”能使他从一个奸诈猥琐的强盗,变成慷慨凛然的英雄。所以即使犯下强奸、杀人的罪行,他的耻辱反而成就了他的“丰功伟绩”。
最后多襄丸气概昂然地“请以极刑”。再英勇无畏也掩盖不了他的犯罪事实,因此他便是想通过请求极刑来表现自己的悔过,使“无心之过”因他的“坦诚”而显得无可厚非。但若他真的光明磊落,何不早早自首,使他的壮举为人知晓,又能表现他诚心悔过。这一矛盾恰好说明了多襄丸并非真心自首,而是在被捕后想借机谋求荣誉的“不得已而为之”。
(二)洗雪耻辱
冈仓由三郎将雪耻比作“晨浴”,蒙羞的人要像洗掉身上的污秽一样洗刷名誉的污点。武宏夫妇作为屈辱的受害者,分别提供了两种以自我无辜为主题的辩词。
真砂哭诉多襄丸侮辱了她的身体,武宏又杀死了她的灵魂。她无力报复强盗,于是向蔑视自己的丈夫复仇,然后自杀。耻感文化要求受到侮辱的人要通过复仇或自杀来洗刷耻辱,真砂回到清水寺认罪,不过是借“供认”来告诉旁观者她已尽最大可能地雪耻了。
武宏的鬼魂说真砂背叛了他,他是因这莫大的屈辱而自杀的。在日本封建时期,自杀是一个人对自己的名誉进行的最后也是最有力的声明。武宏无法改变自己和妻子遭受侮辱的事实,就只能以自杀来维护一个武士的尊严。
名誉之于多襄丸三人甚至高于生命,因此他们编纂案情,将自己塑造成用生命维护名誉的“知耻”的人。但他们相互矛盾的说辞又恰好成了彼此说谎的证据。三个人靠谎言修饰名誉,并以践踏他人的人格和名誉来成就自己的形象,殊不知在看客的眼里,枉顾道德与生命却不得善终的他们,不过是上演了一场滑稽的悲剧。
二、耻感文化的实质——不可承受的“名誉之重”
耻感文化下,一个人越是为了名誉而牺牲其财产、家庭甚至生命,就越可见其品德高尚。然而求生是人性本能,当文化习惯与人性本能相冲突时,便产生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掩盖耻辱,这样既能维护名誉,又能保全利益。
《竹林中》的三人都有亏于名誉,也都企图隐匿案件真相。尤其是武宏夫妇作为受害者却没有主动报案以求公道,正是因为事实上他们并不像自己说的那么高尚。
掩盖污点是为了迎合舆论而非自我救赎。耻感文化下名誉被推崇为道德标杆后,为了迎合社会评价,个体就可能要以压抑本心、做出不情愿的事情作为代价。这种不情愿一如三位主人公,真实案件中的他们并不愿意如各自供词那样做,谎言正好印证了他们虚伪的荣辱观。
萨特说:“如果我们同他人的关系扭曲了,变了质,那么他人只能是地狱。”过分强调名誉至上,人们反而更加善于说谎。重视名誉本应是规范自身行为的一种手段,而过度依赖于他人的评价,在一举一动中自己首先充当了“他者”去审视自我,反而使名誉的约束变成了扭曲人性的枷锁,从而让自己陷入了一个不断做着不情愿的事情的“地狱”。
三、耻感文化的文化根源
日本耻感文化追根溯源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入密切相关。张哲俊先生提出,在以汉字和宗教文化为基础因素的东亚文化圈中,日本以汉字为媒介从中国引进了儒释道文化,其中又以儒释两家文化影响更为深远。
(一)耻感文化的儒家文化根源
维护封建伦理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特征,其实质是集体主义。儒学传入日本后,从淳仁天皇根据儒家思想颁布仁政律令,到江户时代真正深入百姓生活,集体主义思想也随着儒学渗透进日本国民的日常言行。
集体主义是名誉存在的前提。集体意味着不容忽视的他人存在,而名誉是他人对自我的评价。当一个人名誉有损时,表示社会对其行为的否定。集体主义下,一个人若是得不到集体的承认,必然导致毁灭性后果。多襄丸三人不得不面对审讯时,他们根据自己的社会身份,为了维护在集体中的个人名誉而说谎。因此多襄丸成了敢做敢当的侠士,武宏真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只有这样他们才不负自己的社会身份甚至能获得荣誉。
(二)耻感文化的佛家文化根源
佛教在公元六世纪传入日本,通过本土化和世俗化,到七世纪后期被尊为护国教,为日本社会广泛接受。
儒家思想构成了耻感文化的他律因素,佛家思想则构成了耻感文化的自律力量。佛教最重要的信仰是轮回果报,即前世善恶决定了轮回之道,有罪入地狱,无罪入极乐。在轮回果报的影响下,耻感文化形成了引人向善的初衷。名誉代表社会普遍的善恶标准,行善能因社会赞赏而获得名誉,而作恶则会因被人唾骂而有损名誉,其实质就是善恶有报。武宏的鬼魂说:“妻子的罪恶,还不止于此。要仅仅是这样,我也不至于在冥冥之中这么痛苦了。”②妻子的罪恶构成武宏的耻辱,这份耻辱如同他自己作恶一样让他堕入地狱,这也说明耻感文化与善恶果报之间的源承关系。
四、总结
虽说小说中的三人都身处名誉泥沼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耻感文化从一开始就是扭曲人性的。相反,恰好是因为这种羞耻观是出自内心尚未受到玷污的时代,人们自愿维护名誉,且效果是日本民族所梦想的,所以他们才会在耻感文化上极尽努力,以至于发展到小说中这种极端地步。《竹林中》这篇小说直指文化畸形下的社会荒谬,让人意识到荣誉与罪恶的仅一墙之隔。不仅是日本社会,同样存在耻感文化的东亚文化圈也能从小说中得到警示,看到耻感文化的弊端,并且寻找一个更加合乎人性的方式辅以律法去弥补过错,从而使有错之人在社会中和心灵上都能得以救赎。
注释:
①[美]本尼迪克特著.菊与刀[M].田伟华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1:102.
②[日]芥川龙之介著.芥川龙之介小说选[M].文洁若,吕元明,文学朴,吴树文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90.
——评章越松著《社会转型下的耻感伦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