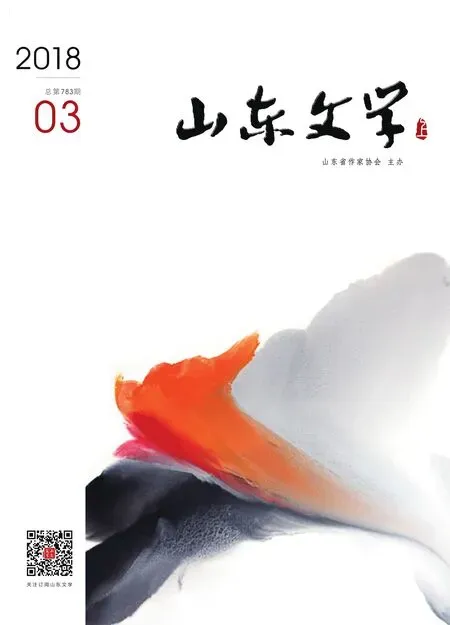破茧之功
——从《茧》与《家》看张悦然06年以来的创作
张天棋
张悦然出身“新概念”作文大赛,是最早成名的80后作家之一。彼时的一些“明星”如今已不见文学道路上的探索,张悦然却以作品证明了她对文学的坚持。从出版作品的时间来看,自2006年推出长篇小说《誓鸟》以来,张悦然的脚步有所放缓,主要作品包括十余篇中短篇小说和201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茧》。翻开这些作品,我们似乎能触摸到她前行的足迹和洒下的汗水。
风貌的蜕变
相较06年以前的作品,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张悦然的转变,这种感受,来源于作品的题材、情节的组织以及文笔风格等许多方面。《茧》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尤其能展现这种转变。
《茧》可以说是张悦然近十年来分量最重的作品,面世以来颇受关注和好评。故事发端于医院领导程守义在文革中被遭他压制的下属李冀生自太阳穴按入一颗钉子,程守义由此成了植物人,李冀生却未被查出,钉子的所有者汪良成牵扯其中,选择自杀。这一事件,影响了三个家庭三代人的命运。小说以李冀生的孙女李佳栖和程守义的孙子程恭交替讲述的方式,展现了三个家庭三代人命运的纠缠,探讨了历史对一个人的影响,以及一个人应该如何对待这种影响,从而如何影响别人。
与时代历史相结合,是《茧》 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早期80后写作者曾因过分关注个人世界引来不少批评,关注社会现实、关注时代历史成为文坛对80后作家的一个期待。张悦然06年以前的作品较少涉及历史,而在《茧》中,时代历史被用心地编织进故事:从文革到恢复高考,从80年代的启蒙思潮到90年代的出国、下海热潮,从迈进新千年到经历非典,我们循着字句,走过中国新近经历的四十年。
走进这个故事,我们会发现,它编织得是比较细腻的。回顾张悦然06年以前的作品,往往是作者的情绪推动情节的发展,而在《茧》中,情节的发展基本是由合理性推动的。在历史形成过程中,各人的心理和行为有其合理的解释,钉子事件就在这些心理和行为的推动下不断发酵。一些论者以“绵密”来形容这部作品,这是对张悦然驾驭情节能力的肯定。
选择这样的题材,讲述这样的故事,必然要涉及相应的人物。在这部作品中,张悦然涉及的人物类型明显拓宽,跳出了散发艺术气质的少男少女的范围,对人物的塑造也更为有力。比如程恭的奶奶,在丈夫成为植物人后去有关单位讨说法,她以哭为武器,哭出了一副“鹧鸪嗓子”,讨来了说法。从那以后,“只要遇上什么不如意的事,她就搬着凳子去那里哭一哭。我们家住的这两间屋子是她哭来的,姑姑的工作是她哭来的。连她嘴里那两颗金牙,也是哭来的。”一个既不幸又令人感到棘手的社会底层妇女的形象跃然纸上。又如程恭的姑姑,在小程恭被送到奶奶家,姑姑为他换裤子时,“我那只小小的生殖器暴露在灯光下,她的脸腾的一下红了。像是害怕被我察觉,她立即把秋衣套在了我的头上”,一个爱难为情的老处女的形象如在眼前。
不仅如此,与张悦然前期的作品相比,《茧》中的人物,其性格的层次也更为丰富。前期的张悦然,偏爱一种“过”的状态:“偏执的,疯狂的,奔着一个方向就一头冲过去,那是多么奇妙的事”,这往往造成笔下人物性格的单一和极端。单一如《樱桃之远》中的段小沐,是全然的纯洁、善良;极端如《竖琴,白骨精》中的小白骨精,甘愿丈夫一块块取走她的骨头打磨成让他如痴如狂的乐器。这种情况已然发生转变,《茧》中的人物就体现了这一点。
程恭的奶奶,丈夫先是成了植物人,后又被人从病房运走,不知去向。对害自己守活寡的丈夫,她恨得牙根痒痒,对他全无照顾,只等哪天他死了算了。可张悦然却写她在临终前问程恭的姑姑:“你说你爸早就在那边等我了吗?”程恭的姑姑犹豫着说自己不知道,“过了一会儿,我奶奶忽然摇了摇头,‘我不想再一个人了。’”程恭的奶奶一贯尖刻凶悍,让人忘记了这其实也是由于她的不幸。面对死亡时的朴素反应,暴露了她脆弱的一面,令人唏嘘。
女主人公李佳栖,从小父爱缺失,父亲在她心里有着无可取代的地位。父亲去世后,她认识了父亲的旧交殷正。殷正亦师亦友,对她怜爱有加,渐渐与她父亲的形象重叠起来。她向殷正表明心迹,殷正没有接受,她选择了离开。有一天,张悦然写她傍晚一个人到海边游泳:“天已经开始黑了,风很大。水里只有寥寥几个人,正往岸边游来。我朝着大海深处游去……海水很冷,骨头咯噔作响,双脚开始有点发木,蹬得越来越慢……我在等着更大的海浪打过来,等着咸腥的海水灌入喉咙。等着恐惧消失,意识消失。”然而张悦然接着写道:“一声轮船起航的汽笛声响起,在远处,看不到的什么地方,好似呢喃的耳语,低沉,如泣如诉,仿佛是一种召唤……我开始调转方向向回游……气力很快就耗尽了,身体也没了知觉,好像下一秒就要停下来了,但我仍在向前游。到达岸边的时候已经虚脱,我躺在沙滩上,一动也不能动。”这一次,生命再也不是可以轻易放弃的东西,刻骨铭心的感情结束了,人还是要继续走下去。死没有那么容易,也不该那么容易。
承载着上述种种转变的,是张悦然日益简洁有力的文笔。张悦然以“换笔”来比喻自己文笔风格的转变:“我的这种转变就好比,写书法,原来用的是特别细的笔,当我要写另一种字体,就必须换一支粗笔,换笔的过程特别痛苦。”但她同时又说:“但又必须完成这个转变,不然以后很多东西都写不了。”
从开始发表作品以来,张悦然便以其大胆的想象,瑰丽、奇特的语言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一方面是她文学天赋的体现,令人击节赞赏,一方面也有令人费解和形式大于内容之病。任举一例,如《誓鸟》中,女子为了救人被困在燃烧的高塔上,最终从塔上跳下。她的丈夫目睹了这一幕:“他跑过去,看见女人犹如孔雀一般雍容升起,她的身后,缓缓地开出一扇鲜红的屏。”他们的女儿未在现场,却相信自己“看见了孔雀开屏那一刹那的兀艳”。“孔雀一般雍容升起”似在描述女子落地后弹起的样子,“缓缓地开出一扇鲜红的屏”则是形容鲜血的漫流,“雍容”与“缓缓地”产生了慢镜头般的效果,“兀艳”则是张悦然自造的词。这里的比喻颇为难解,表现手法也很繁复,只为表现女子之死的凄艳与高贵。这样的句子在张悦然前期的作品中并不少见,虽颇具才气,却为读者准确理解带来困难,也影响文章的流畅性。在张悦然06年以来的作品中,这样的现象大大减少了。作家在文学上的才情没有减退,而是蕴于更为简洁有力的文字中。仍旧以《茧》为例,在小说的开头,李佳栖约程恭见面,但不确定对方会赴约。她站在下着大雪的窗前眺望,久久等待,终于,“一个黑点在眼底出现,像颗破土萌发的种子”,程恭来赴约了。联想巧妙又易于领会,既是对画面的生动呈现,又点出李佳栖初现希望的心情。而在一些地方,作者甚至更加不动声色,表现力却不减反增。如李佳栖回忆一家人吃饭时的情景,这样描述爸爸和爷爷的关系:“奶奶经常对爸爸说一些话,然后补充道,这是你爸爸的意思。而爸爸对奶奶讲话,有时以‘你告诉他’开头,那就是说给爷爷的。”平铺直叙,却使读者对父子隔阂之深、之久有了充分的体会。
方方面面的转变,推动着张悦然作品风貌的蜕变,更新着我们的印象。而风貌的蜕变,也透露出其它重要转变的发生。
思想的深化
2003年,《葵花走失在1890》出版,这本短篇小说集,是张悦然的第一部作品。莫言在为它作的序言中指出,张悦然以小说营建了一个高于现实的世界,那是由梦想构筑的世界,这里有希冀,也有梦想受阻的痛楚。张悦然小说的价值在于“记录了敏感而忧伤的少年们的心理成长轨迹,透射出与这个年龄的心力极为相称的真实”。在序言的最后,莫言写道:“伟大的文学,从不单纯停留在梦幻的层面上,它要涵盖历史,涵盖广阔的现实与责任,涵盖琐碎、艰难而具体的现实人生。”这是文学的优秀传统,也是老一辈作家对年轻一代的期望。彼时的张悦然,基本上是从自身出发,去感受,去梦想。这是写作的原初冲动,也是认识水平与生活经验局限的必然。到了2006年,长篇小说《誓鸟》出版。张悦然在后记中写道:“我花了那么久的时间,才终于明白,梦不是我此生的全部。梦可以停息,但生命仍在继续,也许还会更活泼一些。”
如今的张悦然,已不再是两三天不出门,在浴室、床、书桌二十五米间的距离里活动,没日没夜地写作的文艺少女。她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是《鲤》系列杂志书的主编,还是人民大学文学院的老师。生活环境的转变、生活经历的拓展,使张悦然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发生了转变。同时,张悦然也在有意识地提升自己,如前辈作家所期望的那样,向伟大的文学靠近。深入张悦然2006年以来的作品可以发现,长篇小说探讨的问题比较独立,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相对超然;中短篇小说反映的问题涵盖广泛,与当下生活息息相关。而无论长篇小说还是中短篇小说,从关注的问题,到思考的深度,与以往作品相比,都上了一个台阶。
长篇小说《茧》探讨了个人与历史的关系,这里的“历史”受到时代的影响,但主要还是个人的历史。它可以是一个故事在几代人身上的延续,可以是一个人从另一个人那里继承来的历史遗留,也可以是一段生命历程,一种过往。人是否可以脱离历史而存在?人应该怎样对待历史,进而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小说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探讨。
小说的主人公李佳栖和程恭不是钉子事件的亲历者,但李佳栖父爱的缺失,程恭家境的窘迫却分明是历史的遗留:李佳栖的父亲在自身的矛盾中无暇他顾,程恭的爷爷程守义成为植物人是家庭命运的转折。历史的遗留在童年是不明所以的切身感知,长大后又成为牵引他们脚步的无形力量,正如小说中所说的那样:“多年以后我们长大了,好像终于走出了那场大雾,看清了眼前的世界。其实没有。我们不过是把雾穿在了身上,结成了一个个茧。”历史对他们的影响,使他们不可避免地踏上了探源之旅,对历史置身事外,可能只是一种幻想。当历史以污点的形式存在,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伤害,一个人该如何对待自己的过失?李冀生使程守义成为植物人却未被查出,他至死拒不忏悔,对此事避而不谈,过失却不能由此被消除。殷正曾举报同事李牧原,并一直以李牧原的悲剧主要源于自身性格来说服自己。但在遇到他的女儿李佳栖后,殷正的内心受到触动。多年后,他在回忆录中反思了自己的所为,并向李佳栖坦承。张悦然借殷正之口传达了自己的观点:“每个人的灵魂里都有肮脏和丑恶的部分,跟善良和美好的品质混杂在一起,是没办法切除的,承认它们,指出它们,可能是唯一和它们分离的办法。”对待历史的态度不同,产生的影响也不同。李冀生的拒不忏悔使受害者无法得到真正的告慰,使受害者的原谅失去基础,也使李冀生自己的家人受到罪恶感的煎熬。张悦然以不同人物的命运向我们表明,一个人越是逃避历史,越是走不出历史,死也不过是另一种逃避。只有正视历史,以实际行动去弥补,才能使自己得到解脱,减轻对他人的伤害。反思越彻底,历史的余毒代谢得越干净。人不是孤立存在的,一个人既是影响的消受者,也是影响的施加者,既是历史的继承者,也是历史的书写者。钉子事件的影响之所以从两个人扩大到三个家庭并一代代蔓延,正是因为受害者也成了施害者:李牧原为父亲的罪受煎熬,却也使自己的女儿父爱缺席;汪良成的妻子因为丈夫自杀而发疯,却又成为女儿汪露寒走不出的阴影;程恭的奶奶陷入守活寡的不幸,也不许“罪犯的女儿”汪露寒赎罪获得解脱……张悦然的思考是丰富的,延伸至事件的方方面面,演习着种种可能性;她的思考也是深沉的,人与命运的相处是艰辛的,艰辛中又有光辉。
张悦然2006年以来的中短篇小说主要发表在她主编的《鲤》系列杂志书上,也有中篇小说《大乔小乔》发表在《收获》杂志上。其中九篇小说被收入小说集《我循着火光而来》,于2017年出版。从这些小说中不难看出,张悦然已经悄然走入成人世界,正如少女时代的作品反映出少女的世界一样,如今的作品反映了成人的生活场域、心态、规则和痛点。在《沼泽》中,跌跌撞撞的少女初初与略经沧桑的女性美惠相识,在酒吧里,喝了一杯又一杯的初初问美惠:“你平常都不喝酒吗?你难道就没有什么难过的事吗?”美惠说:“要是喝完了不用再醒过来我就喝。”这是两个世界的差别的生动诠释。对于成人世界,张悦然观察着,也思考着,《家》在呈现这种观察与思考上颇具代表性。
《家》讲的是同居的情侣裘洛和井宇感到生活没有意义,不约而同离家出走的故事,而此时井宇刚刚实现了期待已久的升职。两人已许久没有真正的交流,对彼此的出走毫不知情,留下家里的钟点工小菊揣摩着这一桩怪事。而小菊对她的丈夫也是一边怨着,一边过着。
裘洛在出走前,最大的感受是虚假,这种感受在她去老霍家时最为强烈,老霍们的生活除了对物质的讲究外再不见别的什么。这样的生活,作为奋斗目标,是那样真实,当裘洛感到它的不真实时,却无法告诉井宇这一点,因为,“为了维系辛苦的工作,他必须全神贯注并且充满欲望地看着这个目标,动摇这个目标,相当于把放在狗面前的骨头拿走”。殊不知井宇自己也在希求“一点热情、一点理想化的东西”,害怕自己变得“像那些同事一样无趣,一样庸俗”。可是联系裘洛对井宇的看法,怎知那些同事不像井宇一样,也在希求“一点热情、一点理想化的东西”?本以为是为了过上老霍的生活而奋斗,到头来却成了为了工作而需要这个目标。可如果不以这个为目标呢?“一点热情、一点理想化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生活的意义是否就是“一点热情、一点理想化的东西”呢?当代人找不到生活的意义而需要依靠自己也不甚信服的意义生活下去的困境,透过张悦然的文字浮现出来。至于人们为什么会把“老霍的生活”作为目标,在小说中也能看出端倪。裘洛和井宇出走后,他们的房子成了钟点工小菊的乐巢,看到伍尔芙那句“女人必须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她深有同感。可小菊在北京并非没有栖身之所,让她感到自由的,与其说是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不如说是“水流粗壮”的热水和浴缸,是她原本无缘享受的舒适生活。即使知道主人随时可能回来,她仍然“快活地迷失了”。物质对人的吸引,怕是再自然不过了。为了对抗过剩的物质,过一种“有节制的生活”;为了摆脱生活的种种虚假;为了不再过看不到意义却如陀螺般转个不停的生活,裘洛们出走了。可他们的出走,只是因为“花了太多的时间想象这件事,所以这件事必须成真,否则生活就是假的”,对虚假的反抗就是假的。只是因为不想对现实束手就擒,如同赌气的孩子。至于要去哪里、要做什么,“我并没有打算,真的”。他们选择以善良这种最易得、最不会出错的,“热情的”“理想化”的东西为意义,抱着自救的目的去救人,成为了地震灾区的志愿者,这与他们把老霍的生活拉过来作为目标何其相似。娜拉出走后,不是饿死,就是回来,是因为现实;裘洛们出走后,似乎注定要回来,因为他们缺乏反抗的纲领。张悦然以她的观察和思考,为我们呈现了困扰现代人的精神谜题。由想象到观察,由感受到思考,张悦然的创作方式发生了转变;从关注个人感受到关注社会现实、关注普遍人性,使得张悦然的观察和思考有了更高的平台。从作品的思想深度来看,张悦然已经有了可喜的开始,也留给我们更多的期待。
结语
总的来看,2006年以来的张悦然,保持着稳定的创作态势,杂志书主编、文学院教师的工作,也对她的文学创作形成支持,显示出她在文学道路上继续探索的志愿。关注历史、关怀现实,张悦然正在向文学的优秀传统靠拢,手中的笔也被磨砺得更加有力,来传达她的所思所想。怀着对文学的坚持,相信张悦然会进一步完善自己的创作特色,为文学的优秀传统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