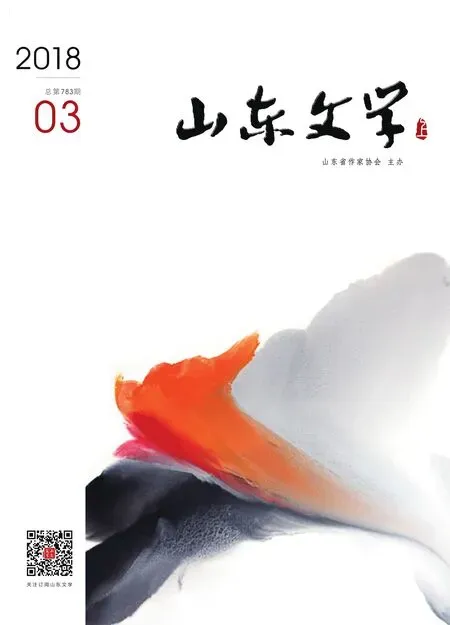从《一顿浆水面》说开去
——论马金莲近年的小说创作转向
雷作安
马金莲的文学创作始于世纪之交,在80后作家群体中,马金莲无疑是极具个性的一位。这一方面源于在伊斯兰文化背景的浸润下,她以女性敏锐而多情的视角,用散文化的叙述方式所呈现出的小说创作的独特风貌。另一方面则源于在城市化、现代化日益推进的今天,当大多数作家将叙述生活的笔触伸入城市,描绘现代生活的复杂与困顿时,马金莲却从个人真切的情感、生活体验出发,扎根于宁夏西海固这片贫瘠的故土,用纯净、质朴而饱含深情的语言展现出了西海固丰富而饱满的乡土世界。如果说马金莲早期的小说创作,通过对以“扇子湾”为中心的农村穷苦、饥饿的日常生活,敏感、单纯的家庭伦理关系,细碎而又繁重的农事活动等风土乡情的描绘,表现了其笔下所延展的乡土世界的广度;那么近两年来以《一顿浆水面》、《凉的雪》、《听见》等为代表的小说,则将叙述的焦点从乡土世界转移到了走入城镇的农村人,通过他们在城市生活的见闻和切身遭际,马金莲试图重建城市生活中富有温情的“乡土家园”,努力探寻着当代底层乡土叙事的新空间和所能达到的精神深度。
一、一顿浆水面:乡土经验与城市生活
《一顿浆水面》中的田寡妇怎么也想不到,一顿浆水面会引起如此大的风波,让她被迫与逐渐熟悉起来的城市生活走向决裂。这样一顿饱含着温暖乡土记忆的浆水面,是田寡妇、陌生老汉这些因照顾孙子而来到城市生活的“老农村”所念念不忘的“故乡”与“青春”,代表着他们的“窝窝梁”和“扇子湾”,也正是基于共同的乡土生活经验,使得田寡妇最终抚平了内心的忐忑和不安,趁儿子、儿媳上班的空当,大胆将这位“一张脸总是笑眯眯”的老汉引入家里,美美吃了一顿浆水面。熟悉马金莲的读者应该知道,其以“浆水”命名的小说创作,在这之前还有发表于2016年的《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而从田寡妇一开始食材的准备,到卧浆水时一系列熟稔的程序性动作,田寡妇俨然就是1987年在扇子湾的锅台上烧水、洗菜,戴着白帽子卧浆水的“奶奶”。只是与村里土院子中整日忙于农事劳动的“奶奶”相比,进城带孙子的田寡妇显得悠闲很多,她以农村生活的日常经验打量着城里新奇的一切,并由衷地发出感叹“城里真是和乡下不一样”。
外在的“城乡差距”表现在田寡妇身上,固然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消退,例如在城市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田寡妇“只从衣着上看,跟城里的老婆子差不多了”“说话也变得文雅了”“她现在已经学会了独自过马路,先左后右,在车流缝隙里自如地穿梭。城里的水绵软,几年时间,她的手和脸细腻多了,自己摸着都软绵绵的。”而根植于田寡妇骨子里的乡土情怀和生活经验却丝毫没有减少,并与城市固有的生存状态之间构成了一种紧张关系。这不仅表现在当田寡妇将家里的详细情况“麻袋倒核桃,哗哩哗哩全倒给一个老婆子”时,想起了儿媳妇言传身教的城市生活“准则”,使得她“回到家赶紧锁上门,不放心”“出汗了,心有点跳”“不踏实”;更深层地表现为在田寡妇看来,请接孙子时搭过话的老汉在家吃一顿浆水面,就如同“在窝窝梁,大家随时到别人家串门子,碰上谁家女人的饭熟了,吃一碗是常有的事”,而在“像个主人一样”“很从容”,毫不客气且广场“舞姿娴熟”的老汉眼里,这是田寡妇有意表露的“她的心”,田寡妇的儿子甚至认为这是“背着我们寻人”、是“引狼入室”。由此,植根于田寡妇内心深处的乡土人情观念,在城市生活的语境中被彻底地“误读”了,她不得不踏上了返乡的路途。
实际上,表现诸如田寡妇等人的乡土经验与城市生活的矛盾、隔膜与融合,是近两年来马金莲的小说创作所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海固的乡土世界固然是马金莲文学语言的词根,可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生活环境的改善,马金莲和她的文学创作不得不面对着这样一个事实:即来源于其切身乡土生活经验的早期小说创作所获得的文学成就,客观上将她从乡镇推入了城市生活的怀抱,而作为其小说创作灵感源泉的村庄,也不再是一种封闭、保守、稳定的文化结构,社会的裂变和价值追求的转化无不渗透和冲击着西海固传统农村的乡村伦理,宗教信仰和生活观念。这一既定的事实迫切需要已然谙熟乡土写作的马金莲,站在新的价值立场和观察视角上,透过破碎的乡土生活表象,进一步走向社会、人生的更深处。正如作家自己所说:“乡村像一个我们熟悉的面具,一不留神,它已经变得让我们感觉面目全非和陌生难辨。而在意识里,却对乡村寄予了我们最初成长岁月里的美好和情感,现在我们还以这样的尺幅去衡量乡村,无疑现状会让我们失落。这种落差,怎么在文字里呈现?怎么扣问追索乡村失落的东西?又怎么重新发现、讴歌和守望乡村?这一命题,随着我一直书写的那个村庄扇子湾的搬迁,很直接很残酷地逼到我面前了。”
二、听见:抒情笔触与叙事话语
乡土世界是马金莲情感的寄托和小说创作语词的家园,从温热的乡土记忆中跳脱出来,转入城市叙事的马金莲,仍然保有鲜明的乡土印记。这不仅体现在其小说中惯有的方言土语的运用,更包含在其近年来城市叙述话语客观、冰冷的底色中,那满怀深情的对乡土生活的追忆和眷恋,而这抒情的笔触想要遮蔽与淡忘的,正是失落的乡土和现代生活中不得不面对的世态人情的冰冷、残酷的生存竞争,正如其在早期短篇小说集《父亲的雪·后记》中所说:“文字营造的世界,是温暖的,是矛盾的,当然也难以避免生活中那些必须面对的残酷和冰冷。”在以《永远的农事》、《碎媳妇》等为代表的乡土世界破碎之后,对处于乡土与城市夹缝状态中青年人命运的关注和书写,自然成为马金莲近年来小说创作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当外部世界的现代化浪潮快速推进的时候,“扇子湾”的年轻人,注定再也无法固守着这片干旱、贫瘠的土地,继续“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生活。然而,当他们满怀着“重建家园”的希望涌入城市,与以往充满情感温度的乡村不同,迎接他们的将是陌生、冰冷而残酷的城市生活。
《听见》中以青年教师刘长乐为叙述视角,是马金莲对之前小说创作大多从儿童、女性叙述角度出发的突破。刘长乐其实是一位工作踏实、认真负责的好老师。作为跳出农门吃公家饭和“改写了刘家人祖辈以来的农民族谱”的年轻人,对学生他完全可以“不打也不骂,他只要尽到自己的责任,学生学好学坏,和他无关……只要把日子混着往下推就是。”可是他错就错在想对他班上留着长发、上课揪女生头发被抓现行的“刺儿头”学生腊志东进行批评教育。然而令他万分惊讶、措手不及的是,当他“想拍一下学生的肩膀,很绅士地请他跟自己走,去办公室详谈”的时候,腊志东竟一把“死死地反手扭住了他的手腕”。刘长乐被彻底地激怒了,在和“不服管教”的腊志东厮打的过程中,当他夺过其手中的书“卷了起来往腊志东头上戳去”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书里卷着一只脱了帽的钢笔,而现在这只钢笔插在了腊志东的耳朵里,“血开始从腊志东的耳朵里往出流”。
与以往细腻舒缓、沉溺抒情的笔触不同,《听见》一开篇,马金莲就用强烈的矛盾冲突、稳健的叙述,严谨的逻辑架构和快速推进的故事情节,持续吸引着读者的注意力。之后发生的事情远不是刘长乐这位单纯、刚入职却因冒失犯了教学大忌的青年教师所能想象和承担得起的。事实上,被误伤的腊志东的耳朵并没有眼见的那么严重,县、市两级医院全面检查后的结果都是:“出血是因为外耳道损伤,现在血止住了,没有耳鸣、耳聋和继续疼痛等症状,说明鼓膜没破……不要用手抓,掏,等耳道伤口结疤,就可以了”,甚至“没必要住院”。真正让刘长乐难以承担和无法理解的是同样作为教师的腊志东的父亲,竟然利用此事将他的儿子作为讹钱的工具,“狮子大开口”,向刘长乐及其远在农村年迈的父母要四十万私了费,这对于刘长乐及其家人来说“简直要人的命哩”,而伴随着讹钱接踵而至的是腊志东家人夸大其实将此事散布在网络上的舆论压力、攻击谩骂,以及教育局对此进行的停课调查。利欲熏心的家长,冷漠无情的领导、同事,罔顾事实、装腔作势的调查,最后,终于将刘长乐逼上了跳楼自杀的悲剧道路。
《听见》中刘长乐的悲剧足以令读者沉思良久,如果我们将作家笔下田寡妇因一顿浆水面而引发的风波,看作乡土经验与城市生活相互碰撞而激发的一个“事件”,那么刘长乐因体罚学生而最终走向自杀所面临的各种打击,则是近年来马金莲小说创作中,每一位带着乡土气息步入现代化都市的农村青年,所无法避免、或多或少,都要面对的普遍“现象”。在实用主义、拜金主义甚嚣尘上的今天,随着乡土人情一起消散的,是城市道德秩序的瓦解,而面对着种种社会、人生的困顿,马金莲并没有给读者一个明确的答复:《平安夜的苹果》中在玩具厂打工的男孩,为了三块钱将水果刀插进了坐地涨价、羞辱自己的水果店老板的心上,以此表达着自己的愤懑和反抗;《凉的雪》中从小失去母亲进城打工、沾染恶习的毛子,通过在坟坑穿堂中与大满拉的推心置腹,获得了内心的安慰和宗教的救赎;《听见》中无法寻到出路的刘长乐更是以自己年轻的生命,希望在那些逐渐被金钱、权利腐蚀而干枯、坚硬的心灵中唤起“疗救的主义”。
三、小结
将细腻抒情的笔调从逐渐陷落的扇子湾提出,转而用平静沉稳的叙述关注当下的生活,是近年来马金莲小说创作转向的明显趋势。这种对当下生活的关注,既包括随着时代变迁,社会进步而走出乡村、进入城市谋取生活的年轻人,他们作为城市“边缘人”的生存状态、情感经历,以及内心隐秘的变迁;也包含着马金莲对那些依然留守在村庄的老人和儿童,对他们孤苦无依的生存境遇的关怀。当然,对扇子湾的一切满怀着温暖记忆和深厚情感的马金莲来说,这样的抽离无疑是痛苦和需要时间的,对故乡的眷恋和依依不舍,依然促使她时而走入已然远逝的乡土风物,去提取残存的暖意,至少用来慰藉自己内心的那些奔突。
在配合《文艺报》所做的17年年末小总结中,马金莲这样写道:“2018年,我会依旧坚信生活和文学的美好,以文学的名义和方式祝福自己。希望在坚持每年10万字左右的中短篇写作之余,改定即将完成的留守题材长篇小说《孤独树》,并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回望》。”是的,作为读者,我们也关注着这些矗立西北贫瘠土地的“孤独树”,并满怀希望地期待着,那饱蘸乡土气息的深情“回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