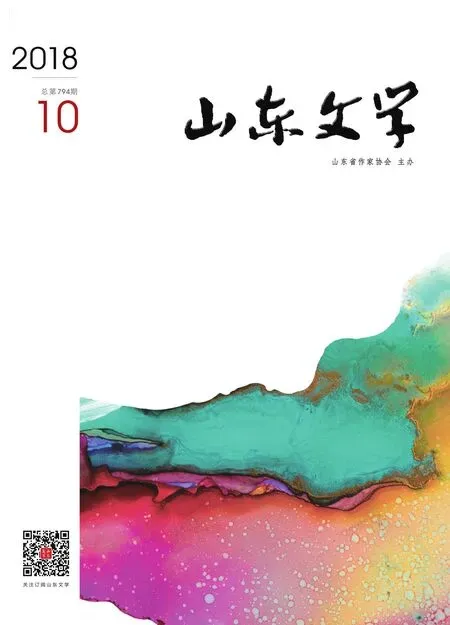改革文学与左翼叙事传统
吴 辰
在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被邓小平同志提出,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支持。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文学界很快也对“改革”这个关键词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在1980年前后,各类文学刊物上以“改革”为题材的作品如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蒋子龙、张洁、李国文等作家一时间几乎成为了文化英雄,而他们在作品中所塑造的诸如“乔厂长”等人物形象也深入人心,读者们纷纷呼唤着这样的人物,“愿有更多的乔厂长上任”,并给编辑部写信,希望派“乔厂长”到他们的单位去。而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改革”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了一种常态,其在文学中的作用也由一种思想性的资源向着素材性的资源转变。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思潮,改革文学在1985年之后就已经不复存在,而改革的精神和题材却不断地与各种文学思潮相结合,成为了贯穿新时期文学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
就存在的时间而言,改革文学可以说是昙花一现,但是,在这短短的几年中,其所产生的社会效应是轰动一时的。在这令人瞩目的效应背后,文学作品与时代主题的契合当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但是在这些作品的文本内部,叙事结构也是其可以与读者、与社会进行“无缝对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美国新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詹姆逊的眼中,一部作品的文本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意味,它显示了作者所代表的那个群体对某种政治愿景的诉求。之于改革文学,其内部的这种文本政治并非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以断裂式的姿态凭空塑造出来的,而是深植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左翼叙事传统之中。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左翼文学的出现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而在左翼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斗争经验形成的一套具有明显左翼特色的叙事传统更是使其在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体脉络中有着较高的辨识度,改革文学正是继承了左翼叙事传统,才能够在短时间内成为最能代表转型期中国精神气质的文学景观。
首先,改革文学对左翼叙事传统的继承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其文本内部呈现出的强烈的现实主义叙事倾向。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对于左翼文学的叙事传统而言,社会语境是决定文学作品具体情节发展的第一要素,有什么样的社会,才有什么样的主人公;故此,左翼文学家们不惜以大量的篇幅去在作品中交代时代背景。关于这一点,茅盾的创作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了,在短篇小说《春蚕》中,他毫不吝惜笔墨,将当时社会上从兵乱到贸易逆差的状况描写的淋漓尽致;而改革文学显然也给予时代背景以相当程度的重视,在《乔厂长上任记》中,作者在文章的一开始就将时代背景交代给了读者:“算算吧,‘四人帮’倒台两年多了,七八年快过去了,电机厂也已经两年多没完成生产任务了。”不难看出,无论是左翼文学还是改革文学,其对文本背景的交代都倾向于细致化,甚至精确到了某一个具体的时间点,而正是由于在时间设定上的精准,使得原本充满了“变量”的文学创作找到了一个可以赖以锚定的“常量”,进而收拢那些由于文本裂隙而充满歧义的文学能指,使读者的注意力在最大程度上聚焦于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在这一方面,改革文学甚至超越了左翼文学,作者不但限定了小说的文本时间,甚至还将小说发生的地点进一步缩小,或是工厂,或是生产队,进而紧紧地将叙事的中心集中于“改革”二字。
对时代背景的重视实际上反映了左翼文学和改革文学试图干预时代、干预生活的一种内在冲动,左翼之“左”,其精神的实质在于实践,在于对落后于时代的生产力或生产关系采取一种直接干预的态度。早在1930年代,鲁迅就曾经叮嘱左翼作家们要和实际的社会现实多进行接触,并要深入了解自己所要改变的对象的详细情况,夏衍的《包身工》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作,为了完成这篇作品,夏衍曾经亲自深入上海东洋纱厂,伪装为包身工去获得第一手的资料,其意图在于通过文学的方式来干预生活,从而解放那些在资本家铁蹄之下的纱厂工人们。改革文学显然继承了左翼文学在干预生活这一方面的优长:面对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新的机遇和挑战,1980年代的中国,在方方面面都面临着变化,而变化则意味着对既得利益者和守成者现有状态的挑战,随着改革的深入,其暴露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改革文学的作家们毫无惧色地以文学对生活发起攻势,去批判那些存在在改革领域的乱象。张洁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小说通过描写曙光汽车制造厂在改革领域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国家重工业部,这种批判是极其大胆的;而且由于作者长期对制造业以及高层决策者心态的深入了解,其批判可以说是直接触碰到了这一领域改革中的痛处,故而小说一经刊出,便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和《沉重的翅膀》类似,改革文学中的大多数作品都继承了左翼叙事传统中那种干预现实的精神,直接面对社会发出声音,以最大的热情去推动改革的发展。
由于强调对现实生活的干预,改革文学和左翼文学一样,在叙事时间上往往会选择一种共时性的策略,即文本发生的时间和现实生活的时间高度一致。在左翼文学中,张天翼的《华威先生》、丁玲的《水》等作品都是直接取材于身边发生的事件;而在改革文学中,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更是步步跟进时事,《“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战术》《种田大户》《陈奂生出国》等作品一步步地将中国农民在农村经济改革中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共时性的叙事策略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模糊文本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使文学发挥其最大的社会效益;而将纸面上的文学转换成实实在在的社会效益,达到文学与社会实践之间的互动,则是左翼文学和改革文学选择现实主义叙事倾向之鹄的所在。
第二,改革文学对左翼叙事传统继承的另一个表现是在叙事过程中呈现出的大众化倾向。
在左翼文学的叙事传统中,文学的大众化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左翼作家们纷纷以各种形式表达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在一份“左联”的文献中,还明确规定了“文学的大众化是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个重大的问题”。而对改革文学的作者来说,大众化也是他们所一直追求着的美学目标,由于这些作家的写作目的是在于干预现实生活,其必然会在最大的范围内去追求作品的影响力,这样一来,这些作家在写作时便纷纷将其潜在读者群体设定为普通的人民群众,而在文本结构上,他们也一定会选择一种最符合当时语境下人民审美心理的形式。在1980年代初期,改革一词出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频率是极高的,而面对着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重大变化,每个人在兴奋的同时也都怀着一丝丝的不安,“摸着石头过河”成为了当时时代气氛的最好写照。在这种语境下,人们更希望看到的是一些描写改革成功的案例,激励改革深化,给自己带来希望的作品,而这也成为了改革文学的作者们所孜孜追求的写作目标。在《乔厂长上任记》的结尾处,厂长乔光朴“用很有点裘派的味道唱”“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不但给了小说一个强有力的收束,还给了读者以信心和动力,他们真的会盼望着生活中乔厂长的出现,不畏艰难和困阻,带领着他们锐意改革。可以说,改革文学和左翼文学相同,其在选题上往往是那些和人民日常生活相关的事件,以文学的方式展示出了大众心中对于未来的愿景。
改革文学之所以能够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获得认可,其内容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则在于它的语言。语言决定思维,文学作品的语言在最大程度上决定着它与读者之间的距离,改革文学在语言方面显然是特别注意了的,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们于行文上很少进行艺术的再加工,而是一气呵成地按照故事发展的内在逻辑将作品铺展开来,而其叙述方式也是选择运用了一种相对比较传统的、讲故事一般的语气。在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中,一开始,作者就以一名故事讲述者的姿态出现在文本当中:“一幢建筑物,往往就是一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你信也好,不信也好,你听我给你讲讲花园街五号的故事吧。”不难看出,诸如“你信也好,不信也好”这样的口语化句式再加上句末的语气助词,拉近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读者仿佛面对面地和作者坐在一起,听作者讲述小说中的故事。显然,这种语言是一种日常生活的语言,是最能够和大众读者的灵魂产生共鸣的。实际上,这种对于语言大众化的追求也是源自于左翼文学的叙事传统,左翼文学很早就注意到了语言在拉近文学与群众之间距离等方面的重要作用,1934年前后发生的大众语和文字拉丁化的讨论就是其在理论方面的实践,不仅如此,左翼文学还强调文学形式上的大众化,将文学创作素材转化成民间艺术形式来吸引大众读者,这其中那些来自于民间的生机勃勃的语言显然也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改革文学显然借鉴了左翼文学的这种叙事策略,以大众的语言将大众的故事讲给大众听,进而与社会产生互动。
第三,改革文学对左翼叙事传统继承的还在于在叙事的过程中往往会将客观的日常生活加以理论化的转译。
虽然有着大众化的审美追求,但是左翼文学并非是完全写实地呈现出生活本真的样貌,其呈现出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滤镜将生活扫描之后所得到的景象。左翼文学从一开始就对理论有着较高的要求,左翼文学的倡导者们在左翼文学还未取得太多实绩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把诸如普列汉诺夫、梅林、卢那察尔斯基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著作介绍进了国内,意在以之来限定左翼文学的理论资源,乃至不使之在方向上走偏。而之于改革文学,一种基于改革本身的“社会进化论”与“现代化”的观念则成为了为文学创作指明方向的理论框架,改革文学的作者们或是从正面赞扬,或是从侧面抨击,或是写城市,或是写乡村,都离不开基于改革和现代化而建立的一套话语逻辑。这样一来,在文本中就必然会出现两个相互对立的行动主体,即“改革/反改革”、“现代化/反现代化”,也正是因为这两个行动主体的存在,才构成了改革文学的基本故事冲突。
在1980年代的中国,随着改革呼声的日益迫切,作家们甚至都没有时间去细细咀嚼“改革”两个字背后的深意,便以纸和笔投入了改革的事业当中,由于并没能深刻地理解改革背后的一套理论体系,故而在将这套理论体系转译为文学语言的时候,文本中往往流露出作家们的力不从心。一般来说,改革文学中需要一个可以寄托作者改革理想的人物形象,这个人物形象可以是《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厂长,也可以是《花园街五号》中的刘钊,他必然是整个文学作品的核心,但是,正是对于这样一个足以影响文本进程的人物设置,作家们却往往表现出了脸谱化、公式化的写作倾向,他们往往是在上一个历史时期遭受过迫害的人,有着满腔的热血和超越常人的智慧,他们在各种人际关系中游刃有余,并总能验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古谚。对于这样一类的高度概念化的人物形象,很多读者显然是不买账的,他们在呼唤着乔厂长的同时也坦言乔厂长的人物形象有时候甚至不如石敢等次要人物令读者印象深刻。这当然是改革文学的一点不足,但是在这点不足背后,却是改革文学的作者们对改造社会的迫切期望。同样的事件在左翼文学的发展史上也屡见不鲜,当左翼文学的倡导者们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引入中国文学创作的时候,一度因为来不及对其中一些词语进行学理性的翻译,而直接使用音译,这里边比较著名的就是将扬弃(Aufheben)直接译为“奥伏赫变”。改革文学在继承了左翼文学叙事传统中的革命性和实践性的同时,也将左翼文学中所特有的急进继承了过来,当然,这种急进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害改革文学的艺术性,但是,在其背后却显示出了文学工作者的良心以及他们对于社会的深沉的关怀。
在20世纪的中国,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可以说是一条贯穿了每个时代的主线,无论是经济、社会、文化,其产生和发展必然是一种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呼应,文学更是如此,20世纪的种种文学思潮背后,现代民族国家的作用都是显而易见的。其中,左翼文学与其背后所依托的那一套叙事传统以其对现实的呼应和对生活的干预成为了最能与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概念发生互动的文学类型。在1980年代,改革文学成功地继承了左翼文学的叙事传统以及在这套叙事话语之下所蕴含着的实践精神,虽然它的存在在中国文学史上只是短暂的一瞬,但是其所呈现出的精神光芒将和乔光朴等名字一起被这个民族所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