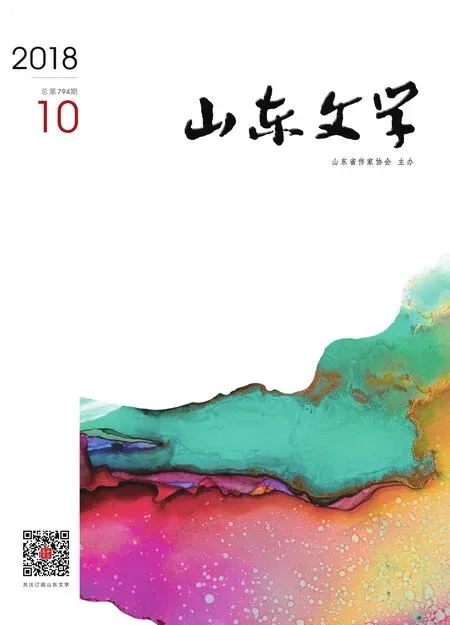风吹麦浪
李云雷
我骑着自行车拐进那片田地的时候,我爹和我娘正在地里割麦子。这是六月,田野中一望无垠的麦子已经成熟,散发出清新馥郁的气息。风吹着麦田,麦浪一滚一滚的,此起彼伏,向我涌过来。天上的太阳像一个大火球,定定地悬挂在半空中,散发出炽热的火,炙烤着泛黄的小麦和干活的人们。那些人弯着腰,一只手握着镰刀,另一只手抓住麦子,用镰刀在根部一割,麦子就被割了下来,他们将割下的麦子放在地下,继续向前走。他们的脸上淌满了汗,身上的汗衫也被汗水打湿了,偶尔他们会抬起头来看看天,天空万里无云,只有一个大火球!他们咒骂一声,低下头继续割。天气又热又闷,像蒸笼一样,可又是他们盼望的,割麦子的时候最需要的就是响晴的天,要是赶上阴雨天,虽然人凉爽了,但是成熟的麦子可能会发芽,打麦场也一片湿漉漉的,根本没办法将麦子摊开碾压,那样损失就更大了,所以他们宁愿冒着火球的炙烤,在烈日下挥汗如雨,匍匐着,蠕动着,蚕食着那一大片麦田。
骑车穿过坎坷不平的田间小路,来到我家地头那棵大槐树下,我喊了一声“娘——”,我娘正弯着腰在捡麦穗,她抬起头来看到了我,“哎”了一声。我姐姐家的几个孩子也在跟她一起捡麦穗,他们看到我,欢天喜地地叫着向我跑过来。我走到麦地里,迎接他们。我娘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向西边地里正在割麦子的我爹和我姐姐喊:“先别割了,歇一歇吧,二小回来了!”我爹和我姐姐听到喊声,回头看到我,他们停下镰刀,擦擦脸上的汗,说说笑笑着向回走。这时我已走到了我娘身边,我娘的腰上坠着一个包袱,捡到的麦穗就放在那里面,那包袱沉甸甸的,坠着她的腰,她的脸上满是汗水,沾湿了她额头花白的头发。我娘解下包袱,我拎着这个沉重的包袱向回走,走到地头上,将包袱里的麦穗倒在地排车上。孩子们叽叽喳喳叫着,笑着,我娘在后面擦着汗问我:“你怎么这时候回来了?”我说:“我跟学校里请了假,回家来割麦子。”我爹和我姐姐也走过来了,来到大槐树下,他们将镰刀放在一边,抓起晾在那里的玻璃水瓶,仰头咕咚咕咚喝了一阵水,随后在树荫下的田埂上坐了下来。我爹也问我:“你咋回来了?”我说:“我觉得快到割麦子的时候了,回来跟你们一起割麦子。”我姐姐笑着说:“你在学校里好好学习就行了,割麦子这么累,你哪里干得了?家里有我们呢,紧一阵就割完了,你不用担心。再说,哪有大学生回家来割麦子的?”我说:“我怎么干不了?干不了重活,也可以干点轻的,多少也可以干点吧。”我从小就在学校里读书,家里的重活都是我爹和我姐姐做的,我只是假期里才帮忙干一点活,在我姐姐的感觉中,我好像就是一个不能干活的人,做什么都笨手笨脚的,不像她那么利落,什么活都做得很漂亮。以前即使我在家里的时候,地里的活也主要是我姐姐做,只是她实在忙不过来了,才让我搭一把手,但我做的也都是些轻活,割麦子是在阳历6月初,学校里也不放假,那时正是快要期末考试的时候,很紧张,我在家里也没割过几次麦子。
割麦子是一年之中最苦最累的活,那正是最酷热、最紧张的时节,当时流行的词是“双抢”——抢种抢收,我们要抢着割麦子、打麦子、收麦子,再抢着种上下一茬庄稼,谷子、花生、玉米、高粱等等,才能喘一口气。在那之前的十多天,大家都抢着时间种,抢着时间收,怕万一老天变脸,刮一阵大风,下一阵暴雨,辛辛苦苦一年好不容易就要到手的收成就打了水漂。割麦子的时候,男女老少齐上阵,时间紧张,人们冒着烈日酷暑,冒着暴风骤雨,从地里将麦子抢收回来,才能安下心来。那时候生产队已经解散了,村里不再组织集体生产,家家户户都只能按各自的力量全力以赴,家里有壮劳力的还好说,他们割起来飞快,两三亩地一天就割完了,家里没有壮劳力的就麻烦了,老人、妇女和孩子,割起麦子来又慢,又费劲,有时割着割着就下起了雨,不少麦子就沤烂在地里了,他们只能请亲戚朋友帮助。但这个时候,家家户户都很忙乱,很少有人能靠得上。我们家就属于没有壮劳力的,那时候我姐姐已经出嫁了,家里只剩下我爹、我娘和我,我爹娘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我呢,先是在县城读书,后来到北京读书,家里的活做得很少,但好在还有我姐姐,在我姐姐看来,我家的活就是她的活,所以她干起活来从不嫌累,也没有计较,她就靠着她的肩膀支撑着我们的家,她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我呢,似乎也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我是什么时候想要回家割麦子的呢?我也不知道。我们的大学在颐和园附近,周围重峦叠嶂,风景秀美,在课余或周末的时间,我们时常到附近的山上去游玩。那时我刚离开家乡,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兴趣,站在北京遥望家乡的时候,我才感觉到我们那个村庄是那么遥远,那么偏僻落后,在北京这个国际大都市,我似乎才第一次睁开眼看到了世界。这个世界是那么新奇,那么绚丽多姿,我跟我的同学爬长城,吃烤鸭,逛遍了北京的名胜古迹。我们学校的外语教学极为先进,我们在收音机里听BBC、听NHK,既锻炼听力,也感觉到世界原来离我们这么近。课间休息时,广播上播送的是欧美的流行歌曲。高年级同学最关心的是GRE成绩,大家最向往的是出国留学,似乎到了海外,就能见到更多的世面。我只是一个来自乡下的孩子,刚来到这里时,内心很不适应。这里的同学都比我有钱,穿得也比我漂亮,他们都在忙着谈恋爱,忙着打网球,我也想打网球,但是我买不起几百块钱一副的网球拍子,我也想谈恋爱,但我只是个乡下孩子,哪里有人看得上我呢?我只好一个人到图书馆去读书,我读中文书,也读外文书,我在图书馆读,也在宿舍读。周末的时候,我时常一个人带一本书,骑着自行车跨过青龙桥,沿着西山脚下的公路向北骑行,骑累了,就歇一歇,爬上附近的一座小山,在山顶上找一块大石头,坐在树荫下读书。一读就是一整天,直到夕阳西下,我才下山。后来我才知道,我经常骑行的这条路,就是《骆驼祥子》里祥子赶着骆驼进城的那条路,沿着这条路可以一直走到西直门。
那一天我正在山顶上读书,突然听到鸟声啁啾,我抬头一看,只见两只喜鹊正在枝头鸣叫着,跳跃着,看到我在看它们,这两只喜鹊跳起来,离开枝条,像箭一样向远处飞去。望着它们远去的背影,我想起了小时候爬树掏鸟窝的往事,突然感到怅然若失,好像那已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了。我站起来,走到山顶的南部,向远处眺望。山脚下是一大片麦田,一直绵延到天边,青色的麦子已经开始抽穗了,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麦香,风吹来,我看到麦浪在随风翻涌,此起彼伏,一波一波向我涌来,像是要涌上山顶,涌上天空,将我整个人淹没了。我还看到,在麦浪中还飘浮着一些小黑点,那是戴着草帽的农民,他们顶着大太阳的炙烤,时而弯腰,时而伸腰,在地里做着农活。看到这些小黑点,我想起了我的家,我想不知我爹娘现在在做什么,是否也像他们一样,戴着草帽,弯着腰在地里干活?在那一刻,我突然感到,我离他们是那么远,心里涌起一种疏离感,这种感觉让我恍惚,让我恐慌,站在山顶上,让我一时不知置身何处。
我想起了小时候的一件事,那天我和我爹在地里割了麦子,装上车往家里运,我们将一辆地排车装得高高的,我爹在前面驾着辕拉车,我在后面推着。路面崎岖不平,车子不停地晃动着,我在后面推得三心二意的,有时用力推一下,有时就将手搭在车上,松松地扶着。车子来到一个上坡,我爹弓起身子用力向上拉车,我在后面绷住腿用力向前推着,车子一点一点艰难地向上挪动着,车上的麦个子也不停地摇晃着,我脚下没有踩稳,忽然一个趔趄,摔了一跤,车子失去了后面的推力开始慢慢向下滑动,我不顾脚上剧烈的疼痛爬起来又往上推,或许是我用力过猛,摇摇晃晃的车子一歪,一车高高的麦个子倾倒下来,跌落到路边的深沟里,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这时有两三个人骑着自行车路过,看到这惊险的一幕,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我爹将车子拉上坡,铁青着脸看了我一眼,也没说什么。接下来我们只能将麦个子从深沟里抱上来,重新装车,干了一晌活,我们本来已经又饿又累了,这突然增加的劳动耗尽了我们最后一丝力气。好不容易装好车,拉着车子向回走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天下虽大,在拉车爬坡时却没有任何人可以帮你,只有我爹和我两个人互相帮衬,而我只要多出一分力,我爹就可以少出一分力。看着我爹弓起的腰和花白的头发,我好像懂了点什么,那一刻我似乎一下长大了十岁,身上也涌现出了无穷的力量。我跟我爹说,让我在前面驾辕拉车吧。我爹也累了,就把驾辕的位置交给我, 我双手用力压住车把,肩膀上套起绳子,拉起车子向前走,等到家的时候,我看到我爹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此刻站在山顶上,遥望着南方,我好像看到在千里之外的田野上,我爹正一个人在拉着车爬坡,他的腰弓着,他的腿绷着,汗水打湿了他身上的汗衫,那辆装得又高又满的车子摇摇晃晃着,似乎又要倾倒了。不知为什么,我的心突然刺疼了一下,我向远处看,又看到青色的麦浪在随风翻涌,一波一波的,像是要涌上山顶,涌上天空。
那天我去向辅导员小叶老师请假,说要回家割麦子的时候,她很吃惊。我是在小秦请假之后才想到要请假的,小秦是我们宿舍的同学,他的女朋友在另外一个城市读大学,小秦想去看看她,便去向小叶老师请假,去的时候他还是心怀忐忑的,没想到小叶老师听了他的理由,笑眯眯地就答应了。小叶老师是刚毕业留校的研究生,是我们班的辅导员,她人长得很漂亮,也很和气,夏天喜欢穿白色的长裙,是我们班很多人的偶像。我们班的男生喜欢她,女生也喜欢她,觉得她像一个邻家的小姐姐。我也很喜欢小叶老师,我觉得她很美,但是她的那种美是属于城市的美,也是来自知识的美,这让她有一种雅致的气质,跟我见到的来自民间的、朴素的美不一样,这对我来说很新奇,很有吸引力。
小秦回到宿舍,跟我们大声宣布他马上就要去看女朋友了,我们都很为他高兴,当然也敲了他一顿竹杠。小秦那天晚上请我们喝酒,他说小叶老师可开明了,她说,读大学最重要的一是学习,二是谈恋爱,要不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辜负了这么好的良辰美景,大学就算是白念了。就在那天晚上喝酒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小秦可以请假去看女朋友,我为什么不能请假回家割麦子呢?但是想是这么想,该怎么跟小叶老师请假,却让我颇为犹豫,我觉得像她这样在城市里长大的女孩,大概很难了解割麦子对一个乡下人的重要性,要怎么才能让她知道呢?我想了又想,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只能硬着头皮试试。
辅导员的办公室在楼梯的西侧,跟我们班的教室在同一座楼上,但不在同一层。那天上午课间休息时,我上楼去办公室找小叶老师请假。我敲门进去的时候,小叶老师正坐在办公桌前愣神,她面前摆放着一本打开的书,书架上和桌上还摆放着四五盆绿植,阳光照进来,洒落在那些花上,也洒落在她身上,亮闪闪,明晃晃的。窗外的广播上正在播放一首最新的日本流行歌曲《恋人よ》,那舒缓的旋律在整个校园飘荡着,很沧桑也很动人。小叶老师像是在想着什么事,我又喊了她一声,她似乎才回过神来。
她问我,有什么事呀?她的声音又细又慢,很好听。在小叶老师面前,我还是有一点紧张,匆忙说了自己要请假,以及请假的理由。没想到小叶老师听了,轻轻蹙起了眉头,好像不认识我似的,看了我几眼,才说,你要请几天假呢?请假的时间我早就想好了,回去一天,回来一天,再加上在家的时间,怎么也得五天,除去周末,那就是三天,于是说,我想请三天的假。她想了想,又不相信似的问,你真的是要请假回家割麦子?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好像为了割麦子回家,让她感觉很是不可思议。我低下头,不好意思地嗯了一声。小叶老师又问,你家里没有人割麦子么?站在她装了空调的办公室里,我身上的冷汗也冒了出来,我于是又支支吾吾地跟她解释,割麦子的活很累,我父母年龄大了,我姐姐家里也忙……我越说越急,在她面前很不好意思,同时我心里又涌上了懊恼,觉得似乎不该用自己的事来烦扰她,说着说着我就说乱了,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正在这时,上课铃响了,小叶老师听到愣了一下,对我说,别着急,你先去上课吧,下午你再来,我也考虑考虑。我冲她点点头,转身走出了她的办公室,一头都是汗。我走出来的时候,广播上的五轮真弓还在深情地唱着:
恋人よ さよなら
季节は巡ってくるけど
あの日の二人宵の流れ星
光っては消える 无情の梦よ
中午的时候下起了小雨,吃完饭回到宿舍,我想着下午还去不去,去了之后怎么说。小秦见我魂不守舍的样子,问我有什么苦恼。我跟他说了向小叶老师请假的事,小秦家是城市的,他听了我的话似乎感觉有点不可思议,奇怪地看着我说,你既然离开了家,就别总想家里的事了,你要是不想离开家,又为什么考大学呢?他的话好像很有道理,我一下竟然说不出话来。小秦打着伞走了出去,他的女朋友来看他,他要带她去游颐和园。我看到他走出男生楼,向女生楼走去,一会儿又从女生楼走了过来。他和他的女朋友,两个人手挽着手,合撑着一把伞,说说笑笑着向我走来,又在楼角那棵核桃树下拐了个弯,向学校门口走去。他们的身影是那么青春健康,那么自然美好!他们才是城市的主人,他们的青春才是青春,望着他们身影消失后的一片烟雨迷蒙,我不禁这样想。
我一个人坐在宿舍里,静静地看着窗外,想着小秦说的话,我的心里是矛盾的,我喜欢城市,但我的根却在乡村,我的情感与牵挂也都在乡村,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变成一个真正的城市人,而真正的城市人又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也有一些来自乡村的同学,他们来到大学后,模仿着城里人穿衣,模仿着城里人说话,甚至行为作派比城里人更像城里人,但却总是让人感觉是在模仿,让人看着很别扭,那我呢?我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已经越来越城市化了,离家乡的人越来越远了,我将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会变成一个让我爹娘陌生的人吗?我不知道,但在我心里,我却总想保持原来的自己,让自己跟家乡的联系更紧密一些,但是一些改变是难免的,甚至也是我愿意或主动追求的,或许这是一种两难的困境吧,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在我们宿舍窗外有一棵核桃树,雨滴敲打着宽大碧绿的叶子,发出细微清脆的声音,那些叶子微微颤动着,一直伸展到我们宿舍的窗前,也有雨点斜落在玻璃上,蜿蜒曲折地流淌着,画出些不规则的雨痕。听着窗外细密的雨声,我看到不少女生打着花花绿绿的雨伞,在校园的小路上走着,那些伞像花儿一样绽放在雨天里,一朵朵,是那么飘逸,那么迷人。
等下午我再去办公室时,小叶老师仍在看书。见我进来,小叶老师合上书站起来,她的白裙子飘着,来到我面前。她让我坐下,笑着对我说,你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我跟系主任张老师说了,他也说这么多年,我们的学生还没有请假回家割麦子的,我们商量了一下,考虑到你的家庭情况,还是准你的假,但是你要保证按时回来,别耽误太多课。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你要好好补习,别把课程落下了。我低下头倾听着,只看得到她的白色裙子飘拂着,只听得到她的声音是那么温和悦耳。她说完了,顿了一顿,又问我,你听明白了么?我赶紧站起来说,明白了,谢谢叶老师。小叶老师看了我一眼,说,好了,那你回去吧,路上注意安全。我向小叶老师告别,离开了她的办公室。
走出教学楼,回头看看,微微细雨中,我看到小叶老师站在窗口,正在向远处眺望着,她的白色裙子随风轻轻飘拂着,她细长的身影像一幅剪影,我看到她的脸上似乎有一种难言的忧伤。直到很久之后,我才知道小叶老师那时的心思并不在我身上,就在前不久,她接到了去美国留学的男友的一封信,信中谈到了分手,她正陷入在精神的痛苦与折磨之中。但是她忍住内心的伤痛,平静地帮我请了假,不过或许我请假的理由让她印象太深刻了,新学期开始之后,她主动帮我申请了学校的助学金,而在那年的圣诞晚会上,她和我们班的同学一起喝酒,才偶然谈起了她和男朋友分手的事,但这些都是后来的事了。
在那天晚上,我就坐上了从北京出发的火车,第二天凌晨到达H城,再从H城坐两个小时的汽车到了我们县。一路上火车穿过山川、大地、河流,无数个村庄在车窗前一晃而过,我看到华北平原上的麦子已经成熟了,大片大片的麦田纵横交错着,从我的眼前一直延伸到天边,那是多么巨大的一片金黄色的麦田,简直就像是一片麦子的海洋!风吹麦浪,吹来了一阵阵麦子的清香,那些麦浪在太阳的照耀下,泛着金黄色的光,一波一波向我汹涌过来。在这一刻,我感到自己置身于麦田的中心,我想到华北大地是多么辽阔、宽广、厚重,她承载了那么多苦难与悲伤却沉默不言,让麦子在她的怀抱中默默地生根,发芽,成长,成熟,滋养了平原上的人们。我感到自己终于回到了平原的怀抱,回到了麦田的怀抱,只有在麦田的怀抱中,我的心似乎才能安稳下来。我想起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他们承受了多么深重的苦难,但是他们却是那么坚韧而顽强,他们默默地耕耘着,默默地收获着,默默地生活着,就像大地上的麦子一样,一茬又一茬,生生不息。想到这里,我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车窗前,向远处眺望着。远处仍然是无边无际的麦浪,翻滚着,翻滚着。
经过漫长的跋涉,我终于到了我们县的汽车站。从车站出来,我到附近的同学家里借了一辆自行车,一路骑行到我们村。在路上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时候我爹和我娘可能会在地里,所以在路过我家那片田地的时候,我先拐了个弯,看看他们是否在这里,没想到他们果然在,我姐姐也在,没想到他们已经开始割麦子了。
坐在地头的那棵大槐树下,我爹、我娘和我姐姐见到我回来了,都很高兴,我爹的眉眼都带着笑意,他的头发有些谢顶了,又有汗,阳光照在那一块地方,亮亮的。他的牙好像又掉了一颗,一说话就漏风,嘴也瘪瘪着,像个老太太,但是见到我回来了,他的嘴角都带着笑。见到我最高兴的是那些孩子,那时他们才五六岁,八九岁,最大的不过十二三岁,从小我就带着他们玩,他们都很喜欢我。尤其是小花,她从小在我家里长大,跟我最亲了,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说起来我从寒假离开家,到现在快有半年了,一见到家里的人,心里也有种说不出的高兴和亲切。
在树荫下休息了一会儿,我爹说,咱们开始割吧,二小来了,咱们早割完早点回家吃饭,越等天越热。我说,爹你歇一会儿吧,我去割。说着我拿起他放在脚边的镰刀,跟我姐姐一起走进麦田里。刚走出树荫,迎面便扑来一阵热浪,我看到热风吹拂着麦地,地里的麦子随风高低起伏着,一浪一浪涌过来。我跟姐姐走到他们刚才割到的地方,弯下腰来跟他们一起割,我也像他们一样,右手握着镰刀,左手抓一把麦秆,用镰刀在麦秆底部一割,麦子就割下来了,接下来将麦子平放在地上,向前再跨一步,左手再去抓麦秆,右手再用镰刀割,再平放在地上,如此反复地重复这个动作。等割了几步,约莫割下的麦子差不多了,就将平放在地上的麦子收拢在一起,用一根草绳捆起来,这就形成了一个个麦个子。我们在割麦子的时候也要捆麦个子,以免太阳暴晒,平放在地上的麦子被晒得干裂,麦粒很容易脱落,捆成了麦个子,等回去时装车也方便,那时只要用一把钢叉挑起一个个麦个子,扔到车上就可以了。
在地里干了一会儿活,我身上的汗就涌了出来,腰弯得也酸了,握着镰刀的手也开始颤抖,我的动作渐渐慢下来,被我姐姐远远甩在了后面。我姐姐直起腰,擦了一把汗,笑着对我说:“怎么样,干得了吗?干不了就说一声,可别中了暑。”又说:“你跟我们割一样多,肯定赶不上我们,你少割几行吧,前面的我给你割了。”我也直起腰来,擦擦汗,解嘲似的说:“好长时间没干活了,干一点活就累的不行,没想到割麦子这么累!”我姐姐笑着说:“割麦子不累干啥累?以前你学习紧张,没怎么叫你割过,现在离得远了,想叫你割,也叫不着了。”我又擦了一把汗说,“我这不回来了嘛?”我姐姐又笑着说,“你能回来几天?家里也不盼着你回来,你在学校里好好学习,毕业找个好工作,不怕风吹雨淋的,比什么都强,再也不用头顶着大太阳割麦子了。”说了几句话,我们又弯下腰继续割,不一会儿我身上的T恤衫就被汗水湿透了,这件T恤是我在学校里买的,上面还印着我们学校的校徽,这个校徽也湿透了。我姐姐在前面割着,我割的是原先我爹割的部分,每人六行,我割得慢,我姐姐在前面替我割了三行,给我只留下三行,尽管如此,我仍然赶不上她。
天上的大太阳照着,那种酷热的炙烤让我喘不过气来,这时候还要重复着收割的动作,重复了一会儿,我的腰和手臂已经酸软得不行了,可是抬起头来看看,到地边还有很远的距离,我的心中郁闷而又绝望,甚至有点后悔自己回来了,如果不回来,这时候我或许正躺在宿舍的床上看书呢,微风习习吹来,太阳也照不到,看够了,和同学说说笑笑着去食堂吃饭,回来再睡个午觉,是多么惬意!但是如果我不回来,我家里的麦子就只有我爹和我姐姐割了,我爹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我姐姐呢,说起来我姐姐已是嫁出去的人了,她来帮我们家里干活,只是出于儿女之情,而不是必须的义务,我回来能帮她分担一点,心里也会好受一点。
我直起腰来看看,前面到地边,距离还很远,我姐姐在我前面大约两三丈的地方奋力向前收割着,我娘和那些孩子在地里捡着麦穗,我爹这时也走过来,他跟在我后面捆麦个子,这又减少了我的一个步骤,于是我又凭意志弯下腰继续向前割,热风扑面,麦秆上的麦芒偶尔会扎到我的手,又痛又痒,汗水一蛰,痛痒处就更难受了,但这时我也顾不了这么多了,硬着头皮向前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向前,向前,奋力向前!
割着割着,突然一不小心,我右手握着的镰刀在左边的小腿上划了一下,我啊地叫了一声,一下将镰刀抛到一边,扑通一声坐在地上,剧烈的疼痛让我紧紧抱住了左腿,我一看,小腿的胫骨处划破了一层皮,正有鲜血从伤口处流出来。我娘和我姐姐听到了我的叫声,连忙跑过来看,问我:“怎么了,怎么了?”我说:“没事,让镰刀划了一下。”我娘心疼地说:“没事吧?”这时我腿上的疼痛已减缓了一些,我说:“没事,没事。”我娘已经看到了,着急地说:“还流血了!”我姐姐察看了一下伤口,说:“没大事,划得不深,只是划破了一层皮,回去抹点紫药水就行了。”又说:“你别割麦子了,带着孩子们先回家吧。”我说:“不用,这么点小伤!现在不流血了,也不疼了,咱们一起割吧,割完再回家。”我娘和我姐姐又劝了我几句,我还是坚持不走。我娘从地上抓起了一把干土,撒在了我的伤口上,又从兜里掏出一条干净的手绢,系在我的小腿上包扎好,说:“一会儿就好了。”我想起了小时候我哪里受了伤的时候,我娘也经常在伤口上撒一点干土,她觉得土地是很神奇的,什么伤都能医治。果然撒上土之后,我的伤口就收缩了,也不疼了。
包扎好伤口,我抓起镰刀,又站在了麦子跟前。我弯下腰,瘸拐着一条腿,努力追赶着,前面我姐姐已经割到了地头,田野上只有我要收割的那三行麦子孤零零地在风中摇摆着。我姐姐直起腰来,擦了一把汗,又从地头那边开始迎着我向回割,那三行麦子的距离在慢慢缩小,不一会儿我姐姐就割到了我面前。剩下最后一把麦子,我一镰刀下去,从麦秆根部割断,左手将麦子抓起,艰难地直起腰来,大叫一声:“终于割完了!”
这时候,小花在地头的树荫下呼喊着我们:“快来吃冰糕,快来吃冰糕!”我跟我爹将最后一个麦个子捆好,便迈着踉踉跄跄的步子向地头走。我姐姐担心地问我:“你没事吧,腿还疼不疼?”我说:“没事了,早就不疼了。”我姐姐又问:“热不热,你没有中暑吧?”我笑着说,“没有,就是有点累,有点热!”
走到那棵大槐树的浓荫下,我一屁股坐在田埂上,脱下湿透的T恤衫,搭在车帮上,抓起水杯,咕咚咕咚灌下去一杯水,才慢慢缓过一点劲来。小花拎过来一塑料袋冰糕,让我挑,我随便抓了一个,撕开包装纸,咬了一口,那种冰凉带着甜意慢慢浸润着,一下让我清凉了下来。我爹、我娘和我姐姐也都坐在田埂上,开始吃冰糕,我爹不敢吃太凉的东西,只是拿冰糕贴在脸上,贴在额头,不时挪动着位置。那帮小孩吃着冰糕,也还是叽叽喳喳着,相互争抢着,有的要吃苹果味的,有的要吃橘子味的,吵闹个不停,也笑个不停。原来是我娘看我们太热了,就让小花和两个小孩到我们村小卖部去买冰糕,他们飞快地骑着自行车,一路尘土飞扬,一路欢声笑语,飞奔回我们村,买了冰糕,又飞奔到地里,一个个热得脸上都淌着汗。此刻坐在树荫下,吃着冰糕,他们才算安静下来了。我爹和我姐姐在商量着,麦子拉回去之后,什么时候打麦子,什么时候扬场。割麦子只是这些农活中的第一步,直到麦子脱粒晒干,颗粒归仓之后,直到平整土地,种上谷子之后,繁忙紧张的抢种抢收才算是结束了。听他们谈论着,我的心慢慢也安静下来了,像是触及到了生命中最安稳的部分,听着他们随意的闲谈,让我觉得很踏实。
凉风习习吹来,我站起来,走了几步,向远处眺望着,远处一大片麦田在太阳的照耀下闪着金光,风一吹,麦浪起伏波动着,一波一波向我涌来。站在树荫下,不知为什么,我的脑海里突然闪现出小叶老师飘动的白色裙角,但又感觉是那么遥远。就像那首歌,始终缭绕在我的脑际,却又是那么陌生:
我的恋人啊,再见了
季节总是循环轮回的
那天傍晚我们还在一起看流星
如今光影已经消失,像一场无情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