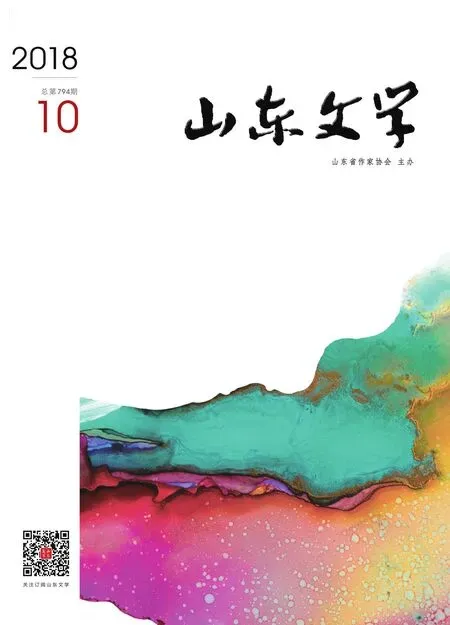邮筒街97号
王 威
这是我第三次遇见前女友了。
前两次我都是躲在邮筒后面,等她过去我再出来。可是这次邮筒离我很远,没有办法,我只能装作打电话的样子。却是我刚举起手机,前女友就堵在了我前面,挑衅地看着我说,假装打电话,有意思吗?
我讪讪地收起电话,左顾右盼想找个其他借口离开。可是除了那个离我十几米远的废弃邮筒,周围啥也没有,连棵树也没有。没有树的街道乏味无比。
我装作无所谓地说,你不在商场卖袜子,跑这干嘛?她的嘴角往上一挑,冷笑就蹬鼻子上脸了。我很熟悉她这个表情,一般伴随它的是激烈的控诉,控诉我是个废物,用复读机的方式。我觉得她今天不会那样做,因为我们从去年夏天就已分手,我再怎么废物也与她没有关系了。
果然,她只是嘴角往上挑着,冷冷看着我,并不说话。在她不屑的注视下,我的脊梁开始发热,虽然北风呼啸,天气寒冷,可是细汗还是从背上冒了出来。对于跟她的战争,不管是正面冲突还是背面冷战,我从没有赢过,看来今天也不会例外。我经受不住她这样看我,我情愿撒谎。我说,我从这里去汽修厂近便些。说完我自己也觉得不可信,因为我吃住就在汽修厂里,邮筒街离那里远着呢。一切由她去吧,反正我不想说出真实目的。
她从牙缝里挤出来一个“切”,然后冷笑说,你不就是想知道我来这里干什么吗?用不用我告诉你?
不用!我心里说。然后,落荒而逃。
跑到汽修厂,我的手冻僵了,很长时间钥匙插不进锁孔里。我把钥匙扔在旁边的废轮胎上,把手放在嘴边呵气,呵着呵着,我蹲在地上哭起来。我跟前女友从小在一个大院里长大的,那是煤场的家属院,我们两家的父母都在煤场里干,并且处得不错,偶尔我或她会端着盘饺子、咸菜啥的互相交换着吃。可我现在不想叫她的名字,那个名字在我心里是珍宝,我只想叫她前女友。虽然从小一起长大,可是我们并没有像书里写的那样青梅竹马。她家里很穷,那时都九十年代了,咋还那么穷呢?她为了要件新衣服,经常被她妈用接水的黑胶管子抽打,她也不躲,站在那里任凭黑胶管子啪啪地抽。我碰到的那次,黑胶管子正好抽到了她脸上,她鼻子里的血刷的流进了嘴巴,又从嘴巴流出来,看上去要死了一样。我撒丫子就跑,她却仰着头在我身后哈哈大笑,边笑边用带血的声音追击我,你丫的就一窝囊废!我能想象到她那鄙夷的眼神。直到现在,她还是用这种眼神看我。
我们恋爱后,她对我说,小时候她家里也不至于那么穷,是因为她妈太顾娘家了,他们的那点工资需要连姥姥一大家子养着,所以导致她天天穿哥哥的旧衣服旧鞋子,没脸出门见人。每当说到这些,她都后缀上一句:我们得好好挣钱啊,要不还得穿旧衣服旧鞋子。
蹲在我那个简陋的汽修厂门口,我哭的时间不长,因为很快就哭不出眼泪来了;加上天寒地冻,蹲着受不住,我就又站起来开锁。这次卷帘门很容易就松开了。我租赁这间沿街房开汽修厂,还是她的主意。那时,我们俩从职高毕业,在鞋厂干了两年,鞋厂倒闭了,她说,你在职高学的汽修,为什么不开汽修厂?我开始并没有被她这个建议打动,因为我不愿意冒险自己做生意。可是经不住她天天说,夜夜念,我只好跟在她后面看房子,置办设备……我不想回忆那段日子,那段日子太辛苦了,天天求爷爷告奶奶的,一言难尽。
其实,这算不上个汽修厂,就是一间沿街房,里面有几台修车的小设备而已。开业时我说还是叫“洗车”吧,她斜眼瞅我,我怕她再骂我“没有凌云壮志”,赶紧闭了嘴。不只叫修车厂,在她的指挥下,我们还从家里搬了出来。她说要是不搬出来,我们挣的钱就让她妈全抠去了,她可不愿意像她妈那样过一辈子。
我从屋里拿出一个马扎,坐在门口晒太阳。已经连续一个礼拜没有车开进来了,自从我们分手后,本就惨淡的生意更没有了模样。
我们为什么分手?我经常想这个问题,起因看似是为买烤地瓜。那天很热,肚子里像烧火,吃冰块都觉得不能解热。我坐在门口看蚂蚁搬家,她拿着一个热气腾腾的烤地瓜,满头大汗地走了进来。我抬头看了她一眼,我那一眼并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觉得天这么热竟然还有人卖烤地瓜。可她非说我那一眼很恶毒,是在谴责她买烤地瓜吃,乱花钱。听她复读机一样数落我,从上年她买纱巾上上年她买裙子我也是这么看她,一直数落到过年时她妈来要钱,我也是这么看她妈,最后总结出我挣不来钱,就知道从她身上省,她跟着我快要苦死了。我依旧没有争辩,认真地看蚂蚁搬家。她把一壶开水浇在了那些疲于奔命的蚂蚁上,看着飘荡在沸水上面无辜的黑色尸体,我看着她说,我们分手吧。她说,好。于是,她放下烤地瓜就去布帘子后面收拾衣服。不到半个小时,她走了。我觉得很放松,没有一点悲伤。她走以后,布帘子后面的小床更冷了,夏天也冷,像是被她下了诅咒。
我倚在门口被太阳晒得快要睡着了。老邱在旁边咳嗽,见我睁开眼,神秘地说,去看了?我又闭上了眼睛。老邱骂了我一句闷X,走了。
老邱是隔壁宠物药店的兽医,上个周末,他来买机油,买好以后也不走,老在我跟前磨蹭,明显一副有话要说的样子,但我没跟他搭腔。我不是单单不喜欢跟老邱说话,我是不喜欢跟任何人说话;我喜欢把话放在肚子里,自己跟自己说,说错了我也不会像复读机一样骂自己,很省心。老邱见我没有问他的意思,只好主动凑我耳边,我看到你前女友了,神秘兮兮的。我偏了偏头,他嘴里热乎乎的大蒜味直冲脑门,让人接受不了。他没有在意我的情绪,而是贼头贼脑地往门外看了看,仿佛在泄露国家机密,你知道老朱吧?我脑海里先飘荡出一个后脑勺有刀疤的脑袋,然后是上身长下身短,加起来不到一米六的肥胖背影,这个背影转过来,就是大得惊人的鼻孔,说话前这两个大得惊人的鼻孔总是先忽闪两下,然后肥胖的脸上浮现出面里面气的笑。他是南方人,在这条街的最南端开了一家红茶店,据说因为强奸罪坐过牢,在牢里吃了很多苦,包括……
我一震,眼睛直盯着老邱。老邱可能明白了我看他的意思,满意地笑了。我说,他不是,那玩意不行吗?我现在怀疑老邱在刺激我,我前女友虽然人强势,喜欢钱,可是不至于去跟老朱干那码子事。老邱笑得很奸邪,很猥琐,他有他的办法呀。说完竟然立起身,走了。
我开始呕吐,蹲在门口的下水道前,吐了很长时间,吐出的全是很苦的绿水。我打算再找老邱谈谈。
那天晚饭后,我去了老邱的宠物药店,我想探寻个究竟。可老邱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你自己去看看不就得了。去哪儿看?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有破釜沉舟的悲壮。老邱却仍是轻描淡写,邮筒街97号呗。
老邱不提邮筒街,我都快忘记小时候那些梦想了。上初中时我会时不时跑去这条街,偷偷摸摸往那个邮筒里扔几封给杂志社的投稿,所以那个邮筒就是我少年时文学梦的入口,我经常去抚摸它,期待着远方来信。那个时候,这条街上就没有树,据说是因为土质的原因,栽啥死啥。现在老邮政局搬走了,街上更加冷清了,除了那个已经废弃的邮筒,就剩下一两家油腻的小店铺了。
于是,从这周开始,我就在邮筒街挨着门头找97号。我怀疑老邱在玩我,因为这条街不长,几天来,我都是找到96号就没有了下文。我问过96号的主人,那是一家布店。布店店主嬉笑着对我说,我都不知道我的店是几号,哪知道97号?您看好哪块布料了?我只能再走街串巷,直到一无所获。
就在我昏昏欲睡的时候,有人拍我的肩膀。我以为老邱又回来了。睁开眼睛,却打了一个激灵,是老朱的大鼻孔在我眼前忽闪忽闪,像一条狗在嗅来嗅去。看到我醒了,他笑嘻嘻地说,刘经理。整条街,或者说整个世界,也就只有他会称呼我刘经理。我盯着他没有吭声。他说,刘经理,我的车得保养了,送你这儿来成吗?这时隔壁宠物药店的门无声无息地开了,老邱站在玻璃门后,朝这儿看;然后是老邱隔壁的店铺门也开了,朝这儿看;再后,整条街的店铺门都开了,都朝这儿看。我瞧了瞧站着跟我坐着差不多高的老朱,说,我会一直找下去的!老朱说,我明天把车送过来成吗?我点点头。老朱笑了,仿佛他取胜了一般。
第二天,老朱让店员把车开了过来,那是辆最新款宝马7系。店员四下打量着我的汽修厂,不放心地说,好好保养啊,用最好的机油,搞坏了你可赔不起。我说,你们老板怎么不去4S店保养?店员说,他有病呗。我说,你知道邮筒街97号吗?店员警惕地说,你问这个干嘛?赶紧干活,我下午来取车!说完,匆匆离开了。
一上午,我竭尽全力地保养那辆宝马7系,跟伺候我爸没两样。昨晚躺在床上我还想,他要敢把车开进来,我就给他大卸八块。可是今天真的见到车了,我反而心生不舍,这么漂亮的车子,像前女友刚跟我谈恋爱时一样美。
那时我们刚去鞋厂打工,看到周围工友们都成双结对,有一天上班的路上,她跟我说,闷子,我们谈恋爱耍吧。我说好啊。从小到大,我已经习惯她说啥我同意啥了。她麻利地跳下自行车说,那你敢在大街上抱抱我吗?我踩着自行车加快速度逃离了她。她在后面骑车追我,边追边骂我怂货、窝囊废、没出息。直到进了厂里的车棚,她还是不放过我,堵住我说,谈恋爱就得拥抱。周围放车子的人也跟着起哄,她愈发得意起来。我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不知道该怎么结束这场闹剧,最后是她上前踮起脚亲了我的脸颊一下。阳光透过破败的石棉瓦照在她的脸上,她长长的睫毛微微颤抖,有一股说不出的美丽和哀伤。不知道哪来的力量,我一把抱住了她,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大胆举动。我们在破瓦颓垣的车棚里,确定了恋爱关系。
老邱背着手站在门口看我忙碌,忽然说,看来你们两口子都傍上老朱啦。我感觉心脏被“刺溜”插进了一把刀,所有的血都涌向了脑门,当下拔刀的最好方式就是武力。我拎着扳手从车边一下就窜到了门口。恐怕老邱做梦也没想到,我敢把扳手抡到他的额头上,可是真真实实地毫不含糊地抡过去了,“啪”的一下,他的额头就盛开了一朵鲜艳的 “红花”。他捂住流动的“红花”,蒙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说,好好好,你这个蔫X、闷X!你敢打我,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我把口袋里的电话送到他脸前说,你打110,把我抓进去。他又惊又恨地看着我,转身跑了。
我扔下扳手开始换衣服,我要去商场找前女友谈谈。我不去找那个什么邮筒街97号了,它是老朱给她买的豪宅也好,给她开的店铺也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听她怎么说。
我在商场楼下的米粉店找到了前女友,她正在跟同事一起吃米粉。我见桌子的牌上写着:“吃一碗送一碗,就是这么任性。”她不在乎地说,合伙吃便宜。同事走了,她碗里还有多半碗。她把碗推到我跟前说,吃了它,我吃饱了。我没有拒绝,呼哧呼哧很快吃了个干干净净。我们小时候经常这样吃同一碗饭,有时她在院门口边吃东西边玩游戏,看到我,就会把吃剩的塞我口里,自己继续玩,也不管我吃得下吃不下。她看到碗里汤水没剩,问,你几天没吃饭了?我说,家里最近又问你要钱了?她把嘴撇了撇说,我已经跟他们断绝关系了,我妈拿自己当例子教育我要顾娘家,我才不吃她那套呢。我又问,你遇见什么难事缺钱吗?我从没这样耐心过,我想把邮筒街97号这样一点点剥出来。她朝我笑了,就像一朵花在我眼前慢慢绽放,明媚灿烂。自从跟我在一起后,她从没这样笑过,我晃了晃头。这朵明媚的花声音居然很冷,她说,我不缺钱了,我的好日子开始了。我打算把心里积压的那些话都说出来,在这个充满番茄味道的米粉馆。却是还没等我开口,她朝我摆摆手说,我的事你少管,邮筒街以后也不要去了。我说为什么?你在那里干嘛了?她很无辜的样子说,我这不在这里好好地上班吗?一个月挣我的1700块!我想问她老朱是怎么回事,可是面对这样明媚的笑容,我实在不忍心用“老朱”来糟蹋了。我站起来走了。
老朱的店员在修车厂门口等我,见我回来,满脸不高兴地说,车子保养好了吗?我说你明天来开吧。他很愤怒,想不到我居然敢违背约定,我没有理会他,拉开卷帘门进去了。
车子保养完,我开始洗车,用吸尘器吸车内的灰尘,如果这一切顺利的话,晚饭时我就能完成这单生意。可事实是直到半夜,我也没有完成。因为我从车内的脚垫下面发现了很多男式袜子,颜色鲜红,全都是分趾的。记得我以前去找她,看到过这种袜子,她说,这种脚趾头分开的袜子一般都是有脚气的人买去了,由于贵,她得的提成也会多。脚垫下面的这些袜子全都一个尺码,足足有二十双,铺在那里,就像流淌了一车子的血。我疯狂地在车里找买袜子时的小票,我认得她写的字,可是找遍了角角落落,甚至连空调都被我卸下来检查了,却没有找到一丝与袜子有关的痕迹。我仿佛看到老朱在朝我笑,这一次的笑里没有面里面气,只有猫玩老鼠的洋洋得意和不可一世。我把拳头攥得嘎巴嘎巴响,王八蛋!王八蛋!我瘫倒在副驾驶的座椅上喘粗气。我下定了决心,挖地三尺也要找到邮筒街97号。
第二天,是老朱亲自来开的车,他面里面气地说,刘经理,谢谢你哦。我口袋里的那只手快要把手机捏碎了,如果它是老朱就好了。老朱掏出一叠钱拍在桌子上,做出一副转身要走的样子。我让他等着,我把钱数了一遍。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数钱,直到我把多余的两张扔给他,他才松了一口气。看来刘经理不贪小便宜哦!他一边说着,把钱小心地放进了钱包里。我说,你说,谁贪小便宜?我掐腰站着等他回答。王八蛋不愧是老手,只是愣怔了那么半分钟,然后说,还能有谁,其实咱们心里都有数呢。大概看到我变了脸色,他又补上了一句,整条街上谁不贪啊?我说滚!
老邱头上贴着纱布,理直气壮地堵在我们跟前问,你们谁出医药费?老朱很好笑地说,邱经理,我出的什么医药费呀?老邱说,都是因为你我才挨了这一下!老朱转头对我说,我说什么来着?你看看贪不贪?老邱质问,谁贪了?你说谁贪了?你开着这么贵的车,拿出点钱来又怎么了?老朱一头钻进车里,车门落锁比老邱抢开车门快了一秒钟。老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宝马扬长而去。我说,老邱,你告诉我邮筒街97号在哪里,我给你出医药费并且道歉。老邱大笑起来,笑声很洪亮很开心,他说,两码事,我也不指望你这个穷鬼能拿出医药费来,我就指望这个笑话活着呢。说完,他和门口几个看热闹的人摇摇晃晃地走了。
我把屋子里所有站着的东西都打趴下了。走到门口回头一看,墙角还有一瓶防冻液站在那里,我冲过去一脚把它踢滚蛋了。关门上锁,我发誓今天要踏遍邮筒街。天下雪了,密密的雪花撕撕扯扯从空中飘落。小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雪的作文寄出去,那是我收到的唯一一封编辑手写的退稿信,这封信被班里的男生们嘲笑了好久。那一阵,放学路上他们天天跟在我身后怪声怪气地背诵信的开头:“亲爱的刘水果同学,你的作文我们读了,立意很好……”然后再一起哄笑。有一天,也这样飘着大雪,那封信被他们抢去了,他们当着我的面把信撕得粉碎。看着混进雪花里四下纷扬的碎纸屑,我疯了一般跟他们扭打在一起,她也勇敢地跟我并肩作战。然而其后果可想而知,我俩被他们打得鼻青眼肿。坐在雪地里,我寻找那封信的碎屑,边捡边哭,她用雪把脸上的血胡乱擦了几下,把我捡在手里的碎纸屑打掉,拽起我往煤场大院走去。
我缩起脖子,把手拢在袖子里,尽量让自己缩成一团以减少热量的付出。走了没有几步,我听到身后有人喊我,果果!很少有人这么喊我,除非是我爸妈和住在煤场大院里的老人们。我转过身子,果然,是前女友的妈。她从出租车上下来,跑着追我,脖子上的围巾被风吹跑了。
我想带她去这条街的一个小吃部,里面生着炉子,很暖和。可她不去,她抓住我的胳膊说,果果,你见过那个死女子吗?刚才我去商场找她她不在,电话不接!这多半年她一分钱也没往回拿,你说,她咋就这么狠的心啊!我说,她不是跟你断绝关系了吗?前女友的妈开始放泼,为我这句话。她呼天喊地骂我和她都没有人性,还说要去告我们。我没有道歉,我感觉活着他妈的就是遭罪,天这么冷,还得站在这里挨骂。最后,她扭着我胸前的衣服说,你跟她说,让她回家收尸,就说她爸她妈买不起煤烧冻死了!当初我咋就生了这么个玩意!她说完,松开手走了。我看见她好几次差点滑倒。
她却在大雪中挣扎着,越走越远。
我往邮筒街走的路上,给前女友打过去了电话,我没有说她妈过来找她,而是让她搬回汽修厂住。她停顿了一会儿,忽然笑起来,仿佛我这个建议很好笑。我想等着她笑完,可是她的笑竟没完没了,里面还夹杂着汽车喇叭声和音乐声。她现在应该在商场上班,怎么会有这些杂音呢?我问她,在哪里?她说,上班挣钱啊。我挂断电话就往邮筒街跑。跑的过程中我碰翻了一家理发店门口的雪人,两个黄头发的男孩出来挡住我,要五十块钱的雪人残疾费,我把口袋里零的整的票子全部掏出来,扔在了那个残破的雪人上。我只一路奔跑,奔跑,朝着邮筒街。
可是,除了白茫茫的大雪,邮筒街上什么也没有,就连那个老邮筒都无了踪影。我绝望地四下张望,忽然想起了老朱的车。我在邮筒街找老朱的宝马,我相信,找到老朱的宝马,就能找到前女友,我要把她带回汽修厂。然而我从这头找到那头,寻了这边寻那边,根本找不到老朱的宝马。倒是在一个角落里终于看见了那个斑驳的老邮筒,我用袖子把上面的冰雪一下一下擦拭干净,然后,一个门一个门地进去问,见没见过一辆香槟色的宝马车。却是态度好的对我摇头,态度蛮的要把我送派出所,他们质疑我是个贼。我不管这些,只要能找到前女友,骂我什么我都不在乎。我开始扒拉掉门牌上的雪看上面的号码,从1开始,一个一个地看,看到96,再也没有了任何建筑。嘴里呵出的热气把头发冻硬,一根根白茫茫地直竖着。太阳西移,我的肚子已经饿得贴到脊梁上,这才记起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
进了一个小馆子,我跟老板说,我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我用身份证抵押在这里,给我碗面吃吧。老板倒是爽快,他说,尽管吃,过后送钱来就行。我一连吃了三碗,身上才逐渐暖和过来,头发上的冰凌也渐渐化成了水,滴在棉袄上。老板说,现在你脸上有点人样子了。见老板说话和顺,就问,您知道,邮筒街97号在哪里?没想到,刚才和颜悦色的老板突然狂笑起来,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仿佛我说了一个很好笑的笑话。他擦着笑出的泪水说,你说你,饭都吃不饱了,还有心思打听97号。说完,又笑,盘在炉子旁打盹的黄狗被他笑得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走了。
老板的笑是被老板娘呵斥住的。老板娘说,闭上你的鸟嘴!你就是个好东西?要不是我拦得紧,你也早去了!老板的脸色变青了,他上前拖住我的一条胳膊说,兄弟,出去,出去哥告诉你!谁料还没到门口,老板就被老板娘一脚踹趴下了。但老板没屈服,他从地上爬起来,不在乎地拍打了两下身上,又拉住了我,还是那句,兄弟,出去,出去哥告诉你!
我离开小馆子时,天已黄昏,雪依旧下得很大,纷纷扬扬,像我在邮筒街游走一样。我不大相信老板说的话,可是,我还是按他说的,朝街上那个斑驳的老邮筒走去。老板告诉我,那个邮筒就是这条街的97号。这是老朱专门取的名字,每天黄昏,他都会开车从那里过,看上顺眼的,就带走。我走着,听老板在后面喊,你可别押身份证给她们啊,其实也不贵,一次才一百。
透过迷离的风雪,我看到有个纤瘦的身影正倚着邮筒玩手机,手机屏幕上的光把她的脸耀得蓝荧荧的,我分辨不出她是前女友,还是另外哪一位。
我大步朝邮筒走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