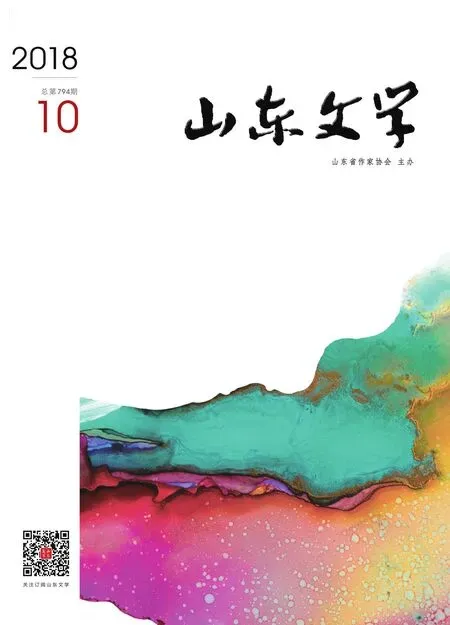凉夏(组诗)
魏友太
宁静
在雅姆的诗歌中
弥漫着强大的宁静
从法国山脉开始
一直浸到海滨城市
让汹涌的波涛安静下来
等待世界发声
世界沉默,喧嚣闭嘴
一切的杂音被调试到最小
小到听不到任何声音
只有心跳定期地敲打
提示生命正在悄悄行进
此时生命的脚步正踏在道路关键部位
每一双脚印像对好的暗号
逐一打开前面的门
又好像兆示秘密的音符
一脚踏下之后
一支宁静深邃的乐曲
在屋内屋外响起
等待
落下又升起的飞机
让乘客等待的心一次次落空
广播里延误飞行的善意
难以安抚盼望的焦灼
在机场的等候区
学习耐心的等待
用一杯茶水或咖啡
浇灭不现实的非分之想
把过程当成目的
把想像当成现实
把等待变成一种难得的享受
把书打开
把书中的故事打开
那远方的诗意渐次来临
裹挟着修饰完好的人物
当阅读中的我们打成一片
让我们感受到生活中的美好
没有远离就在我们身边
在我们的每次举手投足之中
机场变成巨大的剧场
不是我们在等待什么
而是飞机作为观众
等待我们随时的精彩演出
变化
在重庆磁器口
徐记杂货店柜台边
没有听到店员亲切的问候声
身穿七十年前的长袍马褂人
只是一个演员
勾引起人们对那个时代的回忆
没有人前来送达信息
没有人发出接头暗号
放心地走进走出
不会有卜志高出卖我们的年份
况且负责盯梢的警察
已在麻将桌前睡觉
对门的五行道观
消失了读经声
代替的是茶馆的工作人员
在门前好客的语调
即使语气充满着广告的味道
掩饰不了那份热情和善意
沿街是市场经济的繁荣气象
此起彼伏的叫卖声
比当年的枪声还要密集浓烈
那些高官或英烈的后人们
忘记了前辈的咬牙切齿的仇恨
或在一起制作重庆酸辣粉
或在一起搬运陈良银麻花
或把生命中的酸咸苦辣糅合进各种食品
被销往全国的四面八方
变化还表现在洪崖洞、渣宰洞
中美合作所
苦难记忆被打扮成观光地
血雨腥风旋即刮成和风细雨
让外地人更加理解
重庆人热爱生活的原因
海边
习惯在海边居住
就不愿躲在山后面
巨大的岩石和被雨水冲刷的泥土
常常堵塞呼吸通道
石沉大海的消化能力
让海边的空气温度适宜
海水像一台庞大的空调
让冬天的温度升高
让夏天的气温降低
调试心理的感受恰到好处
在海边容易与诗人接近
感受雅姆的宁静
学写关于大海的诗歌
平静的海岸线,抚平汹涌的波涛
在海边居住久了
大海成为永远的居所
即使无人理解你
海浪却能听懂你的心
安静
安静在你的里面
将心中的挂念弃掉
如同将苹果腐蚀的部分去掉
只留下干净的那一块
安静在你的里面
听到楼上楼下的声响
脚步声、说话声、电钻声
没有一点恐惧
响起消失,消失响起
像心中的一首曲子此起彼伏
而曲子的声音也是轻微
轻微得只听到你的呼吸
安静在你的心里
就像婴儿安伏在母腹
巨大的温暖紧紧地托住
这即将来临的啼哭
安静在你的里面
就像流浪多年的孩子
回到家里那伏肩的痛哭流涕
父亲的手掌
在儿子背上的安抚
安静在你的里面
就像粮食储藏于粮仓
等待着播种和分享
就像一粒子弹从枪膛里取出
成为艺术品供人观赏
就像一只水笼头刚刚打开
肚腹中涌出活水的江河
顺服
行走前的每一步
都谨慎得让脚下渗出水来
都安静得让耳朵听到心脏的跳动
听到那一位的轻轻诉说行走时的每一步
都是按照说话者的嘱咐
都是让脚印成为说话语句的逗号或句号
行走后的每一步
都是说话者话语的应验
走过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
长满了那一位的荣耀
行走的脚步
不是跟着脚掌运动
而是顺服内心的声音
顺服说话者在心室中的密谈
低下
低下头颅
几乎要埋在打开的书页中
书中的文字
文字描绘的人物
人物所做的事情
深深地将目光吸引
低下头颅
不仅仅是一种物理运动
更是一种心理活动或人生态度
是对肉身的轻看
是对灵魂的重视
书中描写的不是神话故事
而是真实的经历
关于救赎、舍己
关于复活、重生
让内心充满感动和敬意
低下头颅
就是放下自我的架子
垂下骄傲的双手
顺服在强大的气场中
让庄重、肃穆、平安、喜乐
从内而外,散发在房屋中
大地上
让低下的头颅
成为仰望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