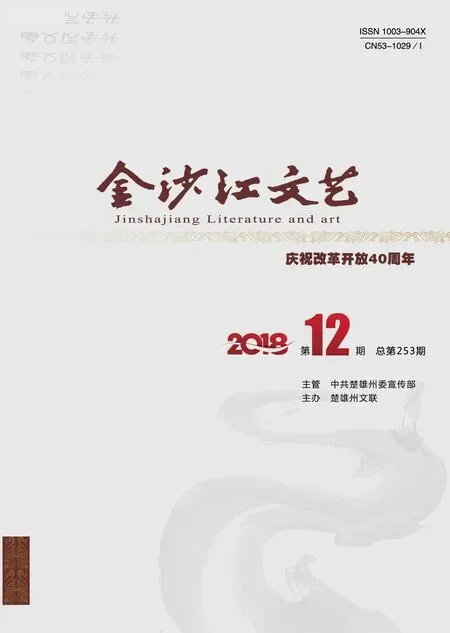村落的葬礼
袁智中 (佤族)
一
晚饭刚过,传来了拱弄大寨坡头五组桑木倒去逝的消息。本以为,在这样一个只有240多户人家的村落,一个人的死亡会闹出很大的响动,但我所处的四周却安静如初。星罗密布的建筑,层层叠叠的群山,空荡高远的天空,将人间凡尘的喧闹遮蔽得严严实实,稍不留意便无影无踪。
我到达的时候,桑木倒的棺材已经停放在木楼门前先祖的神龛前。祭祀先祖、家魂的仪式已经结束,主祭司、副祭司和老人们正散坐在棺材前,整栋木楼上上下下满满的都是人。桑木倒年迈的双亲正木然坐在火塘前,精神上的疾病和老年智障为他们筑起了对抗现实的阀门,以空茫的双眼望着眼前熙攘的人群,像一对未成年的智障孩童,既无欢喜,也无哀愁。桑木倒的妻子则在这样的喧闹中陷入极度的悲伤,一边哭着唱着,一边一次又一次重复着丈夫临终前的每一句话,情绪随着悲伤的哭调上下起伏。
悲伤的女人用哭调诉说着自己的不幸、孤单、无助和对未来的恐惧。30年前,为了这个不幸早逝的男人,悲伤的女人只身从邻村班列嫁到了拱弄,连续为他生育了一个女儿、两个儿子。眼看着女儿出嫁、儿子长大,以为生命的阳光就会照进未来的生活。却不想,几年前,除了患有精神疾病的婆婆、罹患老年痴呆症的公公外,家里又平添了一个因恋爱挫败引发精神错乱的小儿子,没有婚配的大儿子要么云游在去往打工的城市,要么沉迷于酒精的迷醉之中。整个家庭的重担落在了已年近五旬的夫妻俩身上。生活是悲苦的,无望的,但有着丈夫的担当,女人终究还是能够在与丈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中,获得一丝丝慰藉。
女人对于苦难没有抗拒的承受,反而助长着苦难成倍的增长。三个月前,她生命中唯一可以依靠的男人——桑木倒,被查出患上肝腹水,且已是晚期!这是一个多好的男人啊,不抽烟、不酗酒,总是默默地将生命中的全部力量投入劳动生产,与妻子携手支撑着这个苦难家庭。
作为一栋房子的大梁,作为一家之主,桑木倒知道,选择住院治疗,会将这个不堪一击的家庭拖入绝境。不用说因住院治疗平添的各种费用,仅仅是陪护住院一项就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一个姐姐远嫁山东、两个妹妹远嫁安徽,作为父母唯一的儿子,他没能从父母那里承续到更多可支配的亲戚人脉资源,两个儿子又指望不上,唯一能够依靠的妻子,则要替代他服侍两个年迈的老人和担负起整个家庭的责任。
因此,当他的四肢在肝腹水的压迫下日益肿胀无力,仍旧独自默默地承受着;当他接过命运无情的宣判时,仍旧默不作声地将诊断书装进随身的挎包,要求儿子将自己送回家,他要在家人的陪伴下等待死神的召唤。苦难了一生,他不想死在陌生的城市、死在离家这么远的地方,让阴魂落魄成一个孤魂野鬼,连寨子的大门和家的木楼都不能够靠近。
二
驻村的时间越长,看到这样的家庭悲剧就越多。入驻村落的第一个早晨,就在村委会遇见了一个儿子罹患脑瘤和脑积水的父亲。
这位父亲说,一切来得都是那样的突然。儿子所在小学刚进入期末考复习阶段,儿子便突然出现了头痛、呕吐和昏昏嗜睡的症状,到县医院检查说是患了脑瘤和脑积水。为了挽救心爱儿子的生命,这位从未去过城市的父亲,在医院120急救车的护送下,立即转到省城医院就医。从那一天起,他们一家的生活就陷入了永久的黑夜,但是,仍旧希望着现代医疗带来的奇迹。
说这话时,这位父亲黑暗着脸,空腹喝下大量的白酒,眼睛在酒精的作用下泛着晶莹的泪光。
支书告诉我,他是五组的组长田艾砍。这次带儿子去省城就医,前后总共花费了12万多元,就是按医保和大病医疗救助政策报销8万多元后,家里还必须负担近4万元的开销。支书深深叹了一口气后接着说,这对于农村,对于拱弄村人来讲,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我第一次到田艾砍家探视时,他的儿子正坐在阳台上一个垫满被褥的靠背椅子上,目光呆滞,脸色惨白而空洞,瘦得只剩下一个骨架。生命的活力,全部凝结在手中那部放着流行音乐的手机上。田艾砍在向我讲述儿子的病情时,妻子只是沉默着,用手和空洞无助的双眼一遍一遍抚摸着儿子。田艾砍说,这趟省城就医,并没有给儿子的病情带来什么好转。医生说,手术只能延长儿子的生命,并不能让儿子生命重新焕发生机。但他们一家还是希望通过再一次手术,让儿子多留在他们身边一段时日。田艾砍说,只要报销的医疗费一到账,他就要和妻子一起送儿子到省城再次手术,抽出积压在儿子脑子里的积水。
我第二次到田艾砍家探视时,他的儿子已经不能够坐在阳台上,只是睁着两只空洞的眼睛,静静地躺在火塘边的竹笆床上,连心爱的手机都握不住了。母亲匍匐在枕边,将手机举在儿子的耳旁,希望儿子喜欢的流行音乐能够给儿子的生命带去一丝慰藉。我跪在床前,用手抚摸着他瘦弱无力的手臂和手掌,望着这双神似母亲的眼睛、嘴巴和脸。当我的手再次滑落在他的手掌时,这个一直面无表情、空洞着双眼睛的男孩,突然间抓住我握着他的手掌,将曾经通过流行音乐传递的对生的渴望,以电流般的速度一股脑地传递给我。他是多么地想要活下去,像村落的大多数男孩一样,在村里读完小学,到勐来读初中,到县城读高中,然后到那些传说中的城市打工挣钱。但当他生活的梦想还未全部展开的时候,却戛然而止,让他以这样的方式一步步走向生命的终点。
还没等到第二次省城就医和我的第三次探视,这个一直面无表情、空洞着双眼的男孩便离开了人世。
手腕上,男孩身体的余温还未全部散去,又听闻八组76岁的魏尼胆罹患尿毒症的消息。四年来,老人靠着每周一次 (后来是每周三次)到县城医院透析维护着生命。家里虽然时常得到在外工作的孙子资助,但每周三次透析、四年多的治疗陪护,仍让魏尼胆一家不堪重负,整个家庭陷入了赤贫。
三
或许是看了太多相同命运的人,桑木倒在得知罹患肝腹水晚期的时候,决然选择不再治疗。终究都是要死,他不想因为治病给这个本来就灾难沉重的家庭陷入更深的黑暗。
桑木倒的妻子一边抽泣着,一边一遍又一遍复述着丈夫死前说过的每一句话,每哭诉一句,身子就因为强烈抽泣而上下抽动一次。桑木倒年迈的双亲仍木然坐着,望着上上下下往来的人群。老人们散坐在棺材的四周为桑木倒做着临行前的准备。祭司的祷告仍在时断时续,时起时落:
谁也挡不住落山的日月啊!
谁也唱不完葫芦的歌。
江河虽然已经干枯,
葫芦之歌却从未间断。
自从人们告别司岗,
我们时时送走同胞。
莫哀伤啊!
葫芦里还有欢乐的歌。
没有不落毛的斑鸠,
没有不完结的人生。
什么鸟都会落毛,
什么人都会死亡。
水不流就会淹没田庄,
人不死就会住满山岗。
……
见我盯着神龛前那口没有上漆、还泛着木头鲜活本色的棺材,老人们说,虽然是做外公的人了,但父母还健在,葬礼仍旧只能从简。因为,在他们看来,葬礼的任何铺张都是对老人的一种伤害。但毕竟是有儿有女、且已是有了外孙的人,老人们还是决定破除父母健在不用棺木入殓的传统,破例为桑木倒做了一口棺材,让他体体面面去往阴界。
但就是这样,因为姐姐远嫁山东、两个妹妹远嫁安徽,无法按照佤族礼俗,在家祖的神龛前杀一只公鸡、在他棺材的祭台前放上一套衣服或是一个亲手织的被单;因为没有同胞兄弟,两个儿子也未成婚,除了本家祭祀的一头小伢猪(骟过的猪)外,木楼的房柱前没有再杀倒过一头猪,家祖的神龛前没再祭献过一头猪的肉;因为家族人脉不够宽广,家祖神龛旁的供品也没有其他人家的丰富。辛苦了一生的桑木倒,只能够枕着妻子亲手为他编织的麻线被单和女儿祭献的衣服、被单,孤单去往阴界的路。如果不是他一意孤行,死在了县城的医院,那么,孤苦了一生的他,连这样简洁的葬礼都享受不到。
四
坐在繁忙的人群和往来的人流中,我一边注视着家祖神龛前琳琅满目的祭品,一边想像着死者生前的生活。从木楼的格局和眼前的家庭布局观察,桑木倒一家的生活极度贫困,遇上这样突如其来的绝症,等死或许是最为理性的选择。
天已经黑尽,木楼里仍旧是人来人往。只要有人提着烟、酒、糖、茶走进木楼,和着一块生白布、一双蜡烛、一元的纸币一起,摊开放在棺材前的祭坛前,祭司的祷告就会一次又一次在人群中响起。
老人们说,这是祭司在代前来献祭的乡亲,请求亡魂帮忙将这些祭品带转给他们阴间的亲人。据说,一次村落葬礼上,一户人家因没有请死者带转给在阴间亲人礼物,家祖先魂每日都到梦中来寻问,弄得家人无法安身,因为阴魂的缠绕,家里的人和牲畜也是接二连三地生病。
因着这样的传说,村落葬礼上,死者的棺材前和家祖的神龛旁,总是堆满琳琅满目的饮料、烟酒和糖茶。直系亲属越多,祭祀的鸡猪就越多,陪葬的衣物和生活用品就越丰富;村落人缘越好,家族越庞大,亡魂前的供品就越多、越丰富。据说,去年村落一位老人去逝,七个子女和至亲祭献的鸡猪就多达十多只和十多头,饮料、烟酒、糖茶更是堆积如山。
五
因为第二天村落一户人家进新房,死者必须于当晚安葬。桑木倒的葬礼只能连夜进行。
晚上11点,在桑木倒妻子悲切的哭声中,院落里,用于祭献亡魂的大母猪开始在凄厉叫声中走向祭坛。母猪被捆绑着,被一群年轻小伙奋力压在脚下,桑木倒女婿手握尖刀向着脖子狠狠地扎了下去。
这是一头名副其实的大肥母猪。因为多次孕育和生产,肚腩宽大厚实,肚皮上的两排奶子饱满而坚挺。据说,为了寻找这头祭祀亡魂的母猪,桑木倒的家人找遍了全村的每一个角落,最终于以2400元的高价买了回来。他们希望,以这样的慷慨为父亲铺平去往阴界的路。
猪血奔涌得很旺盛。灯光下,盆里的血泡汇聚成暗红色光亮如一朵朵绽放的花蕾。猪肝也是那样的宽大厚实,筋络也是那样的宽大白亮,胆汁也是那样的通透饱满,脾脏也是那样的光润顺滑。所有迹象都在向人们传递着一个欣喜的信息——桑木倒的亡魂接受了这头母猪的献祭,心甘情愿踏上去往西边的魂路。祭司摆上了篾桌、铺上了白布、摆上了香烟、点燃了蜡烛,将这一喜讯报告给了寨魂、家魂。
在祭司的祷告声中,桑木倒的父亲带着妻子、女儿和儿子依次向桑木倒的亡魂献食。他们一边哭述着逝者生前的故事,一边将副祭司切下的碎肉和米饭祭献在棺材跟前的篾盒里,与桑木倒做最后的告别。
直到丈夫的棺材被抬出木楼,沉入黑夜,哭声仍旧在黑夜里回荡。
六
我追随着火把、电筒的光亮,混迹于清一色的男人送葬队伍中。男人们举着火把、打着电筒、戴着顶灯,像一条火龙蜿蜒在夜色中。
连绵的雨季将亡魂西去的道路泡得潮湿酥软,阴森森的黑夜让这条西归的路变得漫长而艰辛,男人间时而喧哗、时而底沉的母语也变得阴森诡异起来。走过了许多的坑坎,爬过了许多的山坡,跨过了许多条溪流,走过了许多道木桥,队伍终于停留在一片荒坡的凹地前。
男人们将棺材缓缓放下,解开绳索,奋力将棺材推进早挖好的墓坑。随着人口的增长,墓坑与墓坑之间距离变得越来越近。所幸的是,经过十数年或数十年的自然腐化之后,旧的墓坑又可以成为新的墓地,以便让后亡之人能够前赴后继奔赴这里,与其他阴魂一起聚集于此,以另外一种方式团圆。
距离墓坑不远的地方,燃起了熊熊的篝火。每当小伙子们将桑木倒妻儿为他编织的被单、衣服、鞋帽和其他陪葬的生活用品扔进烈火中时,都会腾起高高的火焰,照亮刚刚隆起的土墓。桑木倒的大儿子头顶着照明灯,跪在父亲的坟前,一遍一遍梳理着坟头的树根和杂草,直到坟头的泥土堆成尖尖的完美的长方体。然后,再用竹笆、竹子栅成一个看上去能够遮风挡雨的小屋。
篝火已经渐渐暗淡了下来,天空明亮高远了许多。空旷的黑夜里,摇曳的烛光下,祭司的脸忽明忽暗、阴阳不定,人群也如同隔着一条时光的河,在河的彼岸不断摇摆起舞,如同一群狂魔乱舞的阴魂。
安息吧,
安安心心长眠于地下,
从此黑土就是你的家。
不要跟着我们的脚步走,
不要跟着我们的声音来。
我们会把你供奉在家祖的神龛前,
我们会用最漂亮的公鸡祭礼你,
我们会用最好吃的饭菜献祭你。
你要保佑好我们的人魂,
你要保佑好我们的家魂,
让我们的鸡猪满圈,
让我们的后人站满山岗!
七
返回村落的时候,已是深夜2点半钟。祭司手里的鸡卦显示,桑木倒的阴魂已顺利抵达先祖所在的世界。
接下来的五天,桑木倒的家人都要在每个黄昏来临的时候,为桑木倒的亡魂送饭喂食一次。第一天,他们会在距离墓地最近的一个路口,搭建一个临时的祭台,为亡魂供奉上饭菜和酒肉,在祭司的安魂曲中,供奉跪拜辞别亡魂。第二天,他们会选择距离墓地更远的一个路口,供奉饭菜、酒肉,在祭司的祈祷中作别亡魂;第三天,选择作别亡魂的路口会距离墓地更远,直到第五天在村落路口与亡魂作最后的告别。
自此之后,桑木倒将作为亡魂被供奉在家祖的神龛前,虽然同住一个屋檐下,却从此阴阳相隔。它所要做和所能做的就是,在节日和叫魂做赕时,接受家人的供奉和祭拜,其余的均与他无关。死对于他,或许成为了一种解脱,成就了他在世时未尽的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