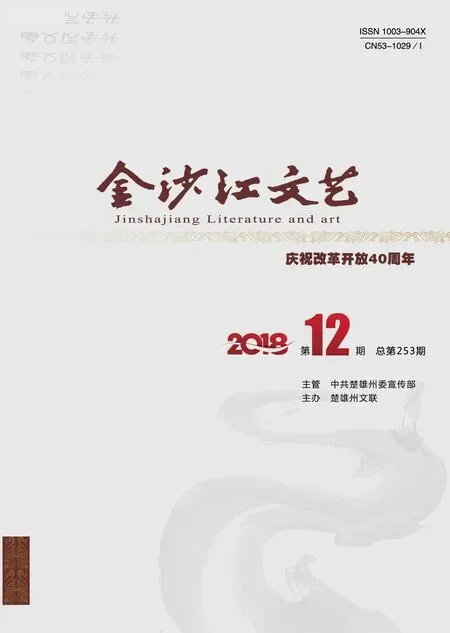春祭爷爷
余自华
2010年的春节前一天
我带着您的重孙
徒步攀爬十多公里
气喘吁吁地站在您的面前
“小宝”——一个十岁的男孩,一个吉祥的名字
他降生在本世纪初的龙年
寄托着我们一家人的希望
现在正嬉戏在小学校园的阶梯上
据他说——“读书一点都不好玩”
不过,我们都希望家族里最柔软的血脉潜移传承
因此,我们四代人站在这个山坡上
站在您的面前,看不见您烟斗的嘴、雕刻的脸以及挺拔的身影
四代人曾经在一个屋檐下
用不同的方式表达深沉的爱意
大家纷纷感到——“活着真不容易!”
在哀牢山的深处都如灰尘一粒、都如露水一滴
都长成了一张弓、一棵松树、一段木柴
始终看不到想像中的“幸福”
大家因此争论了若干年
您走了之后我们蓦然发现——“活着多么幸福!”
今天,当您躺在泥土里半年多的时候
我们纷纷沉默,牢骚、抱怨又能解决些什么
因为时间的凳子上再也看不到您端坐的身影
您坐落在哀牢山近3000米海拔的地方
比孟良崮高大雄峻很多倍的地方
足以攀爬若干支庞大的野战部队
在历史方阵里留下若干光辉的战役
也可养育很多个啸聚山林的英雄
对着一根古老的树桩歃血起誓
拉起一群贫苦弟兄“造反有理”
有多少悲欢离合凶杀流血在此上演
但是,这里百鸟朝歌,重峦叠翠,晴空万里,清风徐徐
送来这个时代最和谐的音符
我们都忍不住意气风发,怀念起毛主席
在一个朴素高于意义的时代
看到碗里的肉想起别人空着的胃
世界那么温暖,贫穷也是一种幸福
你们的“江湖”变得陌生而遥远
那个时代的逻辑早成昨日烟云
您经历了80多个年头
对于我来说是何等的高度或是传奇
刚迈入30岁就被莫名的苦痛没完没了地纠缠
时间遥远地锁定了人和物的渺小卑微和无助
我找过很多医生,吃过很多药,花了很多钱
但是我始终被莫名的恐惧纠缠着折磨着
痛苦本就是人生的常态
就如您走之前的那半年里
癌症对您身体的侵蚀让任何描述惨白无力
让您一生的奔波流离、委屈痛苦变得那样抽象
绵延百里的哀牢山让我们更加渺小无比
哀牢山站起的时候我们家族没有自己的历史
我们的一生一世显得如此不堪一提
现在,您已经融入这块时间的镜面
生生世世、苦苦痛痛、波波折折、一了百了
我们不容易地或许不经意地走完了一生
最终都要归宿于一块土坯、一个墓碑
文字不能解决任何东西,演绎变得那么虚弱
我们如此渺小,更应该敬畏和戒惧
唯有仰望,才能长久站立
您的重孙——“小宝”正在认真地和您说话
“老祖,大舅带我来看您!”
“老祖,您慢慢喝酒噶!”
交谈要有对象,而另一方却不在场
交谈因此变得独特而深刻
问题的展开和结束都由自己决定
有一些写作本来就不需要读者
有许多交流本来也不需要对象
再宏大的人生也镶嵌在点点滴滴的细流中
把细节拧成长绳,很多虫子正在漫长地爬行
再柔韧的东西也能洞穿坚硬
我们再也不想谈价值和意义了
譬如,10多年前,我上学读书苦不堪言
理想那么遥远,步伐那么漫长,时间那么难熬
今天,在机关大楼里,我远离了村庄、泥土、汗水、灰尘
却更加辛苦,更加疲惫,更加憔悴
本来要消解意义,却被意义包围,这就是悖论和无奈
又譬如,您劳苦奔波80多年
没有自己的传记,现在还没有碑记
本身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一个普通的汉子
但是作为一个读书人,我读出的是您深远的意义
对于我们家族来说,目前没有任何一本教科书比您厚重
又譬如,您只是6个子女的父亲,不是县长,不是乡长,甚至村主任都不是
但却是响当当的父亲,铿铿锵锵的男人
又譬如,您当过国民党的兵、共产党的兵
经历了新社会、旧社会,跨过了20世纪、21世纪
您安静地躺在这方山头上,时间如虫、孤独如虫
早就不准备和世界争论什么啦
您坐落的高度足以验证您的一生
那是洁白朴素、坚韧伟岸的一生
您就安息在此吧,世界已经和您没有了关系
我将下山,明年一如既往地上山,和您聊天
关于故事
好些日子之前
无数的鸽子飞来
告诉我
她们都在日子的深处
各自怀孕啦
是否链接着我们爱情的鳞爪
和曾经的我有过何种瓜葛
我们统统不清楚了
在季节疯狂变换的时候
我们选择遗忘
也许成长正在点燃
一种宿命的光亮
我还得回望一些过往
怀念她们水一样的圣洁
老人讲过很多故事
也在重复一个道理
这个世界上
总有一些眼睛在为别人活着
她们多么伟大
多么神奇
不知道雪山之外
那只眼睛此刻安好吗
我们站在各自的位置
像爱情一样的距离
至今说不清楚
也不想说清楚
总之我想起画布和一些艺术的抽象
据说可以寄托一些
也可以美丽一些
感动
昨晚我真的想和父亲说点什么
孤独又一次抵达我们的世界
沟通如此奢侈
在多维的空间里
包装着的我们
轻易地被痛苦击中
我想告诉父亲
我们更加需要那个沉默的鼓手
一直敲打我们的神经
直至淹没我们的喜怒哀乐
今天真切地洒了场暴雨
温度截然分开
一个春天一个冬天
伴随感冒或是其他
想起父亲的家和房舍
老了的他没有力气
再撑起一个像样的家
一只酒杯之后
他指望我和姐姐一起
撑起另外一个崭新的希望
一家人的幸福各自走远
连接着很多历程
小外甥一天天地真切长大
伴着阳光朝前
我们的成长何其相似
他们说
写诗的人是一个孤独的国王
统治着一群无家可归的孩子
当大街上最后一盏灯熄灭的时候
我已经适时打开心灵的窗
暴风雨来临的时候
我已经勾勒出了想象的楼宇
让我们都相安无事地
走过自己的旷野
被自己前进的步伐感动
那是多么奇妙的人生体验
15年前
我被一本诗集感动着
于是放逐了自己
走上一条不归路
20年来
我仍然被一本诗集感动着
因为我始终相信别样的生存
正抵临我们的心灵的窗
这座城市分割了陌生和熟悉
陌生到每一个公交车站牌
都指向一个遥远的地方
在下车的那一刻
我更感觉到另外一个可怕的陌生
家消失在十米之外
被一个人遗忘也许是幸福
被一种陌生包围却是可怕的梦魇
从小城市来的哥们
再也不提起脑袋的秘密了
都在午夜安静地喝茶品酒骂娘
天亮的时候
乡村的父亲照样上山
日复一日地劳作
朴素的生命维系着一亩三分地
我一直想用诗歌的形式
给母亲一个问候
从某年以来
这个愿望更加奢侈了
东西南北的身体抽搐不已
故乡被母亲完全覆盖
我能摸到的只有故乡的一根脚趾
我已经告别一生的村庄
在城市弯腰系鞋带时
我想到的母亲没有任何诗歌的意向
50年来
她背负着大山一样的担子
更加瘦弱更加衰老
我知道一种力量
正在支撑着我
河流一样卑微的成长
在堆砌文字的那天
我旗帜鲜明地捍卫朴素
不想让任何一个词语戴上镣铐
然后被意义洞穿
词语生发的地方
有一些微亮的光芒
需要语言的主人
保持素白的品质
千万别运用语言
试探实质的魂魄
我们知道
实质是一种可怕的显现
考验着对真善的坚持和守候
我们也知道把一项事物扭曲或放大
正在经历着一些是非考验
如果要表达意义
就放弃语言的折腾
在语言里只有朴素
除此外别无其他
有一股风把我唤醒
一起惊醒的还有一群神祉
村庄已经淹没很多哑然的传说
等待我用知识之手去发掘
细数一些面孔和手指
忽然发现一种实在正穿过泥土
高大建筑里的高贵身体
正在酝酿着无助的生命
忽然想念五月的乡村
雷从天空撕破平静之幕
涌流着强悍的电光
点燃季节变化的强大信号
年复一年的乡村大地
有条不紊相安无事
殊不知
此刻我们的时代正经历一场跨越
诞生一座世界上最高的楼
最长的立交桥
在世界脊背上筑起了铁路
一群失业的人正在密谋商业帝国
伴着雷声他们悄悄地说
“天空很高 适宜飞翔”
我也扯断了沉睡的脐带
开始紧贴大地的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