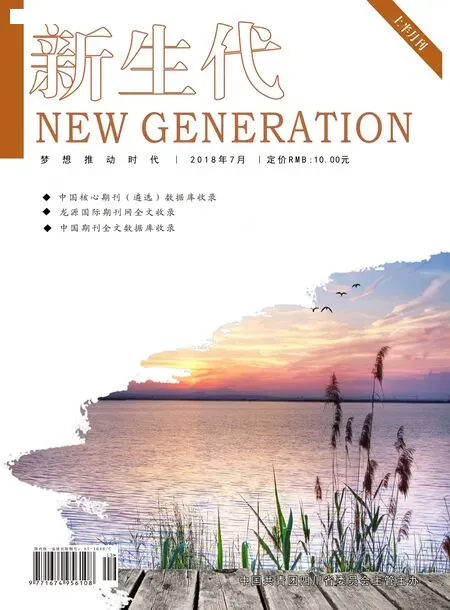社交媒体上的媒介“朝觐”
郑森楠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 401331
一、前言
《电视指南》用这样一句话形容录像镜头的真实:“一切都没变,只是你身临其境了。”媒体把虚拟空间等同于现实空间,使得我们不得不反思这样一种现象:在社交媒体上,人们对媒介建构的空间等级秩序的认同,已经超过了自身对空间重要性的感知和排序。媒介“朝觐”也由此而生。
二、概念界定
“朝觐”这个词语的本意是指,在以往的东方文明中,附属国通过向其所属的中央政权朝贡和拜谒,进而以表示对帝王的尊拜和臣服的行为。而媒介“朝觐”则是由迷文化演化而来的比喻,带有一定的戏谑和反讽意味。社交媒体上最常见的“朝觐”行为就是,粉丝自发前往某一明星拍戏的地方,或者某一电影的拍摄场地(媒介叙事中的重要地点)旅行的行为。这种带有较强仪式感的媒介“朝觐”既是在真实空间中的旅行,又是在建构的真实世界与媒介世界的“距离”空间中的表演。
三、媒介“朝觐”的驱动力
关于媒介“朝觐”驱动力,梅斯特洛维奇认为,这是一种事先被程式化的情感,人们在“朝觐”过程中表现出的兴奋、激动(而非失望)等情感流露,是“他们很清楚那是其该做的事情”。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这种行为强化了媒介仪式空间的等级结构,同时,给我们带来这样一种认知:媒介表达“里”的地方等级,要高于那些媒介没有提及的地方。这就形成了一个景观化的媒介空间维度。
深层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媒介“朝觐”行为,实质上是一种媒介的复制式体验。媒介为我们建构了一个拟态的世界,通过与真实的世界缔造“连接”使观众忽略了空间和距离的存在。而粉丝在观看媒介为其提供的这种内容的过程中,又把对仪式形式的内化当作一种具体的行为习得。换句话说,媒介不仅提示了媒介空间中的等级秩序,还成功的把这种等级秩序加之于受众的生活以及行为当中。
四、社交媒体上的“朝觐”特征
(一)源自对符号权威的信赖
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照片、视频,留下“朝觐”印记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但这种“朝觐”分享在达成“共识”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人们越来越重视虚拟平台中的仪式,而非信息的传递。因此,我们在思考媒介“朝觐”的同时还应该思考其可能带来的影响。在库尔德里眼中,媒介“朝觐”代表的是媒介景观的权利梯度,这种梯度不仅仅作用于引导我们去什么地方旅行,还会直接而深刻的影响我们的普通生活。试想一下,当这种权利梯度向你而来,你被要求向“全世界”发言时,也可以看做一种反转的“朝觐”。因为这种等级关系会直接体现在你身上,无论你喜不喜欢,是否接受,你都会被受众所标记出来。
基于这种假设,社交媒体上的媒介“朝觐”现象,既可以看做是受众对符号权威的信赖,又可以看做是符号权威对媒介景观化空间维度的建构。受众不会因为到达媒介呈现的地方而变成“中心”,相反,受众通过亲身的这种“朝觐”行为,会加强对媒介仪式的认同。在现实维度下,虽然普通受众难以真正介入实在的媒介地点,但仍保持着对媒介“里”的“神圣性”的向往和敬畏。在这个层面,社交媒体中的媒介“朝觐”可以算作是一种偶发的追随行为,这种行为代表了大众与媒体的间隔。因此,网络也逐渐成为一个使与媒介相关的“神圣物”的“感染力”得以扩散而非消失的地方。
(二)场景由现实转向虚拟
社交媒体建构的网络空间粘合和时空,使得虚拟与现实相互交织。社交媒体所构筑的虚拟空间已经侵入个到社会个体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也导致生活中被“朝觐”的对象,从现实环境中的某一个特定的地域或者某个特殊的人,转向了由媒体构筑的虚拟空间。进而“朝觐”对象的场景,在社交媒体中也表现出虚拟化、区域化、部落化的特征。可以说,基于共通价值认同的个体,彼此聚合,以实现意义的共享与交互的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往的平衡——媒介“朝觐”的参与个体从以往相对平等的位置,转向了由媒介构造的虚拟场景的权力梯度之中。在这种梯度下,参与“朝觐”行为的个体身份已经不是处于同等的位置。然而,这种媒介“朝觐”中的不平等并不是按照参与者的社会地位决定的,它是一种基于网络空间对“朝觐”人群进行划分而赋予的一种权利,更类似于一种识别的标签。因为虚拟的网络空间“朝觐”人群本身就存在一种社群和部落化的结构,参与程度越高的个体,往往能获得更多的赋权。这也就进一步加速了“朝觐”空间由现实转向虚拟。诚然,现实生活中的绝大部分人是无法亲自前往真实的地点的。这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在社交网络上上传图片、分享文字的行为会吸引那些无法身临其境的探寻者。他们也因此在网络中集聚,将虚拟的网络空间塑造为新的“朝觐”地。
(三)存在参与主体的利益争夺
社交媒体建构了一个虚拟的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朝觐”行为可以看做是一种程序化的生产。在大量的碎片信息充斥着在网络中的今天,公众的注意力成为了一种稀缺的资源。这也导致了各种竞争的出现:主体之间的竞争、地域的竞争。简单的来说主体之间的竞争更类似于话语权力的争夺,不同的是,主体之间的争夺不是为了表达自我,而是寻求一种社会心理上的认同,而这种认同需要通过媒体获得。简单地说,就是按照媒体设置的“朝觐”等级进行相关机械化、程式化的活动,也就是参与到“朝觐”的信息生产过程,而不是局限于当一个虚拟空间中的观众。此外,地域的竞争则主要表现在媒介的建构作用,部分地域对象的位置被强化,则会导致另一部分没有经由媒介赋予意义的地域失去中心位置,从而处于一种失势的状态。
可以说这种掺杂着商业利益的参与主体的竞争,使得“朝觐”行为进一步被程式化,机械化。但由于这种参与,能带来被认同感和中心感,“朝觐者”们仍处在虚拟与现实的边界中乐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