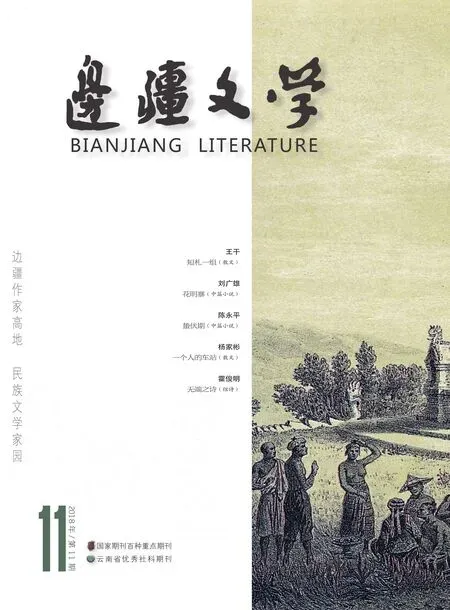两代人
唐晓华
一
十八岁我们都向往远方,眺望山,就认为山的背后会有不一样的风景。带着去看世界的迷茫和激动,我参军入伍,第一次远离家乡。从湖南到了四川,那是一个峨眉山脚下叫黑桥的附近的无名山头。对于我这个从小生长在农村的青年,站在那个无名山头上,看着周围几十里连绵不尽的山峦,我想,那天我的失望肯定如那天的黄昏一样笼罩四野。
这个山头在群山怀抱之中,偏僻、孤独,走出山头几里路才能看见集镇。山头上,驻有我们侦察连和防化连两个连队,营房都是平层的,听说是早前在这里的一个汽车运输公司留下的,很陈旧,就像堆在山上的没有人要的废旧盒子。山下有几户农家,或许还有一条孤独的老狗。在靠近农家的一侧,距离连队二百多米远的山坳中,有一条蜿蜒的公路,是乐山通往峨眉的主干道,黄昏时从山顶上往下望,路像一条断断续续的河流,也像一条被雨水洗得发白的扔在草丛中的绳索。当地老百姓对当兵的很好,过往的客车看见有当兵的招手搭车时,都会一脚刹车停下来。
到了连队后,我对能够分在城里的同乡很羡慕,每次请假外出,我们不是去名山峨眉山和乐山大佛等景点,而是迫不及待地到乐山和峨眉的县城里去逛街,五光十色、琳琅满目,城市的热闹和浮华,从来让我们留连忘返。或许是我继承了我父亲不认输、做事努力的脾性,加上连队干部见我是带着画夹到部队的,喜欢写写画画,就把我调到连部当了通信员。第二年,还推荐我报考了军校。我到连队后,就听说我们连队已经有好几年没有人考上军校了。为了给我报考军校创造条件,在连队主持工作的副连长临时动议让我当了副班长。副连长是湖北人,胖高个,讲一口普通话夹杂着地方口音,像流水里滚着流沙和卵石。但军事素质过硬,在连队,这样的领导威望极高,很多兵都惧怕他、服气他。在他宣布我任副班长的命令时,一些战友是不服气的,在队列中纷纷交头接耳,我自己也觉得过意不去,浑身不自在。特别是一些兵龄比我老的,军事素质比我好的战友,而我却仅仅因为要报考军校就当上了副班长。如果考不上军校,那就太对不起连队对我的关心和寄予的厚望了,当然也无法面对战友的眼光。我在师部参加完军事院校招生统考回到连队后不久的一天上午,我记得那天阳光明媚,万物清晰,我正带着全班在训练场上搞器械训练,突然耳边响起“嘟嘟嘟”的紧急集合的哨声。全连列队整齐清点人数后,才发现在平时连队干部站的地方,多了几位陌生的军官,个个神态严肃、肃杀。原来是师副参谋长和侦察科长带着一些人来连队宣布作战命令的。当天下午,连队的兵一律理了清一色的光头,晚上,在野草涌动的山坡上,我们看了一场《南征北战》的战争影片,算是出征前的慰问。
几个月后,我从战友的来信中知道我已经考上军校,师部机关的大门口已经张贴了军校录取人员的名单,当我得知这一消息时,已经距离战友写信的时间有两个月了。也许是命中注定,我这一生该与云南有缘。当兵时,我从四川到云南参加作战,军校毕业分配时,其中大部分的学员分到了其他省份,而我又来到云南。转业后,又留在云南工作和生活。我是湖南人,但是我对湖南的了解没有云南的多,我到过云南的一百多个县,而在我的故乡,却只到过有亲人居住的三个县市和省会城市长沙。
二
我的父亲唐自书也是个军人,高大个子、脸方长,颧骨微突,目光犀利,生于1934年,因为上世纪50年代没能入朝参战,至今耿耿于怀。至今依然最喜欢说抗美援朝第二批的事,这是他的骄傲,也是他的块垒。
1950年10月,战争爆发后不久,部队要征兵开赴朝鲜,村头的土墙上张贴了红纸书写的标语。那时候父亲刚满十六岁,可当父亲气喘吁吁地到了乡政府后,接兵的干部看他还不满十六岁,硬是没有接收他。许多年后,父亲说起当时参军的动机,一是毛头小伙子一个,虽不完全明白事理,但知道响应号召;二是在农村的日子太苦,经常连饭都吃不饱,没有像样的衣服穿,盼望当兵能在战场上建功立业,改变家庭贫困生活的窘境。直到第二年的1月,部队开始征召第二批抗美援朝的兵员。当时的乡政府在火湘桥,离村里有十多公里的土路,爷爷走得早,家里缺乏劳动力,加上父亲的年龄又小,奶奶说什么也舍不得让父亲去当兵,一路哭着喊着追了出来,羊肠般的土路坑坑洼洼,凌晨的小雨让人走在路上像是荡船,奶奶追了一半的路程就跑不动了,齐耳短发被风吹得零乱,悲伤的哭声,也没能赶上父亲的步伐。但父亲他们坐上火车后才被告知,这批原本第二批抗美援朝的兵员,因为战场情况的好转,不再开赴朝鲜了,要送去福建的部队。故乡渐远,我无法想象父亲坐在轰隆隆的铁皮列车上,回望落日中故乡村墟的心境。只知道后来父亲被分到了炮兵十四团当了一名炮兵。且那支部队打过淮海,过江打过上海,是一支打硬仗出了名的部队,1952年才转隶炮兵建制。能在一支有着光辉岁月和历史的部队服役,我想父亲是感到荣耀的。即使在晚年恬淡的生活中,我依然能够从他闪烁的眼光中,看见他对他的军旅生涯的热爱。
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大都能够吃苦耐劳,父亲又是个要面子的人,不管做什么事都不甘心落后,事事争表现,又写得一手好字的父亲,在部队的那些年,算得上是成功的了,他立了功,在全团只有一个入党名额的情况下,还光荣地入了党。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都会有割舍不开的军人情结。这我深有体会,我想父亲也是。在父亲转业后的几十年来,他穿的用的,总是喜欢部队的东西,老式军服、胶鞋,部队时带来的生活习惯——就连在门球场上担任裁判时的判罚动作,也规范有序,干净利落,口令声如洪钟就像当年指挥炮兵炮击金门一样。
三
人一生都在路上走,不管走了多远,脑海里都无法走出故乡的版图。有时恰恰相反,离开家乡的时间越久,思乡的情绪却越浓。光阴流转,人情凉暖,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在外地工作和生活的这些年,走过和历经的山水很多已经忘却,而家乡的山山水水、孩提时的点点滴滴,却时常忆及,并越来越清晰。
父亲勤奋节俭,他转业到地方工作的时候,每个月领着三十四元五角钱的工资,在维持他和两个哥哥的日常生活开支外,还要想方设法省下点钱,留给在乡下生活的我和姐姐用。整个家庭经济上的捉襟见肘、入不敷出,让我们兄妹几人很早就懂了事,两个哥哥每天放学后和星期天,就到火柴厂去背回一些火柴盒的半成品,在别的小孩外出玩耍时,就在家里糊火柴盒。一盒装有火柴棒的火柴,在商店里售价是二分钱,两个哥哥糊十个火柴盒只能换来二厘钱的报酬,每次赚了钱后,都舍不得用,都要将硬币全部存在一个铁罐罐里,每天都数一遍,仿佛多数几遍,钱就会多出几分那样。省钱的办法,在父亲那儿也是各式各样,到外地出差时,他带着自做的辣子酱下饭,省单位的伙食补贴;食堂里吃饭时,三个人只买二份菜吃,只买素菜不买荤菜也是经常的省钱方式,所以那些年父亲学会了腌制各种咸菜,家他腌制的蒜台、黄瓜、生姜、辣子,后来竟然还特别可口。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父亲到外县出差,看见商店里有便宜的白毛巾卖,三条毛巾可以做一件衣服,他就买了一大梱白色的大毛巾回来,染了色后给两个哥哥缝制衣服穿。
然后就是对我们管教特别严厉。我从小就和姐姐跟着母亲在乡下生活,父亲带着两个哥哥在城里读书。有一次我从乡下到父亲单位去玩,看到过道上有一件小物品,觉得很好看,就懵懵懂懂地拿回了家,父亲知道后,十分生气,左手五指抓着我的屁股,右手抻开巴掌就揍了我一顿,两个哥哥在旁边吓得也不敢出声。打完了我,父亲就问我在哪拿的,牵着我的手,将小物品还给了人家,还反复向人家解释和赔礼道歉,嘴里不断说:小孩不懂事,小孩不懂事。而在之前,我每次到父亲那里,父亲总是含着宽厚的微笑,向我伸出溺爱的双臂。
初中毕业后,我心想高中可能考不上了,很沮丧,对前途一片茫然,就去找父亲,想在城里找点事做。那晚,父亲和我并肩走在街上,父亲一会儿沉思不语,一会儿自言自语。返回时,碰见一位四十来岁的阿姨,这位阿姨听说我刚毕业,想找点事做,想让我跟着她去砂石场碎石,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把我带到了她家门口。砂石场人声嘈杂,大多是中年妇女和一些年龄跟我差不多的青年。砂石是送去钢铁厂炼钢用的,要将石头碎成核桃大小的多边形,才能验收合格,按立方米计价。每次放炮炸石后,人们都争先恐后,蜂拥而上。一天下来,我累得精疲力竭,穿在身上的白衬衣被汗水浸透得变成了黄颜色,右手掌也被小铁锤的竹片手柄磨出了水泡。黄昏时,我回到家,父亲一见我就说:还是要读书才有出息呀!若干年后,我才发现,这是父亲对我进行的最好的教育。
记忆总在留存给我们人生的另一个侧面,那么多年了,我依然记得我拿走小东西的县革委会的,那个堆满了坏掉的椅子、破败的蜂煤球、在锅碗瓢盆的叮叮当当的打架声中,永远弥漫着一股油烟味的昏暗的走道,以及走道望出去的几栋青砖的瓦房,瓦房旁边空荡荡的篮球场,和篮球场边停着的绿色吉普车。
还有我中学毕业和父亲并肩走在路灯下的那一晚,有些焦躁的气氛和路灯下飘飘荡荡的碎屑,那飘落的碎屑,像一些蛾子碎下来的翅膀。当然,还有碎石场那被削平了半边的石山、轰隆隆的人声和叮叮当当的碎石声,已经烈日下的滚滚尘土和我耳后的汗滴。
四
我坐在父亲的办公室里,看他起身提起一个竹编外壳热水瓶,若有所思地拧开软木塞,给我倒了杯雾气腾腾的白开水后,然后左手按住桌上的黑色手摇电话机,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捏着话柄摇了几圈子后,拿起话筒,请单位的总机挂长途电话,到县民政局了解情况。通话结束后,父亲反复告诉接线员,这是私人电话,一定要从自己的工资中扣除。这是在我当兵两年后,请父亲帮忙问参军补助费的场景。我坐在父亲办公桌的对面,听到他和接线员的对话,心想父亲也太死板了,打个电话是公是私别人未必会知道,父亲从我的眼神中看出了我的想法,对我说:“别人是不知道,但是我们自己清楚”。三十多年的工作中,当初父亲与接线员对话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与之相反,父亲总爱说的一句话是:朋友不怕多,仇人怕一个。在朋友眼中,他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和幽默感,还经常根据当时的情景脱口而出打油诗。无论是单位离退休的老同事,还是家属院里的年轻人,都喜欢听父亲谈天说地。有父亲在的地方,总会爆发出阵阵笑声。特别是在退休之后,他的一些同事和朋友在寿辰、乔迁等喜庆事时,也都喜欢邀请父亲到场,父亲也都会说上些开心的俏皮话,活跃气氛。父亲好友的儿子程一平,在新房落成乔迁之喜时,父亲不顾年迈行动不便,赶到几十里外的乡下,前去庆贺。父亲看见这里的村村寨寨都通了水泥路,镇上新建了许多房屋,很高兴,现场即兴书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横塘镇成闹市,民众欢天喜地”;下联是:“小河边建高楼,我家幸福来临。”横塘镇地处山区,每逢街子天,方圆数里的村民们都要到镇上来赶街。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几年来,这里的交通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村民们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父亲的这副对联,正是我国新型农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的真实写照。
父亲喜欢用打油诗的形式,喻事说理和为年轻人励志。为教育晚辈们为人处事,搞好邻里关系,还专门写有一首打油诗:“见面问个好,点头笑一笑;邻里常往来,和睦最重要”。老家姑家塘的一位亲戚在工作和生活上遇到困难,想打退堂鼓。父亲知道后,就为她打气鼓劲:“困难好比是座山,看你敢攀不敢攀,胆小的永远在山下,胆大的就能站顶端;困难好比是石头,决心好比是榔头,榔头敲石头,困难就低头”。在家里,父亲也同样喜欢用打油诗表达自己的心情。大年三十这天,在除夕夜的年夜饭桌上,全家人四世同堂,父亲异常高兴,兴致勃勃,当即吟到:“儿孙孝敬好,老人寿年高;年年闹春节,岁岁都欢笑。”,见父亲如此高兴,全家人心里也是乐滋滋的,常年在外地的我,也深深地感受到了“父母的健康,就是儿女的幸福”和“家有老人是个宝”的真切含义。毕竟我的父亲,已经是80多岁的高寿老人了。
但父亲不服老,对社会上流行起一些新的时潮时,他也喜欢去琢磨。送了一台电脑给了父亲,他还笨手笨脚地学着在电脑上与我视频。当流行起在手机微信上视频聊天后,他就时常与我在微信上视频聊天。并得意洋洋地到处宣称:我的QQ号和微信号的昵称都叫活到老,学到老。以前通信太不方便了,现在不管相隔多远的距离,拿起手机就可以通话和视频,这是他以前做梦都没有想到的。大哥在读小学的时候,提着热水瓶到锅炉房去打开水,因为看管锅炉的人离开岗位的时间过长,水温超过了极限,锅炉发生了爆炸,大哥的全身被开水高度烫伤,危及到了生命,不巧的是父亲又在外出差,单位的人打了一天多的电话才找到父亲。想想当年,看看现在,通信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
去年春节我回家时,第一次见到父亲流泪。父亲流泪是因为话题突然转到爷爷奶奶时。他的声音突然变得低沉而沙哑,低着头一直在看脚下的地面。
在我出生前,爷爷奶奶就已不在人世。太爷爷生有爷爷和大爷爷两兄弟,爷爷是老二,叫唐贵灿,大爷爷叫唐贵炳。爷爷生于1900年,在种田的间隙,还靠着给村里村外的人做些木工活和缝制衣服来养活家人,1947年5月,他在四十七岁那年,因贫穷和过度劳累患了痨病,无钱医治而早逝。奶奶叫卿桂兰,在大闹饥荒时饿死了。她离世时才五十多岁。父亲小时候日子过得很苦,家境十分贫寒,经常是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煮青菜时锅里都没有油放,因为家里太穷了,无钱供他读书,在十一岁时,他才偷偷地跑到邻村的一个私塾里,零零星星地读了两年的私塾。他十三岁时下地种田,也就是那年,他当了村里的儿童团团长,十五岁时,全国刚解放不久,因为个子高大,还当上了民兵营长。奶奶生有父亲和叔叔两兄弟,因为爷爷奶奶走得早,所以父亲一生都和叔叔相依为命,感情特别好,叔叔小父亲六岁,人老实,不多说话,在四十多岁时才和婶娘生下堂妹。父亲把堂妹视为己出,拿堂妹比我和哥哥姐姐几个还要紧,从堂妹一出生到读完大学,事无巨细,样样关心,就连堂妹叫晓亮的名字也都是父亲取的,直到堂妹考上公务员,当了一名警察后,他才彻底放下心来。
父亲四十多岁时,就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天气一冷,四肢骨关节就疼痛。二十多年前来昆明看我时,就查出右大脑毛细血管梗塞,这些年来,一直靠着药物治疗。岁月不饶人,辛苦操劳了一辈子的父亲,已逐渐显现出来老年人的形态:躬着背、步子缓慢,读书看报和摆动东西时,也显得有些迟缓了,在门球场上打球时,动作也没有了前些年的灵敏。所以我最怕离开家时父亲送我,我最怕车子驶离了老远,后视镜中,父亲还站在屋外几十米远的斜坡路上。
第一次见到父亲流泪的那天,天空一扫阴绵细雨,突然放晴,在凉意渐少的和风中,一家人围坐在门外还没有干透的水泥路面上,听父亲聊天。门外几十幢清一色的红砖墙青瓦屋顶的平层老房子,从坡顶到坡下呈阶梯形,在一条水泥路的两边依次并排矗立着,因为地势较高,视野开阔,可以看见大半个县城的面貌。斜面有一颗没了树叶的大树,上面还零星挂着不知名的果子。每一幢房子的门前,都留有十多米宽的空地,大嫂种的蔬菜在蓝空的映照下,正在那块空地中迎风泛绿。

刘宇 雪山下 36cm×51cm 水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