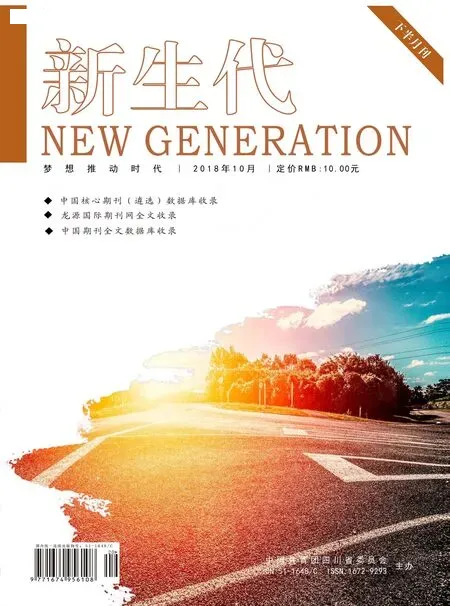探讨《内在体验》中死亡与悲剧主义的关系
陈辰 湖北大学 哲学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1
一、《内在体验》中关于死亡的理论基础
1、罗马死亡文化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一般会认为死亡只是一瞬间的事情,在人死后延迟两天到三天的时间才埋葬逝者的理由仅仅只是为了召集死者的亲友和筹备葬礼。并没有一格间断的时间将今后的生活与逝者分隔开,仿佛死者一咽气,他的灵魂就不假思索的出现了,甚至准备好了接受为他生前所做之事进行的审判(上天堂或者遭报应)。在死亡的阴霾降临之后,逝者的亲人们便开始了一个或长或短的服丧期。通常纪念逝者的时间在一些特定日子,比如我国的清明节和广泛适用于世界的“年终”。这些关于死亡的观念和死亡之后的一些列事件的特定模式,我们都十分熟悉,以至于我们丝毫不认为他们多余。但在过去并不是如此。正如拉菲托所说:“在大多数原始社会中,死者的尸体最终只是暂时被放置在坟墓里保存,过一段时间之后,人们还要为他们举行葬礼。”原始社会与现代社会在死亡习俗上的差异并非偶然,他说明了过去的人与我们对死亡的表述和感受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不一致。
欧洲文化起源于古希腊罗马文化,根据罗马法令的规定,一般要给逝者举行两次葬礼。第一次的临时葬礼应该在逝者去世后的第八天,逝者家属会给逝者清洁身体,穿戴整齐并停放在庭院中。四十天后,遗体会被转运到城外的墓地进行最后的葬礼。葬礼一般在夜晚举行,在逝者入土或被火化之后的第八天按照惯例会举办宴会,并向逝者敬酒。在举办这个宴会之前,逝者生前所居住的屋子被认为是不洁的,直到第八天进行过大扫除之后才象征清扫走了厄运。
在当时的人们看来遗体是非常肮脏的,会向四周扩散污染传播疾病,甚至连罗马的法令都规定遗体不能安葬于城内,以避免城内神圣的土地受到污染。在第二次葬礼还没有举行之前,死者的尸体始终暴露在危险之中。民俗学家和人类学家一般认为尸体在某些特定的时间里极易受到魔鬼的影响;必须通过无数手段不断加强它的不断消解的抵抗力量。因此,在逝者死亡后这一阶段是极危险的;这就是为什么尸体要祈祷和驱魔的原因。这一首要任务要求人们在死者死后立即为他清洁身体,和举行尸体有关的各种仪式:例如,涂抹香膏和祈祷等,同时还要有人时刻陪伴着死者死者直到度过这段危险期,以防恶魔靠近逝者。这种备受特殊虚弱困扰的尸体,成为生者们为之惧怕又特别关心的对象。不仅逝者的亲属被迫卷入对逝者的各种照料,要为死者服丧,还要为厄运所笼罩,就连当时负责处理和搬运尸体的人都被隔离了。丧葬事务的承办者也常常被认为是精神污染源,是不可接触的人,会带来疾病和厄运。
2、基督教死亡文化
依托于罗马帝国的死亡文化,各种死亡文化逐渐发展了起来,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死亡只是肉体的死亡,灵魂不会死亡,灵魂会在肉体腐烂发臭之后彻底抛弃肉身获得新生,去往另一个世界。在这些丧葬文化中,基督教丧葬文化一方面继承了罗马丧葬文化中仪式的部分(即临时葬礼和最后葬礼),另一方面也发展出了其独特死亡观念。
首先,有别于犹太教徒和异教徒认为尸体是污秽的,接触尸体的人会被污染,基督徒认为逝者的身体是神圣的,鼓励人们不要畏惧尸体并轻松地接触尸体。死亡意味着灵魂离开肉身,对于虔诚的基督徒而言,死亡是通往得救的大门。他们也因此非常崇敬圣徒和殉教者们,殉教者们荣耀的死亡使得他们的灵魂升入天堂,基督徒也乐意集中将逝者埋葬在殉教者们坟墓所在的地方周围。其次,基督教丧葬文化有一个十分独特的地方,在于忏悔。由于只有完全纯洁的灵魂才能升入天堂,基督徒害怕生前的罪恶影响死后灵魂是否能升入天堂,死亡仪式中的忏悔变得不可或缺,他们试图利用忏悔来请求教会乃至上帝的宽恕,使自己在死后能够得救。即使在死后不能马上得救,灵魂也会在炼狱中受到惩罚并使罪恶得到洗涤。灵魂在炼狱中通过暂时的受苦赎罪来洗涤自己,直到灵魂再次纯洁才能升入天堂。炼狱中处罚灵魂的纯净之火来自上帝,上帝拯救了灵魂。
二、乔治·巴塔耶的悲剧主义
1、内在体验与人的降格
乔治巴·塔耶的内在体验不通向任何的避风港(而是通向一个困惑之所,一个无意义之地),为了通向无休止质疑(追问)一切事物,他发现了不顾宗教信仰的必要性,脱离教条的预设,体验不再被过分的限制:一个已知的人无法超出一个已知的视野。乔治巴塔耶以非知为原则,但又极其严格的遵守基督徒所擅长的一种方法(他们在教义的允许下踏上了这条路)。但这种诞生于非知的体验断然地停留在非知。他是未知者,狂野而逃避了知性,和上帝是截然不同的。上帝是绝对者,世界的根据,如果不是知性就什么都不是了,所以上帝对于未知者来说是需要排斥的预设。无论如何,上帝和灵魂拯救相连——同时也和其他从不完美者到完美者相连。而未知者对完美(“必须是”)的观念,产生了一种不安的敌意。
内在体验的原则,是通过谋划逃离谋划的领域。戏剧化在所有的宗教中都是本质的,但如果他是纯粹外在和神秘的,他就不能同时拥有几个独立的形式。具有不同来源的意图和献祭被结合了起来。但每一个献祭,从祭品被献出的那一刻起,就标刻了一种戏剧化的强度。要逃离被理智所蹂躏的大厦,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戏剧化,就无法脱离自己。
通过这种:通常是强制的、戏剧化的方式,一种喜剧元素,一种愚弄元素。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戏剧化,我们就不知道如何发笑,但笑声总在我们身上准备就绪,它让我们在一种反复融合中再次迸发,他听凭意图打碎了我们,但这一次没有任何权威。献祭意味着人凭他的意志,把某些财产置于一个危险的领域,那被毁灭的力量所统治的领域。以嘲笑为例,我们就这样祭献了我们所嘲笑的人,把他,没有任何苦恼地,抛入一种在我们看来微不足道的降格(笑声无疑缺乏献祭的庄重)。
2、喜剧就是悲剧
通过极限的戏剧化的方式,我们可以在传统内部,让我们自己远离传统。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内在体验都依赖于对拯救的迷恋。拯救是一切可能之谋划的巅峰,是谋划之手段的顶点。根据圣十字若望的说法,我们必须模仿上帝的降格,苦恼,“拉马撒巴各大尼”的“非知”时刻;说到底,基督教是拯救的缺席,是上帝的绝望。上帝在人的位格上,上帝的苦恼是致命的;它是诱使人坠落眩晕的深渊。上帝的苦恼只能说明罪。它不仅为天国辩护也为地狱开脱。在圣十字若望那里,除了上帝面前的羞耻,宿主不死的欲望,甚至惯常的手段,都几乎存在缺陷;他坠入了非知的黑夜,触摸了到可能性的极限。
乔治·巴塔耶认为对幸福的欲望意味着对苦难和逃避的欲望。拒绝幸福等于拒绝得救,不再哀求诞生与意义的缺席,并脱离了一种固定的一一,一种最终的意义。由此才能触摸到可能性的极限。对极限的追逐逐渐的能够成为习惯,依赖于孩子气(错过真理):一个人必定嘲笑它,除非他意外地感到悲痛伤心:那时,狂迷和疲惫相互接近。而当嘲笑发生时,某个放声大笑的人本身是可笑的,并且在深刻的意义上,比他的祭品更加可笑;但一个轻微的过错,就使人们同大笑者不受限制的世界进行交流,没有苦恼、充满欢乐,将人从他们空洞的孤立中抛出,让他们融入不受限制的运动。由此,它们在自身中间进行交流,带着巨大的噪音如海浪般冲向彼此,能够做到这个的只有死亡。死亡是令自我恐惧又合乎逻辑的结果,因为我们的生存是一种要完成存在的恼怒的尝试。我们不敢完全的肯定我们要无限存在的欲望,岁永生不死的渴望让我们恐惧。但只要我们悲惨的证明出来,我们甚至更加不安的在自己身上感受到一个残酷的欢乐的时刻。人只有当接近死亡时对死亡的意识才会形成,但只要死亡完成了他的作品,意识也不复存在。由此乔治·巴塔耶为悲剧定义:悲剧就是喜剧,反之亦然。悲剧的本质体现于不可赎尝,而极限,是疯狂的悲剧。
3、悲剧主义与死亡
“我知道我一边或者一边下降,不是下降到一座坟墓里,而是降入一个普通的坑,既不庄严,也不理智,真正的赤裸。”乔治·巴塔耶在《内在体验》中如是说道。即在他的认知中一切回避极限的一本正经都是人的降格,人惧怕死亡,而人活着就会不断地降格直至死亡,死亡是人降格的最低点,在完成死亡的作品后,不再有意识。在某种意义上,死亡是庸常的,不可避免的,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又是深刻的难以通达的。动物意识不到死亡,即便死亡把人抛向了动物性。化身为理性的理想之人仍然陌异于死亡:一个神的动物性对死亡的本质而言是根本的;既污秽(发出恶臭),又神圣。只有人才可以降格,因为人模仿上帝。总而言之,坠入死亡是污秽的;在一种孤独里——其沉重的方式不同于情人的裸露——腐烂的临近把死去的自我和缺席的裸体联系了起来。
死亡的令人苦恼的特点表明了对人的苦恼的需要。没有这种需要,死亡将看似安逸。人,可怜的死着,让他自己远离了本质,产生了一个为艺术而塑造的幻觉的、人性的世界:我们活在一个悲剧的世界里,活在一种虚假的氛围中,悲剧就是这一氛围的完成了的形式。对动物来说,没有什么是悲剧的,他们并不落入自我的陷阱。悲剧是人造的世界
三、结语
乔治·巴塔耶在《内在体验》中表达了,死亡文化和丧葬文化是诞生于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和对逝者的同情的艺术行为和艺术创造的观点,如果我们将死亡仅仅视为肉体的消亡,那么死亡文化的存在就不再被富有意义,这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当肉体死亡灵魂升入天堂,若是人造的喜剧,人死不能复生,死亡作为降格的底点就显得更加无法挽回和不可赎尝。死亡在乔治·巴塔耶的悲剧主义思想中是超越已知的未知,是触摸极限的可能,当进入天堂成为最迷狂的喜剧,若我们无视这种狂迷的启示价值,自我燃烧的激情就会化为灰烬,喜剧则转为最大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