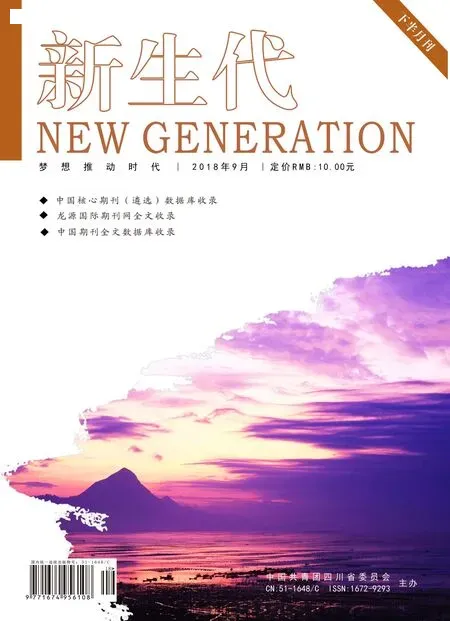浅谈后代文学中的“宰予昼寝”
邓春妮 长沙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湖南长沙 410000
对于《论语·公冶长》中“宰予昼寝”一章的理解,后代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为宰予不平者,认为孔子小题大做,如王充《论衡·问孔篇》:“昼寝之恶也,小恶也”有支持孔子者,认为夫子之言实有深意,如朱熹《论语精义》:“宰予以言见取于圣人自其昼寝而夫子始不信其言,以其华而无实,不足以有行也。”关于“昼寝”二字词义的理解也分出了昼眠说、画寝说、昼居内寝说、午睡说、昼御说五大类,至今仍无定论。
而文人们从文学的角度出发,对其作出了更具趣味性的解读。本文避开训诂与考据,试从后代文学作品的另类解读中,分析古代文人对“宰予昼寝”的评价及形成原因,或许可为《论语》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一、“宰予昼寝”与士人昼寝诗
周密《齐东野语》:
“饱食缓行初睡觉,一瓯新茗侍儿煎。脱巾斜倚绳床坐,风送水声来枕边。”丁崖州诗也……及观昌黎《语解》,亦云“昼寝”当作“画寝”,字之误也。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昼寝”之责?假或偃息,亦未至深诛,若然,则吾知免矣。”
先是举了不少昼寝诗,又引名家谈昼寝的言论,最后搬出“宰予昼寝”来,都是为了表现昼寝之美妙无穷与名正言顺,为自己的昼寝“开脱”。
昼寝诗的发展有一条鲜明的轨迹,其出现和兴盛与儒家思想的时代发展息息相关。魏晋前,儒学思想对文人的影响颇深,鲜有昼寝诗歌。魏晋时,庄老思想占据上风,士人以放荡不羁为尚,《世说新语》中出现了不少名士高卧的故事,陶渊明也有“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的美文。中唐白居易写了大量的昼寝诗,“食饱拂床卧,睡足起闲吟”等,表现了诗人醉心睡乡,远离名利的闲适心情,符合其“中隐”思想。
宋代开始出现了大量昼寝诗,究其原因,一是宋代文人待遇好,有时常昼寝的条件。二是受佛道影响,审美偏于清淡,思想更为多元,不拘泥于儒家经典,于是创作出了大量诸如昼寝诗一类重个人性情的诗歌。
二、古典小说中的“宰予昼寝”
清代王希廉说“从来传奇小说,多托言于梦”,《古今小说评林》作者之一的著超说“小说写梦,实常落套,且于辟除迷信四字,尤不相宜。中国小说,无一书不说梦。”有睡才有梦,说梦自然也离不开说睡。
清代文康在其小说《儿女英雄传》之《缘起首回》中,自述幼时私塾读书,读到了“宰予昼寝”一章,就心生效仿,“偶然有些困倦,便把书丢过一边,也学那圣门高弟隐几而卧”,恍惚之间一路由人间走上天界,目睹帝释天尊发落儿女英雄一桩公案,由此作为整部小说的开端。看来孔子之责不仅没能以儆效尤,反而起到了使人心生效仿的反作用。
明末话本小说《七十二朝人物演义》第四卷“宰予昼寝”。小说中宰予昼寝的原因是与子共辩论,不觉多言,受到孔子“以言取人,失之宰予”的批评,孔门弟子议论纷纷,宰予因而醒悟,慕黄帝之道,从睡乡之学。并说“孔子犹恐他不能直证黑甜乡,故把朽木粪土的譬喻提省他。子我自得了夫子唤省一番,于此道愈加精进”,由此说来,昼寝倒是受孔子支持的。
冯梦龙的《笑府》卷二中也有两则与“昼寝”相关的笑话:
一师昼寝,及醒,谬言曰:“我乃梦周公也。”明昼,其徒效之。师以界方击醒,曰:“汝何得如此?”徒曰:“亦往见周公耳。”师曰:“周公何语?”答曰:“周公说,昨日并不曾会尊师。”
师喜昼寝,弟子曰:“‘宰予昼寝’四字如何解?”师曰:“宰者,杀也;予者,我也;昼者,日中也;寝者,眠一觉也。”又问:“如何贯串?”曰:“便杀我也说不得,到日中定要眠一觉。”
这里为宰予辩护者的身份不是诗人、小说家,而是与孔子同为老师的私塾先生,由此可见犯困乃人之常情,师生都不可免。
三、另类解读产生的原因
后代文学作品中对“宰予昼寝”的解读为何会如此偏离孔子原意呢?笔者认为原因有二。
一是出于对经典颠覆结构的心理。唐人不拘于前人的阐释,宋人常有自己的见解,于是韩愈刘敞“画寝说”的盛行,为士人昼寝诗的发展扫除了思想障碍。而明清时期资本经济开始萌芽,文人对思想自由更为向往,渴望摆脱礼教束缚,社会风气也偏于享乐纵欲,肯定人类正常欲望之一的睡欲,甚至进一步将宰予推向睡乡神坛,都带有一种解放宣言式的狂欢意味。如果说宋代昼寝诗中隐藏的宰予形象是闲适淡然,那么明清小说中则是不羁放纵,并带有些许挑衅,对“宰予昼寝”的解读也更为反叛大胆。
二是昼寝这一行为本身就有丰富的艺术性与文化渊源,它不符合古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习性,因而具有一种不平常的审美。黄帝昼寝梦游华胥氏之国,于是垂手而天下治,满足了后代士子对治国的愿望;楚襄王昼寝而有高唐的一番云雨,满足了士人对艳遇的幻想。由昼寝而生的华胥梦和高唐梦是古代文人创作中常见的题材,昼寝这一不同寻常的行为本身就有很深的文化内涵和生命力。
总之,后代文学作品对“宰予昼寝”的解读出于文人或闲适或叛逆的心理,读者应从文学审美的角度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