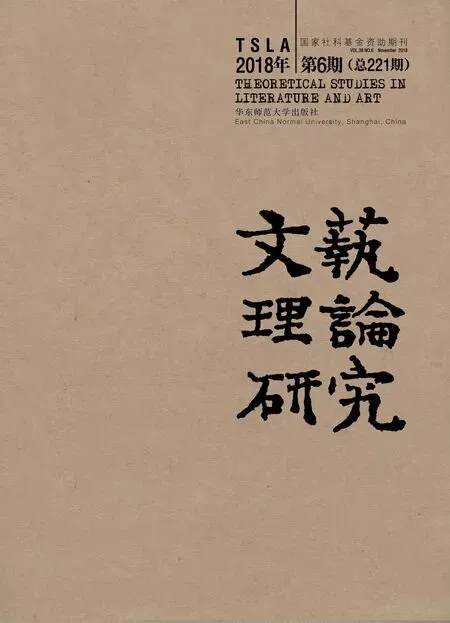世界文学、距离阅读与文学批评的数字人文转型
——弗兰克·莫莱蒂的文学理论演进逻辑
陈晓辉
即使不是最活跃的,弗兰克·莫莱蒂(Franco Moretti)也“大概是今日英语文学和比较文学界最有争议的人物”(Serlen214),其世界文学观一经提出就引发广泛争鸣,被誉为“从恶魔那里收到的最狡猾的概念之一”(Batuman, “Adventures”)。窃以为,其“狡猾”之处正在于它破解了世界文学的“实存性”限定,以“观念性”开启了“距离阅读”(distant reading)的征程,表征了文学批评的数字人文转型,体现出鲜明的前瞻性、问题性和方向性,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一、 世界文学: 从实存性到观念性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传统文学批评无法驱离现实文本,世界文学“首先必须聚焦在翻译的具体作品上”(Miller378),因而“实存性”向来是世界文学的核心标签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看,实存性世界文学是文学批评选择的对象性结果,与文学创作关联不大。在创作时,作家大多不会考虑所创作品是否是世界文学。然而,在批评时,受文本特征、个人才能和批评风尚等因素的限囿,取样范围和规模成为必须切实考虑的焦点。实存性世界文学变成取样经典文本作为批评对象的必然产物。
实存性世界文学确信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认定世界文学有明确的指涉对象,将影响超出本土的文学经典及作品选、文学史论著等作为世界文学的代名词。比如杜瑞辛(Dion’yz Durišin)的世界文学指世界文学史、各国最优秀的文学作品集和具有相似性的文学作品(80—81);吴雨平、方汉文的世界文学“包括来自于不同文明体系的经典与代表性作品”(82)。最典型的是盛行全球的世界文学选本,如《诺顿世界文学杰作选》《朗曼世界文学文选》《哈泼柯林斯世界读本》等。无论是经典杰作、作品选,还是史学著作,均能在文学的物理世界找到确定的对应物,凸显出世界文学的实存性。
问题是,实存性世界文学的文本选择和历史叙事不仅透射出浓重的精英意识和主体偏好,同时受文本数量的钳制而无法真正表征世界文学赖以存在的“整体性”,其批评变成膜拜极少数作家的“神学训练”(Moretti, “Conjectures” 57),文学史变成少数人、少数作品的“丰碑”或一些特殊人物和稀有事件的“怪物收集者”。与此同时,这种文学史是以牺牲大量当时实存的非经典作品为代价的,致使它们被无情地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造成科恩(Margaret Cohen)所谓的“伟大的未读”(the great unread)(23)。在全球化背景下,人们如何找到公平对待所有作品的方式,真正构建整体性的世界文学?莫莱蒂正是以此难题作为思考的基点,实现了世界文学从实存性向观念性的转化。本文所说的观念性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莫莱蒂的世界文学不再指涉具体文本,二是它指一种重新认识和思考世界文学的思维方式。
从观念性出发,莫莱蒂首先强调将世界文学“看作”一个整一体。它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共时的整一体。比克罗夫特(Alexander Beecroft)断言,莫莱蒂的世界文学是“作为文学与其环境间关系这一普遍难题的当代表征而出现的”(91)。莫莱蒂号召“重拾世界文学雄心”的时候,“身边的文学已宛若全球性系统”(“Conjectures”54)。全球化的境遇敦促人们重新思考世界文学,“世界文学是当前全球化的伴生物”(米勒8)。如果说全球化是人类无法逃避的命运,世界文学是全球化的文学版本,那么,世界文学批评是理解全球化的一种方式,莫莱蒂不过是众多批评者之一。按照鲍曼的说法,全球化从根本上具有“流动性”。由此看来,世界文学本身是一种“旅行的文学”,它是商品、资本、信息技术的全球流通而导致的文学全球化。在全球化时代,不同民族文学的数量和类型激增,在跨国族流通中同存镜射,相互融汇,既产生了具有相似性的“世界性文本”,又产生了关联性的“世界文学体系”,建构了文学的世界共同体。莫莱蒂认为,该共同体“不能通过把个别案例的知识点拼凑在一起来理解,因为它不是单个案例的总和,而是一个共同的系统,应被理解为整一体”(Graphs
4)。在莫氏看来,世界文学是全球化时代文学相互影响和关联所形塑的变动不居、整一但不平等(“Conjectures”64)的整体性系统。其二是历时的整一体。莫莱蒂从进化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中获得灵感,坚信“进化论和世界体系分析是研究世界文学的两种理想模式”(“World-Systems”218)。因为在传统文学批评中,历史研究不关心形式理论,形式理论往往忽略历史研究,“进化论在历史进程的基础上阐释了现有形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World-Systems”219),不但能展示文学形式的适时变化,而且能把文学的历史变迁和形式转换整合为一。而世界体系理论倡导“唯一真正的历史是整体史”(Bloch61),它为世界文学批评提供了理论参照。据此,莫莱蒂将世界文学分为“18世纪前”和“18世纪后”两个阶段,前者“是多种独立的地方文化的马赛克拼贴”,后者则“由国际文学市场整合为统一体”(“World-Systems”228)的世界体系。这样,莫氏把长时段、跨空间的文学全部摄入世界文学这一概念,暗含了一种超时空整体性批评的雄心。以这样的方式,莫莱蒂不仅建构了世界文学的共时整体性,也建构了它的历时整体性,为探索文学的系统研究和整合研究开辟了新思路,充满了想象力和时兴性,与尼希(Almando GiliS-ci)的观点相映成趣。尼希就说 :“我们既有与全球市场和大众文化产业相一致的‘全球文学’,又有由众多不同世界组合而成的‘世界文学’”(127)。
当然,与莫莱蒂一样将世界文学看作整体的批评家大有人在。卢卡契也讨论过世界文学的整体性,认为世界文学“既不是所有民族文化、文学和大作家的总和,也不是他们的平均数,而是他们活生生的整体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一个活生生的整体”(卢卡契449)。这种整体性和莫莱蒂的世界文学整体性有异曲同工之妙。遗憾的是,卢卡契在发现这种整体性后,并未致力于对其批评的思考,而是致力于如何创作这种整体性的世界文学,提出了一种融现实主义、批评现实主义,甚至浪漫主义的“大现实主义”创作观。弗莱(Northrop Frye)在反对新批评“使单一作品拜物教化”的倾向后,认为文学批评就像从远处看一幅画,要“往后站”,从整体上把握文类的共性及演化规律,着眼于文学中相互关联的整体因素(140),但在批评实践时,他却依然选择细读法。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认为,世界文学是“将文学作为一个世界来思考的概念方式”(73),不但以观念性世界文学回应了莫莱蒂的设想,并创造了“世界文学的空间”来表征这种整体性,但他更强调文学与民族政治的关系以及充斥其间的身份认同,不仅与莫莱蒂源自生物进化和经济体系的整体性大异其趣,而且仍未脱离细读批评。
其次,莫莱蒂将世界文学看作一个亟需新的批评方法予以解决的“问题”,也是问题本身。如前文所述,世界文学是一个有关文学批评的概念。当莫莱蒂将世界文学看作整一体的时候,势必面临如何践行整体性批评的挑战。麻烦在于,多数批评者因精力有限,不能掌握不同民族的语言,又因生命有限,没有时间直接阅读各民族的所有作品,逾越时空的掣肘,规避不可通约的语言、异质的文化和无法计量的文本,进行跨界批评。对此,实存性世界文学学者们早有预见。上世纪70年代,艾田伯(René Etiemble)就认为与其读贝拉当、萨冈的原文,还不如读井原西鹤、阿迪伽的译文。在列举了一系列译文优于原文的例子后,他又算出,以50年职业生涯、每天1部的速率阅读经典,也不过18262部作品,“与现有优秀作品的总数相比,它又算得了什么?实在少得可怜”(93)。艾田伯对翻译的肯定和对阅读数量的担忧契合莫莱蒂遭遇世界文学的问题基点,只可惜艾田伯最后的破解之道却仍是从千百万的书库中挑选经典作品,未能突破实存性世界文学的既有方式,并寄望于通晓各种语言和文化的天才出现,以撰写真正的整体性世界文学史,充满了乌托邦色彩。有趣的是,对莫氏理论深恶痛绝的批评家布鲁姆(Harold Bloom)也发现了该悖论。他曾说 :“读书必有取舍,因为实际上一个人没有足够的时间读尽一切,即使他万事不做光读书也罢”(11)。同样出于对生命有限和精力不足的担忧,但在“读什么”的问题上,布鲁姆选择阅读西方正典,从而走向文本细读。上述诸人以极少数经典作家作为观照对象,以有限的取样表征世界文学的整体性,不仅难以回应文学新变,而且将自己形塑为固守实存性观念的批评者。
在《文学的屠宰场》中,莫莱蒂感慨 :“文学史是文学的屠宰场。大量的书籍永远消失了——‘大量的’实际上消失了的书籍指的是: 如果我们今天在19世纪英国的小说中选择出200多部经典,它们也不过占全部出版小说的0.5%,那剩下的99.5%呢?”(“Slaughterhouse”207)。在此,困扰莫莱蒂的仍是文学阅读的不充分,只选取经典文本做取样的实存性世界文学肯定不是释疑的最佳方式,“无法阅尽一切”成为世界文学整体性批评的痼疾。该如何体现这种整体性?按照实存性世界文学的逻辑,扩大文学选本的范围与阅读数量是首选方案。但莫莱蒂认为,“通过提高阅读数量,恐怕不能解决问题”(“Conjectures”57),问题的症结不在时间和数量,而是认识和方法。我们需要的不是阅读数量的变化,而是批评观念的变化,改变看待世界文学的思维方式,寻求新的破解思路,从而与实存性世界文学分道扬镳。
莫莱蒂发现世界文学不仅是批评对象,而且自身成为“一个需要用新的批评方法加以解决的问题”(“Conjectures”55)。在莫莱蒂看来,世界文学首先应该坚守以表征其本质特征的整体性批评为基本路径。虽然实存性世界文学无疑是整体性批评失败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文学批评就要放弃整体性症候。世界文学批评的问题核心“不是我们应该做什么,而是怎么做”(“Conjectures”54),通过重构观照对象,创建新的批评方法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实存性世界文学的发问总是纠结于世界文学“是什么”,几乎于事无补。其实,面对庞杂的世界文学体系,批评者应该“通过聚焦现代小说崛起,概括文学的世界体系是如何运转的”(“More Conjectures”73),其变迁如何改变国族文学,揭示形态的宏观演进。在此,莫莱蒂试图撰写一部文学演变史,既展示文学在一个固定区域中的地理分化,又展示其漫长的历时进化,以世界文学的流通趋势和运行机制,来展现动态流变的长时段、跨地域的整体文学史,“文学在系统层面的演变和文学文化的变革功能因此成为莫莱蒂的核心利益问题”(Thomsen)。
可以说,莫氏的世界文学是一种观念性判断,是超越国族、文化、语言的本土化的形而上概括,不指向具体作品。这种世界文学的核心价值不在于阐释少数世界文学范本,而在于变更批评者据以观察世界的概念网络,以思维方式的转变重建世界文学的理论体系和阐释框架。虽然按照麦克里米(Scott McLemee)的说法,莫莱蒂试图以新的方式思考文学史上的证据,冒犯了人文科学致力于对文献和文化产品中蕴含的意义的解释,但是,莫莱蒂的世界文学在认知方式和方法论上突破,打开了一个供人们讨论的迷人的新维度和新领域。
与此同时,它表明了世界文学批评中思想观念的转变。如果说实存性世界文学注重以具体文本回答“世界文学是什么”的问题,体现的是本质论,那么,观念性世界文学观则以对世界文学的认识来回答“怎么样”和“怎么办”的问题,体现的是认识论和方法论。从本质论到认识论、方法论的迁移,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文学的方式,为新的世界文学批评指明了方向。更有甚者,实存性世界文学以具体文本为阅读对象,体现的是一种文学批评,而观念性世界文学更看重以抽象概念为思考对象,体现的是世界文学研究的理论化倾向。从文学批评向文学理论的转变,或者说,弱化批评,强化理论,正是全球化对世界文学的影响之一。最重要的是,它开创出距离阅读这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构成莫氏观念性世界文学最具启发性的部分。
二、 距离阅读和莫莱蒂的方法论
作为解决世界文学难题的药方,距离阅读甫一提出就饱受热议。褒之者认为距离阅读“可能是颠覆百年来的新批评霸权的最佳方式”(Esposito),也是“前所未有的,更会是将来文化批评前行的一个方向”(Sunyer),贬之者称其是“荒谬的理论”(黎文15),其“不读书”的主张“简直是毒药”(Walters)。如此吊诡的评价归因于距离阅读与文本细读的复杂关系,它在开拓出一个新的批评空间的同时,却公然挑战了实存性世界文学所固守的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的权威,一如汤姆森(Mads Thomsen)所言,“距离阅读是莫莱蒂对世界文学时代主题、范围等繁乱广泛,很难执行文学批评的复杂情况的挑战性处理,经常被认为与文学研究中的核心价值观——文本细读,背道而驰”(Thomsen)。
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功绩之一是将文本细读塑造为文学批评的核心范式,并已经受了新批评、结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浪潮的洗礼。虽然理查兹、燕卜逊、兰瑟姆、布鲁克斯等人均未对其明确定义,但学界普遍承认它设想文本是一个独立自足、非历史的空间客体,注重个人对经典文本的直接阅读,集中讨论文本及其在语义和修辞上的多重关系,探索内含于语言的文学隐喻力量,寻求一种审美和意义阐释,是文学文化分析的本质所在,也是唯一正确的文学阅读范式。
受科学语言学的影响,文本细读重视整体性批评,但这种整体性立足文本自身。在面对世界文学要求批评者“承认无知”“认识一切”和“充分阅读”的整体性诉求时,以经典阅读、个人体验和意义阐释为标签的文本细读明显力所不逮。虽然实存性世界文学以经典文本作为批评对象,符合文本细读的要求,但莫莱蒂认为,“世界文学的雄心要求我们与文本间的距离成正比: 雄心越大,离文本的距离就应越远”(“Conjectures”57)。距离阅读变成莫莱蒂针对世界文学新变和细读批评弊端而提出的诊断性概念。与文本细读相较,它呈现出四个明显迥异的特征。
第一,它是“二手阅读”。文本细读一直奉直接阅读为圭臬,但作为一种批评方法,莫莱蒂认为距离阅读是“把别人的研究成果缝合在一起,而无需通过对单一作品的直接阅读”(“Conjectures”57),意谓研究者要与文本保持“距离”,不用直接阅读作品,只需阅读相关成果并对其加以综合分析就可以研究世界文学,诚如德鲁克(Daniel Drucker)所言,距离阅读是“把内容置入(科目、主题、人物、地点等)或者把信息置入(出版日、出版地、作者、题目)大量的文本条目,而不参与实际文本的阅读”(Drucker)。其目的在于“让我们着眼于比文本更小(策略、主题、修辞)或更大的单位(文类和体系)”(“Conjectures”57)等形式要素,“这些要素意义的获得不仅是对社会经济条件变化的回应,也是对这些要素所参与的更大的文学网络的回应”(Armstrong and Montag618)。在此,距离是一种认知条件,帮助人们摆脱具体文本的限制,在更长的时段、更广的范围中探讨文学的宏观尺度。距离阅读本质上是一种“二手阅读”或“非文本阅读”。
罗德(Lisa Rhody)说 :“迄今为止,关于距离阅读最大的争议在于它与文本细读相较而显示出的优点,聚焦于读者或观察者在文本上的位置”(660)。和文本细读强调深入文本内部体验不同,距离阅读强调“站在文本外思考”。文本外的思考不仅能使我们宏观观照批评对象,更重要的是致使观察者处于旁观者的位置,脱离具体文本的羁绊,冷静、客观地体察对象,为主客体的平等对话创造条件,达到公正评价的效果。如果说文本细读让每个学生从十几岁开始学习仔细审查、剖析单个文本的方法,那么距离阅读却是一种重构批评者与文本的结构关系的假想方式,通过让批评者在历史和地理中追踪大量作品的形式元素的调查方法,从远处观察一切,寻找整体的模式和线索,继而建立一个关于文学某些方面的出现、消亡或转换的解释模型,在文学与社会、形式与历史之间建立联系。
第二,它是大规模文本分析。如前文所述,实存性世界文学是针对极少数作家的经典文本细读。莫莱蒂认为文本细读将文学作为杰作的集合,而这“一小部分文本所允诺的概念性的说服力是很微弱的”(Distant
Reading
2),无法整体展现世界文学的相互关系和形式进化。反言之,莫莱蒂相信文学史“只有在检测团体和多数时,它的过程和结果中才有更多的合理性”(Graphs
4),所以他提出距离阅读,寻求以巨量文本作为阅读对象,获得更具客观性的批评结果,恢复被严重“屠宰”的文学史。作为具体方法,距离阅读“最初的假设应该针对更大、更精确的数据集进行测试”(“Planet Hollywood”4),它是一种针对尽可能多的文学作品的“大规模文本分析”。乔克斯(Matthew Jockers)认为,距离阅读注重有关文学和非文学的整体,诸如书目研究、传记研究、文学史、语言学和作为人文计算基础的整体性计算分析,以此帮助人们观察并理解更大的“文学经济”,而且通过它的范围和规模,助推我们理解文学的发展及个人作者在经验中制造顺应或反对文学和文化的趋势(“On Distant Reading”)。哈德姆(Amir Khadem)认为,“距离阅读倾向于把焦点放在经典和非经典的文献上,并试图通过阅读通常被忽略的文学作品来发现文学史的新的相关性”(410)。可见,距离阅读的聚焦对象不仅是经典文本,还包括非经典作品,甚至其他非文本文献。通过大规模文本分析,莫莱蒂给大量未读作品赋予新生命,扩大了世界文学整体性的表征基础。按照瑟莱恩(Rachel Serlen)的统计,“距离阅读因而恢复了档案中丢失的99%”(219),揭示不同因素之间的联系,恢复了文学史的全貌。而且,该分析中必然出现的抽象元素提供了一种适合海量文本的新的认识论,它用系统知识取代了文本知识。正是这种系统知识,致使无论是关注文学史还是关注更小的单位,距离阅读都强调对世界文学历史实验的宏观尺度。换言之,通过与文本保持距离,批评者通过抽象还原的方式,客观把握了文学史的整体脉络,产生新的认知和知识,用洛夫(Heather Love)的话说,“距离阅读拒绝丰富的文学文本,更倾向于支持大规模的知识生产”(374)。距离阅读变成一种借助于实证试错的系统知识生产,而非传统的审美体验。很明显,莫莱蒂的目标不只是粉碎各民族经典,而是力图粉碎经典法则,拓展文学概念,甚至把他的研究导向对世界文学,乃至文学史边界的破除。
第三,它是协作阅读。毋庸讳言,过去两百年的人文学科一直是属于唯一的学者的,文本细读依存于个人对经典作品的解读,其本质是一种个体阅读,但距离阅读是集体阅读,读者不是单一的个人,而是协作的集体,分工合作成为它的必要方式。莫莱蒂说 :“没有集体协作,世界文学就是镜花水月”(“More Conjectures”75)。这种协作性体现在: 其一,距离阅读是“民族文学专家”和“世界文学学者”之间的协作批评。莫莱蒂写道 :“在世界文学体系中,发展只能通过与具体的本土知识的有效协作才能取得进步”(“More Conjectures”78),而掌握“本土知识”的批评者非民族文学专家莫属,世界文学批评变成民族文学专家和世界文学学者的协作批评,如阿拉克(Jonathan Arac)所言,距离阅读的程序是“读者以世界各地语言细心阅读,然后将发现提交给总的综合者”(45)。这在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的思想中得到印证。达姆罗什把世界文学学者分为“专门研究专家”和“总体研究学者”,强调研究方法的不同而非个人身份的差异。任何人都可能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又是从事其他总体性研究的学者(329)。其二,距离阅读是文学学者和非文学学者之间的协作批评。对距离阅读而言,除了文学学者之外,你还“需要一个程序员,一个接口专家,等等”(Sunyer)。因为在现实世界中,人们几乎无法找到一个既熟知社会批评、文学理论、历史知识,又能熟练电脑编程、建模、统计与数据分析的批评者,没有团队的集体协作,批评将无法完成。其三,距离阅读是人类阅读和机器阅读之间的协作批评。虽然材料的筛选分类、阅读程序设计等是由人类完成的,但计算机处理巨量数据材料的运算能力,是人类无法比拟的,距离阅读常借助“计算机处理成千上万的文本”(Schuessler),所以它还是人类阅读和机器阅读之间的协作批评。
第四,它是计算批评。在《距离阅读》一书中,莫莱蒂坦承自己的形态进化论研究已经自动演变成定量数据分析(Distant Reading179)。他认为,“量化分析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计算不是针对一些主要的、快速的变化,而是针对许多更小也更慢的变化”(192)。对这些“更小也更慢的变化”的观测只能在漫长的文学史序列中实现,而对长时段观测最有效的办法是借助网络和计算系统,建立在经验之上的人工调查和数据征集、定量实验,以及假设有效的小范围测定,无法完成莫氏预设的宏观批评任务。正因如此,德鲁克说,定量分析“实际上是一种对文学或历史(或其它)作品语料库的统计整理或数据挖掘”(Drucker),凸显出鲜明的计算批评(Computational Criticism)症候,它“依赖于数字化的数据库,以便揭示类型和作品在世界各地传播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形态,及其发生(或没有)转变的过程”(During35)。距离阅读变成有关文本计算的讨论,它所依赖的机器检索、文本与数据挖掘、视觉化、网络计量和模型分析等,本质上都是计算技术。它采用实验模型展开阅读,重视文学叙事的网络建构和文学批评的数据挖掘。凭借量化计算,莫莱蒂将计算机和统计学引入文学分析中,也将科学技术引入美学形式中。
按照莫莱蒂的说法,距离阅读是文本蓄意缩减和抽象的过程,其表现形式是图表、地图和树图(Graphs
1),通过这种图像形式的量化计算,反映人物关系是如何随时间而变,或者文类在代际之间是如何流变传承的。距离阅读利用电脑来处理大数据,或存储大量信息,其目的是从各种文本、非文本中提取要素,通过大量数据处理来说明文学的形态和结构,以体现文学内部各要素、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复杂关系。距离阅读的创新之处不仅在于它把“数据”“算法”引入文学研究,而且更有意义的是,量化模型成为一种推理和分析形式。由是观之,距离阅读体现了一种实证主义方法论。从莫氏的批评实践来看,受弗莱(Northrop Frye)文学的“自然科学”研究和波普尔的实证主义“猜测-反驳”方法的感召,特别是受实证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沃尔佩(Della Volpe)的重大影响,莫莱蒂认为对科学精神的尊重成为必要,相信我们可以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学得更多(Graphs
2),继而提出距离阅读的方法。距离阅读所表征的方法论实则是挽合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为一体的实证主义实验方法。安德伍德(Ted Underwood)写道 :“距离阅读是通过一系列的测试而出现的,它逐渐将偶然的历史编撰实践转变为一种明确的实验方法”(5)。莫莱蒂借助波普尔的知识考古,运用计算网络,通过假定-证伪的方式,对更新的工具、更大的数据、更远的距离的文学情状做出校验,以实验模型验证文学间的融汇互构和形态演化,完成文学关系网络的建构批评。距离阅读赓续了19世纪以来的科学实证主义传统。虽说诞生于新批评的文本细读也是科学主义的结果之一,但它是立足于语文学的个体整体性,距离阅读却试图在文本与社会、形式与历史之间建立联系,用莫莱蒂的话来说,是一种“没有文本细读的形式主义”。另外,文本细读为实存性世界文学所采用,通过典型文本间的平行比较和纵深影响来讨论问题,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文学科的审美阐释;但距离阅读服务于观念性世界文学,通过对大规模文本的宏观批评来揭示文学形式的缓慢演化,以科学实证的方式建构文学各要素、各环节的关系,形成对文本细读的补充和诘问。
距离阅读是莫莱蒂创造的一个解决文学发展的现实问题的知识革命梦想,试图以不同的阅读方法来解决全球化时代的文学问题,改变时下的批评现状。距离阅读的贡献在于,打开了一个供人讨论的新领域,继而将其对世界文学的理论构想与构想实践结合起来,促使人们“重新定义何为我们所认为的遗产,并要求我们找到新的方法和工具来概念化和管理这些日益增长的物质”(Pauloshea, “How” 86)。更重要的是,距离阅读不仅是一种方法,也是思维方式的革新。无论莫莱蒂个人的研究项目自身如何发展,距离阅读本身显示出重大的意义。它促使批评家,特别是那些自认为博览群书的批评家承认无知,并重新思考他们所做的事情,体现出人们对其认知能力的反思和探索。
三、 数字人文和文学批评的范式转型
据库恩(Thomas Kuhn)所言,范式革命是一种打破那些在一段时期内被公认为普遍问题和解答模式的抽象规则的活动,更是常规世界观的改变,迫使人们抛弃旧有的知识传统,促成观照对象、言说方式和知识结构的转换。不过,这种转换只有在常规范式产生诸多问题时,“时代才会给它的竞争者一个机会”(76),更换工具和方法的时机才会到来。与此类似,距离阅读恰是莫莱蒂在世界文学的整体性批评期待与文本细读的典型性批评实践违和之际创生的具体方法。在此过程中,距离阅读显示出三个向度的革命。
第一,阅读对象革命,即从极少数的经典文本向无限大的档案库转换。如上所述,距离阅读在反对经典细读的过程中擎持以海量文本作为批评对象的观念。从经验来看,莫莱蒂最具代表性的距离阅读范例是《图表、地图和树丛》,通过对国族文学中文类兴替的长时段量化分析,塑造了文学史的抽象模型;其最新论文《灵之舞》以对瓦尔堡(Aby Warburg)《摩涅莫辛涅图集》的“激情程式”(pathosformel)的可视化操作,完成了对20世纪的艺术史批评。这意味着距离阅读已从世界文学、文学,延展到整个艺术领域,其观照对象已从世界文学向全部文学、从经典文本向日常文本转移。如果承认更多的非文本批评资料,如书籍史、出版史、借阅史、翻译史等所具备的合法性,另加大家熟知的已有纸质文本的批量电子化和依托网络创作传播的数字文学的兴盛,更是一个无法估量的文本数量的激增。虽然目前还没有看到莫莱蒂以所有文本为对象的距离阅读,但其大规模文本批评实践表明了建构并处理全数据库在理论上的可能性。
第二,阅读主体革命,即从人类阅读向机器阅读转换。传统批评强调人类对经典杰作的独特体验和理解,但距离阅读代表一种利用计算机、数据库和其他机器智能形式的阅读分析。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从人类阅读到机器阅读的主体迁移,机器阅读参与并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人类阅读,人类从阅读批评中逐渐隐退。这是阅读史上从未有过的颠覆性变革。阅读主体的技术性转移引发了一系列变化: 文学及其批评的人文学科特征弱化,不再需要文学研究专家,预测假设和采样验证成为主要特征,可比性依靠电脑量化分析获得,等等。虽然在机器阅读中,机器的生产、程序的设计等事项都是出于人类智识的决定,但随着机器神经元系统的养成和深度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几乎无人敢否认人工智能这一后人类形态超越并替代人类的可能性和它所潜藏的危险,这让阅读主体的转变充满了刺激和挑战。
第三,阅读方法革命,即从细读批评向算法批评转换。如前文所述,距离阅读是网络信息和计算分析技术发展的自然结果。它常以文本外观察的客观方式,宏观探讨人、事、物在时空中的演化,勾勒文学的主要发展趋势和重大变迁,或是寻绎文本、社会的结构与关系,是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常见的阅读方式。在处理文学问题时,传统的人文阅读致力于阐释角度的变化,坚持细读批评,但莫莱蒂却将科学技术引入文学批评,试图养成利用现代科技解决批评问题的习惯,并将其发展成一种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和讨论的学术问题,他的著作助推计算批评和更加普遍的数字人文变成一场真正的知识运动,加速了数字人文范式的形成,与传统人文批评形成良性互补。莫莱蒂兴奋地说 :“在过去几年,文学研究见证了所谓的定量证据的激增。当然,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过,但未能产生持续影响。这次情况有所不同,因为我们拥有了数字化的资料库和自动化的数据检索技术”(“Network Theory”80),瞬时就能处理过去几个月或数年工作的调研结果。文学批评变成“一种依靠巨大的信息共享的语料库的合作学术研究形式”(Batuman),不仅取消了单一、直接的文本阅读,聚焦全部作品和整体文学史的建构,而且以新的理论体系和阐释框架,塑造了一种合作学术的田园牧歌。
可以说,距离阅读所表征的阅读对象、阅读主体和阅读方法的革命分别回应了文学批评中最为关键的“读什么”“谁来读”“怎么读”的问题。它以针对巨量档案数据库、机器阅读和计算批评改变了传统的人文阅读常规,开启了数字人文批评的先河。陈静说 :“数字人文之所以不同于传统人文研究之处,正在于‘数字’背后代表的是一批学者试图以科学方法介入人文研究从而建立新的认知方式、新的研究范式的自觉意识和实践”(陈静)。莫莱蒂以距离阅读为表征的数字人文批评也不例外。在2014年《距离阅读》获得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奖后,罗斯曼(Joshua Rothman)写道 :“从某种意义来讲,距离阅读获奖的价值在于新的批评范式的胜利,在文学批评的餐桌上获得永久席位”(Rothman)。罗斯曼所谓的新范式即数字人文。莫莱蒂以距离阅读表征的数字人文批评得到了主流学界的认同,距离阅读被当成数字人文批评的转折点,莫莱蒂也被看作数字人文批评的奠基者。如果细数当今的数字人文学者,大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莫莱蒂文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在从传统人文阅读向数字人文范式的转换中,莫莱蒂有意无意地规避了数字人文批评的主要缺陷,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了数字人文批评的内核,凸显出非凡的智慧。
一是奉行传统人文批评的标准,摆脱机器和技术黑箱的制约。虽说有关数字人文的争议很多,但通过数字化和数据化的“人文计算”(humanities computing)无疑是其最突出的特征。人文计算本身会让人看到一种巨大的、社会的、客观的文学,但也会造成人类对机器运算的迷恋。同时,这种借助机器存储、网络检索和量化分析的计算往往难逃将文学批评“黑箱化”的诟病。简言之,由于计算程序的背景化,数字人文的计算往往变成只见最终结果,而无法展现其中间运算过程的暗箱操作。可是,从莫氏的批评实践来看,他不但祛除了对机器的依赖,揭开了黑箱的盖子,抵达人文阅读奉行的批评标准,而且发现了传统批评不能洞察的问题。
在《网络理论,情节分析》一文中,莫莱蒂坦言论文中的人物关系图是花费四小时手工绘制的结果,根本没有使用网络分析软件和工具,甚至认为表格和图形都不重要,因为在他看来,人文学科亟需宏大的理论和大胆的概念,数字人文批评的重点是能够创造高层次的理论和概念,“一份报纸里面应该有柱形图,但文学批评的论文里却未必需要”(35)。因此,在该文中,莫莱蒂不仅在《哈姆莱特》的网络模型中重新发现了霍拉旭的中心地位和叙事功能,修改了现存的批评结论,而且通过网络模型将线性的情节关系视觉化(时间空间化),将文体作为情节的一个功能而整合进情节,建构情节-文体的连续统一体(plot-style continuum)(“Network Theory”94),在理论和概念上得到双重突破和创新。
莫莱蒂在数字人文批评中注重揭示批评意图和操作程序。海勒斯(Katherine Hayles)写道 :“阅读总是由复杂多样的时间活动构成,但在由字词、图片、声音、动漫、图像和字母构成的21世纪阅读环境中,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何为阅读,以及它是如何操作的”(79)。操作是人们实施数字人文批评的具体行为。在《操作,或测量在文学批评中的功能》一文中,莫莱蒂自言该文的目的是通过测量文学形式,在理论概念、量化形式与文本之间建立关联性(“Operationalizing”104)。在他看来,操作揭示了数字人文批评的绝对核心过程,也检测了现有文学理论的效能,不仅利于改变现有的文学理论,而且利于改变文学史。莫莱蒂以《淮德拉》和《安提戈涅》为例,通过精确统计人物话语的体量和话语交互作用的数据,逐一展示了对“人物空间”和“悲剧冲突”的操作步骤和图像解析过程,一方面发现了诸如冲突和叙事网络的关系问题,得出“冲突产生于网络中心”等拓展传统认知的结论,另一方面在测量与文学概念、数字工具和档案材料之间建立了联系,借助大型语料库及其话语分析工具,以将概念转换为经验数据的方式,打开了人文计算的暗箱,强化了数字批评的有效性。
二是以问题性为核心驱动,寻求文学批评的新可能。由于强调机器计算,数字人文批评热衷于编写各种算法和可视化模型,有忽视批评的问题性之嫌。虽说数字人文批评的效果取决于算法的有效性,但如果没有学术问题予以驱动,它将流于“工具性”的苛责,很难反思自身,生产知识。但汉松曾说 :“算法批评的意义恰恰是利用人工智能,促使批评家发现之前使用别的方法未曾觉察的问题,帮助批评家阐释文本并解析出新的意义”(但汉松)。虽然我并不同意他所谓的数字人文批评的目的是阐释意义,但我认同他对数字人文中问题性的强调。反观莫莱蒂从世界文学到数字人文批评的演进,不仅凸显出“计算”的症候,更呈现出鲜明的问题意识。
无论是文本批评(textual critics)、电子编辑(electronic editing),还是图像分析,莫莱蒂都是为了解决文学批评中面临的关键问题。比如,观念性世界文学是为解决实存性世界文学批评名实不副的问题;距离阅读是为解决文本细读对整体性批评的失效问题;数字人文的一系列操作,如对7000多英国小说标题的流变研究、对《哈姆莱特》等作品的网络分析等,一方面是为检验量化分析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则尝试建构自己的文学整体性批评梦想。莫莱蒂立足具体的学术问题,通过务实的批评实践,既得出可靠的结论,又赢获了学界的认可。正因如此,当人们把莫莱蒂视作数字人文批评的代表人物时,莫莱蒂却自言,“数字人文这一术语没有意义”(Dinsman and Moretti, “Digital”)。
对问题的重视不仅形成莫氏扎实的批评逻辑,而且拓展出新的批评领域,提出更多的新问题,引发更深的思考。例如,就阅读对象而言,距离阅读意味着取样范围的扩大,那么取样范围变化之后对文学批评有何影响?巨量文学档案对文学批评意味着什么?取样对象越大就意味着越能得到有效的批评结论吗?这种结论和传统批评有何不同?对数字人文批评的结论判断还应坚守传统批评的标准吗?如此种种,不一而足。霍基(Susan Hockey)曾说 :“人文计算不得不包含‘两种文化’,即将科学的严格、系统、明确、程序的方法特征带到人文学科中,来解决那些迄今为止大多以偶然的方式被处理的人文学科问题”(174)。也就是说,批评者既要规避将数字人文“工具化”的简化倾向,又要致力将数字人文导向人文研究。莫莱蒂以距离阅读开启的数字人文批评范式,提醒我们必须在强烈的学术真问题的前提下应用计算法则,这样才能避免将计算工具化的宿命,进而探索计算在思维改造、文学认知等方面所带来的深层变化。
三是自觉强化边界意识,定位数字人文批评。当前数字人文批评中出现了“我不跟就会死”(follow-us-or-die)的狂热现象,似乎数字人文是包治百病的圣药,但忽略了数字人文范式并非传统人文阅读范式的替代,而是一种有效补充,适用于世界文学的整体性、长时段文学史、文类概念演化等抽象批评,而非一切对象。苏珊·朗格说 :“不管是在艺术中,还是在逻辑中,‘抽象’都是对某种结构关系或形式的认识,而不是对那些包含着形式或结构关系的个别事物(事件、事实、形象)的认识”(156),其实质是批评(认识)方法的不同。事实上,莫莱蒂从未说过数字人文是传统批评的替代品,反而强调二者是不同的方法,代表不同的范式。莫莱蒂说 :“我在《距离阅读》中采用的批评方法所做的研究,完全不同于在《资产阶级》中采用的批评方法所做的探讨。在写作《资产阶级》这样完全或是几乎没有数字人文方面内容的著作时,我发现自己根本无法运用计量批评的方法”(Dinsman and Moretti)。也就是说,以距离阅读为代表的数字人文批评,并非是适用所有文学批评的万能方法,而是针对具体问题所采用的最合适的方法。如果无视这种差异和定位,数字人文将潜藏着从文本细读所塑造的“文本拜物教”转向距离阅读的“技术拜物教”的风险。
而且,数字人文批评应定位于寻求新的批评结果。莫莱蒂说 :“我一直致力做的都是给出说明,而不是作价值评判。另一方面,我也不确定对于整个社会、整个世界而言,说明是否比价值评判更重要。我想,对于那些致力于认识事物是如何运作的人而言,说明更重要”(Dinsman and Moretti)。且不说莫氏观点的正确与否,它起码表明,新的批评范式应该产生新的批评结果,并且对其效果的评价,也只能以新的标准予以衡量。布伦南(Timothy Brennan)、阿兰·刘(Alan Liu)等人强调,要让数字人文重回传统人文政治研究和审美意义阐释的老路。但我以为并不妥当。毕竟,新的范式采用新的认知方式,势必产生新的批评结果。如果真要回到原来的路径,那又何必使用新的范式呢?最重要的是,数字人文的范式变革既要“找到对于文本分析效果更为关注的读者”(Ramsay17),又要同时注意培养批评者和阅读者群体。
从实存性走向观念性,从文本细读走向距离阅读,从审美阐释走向计算批评,莫莱蒂以其革命性的勇气将传统人文批评推向数字人文的批评范式,展示出清晰的演化逻辑,充满理想色彩。在舒斯勒(Jennifer Schuessler)的访谈中,莫莱蒂说 :“我宁愿做一个失败的革命者,也不愿做一个从未尝试过革命的人”(Schuessler),对尝试计算批评毫无悔意。其实,学术研究本就始于一个可能的故事,而终于一个真实的故事。莫莱蒂由世界文学引发的文学批评的数字人文转向到底结果如何,还有待检验。但像莫莱蒂这样的学者,实际上把自己交给了知识和直觉,交给了前途未卜的未知领域。他或许已下定决心,将会用自己的生命和学术信念探索未知的领域甚或禁区,激发人们的学术好奇心,解密文学规律,为文学祛魅。
注解[Notes]
① See Jon Saklofske, Estelle Clements, and Richard Cunningham. “They Have Come, Why Won’t We Build It? On the Digital Future of the Humanities.” Ed. Brett Hirsch, et al..Digital
Humanities
Pedagogy
:Practices
,Principles
and
Politics
. Cambridge: Open Book Publishers,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