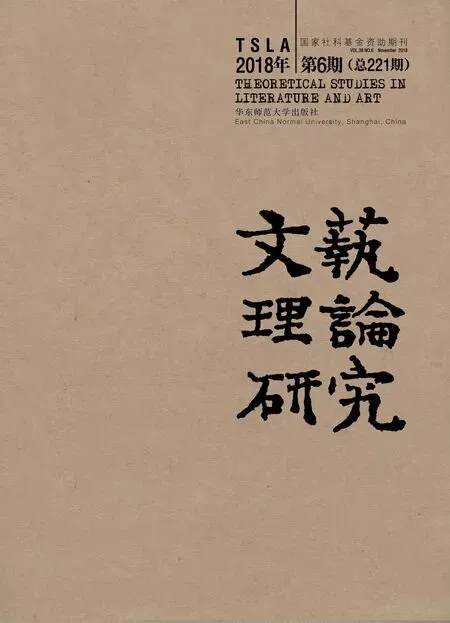音乐化: 徐志摩的诗歌美学
陈历明
五四时期,文学革命主要是作为语言革命的手段,当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作为各类文体的主要媒介,其逻辑性、通俗性以及散漫性在诸如小说、散文、戏剧等叙事文体的表达中并无多大的龃龉,对于细微的刻画描摹等方面反而有着文言所缺乏的优势;但对于特别追求语言精练化、意象艺术化、意旨多元化、结构音乐化、意义追求言外之旨的诗歌来说,五四时期白话新诗的基本主张——“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胡适,“谈新诗”)——给新诗的写作最直接的负面影响就是语言的浅白、意义的显豁、音韵的流失、节奏的散漫无羁。白话入诗,在很大程度上基本就是简单地化约为分行的白话。在救亡和启蒙的双重变奏语境中,以“我手写我口”为大旗的如此诗界革命已成不可逆转的大势。
不过,这一非诗化倾向还是受到了坚守诗歌的美学基本原则立场的梁实秋等作家、学者的质疑,他们批评唯白话是举的白话诗 :“白话诗必须先是诗。否则但是白话仍然不能成为诗”(梁实秋,“关于新诗”227);然而“我们的新诗,一开头便采取了这样的一个榜样,不但打破了旧式的格律,实在是打破了一切诗的格律。[……]我们的新诗,三十年来不能达于成熟之境,就是吃了这个亏”(228)。怎样用白话做成富有诗意的诗是现代诗人面临的最大挑战,他们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当现代诗抛弃了格律、文言文和词藻,它如何被认可为诗?没有古典诗歌那些长久以来经典化的语言和结构特征,现代诗人如何证明自己的作品是诗?”(奚密73—74)。
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诗歌的音乐性的不足或缺失问题。对此,夏济安在50年代就指出,“现在新诗人最大的失败,恐怕还是在文字的音乐性方面,不能有所建树”(75)。学者诗人郑敏半个世纪后亦呼应了夏济安的批评,认同“白话新诗却至今没有解决它的音乐性问题”(郑敏,“我与诗”54),为此感到非常遗憾。这里所指的音乐性,主要包括音节、音韵、律动与(结构)再现等与音乐写作紧密联系的几个方面。
一、 诗歌与音乐之关系
音乐无疑是各种艺术追求的素养,惟有臻于音乐的境界,艺术才能具有更本真的魅力。著名作家瓦尔特·佩特曾洞见地阐明音乐之于绘画和文学的不可或缺,指出“一切艺术总是以趋近音乐为旨归”(Pater135),因为“音乐最完美地实现了这一艺术理想,这一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在其最圆满的时刻,目的与方法、内容与形式、主题与表达之间差异消泯,且互相完全渗透融合无间,因此,所有的艺术或许都可以被认为不断趋近且渴望达到这种完满的状态。与其说在诗歌中,不如说在音乐中,能够发现完满艺术的真正典型或尺度”(138—39)。
毋庸置疑,诗歌与音乐的关系更是密切,甚至“诗没有音乐就不成为诗”(马利坦229)。这一点无论中西,自古皆然,在我国尤其如此,我们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首先就是可歌的诗 :“诗三百篇皆可歌可颂可舞可弦”(郑樵,《六经奥论》)。在古代中国,音乐和诗歌一直相伴相随,相得益彰 :“诗者宫徵之所谐,管弦之所被也”(朱谦之18);“凡乐辞曰诗,诗声曰歌”(刘勰65)等等,无不将诗歌与音乐并称。简言之,从诗三百到乐府,再到唐诗、宋词、元曲、明剧,诗与音乐总是如影随形,须臾难以分离,这一传统可谓渊源有自。但是诗歌一旦走向白话的道路,似乎注定要越来越走向去音乐化的歧途。朱谦之曾指陈胡适提倡白话入诗而忽视音乐,批评他们“主张‘废曲用白’,要把文学和音乐脱离关系而独立发展。他们的根本错误,在没有认清文学的起源是音乐的,而文学作品的本质属性,尤其就是音乐的”。最终导致其散文化的弊端 :“他们没有认清中国文学的定义,没有认清纯文学和散文的不同,所以结果是太把文学散文化了。其实散文决不是真正表现情志的文学,更不是文学的极点,如他们极力提倡散文诗,以为散文诗才是完全脱离音乐拘束的自由诗,其实自由诗虽反对定型的音节,但决不是什么散文体的,如法国象征派诗人所提倡的自由诗,才是真正的音乐文学哩!”(朱谦之20)。
尽管唐代以来诗与歌就基本上已经截然两途: 一条是诗与歌继续相辅相成,另一条则是诗与歌各自为政;然而,诗与歌在本质上仍一直保持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那种或隐或显的关系,远非完全各不相交的并行线。就此而言,无论是对古典诗词重音乐的歌唱性诉求的赞许,还是对白话新诗轻音乐的散文化倾向的诟病,朱先生的观点自有其道理,也点中了初期白话新诗的软肋。毕竟,古典诗词的音乐化诉求和现代新诗的散文化倾向之间的对比是比较明显的。朱先生的批评如果仅指白话新诗初期“去音乐化”的散漫无羁,倒是颇为切中要害的,但是如果用来概括20世纪20年代后以徐志摩和闻一多为代表的新月派诗人,就不无偏颇了。
为何白话诗难为诗?换言之,白话诗何以难以取得“诗歌”的身份?其原因除了早期新诗语言过于直白松散、意境浅露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缺少音韵、节律等音乐性问题。后继的诗人对此已有一定的意识,并且在写作中注意到音节等方面的音乐性构建。1928年,时为《小说月报》编辑的叶圣陶,在收到戴望舒的《雨巷》一诗后,称许其“替新诗底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杜衡,“《望舒草》序”;梁云52)。究其本质,就是新诗的音乐性问题。不过,其后新诗的音乐性无论在创作实践还是理论探讨都没有在此基础上取得令人期待的成绩。
新诗的音乐性探求,其实并不始于戴望舒,徐志摩在翻译与创作中对音乐性的关注还要早于前者。卞之琳曾洞见地指出,徐志摩的诗歌“最大的艺术特色,是富于音乐性(节奏感以至旋律感)”(“《徐志摩选集》序”222)。但对于其音乐性的具体体现,却语焉不详。八十余年来,学界对此的研究基本上都停留在诸如“复沓”“反复”“回环”等片言只语的印象式的感悟层面,既无意证实,亦无因证伪,深入的文本细读基本付之阙如,对新诗的音乐美学追求自然无法获得全面深入的梳理和总结。长期以来对新诗的实践与批评因为缺少这一重要环节而导致我们的现代诗歌写作与评价都难以层楼更上,这似乎更回应了郑敏所言“汉语新诗始终没有在母语音乐性上有所突破”的批评(“试论汉诗”88)。虽说不乏道理,起码徐志摩却是个例外。其音乐性最明显的表征,借用音乐中的术语来说,就是表现各异的“再现”。
“再现”(recapitulation)这一音乐术语,简言之,表示已经呈示的主题或其他音乐素材在新的乐段之后的重新出现。如三部曲式(ABA)中主题A在B之后再次出现。根据其不同的形态,可分为完全再现、局部再现以及变奏再现等。在大型音乐作品中,特别指奏鸣曲式中一个乐章或乐段包含着三个次乐段(subsection): 呈示部(exposition)、展开部(development)和再现部(recapitulation),此外,呈示部前可能会有一个前奏,再现部后加一个尾声(coda)。呈示部提出两个不同的对比主题,音乐以主调从主题一过渡到属调的主题二;展开部包含所有主题的扩展,呈示部直接呈示主题,而展开部则通过作曲家选择各种组合的旋律片断,协和快速变化、对位处理以及其他技巧,常常把这些主题拆成种种片段,然而,又必须按再现的要求回归主调;再现部在主调上重复呈示部的主题,稍有改变,但秩序相同,首先是主题一,然后是主题二(Ammer388)。
音乐中都不可缺少诗的言说,而诗歌的基因图谱中又总不乏其音乐的传承。其中的许多表达方式,既是诗歌的,同时也是音乐的。音乐中最常见的这种再现,完全可以用来分析许多具有类似结构的中外诗作(包括新诗)。如果说徐志摩的诗歌最大的艺术特色就是富于音乐性,那么,其音乐性最突出地表征为音乐再现艺术的运用,主要体现为完全再现、部分再现和变奏再现。本文拟就此通过实例分别进行论证,并尝试论述其音乐性的师承以及音乐诗学的内涵,借此为新诗的音乐性正名。
二、 完全再现
完全再现是指诗歌中的一节(或以上)的乐句(即诗行)从文字到结构完全重复再现。苏珊·朗格说过,“当一个诗人创造一首诗的时候,他创造出的诗句不单纯是为了告诉人们一件什么事情,而是想用某种特殊的方式去谈论这件事情”(《艺术问题》140)。其中一个重要诉求就是求得音乐(旋律)的美感,因为诗“在有机统一性和节奏方面,它有点像音乐”(155),而音乐中常见的表现方式就是再现或曰重复。概言之,它能重新唤起并加深对主题意象的同情与共鸣,切合了人的生命节奏与自然的季节更替等自返性的律动,给人以回环往复的圆满感,易于勾起某种起点即终点、终点即起点的或痛或快的萦回记忆、幻想与期待,同时也能满足人们期待美好重现的轮回感与审美诉求。
下面,我们来看看徐志摩在诗歌写作中完全再现的运用。先看《盖上几张油纸》(《晨报》):
一片,一片,半空里
掉下雪片;
有一个妇人,有一个妇人,
独坐在阶沿。
虎虎的,虎虎的,风响
在树林间;
有一个妇人,有一个妇人,
独自在哽咽。
这首诗共十节,这是首尾的四节。很明显,结尾两节完全再现了开头两节所呈示的主题意象及其结构,属于完全再现。这种反复的诉说,给人以一唱三叹那萦绕胸中、挥之难去的伤感。这种反复萦绕的音乐手法,在特定的情景下,容易勾起读者人同此心的共鸣与悲哀。这种再现富于音乐的歌唱性,表现出叙述者给予叙述对象人生的同情,音乐表现人生,“音乐有着意味,这种意味是一种感觉的样式——生命自身的样式,就像生命被感觉和被直接了解那样”(Langer31)。不过,这种完全再现手法,在徐志摩的诗歌里并不常见。其他例子还可见《草上的露珠儿》(《徐志摩全集》卷47—12)。尽管在音乐中,完全再现并不少见,但在诗歌创作中,诗人一般比较慎重。必要营造这种反复吟咏的意境时,却能收到良好的艺术效果。否则,则容易流于单调,因此,相比其他两种,古今中外的诗人并不多用此法。
徐志摩使用最多的还是部分再现和变奏式再现这两种。
三、 部分再现
部分再现分两种,其一是在同一诗节中部分乐句(即诗行)完全再现(或曰重复);其二是一节诗歌中部分乐句(诗行)在另一节诗中完全再现(重复)。这种手法在徐志摩的诗歌中写作中比较常见。先看《夏日田间即景》(《时事新报》):
柳条青青,
南风熏熏,
幻成奇峰瑶岛
一天的黄云白云,
那边麦浪中间,
有农妇笑语殷殷。
[……]
南风熏熏,
草木青青,
满地和暖的阳光,
满天的白云黄云,
那边麦浪中间,
有农夫农妇,笑语殷殷。
这首诗初刊于1923年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全诗共四节,以上所引为首尾两节。这两个诗节中,除三、四行不同外,第一、二、五、六行跨节对应再现,仅仅是一、二行换了一个位置而已,属于前后的部分再现。当然,也可以将第四节视为第一节主题及其结构的变奏式再现,因为它们的结构一致,语句基本相同,只是其中个别词汇稍有变化。容易给人一种可以回放的欢快感,一种回环的美,体现了诗人对这种自然的田园生活的赞美与向往,以及自然美好生活的反复与回归的期待。类似的手法也见于《一家古怪的店铺》(《晨报》)。本诗初刊于1923年,共五节,这是首尾两节,除了首行的不定指改为定指外,几乎就是完全的再现。不定指的置换,产生了一种由远而近,由疏而亲的效果。世界沧海桑田,但在此却是时光停滞,似乎从一开始他们就与时光一样苍老,这一再现构成一种新与旧的强烈反差,凸显了一种历史的轮回、无奈与沧桑感。
与《夏日田间即景》中诗节的前后两部分再现不同,徐志摩的诗歌中还有前中两部分的叠句再现,最后的结句变奏式再现,这是音乐写作中比较常用的再现方式。《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新月》第1卷第1号)就是这种跨诗节的叠句在四行体的突出例子: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在梦的轻波里依洄。
[……]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黯淡是梦里的光辉。
这首诗在结构上不脱《诗经》的遗风。每一节前三行完全再现/重复,但是把梦作为一个主导音乐动机,看似单调之中却有变化,适合表达那种绝望与希望反复纠结、相伴相随的心境。小而言之,这是诗人所在的“新月”的态度 :“成见不是我们的,我们先不问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功利也不是我们的,我们不计较稻穗的饱满是在那一天。[……]生命从它的核心里供给我们信仰,供给我们忍耐与勇敢。为此我们方能在黑暗中不害怕,在失败中不颓丧,在痛苦中不绝望”(徐志摩,“创刊词”)。人生如梦,希望与绝望同在,幸福与痛苦同在,黑暗与光明同在。哪怕仍然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也无法左右风朝“哪一个方向吹”,仍然徘徊行走在梦中,无论现实如何严峻、残酷,梦在希望在,黯淡也会成为照亮“梦想的光辉”。大而言之,谁又能否认,这何尝不是一种积极的人生之态?另如《黄鹂》(等候它唱,我们静着望,/怕惊了它。但它一展翅,/冲破浓密,化一朵彩云;/它飞了,不见了,没了——/像是春光,火焰,像是热情(《新月》)。这首短诗,只有最后一句重复再现,每行基本都是由三个音尺构成,形成一种类似轻快的华尔兹节奏,它由黄鹂、飞翔、星空等构筑的天空意象,无论是蓄势待发的兀立枝头,还是一飞冲天地展翅云霄,都羽化为诗人眼中那元气淋漓的春光、火焰、热情,回归到诗人充溢的那一行生命之旋律。黄鹂生于尘世而不为尘世所囿,遗世孑立,激情、飘逸而潇洒,切合徐志摩的人生追求。与其说是歌咏黄鹂,还不如说是诗人自我抒怀,自况俊逸如黄鹂那高飞之心。难怪此诗一直是诗人的挚爱。
四、 变奏再现
变奏式再现是指运用各种手法将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句法结构、主题、动机、音型的乐句(诗行)在不同的乐段(诗节)中以大致相同的形式加以变化重复,涉及形式和/或内容的部分被置换,语序的局部调整等。主题结构基本保持不变者可称“严格变奏”;主题结构有所改变者可称“自由变奏”(音乐中还有主题体裁特征有显著变化者,称为“性格变奏”,徐诗中罕见,故从略)。这种大同小异的再现手法同样见于《在那山道旁》(《晨报》):
在那山道旁,一天雾蒙蒙的朝上,
初生的小蓝花在草丛里窥觑,
我送别她归去,与她在此分离,
在青草里飘拂,她的洁白的裙衣。
[……]
在那天朝上,在雾茫茫的山道旁,
新生的小蓝花在草丛里睥睨,
我目送她远去,与她从此分离——
在青草间飘拂,她那洁白的裙衣!
这首诗可称为严格的变奏式再现。与前一诗节相比,后一节结构几乎完全一样,所不同者在于个别词汇的同义同位置换或交替的错位置换。就如人生的聚散,看似相反,其实相成: 相遇和相别,本就在一念一瞬之间,它们互为起点和终点——相遇是相别的开始,相别是此次相遇的终点,又是下次相遇的起点,从形而上的角度看,两者并无截然的区别,只是不同的时空和不同的形式而已。如斯观之,人生的悲欢离合、月亮的阴晴圆缺,原是自然的轮回和宿命。只是,现实中人生苦短,往昔难再,一次相遇和一次相别就可能构成了唯一的一次亘古命运,瞬间即成永恒,又有几个能真正跳出三界超脱五行呢?因此悲喜相生相伴,聚散随时随地,感慨心牵梦绕。多少别离或相逢一旦启程,最终却只能在回忆中坚守,平添无望的惆怅,只能揣着明白当胡涂而已。这种音乐化的再现总是给人某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一种穿越时空的幻想。
徐志摩诗歌的音乐变奏式再现还有多种尝试,如《恋爱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徐志摩全集》卷4345—46):
恋爱他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他来的时候我还不曾出世;
[……]
他来的时候我还不曾出世,
恋爱他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这首诗从内容到结构都有所改变,可视为自由的变奏式再现,类似于一种回旋曲式的结构。徐志摩通过将“恋爱他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他来的时候我还不曾出世”这一主题动机诗行变奏式地再现于首节开头和结束以及尾节结束,诠释了对爱情对人生的领悟,昭示了人生的某种轮回感。有种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谓的人生三境界的况味。从青涩作势到瓜熟蒂落,中间要历经几多沧海桑田的变迁与酸甜苦辣、悲欢离合的蒸馏,才能收获回归自我的人生感悟,生发天凉好个秋的慨叹和洒脱。人生在世,我们每个人几乎都经历过或即将经历这样一个阶段,走过禅修似的人生,才能沉淀有如古代禅师般的顿悟。这种“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人间真象与幻象,给人以世界与人生的轮替感。落实到人生的某个阶段,亦可作如是观。沧海桑田之下那同一个太阳其实每次都是一轮新的太阳,生命的轮回与音乐的回旋,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参照。
当然,更多的是那些具有对称的结构与节奏的严格变奏式再现(如《悲思》),特别是众多融合中西的四行体,以及经诗人创造性转化的西方五行体式(原出英国的Limerick),如《雪花的快乐》(1924年)《呻吟语》(1925年)《青年曲》(1925年)《偶然》(1926年)《最后的那一天》(1927年)等,这些五行体或可称为互文性再现。
徐志摩诗作中最为我们所熟知和喜爱的恐怕非四行体的《再别康桥》莫属了: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新月》)
本诗结构完全一致,首尾两节色彩略加变化,可归为稍加变化的严格变奏,就此而言,与戴望舒的同期作品《雨巷》有异曲同工之妙。与其说这是奚密所谓的这两首诗作属于“环形结构”(Yeh89-113),不如说是一种行诸外在感官、诉诸内在审美的带再现的音乐结构,可视、可感、可心,给人以表里一如的圆融感。可以类比何占豪、陈刚根据传统越剧素材,用西方现代音乐技法谱写的著名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其呈示部和再现部的结构与《再别康桥》非常相似: 呈示部的主题呈现后,展开部进行扩展书写,而在再现部中,独奏小提琴完全再现主部主题,只是加了弱音器而已。其音色的变化却烘托出一种遥远、缥缈、梦幻的星空世界,把现实世界未了的愿望升华至梦幻世界的既了,构成一种由绝望而希望的凄美回环,前后呼应,前世、今生与来生交错,现实、理想与梦幻交织,失望、绝望与希望交汇。以此观《再别康桥》,流淌的是对留存心底之美好的追忆与牵念,一种欲走还留,欲说还休的难舍而又不得不舍的别绪。这种相见时难别亦难的心境,在作别还是带走心中的那片云彩之间,在看似无情却有情的犹疑与洒脱之际,弥漫的却是收放自如与进退失据的两难与眷恋;徘徊在参透与执迷的人生,世间多少风流如梭,谁又能逃出“得之我幸,失之我命”的轮回宿命?这种艺术的变奏再现,无疑能带给读者强烈的情感共鸣。
当然,无论哪种分类都无法穷尽徐志摩的再现艺术,因为他更多的时候都是娴熟地综合运用这几种音乐化形式。以上三种分类主要是基于其内容的,如果按照其织体来分,也可分为完全结构再现、部分结构再现、变奏结构再现,以及用体式相同、意境相似的系列诗歌构成的互文性再现。互文性再现是指用同一结构体式创作的多首诗歌,特别是徐志摩对源出英国的Limerick(类似打油诗)创造性转化的五行体系列。这种诗体集大成者是英国诗人李尔,他以此诗体专门出版了名为A
Book
of
Nonsense
(Lear)的一个诗集,并且一再重版。它一般一、二、五行押韵,三、四行换韵,押韵模式标为: aabba,节奏类型常为抑抑扬格(即两个非重音加一个重音构成一个音步),一、二、五行为三个音步,三、四行为二个音步。徐志摩最知名的被谱成歌曲的五行体就是《偶然》,可谓一种音乐结构性的再现: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晨报》)
徐志摩套用了英语Limerick的韵律形式: 一、二、五行各3个音尺(meter),三、四行各2个音尺。不过,诗人并非机械照搬英诗体式,而是化欧为己,扩充了诗体的表现力: 首先,这种英语诗体一般用于一些幽默诙谐的书写,而徐志摩把它转化为抒写或忧伤或快乐的情诗;其次,英文诗体只有一节,徐志摩则加以扩展,通常为两节的对称结构,以包容更为复杂的情感 :“这该是一首情诗,写的是有缘的邂逅,无缘的结合,片时的惊喜,无限的惘然。语气以退为进,实重似轻,洒脱之中寓着留恋。如果真的在一转瞬间形消影灭,那当然最好是忘掉,又何须记在诗里呢?所以表面上虽故示豁达,内心却是若有憾焉”(余光中179)。
这种诗体深得徐志摩的偏爱,他借鉴此种模式写过好几首新诗,如《雪花的快乐》(1924年)《呻吟语》(1925年)《青年曲》(1925年)《偶然》(1926年)《最后的那一天》(1927年)等。其对称性的结构和灵活的句法,使得这一诗体在诗人的笔下具有了丰富的韵律和音乐感,可以说完成了对英语原诗体的继承和全面的超越。就连对新诗的音乐性多有诟病的郑敏也承认“徐志摩的《偶然》在音乐性和境界上都是与优秀的古典诗一脉相承的”(“中国新诗”69),尽管徐诗的音乐性主要师承的并非中国古典诗,而是外国诗。
这首诗也为当代歌坛所钟爱。上世纪八十年代它曾被香港歌影双栖艺人陈秋霞谱曲,由包括齐秦、齐豫、黄凯芹及作曲家本人在内的不下于30位歌手收入各自的专辑,同时被改编为民谣、抒情、摇滚、爵士、交响、水晶乐等多种音乐风格,还有2014年《中国好声音》节目组决赛歌手重新演绎、演唱、演奏至今;经重新谱曲,又被列为据琼瑶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的插曲,由主角赵薇演唱。这首诗至今传唱传颂不衰,足见一首意境悠远的音乐化诗歌经久不衰的魅力。
五、 徐志摩诗歌的音乐化传承
就徐志摩诗歌中的音乐性问题,卞之琳认为,徐志摩的白话诗,“即便‘自由诗’以至散文诗,也不同于散文,音乐性强。诗的音乐性,并不在于我们旧概念所认为的用‘五七’唱、多用脚韵甚至行行押韵,而重要的是不仅有节奏感而且有旋律感”(“徐志摩诗重读志感”92)。他的诗歌“最大的艺术特色,是富于音乐性(节奏感以至旋律感),而又不同于音乐(歌)而基于活的语言,主要是口语(不一定靠土白)”(“《徐志摩选集》序”222)。认为“他的诗思、诗艺几乎没有越出过十九世纪英国浪漫派雷池一步”,但“妙处却在于徐志摩用我们活的汉语白话写起自己的诗来,就深得他们那一路诗的神味、节奏感”。其所指的“诗艺”“节奏”其实都包含了音乐性问题。卞之琳进一步认定这种变奏式“叠句或变体的叠句”,不仅见于外国诗,也见于我们的《诗经》(“徐志摩诗重读志感”93)。然而卞之琳对徐志摩诗歌中的音乐性问题,也只停留在印象式的片感,并没有寻求坚实的文本证据来进行论/据的互证和系统的梳理,因而难免流于泛泛之论。而学界对此亦重视不够,扎实研究因而基本付之阙如。
徐志摩诗歌中这种音乐化的诉求,一部分的确来源于中国古典诗歌特别是《诗经》这种乐经中,正如卞之琳和郑敏所指出的那样;另一部分则要在其所阅读、模仿或翻译过的英语诗歌中寻找,后者影响更为深广。《偶然》自不必说,上文所引的《恋爱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中的音乐化再现方式就与他约1924年翻译过的哈代的《多么深我的苦》(“How Great My Grief”) 极为相近:
多么深我的苦,多么稀我的欢欣,
自从初次运命叫我认识你!
——这几年恼人的光阴岂不曾证明
我的欢欣多么稀,我的苦多么深,
记忆不曾减淡旧时的酸辛,
慈善与慈悲也不曾指示给你
我的苦多么深,多么稀我的欢欣,
自从初次运命叫我认识你?(《徐志摩全集》卷7237)
照哈代的原诗中,诗歌的开头和末尾两行(除一处标点外)完全再现,主题动机“How great my grief, my joys how few”(我的苦多么深,多么稀我的欢欣)构成了一种名为“交错配列”(chiasmus)的修辞结构,又在中间予以部分再现。在徐志摩的翻译中,中间却加了一点变化: 将开头的“多么深我的苦,多么稀我的欢欣”换成“我的欢欣多么稀,我的苦多么深”。类似一种加花的变奏,再加上他将这一主导音乐动机在诗歌尾部的再现调整为“我的苦多么深,多么稀我的欢欣”,还原了这个交错配列的句法结构,使得全诗在节奏上比原诗更加灵动律感,节奏整饬而不乏变化,首、中、尾交相呼应,有一种循环的圆满,非常富有音乐性,类似于音乐的回旋结构: A-B-A-C-A。他的翻译并非寻求机械的对等,而是巧妙地赋予了自己的创造性,从而使原作之花在目标语中获得了更新更美的绽放。
类似的变奏式手法,还可以在徐志摩翻译的哈代的《对月》(《新月》第1卷第1号)一诗中见出。这首诗歌每一节的最后一行分别与各节的第二行(第三节中的第三行)分别形成变奏式的再现,其主导动机略加变化。而类似我国古典诗词中的叠句(再现)的,有徐志摩翻译的哈代的另一首作品《公园里的座椅》,这是其中第一节:
褪色了,斑驳了,这园里的座椅,
原先站得稳稳的,现在陷落在土里;
早晚就会凭空倒下去的,
早晚就会凭空倒下去的。
这种常见于音乐中的叠句的运用,与我国的《诗经》颇有相似之处。卞之琳也很肯定地认为,徐志摩这些手法,早就见于《诗经》中 :“叠句或变体的叠句,也不是歌曲里才有,外国诗里才有,看看我国《诗经》有没有?”他接着还对某种反对新式音乐性的质疑提出反质疑 :“难道我们写新诗用这一套就是浪费吗?精炼,并不在于避免这种重复。节奏也就是一定间隔里的某种重复”(“徐志摩诗重读志感”93)。在此,我们抄录《诗经》中的几首诗作为佐证:
羔羊之皮,素丝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羔羊之革,素丝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缝,素丝五总。委蛇委蛇,退食自公。(《羔羊》)
殷其雷,在南山之阳。何斯违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归哉归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侧。何斯违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归哉归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违斯,莫或遑处?振振君子,归哉归哉!(《殷其雷》)
的确,卞之琳所谓的“完全的叠句”(即完全再现)以及“变体的叠句”(变奏式再现),除不见于《诗经》中的《周颂》和《商颂》外,无论是《国风》中的《关雎》《桃夭》《芣苢》《羔羊》《殷其雷》等,还是《小雅》中的《菁菁者莪》《鱼藻》《庭燎》《鹤鸣》等,抑或《大雅》中的《旱麓》《文王有声》《既醉》《凫鹥》《泂酌》等,以及《鲁颂》中的《有駜》《駉》《泮水》等等,这些诗篇中都不乏其例。不过,从这些诗歌的结构来看,这些叠句几乎都只是出现在每一个诗节(或乐段)中,基本上都属于单乐章或完全重复的单部曲式,适合简洁精炼的中国传统宫、商、角、徵、羽的五声调式。从诗三百到唐宋诗词、元明曲剧,都是如此,基本不外单一的完全对称或准对称结构,这些作品有色彩、风格的嬗变,并没有在结构上的革命性变化(如现代西方音乐的复调结构,或交响奏鸣曲式结构),缺乏现代音乐中多转调、对比的附歌(refrain)曲式,更谈不上有呈示部、展开部和再现部组成的三部曲式。亦即,徐志摩《再别康桥》等这种带再现的现代三部曲式,并不见于《诗经》或其他中国古典诗歌中,而更接近于他所翻译的布莱克的《老虎》,只不过徐志摩的变奏手法更加丰富而已。由此看来,无论是卞之琳还是郑敏的说法,都属于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种更复杂的结构曲式既有对比也有(变奏式)再现。仅就尾行的重复再现而言,我们的《诗经》中比较常见,西方现代诗歌也是如此,既有哈代的“A Broken Appointment”(《失约》)那种首尾两行的再现(从略),也有雪莱的《哀歌》等。
哈代和雪莱是徐志摩最钟爱、也是受其影响最多的两个诗人,徐志摩很可能读过这两位诗人深受选家青睐的这些作品。他曾于1924年撰文评介哈代的诗歌,认为“哈代与史文庞都是孤高的歌吟者,他们诗歌的内容既与维多利亚主义分野,他们诗歌的形式也是创作。哈代最爱卫撒克士民歌的曲调及农村的音乐,他从小就听熟的,后来影响他的诗艺甚深”。“他诗段变化(Stanzaic variation)的实验最多,成功亦很显著,他的原则是用诗里内蕴的节奏与声调,状拟诗里所表现的情感与神态”(“汤麦司哈代的诗”)。哈代丰富的诗体变化也直接影响到徐志摩翻译的选择以及多种诗体的创作实验: 徐志摩的诗歌翻译中,哈代的作品最多。如上所述,哈代对诗歌创作中的音乐手法也在徐志摩的翻译与创作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朱自清认为徐志摩在创作中尝试的诗体的确最多,其中就不乏音乐化的诗体形式。
徐志摩还翻译了布莱克的《老虎》(“The Tyger”)这种严格变奏式再现的诗作:
猛虎,猛虎,火焰似的烧红
在深夜的莽丛,
何等神明的巨眼或是手
胆敢擘画你的惊人的雄厚?(《诗刊》)
这里,无论是原文还是译文,诗歌的第一节和最后一节只有一个词“Could”(能够)换成“Dare”(敢于)的不同(“骇人”和“惊人”在原文中是同一个词“fearful”),可归为严格变奏。这种变奏式再现与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这种自由变奏式再现比较接近: 主导动机不变,个别音符有变奏(当然,在《再别康桥》中,首尾两节的变化更丰富一些),尽管这首译诗的正式发表是在《再别康桥》之后,但不足以否定徐志摩所受布莱克的影响与启发;而这种影响与启发却丝毫无法遮蔽诗人创造性的融会贯通。类似的结构性变奏手法还可见于布莱克的“To Tirzah”等。此外,徐志摩的音乐化诗歌创作还有一个重要来源——泰戈尔,特别是后者的变奏式的音乐句法及其旋法,也可以明显见出其影响。
徐志摩在选择翻译的诗作中,特别钟情于那些音乐性强的作品,这当然是他诗学观的具体体现。他曾将自己与诗歌结缘、与外国诗人结缘归为“偶然”而非“约会” :“文学本不是我的行业,我的有限的文学知识是‘无师传授’的。[……]柏拉图是一次在浴室里忽然想着要去拜访他的。雪莱是为他也离婚才去仔细请教他的,杜思退益夫斯基,托尔斯泰,丹农雪乌,波特莱耳,卢骚,这一班人也各有各的来法,反正都不是经由正宗的介绍: 都是邂逅,不是约会。”(“济慈的夜莺歌”)。
尽管徐志摩转入诗人这一行有一定的偶然性,所遇到的外国诗人也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这种看似偶然的背后,却是他的个性使然,因而有其必然。从相遇到相知,总是一个相互寻找的过程。读者寻找艺术、艺术寻找读者,这总是一个循环的双向过程。诗人那种审美的期待实际上是一种“前设计”,它在审美的寻找和理解中,一直被审美主体所修正。借用伽达默尔的话说,这也是一种“视域融合”(Gadamer367): 视域并不是封闭的,阐释者总是在不断扩大自己原有的视域。艺术文本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由特定历史存在的个人所创造,而审美主体在理解艺术文本时又有着自己特定的视域,它同样由历史语境所赋予。审美寻找与理解的最终实现就是这两种不同的视域的相互融合,形成一种新的视域,这一新视域又会成为寻找或理解新的艺术文本的出发点。如果“所有这种理解最终都是自我理解”(251),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所有的寻找都是自我寻找,所有的邂逅都是自我的邂逅,他们最终都指向主体自身。徐志摩的这些邂逅其实都是其内心诗学、美学诉求的对象化与现实化的结果。这是一种邂逅的约会,这些带有前见甚至偏见的作家作品其实就是徐志摩的前见与偏见的外化与期待,偶然遇到恰当的时机就会一拍即合,质变为相互一见钟情的必然。舍此,我们便无法解释,为何在浩如烟海的世界文学家及其作品中,徐志摩偏偏仅取此一瓢饮?
除了个人性情以及感情际遇等方面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雪莱是对徐志摩的诗学观和诗歌创作影响致深的一位浪漫派诗人,他的理论和实践都可以在徐志摩身上找到明显的痕迹。雪莱在《为诗辩护》中义正词严地张扬伟大的诗人及其诗歌在社会文明中的作用 :“一首伟大的诗是永远充溢着智慧和快乐之水的源泉;一个人和一个时代借助其可共享的特殊关系斟尽其琼浆之后,另一个人和另一个时代又接踵而来,新的关系持续在发展,一种难以预见难以预想的快感之源”(Shelley,A
Defence
67)。徐志摩毫不掩饰对雪莱的钟情及其人诗合一的推崇,认可诗人与生俱来的天赋及诗歌的崇高与纯粹 :“我们至少要承认: 诗人是天生的而非人为的(poet is born not made),所以真的诗人极少极少”。他认为“诗是极高尚极纯粹的东西”(“诗人与诗”),所以,“在最高的境界,宗教与哲理与文艺无区别,犹之在诗人最超轶的想象中美与真与善,亦不更不辨涯沿”。在他看来,诗化的生命和诗化的写作是一致的 :“诗是最高尚最愉快的心灵经历了最愉快最高尚的俄顷所遗留的痕迹”(徐志摩,“征译诗启”)。这一定义干脆直接就是雪莱在《为诗辩护》中一句名言的翻译 (Shelley,A
Defence
79)。雪莱也非常非常重视诗歌中音乐性的再现/重复 :“诗人的语言总是含有某种划一而和谐的声音之重现(recurrence),没有这种重现,就不成其为诗,而且,姑且不论它的特殊格调如何,这种重现正如诗中的文字一样,对于传达诗歌的感染力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凡在诗情充溢的心灵的语言中,遵守和音重现的规律,同时还注意这种规律与音乐的关系,结果便产生韵律,或表现和音与语言的传统形式的一种体系”(Shelley,A
Defence
24-25)。受其影响,徐志摩也非常重视诗歌中的音乐性,在创作中尤其在意各种重复再现,关注诗歌的内在音节 :“诗的灵魂是音乐的,所以诗最重音节。这个并不是要我们去讲平仄,押韵脚,我们步履的移动,实在也是一种音节啊”(“诗人与诗”)。并反复强调这一点 :“正如一个人身上的秘密是它的血脉的流通,一首诗的秘密也就是它的内含的音节,匀整与流动。[……]明白了诗的生命是在它的内在的音节(internal rhythm)的道理,我们才能领会到诗的真的趣味”(徐志摩,“诗刊放假”)。徐志摩非常认同象征主义诗歌中的音乐性成分 :“我不仅会听有音的乐,我也会听无音的乐(其实也有音就是你听不见)。我直认我是一个甘脆的Mystic。为什么不?我深信宇宙的底质,人生的底质,一切有形的事物与无形的思想的底质——只是音乐,绝妙的音乐。[……]我昨夜的梦……无一不是音乐做成的,无一不是音乐”(“《死尸》序”)。六、 徐志摩诗歌音乐美学的贡献与局限
如大多数新诗人,徐志摩也没有受过音乐的专业训练,亦无意深究。他对音乐的理解也如对西方诗人及其诗歌理论的了解一样,都是诗人率性而为的不经意的偶然 :“都是邂逅,不是约会”(“济慈的夜莺歌”)。但他凭籍自己的灵气和睿智来体悟音乐,尽管一鳞半爪,却不乏灵光的闪现和顿悟,达于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诗感、乐感、情感、灵感的相通相契相成。这也是其人其情其境的格调使然,轻灵、洒脱、飘逸而不乏狂野,又淋漓地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这些,对他的音乐化写作都不乏可见的影响。上述三种音乐化再现方式并不是割裂的,而是相互包容的综合呈现: 如《夏日田间即景》《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等,从内容上看属于部分再现,从结构来看,又可归为变奏式再现;而《在那山道旁》《再别康桥》等内容上归为变奏再现,而结构上也可视为完全再现,无不体现出徐志摩音乐化再现运用的娴熟与繁富多彩。
徐志摩的音乐素养并没有超出当时的诗人们的视域,他的局限也是那一代诗人的局限,一个时代的局限。这与现代中国的启蒙压抑抒情有着直接的关系。尽管20世纪初期的中国一直处于“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压力之下,国人大多无意、无暇亦无力特别关注文学的音乐性、文学性等非功利的无用之用的艺术性,审美的政治化与政治的审美化导致无论是公共教育还是自我教育,普遍缺乏音乐的内在或外在诉求。
而古代的优秀诗人大多精于音律,诗琴书画贯通,温庭筠、周邦彦、姜夔等都能自度其诗词。诗的歌唱性是诗人与受众的普遍诉求,尽管诗与歌一度两分,但一直保留诗乐合一的一脉;哪怕不再谱曲,其音乐性也一直相伴相随。因此,朱谦之会断言 :“差不多中国文学的定义,就成了中国音乐的定义;因此中国的文学的特征,就是所谓‘音乐文学’”(16)。
晚清以启蒙为主调,新启蒙运动的马克思主义提倡者,只认可文化与思想为革命服务的意识形态功能”(余英时12),为“感时忧国”所笼罩,但仍然“到处弥漫着抒情主义”(梁实秋,《浪漫的与古典的》24)。表现在文学写作与音乐的互动中,以闻一多、徐志摩、朱湘等“新月派”代表诗人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提出了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和建筑的美这一现代汉语格律诗学主张;深受法国象征派诗人影响的戴望舒的诗作追求音乐性的意象呈现,取得了不菲的创作实绩;而梁宗岱受法国象征主义诗学的启发,坚持要“彻底认识中国文字和白话底音乐性”,追求诗歌的形式与意义之间“富于暗示的音义凑泊”(“音节与意义”)。
救亡、启蒙与抒情的纠结中,前者压抑后者仍然显而易见。中国新诗人普遍缺乏传统音乐的素养,而对西方现代音乐的认知更是匮乏。先驱陈独秀在二十年代初期曾敏锐地看出张扬民主与科学的五四运动因忽略人类情感的利导所造成的情感皈依匮乏之弊,罕见地公开为此而自责 :“现在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既不注意美术、音乐,又要反对宗教,不知道要把人类生活养成一种什么机械的状况,这是完全不曾了解我们生活活动的本源,这是一椿大错,我就是首先认错的一个人”(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大多缺乏音乐素养的现代文学创作几乎就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个较为普遍的缩影。
而近现代西方却迥异其趣。如复调音乐,最早产生于9世纪的西欧,至15世纪后半期至16世纪收获其黄金时代;进入18世纪后半叶,其主导地位开始逐渐被主调音乐代替,发展出包括赋格曲等繁富辉煌的复调音乐体裁。其对位、模仿、变奏等音乐技巧、曲式也大量运用于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创作中。因此产生了诸如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Four
Quartets
)、庞德的《诗章》(The
Cantos
)等大型类音乐作品。前者师承弦乐四重奏大师如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等,运用西方现代器乐复调音乐结构;后者则采用赋格曲式来构建其诗作的宏富结构 (Pound 285, 386; Davis71-94)。哪怕是对西方音乐并不特别精通的泰戈尔,其原创和翻译都极富音乐性,因为他本人就是音乐家,得益于深厚的传统音乐素养,自己为自己的诗歌谱曲(包括印度国歌在内的)一千余首,既立足民族音乐,又拥抱世界,因此他的英文自译和英文写作都有为人称道的音乐美感。而美国歌手鲍勃·迪伦(Bob Dylan),更是作为诗人兼词曲作家,以其特殊的跨界写作与表演,赓续了自古以来文学艺术的歌、诗、乐融为一炉的传统,由于“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崭新的诗意表达”而荣膺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更是向世人召唤诗的音乐性与音乐的诗性之本质回归,不乏可取的历史与现实之双重意义。可见,音乐和文学发展具有互为表里的相关性。这都是与一个时代音乐的发展相辅相成的,正如朱谦之所言,“所以文学史和音乐史是同时合一并进的,如一个时代的音乐进化了,便文学也跟着进化,另发展一种新文学”(35)。由于长期闭关锁国,清代以来自身的民族音乐并没有长足的发展,遑论西方现代音乐。这制约了评论家的音乐思辨能力,同时限制了作家特别是诗人的音乐想象力和创作空间。就拿新诗人中理论水平最高的闻一多来说,他对诗歌音乐性的理解即“音乐美”,指的只是“音节”。其实,音乐美远远超过这一点,明显体现出他对音乐认识的局限。戴望舒曾获赞为“替新诗底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施蛰存,“引言”52),至于如何开了一个怎样的新纪元,却不甚了了。而且因音乐美见长的戴望舒自己对此亦不在乎,日后更是放言“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要去了音乐的成分”(戴望舒,“诗论零札”691),从此不惜改走一条“去音乐化”的歧途。在诗歌批评界,更是鲜有学者具备足够的音乐识见,指陈创作界的不足。中西古今音乐传承和发展互为因果的不足直接影响到新诗音乐性在深度和广度的开发,延滞了文学(特别是诗歌)与音乐与时俱进的进步。
以徐志摩的性情,他本无意也无力建立自己的音乐诗学体系,正如他无意像闻一多那样建构自己的格律诗学,而只管以丰富的创作和翻译践行对诗歌音乐性的直觉主张与本能领悟。现代新诗因此不仅收获了文体的繁荣,也部分找回了它应有的艺术气质。郑敏所称许的古典诗歌的“词藻的丰富斑烂,句法的简洁多变,表达力的深透灵活,文本的多彩多姿”(郑敏,“中国新诗”69),其实大致已由徐志摩通过本能的灵性加以继承并结合西方传统而有所光大了,其新诗比较接近闻一多对新诗的期许 :“不但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诗,换言之,他不要做纯粹的本地诗,但还要保存本地的色彩,他不要做纯粹的外洋诗,但又要尽量地吸收外洋诗的长处;他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女神之地方色彩”)。概言之,徐志摩为新诗的艺术化与音乐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石,部分促成了新诗文学性、音乐性的回归。不过,此后大陆几十年意识形态的高扬使得“审美的政治化”一骑绝尘,作品的文学性、音乐性等艺术审美退场,作家或学者多只好帮忙或帮闲,或就此搁笔,亦无暇清理并继承前辈的优良遗产,遑论层楼更上。这在当代诗歌中仍不见多少改观,令人遗憾亦发人深省。
注释[Notes]
① 罗传开:《外国通俗名曲欣赏词典》(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1082。
② 陈历明 :“中国现代诗歌创作与翻译”,《文艺理论研究》5(2017): 118—31。
③ Percy B. Shelley. “Oh World, O Life, O Time.” pp.715. 译文见黄杲炘: 《英国抒情诗选》,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137。
④ 朱自清 :“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赵家璧主编(上海: 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7。
⑤ William Blake. “The Tyger.”
⑥ William Blake. “To Tirzah.” pp.41. 译文见张炽恒: 《布莱克诗集》(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78—79。
⑦ 参见〈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2016/announcement.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