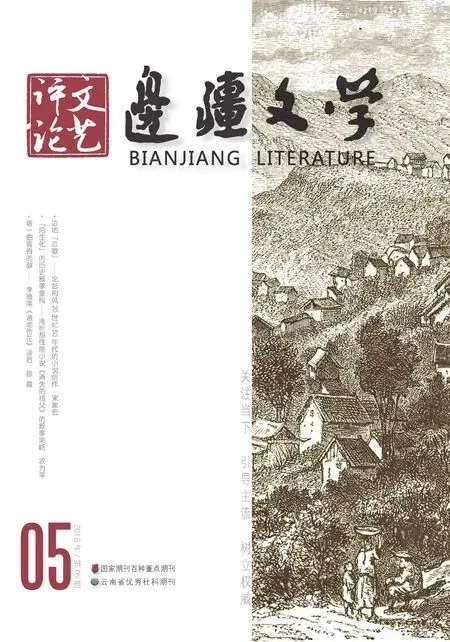哈尼族作家艾吉散文的“实正裸方”
——以《吉祥寨神》为例
南 马
在“石头埋在土里也会发芽”的滇南,“目光所到之处,全是绿色,时间一久,连人的目光也成了绿色。在山上,没有污染,气候总是凉爽,树又那么慷慨地生产新鲜空气,风一吹,肺就像泡在清水里,湿淋淋的,连咳嗽都成了享受。鲜花盛开,树木吐绿时,空气中多日飘满了清香,让人如同掉进了蜜池,晕晕乎乎……林子多,泉水旺。从山上流下来,水质好,人们张口就喝,一路凉到底。人们很少喝开水,以为会破坏口感。大旱的年头,泉水依然手腕粗的咕咕欢腾。”
这是哈尼族著名作家艾吉衣包生长的滇南故乡,也是散文集《吉祥寨神》为我们营造出的精神家园。在这个“空气中也捏得出清泉的风景”的精神家园里,艾吉就是大地上的泉,以甘洌的内涵,不竭的姿态,滋润着读者的心田。
通观全书,艾吉给我的阅读时空里增添了“实、正、裸、方”四个特点。
——实,即实在。实货。
艾吉出生在红河南岸一家哈尼族的“一只竹篾编制的倒垃圾的撮箕里”。这就意味着他先天就与“温床”无缘。盖是那种“赤条条”来到人世间的主儿。在那个“越穷越光荣”的时代,乡间人靠把月亮摘来当镰刀撸山茅野菜过日子,嘴巴和肠子经常生锈,生孩子哪有那么多讲究?据我所知,我们乡间的良家妇女还有在野外劳动时就生产的。乡间人,一代代从母亲的肚子落到地上,他就成了大地的一员。“哭一阵后,没人再愿意听你没完没了的哭。在大自然的怀抱,你搞不了什么特殊化,一棵树怎么活着,你就得学会它的坚韧;一把泥土怎么强盛,你就得吸取它的营养。哈尼族的娃娃,到一定时候,母亲就要背在背上,到田边进行象征性的劳动教育。这是人生教育的第一课。在那里,母亲说的话,不含半点长大后如何收起来手脚享清福的意思。而是财富和幸福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你要学会挖田种地,要学会坦坦荡荡做人,要学会忍受一切不幸,你的骨头要比石头还硬。”
艾吉从撮箕里爬到母亲的怀里,蹭到父亲的背上,然后梭到梯田野地,与小伙伴们捉了泥鳅黄鳝,玩了雀窝,到甘蔗地里嚼了“甜咪西”的甘蔗杆,醉了几回哈尼汉子自酿的酒,在酒醉嘛嗨后居然纵上了牛背,成了一名乡村牛倌。在乡间,小牛倌的“工作”充满了“裸意”。有童谣为证:“放牛娃儿小的的/天晴下雨背蓑衣/肚子饿来吃牛屎/雀儿硬来戳牛逼。”牛在乡间是人家的顶梁柱,实在。牛倌艾吉也是小牯子一样的实在。他从牛背上下来,13岁那年从寨子步行到红河县城那个“大地方”,远远地看了一回省杂技团下来的“精彩”演出,算是“开了眼界”,15岁到另一个寨子的小学里当了一回“娃娃王”,为自己的“今后”埋下了伏笔。粉笔灰还没有吃到头,他居然用哈尼汉子做犁耙的钢硬椎栎树,为自己做了一支笔,不停地书写着故乡的意境,走上了文学的寂寞路。
实在的艾吉就有了实货的《吉祥寨神》。全书凡73篇,除少数的《大烟窗》《上老阴山》《我看见红河入海处》等篇什外,全是由故乡的山水草木,人情世故,多舛命运,民族文化等组件构成。这些或长或短、或深或浅、或疏或密、或庄或嬉的审美物质,使得艾吉的散文创作形成了宛如“哈尼蘸水”的“这一个”。这是艾吉对中国当下散文繁荣发展的一种贡献。新时期以来,中国的文学领地,诗歌以发情牯子为了获得“交配权”而干架的方式不顾一切往前冲。但往往是冲到前面未免难见到水生生的“小妹牛”在那里等着。小说则是热情有加的青年牛,朝着水草的丰美,一路变幻姿态,在吃撑了肚皮,收获了肥膘的同时,也因为消耗了大量的资源,给人以“不划计”之感。当然,以为了“吃上饺子”而躬耕文学田园而斩获诺奖的莫言等少数中国作家,又另当别论。而散文,这个“最具中国传统”(汪曾祺语)的文体,刚好是那群成熟牛,他们在文学的草地上,自信、自觉,自强,在尽情享受着丰美的同时,也不会忘记给路边的野花一个眼神,抑或对甘洌的山泉奉献一声“哞——”的问候。牛对大地水草的问候,山泉对水草润泽,就是散文,而且是我要的好散文。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对散文创作产生了一个美丽的误解,认为散文就是空气,无处不在,什么物种都可以享用,什么人都可以写,人人都可以当散文家。一个尚未出道的写作者,撸了一堆身边的鸡毛蒜皮,掏了点银子,请所谓“名作家”作一序,给出版社一点赢利,就印了书,就到处宣传,就成了“作家”了。有的在网上发了“一贴”,一贴触动一网,一夜间就成了“一网作家”。有的虽然是作家了,且大有名气,可一本百十篇的集子,能读的,算得是好的作品不过那么三五篇,其他的可以叫作“凑印张”。出来了也是文学的“可乐”,没有什么营养的。支撑这个美丽误区的,就是不实在,就是叶子离开大树的“飘”,没有实货。我们不难想象,树叶离开了大树,泉水离开了大地,北极熊离开了冰川,后果会是什么样子。
而《吉祥寨神》之所以吉祥,就是因为她从未离开寨子,离开敬畏她、爱戴她、奉献她的乡村人们。“寨神”在梯田民族中为什么会有至高无上的美誉度,这恰恰体现出了梯田民族人与自然完美结合的高度典范。艾吉大声向我们宣誓:“我们的眼睛不是朝着天上虚无缥缈的神,这活生生的身边的树,才是需要我们跪下来磕头的至高无上的神。假若对神树没有如此的敬畏,我们这个山地民族,也许早就消失了——寨神是我的父母啊!”
人不是猴子,更不是悟空。父母是人生的第一个“实在”。
——正,即正当。正宗。
时下的散文创作,尤其是在书写乡村世界的活动中,许多作者的“乡村身份”与被审美对象的关系不正当,其作品就不正宗。
我曾在理论拙作《乡村身份与作家在场》一文中指出:所谓作者的“乡村身份”是指作者是否谙熟中国乡村的真实生活,其思想意识、审美情感、艺术旨意是否指向于乡村并被乡村所接纳。如果上述四题都是“打钩”的话,作者就取得了创作上的“乡村身份证”。这个“乡村身份证”就是作家自己与乡村生活结成连理,为获得“交配权”而申领到的《结婚证》。在当下中国社会,男女要长时间在一起来“好在”(做爱的意思),必须得有一个叫“证”的东西来证明你们的“正当”,否则,弄出的后代(作品)也是被称作“野种”,不“正宗”。这个界定还需说明的是,“乡村身份”不是作者的“出生证” ,也不是“身份证”。它不考证作者是否“呱呱坠地”在昏暗但柔软的乡村,抑或在明亮但冷硬的城市。它获得认证的唯一标准就是:作家个体的文化身心是否流淌着乡村血脉。有了乡村血脉,你与乡村就有了正当的“血缘关系”,作品就正宗。翻开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从沈从文、汪曾祺、孙犁到赵树理、柳青、浩然,从贾平凹、陈忠实、莫言、韩少功到铁凝、孙惠芬、迟子健等等,不管他们采用什么方式,都取得了表现“乡土中国”的乡村身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瑞典皇家文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极具中国“乡村身份”的作家莫言。这不仅仅是中国作家的胜利,更是中国作家“身份正当”的胜利!
艾吉是乡村的直系血亲,有“乡村身份”的作家,其散文创作,与被审美对象的关系正当。因而,其作品的内涵正宗。
我记事起,奶奶就是那副矮夺夺的模样。她干不了重活,但平常总有忙不完的琐琐碎碎的活计,她是作为强壮的劳力打整伯父家里里外外的农事。奶奶话少,她静静地坐在墙脚的蓑衣上时,别人会忘记她的存在。她只有走在路上的时候,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她是苦出身,据她讲,从记事起,就没有见过父母,她的村子,只有几小户人家,森林里,野兽的叫声中,如今连遗迹也不存在了。她很小就被亲戚收养。到了一定的年纪,跟同样穷的爷爷凑合。爷爷的家丢石头进去,丢不着值钱的东西,只会伤着饥寒交迫的人……没有听过奶奶说自己苦,她像所有乡下的穷苦农妇,无论承受着多大的生活压力,认定那是命中该有的一份哀痛,身上的背箩那样不可能放下……奶奶虽然守寡长,因有孝顺的儿子,她是幸福的。我们的父母对她没有过针尖大的伤害。
外婆的命却是另外一种格调了。“旧社会”整个村子遍地都是穷鬼,外公家有几片田,忙时请人帮工,不至于吃了上顿愁下顿。后来时代变化,她家被戴上了“剥削劳动人民”的帽子,从炊烟有点暖和的家庭一下子跌进狗屎堆。现在村里最贫穷的人家,都比外婆那时的光景要富。还不到10岁,背着狗屎臭的寄生虫的“地主”子女的名声,我的母亲跟在外婆后边,到外面接受劳动改造,比如挖路、背石头。外公也是早死,他什么责任也没承担,把深重的“罪孽”留给孤儿寡母从肉体到灵魂的洗涤来偿还。说不清的原因,外婆的晚年,虽有其他的亲人,却唯有我的母亲里里外外的尽孝。她跟奶奶相比,生命的后期掺拌了难言的凄凉。
以上两段文字均引自《回到祖先身边》。这是《吉祥寨神》一书中我特别看好的篇章之一。两个像所有乡下的穷苦劳动农妇,无论承受着多大的生活压力,认定那是命中该有的一份哀痛,一份担当。那担待像身上的背箩那样不放下。艾吉用“正当”的文字,“记略”的手法,寥寥几笔,让两位乡村劳动妇女痛痛地站立在你的眼前。内心的疼,是用钝刀扯着割肉的那种!这还不是《回到祖先身边》的最高妙处。最高妙的,是作者对亲人后事处理所展现的重大文化命题。作者在自己的视界里,窥视到了中国乡土中的“超稳定文化结构”。所谓“超稳定文化结构”,是指在中国乡村社会一直延续的风俗风情、道德伦理、人际关系、生活方式或情感方式等。这些“超稳定文化结构”的元素,融合成了《吉祥寨神》。虽然世风代变,政治文化符号在表面上也流行于农村不同的时段(一段时期禁止祭祀“寨神”就是一例)。这些政治文化符号的变化告知着我们时代风云的演变。但我们同样被告知的还有,无论政治文化怎样变化,乡土中国积淀的超稳定文化结构并不因此改变,它依然顽强地缓慢流淌。
对于人的出生与死亡的“生死观”,不同的民族,不同地域的人,意见可能会见仁见智,甚至南辕北辙。哈尼族的生命观是豁达的。离开人世,只不过是一种方式的转换;只是在阳间度过的时间已到了期限,被祖先叫走,回到祖先的身边罢了。因此,不论是最穷的家庭,也要让丧事办的体面一些,“让受了一辈子苦的老人心满意足的去见祖先”。这就是本文的“节点”,草民与皇帝同去的公平。一个民族的生死观,往往就是这个民族世界观的集中反映。
作家客观、公正、艺术地表现了民族文化的本质,就是“文化担当”。 作家文化的担当,就是指在作品中表现的文化责任,关乎人文和生命意义的写作,是文化审美烛照下的历史反思与感悟,灵魂的探寻与追问。在从事创作的过程中,作者不但进行着自由的精神审美过程,同时亦进行着深入的精神审己活动。只有对自我深入地审思,才能使艺术与思想得以升华,才能畅达地抒发自己的思想情感,发挥自己的艺术才情,其作品也才会“正宗”。
类似挖掘与展现深厚民族文化内核的篇什,在《吉祥寨神》一书中,还有不少的部分,此不多喙。关于这一类题材,在我十分有限的阅读范围中,曾读到过不少作品。好些外族作者,参加过一些体验,得了一些表皮,就大事书写其表象的过程,无法进入民族的情感深处,对民族的传统文化挂一漏万,一叶障目,有的别有用心,断章取义,所得之文或者浮泛轻飘,或者南北颠倒,引起误读,走向民族不团结的歧路,成为阻碍民族文化繁荣的帮凶。究其原因,就是没有摆正作者与书写对象的关系。关系不正当,所以作品就不正宗。歪锅配歪灶,麻子婆娘生得好娃娃的个案是有,但凤毛麟角。
“没有不枯的树木/没有不烂的石头/没有不干的河流/从来的路上回去。天也是这样/地也这样/太阳也是这样/月亮也是这样”流传在民间的歌谣,所拥有的内涵,已远远超过了歌谣本身!人,无论你多么的高贵,生前多么的“万寿无疆”,既然有来的日子,一定就有去的时候。这是绝对真理。
我们滇南的文学创作在对人的本质,对宇宙的本质的追寻,对涉及人的生存、未来,涉及民族发展重大问题的思考等等“节点”上,做得显然是不够的。文学在民族精神力量,鼓舞人们的思想力的提供等方面,尚显薄弱,即使有所触及,化为深入人心的艺术表达也还有一定距离。这也是艾吉们尚需努力的方向。
——裸,即裸体。脱光。
艾吉在《吉祥寨神》一书表现出来的另一个创作特点是裸,“脱光了写”之谓。故乡大地的美丑在他的心中一目了然。他不溢美,也不遮丑。既高歌大地上的美,也鞭笞大地上的丑。把心掏出来,赤裸裸的,让你看到心血管的内部。
“在城市待久了,人就会变得迟钝,丧失掉仅有的那点艺术感觉。我喜欢出去,乡间是我最好的去处,是我整个生命的寄托与归宿。我指的乡间,是远离喧嚣的、自然景物还完好保存的农村。那里有青山绿水,有带牛粪味的袅袅炊烟,有生动的方言土语,有让你能够静静流泪的地方。乡间有一座座的山,山上很少有清闲的身影,但你也不会感到孤独。相反,因为避开了乱哄哄的人群,你感觉一身轻松。很少有人的感情,能像我与山之间的感情那么长久、那么深挚。”这篇《山那边有我思念的山》,后来发表在中国作协主办的《文艺报》报上。这是艾吉对故乡大地的思想裸体。有了这样的思想支撑,我们才有理由相信艾吉笔下的艺术之真。他风景类的赞美自不必多说,来看一组记人多舛命运的篇什。
酒鬼表哥批处死了,死在48岁的门槛。装进临时拼凑的木板,第二天草草埋进坑里。他说他算过命,要活到78岁。在野外,他的“家”也只有鸡窝大,像鸡笼破烂,不愁漏不进雨水,那是喝不完的酒。(《“酒鬼”做“鬼”去》)
在那个屙屎不生蛆的年代,生产队的牛们被另一个人放得“瘦的烧柴也点不着”,因此队里就换了一个3岁起就爬牛背,“老本老实”,名叫牛沙的来做牛倌。牛老倌跟牛的缘分可能是上辈子就带来的。买一头母的小黄牛,不要几年,母牛生小牛,小牛长大了再生小牛,成了一小窝。牛老倌还根据牛的性格、特点,给每头牛都取了绰号。取得准确、幽默。一条条牛像街头玩泥巴的小娃娃,有了叫起来响亮,笑痛肚子的名字“小三妹”。那头牛会看人,真心的叫它,它就会“咦”地点点头,扇尾巴。如果是挑逗它,它就会拍拍屁股不买账。牛倌牛沙在那个时代出尽了风头,有了媳妇有了儿女,日子还算耗子舔米汤——刚刚糊得了嘴。新时期经济社会转型后,牛沙的日子像缺水的树枝,一天天枯黄下去。因为穷,娃娃们嫁的嫁,分家的分家,最小的儿子跟他苦熬,到30岁还不见婆娘的影子。父子俩一老一小过日子,火塘熄灭没人管,水缸见底无人问,盐巴生蛆地过着,心结满了灰尘……三声火药枪响,村里人知道,牛老倌走了。(《一生牛命》)
四娘的丈夫叫“四姨”,从小胆子大,以打架出名。成年后,更是经常惹是生非,村里每出乱子都有他的份。隔壁几个村与本村因水务、地界引起纠纷动了拳脚,他总是提着脑袋冲在最前面,一人吓倒百人。他在村里成了既让人讨嫌又让人佩服的英雄。而与他的英雄分量相等的,却是做贼的名声。几次出手成功,同样招来几次的教育和惩罚,但四姨就是“狗改不了吃屎”。一个深夜,他去偷别村人的稻谷,被当场发现。在忽明忽暗的月光下,他不但挨了一火药枪,还被拷打得全身伤痕累累。他依然不吭气,依然把家里的肥猪交给了全村人的嘴,外加一笔七拼八凑的罚款。他不出手偷了,却行起莫批(神职人员)来。他的方式很简单,看几眼病人后,在饭桌上用手指蘸开水画莫名其妙的符号,然后“咪里嘛拉的念咒语”。(“他就像一只虫子,手痒了,心痒了,嘴痒了,啃啃咬咬,在一块土坷下,过着盐巴不够加盐巴,辣子不够添辣子的日子。”)(《四姨》)
酒鬼表哥为什么会死于酒?三岁就爬上牛背,老本老实的牛倌为什么会在新时期经济社会转型后一蹶不振,连走下坡路?四姨为什么过着“盐巴不够加盐巴,辣子不够添辣子的日子”?作者没有花更多的笔墨去叙述,去分解,去解释。他只是在幽默诙谐的语言过程中,在“脱光了写”的状态下,把一个个故乡“小人物”的命运“缩影”在你面前,裸露在你面前,让你心酸,令你沉重,给你痛楚。散文人物性格鲜明,个性凹凸,语言丰满,完全可以与小说媲美。写人的散文写到这个层次,不叫好都不行!
——方,即方言。民间。
读文学作品首先是读语言。
“什么是好的语言,什么是差的语言,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准确……准确就是把你对周围世界、对那个人的观察、感受,找到那个最合适的词儿表达出来。”(见汪曾祺《文学语言杂谈》)“最合适的词儿”就是方言,民间通用语。从这个角度看,作家艾吉是滇南大地上行走并快乐着的一坨哈尼赤子。
“一坨”是我们滇南人用来说明单个人的数词,没有对“普通话”不尊的意思。我总是不服气地认为,所谓“普通话”用“个”来表明人,太单薄,太弱不禁风,太我行我素,太孤芳自赏,太不自量力,太一意孤行,太随心所欲,太……一坨石头,一坨泥巴,看起来那是相当的不起眼,但实际上是相当的实在。石头和泥巴,是大地的一分子,你可以藐视它,鄙视它,揶揄它,但不可离开它。艾吉就是这样的一坨。他的散文语言是山泉,咕咕嘟嘟,以民间通用的姿势从开篇到结尾,从山头灌溉梯田般流至山脚,充满了生机与气韵。他赞美的语言无节制,鞭笞的话语同样不吝啬。在他充满了生机与气韵语言之泉中,嘀哩嘟噜地出现了一系列的方言土语。艾吉说:“一个人,最触及灵魂的方式,就是让他用母语说话,唱歌,或痛哭……我崇敬民间,它本身像大自然一样的漫长和悠久,它本身像大自然一样的辽阔和宽敞,它本身像大自然一样的辛勤和富有……语言就像树,一个民族语言的叶子落光了,再也不会发芽,那么,民族的这棵树就已经面临死亡。”也许,艾吉散文语言的个性,与他的民间大自然有关。
“我记事起,奶奶就是那副矮夺夺的模样”;“在大家都风吹屁股冷的年代,他家更显得炊烟都瘦筋干巴”;“老远八远都听得见”;“身体好噜噜的”;“雷打不塌的事”;“要死要死的整过好多回”;“脑袋瓜咪哩嘛啦”……
以上所引民间性语言,在《吉祥寨神》中像山上林中的树叶,随处可见。一个地方的方言土语,进入作品,如果用得好,处理得妙,就会“忽悠”全国乃至世界。反之,就会给阅读造成了障碍,降低艺术价值,妨碍的力量的远播。在这里,我必须美丽地提醒作者:在《吉祥寨神》中,好些民间语言没有处理得好,给人造成了“酿”的感觉。“酿”也是方言,腻的意思。一部作品的语言,出腻了就失度了,不可取。关于艾吉散文语言,我将另文专述。不赘。
好蘸水不怕辣,好文章不怕长。为了凑字数,再抄一段艾吉的创作如是说:
“我写作,实在不过是把一些感动着我的人事、风景,用文字记录下来。但值得欣慰的是,我始终记住故乡的养育之恩,用这颗还能以血性跳动的心,热爱着所有值得热爱的人、动物、山水、草木、庄稼……”(《故乡与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