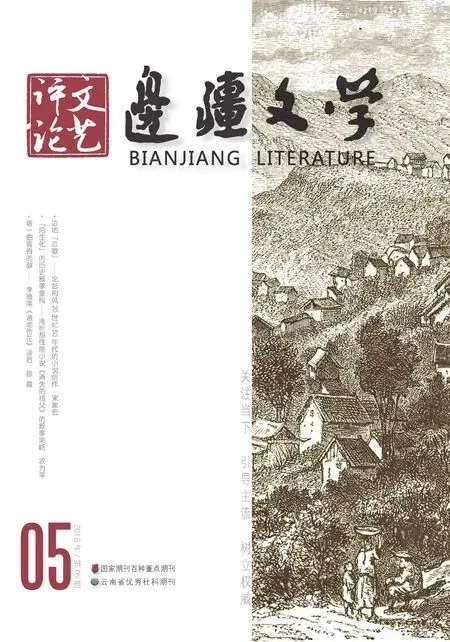霸蛮语言:20世纪南方乡村的一幅桃符
廖令鹏
郭建勋平时笑嘻嘻的,什么事都无所谓,骨子里却藏着霸蛮基因。湖南桃江人,在武汉当过兵,退伍后三闯深圳,光知道这些还不敢用“霸蛮”这两个字来形容他,一来对于暴力,这些个经历算什么。二来“霸蛮”到底什么意思,我还不是太懂。郭建勋来深圳24年了,打工,写作,经商,做文化,他的语言是变化的,变化的语言潜移默化地伴随着他,完成人生角色的转变。《桃符》这部47万多字的长篇小说,时间够长,将近百年,围绕主人公陶桃花,一波波人陆续出场而离场,20世纪中国南方乡村的风云诡谲变幻,命运的乐章曲折离散,郭建勋一些人生经历,也不知不觉地穿插在小说当中。这样一来,霸蛮语言的演变肌理,也就有迹可循了。
以《桃符》为标志,语言实现了回归
1993年来深圳打工的郭建勋,浸淫在打工语言中长达20年之久。《天堂凹》《鸡鸭小心》和《深圳,我投降》这三本集子,是打工语言的最集中的体现,贯穿于工地、工业园、流水线、宿舍、底层消费场所等地。生存不易,欲望起伏,壮志未酬,郭建勋的打工语言,多是用来寄存自我的语言,有点小躁动,小鲜滑。2010年左右,郭建勋的语言悄悄地向中产语言转变,总想在语言中弄出点味道来,从这期间他创作的不少古诗词来看,真空妙有,暗合禅道,多求些小意思。他那中产语言说的时间不长,算是一次深山禅修,趣味上麻醉自我而已。2017年伊始,他拿出了《桃符》这部沉甸甸的小说。《桃符》以极富湖南乡村特色的霸蛮语言,窥探了20世纪百年历史风云,叙述了一个家族繁衍生息的流变,虽不能说是垫枕头的作品,却也可看作是郭建勋的一份中年献礼。
《桃符》不仅让我更新了“霸蛮”的内涵,还加深了对郭建勋的语言的了解,说他的语言就是一种“霸蛮语言”,不仅不粗鲁,反而恰到好处。当代著名公共知识分子乔治·斯坦纳在《空洞的奇迹(1959)》一文说,“语言是有生命的生物体。虽然极为复杂,但仍然是有机体。语言自身就有一种生命力,一种特殊的吸收和成长的力量。”《桃符》的霸蛮语言,其生命力与成长力量,有太多可圈可点之处。掷地有声,刚烈霸气;粗细停匀,收放自如;文质相间,俚俗不却。霸蛮语言之于小说人物,表明立场时,连喘息声都炽热鲜明;糙野情势,一个女人也不怕说脏话;危险境地,一句话也要乖巧灵泛。之于作者,从不玩弄独白议论,从不流于窃窃私语,话接着话,话外有话,浑然一气;之于故事本身,霸蛮语言就像自己长了一双脚,一个情节推着一个情节,一波推着一波,语言鲜活,元气氤氲。
霸,不是霸道,女主人公陶桃花像一粒外来的种子,忽然种在云溪这片土地,入的是陶子长这样的贫苦人家,身世也隐去了,哪来霸道的底气?陶桃花操持的是“霸气”的语言,怀揣着“张五郎”,逆水行舟,不屈不挠,积极乐观,与继母争一身之安,与族人争一席之地,与云溪争一格之位,该让则让,不该让则毫厘不退,就像小说中写到的,“这世上,并非只有直着走,还可以倒着走。哪怕倒着走,我还笑着,笑呵呵的,什么也不怕。”再说蛮,这蛮也不是跟别人蛮,而是跟自己蛮;不是蛮横无理,而是一股不气馁、不妥协的劲儿,倒立行走的劲儿。倒立行走可不简单,紧贴地表,困住了手,还要克服重力,让气血倒流,甚至还要纠正倒视产生的偏见。陶桃花幼年丧母,阴差阳错被陶子长收养,差点被继母卖去作妓女,几度寄居尼姑庵,爱情一波三折,与积极分子斗智斗勇,多次沦落到举家外迁的境地,不久丈夫意外身亡,留下一副生活重担,这对于一个普通乡村妇女来说,可都是一样样的苦。但坚韧、正直、刚不可欺的陶桃花以极强的生存智慧和谋生手段拉扯儿女,撑起一个大家庭。陶桃花一家人用翻来覆去的苦难和永不向命运低头的霸蛮精神,诠释了倒立行走的别样人生。
霸蛮之余,郭建勋把《桃符》写得很灵泛,一点儿也不呆滞。史诗性的深沉作品,就怕背负叙事伦理的十字架,给语言套上枷锁。霸蛮还能灵泛,这是湖南人的性格特征。《桃符》里的人,没有一个人的命运是顺顺当当的,都是八弯九曲,一波三折,如果照实写来,难免悲苦连天,愁肠满腹。我说《桃符》的灵泛,是很多时候的形与势,情与理,郭建勋都能荡开一笔,举重若轻。生活的苦涩滋味,总拌着轻巧机敏的俚俗谚语;道个霸蛮,却先请出个“张五郎”;讲个制茶经,还说个乔致庸;逗个家长里短,张口来支短歌小曲;一场风花雪月,也能唱个《扯白歌》。这是郭建勋一贯的创作风格,在《桃符》中发挥得淋漓尽致。阅毕掩卷,老郭的形象跃然眼前,他在茶余饭后说点什么事儿,总能编些花料,谈些古今啦,作个譬喻啦,打个机锋啦,扯点闲话啦,听着不累,却又是绕着事来说的,所以不至于让人觉得轻滑或者卖弄。这种霸蛮之外,恰到好处的“灵泛”,在当代长篇小说中是不多见的。
为什么说郭建勋的霸蛮语言实现了回归呢?《天堂凹》中的主人公,那个心地善良的农村打工青年德宝,实现了道德意义上的回归,但仍没有很好地解决生存问题,也就意味着,他的语言仍没有与城市融为一体;《鸡鸭小心》和《深圳,我投降》的语言一半是海水,一半却是火焰,从一地鸡毛的结局来看,那种打工语言基本上是一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语言。郭建勋在深圳,打工语言作为底线语言操持了十多年,随着职业的变化和阅历的增长,生存策略与价值取向也慢慢有了变化。人到五十知天命,语言也该朝向天命了吧。
姑且来猜猜郭建勋的人生哲学。创业艰难,霸道完全行不通,但必须有霸气,敢于翻生活的台布;世道浇漓,蛮横要吃亏,但可在蛮劲儿上面做文章,加点儿巧劲(灵泛)和野狐禅,就容易成事儿。那么,对于郭建勋来说,用什么语言来书写理想人生状态,而与现实的本色息息相关?用什么语言来描绘魂牵梦萦的远方,而与体内血液的颜色和温度相近?我想,只有霸蛮语言了。虽然《桃符》写的是时空相隔甚远的湘中云溪,但每一字每一句,都是近年来从郭建勋的手腕底下流淌出来的,从他的脑袋里迸出来的,仍然带有他语言系统中最鲜活的印记,时刻出现在他脚底下的路,眼前的风景,乃至未来要去的地方。在这个人生阶段,写这样一部小说,用这样一种语言,对于郭建勋来说,应是最满意不过的作品。
霸蛮语言,20世纪乡村驱鬼辟邪的母体语言
从《桃符》中横阖的历史语境来看,陶桃花的霸蛮语言是真正从湘中云溪那片土壤里长出来的。20世纪的中国乡村充满动荡和苦难,家族的繁衍与赓继充满变数,族谱上的花枝常常毫无征兆地断裂或者新生。乡村家族史研究很少有专门关于母亲的篇章,可能人们认为在那个年代,母亲的功劳簿上充其量不过是生育和家务这两样。生育是母亲天经地义的职责;家务也在男主外女主内这种中国传统文化中变得稀松平常。如此一来,母亲的语言常常是温和、慈爱、低顺、琐碎、轻量的语言。《桃符》中陶桃花的语言,是辣味的语言,是高调、硬气、张扬、劲脆的语言。20世纪中国乡村无不充斥着贫困、动乱和斗争,断绝之剑时刻悬挂在乡村家族的头上。一个家族可能因一个小小事件而灭绝,也可能因一个小小人物而兴旺。陶桃花的母亲是从一个不知所来,不知所往女共产党员,她在逃难的途中,慌乱地把陶桃花塞到陶子长怀里,之后被枪毙而死。这也意味着,陶桃花被陶子长带回家的那一天起,就跟原本的母系家族割裂,不再有任何联系。陶桃花植入云溪陶子长的家族,从一开始就是野蛮的,这也印证了一个飘摇的家族,只要有霸蛮的语言,霸蛮的精神,总能够发枝散叶,人丁两旺,振兴家业。
一个野蛮的时代,霸蛮语言是最好的武器,陶桃花从破壁的小屋中,来到乡村公共生活当中,面对生存、暴力、纠缠、失亲、生育、抚养,甚至面对外来兴风作浪的鬼邪,语言中若没有霸蛮力量而先行消遁于日常生活当中,她哪里有勇气撑开命运之帆向远处航行?就一个母亲与一个家族的繁衍来说,霸蛮语言就像一幅 “桃符”,贴在多灾多难的乡村家族的祠堂门前,驱鬼辟邪。
毋庸置疑,霸蛮母亲陶桃花们,一定出现在中国各个时代与各个角落。陶桃花是经历40至90年代的南方乡村女性,她的霸蛮语言到底给她自己、乡村社会、中国历史呈现什么意义,从小说中的四代人的命运就窥见一斑。父辈陶子长、李焕生、陈白良等;陶桃花、罗亦能、陈炳章、盛木生、盛土生等;子辈盛梗、盛叶、盛军、陈克已等;乃至诸多孙辈盛敏、盛捷等,虽历经坎坷,但他们都还活着,许多人活着是因为陶桃花的霸蛮。40年代陶桃花的霸蛮让自己野蛮生长,50年代的霸蛮让她过饥饿和爱情的波澜,60年代让她挺过了斗争和贫困,80年代陶桃花把霸蛮的精神传递给后辈,90年代的霸蛮稍有收敛,但后辈受她霸蛮的影响,在各自领域艰难闯出一片天。“人生在世一辈子,学不完的江湖尝不尽的苦,要霸得蛮。尤其是你们男子汉,更要霸得蛮,莫动不动就流猫尿——”因此,可不可以说,陶桃花的霸蛮语言是20世纪中国乡村驱鬼辟邪的母体语言,佑庇乡村家族的繁衍和光大。
中国当代文学中,霸蛮母亲写得好的,要数1996年出版《丰乳肥臀》。莫言给予了“母亲”上官鲁氏以霸蛮气,以顽强的勇气和毅力,活下去,倒着走,历尽艰辛,先后生下了八个女孩和一个男孩,为上官家族传宗接代,发枝散叶。高密山东乡是战争和动乱的热土,上官鲁氏承受的苦难几乎贯穿20世纪。莫言讲“我为什么写作”时提到,“我就想象像我母亲这样一代人,她们为什么能够活下来?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她们活下来的?真是可以令人长久地反思。”从一些学者的研究来看,有三种东西支撑着高密东北乡上官鲁氏“活下去”,一是顽强的生命意识,二是原始的母爱本身的力量,三是信仰。湖南云溪的陶桃花,霸蛮中透出的生力和元气,粗犷中流露的率真,豪放中洋溢的侠情与灵泛,尤其是她崇拜 “张五郎”,倒立着贴地行走,遇事笑呵呵,这种极富地域性的“活下去”的精神图谱,在当代长篇小说中也是不多见的。所以,我们不妨把郭建勋的《桃符》,看作是20年后《丰乳肥臀》的一次呼应,是霸蛮母亲形象的一个补充,是中国大江南北生命信仰的一条支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