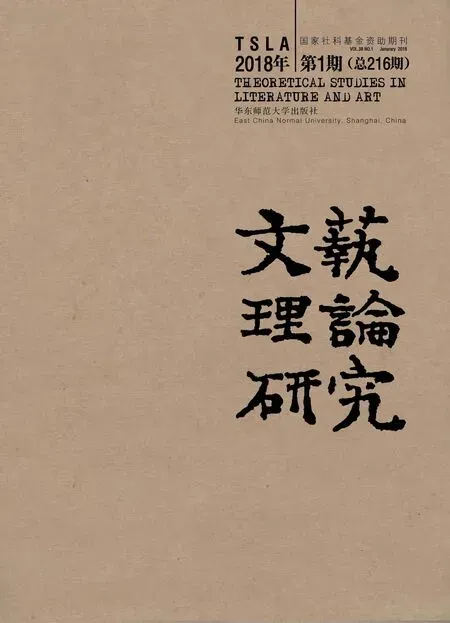仪式向文本的过渡
——春秋赋诗的诗学传播价值
刘彦青 张新科
诗在西周时期到底承担着怎样的社会功用,是学术界依然在不断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传统的“献诗说”“采诗说”在揭露诗来源的同时,也反映了诗在这一时期所承载的政治功用。无疑,政治功用是诗在西周时期承担的重要角色之一,而在诗的政治功用中,与乐舞结合的仪式化用诗又是其中最具特色、影响最为深远的。从周公制礼作乐开始,诗便是周代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诗与乐、舞在从典礼祭祀到宴飨礼仪的广泛场合中承担着告慰先祖、合乐亲亲的实际作用。但在仪式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乐舞,诗在其中的辅助作用十分明显,尽管在仪式中并不舍弃诗义的表达,但诗承载的内容意义在这一阶段并不彰显。随着周王室政治地位的衰落,礼乐制度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春秋时期是一个用诗的时代,诗以引诗、赋诗的方式出现在不同场合,《左传》《国语》等历史文献记载了大量的用诗事例,其中尤以外交场合的宴飨赋诗,风流文雅,是战火狼烟时代的一道风景线。这一时期,统一的诗编结本在诸侯国散布开来,诗的文本意义凸显出来。在春秋外交赋诗过程中“断章取义”“歌诗必类”等现象与原则表明诗的文本意义在这一时期显得十分重要。赋诗仪式需要赋诗参加者对诗的文本意义有娴熟的了解,故而出现了大量的解诗、评诗性话语,这个过程中对诗的权威性阐释在文化传承中显得尤为重要,从而导致了诗由文学发展到经学的必然结果。
一、西周歌诗的仪式化色彩
来自西方的周民族以武力取代东方的商民族后,在新征服的部族里,面临着寻找文化正统性和增强文化自信心的迫切压力。但是,商文化的繁荣程度要远大于周文化。关中出土的大量西周乐器带有明显的商文化色彩,这表明商文化的实际影响力在西周时期一直存在。西周塑造文化权威性的方式不在于强制化地摈弃商人原有的乐舞文化,而是采取一系列文化革新方式,对礼乐文化进行改造,并且使其制度化。从而使得包括新近征服的商民族在内的广泛群体在心理上接受,从而逐步被纳入统一的文化共同体中。这便是周公的制礼作乐。西周初年是最早的诗篇开始出现的时期,这个时期诗是作为典礼用诗而存在的,诗与乐、舞交融是西周礼乐制度的组成部分,具有明显的仪式化色彩。这从以下两个方面可以说明。
第一,《诗》中产生最早的诗篇是典礼用诗。在文学发生说中有一种很有影响的提法是巫术发生说,即文学创作来源于上古巫术活动。《尚书》中记载:“诗言志,歌永言,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尚书正义》卷三 276)。虽然所涉为夏代之事,但说明了上古的意识形态以人神关系为核心,“神人以和”是那个时代最高的价值和境界。诗歌作为娱神仪式的一部分,是为了娱神而创作出来的。《诗经》作为最早的诗歌总集,其中有大量内容与娱神有关。这样的创作来源和创作目的也就决定了诗与仪式的密切关系。关于《诗经》各部分创作时代的讨论一直是传统诗经学上的一个重要话题。最早的诗篇产生在西周初年,这些诗篇的特点是内容上追思文王、武王,形式上古朴,风格上温和典雅,集中在《周颂》、“正雅”及“二南”里,多为一些祭祖用诗,具有明显的仪式性。这些典礼用诗,除了自身具有仪式功能,是周代礼乐制度的组成部分外,还充分体现了周公制礼作乐的文化革新精神。刘毓庆基于《周颂》、“正雅”及“二南”在《诗经》中是最为平和、格调最为雅正的一部分,认为“前人都把这部分看作一个整体,周人是为礼而作乐的,而诗又是从属于乐的,因此最早的诗集应该是为典礼用乐而编辑的”(刘毓庆 郭万金 4)。我们认为在《诗经》中最早也最为重要的是用于宗庙祭祖仪式的诗篇。除了祭祖外,西周时期主要的社会活动如吉、凶、军、宾、嘉五礼体系都带有仪式化的色彩。
第二,在典礼仪式中乐舞的地位高于诗。《尚书·尧典》的记载显示了在早期典礼仪式中诗乐舞呈现三位一体的状况,但传世典籍与出土实例表明,西周时期三位一体的早期仪式中,诗的重要性明显不如乐舞。首先,乐舞制度是商周时期典礼仪式的核心内容。《周礼·春官·大司乐》记载:“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罄》《大夏》《大濩》《大武》。”郑玄注云:《云门》《大卷》为黄帝之乐,《大咸》为尧之乐,《大罄》为舜之乐,《大夏》为禹之乐,《大濩》为汤之乐,《大武》为武王之乐。此即为《周礼》所谓的“六代之乐”(《周礼注疏》卷二十二 1700—1701)。关于商代乐舞,在甲骨文中出现最多的是“万”,针对甲骨文中的“万”字,有的解释为一种乐器,有的解释为从事乐舞的一种人,还有的直接认为其就是一种祭祀仪式。陈致认为“商王每于祭祀先王先妣时兴万舞。以其在甲骨文中出现的频率来看,万舞比任何其他舞蹈都更重要。”万舞在周初依然很受重视,甚至到春秋时期依然存在,但是自武王牧野献俘后,万舞就从周王室祭祀典礼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周王室新的乐舞——《大武》。过常宝考证认为“西周对乐舞制度的改革,应该始于周公制作王朝乐舞《大武》”(过常宝 229)。肯定了《大武》在西周礼乐制度中的标志性地位,也认识到了乐舞制度在周公制礼作乐中的重要作用。其次,在典礼仪式内容中诗的重要性不及乐舞。《礼记·大司乐》所记“六代之舞”的内容仅涉及所用乐器及舞蹈,虽有记歌诗时候所用的乐器如“大吕”“应钟”“南吕”等,但并不记载所歌诗的篇目或内容。以西周《大武》为例,《礼记·乐记》中记载孔子认为“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礼记正义》卷三十九 3343)。孔子认为《大武》“六成”其实反映的是武王开创并逐步稳定周朝的历史过程,可见周公创制《大武》的直接目的是祭祀武王。有学者考证认为《周颂》中的《武》《时迈》《赉》《酌》《般》《桓》即是西周时期与《大武》“六成”相配的歌辞。然而,以其中的《周颂·武》为例,《武》诗云:“于皇武王,无竞维烈。允文文王,克开厥后。嗣武受之,胜殷遏刘,耆定尔功”(《毛诗正义》卷十九 1287—88)。过常宝认为:“这首诗称赞文王,是武王克商后告祭文王的诗,由武王主祭,是周公创制的。武王死后,这首诗被移置《大武》组乐中,用以祭祀武王本人”(过常宝 231)。这种诗与乐舞的不匹配现象表明在典礼中乐舞的功用其实是大于诗的。而通过考查历史文献对西周仪式用乐的记载,也可得出同样的结果。《国语·鲁语》:“夫歌《文王》、《大明》、《绵》,则两君相见之乐也”(徐元诰 179)。《文王》明显是祭祀文王的祭歌,《大明》歌颂了周武王在牧野打败商纣王的胜利,《绵》写古公亶父率领周人从豳迁往岐山周原的历程,与“两君相见”的意义并没有多大联系。并且仪式化用诗有明显的等级性,而这种等级性通过用乐的等级性体现出来。王国维在《释乐次》中分析了先秦典籍认为“大夫、士用《小雅》,诸侯燕其臣及他国之臣,亦用小雅”,“两君相见,则用《大雅》或用《颂》。天子则用《颂》焉”(王国维 90—91)。可见在仪式中,起区别等级作用的主要是乐而非诗,大致是“观乐者身份愈高,则所用之乐愈古,依次递减”(陈致 143)。诗依赖与相关的乐配合才起区别意义。再次,诗的重要性不及乐舞,还表现在《诗经》中产生较早的“颂”“雅”“南”的命名即来源于乐舞。郑玄认为“磬,在东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颂,颂或作庸,庸,功也”(《周礼注疏》卷二十三 1722)。把颂说成是摆放音乐的方向或地点的名词。阮元、魏源和一些现代学者认为“颂”字源自“容”字。阮元认为所谓的“容”,是指伴随诗乐表演的“舞容”。在此基础上有些学者如张西堂认为“颂”就是一种叫“镛”的乐器(张西堂 114—15)。《诗经》中的“雅”是配合周代雅乐的诗的集合。“雅”与“夏”的假借关系,经王引之、朱东润、孙作云等人的探讨,学界已经广泛接受。而关于“南”,陈致在郭沫若、唐兰等人的研究基础上认为“南”是“初生之竹”之义,像早期一种竹木制筒形器物,其后用来指南方的钟镈类乐器,进而代表南方某种特定的音乐体式。陈致认为“风”“雅”“颂”“南”之称,本为乐器或地域名。“雅”“颂”“南”本是具有地方色彩的不同乐钟,而“风”则本为普通乐器的总称(陈致 197)。以乐舞有关的概念区别编结诗篇显示了在诗乐舞三者中乐舞(特别是乐)的主导性地位。
二、春秋赋诗的文本化色彩
到春秋时期,乐舞制度发展产生了新的变化。诗与乐舞逐渐分离,诗的地位逐步凸显出来,并趋向文本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春秋外交场合赋诗言志现象的出现。不可否认春秋赋诗与西周乐舞仪式中的歌诗有直接的关系,刘丽文认为:“赋诗言志是对宴享之礼中原有中乐歌形式的模仿和意义的替换”(刘丽文 183)。但是与歌诗不同的是,赋诗观志对诗文本意义给予了更大的重视。甚至可以说赋诗观志中需要直接依托的便是诗的文本意义。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谈到春秋时期《诗》的文本化色彩,并不是说《诗》的文本化是从春秋时期才开始出现的。应该说从牧野大战后,武王命周公创制《大武》乐开始,周公有意识地集结《武》《时迈》《赉》《酌》《般》《桓》以配乐舞,诗的文本化就已经开始,到春秋外交赋诗言志表明《诗》自西周时期的与乐舞紧密结合的仪式性已经产生动摇,诗面临重视文本意义的时代需求。
周公制礼作乐的目的在于以礼乐文化为依托实现其政治统治。随着周王室的衰微,特别是平王东迁之后,周王室几乎丧失了天下共主的实际地位,然而礼乐文化却依然在各诸侯国存续着,各诸侯国在外交场合依然延续了西周时期的乐舞习惯,很大的目的是通过这一行为显示自己对周王室的尊奉与礼法制度的践行。同样,对具有深远传统与广泛影响的西周仪式的延续,也是诸侯国自身政权合法性的展示。但是源自周初的仪式,在春秋时期出现了明显的损益。通过传世文献,我们发现在春秋外交燕飨场合,乐舞仪式发生了如下变化:
首先,春秋时期乐舞仪式中多有省略状况,诗在仪式中的重要性明显增强。如《左传·襄公四年》:
穆叔如晋,报知武子之聘也,晋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鸣》之三,三拜。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礼,藉之以乐,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细,敢问何礼也?”对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与闻。《文王》,两君相见之乐也,臣不敢及。《鹿鸣》,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劳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必咨于周。’臣闻之:‘访问于善为咨,咨亲为询,咨礼为度,咨事为诹,咨难为谋。’臣获五善,敢不重拜?”(《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九4192—93)
王国维在分析先秦文献的基础上,总结认为西周仪式用乐大致分为金奏、升歌、管、笙、间歌、合乐、舞、金奏等环节(王国维 103)。《左传》记载外交燕飨仪式明显省略了不少环节,但都保留了歌诗环节。歌诗环节对整个仪式的进行有重要意义,晋国乐工的奏乐、歌诗需要穆叔的理解与反馈才得以顺利进行。这表明了诗至少与乐有了同等重要的作用(很明显其作用更加重要)。不论是仪式本身的省略还是《左传》记录者的省略,都显示了在仪式中对诗文本意义的重视。不仅如此,《左传》记载春秋时期还有非仪式场合的赋诗活动,如《左传·文公七年》载:
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犹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辞,若何?不然,将及。摄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为寮,吾尝同寮,敢不尽心乎?”弗听。为赋《板》之三章,又弗听。及亡,荀伯尽送其帑及其器用财贿于秦,曰:“为同寮故也。”(《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九上 4007)
同书襄公十四年载:
夏,诸侯之大夫从晋侯伐秦,以报栎之役也。晋侯待于竟,使六卿帅诸侯之师以进。及泾,不济。叔向见叔孙穆子,穆子赋《匏有苦叶》。叔向退而具舟。(卷三十二 4247)
从上下文看这两例赋诗没有隆重的礼节,甚至可以说没有音乐相配,应该不是在燕享礼的场合。荀林父在直接用语言劝阻无效后,再次通过赋诗相劝。《板》的第三章为“我虽异事,及尔同寮。我即尔谋,听我嚣嚣。我言维服,勿以为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毛诗正义》卷十七1183)。荀林父赋此当是取“及尔同寮”和“听我嚣嚣”的意思,即从同僚之谊出发希望先蔑听取自己的建议。《匏有苦叶》有“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毛诗正义》卷二 637)句,叔孙穆子赋此当指虽泾水很深,但深有深的渡法,浅有浅的渡法,总之一定要渡过去。大有破釜沉舟,同仇敌忾的意思,因此才能激励叔向渡河。可以看出,在春秋时人看来,赋诗的表达效果要强于直接用言语表达。至于为什么赋诗效果强于直接用言语说明,这不仅是因为诗的文雅风格以及这个时代贵族的审美倾向,更主要的是在这个时代诗在文化上依然有着权威性。诗所传达的并不只是诗篇所象征或隐喻的意义,而是借助三位一体的仪式在礼乐制度下产生深刻影响后,诗已然成为了一种代表性的文化标志。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周代礼乐制度的直接承担者。赋诗是这样的,其实更具代表性的是《左传》中出现的大量引诗方式,即将诗句作为经典、真理、权威去佐证自己的观点。
其次,春秋时期乐舞活动中赋诗者身份发生了变化。《周礼》《礼记》所记在西周典礼仪式上,歌诗由乐工来完成。而到春秋时期,卿大夫成为仪式赋诗的主要参加者,《左传》所记载的76首诗篇,其中卿大夫赋诗52篇次,占绝大多数。董治安将《左传》赋诗者的身份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诸侯,如秦穆公、晋襄公、鲁文公、楚灵公、鲁襄公、晋平公、小邾穆公、宋元公、秦哀公;第二类为王侯夫人、子女,如晋公子重耳、宋宣公夫人穆姜、姜戎之子驹支等;除此之外都是周王朝或者各诸侯国的卿大夫(董治安 28)。卿大夫之间的赋诗由于涉及人数多,一场赋诗活动不止是一两个人赋诗,每人也不限于赋一次诗,如文公十三年郑伯鲁文公宴于棐,子家与季文子之间就进行了两轮赋诗;襄公二十七年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出现了子展、伯友、子西、子产、子太叔、公孙段等七人的盛况;昭公十六年郑六卿饯韩起,亦出现子齹、子产、子太叔、子游、子旗、子柳和韩起的七人赋诗盛宴;襄公十六年晋侯与诸大夫宴于温,这次宴会有晋、宋、卫、郑、曹、莒、邾、杞、小邾等九国参加。刘毓庆认为春秋时期在世卿公族之中,涌现出了一批“诗礼名家”,并提出了有春秋诗学十家的说法(刘毓庆 郭万金 42)。诸侯、卿大夫等的参与表明诗已经由乐工独掌扩展到了仪式活动的所有参加者身上,或者说掌握诗已经成为贵族社会活动中的一项必要技能。《诗》文本在诸侯国间已经得到广泛传播。
诗的文本化色彩还表现在赋诗仪式中大量解诗、评诗现象的出现。在春秋典礼赋诗仪式中,有赋诗双方仅以诗对答的现象,但绝大多数的赋诗仪式中有解诗、评诗现象。如前文所引襄公四年穆叔如晋对《肆夏》《文王》《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的评价。再如僖公二十四年秦穆公与重耳之间的赋诗,针对秦穆公赋《六月》,赵衰解释为“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五 3942)而评诗现象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了。因其所评诗大致不出今本《诗经》范围,据此可见至迟到襄公二十九年今本《诗经》统一的编结本已经出现。在赋诗活动中,听诗者需要对赋诗者进行反馈,而反馈的内容或是关于该诗的适用问题,或是该诗的文本意义,或是基于在文本意义之上新意义的认识。解诗所涉及的诗的适用问题,着重强调的是诗乐的等级化,这固然是诗的仪式意义在春秋时期的延续。但是关于诗乐适用性问题的探讨,恰恰也表明诗乐适用性问题在这一时期的陌生,以及诗的仪式意义在这一时期的生疏。而大量关于诗文本意义的评论,彰显了诗文本意义在这一时期的成为新的讨论热点。
三、诗的传播从重仪式到重文本的转变意义
从西周歌诗到春秋赋诗,《诗》的传播经历了从重仪式到重文本的转变过程。伴随这一转变的背后是有关西周文化如何传承的深刻问题。
(一)仪式的一致性维护了文化的一致性
如前文所言,西周时期诗与乐舞密切结合,是礼乐仪式的一部分。与其他方式相比,仪式的特殊性在于它能够原原本本地把曾经有过的秩序加以再现。在西周礼乐制度下,祭祀仪式以诗乐舞的形式叙述和再现祖辈的丰功伟业,通过重复某些《颂》或《雅》诗篇目一方面实现宗族的认同,另一方面也明确了一种既定的等级制度。而燕礼仪式同样按照身份等级划分,各个身份等级有其适用的仪式,彼此不僭越。在符合身份的场合中仪式用诗重复上演着。在西周仪式用诗中,升歌阶段的篇目固定在《鹿鸣》《四牡》《皇皇者华》《清庙》,笙阶段固定在《南陔》《白华》《华黍》,间歌阶段固定在《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由庚》《崇丘》《由仪》;合乐阶段固定在《周南》的《关雎》《葛覃》《卷耳》,《召南》的《鹊巢》《采蘩》《采蘋》。这些篇目在仪式中的重复歌唱,使得仪式的参加者不断联想起祖先的功业与德行。而重复这个仪式也就是传承相关知识的过程。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把这种借助仪式来传承文化意义的形式称为“重复”的压力,并认为正是这种压力保证了仪式的一致性(阿斯曼 87—88)。在仪式一致性的背后所秉持的是周代礼乐文化的一致性,即根植于周民族记忆深处的宗法观念与文德武功思想。这种宗法观念与文德武功思想一方面是周人构建起来的用以解释自己政权合法性、正统性的工具,另一方面也是用以维系本民族统治与发展的重要纽带。我们认为西周礼乐制度背后的宗法观念与文德武功思想使得周民族获得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一种集体认同。正是这种集体认同,使得周人在取代殷商政权及其后的很长一段统治时间内能够持续保持民族的自信心与凝聚力。正如陈来所言:“在西周文化中,人的地位与身份等级的规定,行为细节的规定,礼仪举止的规定,所有这些一个人从孩提起开始学习,养成为一种艺术。这种典型的封建时代的文化在那个时代是一种文明、一种文化上的进步。礼从文化上说也就是教养,在社会上说就是秩序”(陈来 260)。而孔子所谓的“诗可以群”也正是据此而言的。仪式化用诗重要的是诗乐舞三位一体所传达的意义,但并非不关注诗本身的意义。诗的文本意义是仪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这种文本意义并不独立显现,而需要借助乐舞来展现。诗因与乐舞的搭配,其本身的内容意义更加趋于稳固,避免了纯文本传播所导致的多义性解读。而实际来看,正是依赖仪式的一致性,使得礼乐制度背后的周王室的礼乐文化得到持续传承。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室虽然在政治、军事上无力维系其天下共主地位,但诸侯国仍然不得不打着“尊王攘夷”的口号进行实际的征伐,甚至出现对礼制讨论的新热潮,这显示了仪式一致下诗所传承的文化观念的一致性。
(二)仪式的解体导致了文化一致性的消解
然而随着时代发展,西周礼乐仪式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仪式的复杂化逐渐导致了仪式中诗乐舞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即诗与乐舞逐渐疏离,并最终促使仪式一致性的解体。《诗大序》提出了诗的正、变问题。古代的学者多将诗的正变原因归结到政治背景上,而近代学者认为诗的正、变与其使用方式变化有关。魏源认为:“诗有为乐作、不为乐作之分,且同入乐而有正歌、散歌之别。”他认为在入乐的诗中,用于“正歌”的就是“正诗”,用于“散歌”的就是“变诗”。过常宝认为:“在一套复杂的仪式中,诗乐会在不同阶段出现,用于核心仪节的则是正乐正诗,否则,就是变乐变诗”,“西周早期祭典相对简略,可能只有一次乐舞,皆为正乐正诗;随着时代的发展,仪式过程更加复杂,乐舞的层次开始多起来,于是就有主次之分,也就形成‘正’和‘变’的区别”(过常宝 258)。顾颉刚指出典礼中所用的乐歌有“正歌”“无算乐”和“乡乐”三种。其中“无算乐”主要用于娱宾不受礼仪的束缚。过常宝认为春秋赋诗言志是从西周典礼仪式的“无算乐”发展而来的。在“无算乐”阶段,仪式的参与者饮酒、听乐都不算数量,可以随意命乐工奏唱诗歌。“无算乐”仪式不仅使得诗与乐舞分离开来,而且用“诗”的数量和次数大为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无算乐”阶段,仪式的参与者关注的就是诗的文本意义。
与仪式的复杂化以及仪式性的逐渐解体同时发生的是仪式背后所体现的周礼的陌生化。特别是在平王东迁后,周王室虽然曾有过短暂的中兴,但是再也没有实力如西周时期那样行使有效的中央统治了。与各诸侯国实力增长相对应的是诸侯国对周礼的漠视与僭越。僭礼、违礼现象的普遍发生,使得以诗乐舞为依托的周代礼乐制度逐渐丧失了原有的维护宗法关系的存在意义。仪式性的诗乐舞转变为娱乐化的展演。与传统上“礼崩乐坏”认识不同的是,近年来不少学者如晁福林、徐令杰、杨文胜等人认为春秋时期并非“礼崩乐坏”,而是一个礼学的繁荣时期。这种观点肯定了春秋时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西周礼乐制度的变革,也认识到了“礼崩乐坏”背后反映出来的礼学的重构问题,很有意义。《左传》中大量谈礼现象反映了礼制在这一时期被重视,甚至成为了一个热点。但也同时表明了这一时期正是一个对周礼陌生的时期。因为正是因为陌生才需要郑重其事地重新讨论。前文所引襄公四年尽管在宴会上穆叔对晋国乱用礼乐的现象进行了纠正,但借此也可以反映出伴随周礼的陌生化背后直接的结果便是文化一致性的消解。而春秋时期大量僭礼、违礼这种“礼崩乐坏”现象的出现也表明了曾经赖以维持周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的礼乐文化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传承上的重大挑战。
(三)春秋赋诗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文化的一致性
在礼学的重构过程中,诗开始承担起独立的价值。在春秋谈礼的事例中,诗往往作为权威性的佐证观点而被引用。诗已经逐渐与乐舞分离,具有了独立的文本价值。从仪式中逐渐解体出来的诗要想独立承担起维护文化一致性的责任首先必须具备文本的一致性。而文本的一致性所要求的是关于诗义的权威性解读。春秋时期虽然出现统一的诗文本,但是我们不能认为统一的诗文本的出现就代表诗已经具有了文本一致性。诗从仪式一致性中脱离出来,在实际用途中对文本意义的重视,使得诗的传播面临新的问题。因为文本虽然是唯一的,但是不同的人对文本的理解与解读却是多义的。文本的价值在于其传承意义,而只有经过阐释后的文本才具有其传承价值。因为“阐释具有奠基意义的文本的过程就是储存和再现知识。从文化史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转移”(阿斯曼 88)借助经典的阐释,诗才能够重新承担起传承西周宗法观念与文德武功思想的责任。
春秋时期诗的文本意义开始凸显,但是并没有脱离其仪式意义。正是文本意义与仪式意义的结合,使得诗背后的宗族观念与文德思想在春秋时期依然延续下来。等诗文本与仪式彻底脱离开来,诗的仪式一致性彻底解体,对诗的权威性解读尚未产生,其文本的一致性尚未出现的时候,诗背后的宗法思想与文德观念便出现了传承上的断裂现象。春秋时期诗的仪式一致性逐渐解体,文本一致性尚未形成。这数百年间并未出现文化传承上的断裂现象,这中间是什么在维护着文化的持续传承?这成为我们思考的另一个问题。笔者认为春秋赋诗凸现了诗的文本化色彩,而恰恰是春秋赋诗中遵循的相关原则在这一时期暂时维护了文化的一致性。
“赋诗断章”是春秋赋诗最突出特点。杜预认为“取其一章而已”(《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八4342),杨伯峻更加明确地说:“赋诗断章,譬喻语。春秋外交常以赋诗表意,赋者与听者各取所求,不顾本义,断章取义也”(杨伯峻 1145—46)。这种观点认为“赋诗断章”是将诗文本割裂开来,选择适用自己的诗句。这反映了这一时期诗文本意义的彰显。然而这样的认识忽略了一个现象,即大量的赋诗其实并不背离整首诗的文本意义。其实,赋诗断章中,不论赋诗者还是听诗者都建立在对整首诗熟知的基础上,只是以被赋章节为依托进行某种意义的传达,赋诗者所赋章节的文本意义是明显和直接的。相对而言,整首诗的意义虽然显得不明显,却是赋诗双方表达的文化背景,不可谓不重要。
而与赋诗断章这一方法密切相关的是春秋赋诗的目的,即“赋诗言志”。《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诗正义》卷一 563)。赋诗者借助诗表达自己(国家)的态度。也就是将自己内心的“志”借助已有的诗篇传达出来。通过分析春秋赋诗的事例可以发现,这一时期赋诗所言的“志”并非赋诗者个人的情感,而多是其所属的集团或国家的群体态度与心声。从实际来看,与仪式化用诗的内容相似,赋诗言志的内容仍然不出西周礼乐所讲究的宗法观念与文德武功思想。从这个角度来看,赋诗言志在实际上肩负起了这一时期文化传承的责任。其实更能说明这一点的是“歌诗必类”的原则。
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荀偃怒,且曰:“诸侯有异志矣!”使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归。于是,叔孙豹、晋荀偃、宋向戌、卫宁殖、郑公孙虿、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讨不庭。”(《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三 4261)
在这次宴会上,晋侯提出的指导原则是“歌诗必类”,即诸侯大夫歌诗必须与舞蹈相配合。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考察诸侯是否有“异志”,这说明春秋时期诗文本义的使用与乐舞依然有密切关系。“必类”的强制要求暂时维系了诗仪式的一致性,也保障了诗文本意义的规范化使用。关于“同讨不庭”,与其如前人那样将“不庭”解释为不朝奉盟主,不如将其解释为不朝奉周王室更符合春秋时期的实际。因为这一时期晋国的身份是“诸侯之长”,并没有取代周王。晋侯依然需要依靠西周的礼乐文化来维系其盟主统治。礼乐文化成为强国用来征伐的理由与借口。襄公十六年高厚“歌诗不类”造成诸侯“同讨不庭”。此外,襄公二十七年垂陇之会伯有赋诗不类,文子预言其有杀身之祸。透过这些“诗祸”可以看出,春秋赋诗中虽然文本义彰显,但诸侯盟主竭力通过“必类”的原则来维护仪式的一致性,进而试图保障西周礼乐文化的一致性传承。
而春秋时期与赋诗相伴随的大量解诗、评诗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文本阐释行为,如《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
郑之入滑也,滑人听命。师还,又即卫。郑公子士、洩堵俞弥帅师伐滑。王使伯服、游孙伯如郑请滑。郑伯怨惠王之入而不与厉公爵也,又怨襄王之与卫滑也,故不听王命而执二子。王怒,将以狄伐郑。富辰谏曰:“不可。臣闻之:大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 邘、晋、应、韩,武之穆也。 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如是,则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五 3944—45)
周大臣富辰对周襄王的劝谏中实则包含了对《小雅·常棣》诗旨的解读,围绕着《常棣》一诗,富辰追述了其背后的深厚历史渊源与其现实意义。这种解读完全从诗文本意义出发,并不涉及诗的仪式色彩。此外襄公七年晋韩献子告老,卫孙文子聘鲁;襄公十一年魏绛答晋侯赐乐;襄公二十四年郑子产寓书范宣子、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等场合都有解诗、评诗活动。这些解诗、评诗者多是具有丰厚素养的诗礼名家,他们的解诗、评诗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诗的文本意义进行限定,在避免诗文本意义的多样化解读的同时,也对维护诗背后所承载的文化一致性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文化一致性的传承尚需经典阐释的出现
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个时期诗的仪式一致性已经开始解体(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春秋时期才出现大量谈礼、说礼现象)。尽管诸侯盟主竭力去加以维护,但是一则这是一种强势的政治力量干预,已经迥异于西周时期仪式化用诗的初衷。换句话说,需要靠强权力量干预的仪式化用诗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其原有的感染力,而这种感染力正是仪式发挥其维护文化一致性功用的主要途径。这个时期仪式正逐渐沦为一种“形式”。再则随着诸侯国力量的此消彼长,盟主不断变更,如果说襄公十六年的盟主晋国与周王室有着亲密的文化及血统渊源,其倡导的“歌诗必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试图维护西周文化一致性的努力,那么其后升为盟主的楚国,与周王室则并无多么深远的关系,也断无“歌诗必类”的必要了。也就是说在诗文本一致性形成之前,仅仅依赖这些赋诗原则来维护文化的一致性传承显然是无力的,这样的效果也是短暂的。
此外春秋时期大量解诗、评诗现象的出现也从侧面反映出文本化用诗过程中对诗经典阐释的价值与必要性。尽管这些解诗、评诗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诗文本的意义,但是这个时期没有有效的传播机制将这些解诗、评诗话语传播开来,或传承下去。诗背后承载的礼乐文化的一致性传承尚需经典阐释与经典传播机制的出现。而其中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则肩负起了诗意义传承的责任,不断尝试对其进行经典化阐释,并以学派的机制承担起传承周代礼制背后的宗族观念与文德思想的担子,为构建诗文本的一致性而不懈努力。直至诗的经典化阐释出现,诗上升为《诗经》,诗才具有了文本一致性,才能独立承担起传承民族文化精神的沉重责任。
注释[Notes]
① 参看陈致:“‘万舞’与‘庸奏’:殷人祭祀乐舞与《诗》中三颂”,《中华文史论丛》总第32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5页。
② 参看贾海生:“周公所制乐舞通考”中所列表,《文艺研究》3(2002): 第82——93页。
③ 参看王国维《观堂集林·释乐次》所附《天子、诸侯、大夫、士用乐表》。王国维:《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03—104页。
④ 参看魏源:《古诗微·诗乐篇》,《魏源全集》(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第27页。
⑤参看晁福林:“春秋时期礼的发展与社会观念的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4(1994):47——57。 徐令杰:“春秋战争礼考论”(《东北师大学报》2(2000):73——77。 杨文胜:“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了吗?”,《史学月刊》9(2003):25——31。
⑥ 曹建国:“‘赋诗断章’新论”,《兰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2015):12——19。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尚书正义》,阮元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Annotations to The Book of Ancient History.Collections of Annotations to the 13 Confucian Classics.Ed.Ruan Yuan.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0.]
《春秋左传正义》,阮元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Annotations to The History of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s Interpretated by Zuo Qiuming.Collectionsof Annotations to the 13 Confucian Classics.Ed.Ruan Yuan.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0.]
《周礼注疏》,阮元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Annotations to Rites of the Zhou Dynasty.Collections of Annotations to the 13 Confucian Classics.Ed.RuanYuan.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0.]
《礼记正义》,阮元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Annotations to The Book of Rites.Collections of Annotations to the13 Confucian Classics.Ed.Ruan Yuan.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0.]
《毛诗正义》,阮元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Annotations to The Book of Songs Interpretated by Mao.Collections of Annotations to the 13 Confucian Classics.Ed.Ruan Yuan.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1980.]
扬·阿斯曼:《文化记忆》,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Assmann, Jan.Cultural Memory and Early Civilization.Trans.Jin Shoufu and Huang Xiaochen.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Book Company, 2015.]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
[Chen, Lai.Ancient Religion and Ethics: the Root of Confucianism.Beijing: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6.]
陈致:《从礼仪化到世俗化——〈诗经〉的形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Chen, Zhi.From Etiquette to Secularization, the Formation of the Book of Songs.Shanghai: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9.]
董治安:《先秦文献与先秦文学》。济南:齐鲁书社,1994年。
[Dong, Zhian.Pre-qin Literature and Pre-qin Literary writings.Jinan: Qilu Press, 1994.]
过常宝:《制礼作乐与西周文献生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Guo, Changbao.Ritual Formulation and Music Composition and the Making of Western Zhou Texts.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Academy Press, 2015.]
刘丽文:《春秋的回声——左传的文化研究》。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
[Liu, Liwen.The Echo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 Culture of Zuo Zhuan.Beijing:Beijing Yanshan Book Company, 2000.]
刘毓庆 郭万金:《从文学到经学——先秦两汉诗经学史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Liu, Yuqing and Guo Wanjin.From the Literary to the Classics: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etry in the Pre-Qin Dynasty and Han Dynasty.Shanghai: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Book Company, 2009.]
王国维:《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Wang, Guowei.Guantang Jilin.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59.]
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Xu, Yuangao.Collected Commentaries on Guoyu.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2.]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Yang, Bojun.Annotations to The History of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s.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2009.]
张西堂:《诗经六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
[Zhang, Xitang.Six Studies Related to the Book of Songs.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