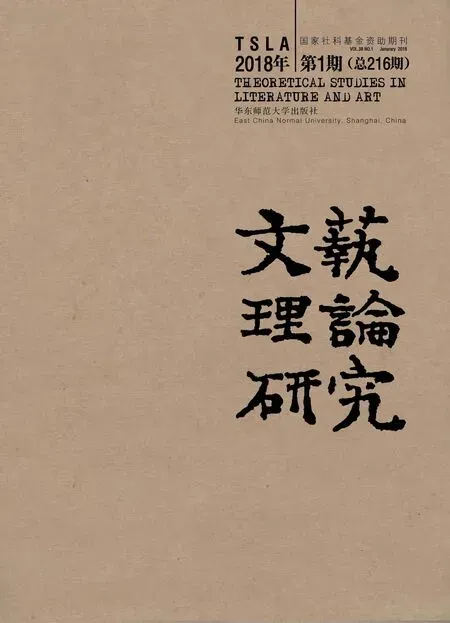“反现代的现代性”之考辩
——兼论理论在双向旅行中的结构变化
吴娱玉
1997年,汪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犹如一枚重磅炸弹,在学界激起轩然大波。此文对1990年代中国社会的思想状况进行了评述,它的亮点,也是其后聚讼纷纭的焦点在于:汪晖一反“新启蒙”运动对共和国以来思想状况所形成的共识,独辟蹊径地提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136)。这一观点甫一亮相,就让众多学者为之振奋,引为同道,比如李杨、韩毓海、旷新年、贺桂梅等人,一时间,“反现代的现代性”成了“新左派”的理论宣言,进而成了“新左派”现代史观(特别是文学史观)的结构性要素。
鉴于“反现代的现代性”是中国思想界左右之争所瞩目的焦点,具有极其强大的思想含量,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和必要来重新梳理它的发生的来龙去脉,并在此基础上对它作出理论反思。事实上,这一理论并非植根于中国,也不是汪晖的原创,而是由西方左派理论家最先提出,影响了求学西方的中国的青年学者,或者经过翻译漂洋过海地影响了本土学界。早在1993年,德里克的《现代主义与反现代主义: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被翻译成中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本文详细地论述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具有“反现代的现代性”特征,显然,汪晖深受影响。同年,海外学者唐小兵编撰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一书阐述了一个核心观点:延安文艺所代表的大众文艺是“一场反现代的现代先锋派文化运动”(6)。几乎同时,李杨的《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一书问世,论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反现代”的“现代”意义。因为唐、李二人的讨论拘囿于文学,没有在思想史层面上进行充分的展开,所以他们的观点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1996年,刘康的英文文章《现代性不同选择与文化革命——毛泽东与阿尔都塞的理论思考》也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现代性不同选择”,虽不能判定此文对汪晖产生过影响,但仍不失为一种参照。直至1997年,“反现代的现代性”经汪晖长篇、系统的阐释,成为最炙手可热的理论话语。
本文聚焦于德里克、刘康、汪晖关于“反现代的现代性”的论述,比较中西文论不同语境中对中国问题的理解和阐释,探讨一种理论如何“迂回与进入”、进而如何完成由中向西、由西向中的双向旅行。具体来说,西方理论家借用作为“他者”的中国的经验进行理论生产,此时的中国是欧美思想资源之外的一种抽象元素,当这一理论经过旅行被重新引回到中国语境时,中国又被还原成一种显性、具体的元素,就在这样的双向旅行过程中,整个结构发生了微妙的翻转,其中被置换的概念、被抽离的语境、被修改的问题意识以及新附加的观点都必须得到重视和清理。本文所要做的正是分析和还原这一理论结构转变中隐而不彰的部分。
一、德里克“反现代的现代主义”的内涵
法国五月风暴挫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活动,而那些因挫伤而更加激荡的反叛情绪成为了左翼知识分子挥之不去的情结,于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目光投向中国,认为中国是左翼运动硕果仅存的一块飞地,也是马克思主义贯彻地最好的一片试验田,顺理成章,左翼情结浓厚的德里克便以中国为例,尤其以毛泽东的理论实践来对抗资本主义现代性。德里克在《现代主义与反现代主义: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详细地论述了“反现代的现代主义”这一理论,认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现代的现代性”,德里克的这一“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提法来自于马歇尔·伯曼的《一切凝固的东西都化为乌有:现代性经验》一书(Dirlik 59—60),实际上他是将伯曼关于马克思的论述和毛泽东的理论实践嫁接后的结果,所以,要弄清这一问题,首先要从伯曼“反现代性的现代主义”开始,他的论述是根据如下步骤铺陈开的:
首先,什么是现代性?德里克认同并吸收了伯曼关于现代性的阐释,即是一种在具体空间和时间中感受到的经验,这种经验是充满矛盾、悖论,处于无休止的变化和解体之中。“它向我们许诺了冒险、权力、快乐、成长以及我们自身和世界的变化,与此同时它又危胁着要摧毁我们所拥有的、所知道和所归属的一切……现代性把全人类统一了起来。但是这是一个充满悖论的统一,一个没有统一性的统一;它把我们所有人都注入旋涡中,一个斗争和矛盾的旋涡,一个混乱和焦虑的旋涡”(Berman 15)。不止伯曼,大卫·哈维也强调了现代性的悖论:“现代性即使对他自身的过去也不尊重,更遑论对一切眼前的前现代的社会秩序了。事物的易变性使得人们难以保持任何历史连贯性意识。如果历史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它的意义必须在变化的旋涡中去发现和界定。现代性不仅要无情地打破任何或者一切以前的历史状况,而且它的特征就在于,它意味着一个自身内部永无止境地进行着内部分裂和解体的过程”(Harvey 11—12)。这样一来,现代化就是制造(和继续制造)现代性状况的历史过程:“科学的发现、工业的膨胀、人口的变迁、都市的扩张、民族国家、大众运动——所有这一切最终都是由‘正在扩张且在急剧动荡着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推动的”(Anderson 97)。这样的现代性,令人喜忧参半。一方面,现代性的力量源泉是科学和科学思维的巨大创造力,这种创造力植根于批判理性和坚信人类为改善自身状况就必须去理解世界、改造世界的启蒙信念之中,并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和社会技术得到体现。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看到创造力所隐含的毁灭性力量:创造力在征服世界的同时摧毁了人类的生存条件,破坏了那些赋予人类生存以稳定性和可靠性的社会关系;它把人性从大自然中解放出来,又顺手把它关进一个由工厂、贫民窟、混凝土丛林以及理性化国家的官僚主义迷宫所构成的“铁笼”之中。伯曼还区分了现代性经验和现代主义:现代性经验是对于努力克服现代性矛盾的无休止试验的经验,而现代主义则是“现代的男男女女们试图不仅成为现代化的客体而且成为它的主体,试图理解并支配现代世界的一切努力”(Berman 5)。对此,德里克认为:现代性是一种经验,而现代主义则是一种努力和实践(Dirlik 60—61)。
其次,什么是“反现代主义”?伯曼认为,反现代主义是针对现代主义提出的,它分享了与现代主义相同的矛盾,如果不参照现代主义,我们就无法理解反现代主义。更重要的是,因为反现代主义本身是由试图实现现代性目标的冲动所驱使的,反现代主义就代表了一种新的现代性追求:只要现代化在实践中没有及时实现(或者背叛了)解放人类的诺言(这一诺言曾在理论和实践中激励了现代化),那么新的现代化就必不可少(Dirlik 61—62)。
再次,什么是“反现代的现代性”?伯曼认为,社会主义是反现代主义的,但它却不可能反对现代性或现代化,在过去两个世纪里,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就是要超越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以便创造出一种新的现代性,这样一种崭新的现代性无限接近于启蒙运动关于人类解放的境界的描述。伯曼说,马克思是伟大的现代性分析家,又是一位现代主义者,他对现代性问题的解决方案体现了现代主义的最深刻矛盾(Berman 11)。马克思认识到,资产阶级在突破过去、征服自然方面获取了惊人的成就,但也为这些成就付出了惨痛的文化代价——“一切凝固的东西都化为乌有”。所以,他的著作试图描绘出(资产阶级)现代化同作为它的文化表达的现代主义之间充满矛盾的关系,而化解矛盾的可能性,就在于其本身也是现代性产物的阶级——无产阶级。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将会从现代性中获得丰富的(解放的)可能性,这样的可能性,资产阶级则因为自身的意识形态缘故而注定会擦肩而过:“现代性的创伤”只能通过“更加充分、更加深刻的现代性”来治愈(Berman 98)。
德里克深受伯曼“反现代的现代性”理论的启发,同时也质疑伯曼所理解的现代主义存在着严重的局限。他认为在第三世界的历史背景下,不能把第三世界的现代主义认为只是欧美现代主义的简单延伸,如果现代主义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就必须超越(Dirlik 63)。于是,德里克引入了中国的维度,将这一理论与中国嫁接。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而两者可以有效嫁接的联结点就在于“矛盾论”。德里克认为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矛盾的论述以及对待矛盾的做法可直接同毛泽东思想形成对照。毛泽东思想把矛盾的概念指认为把握一个流逝、分裂、冲突的世界的最合适的工具。作为社会和自然的能动原理,矛盾被当作原动力,这样一种作为原动力的矛盾在毛泽东思想中具有核心的作用——“一切事物都包含着它的对立面”甚至成了认识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里克认为马克思主义给毛泽东提供了现代性和现代化的语言,也正是在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当中,现代性的复杂和矛盾才彰显得格外分明:毛泽东思想把中国的现代性看作是矛盾的相互作用,而它自身的矛盾性则是解决这些矛盾的根本性策略。在第三世界民族的情形中,前者表现在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结构中,这一思想结构反映了现代化和现代性的矛盾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矛盾。后者则体现在毛泽东力图解决那些与其理论的信念相对立的矛盾所具有的矛盾性。德里克认为毛泽东对于现代性的矛盾心理与马克思对于现代性的矛盾心理具有精神上的一致性,所以说,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反现代的现代性”,具体体现如下:
第一是抵御全球化意义。现代性是欧美缔造的产物,中国的现代性尽管也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力量的产物,但是毛泽东在中国的背景下重新阐述马克思主义时,在现代性上打上了中国历史处境的烙印,正是这一处境导致了中国现代性的产生,并因此为现代主义在中国社会所采取的形式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这个社会是作为客体而不是主体而被迫进入现代性之中的。作为一个中国人和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力求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来改造中国,又根据中国特定历史环境的需要来改造马克思主义。中国从19世纪开始就被卷入到了全球的历史之中,在这个历史中,资本主义是其最主要的动力,而中国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的基本目标都是抵御这一过程(Dirlik 69)。
第二是第三世界。中国社会不同于西欧和北美,但它同绝大多数亚洲社会和非洲社会(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有南美社会)一道经历了历史及其动力——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过程,这一过程不是本国内部发展的结果而是异国霸权的产物。当中国历史和全球历史结合为一体时,中国作为一个第三世界社会也经历了一个被征服的过程。在这一环境下,社会主义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的取代,而且也是一种要从资本主义霸权中解放出来的选择,一种让第三世界社会不是作为客体而是作为主体进入全球历史的选择(Dirlik 70)。
第三民族意义。中国社会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第三世界保存着它自身的历史特征。中国和全球历史的结合并不意味中国社会在全球的汪洋大海中消融了,正如作为一个第三世界社会,它的特征不能被归结为某种同质化的第三世界型构一样。中国的民族主义也是这一过程的产物。这种自然发生的民族主义对新的全球秩序及其依照欧美经验所理解的普遍的现代性设想发起了最初的革命抵抗。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带有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目的论色彩和欧美中心主义思想。现代性的复杂性集中表现于它直接的政治产物——民族主义问题。民族主义展示了既可成为现代化的推动力,又能抵制和克服现代性消极因素。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既是现代主义的又是反现代主义的(Dirlik 70)。
通过梳理德里克的思路,我们可以看出,德里克由伯曼始,到毛泽东终。伯曼先是论述了马克思对于现代性之矛盾的揭示,由此引申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现代的现代主义”的结论。德里克沿袭着伯曼的思路,等量代换成了中国经验:首先是马克思对于现代性的矛盾的揭示与毛泽东关于“矛盾”的方法论若合符契,其次是毛泽东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改造中国,又根据中国特定历史环境的需求来改造马克思主义,形成一种毛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所当然是一种“反现代的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反现代的现代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全球意义、第三世界、民族意义三个维度具体而分层地展现出来,它或许是一种不同于欧美现代性的更好的现代性。作为一位西方的理论家,德里克的问题意识在于反思西方现代性,力图在第三世界的语境中寻找一块冲破资本主义霸权的飞地。
二、刘康“现代性不同选择”的内涵
在《现代性不同选择与文化革命——毛泽东与阿尔都塞的理论思考》一文中,刘康是从阿尔都塞对于毛泽东的“症候式阅读”出发,也提出了毛泽东实践实际上是寻求“现代性的不同选择”,和德里克的分析路径不同,刘康主要是从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作为切入点的。他认为毛泽东的《矛盾论》启发了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从而催生出一场“理论革命”,使得传统马克思主义中的某些概念发生了结构性转变,毛泽东关于矛盾的“特殊性”和“不平衡性”的论述构成了“现代性不同选择”的意识形态基础,为阿尔都塞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提供了灵感源泉。
具体来说,阿尔都塞在《矛盾与多元决定》及《关于唯物辩证法》中“多元决定”的概念来自弗洛伊德,而其中的核心思想来自毛泽东《矛盾论》中关于矛盾“特殊性”和“不平衡性”的论述,为阿尔都塞构建“现代性不同选择”提供了哲学和理论基础。刘康依照詹姆逊的方法论,不再“把马克思主义定位为某种特定的立场(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哲学的立场);相反,应从马克思主义与某一特定问题复合体的密切关联上来认识它”(Jameson 175),于是,他将阿尔都塞和毛泽东的理论回归到各自具体语境,还原他们本来的问题意识。阿尔都塞的问题意识是为了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目的论、决定论,在这一语境中,斯大林现代性的不同选择被否定,那么毛泽东的现代性选择便进入了阿尔都塞的视野,同时,其矛盾观为阿尔都塞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点,反过来,阿尔都塞通过“症候式阅读”发现了一个隐藏于毛泽东理论和实践中的问题式,即对于现代性不同路径的寻求。也就是说,在阿尔都塞的重新解读中,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成为了一种不同形式的现代性选择。文章从三个方面论证了阿尔都塞的理论努力(Liu 10—11):
一、矛盾的“特殊性”与“现代性的不同选择”。毛泽东的《矛盾论》从绝对和相对两个方面界定了“普遍性”,这种界定与“特殊性”相关:
他们(教条主义)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他们也不了解研究当前具体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对于我们指导革命实践的发展有何等重要的意义。(毛泽东 304)
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毛泽东318)
刘康认为毛泽东“普遍性”的概念实际上意味着“矛盾的绝对性”在任何时刻与地方都等同于“矛盾的特殊性”。换句话说,毛泽东的“普遍性”就是绝对的“特殊性”。之所以这么认定,是因为毛泽东的文章几乎没有对作为形而上的、本体论概念的“普遍性”进行翔实的论述,“普遍性”往往只是为了说明“特殊性”而不得不出场的。
在批判黑格尔主义时,阿尔都塞抓住了毛泽东“普遍性”概念中所具有的认识论和阐释学本质,他将毛泽东的概念称为“普遍性的预备‘前提’”,并主张:
[……]真正懂得什么是唯物主义的人都知道,这个“前提”不是普遍性的前提,而是对业已存在的普遍性提出的前提,其目的与成果正是要拒绝这种普遍的、对“哲学”(意识形态)欲念所进行的抽象化,并强迫它回到自己的环境中,即回到具有科学特殊性的普遍性环境中。(Althusser 183)
阿尔都塞旨在对黑格尔主义中所具有的目的论的、形而上学的“普遍性”概念提出批判,他认为,除了在黑格尔主义那里,作为普遍性基本特征的“根本矛盾”并不存在:“因为将整体分为两部分的这种‘只有一组对立面的简单过程’恰是黑格尔矛盾的母型”(Althusser 195)就是在这里,毛泽东的看法被再次援引,以证实阿尔都塞关于“预先给定的、复杂的、结构性整体”的主张:
在他(毛泽东)全部的分析中,我们接触到的都是一些复杂过程;这些复杂过程拥有包含了多种不平衡决定因素的结构,该结构以一种原生性(而非次生性)的方式作用于这些结构。[……]因此,复杂过程始终都是既定的复杂体,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原则上,这些复杂体都无法还原为原始简单的过程。(Althusser 183)
毛泽东“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原则上”都拒绝了普遍性的简单起源,这种简单起源体现在作为现代性意识形态的黑格尔的目的论和决定论中。毛泽东拒绝给予这一概念任何优先性的战略显示出,他致力于提供现代性不同选择,进而以普遍之名将欧美中心的起源论排除在外。就此而论,毛泽东的矛盾论包含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含蓄却明白无误的批判,这一点经由阿尔都塞对毛泽东著作的解读而变得更加直白。
二、“多元决定”与现代性批判。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倒置”涉及一个复杂过程,它不仅是关系的倒置,也是“结构的转变”。具体来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建立在现象体现本质的“表达因果性”基础之上,或者说是建立在普遍性的“绝对精神”的目的论和决定论基础之上。与之相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一种包含着各个矛盾、各种因素,彼此缠绕又相互决定的结构关系,即“结构因果性”:它包含了“结构要素的决定关系,这些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以及这种结构影响下这些关系的全部效应。”以一种“令人惊讶的表现”“被复杂地——结构地——不平衡地决定”(Liu 11)。这种特定结构中各要素之间相互依赖、多元决定、不可化约的观念使得阿尔都塞既强调作为不可化约要素的上层建筑的“相对自主性”,又强调作为结构自身的效应。
阿尔都塞将传统马克思主义诸如“多元决定”“结构因果性”“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等概念进行充分的理论化,在他的理论体系中,他所制造的这些术语已经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内核发生了质的变化,也经历了性质上的“结构转变”。阿尔都塞所要完成的理论任务,是将马克思主义从作为现代性意识形态的目的论、决定论的启蒙理性中解放出来。通过阿尔都塞的“理论革命”,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概念发生了根本性和结构性的“转变”,比如经济决定论的破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区分,以及最为重要的一个概念——不同生产方式决定了界限明确的、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进程。阿尔都塞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做出“结构转变”,以使其内化为现代性批判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讲,阿尔都塞通过对矛盾论症候式阅读,寻找到了现代性的另一种路径,一种不同的现代性选择(Liu 11)。
三、“现代性不同选择”的具体展现:与中国实际结合。阿尔都塞对“特殊性”的理论陈述起始于两个独特的、具体的历史事件: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具体到中国,面对中国紧迫的政治、军事局势,毛泽东开创出“矛盾的特殊性”理论,《矛盾论》特别是其中的“矛盾的特殊性”一节对于中国历史状况、革命战争中战略、战术选择的大量分析,也就是说,矛盾论要解决的是在经济极其落后的农村,一支主要由农民组成的革命武装力量在战斗中不得不面对具有特殊性的具体问题。所以,《矛盾论》首先是一些活生生的战例,其次才被引申、升华成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毛泽东的“另类”理论努力还在于他对于本土思想资源,特别是兵家以及由兵家演变而来的道家的思想的吸收,这些思想资源对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框架中理解辩证法和矛盾的概念起到了重要作用。至此,可以总结出:毛泽东从一种产生于现代性时刻的普遍理论(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普遍主义角度来思考中国的特殊性,中国历史情境的特殊性和独特的思想资源又激发他开启出一种不同于以欧美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另类现代性”。
可以看出,刘康从阿尔都塞对毛泽东的“症候式阅读”阐释了“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思想渊源,其实是一种理论溯源,是在理论推演和文化阐释的层面进行的,意在说明毛泽东思想通过被西方左翼的嫁接和转变为西方左翼理论提供了一种另类的视角,从而对欧洲现代性思潮产生了一定意义上的反思和冲撞。尽管刘康和德里克的论证路径不同,但都是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反思西方现代性困境的一面镜子,殊途同归。与德里克不同的是,刘康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文化革命有更深刻的体验,他将对阿尔都塞和毛泽东理论的解读放在了各自具体的语境中,还原他们不同的问题意识,形成了双重发现和双重批判视角。一方面他站在西方左派的立场上用“矛盾论”思想对西方现代性进行批判,并认为矛盾论蕴含了另一种现代性选择的特质,他认为“中国‘文革’爆发的复杂的、多元的原因,并不能被简化为‘现代性不同选择是不可能的’这种断言。这种断言实质上是以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决定论意识形态为基础的”(Liu 20)。另一方面也辩证地思考并批判毛以及西方左派的文化革命理论,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毛泽东的初衷都是强调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作用来批判和修正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决定论,但到后来,他们都从一种决定论滑入了新的一种决定论,从经济决定论陷入了文化决定论的泥淖,历史决定论是现代性的主导思想逻辑,制约着形形色色的思想家,理论家。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毛泽东都未能超越决定论的思维模式”(Liu 3)。在此,刘康指出了阿尔都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文革的误读,也以此为镜鉴,反思了毛泽东从反一元(经济)决定论、本质论的思路走向另一种绝对化了的一元(文化)决定论的过程。刘康的“症候式阅读”发现阿尔都塞思想中蕴含的唯科学或科学主义的另一种一元决定论思维陷阱,进而犀利地批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逻辑。
三、汪晖“反现代性的现代化”
德里克和刘康实际上是在理论维度经由中国抵达西方,经历了第一次理论旅行,目的在于用中国理论反思西方,刘康的特殊性在于双向批判,而汪晖的“反现代性的现代化”是将这一理论再度引回中国,由西方抵达中国,这已经是第二次理论旅行,在这双向旅行中,整个结构发生了微妙的翻转,当左翼理论家借用中国经验进行理论生产时,此时,中国是一种抽象元素,当这一理论被重新引回中国语境时,中国被还原成一种具体元素。这里发生了两层转变:
(一)修改问题意识:
汪晖认为自近代以来知识界的历史反思集中于中国为什么未能成功地实现现代化以及中国应该如何实现现代化。到了1980年代,问题则集中在对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反思,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经常被视为反现代化或者前现代的方式。进入1990年代,中国的社会思潮还是拘囿于改革/保守、西方/中国、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市场/计划的二元论模式,在这样的对立模式中,当代中国真实的思想问题不可能得到揭示。正是基于此,汪晖发愿重新梳理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并提出“反现代性的现代化”理论。他的论证如下:现代化理论试图从欧美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提炼出现代化的基本规范,马克思就说,现代化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所以,现代化也就一定程度上被等同为资本主义化,但是,中国的情况不同。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工程是由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由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现代化工程,既是一种以实现现代化为基本目标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是一种“另类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汪晖的这一观点在两个维度上契合了德里克和刘康的观点,首先他和德里克的“反现代的现代性”观点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是一种别样的现代性选择。其次他不同意简单的看待文革,这一点与刘康一致,刘康谈到:“虽然‘文革’留下的极其复杂和多层次的历史遗产尚有待进一步清理,但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上所指导的中国革命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维度,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在重新理性地认识文革的时候,不能把文革与世界历史的进程分裂开来,不能孤立地看中国内部的问题。当然,今天要是仅仅用来自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观点来看文革,将其视为‘封建落后’的东西,‘妨碍’现代化和工业化、‘阻止’(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在中国的发展,就站到了两极对立的意识形态立场上去了,这也是无助于深刻地认识文革的复杂性的”(Liu 9—10)。可以看出,三者在中国具有一种“反现代的现代性”这一问题上,具有一致性。
但是在具体论证时,三人的差异便凸现出来,汪晖提到:“当代中国流行的现代化概念主要指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的从落后状态向先进状态的过渡和发展,但这一概念并不仅仅是技术性的指示,不仅仅是中国民族国家及现代官僚体制的形成,而且还意味着一种目的论的历史观和世界观,一种把自己的社会实践理解为通达这一终极目标的途径的思维方式,一种将自己存在的意义与自己所属的特定时代相关联的态度”(136)。正是在此意义上,汪晖认定,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概念提供了一整套的价值观,它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概念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在面对中国问题时,汪晖与刘康都认为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可以提供一套新的思维方式,不同之处显而易见:一是刘康批判一种目的论的历史观和世界观,认为这容易陷入一元决定论而后患无穷,文革正是如此发生,而汪晖却肯定目的论的历史观。二是刘康对中国经验进行了理论和实践多层面的反思和批判,但汪晖却缺少批判的维度,多是肯定之词。三是德里克是从伯曼的“反现代的现代性”而来、刘康是从毛泽东矛盾论到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来论证现代性不同选择的可能性,两者是纯粹的理论推演,而汪晖则是用中国的具体实践进行说明(后文会具体谈到),使得这一论断从抽象的理论探讨滑入为具体实践正名的泥淖,为了避免底气不足,汪晖进一步将“反现代性的现代化”延伸至晚清以降,他认为这一理论并不是毛泽东的独创,而是晚清以来中国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康有为的“大同”世界、章太炎的平等观念、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及中国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都是和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个领域构筑的各种现代性方案(包括现代性的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形态和文化价值)相伴随的。对现代性的置疑和批判本身构成了中国现代性思想的最基本的特征。因此,中国现代思想是以悖论式的方式展开寻求中国现代性的思想努力和社会实践的。
可以看出,关于“反现代的现代性”的论述,汪晖、德里克、刘康都显示出很大的相似性,但三人文化位置却全然不同,德里克是以中国经验作为反思西方现代性的有力武器,持批判姿态,刘康是批判西方、反思中国双重维度,而汪晖则是说明中国现代性的优越性和独特性,在这个理论旅行中,问题意识已经被修改。
(二)抽离具体语境:德里克、刘康是在文本阐释的层面进行理论推演,而汪晖则将理论用来对应中国的现实经验和实践活动。具体来说,一是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上,汪晖认为现代性特征体现在中国的现实经验之中:1.建立现代国家。汪晖认为毛泽东所实施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是要建立一个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正是通过公有化运动,特别是“人民公社”的建立,使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皇权从来不下县的一盘散沙的国家,实现了社会总动员,把整个社会都组织到了国家的主要目标之中,解决了中国数千年来都未能解决的国家税收问题,通过尽可能地剥夺农村的方式来为城市工业化累积资源,并按照社会主义原理来组织农村社会。2.实现公平正义。汪晖认为新中国消灭了工人和农民、城市和乡村、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三大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公平和正义。3.完成民族主义任务。毛泽东在具体实践中通过有效的组织,把社会整体性镶嵌进国家目标,从而尽最大力量完成民族主义的任务。汪晖谈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一方面是一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是对欧洲和美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但是,这个批判不是对现代化本身的批判,恰恰相反,它是基于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立场而产生的对于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形式或阶段的批判。因此,从价值观和历史观的层面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136)。
二是现代性体现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汪晖认为中国试图通过“大跃进”“大革命”的方式促成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嬗变,他谈到:“对于毛泽东来说,他一方面以集权的方式建立了现代国家制度,另一方面又对这个制度本身进行‘文革’式的破坏;他一方面用公社制和集体经济的方式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他在分配制度方面试图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导致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他一方面以公有方式将整个社会组织到国家的现代化目标之中,‘文革’式的体制和运动剥夺了个人的政治自主权,另一方面他对国家机器对人民主权的压抑深恶痛绝。总之,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实践包含着反现代性的历史内容。这种悖论式的方式有其文化根源,需要在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双重历史语境(寻求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种种历史后果的反思)中解释”(汪晖 136—37)。不难看出,汪晖抽空了德里克理论言说的语境,将西方视域中的理论阐释变成了对中国具体的实践经验的解读。需要指出的是理论和实践并非是二而一的关系,理论是对未来的可能性进行超于现实的探索,所以理论可以毫无挂碍地显示自己的先锋和激进,因而具有批判甚至颠覆的力量,正如阿多诺所说理论是抛向大海的信瓶,意味着理论不指向现在,而寄期望于未来某个时刻被点燃,也就是说理论不需要对现世负责。可实践不同,它要在这个活生生的世界上践行、实施,涉及到千千万万的血肉之躯,往往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实践必然是按部就班,不容许异想天开,也就是说越是激进,越具有颠覆性的实践反而越让人唯恐不及。然而,当汪晖将一个理论探索调转成为实践自证,以六经注我的方式将十七年、文革的整体状况拆成碎片,并选取了益于说明自己观点的实践经验作为论据,无疑是对部分真相的回避和掩饰。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同样是对中国现代性问题的阐述,汪晖的文章却在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如此严重的波动和不适。
结 语
在中国学者的视域中,德里克的现代性理论是被当作一个外部观点看待的,他的理论之于中国学界来说,只具有一种形式化的功能。刘康要借阿尔都塞的眼睛来探讨现代性,他分为两个层面,在理论维度里,他发现了毛泽东思想的有价值的部分,在具体经验中,批判了实践对理论的背叛和理论实践化过程中的一元决定论,而当汪晖运用相关理论来对中国现实进行解读的时候,将对纯粹理论思辨的肯定转化为对具象政治、文化实践的肯定,并对刚刚由“新启蒙”运动所形成的相对统一批判的观点产生掀毁式的效应。可以想象,这一论断必然掀起学界的轩然大波。
汪晖的“反现代性的现代化”理论的提出,不同于德里克从中国到西方的单向度旅行,而是一种中国到西方,西方再到中国的双向对转的关系:作为一个西方学者,德里克试图借用中国实践阐述出一种反思西方的理论模型,这样的模型与中国实践并没有实质的关联,而是西方理论生产机器的一次按章操作而已,目的是为了借用中国经验反思西方现代性。刘康作为一个美籍华人,他的文章是写给西方读者的,依然是对西方现代性的一种反思,与德里克一样,是站在左翼的立场上对西方现代性进行批判,但刘康的特殊性在于他的中国背景使得他对中国问题有更清醒的认识,他在运用中国资源反思西方时,不像德里克那样将中国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片神圣的飞地,而是更加客观辩证地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过程中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的龃龉,批判了实践背叛理论后导致行动脱缰的恶果以及实践最终陷入文化决定论后的倒退,可以看出,他解读中国经验时是非常警惕、充满批判意识的。而汪晖毫不批判地用“反现代的现代性”的理论解读中国经验和实践活动时,就取消了德里克的问题意识和言说语境,德里克的理论就被熔铸成中国经验的一部分,形成一种仿佛站在中国立场、从中国语境出发提炼出来的理论的假象,于是,被德里克对象化的理论在汪晖这里像变戏法一样地完成了理论内在化,西方左翼理论进入中国语境后不仅丧失了它的批判和反思锋芒,反而披上了自我美化和催眠的外衣,令人惊叹的是,原本西方理论的洞见竟会变成解读中国经验的盲点。
注释[Notes]
①这篇文章1994年完成初稿,发表于韩国《创作与批评》,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97年改定后在《天涯》(1997年第5期)发表,而后被多家刊物转载,文章收入汪晖论文集《死火重温》(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42-94页。
②这一组文章包括汪晖《我们如何成为“现代”的?》、旷新年《现代文学发生中的现代性问题》、吴晓东《建立多元化的文学史观》,以上文章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1期。
③1994年汪晖发表的《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提出了“谁的现代性”问题引起学界的关注,1996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了汪晖等人的一组文章,“中国现代性”的命题在文学研究范畴的推进,这些都为《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在1997年的推出进行了有效的暖场。
④ Liu Kang.“The Problematics of Mao and Althusser:Alternative Modernity and Cultural Revolution.”Rethinking Marxism:A Journal of Economics,Culture,and Society.8.3(1995):1-25.该篇论文引发多位英美学者的讨论。据向刘康本人了解,专门讨论他这篇论文的英文论文有14篇,引用上百次。中译文至少有三个版本,关于“现代性的不同选择”(alternativemodernity)的翻译问题,一是《现代性不同选择与文化革命——毛泽东与阿尔都塞的理论思考》(史安斌译),翻译为“现代性不同选择”,参见《文化传媒全球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二是《毛泽东和阿尔都塞的遗产:辩证法的问题式、另类现代性及文化革命》(张放译)中翻译为“另类现代性”,参见[美]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保罗·希利(Paul Healy)、尼克·奈特(Nick Knight)主编:《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性透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三是《毛泽东和阿尔都塞的遗产:辩证法的问题式、另类现代性及文化革命》(田立新译)也翻译为“另类现代性”,参见《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2005):24—32。本文选择“现代性不同选择”是因为史安斌的译文经刘康教授钦定。
⑤汪晖显然熟悉刘康的有关论述。他主编的《九十年代的“后学”论争》一书中收录了刘康的几篇著名论战文章。参见汪晖、余国良编:《九十年代的“后学”论争》(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⑥“迂回与进入”来自法国哲学家、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所著同名书籍《迂回与进入》。
⑦正如李泽厚敏锐地观察到的,从革命的农民游击战争中发展出来的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军事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章中充满了俗语、民间传说和古代军事典故,这种语言和修辞特点也反映出军事和战略上的考量。在李泽厚看来,本土化语言的使用也意味着毛泽东文章中处理基本军事战略时所使用的辩证法思想来自道家,这种辩证法可以从诸如《道德经》(老子)和《孙子兵法》(孙子)这样的典籍中找到,而毛泽东也经常在文章中援引这些典籍。中国传统上对辩证法的理解从根本上区别于源自修辞性论辩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辩证法传统。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Anderson, Perry.“Modernity and Revolution.” New Left Review 144(March-April1984):96- 113.
Althusser, L..for Marx.Trans.Ben Brewster.New York:Penguin,1969.
Berman, Marshall.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New York: Penguin Books,1988.
Dirlik, Arif. “Modernism and Anti-modernism: Mao Zedong's Marxism.”Critical Perspective of Mao Zedong Thought.Eds.Arif Dirlik, Paul Healy, and Nick Knight.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1997.59- 83.
Harvey, David.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Oxford:Basil Blackwell,1989.
Jameson, F..“Aotually Existing Maxism.” Polygraph 6.7(1993):170- 96.
Liu, Kang. “ The Problematics of Mao and Althusser:Alternative Modernity and Cultural Revolution.”Rethinking Marxism 8(1995):1- 25.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Mao, Zedong.“On Contradiction.” Selected Works of Mao Zedong.Vol.1.Beijing: The People's Press, 1991.]
唐小兵:“我们怎样想象历史”(代导言),《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Tang Xiaobing. “How Do We Imagine History.”Reinterpretation:Popular Literature and Ideology.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5)1997:133 50。
[Wang, Hui.“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and the Question of Moderinity.”Tianya 5(1997):133-50.]
——重读阿尔都塞的《论青年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