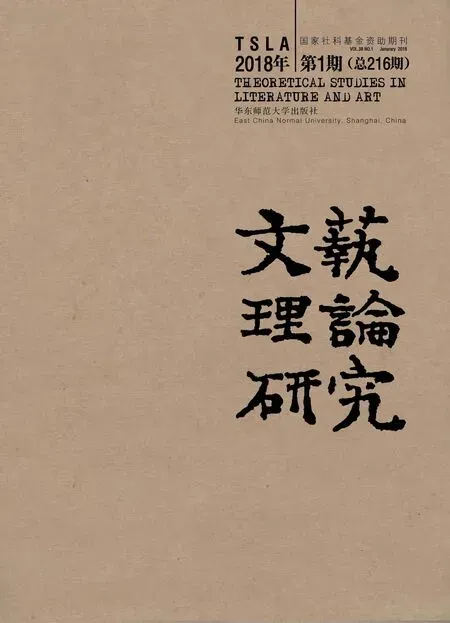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命运
——詹姆逊与詹姆逊主义
刘 康
“西方理论”广义上指的是近四十年改革开放以来大量进入中国的西方思想观念,狭义是指西方的20世纪以来的文艺理论,也是本文关注的话题。西方进入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观念五花八门,立场与价值取向多元。但就文化领域而言,西方理论在中国产生最多影响的,是具有左翼倾向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和各种“后学”,即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中国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以及文化思想理论,本来就是传承了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前苏联的文艺思想。中国从五四以来到延安、到1949年建国以来的文化思想,这些强大的近现代的本土传统跟近期来自西方的文化思想与理论相遇后,发生的碰撞、变异、转化,值得我们从思想史和知识社会学(或曰知识考古学、知识谱系学)的角度来审视。这也就是本文的主旨。
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影响巨大,其接受、变异、转换的过程,牵涉到中国的走向或命运。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自1949年以来始终是中国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此外几乎所有现代化的理论,都是来自西方。回顾中国三十多年来的人文社科发展轨迹,似可发现“译介开路、借用西方”,“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这个特征。这跟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完全吻合,并且高度一致。中国的现代化、改革开放,就是借鉴西方理论和西方经验,来推动中国前进的。当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更早的戊戌变法、五四运动,无不循着这一“西方话语—中国问题”的轨迹而行。所谓中国“强大的近现代本土传统”,其思维与话语范式实际上也都来源于西方。
为什么要从詹姆逊开始?两个原因。一是詹姆逊也许是在中国最有影响的西方理论家(指狭义的文艺理论),笔者以至于生造了“詹姆逊主义”(Jamesonism)一词来描述他的中国命运。二是因为詹姆逊理论的特点是综合与兼容并包,几乎所有西方理论的流派都可以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找到位置。接下来写文章系列的之二、之三,就大致上可以厘清基本方向。用詹姆逊的话来讲,他的理论本身为我们提供了西方理论的“认知测绘图”。但詹姆逊的体系庞大芜杂,他的语言风格在英文写作中独树一帜,晦涩难解,几乎不可译(反讽的是,除了跟詹式语言风格相差极大的中文,他的各种语言的译文并不多。詹姆逊翻译的问题,下文还会提起)。所以本文不敢太多奢求,惟有管中窥豹,略见一斑而已。
本文首先需要回顾西方理论近四十年进入中国的历史背景,并与西方理论在西方(欧美)的兴盛、在西方的现状与问题做一对照。虽基本都是老生常谈,鄙之无甚高论,却可为下面的个案分析做铺垫。案例分析部分,本文把詹姆逊和詹姆逊主义做了一个划分。第一部分主要议论一下詹姆逊的美国学术背景及其接受与影响,第二部分解读中国詹姆逊主义的形成。本文的目的不是做全面的文献综述,而是就笔者观察到的两部分的关联与不关联,美国的詹姆逊与中国的詹姆逊(主义)的异同,做一不无片面、甚而偏见甚多的评述。希望这一评述能进而引发关于西方理论中国之命运的大话题的思索,或许对中国的学界同仁们提供些参考。
一、西方理论与中国
“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的中国道路
1978年初高校恢复招生与这年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人文社科的思想解放新阶段,显露了“译介开路、借用西方”,“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这个特征。如果说从1949年建国到1979年改革开放30年时间内,中国学术基本上自成一体,自说自话(当然,那段时间中国跟前苏联的学术体系还是有着重要的联系的),那么最近这三十几年来的中国学术发展,其首要特点就是开放的、国际化的导向。没有学术的开放也就没有学术的改革,在学术上这是一个先开放、后改革的顺序。虽然我们约定俗成地称“改革开放”,但从开放到改革的历史的轨迹却不可忘却。尤其要强调的是,从八十年代初期开始,中国人文学界成为社会思潮的中心。李泽厚、刘再复、金观涛等中年学者与北岛、陈丹青、甘阳、刘小枫等一批青年作家、艺术家与学者在哲学、文学、历史和美学等领域内开始了中国文化与思想的大讨论,很快就演变成全社会热烈关注的文化反思、文化热。从历史上看,堪与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媲美。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意气风发,以新启蒙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人自诩,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和引领风潮的群体。
八十年代是中国社会思想最为风云激荡的时代。这一阶段的最大特征,就是通过大量译介西方学术思想和文化理论,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几乎所有问题都重新提出来争论,通过西方的新理论、新观点来重新认识中国,重构中国的人文社会研究的话语体系。这一阶段造就了一大批中国人文学者,多数是1977年底恢复高考之后的“七七、七八级”大学生,经历过文革的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和工厂劳动,受到60年代激进政治与意识形态的熏陶,也是最热衷思想解放和启蒙的一代人。这代文科大学生既有强烈激进政治意识形态遗产,又热情拥抱西方现代文化。他们标榜“人文主义、专业精神、学术独立与非政治化”,但实际作为无不透露着极为强烈的政治雄心,更多体现的是五四知识分子积极参与政治的倾向,可以说是当时最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
这一群体最为鲜明地展现了八十年代的译介开路、借用西方,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的基本路径。许多在八十年代文化热中尚未崭露头角的人文社科学者,其中不乏花费大力气攻读英文原著,直接接触第一手的西方理论专著和论文。他们许多加入了西方专著的翻译大军,其中更有不少人一边翻译,一边写作,采用了新式的夹叙夹议手法,即夹译夹叙又夹议的方法。如果我们认真阅读这批从八十年代文化热中脱颖而出的中国人文社科学者的大量著作,可以发现这种方法是极为普遍的。这些著作是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的重要成果,体现了八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政治与思想改革的追求和理想主义精神。当代中国知识界的重要话题如现代性、传统与现代、伦理与法制、公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个人自由与人权、市场竞争与社会公平等,均由这批当年的年轻学者通过这种夹译夹叙又夹议的文风在中国大地推进,成为对中国改革与发展现状最有针对性、最富问题意识的论点。可以说,没有这批学者的思想创新和学术创新,中国当代学术的基础也就无从谈起。
到了九十年代,一度叱咤风云的中国人文社科知识分子,迅速从社会舞台的中心消遁。九十年代在中国兴起的商业化大潮,让企业家群体走上舞台中心。消费主义的大众文化以及商业精英的崛起,把人文知识分子赶回了校园。中国全面与全球化接轨。在这一阶段,“后学”打头的西方理论纷纷登场,迅速取代了八十年代以西方启蒙时代古典主义思想为基础的现代性文化反思。中国一方面跟西方“后学”接轨,似乎中国也跨越了“前现代”“现代”历史阶段,直接进入了“后现代”。另一方面,如李泽厚所言“思想淡出,学术凸显”,学科建设的需求、学术论文生产线的出现、项目驱动型而非问题导向型的研究方向,成为今天中国的学术现状,更是西方理论进入中国近二十多年来的大背景、大环境。本文的主角詹姆逊虽然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来到中国,并第一时间传播了他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从时间上看,他的1985年北大时光正是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构思、酝酿和写作阶段。不过反讽的是,要等到十年甚至二十年之后,詹姆逊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才在中国大红大紫。2004年《詹姆逊文集》四卷本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举办首发式,就是颇具象征意味的事件。
西方理论的多重错位
包括詹姆逊在内的西方理论的中国传播与接受与中国的“时差”和种种“错位”,都需要置于各自的历史大背景来看,可看出有意思的理论的结构相似、历史发展的平行与交叉和不接轨、不交叉(西方理论与中国80年代文化反思在思路和历史背景方面的平行与结构相似,下文再议)。西方理论本来产生于西方特定的历史环境,回应的是西方的问题,这是理解西方理论中国命运的前提。几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
第一,西方理论背后的1960—70年代的全球激进主义思潮与今天的全球化现状之间有强烈的错位。研究对象与理论方法是有时间差的。当代对象始终变动不居,而且瞬息万变,但理论方法却相对稳定滞后。就人文学科而论,欧美近三十年来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方法,其滥觞为20世纪中叶的文化左翼思潮。积半个多世纪的沉淀拓展,现已成蔚为大观。在风云激荡的20世纪60—70年代异军突起的文化左翼(cultural left)或新左派(neo-left)思潮,集中展现了当时席卷全球的狂飙突进式的激进主义理念。而从1980年代以降的欧美社会,迅速走出了激进时代,通过推动全球化和信息革命,而进入了发达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当代欧美社会与四五十年前已然有很大变化,以左翼激进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后现代理论方法与其研究对象之间深层次的差异错位,在更广阔的历史变迁的背景之下也就显现出来了。换句话说,后现代理论的来自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的激进主义立场,越来越与当代西方社会不合拍甚至脱节。
今天人文学科的各种理论、观点和方法基本来自美国。美国自冷战结束后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学术集散地和“思想的自由市场”(free market of ideas),虽然美国并非思想和理论的主要原创地。可以说,世界各国的学术研究无不从美国“进口”或“转口”大量的理论方法,在这点上中国并不例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社会已经进入发达资本主义阶段,以电脑和高科技产业为主导的后工业化、生产的全球分工、跨国资本引领的全球化时代正在开端。这个时代同时也是全球政治与文化大动荡的革命时代。六七十年代的“第三世界”反帝反殖民主义运动,受到欧美“第一世界”知识界和大众的空前关注。印度支那(越南战争)、中东地区(巴以战争)等地区的战乱直接牵动了欧美社会的神经。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早已完全分裂。中国的文革和苏联坦克镇压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在欧美社会都产生了深刻影响,而这种影响又无不带上了欧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深刻烙印。欧美激进知识分子与社会大众普遍的反战情绪、对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不满(美国争取少数民族与妇女权利的民权运动)等,迅速整合,在文化领域的表现尤其突出:无论是美国反文化、嬉皮士运动还是席卷西欧国家的文化激进运动(以1968年的“巴黎风暴”为代表),打着反抗、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旗帜,最终的结果并非颠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与社会秩序,而是在文化与精神领域内开拓了富有反思意识、批判精神、多元与多样化的新思潮。在遥远的中国发生的那场文化大革命,极大刺激了年轻的激进欧美知识分子,他们一厢情愿地以为,东方古老神秘又新鲜的社会主义中国,正上演着思想革命、意识形态革命、情感与文化革命、传统与习俗革命的大戏,实践着改天换地的乌托邦理想。出于想象和一知半解,欧美左翼知识分子构建出了“毛主义”的理论,并迅速成为西方左翼的重要思想武器。本文主角詹姆逊,就是欧美毛主义的一位重要实践者与建构者。西方毛主义想象与中国文革历史真相的错位,岂止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想象与真相基本完全颠倒。但随西方左翼理论的全球传播,以“后学理论”面貌又“回馈”中国,继而产生了更加复杂的后果,对中国今天的知识界依然有难以估量的影响。
第二,西方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错位和对立在日益加剧。美国的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一贯是象牙塔里的精英姿态,与社会现实保持距离,以确保其学术中立和自律自洽的立场。在美国的学术体制里,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是截然不同、互不相干的两个领域,人文学科基本立场是与当下、现实的世俗问题隔得越远越好,强调的是潜心在书斋里做学问。而社会科学却经常采取一个实用的态度,与政策的制定、社会的走向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作为社会科学三大支柱的经济学、社会学与政治学,以及更加专业化的商学院、法学院那些专业学科,更为强调研究的社会实用性。
这个情况近四十年来发生了很大变化。
萨义德1978年出版的《东方主义》开辟了文化批评世俗化的蹊径,把文学艺术等人文学术研究从高雅的象牙塔内拉进了现实生活,走进传媒和大众关注的焦点事件之中。他以一个美国的巴勒斯坦人的身份,一个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参与者的身份,将福柯知识与权力的艰深的法国理论与阿拉伯和以色列冲突、中东问题这个美国社会极受关注的焦点问题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强烈的左翼激进思想,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震撼了美国的传媒及公众,更震撼了美国的学术界。本文的主角詹姆逊作为美国左翼文化理论及批评的另一主要代表人物,与萨义德不同,一直保持了一个学院派学者的姿态。詹姆逊采取了一种折衷主义和兼容并包的方式,将一个对于美国学术界相当陌生的德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念(通常是跟美国的宿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块的思想)变成了一个在学术上受尊重的思想。詹姆逊的代表作《政治无意识》(1981年)把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符号学、解释学和原型批评、叙事学等等五花八门的理论批评、学术派别、思想观点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一个宏大的、后黑格尔主义的、解构的马克思主义宏伟叙事。极具反讽意味的是,正是由于其理论的匪夷所思、自相矛盾之处,奠定了詹姆逊在美国的学术地位。
如果说萨义德是推动人文学术干预社会现实的旗手,詹姆逊更多展现了激进理论依然可以成为精致的学术话语。一方面,人文学科(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史、文化研究、女性研究、少数族裔研究等)的意识形态化倾向不断加强,成为左翼激进主义“政治正确”“认同政治”以及各种左翼社会运动如反全球化运动、同性恋和多重性取向(LGBT)运动的代言人。左翼从传统的学术象牙塔里走出来,积极干预社会,参与政治。另一方面,近二三十年来,美国学术界出现了左翼文化理论与批评的学院制度化与精英化的趋势。学术明星化、商品化与专业主义成为美国高等教育以及社会的一个基本状况。不过在奥巴马任总统的8年内,左翼人文学者一方面高举意识形态大旗,十分活跃参与社会运动,一方面进一步推动左翼理论的制度化、精英化,游走于极端矛盾的两者之间。2016年的美国大选,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社会对“政治正确”的左翼意识形态的反弹。极端保守右翼的特朗普以“政治局外人”的身份得以当选,表明美国的政治钟摆重新向右。
处于另一端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却是越来越向自然科学倾斜,把建立无懈可击的数学模式作为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欧美社会科学近40年来的趋势是追求对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精确描述和实证分析、建立数学模式,宏观、历史和批判的力量却大大削弱。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冷战开始的1945—1946年起,西方社会科学的目标就是通过研究西方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来获得有关现代世界的普世规律和原理。研究方法上,首选量化与经验研究(empirical research,中文译为“实证研究”),以数据为证据,通过理性、客观、价值中性的量化分析,来得到科学的结论,或证实或证伪理论假设。这种遵循自然科学认知逻辑的社会科学研究,多年来虽然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和质疑,但却朝向数学化、自然科学化的方向越走越远。如提出“世界体系”理论的著名社会学家沃勒斯坦,多年来不遗余力地批判欧美社会科学的欧洲中心论。美国华裔经济历史学家黄宗智、华裔社会学家赵鼎新等,也对西方社会学面临的困境作出了深刻犀利的剖析。一方面,社会科学面对的社会现实问题日趋复杂,远远超过了理性选择派所依据的欧美发达社会“理想型”的阐释空间。另一方面,学术精英化、制度化的需求,又迫切要求建立更加精确的评估指标体系。在两者的压力之下,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的“理性选择”,就是从有限的实证和经验数据中,推演建构数学上严谨精准的模式和公式。至于模式与公式跟现实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关联,反而不受重视。在经济学领域,相比“纯粹”的计量经济学,更关注经济现象背后的社会、心理、历史因素的行为经济学、心理经济学、经济史等学科均是边缘化的。更有甚者,“政治经济学”的课程与话题,在美国大学里都开设到文学系里去了(由詹姆逊创建的杜克大学文学系,每年都由文学教授开始政治经济学课程)。
人文学科流行的“后学”致力于对各种“决定论”的解构与颠覆。当然从欧美主流社会科学的观点(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理性选择派社会学)来看,后现代主义理论依然是一种决定论的反映,只不过是从经济决定论换成了文化决定论,脱离了经济与社会的状况和政治制度,不过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已。但欧美主流社会科学迄今并未出现强有力的理论观点来反驳人文学科的后现代理论。此外,面对意识形态研究、当代视觉社会、传媒社会与景观社会的巨大变化,社会理论的探究基本阙如。人文左翼对于号称价值中立、其实倾向新自由主义主流的社会科学专业,更是倍加攻讦。所以,今天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都是各说各话、鸡同鸭讲,左右立场二元对立的状态,难以达成思想共识。欧美左翼作为学术界弱势一方(人文学科在欧美始终处于弱势),对自由主义中间立场和保守主义右翼占据主流的社会科学的攻击不遗余力,不过多半是“茶杯里的风暴”或象牙塔内的“阶级斗争”,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有限。
二、詹姆逊与中国的詹姆逊主义
詹姆逊的学术背景及其影响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1934年- )从1961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他的第一部由博士论文改写的专著《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起,迄今半个世纪时间内,出版了25本专著和论文集,数百篇论文,获得2008年挪威霍尔伯格奖(相当于人文社科领域的诺贝尔奖)和2011年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LA)终身成就奖(相当于电影圈的奥斯卡终身成就奖)。他是20世纪后半期英语文学学术圈为数不多的大师级学者(虽然美国学术界很少用“大师”这样的赞词),更是美国学院派左翼文学与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在欧美当代学术大师中,像詹姆逊这样真诚关注中国,有许多中国朋友和学生、大批中国拥趸的,为数寥寥。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倾向与中国有天然的接近,这是中国产生詹姆逊主义的土壤。关于詹姆逊的学术思想,有大量论著。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教授凯尔纳有研究詹姆逊的专著(凯尔纳本人是美国文化研究、传媒研究的重要学者),他对詹姆逊的简要介绍,可参见王逢振《詹姆逊文集》的中文版前言。以下对詹姆逊学术背景与影响的分析,吸取了学界的观点和评价,但主要还是笔者个人的观察。
詹姆逊1959年于25岁时获得了耶鲁大学法国文学博士学位。詹姆逊的博士导师是埃里克·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他们是美国的文学研究领域的一对熠熠生辉的大师级师生。奥尔巴赫的不朽名著《摹仿:西方文学中的现实再现》(Mimesis: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全景式阐释了西方文学近三千年的写实和摹仿传统。奥尔巴赫将西方文学形式与风格的流变置于历史的大背景下加以分析,他特别关注文学风格背后蕴含的深刻的政治喻义。这些都对年轻的詹姆逊的学术思路有重要的影响。詹姆逊的博士论文《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196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展示了作者对文学风格与政治、历史背景的特别关注。詹姆逊在深入萨特作品文本的同时,跟萨特本人和法国激进左翼知识界有密切的接触,这让他走进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对于主流美国文学研究来说,颇有离经叛道之意。美国的文学研究当时是新批评占据主流,推崇文本细读和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的自给自足,研究对象主要是“为艺术而艺术”的现代主义诗歌。如特里·伊格尔顿指出,新批评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的主流体现了英美人文主义—自由主义价值观与意识形态,蕴含着英美人文领域现代主义精英和“前现代”的贵族政治立场(Eagleton,Literary Theory 17)。而欧洲大陆的法国与德国,知识界的左翼传统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正在形成新的联盟,萨特的存在主义、罗兰·巴特的结构主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等,跟英美形成了强烈对比。年轻的詹姆逊选择了萨特,一下就走到了欧洲学术与思想的最前沿。
随后詹姆逊在哈佛、耶鲁和加州大学等任教,十年磨一剑的他于1971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形式:20世纪文学的辩证理论》。这部书向英美学术界系统地介绍、评述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与20世纪的形式主义批评的关联。一年以后《语言的牢笼》出版,对欧洲的结构主义与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做了更加详尽的介绍。这两部书也奠定了詹姆逊在美国学术界引进激进的欧洲文学理论的引领潮流的重要地位。他与耶鲁大学的保罗·德曼、希里斯·米勒、杰弗里·哈特曼、哈罗德·布鲁姆等“耶鲁解构主义四君子”等齐名,成为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欧洲(主要是法国)理论美国化的重要中介。又过了十年之后,詹姆逊于1981年出版了《政治无意识:叙事作为社会象征行为》,这本书的出版标志了他从方法到思路上的成熟,成为美国学界众多现代欧洲理论阐释者中旗帜鲜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美国传教士”。之后詹姆逊从欧美文学的解读和文学理论探索道路上逐步拓展,关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广阔的文化批评领域。1991年(又一个十年)出版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让詹姆逊成为欧美最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家与批评家,也为他在中国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勤于思考、笔耕不缀的詹姆逊,近二十多年来一直与时俱进,紧紧抓住当代欧美文化的重大问题,几乎每隔一两年就有一部专著问世,涉及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的美学理论、黑格尔、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现代性、乌托邦与科幻小说、电影、建筑、现当代艺术、流行文化等极其广泛的文化领域。他今年(2017年)已八十三岁,仍然在杜克大学讲台上课。差不多每开一门课,所讲授的内容就会形成一部专著问世。
詹姆逊的学术研究在英美文学界和人文学科领域是开拓性的,他在美国文学与文化研究里倡导马克思主义方法,是当代美国人文学科左翼思潮和学术范式的领军人物。在文学与文化领域里,詹姆逊功不可没。他当年是才华横溢,精通各种欧美语言的激进青年。像朱光潜、李泽厚,也像“文化:中国与世界”的青年才俊那样,激情澎湃,倾全力推动学术创新、范式转型,从学术路径来践行社会改革和公平正义的理想。詹姆逊、萨义德等左翼学者跟美国解构主义理论家和各种新派欧陆理论家们相互呼应,在二十年不到的时间内,完成了人文学科的范式转型,创立了各自的美国学派,并由英语媒介全球强大的影响力,传扬世界。有趣的是,詹姆逊的论著被大量翻译成中文,日文也有相当多的译本,但法、德、俄、意、西文的翻译却有限。尤其是法国学术界,对詹姆逊的兴趣似乎很少,他在法、德等国的影响也十分有限。
詹姆逊的主要成就
詹姆逊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杜克大学文学系网站的个人简介用一句话概括:“詹姆逊教授目前关心的话题,其中一是需要将文学作为政治与社会律令的编码来分析,还有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反思,解读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预设观念。”杜克系网的简介一般是本人撰写,编辑整理,所以这句话可以理解为詹姆逊对自己学术研究的概括。根据这个概括和笔者的理解,可以列举三点主要方面:
第一,以阿尔都塞方法论为主导,以马克思主义“总体论”为中心,创立新马克思主义文学阐释理论
。这就是上述的“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反思”,重点是“方法论”与“反思”。而詹姆逊的方法论反思带有强烈的阿尔都塞色彩,可以说阿尔都塞的方法论或阿尔都塞对方法论本身的反思构成了詹姆逊理论思考的基础。前面说到詹姆逊是一个折衷主义大师,其最重要的方法论著作《政治无意识》把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符号学、解释学和原型批评、叙事学等等五花八门的理论批评、学术派别、思想观点融汇一体。这是詹姆逊作为“学术大卖场”中的美国学者的一大特色。但詹姆逊本人的真正特色是阿尔都塞式的马克思主义“总体论”,是宏大的、后黑格尔主义的、解构的马克思主义宏伟叙事。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阿尔都塞对产生于19世纪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做了大量的修正与拓展。他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哲学和认识论领域的核心人物和法国共产党的理论家,对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和苏联斯大林式的“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两面作战,做了一系列有深远影响的理论反思与批判。阿尔都塞把他的理论归结为“双重干预”或“特定的转折关头时的干预”(Althusser 12—13)。他的“干预”带有明显的元批评和方法论的特色。这是由于他试图将马克思主义构建为一种“理论方法”或者说“有关认识论发展历程的理论”,籍此说明理论构成(problematique)的本质及其发展历程,进而把理论本身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来加以解释(Althusser 38—39)。换言之,阿氏的研究对象是双重的,包括了理论所探讨的问题以及理论本身。一方面他要用理论来分析解读具体历史社会问题,一方面他又要把理论本身放置在历史过程中来思考。阿氏的方法尽管具有某种解释循环性,但它与所谓的“解释学循环怪圈”不同,因为它将理论构成的历史性置于理论本身之外,即置于“特定的历史转折关头”里,也就是说,将理论构成置于社会政治和历史之中,而不是将自我指涉性排除在阐释的范围之外,就理论而理论,在理论自身范围内绕圈子。阿尔都塞的元批评方法对詹姆逊影响极大,以至于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称之为“阿尔都塞式革命”(Jameson,The Political Unconcious 23)。《政治无意识》前言的第一段高度概括了詹姆逊的方法论,贯穿他的所有论著,成为理解詹姆逊学术路径的一条主线:
“总是历史化!”这个口号是一切辩证思维的绝对律令(absolute imperative,来自康德的概念——译注),甚至是“超历史”的律令,成为本书的寓意也就不足为奇了。但传统辩证法所教我们的是,历史化的做法有两条路径,最后殊途同归:客体之路和主体之路。一条是事物本身的历史起源,一是概念和范畴的历史,是比较虚和无形的,但我们由此来理解事物。在文化领域(本书的核心领域),我们必须二者选一:要么研究某个文化文本的“客观”结构的性质,包括该文本的形式与内容的历史性,其语言表述可能性出现的历史时刻,文本的具时代特征的审美功能等。要么研究不同的东西,即为我们阅读接受文本时设定的阐释范畴或解码本。不管结果如何,我们选择了第二条路径。因此《政治无意识》关注的是阐释行为的内在动力(dynamics),作为本书立意的假说(organizational fiction),假定(presupposes)我们从来就未能直面文本,真的面对文本物自体般的全新状态(in all its freshness as a thing-in-itself)。其实文本来到我们面前时,早就被读过了。我们通过前人的层层积淀的阐释来理解文本。如果这文本是新创作的,我们则通过长久积累的阅读习惯和范畴来阅读,从多年传承的阐释传统中来理解。这个假定要求我们使用一种我在别处提到的元批评的方法。根据这一方法,我们研究的对象与其是文本自身,毋宁是阐释,我们试图通过阐释来直面文本和运用文本。阐释在此可理解为实质上的寓言行为(an essentially allegorical act),是通过某个特定的主导性阐释符码,来对文本进行重写。(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cious ix)
詹姆逊这里说的“文本”即阿尔都塞的“理论”,研究的是“概念和范畴的历史,是比较虚和无形的,但我们由此来理解事物”;是“为我们阅读接受文本时设定的阐释范畴或解码本”。詹姆逊进而认为,正是这些虚的东西,这些概念、范畴或解码本,就是前人“层层积淀的阐释”。而我们从来就不会“直面文本”,因为“早就被读过了”。这是打开詹姆逊“历史化”阐释的钥匙:需要加以历史化的,正是这些层层积淀的阐释,包括作为一种史观的历史主义本身。阿尔都塞批判的是黑格尔的历史主义史观,即历史是线性、一元、沿特有目的论而进步发展的史观,也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史观。阿尔都塞通过他独创的“症候式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深刻批判了斯大林主义(即阿氏笔下的黑格尔主义)历史观,勾勒了历史的矛盾性与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的图景,这些都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知识谱系学以及之后詹姆逊的“认知测绘图”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在阿尔都塞看来,历史的总体是“缺席的原因”,是结构式因果关系中全部因素的多元聚合、多重影响,而不是黑格尔式表现式因果关系中的“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些貌似抽象的概念,在阿尔都塞那儿都被历史性地无情还原:斯大林主义的历史观是苏联式共产主义的终极真理,是“本质”和“规律”,必须由斯大林主义神坛的教父们才能“透过现象”,看穿看透,然后教诲亿万子民。阿尔都塞总结了斯大林专制主义给社会主义理想与实践造成的痛苦经验,告诉我们,斯大林主义并没有掌握什么历史的终极真理。历史无处不在,但又是缺席的动因,因为它是多元、多重决定的,无法确定什么“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是一个对一元决定论历史观或历史主义的颠覆性的看法。
对于美国学者詹姆逊来讲,阿尔都塞对斯大林主义的切肤之痛的批判,和对毛泽东“矛盾论”高度赞誉与中国文革的理想化认知,具有相同的意义: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论(totality)从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注意与“totality”的谱系关联)理念与实践中解放出来。詹姆逊的毛主义想象是对中国文革历史的彻底误解,但这个误解跟阿尔都塞一脉相承。另一方面,前苏联文化理论家巴赫金汲取了大量马克思主义与欧洲启蒙和解放的思想资源,创立了多元、开放的对话主义。詹姆逊跟巴赫金相仿,从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元批评、历史动因缺席的历史化(historicizing)逻辑中,找到了文学与文化阐释的思想解放之路。巴赫金也在詹姆逊所借鉴的理论巨人中,霍然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詹姆逊论著中大量出现巴赫金理论,《政治无意识》的第二个阐释视野即社会,就是巴赫金文本对话式的。
总之,詹姆逊以阿尔都塞方法为起点,综合各派欧洲理论,提出“元批评”“历史化”的自我反思、坚持历史大格局的文学研究方法与概念,大大拓展了文学文本细读的视野。《政治无意识》是詹姆逊里程碑式的著作。从《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开始,到《政治无意识》,詹姆逊提出了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新理论、新方法,以寄托他早年接触马克思主义、年轻时积极投入六七十年代的激进左翼运动乌托邦理念(他1969年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组织年轻的研究生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小组,并积极参加左翼青年的反越战、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活动)。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家和法共理论家,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方法论探索是企图为左翼社会主义运动、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社会理念创造出新的道路。但因为他的意识形态理论探讨了文艺再现、想象、个人情感与政治现实的关联,启发了詹姆逊和英国文学批评家伊格尔顿,对他们的理论思路起到了关键性引导作用(Eagleton,Marx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 1—6)。反讽的是,阿尔都塞理论在英美政治与社会领域的反响寥寥,反倒在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里开花结果。按詹姆逊的说法,是因为阿尔都塞开启了文学与文化研究的“他者政治”(politics of otherness)的思路:意识形态与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语言学和后结构主义,这一连串相对英美自由主义人本主义新批评的学术主流的“他者”话语与理论,跟英美,尤其是美国这个走在政治与社会“他者”(移民、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后殖民主义等左翼社会运动)前沿的国家一拍即合。在美国这个充满了“他者”的移民国家,“他者政治”自然成为知识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第二,詹姆逊的研究重心从“重写文学史”到关注当代文化,创立了后现代主义作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理论
。半个世纪以来,詹姆逊以惊人的渊博和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精力,孜孜不倦地研究阐释近现代的欧洲文学传统,从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到普鲁斯特的现代主义文学尤其是小说叙事,撰写了一部又一部专著和大量论文,把《政治无意识》中建构的文学阐释学理论付诸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实践。从1980年代开始,詹姆逊的关注点更多转向了当代社会。1991年出版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是1984年发表的同名论文的拓展和修正。期间1985年,詹姆逊到北京大学讲课一学期,题目就是后现代主义。这比较符合他的习惯,一边讲课,一边构思新的著作。他的中文翻译、北大学生唐小兵根据翻译记录稿,整理并交由陕西师大出版社1987年出版了《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这本中文讲稿的出版正值中国文化反思的高潮。文化反思的焦点是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型与中国的现代化。而詹姆逊的后现代理论,虽然在九十年代初期就出现在王宁、陈晓明等中国学者的论述中,却要等差不多十年之后才在中国掀起波澜。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关注既是他从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扩展,研究对象涉及建筑、电影、当代艺术和流行文化,也是他把阿尔都塞式元批评运用于更广阔的社会领域的尝试。他把全球化、金融资本和信息化时代的理解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认为当代西方(后现代)社会的标志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商品化,是历史的平面化。他的“审美作为最后一个私密个人的情感领域被商品化”的观点,受到广泛的重视,而从“历史化”这个绝对律令的认识论角度出发,詹姆逊批判了后现代时代“历史性”(historicity)的消失,这其实是他最为担忧的问题。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既是批判性的(阿尔都塞式的“症候式阅读”或“认知测绘图”),又是描述性的(辩证的方式),他反对从道德化立场批判后现代文化,针对的是美国右翼的新保守主义。在文化与社会批判问题上,詹姆逊一贯的立场是辩证和历史的,后现代“既是一场灾难,又是一个进步”(Jameson,“Postmodernism”86)。詹姆逊思想传记作者、美国学者凯尔纳认为,“詹姆逊的[后现代]著作代表了一种折衷主义、多重角度理论杂糅的潜在风险[……]在于他企图制造一种经典马克思主义与极端后现代主义的别扭的联姻”(Kellner 192)。美国社会学家瑞泽尔的教科书《现代社会学理论》2004年版把詹姆逊的观点说成“温和的后现代社会理论”,跟法国的波德里亚的“极端的后现代社会理论”形成对照。这或许是美国主流社会学界对詹姆逊“跨界”或跨学科的研究的最好评价(Ritzer 477)。但是美国政治学和经济学界对于詹姆逊所做的金融资本、虚拟经济和信息化这些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来不置一词。詹姆逊的后现代理论在中国和欧美之外的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这颇具反讽,因为他关注的对象主要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
如果我们换一种角度来理解詹姆逊的后现代理论,或可以将之视为他坚持不懈的、总体论和元批评的理论探索。他把视野拓展到流行文化和商品化的领域,认为这些是全球化和金融资本时代的产物,其中的文化逻辑是抹杀历史、让一切都变成平面(如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以掩盖、遮蔽各种不平等和非正义。詹姆逊批判的对象是全球化时代权力资本、金融资本、文化象征资本的跨国联姻,“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正是跨国资本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批判是犀利无情的,包括对欧洲中心论的元批评的反思,对非欧美国家和地区文化的真诚关注与分析,是“他者政治”的全球、当代(后现代)的进一步拓展。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后现代理论如同福柯对知识和权势联姻的无情解剖,触动了各种权力、资本的神经,揭露了各种权势集团的意识形态症候,跟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批判,有相似的普世意义和异曲同工的思想效应。实际上,詹姆逊在直面现实,提出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同时,放眼世界,以对中国的持续、真诚的理论关注,以及他的第三世界寓言的一篇振聋发聩、争议迭起的论文,创建了“他者政治”的另一领域。
第三,努力走出欧洲中心论,关注第三世界和中国
。1986年詹姆逊在《社会文本》秋季号发表了“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下简称“第三世界寓言”)论文。两年前的1984年秋天,他在《新左派评论》发表了“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论文;同年他还发表了“断代60 年代”(“Periodizing the 60s”)论文。1985年他来了中国,讲的课是后现代,同时读了许多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英译,尤其是鲁迅。回美国不久,就发表了“第三世界寓言”。关于这篇论文在中国的影响,是本文下部分“中国的詹姆逊主义”的主题之一。在这里主要回顾一下论文在美国的反响和后殖民主义批评的大背景。从1984—1986年,詹姆逊可以说是开疆辟土,从《政治无意识》的方法论基础上,大跨度、跳跃式地进入当代美国文化和世界文化领域,提出了后现代主义与第三世界寓言两大理论。除了《政治无意识》,“断代60年代”这篇论文,是理解詹姆逊的思想转型的另一关键理论文本。“第三世界寓言”这篇论文发表的时候,正是美国后殖民主义批评流派在美国大学人文学科兴起的时候。萨义德的《东方主义》(1978年)是美国后殖民主义批评的滥觞,而从事德里达、拉康等译介的印度裔学者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与其他一些阿拉伯裔、非洲裔的学者,在八十年代中期转向后殖民主义研究。詹姆逊是左翼批评界一员大将,与后殖民主义学者们的理论背景和左翼立场在大方向上相近。然而这篇“充满正能量”的论文,不料想却成了后殖民主义学者们群起而攻之的活靶子。阿拉伯裔学者艾哈迈德(Aijaz Ahmad)在1987年《社会文本》上发表“詹姆逊的他者修辞与民族寓言”,掀起了一场持续不断的对詹姆逊的围攻,焦点集中在他的欧洲中心论和普世主义(马克思主义)抽象的思辨(即辩证)理论框架。美国学者斯泽曼多年后回顾这场围攻时认为,美国后殖民主义学者对詹姆逊的批判,其实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理论的反击,也是一种姿态,使后殖民主义研究彻底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拥抱解构主义。另一位詹姆逊研究学者布坎南也指出,后殖民主义学派对詹姆逊的攻击背后蕴含着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深刻敌意。
不过要了解詹姆逊第三世界寓言理论的思路,最好的方式也许是回到他的基本方法与立场。前面引述的《政治无意识》一大段前言中,詹姆逊给出了答案:根据他的元批评方法,文本的阐释就是“实质上的寓言行为(an essentially allegorical act),是通过某个特定的主导阐释符码(master code),来对文本进行重写。”在“第三世界寓言”一文中,詹姆逊把鲁迅的作品作为“第三世界文学民族寓言”的样本,而“寓言精神(allegorical spirit)在深层次上是不连贯的,是断裂和异质的东西,具有梦的多义性,而不是象征(symbol)的同质性再现”(Jameson,“Third-World Literature”73)。“寓言”和“象征”,均是文学的修辞和隐喻手段,在结构主义(首先是阿尔都塞)、解构主义的认识论框架下,成为重写文本的主导符码。而詹姆逊个人的现代主义文学素养和所处的解构主义大环境,又让他特别青睐寓言。早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他就通过对本雅明、布洛赫的评价,详尽描述了寓言与象征的区别:“象征是自然随意的、抒情的,时间上圆润单一的,[……]而寓言正相反,是我们时代生活的优选方式,是一刻不停的、笨拙的对意义的解读,是为多元、断裂的瞬间恢复连续性的痛苦的努力”(Jameson,Marxism and Form 72)。“寓言模式是向异体性或差异性的一种开放;象征模式是让一切事物回到同一事物统一性的一种折叠”(Marxism and Form 146)。“寓言与象征的区别犹如艺术与宗教。艺术是多元的,其表达方式是间接、迂回、寓言式的多重运动,尽管艺术有自己内在的意义;而中心论的宗教的目标是单一的,要达到象征物的聚合,尽管宗教使用的是透明的诗歌方式”(Marxism and Form 147)。解构主义理论家保罗·德曼进一步阐发了本雅明的寓言与象征的理论。虽然德曼与詹姆逊的政治立场相异,但在寓言和象征的修辞手段、文本阐释上,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詹姆逊的“寓言”既是元批评的阐释策略,又是对文本本身(或社会文本,如“第三世界文学”)的界定,因此会引发许多误解,尤其是涉及欧美文学领域之外的文学与文化,更不用说跨界到了政治、社会和历史的复杂领域。他的对手往往忽视詹姆逊的基本理论框架,而抓住政治(特别是第三世界这样的地缘政治)概念大做文章。反讽的是,其实中国的詹姆逊主义者也跟他美国的对手相似,感兴趣的是“第三世界政治”“民族寓言”和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标志,而忽略其理论的内在逻辑。从认识论角度来看,詹姆逊的寓言阐释学跟巴赫金的对话主义非常相似。“寓言”好比巴赫金的“多声部”(polyphony)、“语言杂多”(或译众声喧哗heteroglossia),是开放、多元、异质、他者的言行;而“象征”则类似巴赫金笔下相对大一统、封闭、中心论一元论的“单一话语”(monoglossia)(刘康,“对话的喧声”24)。巴赫金的对话主义描述的是文化多元和思想解放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表达的是对多元、开放、去中心化的理想憧憬,跟詹姆逊的乌托邦理想主义高度吻合。第三世界寓言是詹姆逊文学阐释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他的“他者政治”的一种理论探索,跟他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相似,其历史渊源在“断代60年代”一文中可见端倪。
“断代60年代”对六十年代的时代风云、左翼思潮从四个方面做了评述:哲学史、革命的政治理论与实践、文化生产、经济周期。六十年代是第三世界的开端,是他者政治的溯源:广大亚非拉国家的独立、非殖民化运动,奠定了第三世界民众的主体性,也唤起了欧美发达国家的黑人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哲学上对萨特人道主义的批判、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兴起,从思想上形成了他者政治的潮流,与广大弱势群体(即詹姆逊所指不分地域国别的“第三世界”)社会运动与转型相互呼应。此刻,詹姆逊话锋一转,提出了“偏题论毛主义(Digression on Maoism)”这个话题。所谓偏题之论,其实是詹姆逊的内心纠结:“毛主义是六十年代新意识形态中最富内涵的,将是本论文影子般但又核心的问题所在
。然而由于毛主义的多义性,无法将之精确嵌入本文任何一点,也不能全然对之回应”(Jameson, “Periodizing” 188)(黑体为笔者的强调)。在这一段,詹姆逊不无一厢情愿地对中国的文革、毛泽东的平等主义理念与实践等等做了语焉不详,但又充满同情的描述。然而,他立即就跳到下一个话题“哲学的凋零”,用大量篇幅阐述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对传统西方哲学的颠覆性意义,以及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理论的种种论点。之后,又奇特地跨越到“马斯特拉山脉”,把卡斯特罗和格瓦拉在马斯特拉山脉从事传奇的古巴革命经历,与毛主义、中国文革、解构主义理论等等,烹饪出理论与历史(想象)的串烧。最后一段“回到最终决定的时刻”,引用阿尔都塞关于“经济是最终决定的时刻”,但又是历史的缺席和不在场作的观点做为结语。这段论述了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种种关联,可以理解为同年发表的后现代主义论文的读书笔记。“断代60年代”对于中国读者是比较陌生的。文章充满跳跃和相互矛盾之处,历史事件叙述(包括想象和道听途说的历史)夹杂着对各种哲学、诗歌、理论文本的评论与分析,展现的是詹姆逊一贯的将文本与阐释、历史与理论混为一体,而又不乏自我反思与批判的风格。囿于篇幅,本文无法详尽分析这篇堪称詹姆逊思想自叙的奇葩论文(作为单篇论文,本文已经篇幅过长),但值得提醒读者(尤其是中国读者)的是,文中提到的毛主义作为“影子般但又核心的问题所在”。这个核心所在是通过大量对阿尔都塞的描述来澄清的:“我们在重读阿尔都塞《为了马克思》时常常忽视,但确实是明白无误的一点,是(阿尔都塞)的新问题构成的来源是毛主义自身,尤其是毛泽东的《矛盾论》。毛在该文中提出了复杂和多元决定的时刻,各种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矛盾得以展示”(Jameson, “Periodizing” 191)。 这个多元决定的时刻在《政治无意识》中构成了詹姆逊阐释学的第三个、也是最终的阐释视野,即“历史的视野”或“生产方式”(第一是“政治的视野”即个别文本的政治喻义,第二是“社会的视野”是各种文本的对话)。詹姆逊写道:“我们建议把这个新的、最终的对象(第三个视野)定位为‘文化革命’(由新近的历史经验而启发),即是这样一个时刻,不同的生产方式的共存明显开始对立,矛盾成为政治、社会与历史生活的中心。”接下来,詹姆逊认为“中国未完成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验”可以有许多历史相似的实践,比如欧洲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等等,可理解为“资产阶级文化革命”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83—84)。在这里,作为阿尔都塞理论来源的毛主义不仅仅是詹姆逊“影子般但又核心的问题所在”,更是理解他的中国情结以及第三世界寓言情结的钥匙,很值得做一番“症候式阅读”。
中国的詹姆逊主义
王宁在2002年认为,詹姆逊“作为一位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比较文学学者,他的著述之影响早已超越了特定的学科界限和国别界限,具有着广泛的世界性影响。也许因为他和中国的特殊关系,他在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学术界的影响更是令他的同行望其项背”(20)。本文前面讨论了詹姆逊“中国特殊关系”的源流,无论是阿尔都塞、毛主义还是中国文革,都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产物,也都是詹姆逊在美国的远距离的了解。这一情形在他1985年北大讲学之后有了很大改变,他终于有了跟中国的亲密接触。六十年代的中国想象与八十年代的中国现实遭遇,给詹姆逊带来了哪些影响?后现代主义与第三世界寓言这两大理论,尤其是后者,跟中国之行不无关联。但詹姆逊的思想体系在《政治无意识》中已经成熟并完整地表述了,他在1986年以及后来数次中国之行,并未动摇改变他的思路。与许多西方左翼跟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不同,他基本不对中国的现状说三道四。对于中国的詹姆逊主义,他也只是审慎地在跟中国学者的访谈中,委婉作出回应。那么,什么是中国的詹姆逊主义?
本文的这个提法,不仅仅是指中国今天已经十分庞大,而且还在不断增长的詹姆逊研究。詹姆逊大概会仿效马克思,多次告诉他身旁的人“我从来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那样,说“我不是个詹姆逊主义者”。中国詹姆逊主义的历史源头,一般认为是他的85年北大演讲和87年的中文书《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詹姆逊虽然八十年代中期就到了中国,并第一时间发表了他最新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但中国学术界真正形成詹姆逊热的时候,却要等到大约十五六年之后的新世纪开端。除了许多研究詹姆逊的博士论文和专著、大量介绍性的论文外,越来越多的文学(不限于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文化研究、史学和哲学的论述中,引用了詹姆逊的观点。在众多西方文艺理论中,也许除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詹姆逊理论是中国学界最为关注的。
本文认为,中国的詹姆逊主义,是指中国人文学术界在本世纪初到今天十几年里,围绕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和第三世界寓言这两大主题,建构出的一种顺应中国学术环境和大背景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跟詹姆逊的理论本身相差甚远。
以下就这个看法做一些简要的阐述。
第一,中国詹姆逊主义与詹姆逊的学术思想有多重错位
。前文曾提到西方理论的两个错位,一个是西方理论背后的1960—70年代的全球激进主义思潮与今天的全球化现状之间的错位,一个是人文与社会科学的错位。1980年代以来的欧美社会进入了发达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詹姆逊企图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乃至全球文化做出新的判断,但他的“温和的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常常陷于左右矛盾之中。虽然他不断地在反省其左翼激进主义的思想基础,看到了理论与其研究对象之间的差异错位而努力修正(如提出第三世界寓言、不断回到欧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文学叙事等),但詹姆逊拘泥于文学叙事的方法论,对于当代世界极其复杂的政治、经济走向的解读往往是苍白无力的,与当代西方社会科学与政治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对话、辩诘、争论也是阙如的。这是发生在西方思想界学术界内部的错位。在八十年代中期,詹姆逊来到中国,这是他后现代主义理论热烈思索酝酿的关键时刻。与此同时,“他者政治”的政治目标、元批评寓言阐释学的方法,与他在中国的阅读(尤其是鲁迅作品)产生了化学反应,催生了第三世界寓言理论。然而他的理论却与中国有时间上很大的错位。这个时间差更多是思想意义上的。詹姆逊来到的中国,当时正值文化反思的高峰。中国思想界的领军人物李泽厚等与年轻一代的人文知识分子,正在通过大量译介西方启蒙和现代性的思想,尤其是自由主义者如哈耶克、阿伦特等对极权主义的批判与反思,对中国五四以来的激进传统,尤其是文革的极左政治展开无情的批判。此时,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法兰克福学派和解构主义等西方新潮思想也陆续进入了中国。中国知识界对现代中国的反思,与西方左翼知识界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在结构上和深层逻辑上不仅有“反思”的相似,而且有距之不远的六七十年代的激进、革命时代大背景的相似。然而“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李泽厚语)中的主旋律,对中国知识界来讲始终是“救亡”。在八十年代,“救亡”即是参政干政。志存高远的文人们,企图以人文思想“批判的武器”来为中国制定改革的蓝图。政治干预倾向性强烈的文化热,对西方理论的选择性同样强烈。虽有深层次的结构与逻辑相似、激进主义的大历史背景相似,八十年代中国译介西方的选择,显然没有选中几乎同时在欧美学术界兴起的后学思潮。思想虽然有平行、相遇、几乎交叉,但终于错过了真正的相恋,唱了一曲“向左向右向前看”之歌(取几米漫画、同名电影和孙燕姿流行歌曲之意,同一屋檐下却相互错过了机会)。
中国詹姆逊主义真正的浮现差不多过了十几年,即二十一世纪之初。这十多年,用李泽厚的话来讲,是“思想淡出,学术凸现”的时代。人文学科从政治舞台中心迅速消遁,商品化、全球化逐渐进入中国。种种西方发达社会的“后现代”文化现象,如消费主义文化、文化产业、社会多元化等趋势,也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出现,并迅速在全国传开来。二十一世纪开始,更是中国学术制度化的开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GDP成为世界第二,中国全球崛起势不可挡。人文社会科学的制度化、国际化呼声越来越高。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服务,成为学术制度化的主导方针。中国詹姆逊主义经过了多年的译介和积淀,应运而生。詹姆逊在美国这个资本主义超级大国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其象征意义对于中国来讲远大于欧洲其他国家。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旗帜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相似。法兰克福学派和其他后学的新马克思主义与左翼色彩,与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有千丝万缕的相似、相近。后现代主义理论广义描述全球化时代西方主导的文化方式(主要是消费主义流行文化),同样适用于中国。在许多后现代理论中,高调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如“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詹姆逊后现代主义,其与中国语境的合适性分外突出。詹姆逊的第三世界寓言和鲁迅范文,是出自西方内部的对西方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西方中心论的犀利批判与否定,也可以被视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文化的尊重。第三世界寓言在中国首先是作为后殖民主义理论介绍到中国来的,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詹姆逊主义的另一根理论支柱或基本点。本文前文用了相当篇幅分析詹姆逊的学术脉络,旨在说明后现代主义理论和第三世界寓言都是詹姆逊元批评和文学阐释学的延伸,是阿尔都塞认识论基础的拓展。但是,近十几年来中国学术界大量的詹姆逊评述和应用,对于《政治无意识》里全面阐述的元批评文学阐释学的“一个中心”恰恰未见重视,而把后现代主义、第三世界寓言这“两个基本点”,当成了中国詹姆逊主义的核心。这是美国学者詹姆逊的学说与中国詹姆逊主义的又一大错位。更深层次的错位,则是詹姆逊反复强调的毛主义的“影子般但又核心的问题所在”。在当前的语境之下,中国詹姆逊主义的大量论述所选择的,是对这一“核心所在”的回避。
第二,中国詹姆逊主义与詹姆逊的学术思想的错位,寓言式地展示了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命运。
本文第一部分就西方理论与中国的关联已有所评述。现以中国詹姆逊主义为“症候式阅读”的范本,再多写几句。似乎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问诊”:1.中国知识界多半以实用主义目标和拿来主义的手段来选择、修正、误读和建构西方理论。学术为政治社会服务,这也许是理论旅行的宿命。这方面中西并无区别,萨义德一篇“理论的旅行”论文,在中国文论圈子里早就耳熟能详。詹姆逊的学术思想也是如此,译介开路,以欧洲之话语,议世界之问题,立脚点是美国。我们注意到,詹姆逊已然与欧洲的思想有时间和空间的错位。他以文学批评方法论(即便是脱胎于阿尔都塞政治哲学)来分析复杂的政治与社会问题,以激进时代的左翼思维把握“后左翼”当代西方,并大幅度跨界到欧美之外的第三世界乃至全世界,已是捉襟见肘,矛盾百出。但毕竟欧美历史渊源一脉相承,加上以詹姆逊深厚的欧美文化底蕴和严谨广博的治学态度,在建构其理论核心即元批评文学阐释学时,做到了学术探索与思想创新的基本平衡。中国詹姆逊主义则遵循了中国接受西方理论的一般规律:一是奉行实用主义至上原则,服务眼前、顾及当下;二是学术上缺少穷其源流、究其真意的求索精神;三是忽视西方理论自身的历史脉络和背景。詹姆逊主义顺应了21世纪以来中国大环境的需要,学术上的国际化,与英语主流学术范式接轨。詹姆逊主义正好符合“西方话语+马克思主义”即“时尚流行+政治正确”的模式。近年来,詹姆逊研究进入中国国家体系,成为国家项目省部级项目。最近新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又成为教育部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由此,中国詹姆逊主义堂皇进入主流学术话语。毫无疑问,这给中国学术界与詹姆逊和众多西方理论的深入对话思想交锋提供了新的机会。
2.在建构中国詹姆逊主义过程中,误读、变异、错位、修正不可避免,而且做起来往往是名正言顺的。往小里说,误读或修正是翻译问题;往大里说,是理解原著的立场问题。王逢振在詹姆逊文集的前言中写道:“不过,必须承认詹姆逊的著作确实难懂。他喜欢用长的复合句,从句套从句,常常使人觉得眼花缭乱”(412)。翻译詹姆逊更是个艰难的任务。因此王逢振认为,“我们主张‘肯定的误读’,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在理解和联想的基础上,说明(翻译)原作的意思。这样说,我并不是为‘不忠实’的翻译开脱,而是希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充分利用自己的知识构成,驰骋自己的想像,前后左右进行联想,以便从这些文集中获取更多的启示”(413)。问题是,这些联想、启示和发挥,跟詹姆逊原著文本有多大的关联?近年来,针对西方理论在中国学术界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现象,张江对西方理论的“强制阐释”做了严厉的批判。他首先举的例子就是詹姆逊。在给北大学生讲课时,詹姆逊用《聊斋志异》的文本做例子,介绍格雷马斯的叙事学理论。张江认为,“这就是典型的‘强制阐释’”(张江)。值得一提的是,詹姆逊对这本由唐小兵编辑的翻译记录的中文书,一直比较纠结。在多个私下场合,他说“那是唐小兵的书,不是我的书”;在杜克文学系网站上,由他本人确定的书目中,并不包括这本中文书。詹姆逊精通西方各种语言,他作品的法、德、俄、西文的译本,都经过他本人的审定和授权。他不懂中文,在中文书出版时,他跟北大本科生唐小兵之间也基本没有就该书做过沟通。单以詹姆逊(唐小兵?)的北大演讲录举的中国文本为例的孤证,来说明西方理论的“强制阐释”,则难以令人信服。至于说到詹姆逊原著的立场问题,许多中文论文毫不吝惜对他的“偏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严苛批评。胡亚敏写道:“我们不禁要问,(詹姆逊)这种多种视角、多种话语并存的批评模式还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吗?[……]马克思主义批评可以吸收和借鉴某些批评流派的特定分析话语,但绝不能异质并存,不能同时持不同立场。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批评可以吸收当今一些新的成果,但其基本原理是必须坚持的”(34)。
中国詹姆逊主义的“中国特色”,有几个方面:一、赞赏来自美国这个资本主义超级大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旗帜;二、强调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三、认同第三世界寓言理论对第三世界特殊性(可理解为中国特殊性)的肯定。基本上对詹姆逊的学术思想采取了切割式、或“六经注我”式的实用主义态度,同时不忘中国特殊语境的“政治正确性”。
但为什么要绕这么多弯子,通过詹姆逊这个“老外”之口,来讲中国的事呢?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始终是中国现代性的一大特色。任何时候,都需要有许多“说中文的老外”与“说洋泾浜的中国人”来谈论中国的事情。今天中国的学术国际化,不仅仅是发表英文论文和专著;更普遍的是在中国无处不在的“洋腔洋调的中文”。我们姑且可称之为“理论洋泾浜化”。张江对西方理论“强制阐释”的批判,可谓振聋发聩。中国多年来翻译外国电影,多半是由一流演员和电影译制片厂的专业配音演员予以配音,而不是保留外语原汁原味的字幕。中国观众早就习惯了外国人讲带着洋腔洋调的汉语,以为这就是外国人讲话的方式。这是中国的一大特色(这个情况近年来有很大改变,外国电影打字幕成为常态)。更早的历史回溯,我们也许都忘记了现代汉语受到的日文及和制(日本式)汉语的影响。如果没有日文首先对欧洲现代观念做了大量的汉字(和制汉语)翻译,今天我们也许无法在现代社会进行沟通。詹姆逊的晦涩文风在中国学术界也颇有影响,尤其是中国的一些新左派学者群体,刻意仿效詹姆逊文风,堪称“理论洋泾浜化”的示范。
3.中国詹姆逊主义跟詹姆逊本人的毛主义想象类似,是选择性的误读和错位,导致了对重要问题的理论遮蔽和对话的缺失。本文行文至此,篇幅已经过长,虽然涉及的内容,也仅仅浅尝辄止而已。就将这个理论遮蔽与对话缺失的问题作为全文的收尾。阿尔都塞的理论是西方左翼思潮的“影子般但又核心的问题所在”,对法国的福柯、德里达、英国的威廉斯、霍尔、伊格尔顿、美国的詹姆逊和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们都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在詹姆逊那里,这一核心所在被认定为“毛主义”。毛主义是西方左翼知识界的想象,当然,其源流是中国的毛泽东思想,或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主义又不限于欧美知识界,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今天,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毛主义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革命的、具全球影响的普世主义或普世价值。毛主义与西方批判理论的关系、与全球尤其是第三世界革命的关系、与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主导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极其错综复杂。在中国詹姆逊主义的话语中,毛主义问题被彻底遮蔽掉了。中国学术界对詹姆逊理论做了割裂式、选择性的解读。究其原因,当然是今天中国产生詹姆逊主义的大时代背景。但是不容忘记的是,在1960年代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毛泽东思想对西方思想界产生了重大的“逆向影响”(“逆向”是指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俄国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对中国“正向”影响的回馈——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后来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反过来又影响了西方左翼)。詹姆逊的中国情结有深刻的理论与思想渊源,即是毛主义的“影子般但又核心的问题所在”。这个问题既然是詹姆逊的核心问题,又跟中国有直接关联,而且跟今天世界知识与思想界的大趋势也密切相关,应该成为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来认真思考。
詹姆逊本人跟中国学者有过许多次对话。几乎成了习惯,中国人文学者到杜克大学访学时,都希望跟他面对面对话,詹姆逊也十分乐意这种跟中国学者的对话。这些对话都很有价值,是了解詹姆逊对中国的詹姆逊主义看法的第一手资料,值得认真研读。中国当代思想界的领军人物李泽厚1994年应詹姆逊之邀,到杜克大学参加全球化问题学术会议,二人终于在美国做了一次迟到近十年的对话(1985年,詹姆逊的学生、好友李黎,也是李泽厚的好友,曾试图安排过二人见面)。詹李对话这次由笔者主持、翻译并记录,经过詹姆逊和李泽厚两人的审定。这个对话有点像外交谈判。两人各自介绍了自己的主要观点,也很有礼貌地提出了问题。谈话涉及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和毛主义时,似乎开始产生火花。李泽厚希望能有一个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在李近期的思想中,他更为关注中国传统思想如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问题)。而詹姆逊则回避了笔者所问的他对毛主义的最新看法,转而向李泽厚提问:“刘康开始时提到毛主义的影响问题,尤其是60年代。作为一种独特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在当时具有普遍性,它在其他不同的政治环境中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既然你刚才强调现在急需创造一种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强调‘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性,我想问李泽厚先生,这一独特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有哪些价值?我们是否也需要创造区域性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你们的有没有什么关联?这就是我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性问题”(刘康,“访谈录”355)。詹姆逊的疑问,现在看来关乎理论的普世性和特殊性问题,具体说来,表达了詹姆逊对“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或中国特殊论(Chinese Exceptionalism)的理论与意识形态基础这个深层次问题的疑问。由于两人对各自的学术观点都未曾有深入了解,作为思想家的詹姆逊和李泽厚,在这种形式的对话里,是难以展开真正意义上的思想交锋与对话的。即便如此,一些思想火花的冲撞可见端倪。詹姆逊提出的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即西方的毛主义)究竟是一种(革命的)普世价值,还是中国特殊论的意识形态?关于中国特殊论或特色论这个问题,是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等政治思想纲领领域的话题。
最后,就詹姆逊而论,他最重要的成就在于文学领域的元批评阐释学。他涉及到的更为深广的政治、社会思想和实践问题,其中包括西方批判理论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等,都是太复杂、牵涉太多学科和方法的问题。我们或许要提醒自己,在文艺理论范围内的研究与探索,在涉及更广泛的问题和领域的时候,各种错位、误读,往往会让我们的思考大而不当,误入歧途。尤其是在意识形态大框架之下,我们不免会忽视不同学术领域和专业的局限(如文学和政治学),混淆真理与思想探索之间的界限。比如说,詹姆逊时刻在讲政治。但他讲的是文学范畴内的政治,是美国人文学术领域内的政治。跟中国语境中的政治、跟政治领域里的政治,是不同的范畴和概念。詹姆逊天天在讲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对于詹姆逊来讲并不完全等于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这句话出自毛泽东《实践论》,詹姆逊对此高度认同。
今天的中国文艺理论界热闹非凡,各种西方理论让人目不暇给。但本文企图表述的一个观点则是,我们实际上的理论资源还是很缺失与匮乏的。西方理论与方法当然对中国有启发。但这些来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激进时代的左翼人文思潮,今天用来解释中国的文化现状,却有严重的历史错位和局限。欧美左翼后现代理论的历史在地性和本土性,根植于发达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社会,来自欧美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制度化结构。而中国却正处于一个历史转型的、逐步走向现代化的时代。欧美左翼激进的批判理论和后现代理论针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的深刻批判,在中国这个现代化转型社会和具有强大左倾的历史惯性的社会里,也往往会产生难以预料的效果。在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依然以实证、经验主义和理性选择论为主导,对于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领域的问题,鲜有涉及,人文学科则有左翼后现代理论占上风,二者基本是两军对垒,老死不相往来。在这样一个理论缺失与匮乏的时代,欲提出中国的问题意识,所面对的困境往往难以想象。西方理论在中国过度的传播,影响了中国学术界的理论创新。尽管如此,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的职责与使命是关注人类命运,文学与文化研究尤其要关注当代社会。再有多大的困难,学术研究也不可回避,更不可放弃。
注释[Notes]
①笔者对这一问题大约十年前做过较为详尽的分析。见刘康:“西方左翼知识界的危机——从美国学术左翼的现状谈起”,《文艺争鸣》2(2008):18-26。
②对于美国2016年大选反映的左右意识形态撕裂、左翼激进派的作用,可参见笔者的媒体时评。刘康:“美国大选中的媒体、民意与意识形态”,《澎湃新闻》2016年11月14日,〈http: //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60868〉;刘康:“民粹-民族主义宣言:解读特朗普就职演讲”,《澎湃新闻》2017年 1月 21日,〈http: //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05476〉。
③有关论述参见ImmanuelWallerstein.“Eurocentrism and its Avatars: The Dilemmas of Social Sciences.” New Left Review 101/102(1998):93- 107.Immanuel Wallerstein.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The Limits of Nineteenth-Century Paradigms.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1.黄宗智、高原:“社会科学和法学应该模仿自然科学吗?”,《开放时代》2(2005):158-79。黄宗智:“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学术?——国内十年教学回顾”,《开放时代》1(2012):60-78。赵鼎新:“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从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谈起”,《社会学评论》3.4(2015):3-18。
④诺贝尔经济奖1998年得主、哈佛大学印度裔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对理性选择理论有中肯的分析与批判。参见Amartya Sen.“Rational Behaviour.”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Eds.Steven N.Durlauf and Lawrence E.Blume.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2008.
⑤ 英 文 参 见 Douglass Kellner:“Fredric Jameson.”〈https: //pages.gseis.ucla.edu/faculty/kellner/papers/JamesonJH.htm〉.中文参见王逢振:“前言: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他的著作”,《詹姆逊文集》(第1卷),王逢振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06页。
⑥ 见杜克大学文学系网站詹姆逊个人页的作品目录:〈http: //literature.duke.edu/people/fredric-jameson〉。
⑦原文如下:Among Professor Jameson's ongoing concerns is the need to analyze literature as an encoding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imperatives,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modernist and postmodernist assumptions through a rethinking of Marxist methodology.见杜克大学文学系网站詹姆逊个人介绍页:〈http: //literature.duke.edu/people/fredric-jameson〉。
⑧此处为笔者的译文。可根据英文原文,与王逢振、陈永国的译文做一对照。参见王逢振、陈永国译:《政治无意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0页。詹姆逊的英文句式和风格独特,句子冗长,从句套从句,受法文和德文的文体影响很深。詹姆逊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旁征博引,蕴意复杂,涉及欧美思想文化传统方方面面,给翻译带来很大考验与挑战。笔者试译的关键一段,希望尽可能用中文来清楚表达原意。把他的长句分成多个短句,语序也尽可能按中文习惯做了调整。詹姆逊的文字晦涩难懂,英文原文本身就非常艰涩,用中文翻译更是一大难题。
⑨关于“结构式因果关系与表现式因果关系”的论述,可参见Robert Paul Resch.Althusser and the Renewal of Marxist Social Theo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尤 其 是 “Chapter 1, Structural Causality,Contradiction, and Social Formations”,34-83,详尽分析了阿尔都塞通过批判黑格尔主义对斯大林模式的深刻反思。结构式因果关系是阿尔都塞的核心概念之一,认为历史的因果关系是在大的总体结构下,由多种次结构、多重因素、多元决定的,而不是一元、线性、唯一的所谓历史本质而决定,按黑格尔的理论,这种本质是透过各种外在的表相表现出来的。
⑩笔者对阿尔都塞理论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关联做过分析。见 Liu Kang.“The Legacy of Mao and Althusser:Problematics of Dialectics, Alternative Modernity,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Rethinking Marxism: A Journal of Economics, Culture, and Society 8.3(1996):1- 25.中文译文(史安斌译)收录在刘康:《文化传媒全球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章“现代性不同选择与文化革命——毛泽东与阿尔图赛的理论思考”。
[11] 参见 Imre Szeman.“Who's Afraid of National Allegory?Jameson, Literary Criticism, Globalization.” Th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100.3(2001):803 -27; 又 见 Ian Buchanan.“National Allegory Today: A Return to Jameson.”On Jameson:From Postmodernism to Globalization.Eds.I.Buchanan&C.Irr.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173- 88.
[12]这句话的中文译文引自钱佼汝译《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24页。
[13]关于寓言与象征的解构主义理论,参见Paul de Man.“ The Rhetoric of Temporality.” Blindness and Insight:Essays in the Rhetoric of Contemporary Criticism.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14]中文有大量论文研究詹姆逊的第三世界寓言理论。近年来一些青年学者的论文颇有深度。吴玉娱的论文从詹姆逊“寓言”线索出发,并引入日本学者竹内好等,从广阔的视野和内在逻辑分析詹姆逊的理论。参见吴玉娱:“詹姆逊‘民族寓言’说之再检讨——以‘近代的超克’为参照兼及‘政治知识分子’”,《中国比较文学》4(2016):187-200。王钦则详尽论述了该理论蕴含的詹姆逊思想的内在逻辑。参见王钦:“杰姆逊的‘民族寓言’:一个辩护”,《文艺理论研究》4(2014):211-18。
[15]参见杜明业:“詹姆逊研究:三十年的学术史回顾”,《文化研究》21(2014):249-61。 又参见李世涛:“詹姆逊后现代批评及其在中国的接受”,《求索》6(2002):184-88。2000—2014年间,有11部研究詹姆逊的中文专著出版。到2016年6月,在“中国知网”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中,在“主题”检索项分别输入“詹姆逊”“杰姆逊”“詹明信”三个检索词,有989篇学术论文专门研究詹姆逊或主要涉及詹姆逊的思想。毛雅睿帮助做了有关文献搜索,谨致谢忱。
[16]中国最早出版的中文后殖民理论读本,把詹姆逊第三世界寓言论文作为第一篇。见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17] 大约20年前,加拿大华裔学者谢少波在中国出版的詹姆逊研究专著,有一章专门讨论詹姆逊与毛泽东的关联。见谢少波:《抵抗的文化政治学》第四章“詹姆逊的毛情节:学习60年代”,陈永国、汪民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04 -21页。这是笔者所见唯一一部涉及詹姆逊的毛主义情结的中文著作。在予以詹姆逊的毛主义想象高度评价时,谢少波热情而浪漫地歌颂中国的文革:“毛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文化大革命不可否认地给臣属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坚实、具体、愉悦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感”(119)。该书原文应该是用英文写的,中文本是译文。笔者并没有查阅到该书出版的英文版,中文译者大概是根据英文未发表稿翻译的。
[18] 胡亚敏2002年取得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学批评——詹姆逊批评”(02JA710004)是第一个国家级詹姆逊研究项目。2016年曾军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16ZDA194)。
[19]张江在《文学评论》发表的学术论文对这一说法有所修正。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6(2014):5-18。王宁在他的回应论文中,针对张江论文中举詹姆逊为例这点,用了相当篇幅来说明,我们需要全面理解詹姆逊庞大芜杂的理论体系。王宁:“也谈场外理论与文学性——答张江先生”,《探索与争鸣》1(2015):27-29。
[20]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对毛主义的兴趣增大,尤其是当代理论与中国的关系。法国文化界(不限于学术界)对激进左翼跟毛主义的关系始终高度关注。关于毛主义的全球普世性,尤其是在第三世界的影响,见 Liu Kang.“Maoism: Revolutionary Globalism for the Third World Revisit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52.1(2015):12- 28.
[21]关于中国学术界对詹姆逊“割裂式”的解读这点,笔者受到曾军的启发。
[22]参见“访谈录:詹姆逊—李泽厚—刘康”(1994年),王逢振编:《詹姆逊文集》(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349 -69页;何卫华、朱国华:“图绘世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教授访谈录”,《文艺理论研究》6(2009):2- 11; Yang Jiangang, Wang Xian and Fredric Jameson.“Marxism and Form: An Interview with Prof.Fredric Jameson.”(杨建刚、王弦、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教授访谈录”)《文艺理论研究》2(2012):77 -81;曾军:“后现代性,或资本主义文化逻辑——詹明信访谈录”,《文化研究年度报告201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52-61页;颜芳:“‘毛主义’与西方理论——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教授访谈录”,《外国文学研究》2(2017):1-17。颜芳与詹姆逊2016年的最新访谈,直接讨论詹姆逊与毛主义的关联,非常有价值。詹姆逊认为,毛主义对西方左翼的吸引力来自毛的农民主体性和平民主义(populism,通译“民粹主义”),并认为“毛主义仍然是关于真正的革命到底是什么的一个典范”(3)。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Althusser, Louis.“To My English Readers.” For Marx.Trans.Ben Brewster.London: Verso,1969.9- 15.
Auerbach, Erich.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íterature.Trans.Willard Trask.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
De Man, Paul.“The Rhetoric of Temporality.” Blindness and Insight:Essays in the Rhetoric of Contemporary Criticism.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187- 228.
Eagleton, Terry.Literary Theory.London: Blackwell,1983.
---.Marx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
胡亚敏:“理论仍在途中——詹姆逊批判”,《外国文学》1(2005):33-37。
[Hu, Yamin.“Theory Still on the Road: A Critique of Jameson.” Foreign Literature 1(2005):33-37.]
Jameson, Fredric.Marxism and For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1.
---.“Periodizing the60s.” Social Text9/10(1984):178-209.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146(1984):52- 92.
---.“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Social Text15(1986):65- 88.
Kellner, Douglas, ed.Postmodernism, Jameson, Critique.Washington D.C.: Maisonneuve Press, 1989.
刘康:“访谈录:詹姆逊—李泽厚—刘康”(1994),《詹姆逊文集》(第1卷),王逢振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49-69页。
[Liu, Kang.“Conversations of Jameson, Li Zehou and Liu Kang.”(1994).Selected Works of Fredric Jameson.Vol.1.Ed.Wang Fengzhen.Beijing: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04.349- 69.]
——:《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中国大陆版);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5年(台湾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新版)。
[---.Dialogism:Bakhtin's Theory of Cultural Change.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1995; Taipei:Maitian Press, 1995(Taiwan editio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2(new edition).]
Ritzer, George.Modern Sociological Theory.New York:MGraw-Hill,2004.472- 77.
王逢振:“前言: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他的著作”,《詹姆逊文集》(第1卷),王逢振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12页。
[Wang, Fengzhen.“Foreword: Fredric Jameson and His Works.”Selected Works of Fredric Jameson.Vol.1.Ed.Wang Fengzhen.Beijing: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4.412.]
王宁:“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他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南方文坛》2(2002):20-22。
[Wang, Ning.“Fredric Jameson and His Marxist Theory.”Southern Forum 2(2002):20-22.]
张江:“当代文论重建路径——由‘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17日。
[Zhang, Jiang. “Reconstructing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From Forced Interpretation to Ontological Interpretation.”Chinese Social Sciences Journal 17 June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