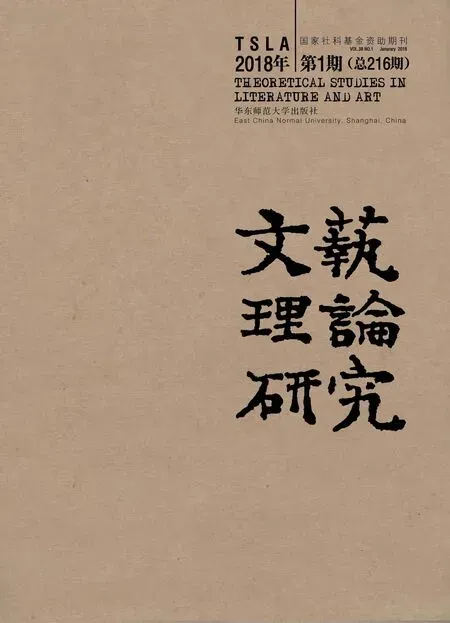克里斯蒂娃与后现代文论之发生
赵雪梅
作为一名生活在群星荟萃,大师迭出的时代的理论家,茱莉娅·克里斯蒂娃的光辉注定会被罗兰·巴特、德里达以及拉康等誉满全球的国际型大师所湮没。尽管克里斯蒂娃在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心理分析和解构主义等领域均有建树,但较之成一家之言的罗兰·巴特、德里达以及拉康等理论巨擘,学界对她的关注度显然要少得多。即便如此,克里斯蒂娃在后现代文论的发生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
后现代文论发轫于法国的后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文论,法国学者对后现代主义的传播与流行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正如美国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的重要代表小约翰·科布(John B Cobb,Jr.)教授所云,“正是法国的后结构主义思潮使‘后现代主义’变成了一种流行的思潮和单独的流派。这就是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福柯(Michel Foucault)领衔的法国学派。他们使后现代主义广泛流行并且获得了最为广泛承认的含义。这个运动中的主要人物有G.德勒兹(Gilles Deleuze)、R.吉拉尔(Rene Girard)、L.伊里加雷(Luce Irigarary)、J.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J.拉康(Jacques Lacan)和 J.F.利奥塔(Jean Francois Lyotard)”(欧阳康 70—71)。 其中,克里斯蒂娃不仅是科布眼中的法国后现代主义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她对后现代主义文论的发生也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本文以克里斯蒂娃为中心,通过论析她对巴赫金、罗兰·巴特和德里达相关理论的引介或启发意义,挖掘克里斯蒂娃及其诗学在后现代文论进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还原其被长期遮蔽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一、克里斯蒂娃与作为后现代文论启发者的巴赫金诗学
关于巴赫金诗学,克里斯蒂娃曾如此评价:“巴赫金的对话性、文本多样性等等启动了后结构主义的时代”(祝克懿)。曾经默默无闻的巴赫金诗学得以誉满全球,进而推动西方文论由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时代的过渡,其中首要之功臣正是克里斯蒂娃。克氏本人也对此予以确认,“现在一般认为,从结构主义时代到后结构主义时代,我对巴赫金的译介,以及对互文性、对话性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推动作用”(“互文性理论对结构主义”9)。克里斯蒂娃向西方世界的引介,不仅成就了巴赫金的世界性声誉,也成就了随之开启的百花齐放、异军突起的后现代主义文论的繁荣局面。
克里斯蒂娃的引介只是一个偶然因素,巴赫金诗学对以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文论的启发意义及其在西方世界的成功,与其本身的理论主张与特质有着必然的联系。首先,巴赫金诗学是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不确定性”“内在性”以及“狂欢化”等概念的直接理论渊源。“不确定性”既是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理论的重要观点,也作为其理论本身的特质贯穿于整个理论体系。“不确定性”意味着“相对性”,意味着任何制度和秩序,任何权势和地位,都具有令人发笑的相对性。换言之,“不确定性”的核心在于“不把任何东西看成是绝对的,却主张一切都具有令人发笑的相对性”(《诗学与访谈》163—64)。“不确定性”也意味着“未完成性”。在巴氏看来,诸如“永恒的”“稳固的”“绝对的”和“不可变更的”这些范畴以及“任何为当代所熟知的确定性和完成性,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可笑的,因为它们都是具有局限性的”(《拉伯雷研究》527)。在后现代主义理论中,“不确定性”作为后现代主义的两种根本倾向之一(Hassan 92),被伊哈布·哈桑认为“是我们的知识新秩序中的一个决定性元素”(Hassan 119)。需要指出的是,在谈到这一概念所涉及的文学理论时,伊哈布·哈桑首先提及的便是巴赫金的“对话主义”理论(Hassan 168),由此可见后现代的“不确定性”概念与巴赫金诗学之间的重要关联。
和“不确定性”一样,“内在性”不仅是后现代主义的两种根本倾向之一,也“构成了(后现代)诗学的基础”(Hassan 76)。尽管哈桑并未对“内在性”进行明确的界定,但如他所言,“这一抽象的倾向可以由诸如散布、传播、推进、相互作用、交流、相互依存等各式各样的概念来进一步描绘”(Hassan 93)。可见,“内在性”更多的是指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关联,这与拒斥封闭,强调众声喧哗、交流与对话的巴赫金的“对话主义”理论不谋而合,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对话理论”的衍生概念。“内在性”普遍存在于后结构主义等后现代文论中,以后结构主义文论为例,“后结构主义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把文学行为,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美学实践——电影、音乐、舞蹈等——作为对话性行为、多声部行为来研究”(“互文性理论对结构主义”9)。
“狂欢化”是哈桑概括的11个后现代现象之一,哈桑坦言,他所谓的“狂欢化”这个术语正是来自巴赫金。它不仅包含了“内在不确定性”等7个后现代现象的内涵,也传达了后现代主义喜剧的、荒诞的精神。哈桑将巴赫金所谓的小说或狂欢节称为“反系统”,甚至认为其“代表后现代主义本身,或者至少代表它的那种不断更新的嬉戏和颠覆元素”(Hassan 171)。可见,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所倡导的消解中心、瓦解权威以及对官方永恒势力的颠覆,正是后现代主义的精神旨趣与灵魂归所。
巴赫金诗学为后现代主义文论的研究领域、路径与模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思维模式与研究方法。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首先,巴赫金诗学的研究路径与思维模式给予后现代的理论研究以重要启发。如大众文化研究某种程度上就是巴赫金民间文化研究启发的结果。以巴赫金的民间文化研究为理论契机,大众文化研究通过挖掘当代大众消费文化找到了与中世纪民间狂欢文化之间的融通点。参照巴赫金以张扬民间文化来颠覆中世纪教会的官方文化的研究路径与策略,后现代的大众文化研究者们以弘扬大众文化来消解现代精英文化及其深度模式。其次,巴赫金诗学的理论特质及其主张对后现代文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文化研究的非精英性、跨学科性和理论的可交往性等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均来源于巴赫金,或者说与巴赫金的学说有着诸多相通之处”(王宁 24)。再次,巴赫金诗学给予后现代理论家普遍的启发与影响。据统计,“近二十多年来,几乎介入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争鸣的所有主要西方学者,例如米歇尔·福柯、尤根·哈贝马斯、茨威坦·托多洛夫、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伊哈布·哈桑、霍米·巴巴、特里·伊格尔顿等,都不同程度地从他的著述中发现了新的启示”(王宁 23)。这种启发与影响更直观地体现为巴赫金的诗学术语及其理论主张在后现代论著中地频繁使用,现有的研究表明,“巴赫金著述中特有的术语,诸如对话理论、时空体结构、话语理论、狂欢化、杂语共存、交往行为等,均高视阔步地频繁出现在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家的著述中,并被他们接纳进论辩的学术理论话语”(王宁23)。最后,巴赫金诗学的前瞻性使其成为引领后现代热点话题的学术明星。伊格尔顿指出,“几乎没有一个后现代热点话题是巴赫金没有预料到的。话语,混杂性,他者,性别,颠覆,越轨,异质性,大众文化,身体,离心的自我,符号的物质性,历史主义以及日常生活。正如格雷厄姆·皮奇(Graham Pechey)叫他的那样,这个早熟的后结构主义者预示了我们时代如此多的事物,以至于他的著作中没有关于辣妹和小贝的暗示都能让人惊讶”(Eagleton, “IContain Multitudes” 13)。
巴赫金诗学为后现代理论家创建自己的理论或概念提供了重要启发。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的直接源头正是巴赫金的对话主义。她坦言,“一切从与巴赫金有关的故事开始,即使这位俄国形式主义者从未使用过‘互文性’这个词。[……]我的贡献是用文本中的多文本的观点替代了巴赫金的话语中的多声部的概念”(Kristeva,“‘Nous Deux’”8)。基于两种理论的这一渊源,著名的互文性理论研究者艾伦指出:“在我看来,与其说互文性概念源自巴赫金的作品,毋宁说巴赫金本人即是一位重要的互文性理论家”(Allen 16)。罗兰·巴特在接受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方法,提出了“可写的文本”这一重要概念。“可写的文本”在否定文本意义的确定性以及作者对文本的决定性权威的同时,主张一种未完成的、动态的开放文本,主张读者与文本、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对话,以及意义的参照、互证与渗透,与巴赫金的对话主义遥相呼应。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也为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及其追随者们提供了解构策略。如他有关史诗的“独白话语”的论述,和“德里达所强调的‘超验所指’和‘自我表现’”(Kristeva,Desire 77)的概念无异,两者均抵制或瓦解以预设真理为基础的独白式话语权威,倡导开放的、复调的话语探讨,高扬一种尊重多元化与差异的后现代伦理。
综上,尽管巴赫金诗学本身的理论特质是其誉满全球,深受后现代理论家追捧的重要原因,但在巴赫金诗学走向西方乃至世界的过程中,正是因为有克里斯蒂娃在世界理论中心、结构主义重镇法国的最初引介,巴赫金及其诗学才得以迅速引起西方世界的关注,进而走向世界,推动西方文论的后现代进程。正如克里斯蒂娃本人所言:“在我的努力下,巴赫金的重要地位得以确立,而且引起后来那么广泛的影响。[……]巴赫金后来成为文学研究中不能绕过的一个名字”(“互文性理论对结构主义”2)。应该说,克里斯蒂娃对巴赫金诗学的引介体现了其敏锐的学术眼光。后现代文论的发展现实不仅证实了她有关巴赫金的“对话主义和狂欢节的概念可能会开启一个新的超越结构主义的前景”(Kristeva,“‘Nous Deux’”8)的判断,也使她因对巴赫金诗学的引介而间接成了后现代文论发生的推动者。
二、互文性理论与克里斯蒂娃对后结构主义文论的开拓
克里斯蒂娃诗学对后结构主义的开拓不仅体现在符号学领域,也体现在互文性和女性主义等理论中。在符号学领域中,她提出的解析符号学通过以动态符号学理论对结构主义的静态符号观的替换,实现了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的超越。在女性主义理论中,克里斯蒂娃也因对差异化女性特质的推崇而实现了对此前女性主义理论的突破。较之受巴赫金的“文化学的与符号学的遗产”影响的克氏的其他诗学理论,作为巴赫金对话主义概念的变体,以及巴赫金的“比较狭窄的意义上的文学的遗产”,互文性理论在文学理论与批评界的影响力要大得多。克里斯蒂娃本人指出,“在巴赫金理论的基础上,我发展出被结构主义忽略的两个方向;这两方面的研究把我推到后结构主义开拓者的位置”(“互文性理论对结构主义”3)。至于克里斯蒂娃提及的这两个方向,第一个是对“说话主体”的研究,第二个方向是对文本历史的开拓,即克里斯蒂娃所说的,主要探讨“某一文本与此前文本乃至此后文本之间的关系,巴赫金对此已经有所阐述。我明确地将这种文本对话性称为‘互文性’”(“互文性理论对结构主义”3)。可见,互文性理论在克里斯蒂娃对自己的“后结构主义开拓者”的角色定位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据此,我们仅以互文性理论为例,来探讨在以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文论的产生中,克里斯蒂娃及其诗学所起的重要作用。
就互文性理论而言,其对后结构主义的开拓首先体现在开放性文本观的提出。开放性文本强调的是文本的历史维度。这里的文本的历史,一是指文本纵向维度上时间的前后顺延,即文本与此前与此后等文本之间的对话;一是文本横向维度上意义的无限拓展,即将语言以及所有与意义有关的实践,包括文学、艺术和电影等均置于文本的历史中,形成一种文学、艺术与文化等相交叉的开放性文本。用克里斯蒂娃的话来说,“互文性既是文学文本之间的关系,也是文学与绘画、文学与音乐之间的关系”(“互文性理论与文本运用”5)。开放性文本的提出,倡导文本与文化间的对话,拓宽了文本的外延,突破了结构主义原有的封闭的文本观,实现了对后结构主义的开拓。
互文性理论对后结构主义的开拓还体现在动态性文本观的提出。克里斯蒂娃指出,由于她“在进行文本分析时,把文本视为一个动态过程。这促成了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过渡”(“互文性理论对结构主义”7)。克里斯蒂娃的动态性文本观首先源自巴赫金的启发。在她看来,巴赫金“是最先用动态文本模式来取代文本的静态切割观念的人之一。在这一模式中,文学结构不止是单纯的存在,而是因它与其他文学结构的关系而产生”(Kristeva,Desire 64—65)。克里斯蒂娃的动态性文本观还来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以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为铺垫,克里斯蒂娃很容易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找到共鸣。她坦承:“弗洛伊德给我的最大启示是:人不是平面单调的,而是一个多声部的构成。他至少有两个舞台:意识与无意识;每一个层面又包含多种逻辑。[……]弗洛伊德让我们看到,人本身也是一个多声部的构成。精神分析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这一点”(“互文性理论对结构主义”9)。随着巴赫金诗学与弗洛伊德理论在克里斯蒂娃互文性研究中所占权重的变化,互文性的动态性文本观的发展也呈现出了阶段性的特点。
互文性的动态文本观首先体现为对读者的主观能动性的凸显。正如克里斯蒂娃本人所言:“互文性给阐释者很大的自由度,让读者处于非常活跃的状态”(“互文性理论对结构主义”10)。这一观点显然是克里斯蒂娃对巴赫金的对话主义的动态文本结构观吸收的结果。克里斯蒂娃在其介绍巴赫金的重要论文《词语、对话和小说》中指出,巴赫金的动态文本结构主张,文本是“多重写作的对话:作者、读者(或角色)以及当下或之前的文化语境”(Kristeva,Desire 65)。克里斯蒂娃还创造性地将文学批评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包括互文性批评在内的结构主义之后的一个受精神分析学影响的批评方向。这一阶段文学批评的特点是“开始重新关注作者的生平,但并不是把作品视作作者经历的镜子,而是认为作品是一种重构”(“互文性理论与文本运用”10)。当批评不再“把作品视作作者经历的镜子”时,作者不再是作品意义的索隐来源与有效阐释者,其权威地位受到质疑,与之相应,一切与作品相关的固有的价值和等级秩序也随之瓦解;当批评将作品视为“一种重构”时,读者以一种平等的身份参与作品,以及作者之间的对话,进而成为建构意义,阐释作品的行为主体。因此,在互文性阅读中,身为读者的“我们可以自比侦探,去手稿、传记、思想史、历史语境里去搜索,发现文本中的秘密。”互文性阅读意味着我们“面对作品时,既从作者出发阅读,也从我们自身出发阅读。他要求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创造者”(“互文性理论与文本运用”11)。这种倡导读者自主性与植根文化历史语境的文学阅读方式,进一步丰富了文学文本的阐释技巧。由此,互文性的动态文本观也可理解为:在互文性阅读与批评中,由被赋予最大自主性的读者的文本阐释所表征的一种读者-文本-作者多元主体互动模式下的文本的动态性存在。
互文性的动态文本观还表现为话语主体内部的多元意识层面文本间的交流与对话。如果说巴赫金诗学促成了早期克里斯蒂娃动态文本观的提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则促进了后期动态文本观的发展与完善,实现了话语主体多元意识层面文本空间的挖掘与拓展。这是因为,前期的动态文本观更多关注的是作者空间、读者空间和外部文本空间(包括此前和此后的文本)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到了后期,受弗洛伊德的人的多意识层面论的启发,包括作者与读者在内的话语主体的文本空间趋向多元化,与之相应的,文本空间之间的动态性互动也更复杂。换言之,随着话语主体多元意识层面文本空间的引入,文本空间的对话也由此前的话语主体间际拓展到了话语主体内部。这就意味着,互文性的话语主体文本空间由此前的单一性文本空间衍变为作者与读者两大话语主体各自的多元意识文本空间,文本空间的主体性对话由作者——读者的单一模式转变为作者内部、读者内部以及作者——读者的多元互动模式,原有的文本空间的范畴得以突破,互文性理论涉及的文本关系研究由此变得更为复杂,也更为丰富。
互文性概念诞生之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是其超越结构主义,走向后现代的主要外因。1967年,当克里斯蒂娃有关互文性概念的首篇论文公开发表时,正是哲学“终结”或“死亡”论在法国盛行之时,也是有关语言或文学的“衰竭论”在美国文学与文化理论界大行其道之时,互文性有关文本的吸收与转化的主张论证了纯粹原创性写作的不可能性,某种程度上呼应了“衰竭论”与“死亡论”的论调,从而获得了国内外众多后现代主义者的青睐。另外,1968年“五月风暴”的失败为包括巴特等人在内的法国知识分子由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转化提供了思想契机。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说:“后结构主义就是1968年的兴奋和幻灭、解放和放纵、狂欢和覆灭相混杂的产物。当意识到无法破坏国家权力结构后,后结构主义转而发现了颠覆语言结构的可能”(Literary Theory 142)。同样,对于野心勃勃的克里斯蒂娃而言,1968年的“五月风暴”也为她提供了成为时代弄潮儿的绝佳机遇。正如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多斯所言:“我们会轻而易举地看到科里斯蒂娃对巴特和整个《原样》(Tel Quel)集团的影响。德里达特别采纳了科里斯蒂娃的文本间性这一概念。即使在《S/Z》出版之前,巴特在接受雷蒙·贝卢尔访谈时就已经谈到:‘我们可以谈论文学的文本间性,而不是主体间性。’这正是科里斯蒂娃的术语”(多斯 79)。美国后现代理论家伊哈布·哈桑将互文视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Hassan 91)。泼费斯特也提出:“互文性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标志,如今,后现代主义和互文性是一对同义词”(Bertens 249)。事实也如克里斯蒂娃本人所言,“自70年代以来,互文性概念已享受到了巨大的成功。与此同时,这个词已经成为了国际‘明星,’[……]互文性如今已普遍存在于大部分的文学讨论之中,它是一个几乎出现在所有文学理论词典中的概念”(Kristeva,“‘Nous Deux’” 8)。
互文性理论的提出彰显了克里斯蒂娃宏大的学术野心。她和德里达曾经先后在研究索莱尔斯的小说《数目》的基础上形成了各自的理论观点,索莱尔斯因此认为,“在德里达和克里斯蒂娃之间存在理论上的竞争”(皮特斯 185)。在罗兰·巴特看来,“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总是摧毁那一我们以为我们能够从中感到慰藉、引为自豪的最新的偏见”(祝克懿)。同时,克里斯蒂娃的这种积极探索理论创新的意识还与她独特的生命体验有关。作为一名来自东欧的女性移民,克里斯蒂娃移民——女性的边缘化身份使她对西方——男性中心等思想权威产生一种本能的抗拒心理。克里斯蒂娃是幸运的,法国的启蒙传统,以及批评与质疑的精神使她如鱼得水,在很快融入了法国社会之后,她不仅享受起了自己的这种身份,也在这个陌生的国度里发出了自己最强的声音。
三、克里斯蒂娃与罗兰·巴特的后结构主义转向
某种程度上说,作为法国结构主义的重要代表之一的罗兰·巴特的后结构主义转向开启了法国的后现代主义运动,克里斯蒂娃正是这一转向的重要促成者。她被认为是促成罗兰·巴特告别体系化人文科学的诸种因素中,对他影响最早、也最重要的人。巴特本人也多次提及克里斯蒂娃对自己的影响。他曾将自己的写作划分为四阶段,认为克里斯蒂娃等人的文本在被他称为“文本性”的第三阶段对自己的写作造成了重要影响。1973年,在克里斯蒂娃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巴特以一种谦卑的语气说道:“好几次,你帮助我发展了自己的观点,尤其是我从产品的符号学发展到生产的符号学之际”(Calvet 196)。
克里斯蒂娃对巴特的影响首先体现为其对巴赫金对话主义以及复调理论的引介。克里斯蒂娃对巴赫金的引介始自1966年初在罗兰·巴特的研讨班上的“巴赫金与小说词语”的报告,由于这次报告,“克里斯托娃在巴特的研究班成了不可或缺的耀眼的存在。带来过去欧洲人一无所知的俄罗斯形式主义的文学理论和米哈伊尔·巴赫金理论、并且将一股新鲜空气吹进巴特研究班的正是克里斯托娃”(西川直子 18)。考虑到克里斯蒂娃“对巴赫金的阐释以及对他思想的发展”是“建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和《拉伯雷的创作》)这两部著作的基础之上”(“互文性理论对结构主义”2),而这两部著作分别直到1970年和1973年才在法国出版,因此真正对巴特造成影响的正是克里斯蒂娃理解与介绍的巴赫金理论。克里斯蒂娃对巴赫金诗学所作的介绍使巴特看到了将文学写作当作一种写作之间以及写作内部的对话来进行分析的可能性。在采用了克里斯蒂娃介绍的巴赫金诗学观点后,巴特“使自己的著作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多斯 75)。如《S/Z》一书的写作更被认为是“科里斯蒂娃1966年的介绍激发了他的灵感”(多斯 79)的典型。
克里斯蒂娃对巴特的直接影响主要是“互文性”概念的提出。对此,克氏本人见证道:“罗兰·巴特说他从我这里得到互文性的启发”(“互文性理论对结构主义”10)。据考证,在巴特于1968年前后发表的著名的《作者的死亡》一文中,虽然没有出现“互文性”或“互文”的字样,但其中表达的理论意图和文学观与克里斯蒂娃几乎完全相同,可以视为对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概念和刚刚被介绍到法国的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呼应。大约从1970年起,巴特开始在自己的多篇文章或著作中借用克里斯蒂娃发明的“互文性”一词。其中,于1970年出版的《S/Z》一书充分反映了巴特“对文本间性的兴趣”(多斯 79)。事实上,作为“巴特使用互文性进行文本解释”的“主要”作品(“互文性理论对结构主义”10),《S/Z》是巴特针对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萨拉辛》的研讨课的成果。在巴特的传记作家让·卡尔韦看来,“这门研讨课极大地受到克里斯蒂娃的影响,巴特从她那里拿来了‘互文性’的概念”(Calvet 182)。
以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概念为起点,巴特开始了对文本的探索。确切地说,正是在发展与完善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互文性理论的过程中,巴特形成并发展了自己的文本观。正因为如此,克里斯蒂娃在提及互文性理论的发展史时甚至指出,“我的互文性概念可追溯至巴赫金的对话主义与巴特的文本理论”(Kristeva,“‘Nous Deux’”8)。事实上,克里斯蒂娃本人正是巴特“文本”理论的直接启发者。巴特的另一位传记作者菲利普·罗歇认为,“巴尔特使用文本的概念与其说与“五月思想”的自由流布有关,[……]或许更同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如是》杂志和《符号分析论》里一直进行的工作有关”(罗歇 37)。不仅如此,他甚至将克里斯蒂娃视为巴特的“文本”概念的界定者:“文本在各种‘大词儿’里的地位十分特殊。[……]巴尔特是让别人,特别是任由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去界定”(罗歇 99)。巴特本人也认同这一观点:“文(Text)的定义主要是由朱丽叶·克莉斯特娃基于认识论的目的而构设的[……]在这一(百科全书)条目的界定里,不言明地描述出来的主要理论观念:意指实践、生产力、意指过程、已然存在之文、生成之文、文际关系特性,都得归功于朱丽叶·克莉斯特娃”(《文之悦》90)。日本著名的克里斯蒂娃研究者西川直子则认为:“巴特文本论的发展如果没有来自东欧的这个女留学生的出现是不可能的,这恐怕不是言过其实吧”(西川直子 18)。
巴特在互文性理论阐释中形成的动态的文本观,为其实现由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转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其有名的《从作品到文本》一文中,巴特写道:
作品能够在书店,卡片目录和课程栏目表中了解到,而文本则通过对某些规则的赞同或反对来展现或明确表达出来。[……]换句话说,文本只是活动和创造中所体验到的。举例来说,文本不能止于图书馆的书架顶端;文本的基本活动是跨越性的,它能横贯一部或几部作品。[……]作品自身作为一般符号发挥作用并代表了符号文化的一般类型。文本,则相反,常常是所指的无限延迟(deferral):文本是一种延宕(dilatory)。(“从作品到文本”87)
概言之,在巴特看来,作品是静止的、孤立的、确定的、有限的,以及封闭的存在;文本则与之相反,是运动的、关联的、不确定的、无限的,以及开放性的一种延迟。巴特在文中有关“作品”与“文本”两个不同概念的论述在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作品到文本》也因此被视为巴特建构其文本观的重要文献之一,并引发了伊格尔顿“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运动,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从‘作品’到‘文本’的运动”(Literary Theory 138)的感慨。尽管从巴特的文本观中,我们不难发现德里达的痕迹,但作为其理论发生的逻辑起点并贯穿其中的却是互文性理论所倡导的开放与动态的文本观。
尽管巴特经历了由作品到文本的观念的转变,但这种转变并非对结构主义的绝对抛弃,而仅是对后结构主义的偏重。这是因为,在巴特众多所谓的后结构主义作品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观念和谐并存这一事实。如在被拉曼·塞尔登称作“最能代表巴特的后结构主义时期的短文”《作者之死》中,尽管巴特在文中“否定了作者是文本的起源、意义的来源和唯一的阐释权威的传统观点”,提出了“作者可以自由地从任何方向进入文本,不存在正确的路径”的观点,但事实上,“作者已死的观念已经内在于结构主义之中”,因此,塞尔登认为巴特观念的新颖之处仅仅在于“读者可以自由地开启或关闭文本的指义过程而无须考虑所指”(Selden 75)这一论断。乔纳森·卡勒在提及《S/Z》,这本在巴特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转变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书时表示:
巴特和其他人都认为,他从《S/Z》开始放弃了结构主义的理论设想。[……]在结构主义的科学雄心和被称之为“解构主义”的后结构主义分支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但这一差异很容易被人夸大。[……]在《S/Z》中,巴特的研究经历了剧变,从结构主义转向后结构主义,这是巴特本人试图传递的印象,但《S/Z》所关注的问题在他各个时期的作品中持续存在。(卡勒76—77)
卡勒的这一论断事实上早已被巴特本人证实,在一次访谈中,他将自己由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转向称为“一个转移的问题,而不是抛弃”(“与雷蒙·布洛尔会谈”25)。
四、克里斯蒂娃与德里达的解构理念之形成
作为解构主义的创始人,德里达注定与后现代主义有着不解之缘。他甚至被弗兰克·伦特里奇亚(Frank Lentricchia)认为是后结构主义的开启者。在其专著《新批评之后》中,伦特里奇亚写道:
大约在70年代的某个时候,当我们从现象学教条式沉睡状态中觉醒时,不禁发现,一种崭新的存在已绝对地控制了我们的先锋派批评的想象力:雅克·德里达。我们十分惊异地获悉,尽管有不少与之相反的特征,但他带进来的却不是结构主义,而是所谓“后结构主义”的东西。随即便在保尔·德曼、J.希利斯·米勒、吉奥弗雷·哈特曼、爱德华·赛义德以及约瑟夫·里德尔的知识生涯中,出现了向后结构主义方向的转变。所有这几位批评家都曾在60年代为现象学的潮流所倾倒,他们的这些转变本身就阐明了进入后结构主义时代的全部过程。(Lentricchia 159)
具体而言,德里达对后结构主义的开启主要体现在其解构主义理论的提出。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在文学界引起了重大的反响,不仅形成了以美国耶鲁学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文学批评流派,“解构”也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观点。
在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体系的形成中,德里达与克里斯蒂娃夫妇等《原样》派成员的交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德里达的《立场》一书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号学和文字学》一文的写作是在与克里斯蒂娃的通信中完成的(皮特斯158),但较之索莱尔斯,克里斯蒂娃对德里达的影响更为隐晦。索莱尔斯为克里斯蒂娃提供了结交德里达的便利与机会,但德里达与索莱尔斯之间的第一次摩擦也正是与克里斯蒂娃有关的论文“泄密”事件——克里斯蒂娃的文章《意义与时尚》拟在《批评》杂志上发表,作为杂志编委的德里达提前将文章透露给弗朗索瓦·华尔(François Wahl)看。从1967年9月28日索莱尔斯写给德里达的信中,我们大致可以窥探到这次事件的些许端倪:
在克里斯蒂娃这里,问题要比您想象的更为严重。关于这一突然而具决定性的思想的出现,已经有过许多的波折,许多的争论,许多小小的事件。我看见华尔对我说在《批评》上发表的关于巴赫金的文章是“胡言乱语”;我看见米勒和巴迪乌激烈谴责《原样》上的文章而引发的这样那样的争论。(皮特斯154)
尽管索莱尔斯在信中并未言明“这一突然而具决定性的思想”的具体所指,但从“关于巴赫金的文章”这一线索来看,克里斯蒂娃所提出的引发许多争论和事件的思想应该是和巴赫金诗学有着密切联系的互文性理论。由作为《批评》杂志的审稿人之一的弗朗索瓦·华尔对克里斯蒂娃的“关于巴赫金的文章”的批判来看,他显然并非这篇论文的推荐者。结合德里达与索莱尔斯的私交,以及他作为《批评》杂志编委会成员的身份,我们尽管无法确认是德里达促成了克里斯蒂娃的“关于巴赫金的文章”在《批评》上的发表,但能肯定他作为这篇文章的读者的身份,由此也可以推测这种阅读经历对他的潜在影响。克里斯蒂娃的论文《巴赫金:词语、对话与小说》是1967年4月在《批评》杂志上发表的。考虑到论文发表的时间差,德里达应该在论文正式发表的4月份之前已读到了这篇文章,此时的德里达正忙于他的三部解构主义巨著——《论文字学》的写作,以及《书写与差异》和《声音与现象》的最后的修改校对工作。巧合的是,德里达在3月底有了将原计划在夏天之前面世的《论文字学》和《书写与差异》同时延至9月份出版的想法。尽管无法确认德里达是否因受克里斯蒂娃论文的启发而对这几部著作进行了修改,最终的事实是,除了《书写与差异》于春季出版外,另外两部解构主义巨著《声音与现象》和《论文字学》均于1967年秋才出版(赵雪梅)。
具体而言,克里斯蒂娃对德里达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异延”(différance)和“播撒”等解构主义概念中。从时间上看,我们甚至可以将“播撒”和“异延”视为对克里斯蒂娃互文性理论的呼应。这是因为,就理论内涵来看,互文性的思想核心是文本的无限援引与衍生导致的意义的不确定性与终极判断的不可能性。意义和真理永远处在“播撒”与“异延”之中:一方面,在横向空间维度,此处的文本与彼处的文本相互交错;另一方面,在纵向时间维度,此时的文本与彼时的文本互相关联。阐释活动陷入了一条无限延伸的长链之中,永无穷尽的可能,意义则永远处于一种延宕的状态,消解在迷宫一般的关系网络之中(赵雪梅)。
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对德里达的影响更直观地体现于德里达的文学观及其文本观中。换言之,德里达对文学与文本的解构正是以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为基础的。1969年2月26日和3月5日,德里达在巴黎理论研讨班上做了无标题演讲,后来在《原样》上以《双重场次》(《双重部分》)为题发表。德里达在文中指出:
写作是阅读、文本[……]概念的绝对延伸。[……]有无穷个小册子包涵、融入到另外一些小册子里,这些小册子只能通过嫁接、取样、摘录、题词、参考等方式生产出来。文学在它的无限性中使自己失效。如果这本文学手册打算讲些什么东西的话[……]它首先应该宣布没有——或几乎没有——文学;应该宣布,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存在文学的本质,不存在文学的真实,无所谓文学的存在或存在的文学。(Derrida,Acts of Literature 177)
由写作和文本的“绝对延伸”,“这些小册子只能通过嫁接、取样、摘录、题词、参考等方式生产出来”等语句,我们不难联想到克里斯蒂娃首次对互文性概念的界定:“任何文本都被建构为引文的镶嵌组合;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互文性的概念取代了主体间性的概念”(Desire 66)。在此,由文本关系的无限性延伸,德里达解构了文学本身——只有文本的无限推衍与关联,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内核并不存在,文学的本质也并不存在。这种类似的文本观还出现在德里达1972年秋出版的《立场》一书中:“这种联系、这种交织,就是文本,它只有通过对其他文本的转换才产生出来的”(Positions 26)。
文本的这种相互交织与转换,被德里达解读为文本的重复与循环。1989年4月,在一篇名为《访谈:称作文学的奇怪建制》的访谈中,德里达明确将“重复性”作为文本结构的主要特点。所谓文本的重复性,即文本“没有单纯的起源,也没有纯粹的独创性,它们即刻地分解并重复自己,它们既能够在其根源处被清除,也能够被移植到不同的语境之中,继续具有意义和效力”(Acts of Literature 64)。这一关于“重复性”的阐述,依然是互文性理论的唱和——根本不存在文学的“独创性”,也没有“第一部”的文学作品:所有的文学都是“互文本的”。正如伊格尔顿所言,一部特定的作品并没有清晰的限定边界:它不断扩散到周围作品之中,产生很多不同的远景,随后逐渐消失(Literary Theory 138)。
文本的这种相互交织与转换,也被德里达解读并上升为文本的主——客体间的意向性关联结构,即文学性本身:“文学性不是一种自然本质,不是文本的固有特性。它是对于文本的一种意向关系的相关物[……]可以说,这种文本的文学特性在于意向主体对意向客体的认知结构中,而不仅在纯理性行为的意向主体本身”(Acts of Literature 44)。可见,德里达的文学性表现为一种文本的意向性关系,它既指向主体对意向客体(文本)的认知结构,也依赖意向主体(读者)的理性行为,是一种基于读者——文本双向互动的动态性文学观。
不可否认,克里斯蒂娃之所以能对包括巴特和德里达在内的当时最前卫、最解构的少壮思想家产生重要的影响,与她独特的《原样》派成员身份不无关系。作为《原样》派——这一当时最活跃和最具煽动性的文艺团体的一位核心成员,克里斯蒂娃抢占了把握社会脉搏,引领时代潮流的先机。作为“领导法国新学术动向的研究者之一。[……]引人注目的学者”(西川直子 19),克里斯蒂娃,这位来自东欧的移民女性,凭借其敏锐的学术眼光与宏大的学术野心在后现代文论的发展史上写下了自己厚重的一笔!
注释[Notes]
①就我国学界而言,克氏的研究者更多的集中于其在符号学、女性主义以及精神分析领域的成就,并根据自身的学科背景对其进行各取所需的分散式研究。如对克氏的符号学的研究,其研究者的学科背景主要是高校的语言学专业,对其女性主义或精神分析的研究则主要是从事女性主义或精神分析理论的研究者。
②此处的后现代主义文论,并非专指以利奥塔德和哈桑为代表的狭义的后现代文论,而是一种广义的后现代,指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的包括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在内的各种文学与文化理论类别。
③当然,对后现代的产生起着推进作用的因素比较繁复,就人物而言,如索绪尔、弗洛伊德和德里达等人均被认为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哈贝马斯在他那本影响卓著的《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把尼采作为转折性的标志,认为现代思想史从尼采这里步入后现代。陈晓明则将德里达推到了后现代主义开拓者的位置上。参见陈晓明:“重论德里达的后现代意义及其转向”,《学术月刊》12(2007):14——27。就笔者掌握的材料看,克里斯蒂娃在后现代文论的推进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至今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这也正是本文写作的出发点。
④克里斯蒂娃在接受弗朗索瓦·多斯的访谈时指出:“巴特的方法十分有趣,因为他认为,任何文本,无论是拉伯雷的,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内部都是复调性的”(多斯75)。
⑤1995年2月底3月初,克里斯蒂娃在巴黎接受《对话·狂欢·时空体》杂志的卡米尔?艾里——穆阿里的采访时指出,“在我看来,存在着两种巴赫金的遗产:从一方面去看,这是文化学的与符号学的遗产,[……]——西方的符号学家们恰恰是关注这一份遗产。从另一方面来看,则有另一种,比较狭窄的意义上的文学的遗产,围绕着对话主义这一概念与这一概念之我的变体——互文性一而得以建构起来的那份遗产。它恰恰已成为一匹简直具有普适性而无所不在的“战马”:不论是在法国,还是在美国,没有一所大学里,在各种文学批评领域里不久前发表的那些著作与文章之中,没有一篇对互文性这一概念不曾加以采用。”参见克里斯蒂娃:“朱莉亚·克里斯蒂娃谈米哈伊尔·巴赫金”,周启超译。《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1(2013):214——24。
⑥克里斯蒂娃本人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了巴赫金诗学与弗洛伊德思想对于自己的研究的阶段性影响。她指出,早期的互文性研究主要受巴赫金诗学的影响,而到了互文性研究后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的地位甚至逐渐取代了巴赫金。参见克里斯蒂娃:“互文性理论对结构主义的继承与突破”,黄蓓译。《当代修辞学》5(2013):1——11。
⑦索莱尔斯对德里达的影响具体见赵雪梅 张振谦:“德里达的文学化哲学书写”,《北方论丛》3(2016):49——55一文,此处不再赘述。
⑧李翔海指出:“相比较而言,‘延异’在形式上依然是把时间放在首位的,而对于‘异延’则可以作出更为注重空间而不是时间的诠释。而正如福柯所明确指出的,对于现代主义中重视时间而轻视空间的价值取向的翻转,正是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特质之一。”见李翔海:《民族性与时代性:现代新儒学与后现代主义比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1页。
⑨从时间来看,互文性理论在1967年4月已正式提出并得到了不断的阐释与发展,尽管在《论文字学》一书中已涉及“异延”的概念,但《异延》一文的正式成型最初是德里达于1968年1月27日受法国哲学会邀请在索邦大学所做的一次讲演。论文《播撒》则写于1968年夏,后分两期在《批评》上发表。参见赵雪梅:“德里达与原样派渊源颇深”,《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2月29日。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Allen, Graham.Intertextualit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
巴赫金:《诗学与访谈》,白春仁 顾亚铃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Bakhtin.Poeticsand Interview.Trans.BaiChunren and Gu Yaling, et al..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1998.]
——:《拉伯雷研究》,李兆林 夏忠宪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Rabelais Research.Trans.Li Zhaolin and Xia Zhongxian, et al..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1998.]
罗兰·巴特:“从作品到文本”,杨扬译,蒋瑞华校。《文艺理论研究》9(1988):86——89。
[Barthes, Roland.“From the works to the text.” Trans.Yang Yang.Check.Jiang Ruihua.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9(1988):86——89.]
——:“与雷蒙·布洛尔会谈”,《本文的策略》,孟悦等编著。广州:花城出版社,1988年。
[---.“Talks with Raymond Blower.” Textual Strategy.Eds.Meng Yue et al..Guangzhou:Huacheng Publishing House, 1988.]
——:《文之悦》,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The Pleasure of the Text.Trans.Tu Youxiang.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Bertens, Hans and Douwe Fokkema, eds.International Postmodernism:Theory and Practice.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Company, 1997.
Calvet, Louis-Jean.Roland Barthes: A Biography.Trans.Sarah Wykes.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
乔纳森·卡勒:《罗兰·巴特》,陆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年。
[ Culler, Jonathan.Roland Barthes.Trans.Lu Yun.NanJing: YiLin Press, 2014.]
Derrida,Jacques.Acts of Literature.Ed.Derek Attridge.New York: Routledge,1992.
---.Positions.Trans Alan Bass.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81.
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下卷),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
[Doss, Francois.From the Structure to Deconstruction: Main Current Thought in the 20th Century in France.Vol.2.Trans.Ji Guangmao.Beijing:Central Compilation&Translation Press, 2004.]
Eagleton,Terry.“IContain Multitudes.” The London Review of Books12(2007):13- 15.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Oxford: Basil Blackwell,1983.
Hassan, Ihab.The Postmodern Turn: Essays in Postmodern Theory and Culture.Columbus: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
克里斯蒂娃:“互文性理论与文本运用”,黄蓓译。《当代修辞学》5(2014):1——11。
[Kristeva, Julia.“Intertextuality Theory and Text Using.”Trans.Huang Bei.Contemporary Rhetoric 5(2014):1——11.]
——:“互文性理论对结构主义的继承与突破”,黄蓓译。《当代修辞学》5(2013):1——11。
[---.“The Inheritance and Breakthrough of Intertextuality Theory to Structuralism.”Trans.Huang Bei.Contemporary Rhetoric 5(2013):1——11.]
Kristeva, Julia.Desire in Language: 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Ed.Leon S.Roudiez.Trans.Thomas Gora, Alice Jardine, and Leon S.Roudiez.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
---.“‘Nous Deux’ or a(Hi)story of Intertextuality.”Romanic Review93.1——2(2002):7- 13.
Lentricchia, Frank.After the New Criticism.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西川直子:《克里斯托娃——多元逻辑》,王青、陈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Nishikawa, Naoko.Kristeva: Multiple Logic.Trans.Wang Qing and Chen Hu.Shijiazhuang:Hebei Education Press, 2002.]
欧阳康:“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与全球化——访美国后现代思想家小约翰·科布”,《世界哲学》3(2002):69——75。
[Ouyang, Kan. “Constructive Postmodernism and Globalization:Interviewing the America Postmodern
Thinker John Cobb Jr..” World Philosophy 3(2002):69——75.]
伯努瓦·皮特斯:《德里达传》,魏柯玲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Peeters, Benoît.Derrida.Trans.Wei Keling.Beijing: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4.]
菲利普·罗歇:《罗兰·巴尔特传:一个传奇》,张祖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Roger, Philippe.Roland Barthes, Roman.Trans.Zhang Zujian.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13.]
Selden,Raman.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Lexington: The Kentucky University Press,1985.
王宁:“巴赫金之于‘文化研究’的意义”,《俄罗斯文艺》2(2002):23——26。
[Wang, Ning.“Bakhtin's Meaning to Cultural Studies.”Russian Literature and Art2(2002):23——26.]
祝克懿:“多声部的人——与克里斯蒂娃的对话录”,黄蓓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7月26日。
[Zhu, Keyi.“The Multi-Voice Person: A dialogue with Kristeva.”Trans.Huang Bei.Chinese Social Sciences Today 26 Jul.2013.]
赵雪梅:“德里达与原样派渊源颇深”,《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2月29日。
[Zhao, Xuemei.“Derrida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el Quel.”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Today 29 Dec.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