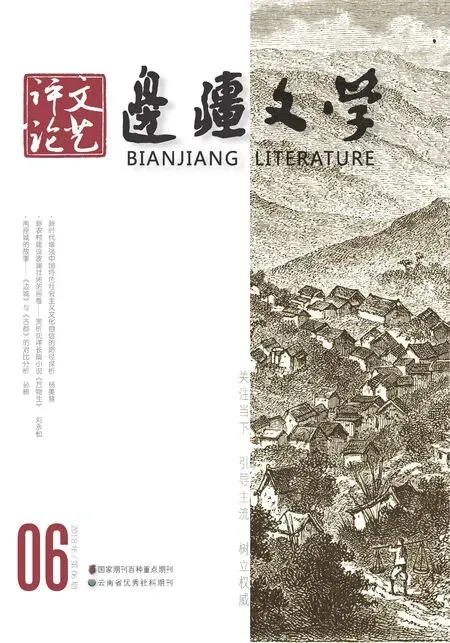细读和深思
李秀儿
一、人是如何不成其为人的?——我看《好人宋没用》
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里,借狂人之口,说,华夏五千年的文明史,就写着两个字:“吃人”。借用这个表述,几十万言字的任晓雯长篇小说《好人宋没用》,我也可以说就读到一句话:人,是如何不成其为人的?
《好人宋没用》里,男人不是人。宋榔头不是人,宋大福不是人,就连佘先生那样有钱有身份有地位的男人,最后也不是人。活着没个人样儿,死了也猪狗不如。死在垃圾堆上的宋榔头,“土布短裤破了洞,被泥浆、污水,和死后溢出的小便精液弄脏了,”与黑压压的苍蝇为伍,其情其景,惨不忍睹。宋大福也重蹈覆辙,活着与死相,一样难看。而佘先生,最后活成了个活死人。
《好人宋没用》里,女人也不是人。宋没用的母亲不是人,宋没用的婆婆杨赵氏不是人,那个反客为主的巧娘子就更不是人。就连斯文高贵的佘太太,最后也活得不像人。宋没用家一屋子儿媳,也没个人样,最小的女儿宋白兰,后来远赴云南,变身为革命的宋爱华,最后客死他乡,也没活成个人。
低贱如苏州河畔药水弄棚户区的难民、流民不是人,中间状态如杨家“老虎灶”串起的市井社会,小市民、平民同样不是人,后来佘家“洋楼”串起的“洋楼帮”,这些就算层次高一点的大市民吧,他们后来即便生活在了新时代的上海都市里,同样还是不是人。
在小说中,善良在邪恶的面前,所有的善念善行被压成齑粉。比如宋没用收留了巧娘子一家,最后落得的是丈夫杨仁道被莫名其妙地告了黑状而失踪,宋没用一家被鸠占鹊巢,最后被挤出家门……
在小说中,美好在丑陋的面前,所有的美好化为乌有。比如教会医院,医生护士辛辛苦苦救了宋榔头,却被丑化成专门卸胳膊卸腿的杀人医院;信奉基督教心存善念的佘太太,救了宋没用一家,最后也是惹火烧身,不得善终。
《好人宋没用》写了上上下下三教九流众多人物,但是就是不见真正意义上的人,大写的人。到处是鸡毛蒜皮,苍蝇走狗,到处是偷奸耍滑,欺行霸市,相互算计,斤斤计较,尔虞我诈,告密盯梢……就是没有人的堂堂正正,没有人的光明磊落,没有人的良善德行,没有人的美好希望。看得见的,都是人性向无尽深渊坠落的各种表现,是“没有最坏、只有更坏”的暗黑现实,是作家对人性的失望,绝望,继而使读者对存在世界产生怀疑和否定。
这就是作家笔下发现的“这一个”世界——真实的肮脏丑陋的世界。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不同层次的人物,命运和结局,莫不如此。在将近七十年的时间跨度里,作家笔下的人物,从始至终,都在以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毁灭性破坏性方式,去获得卑微可怜的生存权。这样的艺术处理方式,多少是有些令我出乎意料的。因为,过去,写旧时代的小人物,通常作家会着眼于他们在苦难中不甘沉沦的抗争,人性在黑暗中会发出或炫目或微弱的亮光,故事结局,真善美总是压倒假恶丑,至少也是打个平手。比较典型的例子,比如老舍先生的名著《茶馆》,从清朝写到民国,也写了大量的坏人当道,好人受压。但是,他依然着眼于写小人物的抗争,不屈服,用黑暗衬托光明,在绝望中看见希望。而《好人宋没用》,却完全拧过来了,假恶丑绝对压倒了真善美,真善美即便存在,也很脆弱——比如那个巧娘子和她的婆婆,在宋没用难产时,也伸出了援手,也释放出一点善意,但是,它是那么微弱短暂,如电光火石,稍纵即逝——当她们发现可以用大军进城来吓走宋没用一家时,她们是那么毫不犹豫果断出手,人的恶行瞬间就占了上风。小说里,更多时候,更多场景,我们看到的是人性的善良被强大的恶所吞噬,假恶丑无时无处不在恣意畅行,即便在母女之间,夫妻之间,亲兄弟之间,也是如此。小说《好人宋没用》就是一个隐喻:好人,没用。在恶行遍地的这个世界,好人真的没用。“74岁的宋没用,回到了最初之地。”小说以凄惶之笔结尾,完成了作家对笔下这个世界,不抱任何希望的否定。“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全部秘史,往往深藏在个人史和人心史之中。”(别林斯基)《好人宋没用》以冷峻笔法,貌似“零度感情”,所写的家族史、个人史以及人心史,让人不寒而颤,并进而深思——
作家为什么要这样写?
我觉得,作家是有意让读者看清所谓国民性中根深蒂固的劣根性:弱者,往往是恶的制度的帮凶。《好人宋没用》展示了弱者世界的污浊肮脏——他们只为欲望而活,毫无节操,毫无底线,这样的活法,是怎样的不堪。在小说里,看不到作家对弱者丝毫的同情,更没有对弱者的歌颂,作品所展示的弱者的生存环境、生存秩序和生存哲学,只是让人恶心,厌恶。作品似乎在警示人们:人的一生,就是要尽可能地远离弱者世界。这其实也符合“人往高处走”的生命规律,我们所有的教育,包括家庭、学校、社会,不都是让孩子、学生,远离低贱,走向高处吗?过去我们的文学价值观,为什么会反其道而行之?
更深一层意思,我觉得是作家借助作品中的人物,在警醒人们,必须抵制多数人中普遍存在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所代表的反智、平均等价值诉求,往往与统治者的专制利益达成高度统一。民粹主义在历史和现实中的表现形态,过去是义和团,今天是砸日系车,驱逐韩国乐天,或者简单反美,借此标榜自己的爱国。在《好人宋没用》里,持有这样价值观的人物可以说比比皆是。是作家的无心插柳还是有意为之,我不得而知,但是,这样的文学事实却是真实充分地呈现出来了。我个人认为,这也是这部小说最为难能可贵之处。
话虽如此说,但是我们仍然应该看到,作品展示了假恶丑的强大,作家任晓雯却是坚定站在柔弱的真善美一边的。这让人想起村上春树那个著名的比方:即便是以卵击石,作家也会毫不犹豫地站在卵的一边。也让人想起卡夫卡曾经在日记里写过的一段话:凡是活着的时候不能应付生活的人,就需要用一只手稍稍阻挡住他对自己命运的绝望……同时他要用另一只手,记下他在废墟中看到的东西,因为他能看到与别人看到的不一样的东西和更多东西;归根究底,他在一生都是个死者,但却是真正的幸存者。
当然,所有这些,任晓雯都是借助作品中人物的人性和兽性的此消彼长,相互撕裂,来具体呈现的。最后,我引用几段革命导师语录,来对我的批评作结:
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与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卡尔·马克思(1956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414 页 )。
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而这个原则比其他很多原则好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单是一个原则,而且还有事实。专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下贱。——卡尔·马克思(1956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411页)
二、为了心中那片海——我看《少年海》
不经意间,打开了一片蔚蓝的海,我被大海汹涌的潮汐、洁白的浪花、翻飞的鸥鸟以及神出鬼没的各种大小动物所吸引,更被以大海和防护林为背景的两代少年艰难曲折的成长故事深深打动。缪克构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少年海》,用如诗如画的语言,构建了一个精彩绝伦的童话世界。阅读这部作品我仿佛回到了自己记忆深处的故乡,小玲子、立权、洪财……那不都是我儿时的伙伴吗?作品中的叙述者“我”,与儿时记忆中的我,又有几分重叠相像呢?
作者谙熟海边的生活了,海边的防护林,海边养鸭,晒海盐,岸边的螃蟹,还有那些貌似恐怖阴险的蝙蝠……这些海边的童年生活经验在作者的笔下,是那么迷人、有趣!
书中“我爸爸”洪林,是我最喜欢也最崇拜的人物了。对他的喜欢,我是从心痛开始的:当他的胳膊在对赌中被腰斩时,我的一颗心提到嗓子眼儿上了——这个过继而来的少年,在没有血亲的家庭关系中,在封闭乡村的宗法势力强大挤压下,他会顺利长大吗?在他注定坎坷的成长道路上,还会遇到哪些痛苦和麻烦?我对他的佩服,是从他插秧开始的:他以手代脚,在田泥中跳跃挣扎的场景,深深印在我脑海里——这是一个怎样不屈的少年啊!我对他的崇敬,是从他养虾开始的,他经历过成功和失败的多重考验,始终没有向灾难低头,始终敢于向命运说“不”!我对他最深的感动,是他为伯伯送终——与其说这是他以善行终结了仇恨,完成了和解;不如说是他以宽容博大战胜了渺小的自我,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觉醒和飞跃。“我爸爸”洪林,就像一面镜子,照见了“少年海”最迷人的风景;更像一部启示录,为所有少年的健康成长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立权,是一个多么复杂的人物!尽管驼背、家贫,他却是一个迎风而歌的俊朗少年。他聪敏,早熟,有着属于自己的生存智慧。洪财,一个让人讨厌、犹如苍蝇一样让人避之不及的“坏孩子”,在成长的记忆中,他却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当我们为立权的苦难和不幸而同情悲悯时,却遗憾地发现:他变了,变坏了?咦!他怎么又在由坏向好的转变中,跌进黑暗的河底,死了呢?作品中每一个人物,好像都背负着一块神奇的调色板,或阴或晴,或明或暗,人物的善恶美丑,在发生着自然而奇妙的转变。正是这些转变,可以照见我们每个人成长道路上,那些刻骨铭心的美好或丑陋,那些难以释怀的惆怅和遐想……
《少年海》中的人物和故事,让我想起另一部写苦难和成长的经典之作:曹文轩的《草房子》。油麻地上的那所乡村小学,秦大奶奶、杜小康,桑乔、桑桑、细马、秃鹤等人物,曾经是赚取过我无数眼泪的文学形象。曹文轩善于将笔下人物渲染到极致,牵动着读者的每一根神经,让你扼腕,揪心,叹息,难受,流泪,失魂;而《少年海》作家缪克构的聪明劲儿,是特别懂得少年读者的审美需求,知道叙事的快慢节奏,特别善于运用停顿。一段血亲家族与过继家庭之间惊心动魄的重重矛盾,固然是推动整个故事发展的内核,但是,作者并不需要时时在这里着力,而是经常笔锋一转,随之呈现的是画风一转:那些明丽的亮色,随着小动物的登场,一一出现了:鸭子、小鸟、小狗、小蜜蜂、老鼠、蝙蝠、海龟、螃蟹、虾、蛇……这几乎就是一个乡村和海洋交织的动物博物馆。一切景语皆情语,这些停顿,有着国画当中“计白当黑”的特殊效果。当作家俯下身子,用诗意的文字去打量这些小动物时,少年读者的好奇心,也会在这里得到极大的满足,他们在此看到了一个与自己成长经验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作家对各种小动物的观察、对童年游戏(像骑猴打仗)的描绘,既充满童真童趣,又特别讨巧地体现出自己的匠心和特色。
《少年海》里的“人设”,也很有特点。不知道是作者有意为之还是无心插柳,小说当中的好几个人物,都是“弱者”:被爷爷丢弃的没有脚的第一个奶奶、驼背的少年立权、独臂父亲洪林、没有户口的“黑人”小玲子……作者花费大量笔墨,倾注于对这些弱者命运的描写,固然与作品“苦难叙事”的视觉以及作家悲悯之心的价值取向有关,更与作家试图借助人物,引导少年读者从小学会同情弱者、平等待人的努力有关。如果孩子很早就学会这些,比取得优异学习成绩更为重要——因为,它关乎着实现一个全面的人。
《少年海》是一部优点和特色突出的小说,是一部让我温暖、感动和受益的作品。如果说还有些小小的不满,那就是作品在充分性、自然性方面,还留有某些瑕疵。在我看来,只有充分的真实描写,才可能实现人物转变的自然而然、水到渠成。这些问题的存在,也许与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的篇幅体量局限有关,也许与作家追求作品画风的简单透明有关。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少年海”。为了心中那片海,每个人,都会为之而不懈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少年海》是一部励志小说。她砥砺我们,不被苦难所吓倒,不会命运而屈服。她以生动的文学形象,让我们记取成长路上那些深刻的经验和教训,以及曾经有过的美好风景。《少年海》,让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三、因为爱,所以爱——我和儿童文学
获得2017年度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我的小说《晚秋》,排在佳作奖第一。这个小说,是写我小时候关于东北黑土地的一些记忆,是收秋之后,短暂的农闲时节,几个农家少女,关于青春,关于美,关于爱的萌动,以及由此而生发出的彼此之间羡慕嫉妒恨的故事。我在小说里写有一段话:“刚才还以为是来看一幅赏心悦目的风景……现在看到的,却是风景背后让人辛酸的真相。”这个“风景背后让人辛酸的真相”,是我少年时候的往事,真事。如今,不仅城里的孩子不容易看到,那些到农家乐、到观光农场去采草莓、摘樱桃、体验乡村生活的城市成年人,以及生活在今天的乡村的孩子们,也是不容易看到的。但是当年,它就那么实实在在地发生在我的周围,我的身上。我的小学、初中、高中的同学,可以说每个阶段的同学,都有因为家庭贫困而辍学者,有的是家里弟妹太多负担太重,有的是家庭遇到一点天灾人祸,还有的是家里有人因病返贫……就像老托尔斯泰说的,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有各自的不幸。文学创作所要承担的任务,一定是写出生活的不同,写出属于自己发现的“这一个”,儿童文学也不能例外。那么,我在《晚秋》里,写出了我所发现的不同了吗?
丫蛋、二妞和秀儿——第三个人物,我直接用了我的本名。前两个人物也都有原型,她们至今还生活在靠近俄罗斯边境那个小县的乡村里。她们的娃已经超过了当年我们一起读初中的年龄,但是,那些娃,他们的生活已经明显改变了。就像稻草垛已经从地平线消失了一样,如今的乡村少年,已经不大为生活的琐屑太发愁了。前年,我带着自己还很年幼的孩子,去了一趟东北老家。小说中的原型丫蛋和二妞们告诉我,收秋早已经与她们无关了,土地流转后,基本都是机械化作业,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基本不存在了。稻草垛没人再去码,要不是烧秸秆稻草会污染空气而受到严格干涉,每到秋天,空旷的田野就会狼烟四起,遮天蔽日呢!而他们的孩子,吃冰棍时也早学会了挑挑拣拣,早就不吃那些廉价的绿豆冰棍了呢!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怎能忘记,自己有过的那些经历——偷偷束胸、偷偷擦蛤蜊油、偷偷描眉画眼、偷偷幽会或偷看别人幽会的那些过往呢?那些带着辛酸泪血的童年和少年生活,如今我们围着火锅,在哈哈大笑中回忆起来,是那么清晰可见,历历在目。我们笑着,说着,又在笑声中笑出了眼泪,直到最后,变成大家在一起抱头痛哭……这时,不要说我那少不更事的孩子感到莫名其妙,就是她们已经读到初中高中的孩子,在一边看了,也完全不解风情:她们的妈妈们,怎么了?
正是这趟东北之旅,回来后,我在忐忑不安中,写下了《晚秋》。如今,小说得到了大奖评委们的赏识,给了我从事儿童文学写作以来第一个重要的奖项,我很感激,也受到激励。我在得到评委会通知,要我写几句“获奖感言”的时候,我这样写道:“热爱儿童文学是因为我热爱儿童,热爱儿童是因为热爱我的儿子。我是当了高龄妈妈以后,才开始接触儿童文学创作的,我的儿子就是我进入这个领域的带路人。他的成长过程,闪电般触动了我儿时的记忆,让我学会了写小说就贴着人物性格去写,写散文就贴着自己情感去写。《晚秋》正是这样的产物。”
在我从事儿童文学写作以来,我很幸运,因为我得到这个领域里很多大家、前辈、老师和朋友的指点、提携和帮助。比如吴然老师,他是中国课本名家,他的很多作品,入选了各种教科书,是国内选入教材最多的儿童文学作家之一。他在《文艺报》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认识李秀儿,纯属偶然。2010年春,我在《文艺报》上,读到诗人晓雪写的一篇评论文章,文章里转述了被评论对象的一段文字,写怒江的:‘站立起来的大江,你见过吗?……车进怒江峡谷,大家就被迎面撞来的怒江给镇住了。这哪里是一条江啊,我们分明撞到一头迎面而立的水狮子!它一晃脑袋,就水珠乱溅,一龇牙咆哮,就有阵阵惊雷滚过……’ 怒江,我去过,写过,也见别人写过。却第一回见到这样写怒江的文字。而且,作者李秀儿——应该是个女性吧?我这样猜想着,顺手把这段文字抄写在当天日记里。也在这一年,秋天,一个电视摄制组来我家采访。互相介绍时,一个年轻的节目主持人说,她叫李秀儿。我一下子想起半年前抄写那段文字的作者,翻出日记,两相对照,我们就这样戏剧性地认识了。旧事重提,是想说,由此,儿童文学阵营多了一名生力军——随后不久,李秀儿出版了她的第一本儿童文学作品,书名就叫:《站立起来的大江》。”这段文字,以及与吴然老师认识的这段经历,深深刻在了我脑海里,成为我写作儿童文学的精神动力之一,永难忘怀。
就在这段文字里,提到的另一个文学前辈、诗人晓雪,那是对我同样有鼓励和帮助的一位老作家。2017年,他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50万字的重要著作《我的文学人生》,居然三次写到了与我有关的一些小片段。其中有晓雪老师为我第一本书写序的过程,有我在他的一次颁奖会上朗诵他的诗作的故事,也有他读到我的一些作品的评点……一位八十多岁高龄的国内文学泰斗,却是那么平易近人地关心一个初学写作者的点滴进步,这些,让我明白了写作应该怎样去把握人、洞察人、理解人,关心人的道理。
浙江有一位国内儿童文学评论大家孙建江老师,他也以自己的方式,从理论高度,指点帮助我在儿童文学创作上怎样获得进步。他把自己读过的一些书的心得告诉我,还开出一些书单,提供给我作为创作的参考。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王宜清老师、楼倩老师、吴遐老师,都是我不曾谋面,却得到她们帮助鼓励的老师。我的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花山村的红五星》,连书名都是她们帮我取的,出版以后,《中华读书报》的陈香老师,还为我这部作品写了评论,她在文章里说:与其说《花山村的红五星》是一部儿童文学战争小说,不如说更像一部“战后小说”。她既写了战争对社会底层和普通大众带来的创伤和不幸,更写了一家三代在“战后”绵延半个多世纪生活中遭遇的扭曲和苦难。小说摈弃了传统叙事模式,自觉地将人物塑造从“脸谱化”“概念化”和“符号化”中解放出来,深刻触摸历史文化中的人文肌理,深度审视人性,拷问灵魂,浓墨重彩地书写出苦难中升华起来的人格力量,成为我国新世纪以来指涉战争题材的儿童小说中的翘楚之作。借她的吉言,这部作品后来入选《中华读书报》2016年度“十佳童书”,这是很高的一个荣誉!而上述这些指点帮助过我的浙江或北京的评论家、编辑家,我至今一个也没见过。我不能不说,我所接触到的儿童文学领域,跟我接触到的儿童一样,真干净!
这些年,我辗转云南、天津等地,现在来到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祥地上海,而且,非常幸运地来到了儿童文学重中之重的核心区——上海师范大学,如今我是这里一名文学博士。这里真是名家云集——单是儿童文学创作和理论大家,就赫然在目,不胜枚举。与他们朝夕相处,耳濡目染之间,即便我再愚钝,我相信自己也会得到一些熏陶和长进。我想,在不放弃儿童文学创作的同时,我要争取多读一些关于文学、特别是儿童文学创作和理论的书,尤其在理论方面也加深一点造诣,为自己打下更坚实的基础而努力。
打开精美的《2017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获奖作品集》,冰心奶奶两段话深深映入我的眼帘和心底:“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得奖仅仅是创作的开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两句言简意赅的话,就像指路灯一样,已经照亮了我。以爱为动力,从足下起步,儿童文学,请等等我!我来了!
——两岸儿童文学之春天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