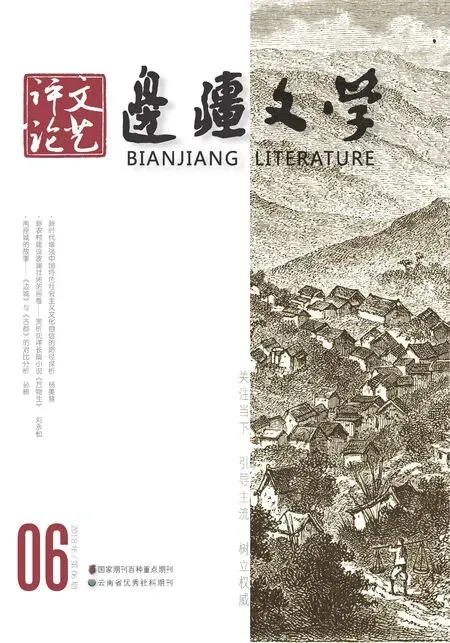以后殖民视角解读《米格尔街》逃离主题
宋海啸
英籍印度裔作家V.S.奈保尔与拉什迪,石黑一雄并称“英国移民文学三雄”。来自于第三世界的他用调侃而又冷酷的笔调犀利地指出很多问题。《纽约时报》曾评价该部小说:“虽然故事悲剧被弱化,喜剧被夸大了,但是真理范围一直为主线。”一部回忆录式的小说囊括十七个短篇,每一个故事都透露着麻木空虚,无所适从,而故事中的每个人却又兴高采烈地活着。米格尔街上的人们一方面没有真正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也无精神归宿,处于孤立的第三空间中,在这种情形之下,逃离确如最佳选择。而殖民主义的统治与压迫对于米格尔街的人们命运迷失更像是助燃气,加速了人们逃离特立尼达这座生养之乡。
一、模拟——逃离从属国文化
特立尼达先后由西班牙、英国入侵统治长达数百年。奈保尔曾回忆说,还在小学读书时他就发誓以后要永远离开特立尼达岛,到外面的世界去,到帝国的本土去展示自己的才能(高照成:12)。长期以来,生活在殖民地的人们既无属于自己的清晰历史加以回望,也无明确的美好未来加以展望,他们只能带着无处安放的认知焦虑活在当下。博加特作为《米格尔街》的第一篇小说,就阐释了殖民地人们的迷失与不安。博加特这个名字是美国电影《卡萨布兰卡》中的一个硬汉角色,受人追捧。而米格尔街上的人们并不知道博加特的真实姓名是什么,他们也不需要知道,因为在殖民话语中,位于边缘的他者早已失去了“表述自己”的权力或者即使表述,表述的内容也是受到宗主国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被边缘化的他者会不遗余力地逃离从属国文化,脱离被殖民者的身份。博加特逃离米格尔街,回来后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他变得蛮横粗野,讲着一口地道的美国腔英语,成为位于中心的殖民国家中一个滑稽的模仿者。语言作为一种象征符号,在索绪尔那里,能指乃是符号的形象和声音所构成的心理现实。这种模拟,更像是一种讽刺性的妥协。虽然相似,却不尽相同。殖民地人们摒弃自己的语言,模仿并使用宗主国语言,无疑是帝国权力的表征,也是所谓文明带给原始或野蛮的民族的副作用。帝国主义不仅在战争中争夺了土地,更为严重的是,它也剥夺了殖民地人们确认自己身份和历史存在的权力。
爱德华彻头彻尾的模仿美国人,嚼口香糖,练美国腔,学美国人健身,这种执着而滑稽的模仿是其逃离从属国文化的唯一的高效途径。可是,就如被困在如来佛祖手掌心的孙悟空一样,纵然万般折腾,佛祖的神力依然在其上空萦绕,难以逃脱。霍米巴巴在其《文化的定位》中指出,假如殖民主义以历史的名义掌握权力的话,那么它便常常通过闹剧的形式来施行它的权威(1994:58)。不光如此,当儿子艾利亚斯成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时,父亲乔治也会改变自己的态度,不再暴打孩子。他们都在努力地成为小街上人们崇拜的对象,可现实却是三次考试失败最终从梦想着成为医生的少年沦为卫生工作者最终沦为卡车司机。以模仿的方式进入上层阶级失败的原因是他们本质上忽略了殖民者把他们当作臣民属下的事实。
二、混杂——逃向宗主国文化
霍米巴巴混杂性理论的核心就是“从中枢进行的海姆利克式施压。也即是说,从殖民话语的内部对其实行压迫,使之带有杂质进而变得不纯,最后其防御机制彻底崩溃,对殖民主义霸权的批判和颠覆也就得以实现(王宁:38)”。
法农认为“殖民者在暴力的征兆下,使用一种纯粹粗暴的语言,把压迫和统治呈现出来……把暴力带到被殖民者的家中和头脑中(2005:5)”。
乔治喜欢打自己的老婆和女儿,老婆死后,乔治也迷失了自己,他逃离了米格尔街,回来后,他的粉红色房子几乎彻夜喧嚣,美国大兵也喜欢来他的房子寻欢作乐。无所适从,迷失又迷茫,内心的空虚也只能靠接近宗主国文化来排解。当时的女性不仅在殖民地生活,同时也受父权制的影响与迫害,双重压迫使她们变成了比边缘还要边缘的人,比他者还要他者的下层人。乔治靠打自己的老婆和女儿来确定自己是家庭里的权力中心,虽然在外面他和街上的人们一样,都是宗主国所摒弃的他者,但在自己的空间里,他仍掌握绝对的权力,以此来自我宽慰。老婆的去世,是他对于自我认知的第一次迷失,迷失在殖民霸权的迷惑下,不能再发挥自己的男性权威,他逃向宗主国文化,试图能找到一己之地,带上象征权力优越性的白人面具,让美国大兵在他的粉红房子里纵欲享乐。而这所粉红色房子就是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产生的第三空间,这个第三空间是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过渡空间,在过渡过程中,很显然,奈保尔笔下的乔治并没有消解西方文化霸权,反而在融合过程中自己越来越边缘化,最后悄无声息的死掉了。
在受压迫的第三世界殖民地环境中,被殖民者的精神和心理压力是其所承受的巨大经济压力的外放表现,但个人由于无力与强势经济的冲击、挤兑和盘剥进行抗争而选择以家庭暴力作为发泄的途径,却使施暴者和受害者双方都受到了殖民主义的双重伤害。
三、颠覆——找自我归属
人们生存总要有一定的精神上的动力,但特立尼达长期的殖民地的社会背景使人们对生活的美好希望变得渺茫,人们似乎是为了活下去而生活,理想受到了压抑,那么他们的理想彻底消失了吗?人的精神总要有一定的寄托,米格尔街的人们也不例外,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精神寄托体现在不同的生活理想形式上,只是它们终结形式多多少少会使我们感到意外、可笑和凄凉。
在《母亲的天性》一节中,身为八个孩子母亲的劳拉身体力行地对殖民者霸权进行颠覆,为女性发声。在被殖民时期,女性只能在夹缝中生存,一方面受到殖民者压迫,另一方面还要受到男性压迫。乔治和比哈库都把打自己老婆当作茶余饭后的放松与调解,唯独劳拉,反其道而行之。她不光没有被男人打,反而共与七个不同的男人生下孩子,但每个都不长久,没有人帮她养家糊口,她只能依靠自己,当然,她也喜欢依靠自己,在自己的王国里可以不受任何压迫,自己的声音也不会被静默,她努力培养女儿接受教育,她认为受教育是世界上最高贵的事情,她不想孩子们像她一样。她所苦苦经营的作为女性的自我认知却被大女儿劳娜的怀孕而打破,得知大女儿怀孕的消息后,劳拉的恸哭令街坊邻居肝肠寸断。劳拉的悲剧性在于无论她如何进行颠覆,试图寻找自我认知,在双重压迫的现实下接连碰壁,而她寄予希望的下一代也是重蹈覆辙,殖民地的女性在帝国主义和父权社会的双重压迫下,是无法发声的,也无法冲破双重压迫所设置的障碍。就如卡利普索小调一样,它兴起于殖民时代,是特立尼达的一种文化遗产。在当时被殖民者们憎恨压迫,用说唱形式抒发情感,讥讽殖民者。二战中美军来到特立尼达,给当地造成了诸如娼妓横行、物价飞涨等社会问题,由此形成卡利普索发展的又一轮高潮。当人们丧失话语权时,歌唱成为小街上人们的另一种精神诉求方式。我歌我历史,我寻我自我。
四、结语
米格尔街上的人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生活着,他们在生活的绝望和边缘的痛苦中逃离,逃离从属国文化,逃向宗主国文化,在这种单向逃离的逃难过程中,孤独,迷茫,迷失,既怀着对本土文化的记忆,又极力靠拢帝国文化,企图用不属于自己的语言,传达属于自己的精神。
[1]Bhabha, Homi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M]. London: Routledge,1994
[2]弗郎兹·法农著.全世界受苦的人[M].万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3]高照成. 奈保尔笔下的后殖民世界[D].苏州大学学报,2006
[4]王宁.叙述、文化定位和身份认同——霍米·巴巴的后殖民批评理论[J].外国文学 ,2002(6):4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