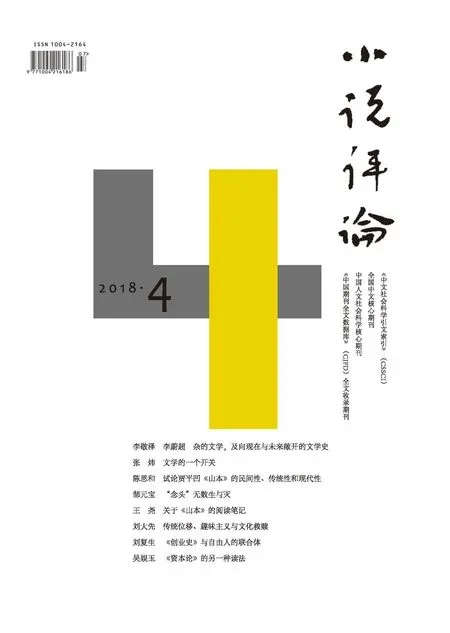莫言与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历史关联性
——路径、方法与可能性的探讨
王金胜 吴义勤
一、学术考辨与意义评估
自20世纪80年代迄今,尤其是近几年,莫言与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关联研究逐渐获得学术自觉。关于此议题的研讨,主要在四大区域展开。
首先,关于莫言与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学者多借助文化人类学、现代主义等知识,以福克纳、马尔克斯、尼采美学/文学为支点,阐释莫言文本中意识流动、时空交错、酒神精神、感官放纵、审丑艺术、残酷美学、魔幻现实主义等“现代”元素,肯定莫言对域外现代主义文学的借鉴、转化及对传统现实主义模式的突破。此类研究实质是将莫言文本视为一种对文学现代性的整体性追求,从文学理念看,隐含将现代主义文学看作普适的、先进的文学形态/阶段的信仰;置诸现代中国文学发展脉络,莫言文本因挑战正统文化建制及其僵化美学范式,在艺术方法和审美效应上“更具价值”,从而满足了“主体性”“纯文学”的主体弘扬和形式至上的想象。
其次,莫言与乡土小说研究。张志忠以“看与被看”“外来人讲故事”为模型勾画从鲁迅、沈从文、赵树理到莫言的乡土叙事脉络;程光炜以“本地人/外地人”的身份差异辨析莫言与现代农村叙事的差别;陈晓明以“在地性”为莫言历史观、文学观和审美修辞上“越界”的根底。刘洪涛认为莫言兼收鲁迅与沈从文的文化立场,并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异域想象形成呼应。凌云岚从乡土文化想象的角度阐释莫言对乡土文学传统的继承与突破。美国学者孔海立认为莫言与端木蕻良对历史和革命的不同理解,来自其乡土文化精神的差异。日本学者藤井省三以《安娜·卡列尼娜》为辅助线考辨莫言与鲁迅“归乡故事”叙述的深层联系,更新了莫言研究的方法和视野。将莫言置入乡土小说论域,无疑能凸显作家文化立场的差异及其在不同语境下的美学选择,也切合乡村/地域文化经验作为莫言基本经验的事实,体现着从历史深层脉络审视审美形式、由“现代传统”观照莫言的学术自觉。
再次,莫言与鲁迅等现代经典作家的比较研究。孙郁、吴福辉、王学谦等学者从莫言与鲁迅精神内蕴、生命体验、感情气质和文化心理上的相近性、相通性、承传性;吴义勤、温儒敏、王春林等探讨莫言“忏悔”和“罪感”与鲁迅的呼应;李静、刘勇等以国民性批判、“看/被看”“魔幻与现实”模式分析莫言对鲁迅的承传与发展;葛红兵、赵勇等比较二者启蒙/反启蒙、作家/知识分子的角色认同差异。研究深入涉及作家个体心性等幽微层面或文化心理和立场等结实内核,是将莫言划归“现代传统”经典谱系的重要实践。
复次,以民间、古典话语阐说莫言。1980年代中期开始,学界也开始关注莫言创作的民族传统美学趣味,199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获诺奖后,伴随着“本土”对“西方”的反思,此阐释角度成为新的学术热点。自1990年代陈思和提出“民间”概念,“民间”逐渐成为莫言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领域,已形成一套相对稳定的学术话语体系。陈思和、张清华等以民间立场作为莫言“新历史小说”区别于传统历史叙事的根本依据;王光东、洪治纲、张柠、张闳等突出其民间文化心理、传奇性、狂欢化和中国精神、本土经验;李敬泽将其还原为古典“说书人”角色,王德威、季红真、马瑞芳等探讨莫言小说对志怪、明清小说的借鉴。此研究自80年代中期延续至今,敞开了民族、古典、本土的广阔视域,形成独特的学术话语体系。
以上论述,涉及莫言与“现代传统”关系的不同方面,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但也遗留一些问题有待研讨。
首先,对“现代传统”作为莫言文学“本体性”构成的意义认识不足。我们认为,中国文学“现代传统”而不是其他传统从根本上塑造了莫言的内质与风貌。莫言、“现代传统”倚重却不依附古典传统,是世界文学的重要构成。它有着现代历史情境中对本土性、民族性的彰显,却无法脱离中国现代性论域而封闭、孤立地存在。莫言、“现代传统”既非西方现代文学的中国翻版,也非中国民间/古典传统的现代转换。莫言文学是立足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现实,以中国文学“现代思想与美学传统”为根底,汲取西方与中国古典/民间营养,传达着中国文学追求、建构现代性乃至反思现代性的价值取向和意义诉求。在莫言,“西方”“古典”主要是作为其“构成因素”被涵纳,而非与后者同等并举的范畴,探讨莫言与二者的关系自能加深对“现代传统”的理解,学术价值不言而喻,但若因此忽视莫言与“现代传统”的内在历史关联,却有可能放过了问题的根本症结。
其次,研究模式较为单维、局促。主要集中于乡土小说论域和鲁迅等经典作家,对启蒙/新启蒙/后启蒙、个人主义/人民话语、政治/美学、民间/民族、本土/西方之间缠绕互渗的关系尚欠历史性的深层的动态辨析。如常见的“传统(古典/民间或现实主义)/现代(现代主义)”二元论,忽略了古典/现代/异域文学各自的文化具体性及其交互关系的历史建构性。
莫言文学作为中国新文学百年历史实践与发展的重要成果,也是理解中国文学“现代传统”之结构与肌理的一个意蕴丰厚的鲜活例证。这需要从中国文学“现代传统”实存经验“内部”着手,溯源究根,发掘莫言与“现代传统”的历史关联性及其对此传统的“发明”、创造和超克。中国文学“现代传统”诞生于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冲击,造就其西方(世界)的面向;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与现实境遇,造就其民族性(本土性)面向;对个体和族群经验的摄取、体悟和精神的淬炼,形成其个体性面向。其中,西方(世界)与民族(本土)并非本质主义的对立范畴,是“中国”“现代”情境下的存在,体现着中国文学的现代创造和作家的现代体验。“西方”和“古典”并非确定“现代传统”(及莫言)意义的终极权威和合法性资源,以“现代化”为基准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方法论、价值论和“中/西”二元性阐释模式,无法释读其内在复杂性。因此,亟需立足中国文学的实际,由内部(中国)而非外部(西方)的历史眼光和价值尺度来寻绎“现代传统”的生成、演进,突破研究中以“现代化”为基准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方法论、价值论和古/今、中/西的二元架构及对传统的本质化认知,以“了解的同情”态度,运用历史主义方法,在“现代传统”中“深描”莫言,以莫言为视点烛照、激活“现代传统”资源,彰显中国文学的内在特性与价值及其蕴含的世界性维度。
二、“经典化”的反思:理解莫言与“现代传统”之历史关联性的学术前提
源于“五四”的中国文学“现代传统”构成了当代作家进行自我想象和文学书写的重要资源,同时,这一传统也深刻塑造了当代中国人对文学及其与历史、时代、现实、人性等关系的期待视野。“现代传统”一方面显示着强大的跨越时空的影响力和传承性,另一方面,它也在经历着不同历史语境下的分化、转变、离散和重组,甚至时时面临着被质疑、解构、颠覆的命运。在与“当代”不断对话的过程中,现实对“历史”提问,“传统”对现实做出回应。由此而言,作为反映或回应现代、当代处境与问题的“现代传统”,在其不间断的历史流转中,每每被历史化,成为一个有着浓重的当代(当下)问题意识的重要资源。而当被视为一个资源时,“现代传统”也同时被再次经典化。经典之成就自身,就在于它通过不断的历史化、当下化,而被视为资源或源头,无论是“积极”的建构还是充满争议的解构。僵死的、无力回应现实介入历史,无法将人们带入某种情思状态,无法激起人们现实感的文本,不是经典,而只是一块化石或动植物标本。这就是经典化与历史化的历史辩证法。因此,“现代传统”必须被置于当代中国的经验之中,它的美学表现力和思想阐释力才能得到检验,现代/当代才能在深入的对话与磨合中,逐渐明确自身。
在此意义上,中国文学“现代传统”并非某种形式主义的规范性叙述,它在打开自身的同时,也敞开历史,与历史对话并在其中获取新的生命。也因此,本文关于莫言与“现代传统”之关联的探讨,其更准确的表述应为:莫言(当代文学)与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历史关联性研究。循此思路,研究的切实问题就是,在“当代”(不同于“现代”)具体的(不是在抽象意义上)历史情境(不是作为过往的已逝的,而是当下与过往交织的)中,他们如何回望“现代传统”,如何以自己的文学实践对其做出理解、阐释、评判和呈现。这些当然需要立足于现代性、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基本事实,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具体考察。在对“现代传统”的多重解读中,哪些因素被淡化,哪些因素被凸显,哪些因素始终“在场”,这些因素相互之间构成何种关系,它们之间是否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其具体联系如何,作家如何运用何种意识、形式和语言来接纳和表现它们。
目前关于莫言与已被“经典化”的中国文学“现代传统”之历史关联性研究,存在着一些可以反思的问题。一是将莫言文学与“现代传统”之联系视为前者始终处于后者的笼罩与统摄之下,在这种学术视野中,莫言及其文学构成了一种始终处于“现代传统”阴影笼罩下的被动性存在。二是与上述现象相反,将二者之间视为一种二元对立性/对抗性关系,认为莫言完全地、彻底地以对抗“现代传统”之主流思想、文化、精神及美学传统,在“反传统”中构建主体认同。在此学术视野中,莫言与“现代传统”处于文学话语的两极。最为普遍的通行范式是在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经典历史叙事/新历史叙事之间,论述莫言的“反现代”“反主流”“反文化”特征。三是将“现代传统”看作一种本质化、规范化的存在,而非一种历史实践和历史的建构过程。研究者或将“五四传统”这一“现代传统”形成与建构的源头视为后者之核心与本质,不同程度地忽视“五四传统”本身就是一个包容着种种矛盾、冲突性思想文化立场的场域,忽视这一传统在特定的具体历史情境下的转变与嬗递,而是以之为本真性、原初性、真理性的事物,将此后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展开、并逐渐成为时代主潮的“新传统”——如“革命”传统、人民性传统、农村叙事传统等对立性地讲述为对“五四传统”“启蒙传统”的背叛或蜕变。在此面向的研究中,比较常见的现象是,选择、确立某一固定不变的“现代传统”命题,在历史性、社会性文化因素“缺席”的状态下对莫言与此命题进行机械、僵硬甚至模式化的比较。
在上述常见的问题中,隐藏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核心观念是,由“现代文学”经典化、体制化所导致的思想、思维与研究范式的保守。经典化的结果,积极的一面是,它形成了一些经典性的学术观点,藉助这些观点的传承、流播,经典作家作品的思想、精神、文化、美学等成为民族和人类重要的根基和资源;消极的一面是,一些程式化、模式化的研究套路,有可能借助某种权威或惯性、惰性渗透和流播,造成心态、观念的保守和思维的僵化。这就特别需要将“现代传统”建构的体系性框架性诉求与现代中国文学实践及历史进程区分开来,从而认识到“现代传统”作为一种现代建构,其阶段性内涵、特征与形态并非一种简单的自然生成的结果,而是与历史、时代对话、对抗与融合的产物,“现代传统”是历史的产物与结晶,也是历史的建构,一种拒绝被本质化的历史性存在。因此,进入莫言与“现代传统”之历史关联性的讨论议题,意味着对其各自及其相互间“历史性”因素的关注和凸显,只有在“历史”的内在视野中,关于莫言与“现代传统”之间才能形成真正有效的互动关联。
三、“历史化”:莫言与“现代传统”之历史关联性研究的方法论
如上所述,被经典化的中国文学“现代传统”,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生成与建构。从“新文学”以来作家评论家的资料搜集、文艺评论,到新文学史、新文学作品选本的出版、中小学到大学各级学校的文学教育,都体现着“现代传统”作为“古典传统”的他者,对自身合法性、经典性的自觉建构。其中,由新文学运动的切身参与者、过来人,编辑出版的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对“现代传统”的阐说及其经典地位的奠基,意义不可替代:“《大系》保存了新文学初期丰富的史料,也最早从历史总结的层面汇集了当时各种对新文学有代表性的评价,可以说是一次新文学史研究的‘总动员’从此,新文学史研究的意识及其地位在学术界得到空前的加强。”19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文学史研究的推进,尤其是“重写文学史”的倡言与实践,以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为代表的海外汉学研究的冲击,包括建国后以“当代”为价值标准对“现代文学经典”的遴选和文学秩序的重构,“现代传统”的话语构造性被步步深入地发现。透过这一福柯式话语权力及解构主义视角,“现代经典”与其说是由“启蒙”“革命”等思想话语或由“鲁郭茅巴老曹”、张爱玲、钱钟书、赵树理、萧红等经典作家作品构成的客观存在/范畴,毋宁说是一个从历史—文化的内在视野出发才能展示其内涵的概念,即“现代传统”是一个过程——一个形成其自身、建构其历史主体位置的过程,一个将自身建构为现代中国文学本体/主体的过程,其本体/主体建构的动力、路径、方式和形态,源自这一建构得以发生的广阔历史形势和文化情境,一种能够将“新文学”转化并确认为“现代传统”的政治力量、历史意志、文化意识纠缠错动的历史过程。
需要注意的是,在强调“现代传统”的主观建构性时,也需突出这种建构性不能也无法脱离“客观性”范畴,而必须是一种既超越那种经验主义地理解“现代传统”的思维模式,强调其是由自觉的历史化乃至政治文化实践所赋予的客观性存在,又能在一种更为广阔的主客观对话关系和实质性的历史关系中,锻造、生成新的“综合视野”。
文学对于莫言来说,包含着对主体存在本身的理解,而不仅仅是形式和文字的自娱自乐。莫言文学并非一个纯审美或幻美的空间,其中有突出的社会和历史的维度,以及极具历史/生活实感的整体性。其营造的生命—审美乌托邦因有着现实的支撑,而具有了返归现实、介入和批判现实,进而生产现实的直接力量。其主体性的建构,因有着切实而广阔的历史维度,而具有了主体的鲜明形象。
在具有鲜明的个体创造性的莫言文学中,印刻着“现代传统”与时代的痕迹,在不无夹杂晦涩的形式和天马行空、泥沙俱下的语言中,有着与历史、时代相纠结、缠绕的心灵世界、精神结构和文化心理的典型症候。莫言文本空间图式中的看似细微的“关节”,往往指向漫长时间—历史之轴,链接着丰富、复杂的历史内容。在历史主义眼光的牵引下,一个驳杂、动态的,作为潜意识和文化结构的“现代传统”得以在当代显影。
以营造生命—审美乌托邦的方式,以对现实的复杂性与内在困境及危机的敏锐体察,莫言文学对包括暴力、堕落、血腥、退化等因素在内,善恶交叠、美丑并生的具体的历史、社会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进行了更具弹性和包容性的道义审视、纠正和美学质疑、反思,体现着文学应有的历史想象力和美学创造力,提供着关于生命个体与历史、现实的总体性理解。
从这个意义上讲,莫言文学体现着“现代传统”的现代性、历史化的内在品质,呼应着时代的、历史的内在需要,它延续了“现代传统”的诸多思想、文化和美学的命题与血脉,但又穿透、突破而非亦步亦趋地遵从某些惯例和成规,从而在实质上对“现代传统”进行了一种个体化,也是历史化的解读和重释。事实上,“现代传统”诞生于“现代”对“历史”(“传统”)的重读,当这一重读实践是在一种“当代”眼光烛照下进行时,“现代”也就成为了“传统”。
在时隔大半个世纪之后,莫言等当代作家再次重读“五四”以来逐渐确立其思想文化主导地位的“现代传统”,将其从被本质化、超历史、超地域的“经典化”状态中解脱出来,从成规化、范式化的美学认知与技术规范体系中释放出来,从而为自身意图表现的历史赋予充满个体创新/创造性的形式感,将自身所处时代繁复嘈杂的现实美学化。
近而察之,莫言文学是对当代中国尤其是“新时期”的社会、历史、文化的显影与表达,体现着作家的“当代”关切和现实情怀,同时,也被后者所深刻界定和规约。在莫言,文学/历史、文学/现实、形式/修辞/语言与意识/无意识之间,构成缠绕难解的关联。更进一步说,莫言对“现代传统”的接续、转换与超克,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和文化条件下发生的。作为“现代传统”的建构者、超克者,莫言如何选择“现代传统”并将其转化为自身的精神与艺术资源,藉以传达、表述其对当代中国的体验、思考、情感,其方式与路径如何,其具体精神内蕴和美学形态如何,“现代传统”作为一种整体性存在与作家的个体化写作之间,究竟构成了何种选择/被选择、承续/转换/创造/超克之关系,这种“关系”得以发生的关节点何在?这就需要透过莫言对“现代传统”的拓展、转换或“冒犯”,突破文本静态的显层比较,发掘其中的“历史”因素;突破对“现代传统”的本质化认知,揭橥潜行其间的社会结构、历史动量与文化逻辑,以及作家言说、表现“现代传统”背后的时代语境和话语策略。同时,如何理解同样作为思想、美学“遗产”的古典传统、民间传统与域外传统,及其与“现代传统”在莫言文学中具体的结构性关系。这同样需要经由历史化的处理,并在一种总体历史—文化视野/结构中得到深层探察。
也就是说,考察莫言文学与“现代传统”之历史关联性,意味着一种对二者之间“普遍性联系”作为基本方法的强调,意味着一种百年中国文学/历史/文化经验的总体性视野。但这种总体性需要与本质主义的历史宏大叙事加以区分,也需要与某种关于“现代传统”的理论表述和理论话语体系建构区别开来。如此做法,首先是基于“现代传统”及莫言文学本身的复杂性与独特性,及由此而展开的一种历史化、批判性思想—文化实践,藉此,我们可以且能够在广阔的历史时空中,透视、把握置身其间的现代中国文学何以及如何生成、建构、衍变、运行、流转。也只有具备总体性视野,我们才能对形塑、规范主体及其文学表现的历史、政治、文化、体制持有一种必要的警醒和批判力,从而对此形塑、规范力量——作为历史及其现实存在形态的“现代传统”和作为总体现实和“氛围”的“去政治化”的时代思潮——如何作用于主体和知识的再生产,而后者又如何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视野中理解自身的存在与美学实践,并借助自身强劲的思想穿透力和想象力,将此关乎自身存在及美学实践的理解,转化为创造主体及作为其表征的美学的历史催动力。
大致说来,莫言与“现代传统”之间大致包含三种不同的勾连形式:其一,以“现代传统”为典范模本的学习、借鉴与“敬仿”。其二,莫言与现代经典作家在精神与灵魂的相通或“相遇”。其三,莫言基于“当代性”对作为历史文化文本/潜文本的对立性、对抗性、解构性、超克性书写。但需要强调的是,莫言与“现代传统”之历史关联性并非不言自明。尽管莫言与鲁迅、赵树理、沈从文甚至端木蕻良等作家、莫言文学与启蒙话语、革命历史叙事、现代乡土叙事等有着可以比较的某些“客观”方面,但莫言及其文本却不应被理解为由这些“客观”因素决定的“客观”存在,也许更为合理的做法是,将其理解为一个被纳入“历史”范畴,与历史实践有机结合的“主体”范畴。莫言及其文学本身就是历史实践和历史创造的一部分,并构成“现代传统”这一始终处于历史动态运作的“历史”的创造。“历史”构成莫言文学及“现代传统”的结构性因素和动力所在。
四、“当代性”:莫言与“现代传统”之历史关联性研究的理论前提
历史化的学术处理,意味着恢复一种历史视野,开掘历史纵深,成就研究者的历史感和现实感、当下感。一种实质性的历史关联只有在实质性的文学/历史及其交互运动中才能真正存在和展开。问题在于,如何对莫言文学、“现代传统”进行更为复杂化的处理和更为深入的推进,对不同文学话语间复杂的结构性关系进行深入的整体把握,突破泛泛而论的浅层文本比较,就二者关系提出建设性构想。这需要将“现代传统”的理论化与自我预设性阐释,置入一种“实质性的历史”之中,并将后者转化为文学流转的内在视野。在这一转化过程中,文学流转的具体情景、脉络、细节转成了重要环节。为了避免大而无当的宏大叙事,“细节”考掘是一个颇有支撑力的藉助。从症候性的关节点入手,在历史与现实、与当下的不间断的、循环往复的对话、碰撞和辩诘中,破解僵化的意义模式和历史叙述,同时,避免依据当下时行的新潮理论、观点、方法做出貌似创新实则简单粗暴的裁决。这种历史感与现实感、当代性的辩证法,也内含于“现代传统”(文学史)与莫言(文学批评)的对立与对话之中。
关于“当代性”,张旭东有如此阐释:“我们必须——或者说不得不——把一切有关我们自己的经验——包括文学经验、政治经验、社会经验、个人经验等——高度当代化,也就是说,作为当下的、眼前的瞬间来把握。”在他看来,当代文学从来就不是“现代文学的弃儿,被现代文学所排斥……相反,在一个更高的意义上来说,当代文学却是要有意识地把现代文学排斥出去,把它作为‘历史’归入另册,从而为把作为当代经验有机组成部分的当代文学经验从‘过去’分离出来,把它保持在一种特殊的思想张力和理论可能性中。通过这种非历史化的自觉意识,当代把自己变成了所有历史矛盾的聚焦点,当代文学则把自己变成了所有文学史的最前沿和问题的集中体现。”更进一步说,“现代文学是被当代文学生产出来的,正如历史是被当代生产出来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文学其实最终都是当代文学……最好的现代文学乃至古代文学研究,应该是当代文学经验和当代文学判断力的一个分支,因为只有搞当代文学的人才能真正地把握现代文学,这是在批评和批判(这既是康德‘判断力批判’意义上的批判,也是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意义上的批判)意义上的把握,而不是历史主义、经验主义和学科专业主义的把握”。很难想象一个对当代文学经验陌生、无话可说的人能做好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研究,因为“文学”来自其当代性而非文学史,“只有在一种‘当代’的意义上,文学的存在才成为可能”。因此,张旭东认为,“批评是第一性的,文学史是第二性的”,而进行批评的最基本的前提,“就是存在的政治性”,在“各种经验的、趣味的、知识的、理论的、甚至技巧的训练和准备”等技术性前提之上,“存在本身的政治性,是激发和推动批评活动的最根本的前提和动力”。这些观点或许不无讨论余地,但其关于“批评”内质与动力的言说,无疑对莫言文学与“现代传统”之历史关联性的研究,极具启发性。
在此议题上,张旭东本人与吴义勤等人关于莫言《酒国》的批评,可为资鉴。张旭东的批评立足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经验,将小说视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寓言。在他看来,小说“形式”(妖精现实主义)与“内容”(作为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当下中国现实的后社会主义中国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对应性和统一性。《酒国》虽然没有提供对这一时代中国的精细清晰的写实性刻画,但“在《酒国》中,所有与当代中国联系在一起的幽暗、矛盾、混沌,尽管在分析理性看来非常令人费解,但在一种叙事艺术品的界定中,则变为一种‘诗学规范’,它以或然性(the probable)同‘实然性’(the actual)形成对照”。作者将作品的形式、技巧实验等文学“内部”问题置于“当代”生产关系内部,而同时,生产关系又在文学“内部”被重新生产出来。作为形式的“妖精现实主义”,是后社会主义时代中国市场经济“最本真的经验”,而恰恰是后者“决定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经验方式和感受方式”。《酒国》与鲁迅《狂人日记》的互文性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吴义勤将“吃人”叙事放在“现代”(“五四”时代)与“当代”(1980年代末90年代初)两种不同的历史情境下,阐释其叙事肌质变异的形式表征及隐含其后的主体精神结构。吴文与常见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最大不同之处是,首先,由形式(元小说、戏仿、多层文本交错等)切入内容(“现代”“当代”作家精神结构),将形式等文学内部问题置入“现代”“当代”思想生产系统之中,而“现代”“当代”思想又在其时代的典型文本中被重新组织、生产。其次,在充分历史化的基础上,立足当代性。批评不是在传统的“影响”或“流变”意义上阐释两个文本,将当代文本《酒国》覆盖于现代文本《狂人日记》的荫庇或阴影之下(如前所述,这样做的后果只会同时封闭两个文本丰富的意义域),而是直面当代中国经验(不同于张旭东的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验,而是特定历史转型期中国文化经验),直面当代文本的形式感、新异性和个殊性,以《酒国》作为莫言个性化的当代美学创制对现代文本的超克为论述基点,实现现代/当代、历史化/当代性之间的同等对话。
文学的“当代性”品质,“当代性”对“文学”定义与存在的规定性意义,对于目前此议题研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启示。当我们以“现代传统”来涵盖莫言,以此为意义前提和价值标准来阐释、评判莫言的思想与美学时,存在着一个似乎不成问题的认识——作为当代文学的代表作家,莫言隶属于“现代传统”并从后者获得合法性和经典性认定。同时,作为对莫言文学的阐释,当代文学批评之价值准则应该从“现代传统”获得。这种认识,不仅以前置意义模式限定、封闭了莫言及当代文学的丰富性、敞开性和可能性,而且几乎完全漠视进行批评的前提——“存在的政治性”。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现代传统”的丰富性、敞开性、可能性被封闭,蜕变为自我内部的封闭循环、话语空转、纯知识传授或资料累积。“现代传统”的生命性存在,不在自我因循,而在自我克服和自我超越。莫言文学即是“现代传统”的超克,二者的意义、价值及其历史关联性,需在当代社会思想文化的错动、矛盾的政治性整体结构中得以阐释和评判。
注释:
①张志忠:《从鲁迅到莫言:表述乡村》,《中国作家》2013年第4期。
②程光炜:《颠倒的乡村——再读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当代文坛》2011年第5期。
③陈晓明:《“在地性”与越界——莫言小说创作的特质和意义》,《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1期。
④刘洪涛:《莫言小说与中国乡土文学的两个传统》,《中国作家》2013年第4期。
⑤凌云岚:《莫言与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传统》,《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⑥[美]孔海立:《端木蕻良和莫言小说中的“乡土”精神》,范晓郁译,《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6期。
⑦[日]藤井省三:《莫言与鲁迅之间的归乡故事系谱——以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为辅助线来研究》,《小说评论》2015年第3期。
⑧孙郁:《莫言:与鲁迅相逢的歌者》,《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6期。
⑨吴福辉:《莫言的“‘铸剑’笔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4期。
⑩王学谦:《莫言与鲁迅的家族性相似》,《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5期;《魔性叙事及其自由精神——再论莫言与鲁迅的家族性相似》,《文艺争鸣》2016年第4期。
⑪吴义勤:《原罪与救赎——读莫言长篇小说〈蛙〉》,《南方文坛》2010年第3期。
⑫温儒敏:《莫言〈蛙〉的超越与缺失》,《百家评论》2013年第3期。
⑬王春林:《历史观念重构、罪感意识表达与语言形式翻新——评莫言长篇小说〈蛙〉》,《南方文坛》2010年第3期。
⑭李静:《不驯的疆土――论莫言》,《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6期。
⑮刘勇、张弛:《20世纪中国文学现实与魔幻的交融——从莫言到鲁迅的文学史回望》,《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3年第1期。
⑯葛红兵:《文字对声音、言语的遗忘和压抑——从鲁迅、莫言对语言的态度说开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3期。
⑰赵勇:《从鲁迅到莫言:文学写作之外的担当》,《中国作家》2013年第4期。
⑱陈思和:《莫言近年小说创作的民间叙述——莫言论之一》,《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6期。
⑲张清华:《叙述的极限——论莫言》,《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2期。
⑳王光东:《民间的现代之子——重读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5期。
㉑洪治纲:《刑场背后的历史——论〈檀香刑〉》,《南方文坛》2001年第6期。
㉒张柠:《文学与民间性——莫言小说里的中国经验》,《南方文坛》2001年第6期。
㉓张闳:《莫言小说的基本主题与文体特征》,《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5期。
㉔李敬泽:《莫言与中国精神》,《小说评论》2003年第1期。
㉕[美]王德威:《千言万语,何若莫言》,《读书》1999年第3期。
㉖季红真:《莫言小说与中国叙事传统》,《文学评论》2014年第2期。
㉗马瑞芳:《莫言的成功在于向经典致敬》,《蒲松龄研究》2013年第3期。
㉘温儒敏等:《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
㉙㉚㉛㉜[美]张旭东:《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61—362页、366页、367页、369—370页。
㉝[美]张旭东:《全球化与文化政治:90年代中国与20世纪的终结》,朱羽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57页。
㉞[美]张旭东:《〈酒国〉读书会》,张旭东、莫言:《我们时代的写作:对话〈酒国〉〈生死疲劳〉》,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38—39页。
㉟吴义勤、王金胜:《“吃人”叙事的历史变形记——从〈狂人日记〉到〈酒国〉》,《文艺研究》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