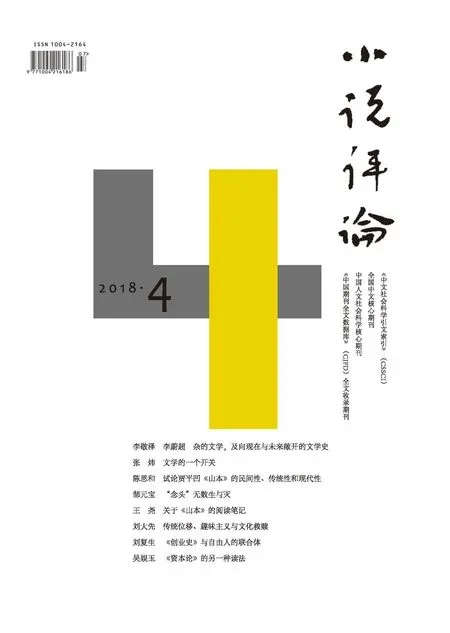贾平凹的《山本》与作为审美形态的“民间记忆”
王光东
民间文化形态与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一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莫言、韩少功、张炜、王安忆等重要作家的小说创作,都从民间文化中寻找着创作的资源,发现并重构一个新的艺术世界。特别是莫言在民间文化传统中建立起的民间叙述、想象使其小说创作具有了瑰丽的艺术魅力,为新时期小说贡献了一个新的审美维度。新世纪以来,贾平凹创作的《老生》《山本》等作品,虽然没有莫言那样奇异的想象力,但是却有着厚重苍凉的“民间记忆”中的生活形态。“民间记忆”作为小说创作的内容或元素,在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创作中一直有着重要的意义,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韩少功、张炜等人从民间立场写作的《马桥词典》《九月寓言》等作品,“民间记忆”的审美意义就已经突显出来,贾平凹与他们不同的是具有更加明显的民间说书人叙述方式,也就是莫言所说的“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贾平凹与莫言相比,莫言突出的是奇异的感觉和民间想象的力量,贾平凹突出的是写实性的民间记忆中的生活形态,这一审美纬度在他《秦腔》《古炉》等作品中就已出现,到了《老生》《山本》变得更为明晰,从审美的角度看就是构建了一种“民间记忆”审美形态。
一
何谓审美形态的“民间记忆”?记忆是
一个和文化、历史等范畴紧密相连的概念,它以集体起源的神话以及与现在有距离的历史事件、社会生活、民间文化等内容为记忆对象,是一种立足现代面对过去的社会、历史、文化建构,与“记忆”相关的研究有集体记忆、社会记忆、历史记忆、民间记忆、文化记忆、个人记忆等等。那么,怎样理解作为审美形态的民间记忆呢?我们试从《山本》的文本分析说起。在《山本》的艺术世界中,天、地、人,儒、道、佛,主流的与非主流的,革命的与非革命的等等因素复杂的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驳杂的民间生活世界,在这里涌动着与生存相关的历史冲突,与命运相关的悲悯情怀,与民间文化传统融为一体的人生态度和世界观。它是历史的、现实的,又是记忆的,在这一民间记忆的历史呈现过程中,能够感受和认识到历史的另一种面貌和人生情怀。历史的绝对客观性叙述在文学创作中是不可能的,不同的叙述角度可能会带来不同的历史情境和不同的情感思想力量。对历史的革命叙事所带来的可能是激情、反抗、英雄理想;对历史的启蒙叙事,可能蕴含着批判性的思想光芒;《山本》在民间记忆的呈现过程中,所看到的则是普通民众与历史生活纠缠在一起的实实在在的生命生存过程。正如贾平凹在《山本》的后记中所说:“过去了的历史,有的如纸被糨糊死死贴在墙上,无法扒下,扒下就连墙皮一块全碎了;有的如古墓前的石碑,上边爬满了虫子和苔藓,搞不清哪是碑上的文字哪是虫子和苔藓。这一切还留给了我们什么,是中国人的强悍还是懦弱,是善良还是凶残,是智慧还是奸诈?无论那时曾是多么认真和肃然、虔诚和庄严,却都是佛经上所说的,有了罣碍,有了恐怖,有了颠倒梦想。秦岭的山川河壑大起大落,以我的能力来写那个时代只着眼于林中一花、河中一沙,何况大的战争从来只有记载没有故事,小的争斗却往往细节丰富、人物生动、趣味横生。”也就是说,贾平凹的《山本》是进入到了民间记忆中的那些具体的普通人的生命中,去理解、感悟、认识那些历史中人的命运、生存过程以及与此相关的山川风物、江河草木。由此,那些在正史中记载的人物、事件,似乎换了一种模样,保安队,预备团,红军游击队,彼此之间的争斗都与具体人物之间的恩怨情仇、生死挣扎、生活伦理结合在一起,具有了鲜明的民间生活内容,那些参加保安队、预备队或红军游击队的人似乎更多的具有了个人的生活需要和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个人生活的选择,如保安队的阮天保去参加游击队是由于保安队被预备团打败后没有去处,阮天保杀死井宗丞的深层原因可能是由于井宗秀与他结下的家族恩怨;陆菊人对预备团长井宗秀深情相助源于两人之间的相惜相知而非政治性的选择,甚至保安队与预备团之间的战争,也是由于个人的恩怨所引发等等。这些人和人、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紧张而又错综复杂,其中有苦难与温暖、混乱与凄苦,更有着残酷、血腥、丑恶与荒唐,他让我们看到了丰富的、有血有肉的历史细节和历史的另一种真实,也就是民间记忆的真实。由如上作品的分析,我们可以对作为“审美形态的民间记忆”作一这样的概括:民间记忆指的是流传于民间的有关人类历史、生活、社会活动、文化等方面的记忆,有时成为一种潜意识或者通过传承,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有些融入到民风民俗的民间生活中,成为一种文化,有些进入到民歌民谣、民间故事传说等民间文艺形式中。这种民间记忆相对于正史或者知识分子的历史记忆而言,具有产生于民间、流传于民间的未经整理的特点,呈现了鲜明的人类生存和活动的印记,在文学作品中呈现出来时,又往往与作家个人的民间化思想情感相联系,构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审美世界。
二
在《民间记忆与〈老生〉的美学价值》一文中,我们曾对民间记忆的这种特点做过讨论,并认为《老生》对于历史的叙述是建立在这种民间记忆的基础上的,它以民间说书人的态度,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以往文学对中国现当代历史的叙述内容,《山本》也同样具有这一特点。在这里需要我们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民间记忆它不能自我呈现,作为审美形态的民间记忆是经过作家叙述的一个与我们相关的有意义的故事,那么激活民间记忆的有意义的思想情感力量是怎样的呢?
在贾平凹的《山本》中,这种力量首先体现在对于过往历史生活中人的命运的巨大同情和悲悯,这种悲悯的力量来自于民间文化世界所涵养的精神。在中国的民间生活里,儒、道、佛的思想影响是深刻的,在某种意义上它构成了老百姓的世界观及其对待人生的态度。虽然儒、道、佛的思想彼此之间有所区别,但都具有悲悯的情怀,孔子讲仁者爱人,孟子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都体现出对于人的生命的关怀和敬畏。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他们奉劝掌权者实行人道,让老百姓有安居之所,则有着对民众的关爱;这种悲悯的情怀在道家思想中则表现为对自然的崇尚,主张清静无为、反对斗争,提倡道法自然、追求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相处;佛家以大智大慧的胸怀和慈爱怜悯,同情苦海中的世人。这种博大的悲悯情怀,融汇在民间生活世界中,构成了普通老百姓为人处世的态度。这一点在中国的民间传说中也体现得极为鲜明,譬如“孟姜女哭长城”对民众苦难生活的深刻同情,就以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想象,表达了对人的生存、生命的巨大悲悯,这是来自于民众内心的一种力量,有着感同身受的同情和深沉的爱意。这种源自于民间文化中的悲悯情怀,是贾平凹长篇小说《山本》激活民间记忆中的历史生活的一种重要力量。在《山本》中,贾平凹写了残酷的战争和苦难的生活历史,但贾平凹在《山本》的后记里说,《山本》里虽然到处是枪声和死人,但他并不是写战争的书,那他写的是什么呢?他写的是苦难中的每一个人的生命以及面对这种苦难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品中的麻县长、郎中陈先生、宽展师傅、陆菊人几个人物形象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他们的存在使民间记忆中的生活有了一种深远的情感和思想的力量,连接着儒、道、佛的博大思想及悲悯情怀。麻县长为官一任,却身处乱世,既然不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他也就只能用手中的笔,记录他所钟爱的秦岭的人文地理,儒家文人改造社会抱负无法实现时的社会责任感促使他走向了另一种人生,其中包含了他对于现实的失望和对民众不幸生活的忧思;郎中陈先生显然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他以自己的智慧,点拨着苦难中人生的迷茫,化解着种种的不平和困厄;宽展师傅代表的则是涡镇人的生命救赎的力量。在小说中,花生问宽展师傅《地藏菩萨本愿经》中写的是什么内容时,宽展师傅在炕上用指头写到:“记载着万物众生其生老病死的过程,及如何让人自己改变命运以起死回生的方法,并能够超拔过世的冤亲债主,令其究竟解脱的因果经”。在宽展师傅写下的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在涡镇的动荡苦难生活中,一种巨大的灵魂救赎的宗教力量,闪现着悲悯慈爱的光辉。陆菊人是现实日常生活中的女性,她善良克己、乐于助人,在精神上与郎中陈先生、宽展师傅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陈先生让她明晓人事,而宽展师傅让她的心和菩萨联系在一起,她对井宗秀、对涡镇上活着的和死去的人,都有一种宽厚的仁爱之心,在现实生活中体现出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
《山本》中的宽展师傅,郎中陈先生,陆菊人等人物所体现出的这种悲悯情怀,使涡镇动荡、残酷、血腥的历史中有了一种美与善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使我们感受到历史中还有温暖,还有抹不掉的永恒精神抗拒着历史的沉沦和人心的丑恶。这是作为审美形态的民间记忆不能失去的美与善力量,这也是民间生活世界中的美好精神,如果没有这种美与善的力量存在,民间记忆就会成为琐碎的历史事件的记录,就会失去儒、道、佛文化所涵养的美好灵魂。正如贾平凹在《山本》的后记中所说:“《山本》里没有包装,也没有面具,一只手表的背面故意暴露着那些转动的齿轮,我写的不管是非功过,只是我知道了我骨子里的胆怯、慌张,恐惧、无奈和一颗脆弱的心。我需要书中的那个铜镜,需要那个瞎了眼的郎中陈先生,需要那个庙里的地藏菩萨”。他需要的这种精神是《山本》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所需要的一种精神。
贾平凹在《山本》的后记中还说过这样一段话:“那年月是战乱着,如果中国是瓷器,是一地瓷的碎片年代。大的战争在秦岭之北之南错综复杂地爆发,各种硝烟都吹进了秦岭,秦岭里就有了那么多的飞禽奔兽,那么多的魍魉魑魅,一尽着中国人的世事,完全着中国文化的表演。”表面上看,《山本》确实写的是动乱时代的战争和各色人物的表演,但实际上更是写出了世事演绎中的人与民间社会中的人心和对人心的思考。那些“尽着中国人的世事,完全着中国文化的表演”的各色人物有着怎样的人心呢?以上提到的宽展师傅,陈先生,陆菊人等人物的内心是高尚、善良、博大的,但另外一些人如阮天宝,井宗秀,井宗丞等人的内心则是复杂的、甚至是卑鄙的,贪欲、权力、自私,使他们的人性变得残酷、阴暗。这些人物也让我们看到了民间社会生活中非理性的生存冲动以及藏污纳垢的复杂性。井宗秀成立预备团的初衷是为了保护一方平安,但后来随着井宗秀权利的扩张,他已成为刚愎自用、不再关心百姓疾苦的拥权者;井宗丞参加革命,为了筹措经费竟然策划绑架父亲致其死亡,阮天保被井宗秀打败后投奔游击队,并非有高尚的革命信仰,而是为了寻一安身之地,后来他枪杀了井宗丞是为了报私仇和争夺自己的权利,等等。在这翻来覆去的风云变幻中,人心的残酷、险恶尽显无遗,又无不与人心的自私相关联。这样的写作也是对于民间文化中遗留的“出人头地”“权力崇拜”等问题的反思和批判,使民间记忆的历史叙述具有了思想的深度。由此可以看到,文学性文本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叙事方式,其思想力量是不能欠缺的,这也是文学文本审美性的要素之一。
三
与文学文本的审美性相关联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文学的呈现形式。我们说《山本》提供了民间记忆的审美形态,那么这个民间记忆的保持形式是怎样的呢?从文化的意义说,民间记忆的呈现形式主要是仪式关联和文本关联,这是借用扬·阿斯曼在《文化记忆》一文里中提出的观点,仪式关联是指一个族群借助于对仪式的理解和传承,实现文化的一致性,而文本关联是借助于对经典文本的阐述获得文化的一致性,具体到贾平凹的《山本》中,除了仪式、文本(对儒、道、佛经典著作的理解与阐述)之外,还应增加民间口头相传和地方志的呈现形式。民间记忆的这些保持形式进入到《山本》中时,是通过作家有意义的叙述完成的,因此民间记忆作为小说文本的审美形态,必然具有个人的审美趣味和思想情感,换句话说,当他进入民间记忆的历史中时,他所拥有的是社会的、时代的、民间的、集体的意识,当他从这种集体的意识中回到他自己,并且要呈现他自己所拥有的这种集体意识时,他对民间记忆的呈现形式与文化意义上的民间记忆保持方式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文学叙述的角度来说,贾平凹在《山本》中把民间的生活逻辑融入小说的叙事过程中,注重日常生活的细节以及琐碎的人物对话,同时又把这些细节与历史的变化结合在一起,达到还原生活真相的目的。这样的叙述方式决定了贾平凹的小说具有了“写实性”的特点,民间记忆在他的小说中与“经验性的真实内容”密切相关,这里所说的“经验性真实”并不意味着所叙述的内容他都经历过,而是指在小说阅读过程中读者所感受到的“经验性真实”,也就是说“我们为其真实感所震惊,我们也许根本想象不到我们翻开书页时会出现什么,但当它出现后,我们感到这是必然的——它抓住了我们历来所了解的,尽管也许是极其朦胧地了解的,经验的真实。”与这种经验的真实性密切相关的是作家在写作过程中对于“历史的客观性”和“人物故事的因果关系”的重视,这两点是保证文学作品“经验真实性”的基础。贾平凹为了这种客观性,陆续去过昆仑山、太白山、华山,去过商洛境内的天竺山和商山,搜集整理秦岭的动物记和植物记,搜集了二三十年代许许多多的传奇,这些资料涉及的人和事引起了他的创作冲动,他要把这些历史的素材写成小说。虽然小说中人、事、故事、情节与历史并不完全一样,但与历史构成了深刻、紧密的内在联系,成为文学性的“真实而又陌生的存在”,民间记忆的经验性真实由此得以产生。在小说文本中保持民间记忆“经验真实性”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小说中的人物、事件及其情节发展过程包含着一种自然因果观,“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然因果观意味着必须全面呈现影响生活的所有因素。正如奥尔巴赫所说,它表现‘被嵌置于一个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总体现实之内,而这一现实是具体的和不断演变的’。”具体到《山本》中就是人物和故事情节的发展结果都是有原因的,这种因果关系又是符合生活的发展逻辑的,譬如:麻县长生逢乱世无法实现造福一方的雄心壮志,才把自己的志向转换为对秦岭各种草木与禽兽的考察与记述;井宗秀领导的预备团伤害了保安队领导人阮天宝的家人,后来井宗秀的弟弟井宗丞在革命队伍中冤死于阮天宝的手中不能不说与此有一定的联系;陆菊人辅助井宗秀“成就大业”是因为两人是情感的、精神的知己,如此等等。这种事出有因的小说发展过程只要是合情合理的,即使我们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也会依据生活的经验逻辑认为“记忆中的历史”是真实可信的。《山本》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保持了“民间记忆”的经验真实性,这种经验真实是文学性的、审美的,与历史学家追求的客观、真实、科学性是有差异的。
其次,在文学叙述过程中的“民间记忆”还涉及到民间文化心理、民间信仰、集体无意识等内容,民间记忆在传承过程中,民众都会依据自己的文化心理进行某些演绎、改变,进而形成民间故事、传说等民间文艺形式,赋予人物超越人世的某种能力和力量,从而使民间记忆中的内容具有传奇性的色彩,这就是民间文化想象。在中国传统的民间故事、传说中,民间想象往往呈现出“万物通灵”、经验世界与虚拟世界融会在一起的特点,相信万物有生命和思想情感,常常把自然物神化或人格化;相信人、神、鬼之间的关系可以转化,人可以成为鬼、神,神、鬼也可以有人的思想和情感并且具有平常人不具备的超常能力。贾平凹《山本》中“民间记忆”虽然重在一种经验真实性的呈现,但也体现出这一民间想象的某些特点,他通过文学的文化想象,试图在天、地、人以及万物众生的内在关联中,看到彼此之间的意义关联,感悟到自然、人事变化的沧桑甚至是无奈与荒凉,特别是小说中出现的尼姑宽展师傅普渡众生的精神力量,医生陈先生洞察世事、逢凶化吉的能力,都与民间信仰、民间文化等精神性的内容相关,这种精神穿越尘世的表面生活,进入人心,使灵魂具有大善大美的力量。
最后,与这种叙事方式、想象方式相关联的是《山本》的语言。小说中的民间记忆是通过语言呈现的,《山本》的语言与琐碎的生活细节、人物对话纠缠在一起,是密集、鲜活、生动的,渗透着的民间气韵,这种气韵又具有浓郁的地方性特色,与秦岭的一草一木、山山水水、民俗风情融会相通,与他的叙述内容天然的融为一体,呈现出悠远、深厚的艺术境界。小说语言的这种地方性、民间性特点在今天是特别应该引起重视的,周作人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写过《旧梦》一文,在文中他提出在“世界主义”的文化背景下,应重视艺术上的“地方主义”,并且“相信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民’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正是这种语言的地方性、民间性呈现出文学的个性、审美性,也正是通过这种个性和审美性,在世界文学中确立民族文学的意义和价值。
作为审美形态的民间记忆的呈现是《山本》对新世纪以来小说创作的重要贡献,贾平凹以民间说书人的姿态,重构了秦岭那一方水土的历史生活,并在民间记忆中历史的叙述过程中表现出他的“史识”和情怀,与莫言、韩少功、张炜等作家的民间叙事有所区别,具有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力量。贾平凹自己说:“我就是秦岭里的人,生在那里,长在那里,至今在西安城里工作和写作了四十多年,西安城仍然是在秦岭下。话说:生在哪儿,就决定了你。所以,我的模样便这样,我的脾性便这样,今生也必然要写《山本》这样的书了”。这本浸透着贾平凹生命与灵魂的书,呈现着民间文化精神和地方性生活内容的小说也就必然以其独特性成为了新世纪文学中的重要作品。
注释:
①②③⑧贾平凹:《山本》,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523页、526页、526页、522页。
④参见《文化记忆理论读本》,阿斯特莉特·埃尔、冯亚琳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12年版。
⑤⑥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9页、62页。
⑦周作人:《旧梦》,载《自己的园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