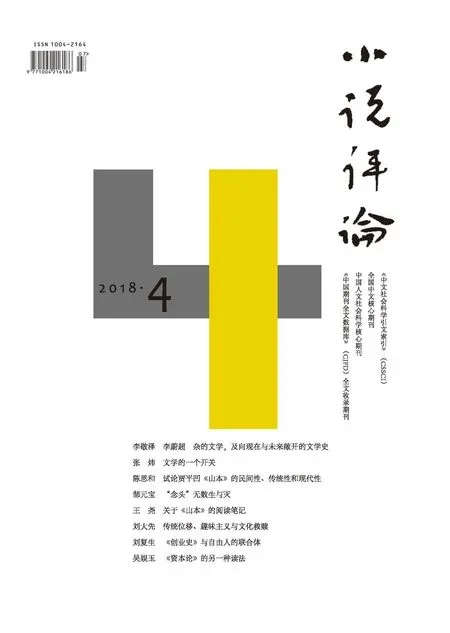文学版图的新拓展
——谈贾平凹长篇小说《山本》
陈思广 李雨庭
贾平凹是当代文坛中少有的几位横贯新时期且至今仍勤奋追梦的文学大家,也是一位笔耕不辍、不断创造文坛神话的文学奇才。也正因此,他的每一部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出版后都会引起文学界的强烈反响,也因之被称为“贾平凹现象”。2018年4月由作家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步出版发行的长篇新作《山本》,是他奉献给读者的第16部长篇小说,也是他酝酿多年立志要写的“秦岭志”。小说的出版自然引发了人们的强烈关注。在这部作品中,作家不仅浓墨重彩地书写了秦岭这方水土养育的子民们平凡、神性而又略带英雄色彩的山民性格,也细致入微地展示了秦岭一带山川草木、虫鱼鸟兽等奇异景观,令人眼界大开。小说以亘古苍茫的秦岭深处一个叫涡镇的地方为中心,以童养媳陆菊人的三分胭脂地为引子,以涡镇枭雄井宗秀和女杰陆菊人“英雄爱英雄,叔阳爱管仲”的惺惺相惜又渐行渐远的人生经历和命运结局为中心线索,在历史的动荡与沧海巨变中,将普通人的大志向演绎成平凡人生与命运的多重交响曲,亦由之勾连起秦岭腹地人事自然的纷繁变迁,显示出作家非凡的艺术才能。而作家在这场动荡的风云变幻中展现的秦岭儿女所特有的性情和气概,如陆菊人的睿智善良、郎中陈先生的圆融通达、地藏菩萨庙师父宽展的悲悯仁慈等,使小说在表现成王败寇的永恒定律中透出一种人道主义的温度和悲悯情怀。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与贾平凹同时代的作家开始逐渐由关注城市转向回归故土,并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乡土小说,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张炜的“芦青河系列”,叶兆言“秦淮河小说”,贾平凹的“商州系列”等,其中贾平凹的商州书写成为当代文学版图中一道温润而古朴的文学风景。虽然商州只是秦岭的一个点,秦岭却是横贯中国中部且东西走向的大山脉,被尊为华夏文明的龙脉。受秦岭庇佑的陕西人,更是自恃为龙脉的正统后裔。出生于秦岭深处的贾平凹自然对这一龙脉及其风情情有独钟,也被他不断地写进《商州》《浮躁》《怀念狼》《秦腔》《古炉》《老生》《高兴》等一系列作品中。通过对秦岭风土人情的深入摹写,贾平凹对秦岭的刻画和感情亦因之而越来越深入、成熟,越来越清晰、敬畏,并最终写就了这部细致、厚实、堪称全面展现秦岭人物山水、鸟兽虫鱼、神鬼礼俗的“秦岭百科全书”。《山本》不仅表现出秦岭人家的自然生态、经济营生、更表现出一种对人事、对历史的新认知,为当代文学的版图开拓了新疆域。具体而言,我们认为,其突破意义至少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用平淡冷静的笔调表现了身处秦岭山区地带的英雄人物的庸常生活,真实表现了出入于平凡日子的英雄的生与死,拓展了英雄人物描写的新视阈。“英雄”历来在人们心目中生得伟大、死得壮烈,也多是一种“神”一般的超凡存在。新时期以来,英雄开始由“神”回归到“人”,“凡夫俗子”式的英雄书写成为文学的常态:莫言《红高粱》中的余占鳌、苏童《米》中的端白、余华《许三观卖血记》的许三观等等,都以各自的人格样态去生存、去抗争,不卑不亢,表现出虽有英雄气概但仍不失为凡人的英雄品格。贾平凹对“英雄”的书写,也是遵从生活的本相,以回归历史现场的姿态书写英雄的成长足迹。无论是《浮躁》中不畏权势巧妙斗争锐意进取的金狗,还是白手起家奋斗立足城市后被名利腐蚀的庄之蝶(《废都》);无论是生于荒村而立志于出人头地的夜霸曹(《古炉》),还是以拾破烂为生却自诩比城里人高贵的刘高兴(《高兴》)……贾平凹笔下“英雄”的血性和烟火气越来越接近于普通人、身边事,越来越体现出英雄的平凡生活和庸常点滴。到了《山本》,贾平凹更注重用基层生活的磨砺来表现“英雄”的长成,在现实生活与七情六欲的日常细节中表现英雄的生存样貌,将“行动着的人”与“人的行动”表现得凡俗而朴实。作家用平淡的笔调书写秦岭深处的涡镇英雄井宗丞、阮天保和井宗秀,用日常的爱怨情仇、名利争夺来表现井宗丞、井宗秀等英雄的成长过程、人生选择和与众不同的性格气质,可谓真实自然。你看,为筹集游击队的经费,井宗丞让队友绑票自己的父亲,而自己却在成为威震一方的游击队领导之际被阮天保的护卫邢瞎子一枪毙命;井宗秀在龙脉护佑的心理暗示下步步为营成为涡镇最大的掌权人,为了巩固地盘和势力,他拉拢麻县长、火烧阮家宅、攻打保安团、建钟楼改造涡镇,正直事业稳定之际又被阮天保打死,死得悄没声息,甚至有些窝囊;而阮天保事事趋利避害,善于钻营,被井宗秀打散后投靠井宗丞,借游击队的势力保存壮大自己的实力,利用共产党的“反右倾主义”,除掉井宗丞,又利用井宗秀疏于防范之际结束了对方的性命,反成为涡镇沧桑巨变中的最大赢家。阮天保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实在出人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整个过程作者没有任何铺垫和伏笔,让一切变得自然而又平常。但正是这种“英雄”的平淡结局,才强烈地冲击了读者既有的英雄观念,解构了英雄必然轰轰烈烈的生与死的“历史必然”。作家让英雄回归到历史现场和生存本相中来,将他们视为与普通人一样都只是滚滚历史大潮中的一粒尘埃,与大自然的草木鸟兽一样,实实在在且又平平常常。这种回归本真的人生观、英雄观,还原了人在大千世界中的本来面目,也将生活的本相原原本本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对此,贾平凹坦言,如此处理是因为现实生活也往往是这样,很少有人死得轰轰烈烈,大多是或偶然或毫无意义就死了。贾平凹自觉地将英雄人物还原到历史和生活的本然状态,用新的历史观、英雄观来重新建构历史生活中的英雄,具体而微地展现现实生活中的人性百态,可以说,作家已经进入到了对人事书写“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至高境界。掩卷体味,《山本》实为“人本”,小说中的英雄人物的生死和秦岭的草木鸟兽一样,普通而又自然,而人生平平淡淡的终结何尝不是真真切切的生活样态呢?
2.用人物大量琐碎的日常生活细节,构成对历史的叙述与阐释,将宏大历史消解于鲜活生动的民间记忆中,拓展了文学新的审美形态。贾平凹在《山本》中对历史和人物的叙述,完全不同于传统小说中宏大历史视野里的帝王将相,也不同于新时期稗官野史的个人主义,而是关注历史的空隙与人物庸常琐碎的小细节,用活跃在历史小舞台上的非凡人与普通人的鸡零狗碎来表现中国动荡不安的大历史,使之成为整个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政治变幻的历史缩影。历史的崇高理想也就在这里化为生活的琐碎与庸常,成为一出出人生常见的正剧、喜剧,甚或悲剧。阮天成的保安队抢走了预备团的12只骡子,镇上居民都找陈来祥索要损失,陈来祥却像贼一样躲着不见,于是山民们也不在北门口抬石条垒门洞了,反都到皮货店来,有的拿皮子,有的搬家具,更多的人则说,陈掌柜,我们知道你拿不出钱来赔,我们也不强取硬夺,但我们就靠骡子过活的,现在没有骡子就只能在你店里。这里,没有同仇敌忾时的慷慨无私,只有各自为己的生活的法则与现实的诉求。保安队押着人质喊井宗秀投降,有家人在人质里的居民承受不了,咆哮大闹,几个妇女还拦着陆菊人要求她去给井宗秀说情,否则她们也不活了要陆菊人一起死。这里,同样也没有大敌当前时的同心同德,有的只是每个家人的私情与诉求。对改变涡镇世事的陆菊人的爱情、人生的书写,作家同样处理的稀松平常:父亲因为还不起杨掌柜的棺材钱将她嫁给杨家做童养媳,丈夫少不更事大大咧咧,陆菊人在失望哀叹中生下儿子剩剩,后来丈夫在诱骗阮天保时大腿中枪流血而死,儿子又从井宗秀的马上摔下来成了跛子后做了药店的学徒。她一心认为龙脉能成就井宗秀的人生,处处维护他的威严,为了让花生能配得上井宗秀,陆菊人教花生怎么做女人,怎么做饭,怎么行、走、坐、站,怎么对待男人,服侍男人的衣食起居,苦口婆心,事无巨细,简直就是秦岭地区的“女戒”。贾平凹用平实的观念,表现人物在世态人情、吃喝拉撒中的日常纷争,将历史的大事溶解于鸡零狗碎的泼烦的小日子中,让时间在琐碎的细节中凝滞,而宏大的时空和历史事件则被具化为涡镇人们为日常的生活诉求而引发的争权斗利的计较之气与生活场景。于是,所有的崇高与伟大、渺小与卑微,都是血肉之躯的喜怒哀乐与生活本相。《山本》以一种反史诗、反英雄的姿态,借助个体的生命体验和民间的认知记忆来表达对通常的历史观念和政治意识的灌输与反叛,表达了别样的历史的真实。所以,《山本》没有读者一贯所能感受到的那种宏大、震撼的历史和鲜明的性格与特殊的人物命运,他们只是涡镇五谷杂粮养育的平凡子民,纵然有强大的时间磨砺和命运之神的观照,也只能以一种平淡的、自然的本能存立于世,生死如草芥、如蝼蚁。作者将记忆中或知识库里的内容都汇集在了小说中,命运、时机、神谕、地利等等,很难说清是哪种力量主导人物的命运转折和历史的发展进程,或许这些都不是(就像龙脉也保护不了井宗秀一样),一切偶然就是必然,一切必然也就是偶然。从《秦腔》《古炉》《老生》到《山本》,贾平凹用日常细节激活被遮蔽的民间力量,重新唤起那个鄙陋又强大的民间本相,朴素而自然。正是作家对生命的存在与消亡、对政治历史风云变幻有了一种来自民间的大朴素和大悲悯,尘埃落定后,英雄与凡人的是非成败都是“转头空”,才使我们对历史有了新的认识,有了新的体味。这才是真实的历史,也是作家欲意给我们复现的秦岭的真实的历史。贾平凹写出了对历史的新感悟,当代文学也因之呈现出新的审美形态。
3.对秦岭山水、鸟兽、花木、神鬼、时令节庆、婚丧嫁娶、绝活土话的详细书写,扩大了当代文学表现的文学版图。中国乡土文学自20世纪20年代由鲁迅开拓以来,在乡村风情的展现上,自成一脉又各具特色,如沈从文倾心于对边城人性自然朴素的野趣描画,赵树理
侧重于对山西民间俗谚俚语的艺术转化,而汪曾祺钟情于“最后一个”的民间技艺的铺陈铭记;叶广芩、迟子建醉心于乡土风情与人物的性情交融,等等,都为中国乡土文学增添了别样的风景。而贾平凹对乡土的书写“立此存照”的意图十分明确,他用文字记录乡土在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衰落和消亡,尤其是那些被现代文明和科学渐至遗忘的民间艺术和信仰,在贾平凹的笔下开始复活起来。《山本》小说的构思与命名就是他为秦岭书志的欲望再现。因此,小说中关于秦岭的一草一木、一鸟一兽,作者都尽量详其物态、性状以及掌故传说,尤其是秦岭所独有的物种,作家更是不厌其详。作家痛惜痒痒树濒临灭绝,于是让它长在了陆菊人家的院子里;可以洗衣服的皂荚树成了“涡镇之魂”;饱含民间智慧和艺术的彩绘成了涡镇枭雄井宗秀的拿手绝活;预兆吉凶的蝙蝠和水鸟成为起承转合人物命运的先知神谕;用铁水耍火花的民间杂技,biangbiang面、醪糟酒、砖茶、金蟾、放蜂的营生、麻县长对草药和动物的习性的整理、宽展师傅做乐器尺八的方法、花生出嫁的规矩禁忌、陈先生开处方的药性与病人性情结合的原理等等,作家都不惜笔墨地予以展示,甚至不惜以大量的无关于情节发展的风物介绍作为闲笔,备忘录式地详细记录并且反复点染其奇特之处,使其成为斑窥秦岭博大深邃的文学窗口。可以说,贾平凹对秦岭的细致书写不仅记录了大山的地情地貌,更勾画了其独特的山水特色与风土人情。这当然关涉到作家对秦岭地域特性发自内心的喜爱和铭记,关涉到小说叙述艺术甚至文学创作问题。他已不是纯粹为了写作而写作,而是想把自己几十年积攒下来的对人生、命运的感悟塞入小说,所以,我们能够明显地看出,这部近50万字的《山本》似乎就是其对生命认知的一个总结:菩萨一样的寡妇、画匠、奋斗者、“阉割”者、智慧的民间星相大师、对未知世界的敬畏、对濒临灭绝的树木习俗的铭记等等,尽现其中。丰瞻的细节尽量照顾到方方面面,即便庞杂而琐碎也在所不惜。为使秦岭的风貌显得更为真切,他甚至用地方性土话语词、句法结构来体现秦岭儿女的一种生命情态。秦岭作为陕西人日常生活的特定性背景,成为贾平凹作品最容易辨识的身份印记,成为当代文学最为鲜明的身份印记。我们也因之可以说,《山本》是最秦岭、最民间、最中国的小说。
《山本》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风云激荡的历史充分具象化、细节化,以广袤的秦岭为背景,用琐碎的日常和普通人构成小说的血脉温度,以一种专注于细节的修辞姿态,摹写出秦岭世界的人间世象,挑战了既有的叙事思维和表现方法,实现了文学版图的新拓展,作家对历史和英雄的反传统书写不仅颠覆了人们的惯常认知,而且对历史的叙述展现出新的途径和审美性开拓,这无疑是贾平凹对当代文坛的新贡献。不过,我们也看到,在《山本》中,一些看似丰富的文学细节却有着似曾相识的感觉,人物的个性亦淹没在过于详细的日常叙述和无关紧要的人物闲笔中,这多少冲淡了主要人物也即是典型人物的描写。在叙述过程中,叙述者“抢话”甚至代替故事人物说话,语言不符合人物身份的干扰痕迹也时常出现,而作品中一些语言过于粗鄙化等,更大大妨碍了读者审美趣味的进一步生成。我们认为,这些出现在《山本》创作中的创作问题,也当引起贾平凹先生的充分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