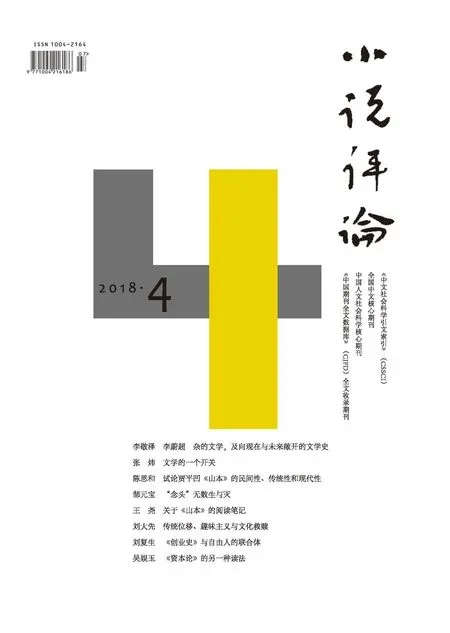“念头”无数生与灭
——读《山本》
郜元宝
一
《山本》全书过半,写1930年代初蒋冯阎“中原大战”时期,井宗秀统率的“涡镇”地方武装,从名义上隶属蒋军的预备团升级为隶属冯军的预备旅,兵强马壮,百废俱兴,遂拜陆菊人为“茶总管”,掌管全镇经济命脉。陆氏一直在幕后支持井宗秀,这时需要走到前台,生怕做不好,举棋未定,就征求公公杨掌柜的意见。
杨掌柜的说——
好不好你没做呀。我当年开寿材铺有个念头就开了,这不一开就十几年。他井宗秀没想过当旅长,如今还不成了旅长。陆菊人没再吭声。
陆氏又向神医“陈先生”讨主意。陈先生似乎隔空接过杨掌柜的话头,帮陆氏看清她最大的“念头”便是井宗秀。既如此,何不帮他?陆氏这才走马上任。
表面上陈先生敦促陆氏做了最后决定,其实杨掌柜的话更关键,看似随口说出,却点中要穴,陈先生不过进一步挑明杨掌柜的意思而已。杨掌柜的话既启发陆氏做事先须“有个念头”,有了“念头”便不妨大胆去行,同时也揭示了涡镇上下男女老幼共同的生存奥秘:他们都有一些主宰性的“念头”,汇聚起来,共同成就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山本》记录这一事业的始终,也描绘这些“念头”的生灭。
事实证明,所有“念头”皆“妄念”,不管执念之人起初何等决绝,何等殷勤,到头来都会适得其反,最后只落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就像如日中天的涡镇,在毫无防备的时候突然化为灰烬。
长篇小说《山本》犹如莽莽苍苍一座大山,读者可以从不同路径进入。比如“中原大战”期间蒋军、冯军、红军游击队、地方政府的军政实体(县保安队)、民间自发的武装(涡镇预备团)错综复杂的关系;比如类似“志怪小说”的各种奇闻异事的记述;比如秦岭地区的博物学知识;比如现代中国历史特有的地方性叙事(像井掌柜发起的“互济会”那样的民间团体);比如川、陕、豫交界茶、烟、盐等重要物资的商贸往来;比如该地区特有的交通、宗教、习俗、方言、山川形貌和气候特征;比如小说中几乎无处不在的那只黑猫的眼睛神秘的注视。所有这一切对理解《山本》都是必要而有益的。
但相比起来,杨掌柜的似乎随意拈出的“念头”二字更关键。《山本》的“世界”,成也因为这些“念头”,败也因为这些“念头”。“世界”的兴废系于“念头”的生灭。抓住涡镇人“念头”的生灭,才算取得打开《山本》大门的钥匙。《山本》是历史的演义,是人物的传奇,是一个接一个战争叙事的连缀,是博物学的炫耀,是宗教习俗和方言土语的大展览,是现代中国地方性知识的大聚会,但在这一切之上,《山本》更是始终关怀人物的心理世界,努力“显示出灵魂的深”的“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
二
杨掌柜的“有个念头”,开了十几年棺材铺,临死却没给自己留下一副棺材。
他儿子杨钟有个“我要飞”的念头,不问家事,沉湎于“轻功”之类驳杂的武艺,令妻子陆氏大失所望,他本人也因这“念头”死于非命。
阮天保怀揣无论如何也要出人头地的念头,总是不安其位。他从涡镇预备团出走,靠着心狠手辣做了县保安队队长,反过来围攻涡镇,惨败后摇身一变,又成了红军游击队的指挥官。他处心积虑谋杀井氏兄弟,像巨人踢平小孩积木一样轰毁“固若金汤”的涡镇,为被驱逐的阮氏一族报了血海深仇。小说并未交待阮天保结局如何。他全家被杀,即使像《老生》里的匡三做了军区司令员,也不过孤家寡人,活在别人的传说中吧?
被架空的麻县长无所事事,起了念头,在兵荒马乱中果然写成《秦岭植物志》《秦岭动物志》。但涡镇毁于战火,覆巢之下岂有完卵?麻县长只好丢了精心结撰的两本大著,葬身于黑白两河交汇而成的无底漩涡。
喜欢给人相面的赖筐子恭维井宗秀的干将巩百林,“你这圆胖脸好,我就跟着你!巩百林说,圆胖脸咋个好?赖筐子说:这话不能说,反正前途无量。巩百林知道赖筐子的意思,嘴里说这话你不敢再胡说了,心里却从此有了想法”。因别人随口一句话(或自以为得到某个征兆),“心里却从此有了想法”,涡镇这样的人岂止巩百林一个?巩一贯好勇斗狠,最后也死于无情的炮火。
土匪“逛山”也有“念头”——
逛山们手上都少一根指头,是经巫师念了咒用刀剁的。巫师有三人,都是神灵附体,能看天象,能抬桥。抬轿也就是用木头做成一个小轿状的箱子,两人闭了眼抬起来,把轿的一只脚不停地在一桌面上敲打画字,谁也看不见画的是什么字,但抬轿人知道,一个字一个字念出来,旁边的另一个人记在纸上,竟然都是顺口溜。他们凡是有什么人生病,神就开药方,凡是有重大决策,神就下指令,他们从来深信不疑。
所谓“抬轿”,大概就是“扶乩”吧。这样的“念头”来历不正,但逛山们“从来深信不疑。”他们会被这样的“念头”引向何处?不问也罢。
陆菊人并不供奉固定的神,但她敬畏瞎子陈先生和哑巴尼姑宽展师傅,凡事请教。她自己也很神道,往往心里临时设个局,比如看街上经过的人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以此占卜吉凶,解决疑难。虽然觉得这做法可笑,但事到临头还是这么做。她的神祗就在疑信之间发挥着奇妙的作用。
促使陆菊人接受井宗秀的邀请,毅然担任“茶总管”,表现出“王熙凤协理宁国府”的杀伐决断,除了上述杨掌柜、陈先生的启迪,还有一个“念头”很重要:她听人说自己是金蟾化身,能招来财运。这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小说开头第六节就写到陆菊人生下剩剩,“显得有些腰长腿短”,暗自琢磨“是不是我越来越要长得像个蟾蜍呀?”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等到井宗秀拜她做“茶总管”,自然又会想起先前那一闪念,似乎跟金蟾蜍果真有了几分瓜葛。
另外,悬壶济世、冷眼观世的陈先生有他的“念头”。哑口无言、惟以“尺八”抒怀的宽展师傅也有她的“念头”。小男孩蚯蚓崇拜井宗秀,立志要做他的随从警卫,他就受此“念头”驱使,整天围着井宗秀打转。涡镇人靠这些来历不同的“念头”活着。他们需要这样的“念头”。没有“念头”就没有生活的动力和方向。再不济,走到皂荚树下面看是否有皂荚掉在自己头上,也是好的。各种各样的“念头”,才是《山本》实际的主人公。
三
陆氏最大的“念头”,还是被陈先生说中的她对井宗秀的那份执念。
陆菊人怎么能想到啊,十三年前,就是她带来的那三分胭脂地,竟然使涡镇的世事全变了。
小说开头第一句话,覆压全篇,可为全书之冠。
当然,改变涡镇世事的并非陆菊人陪嫁的那三分胭脂地,而是“赶龙脉”的风水师在这块地上所作的试验让陆菊人相信,“这地方好,能出个官人”。她不愿给杨钟做童养媳,然而从爹手里要到这三分胭脂地做陪嫁之后,便“心系一处”,坦然嫁入杨家,希望风水师的话应在杨钟身上。
杨钟的所作所为很快令她绝望,她就寄希望于“骑门生”的儿子剩剩。不料就在她做月子时,杨掌柜竟自作主张,将那三分胭脂地无偿让给“老交情”井掌柜的儿子井宗秀,让他埋葬一直“浮丘着”的父亲!
陆菊人知道公公大错铸成,无力回天,懊恼欲死,但慢慢还是给自己转过了弯子。她认定杨家和这“好穴”缘分浅。轻易转给井家,乃是命中注定。于是索性听从命运的安排,把希望从杨钟、剩剩身上挪开,移向杨钟的发小井宗秀。从此以后,陆氏一心所系就全在井宗秀那里了。
但她舍不得立即将秘密和盘托出,起初只肯暗示井宗秀,那“可不是一般的地”,“以后就看你的了井宗秀!”直到最后才将谜底揭开。
由此也就开启了陆菊人与井宗秀之间奇诡别扭的一段情缘,贯穿《山本》全书。他们不是夫妻,但感情的牵扯胜似夫妻,然而又发乎情,止乎礼义,行动上从不越雷池一步。维系他们的不止是普通男女之情,更是对于关乎涡镇生死存亡却又不可泄露的天机的共同守护。
但陆菊人毕竟是善于怀春的少妇,她心系井宗秀,固然是对命运的顺从,却也难免发生男女的情爱。每次想到井宗秀,或听到他的消息,总是禁不住心跳加速,脸红耳热。得知井宗秀迎娶孟家女儿,她甚至产生了一阵难以遏制的嫉妒之心。为了摆脱这种危险关系,他不得不回过头来正视自己与杨钟的夫妻情谊,尤其在杨钟死后不断提醒自己其实也是爱丈夫的,而丈夫也是爱自己,并且确有几分可爱之处。其次,她在井宗秀设计谋杀了孟氏长女之后,很快就为他物色到美丽纯洁的花生,用今天任何一个女权主义者都会气歪鼻子的男性中心主义的一套哲学精心加以调教,最后一手安排他们成亲。“花生”者,化身也。既然自己的化身做了井宗秀合法的妻子,陆菊人也就可以金蝉脱壳,彻底走出她和井宗秀那种随时可能越轨的危险扭结。他们之间终于成功地定格为乱世英雄与红颜知己之间一种超脱性爱的男女情谊。
井宗秀也是钟情少年,起初因为只得到一点朦胧暗示,总是懵懵懂懂,徘徊于差一点就要捅破窗户纸、差一点就要向陆氏表明心迹的边缘。但他毕竟灵性过人,知道自己在陆氏眼里绝非凡品,也模模糊糊知道陆氏所望于他的并非普通的男女私情,于是就强迫自己转移方向,频频从别处感知和验证他的超凡脱俗,比如他的男生女相,白面无须,背靠虎山,天生属虎,后来还得了一个能预知前事、听懂禽言的“神人”周一山做军师,益发觉得自己不同凡响。等陆菊人将三分胭脂地的谜底和盘托出之时,他反而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了。
井宗秀果然凡事顺利,如有神助。涡镇百姓渐渐也认定他是神人下凡,是他们日思夜想,感动上苍,特派来做保护他们的“官人”“背枪的人”。
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涡镇期待井宗秀这样的“英雄”统领一方,保境安民,虽不比犹太人的盼望弥赛亚降临,又如《孟子·公孙丑下》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中必有名世者”那种巨大的“悬念”,但也约略近之。
通过陆菊人和井宗秀的不懈努力,他们共守的“天机”终于成为全涡镇人“念头”隐秘的核心。无数“念头”围绕这个核心汇聚起来,化作伟大的意志,果真令涡镇辉煌于一时,俨然独立王国。
但这个“念头”的集合,既将井宗秀抬上神坛,也让他悄悄走向自己的反面。他变得越来越阴鸷,冷酷,越来越疑神疑鬼,越来越高调张扬,越来越刚愎自用。他滥用酷刑,铺张浪费,连陆菊人的话也听不进去,最后竟然发展到随便将马鞭挂在人家的门环上,强迫涡镇女子像嫔妃侍候皇帝那样侍候他。至于以保境安民的名义横征暴敛,更是理直气壮。稍遇抵抗,便痛下杀手,毫不宽容。他就这样被自己的“念头”带领着,一步步从涡镇的保护神演变为涡镇独立王国的暴君。
这个独立王国由陆菊人的“念头”催生,也在陆菊人眼中轰然倒塌。小说结尾写陆菊人对井宗秀的尸首喃喃自语:
事情就这样了宗秀,你合上眼吧,你们男人我不懂,或许是我害了你。
这与开篇第一句话首尾呼应。并非“成也陆氏,败也陆氏”,而是井宗秀及其伙伴们在涡镇揭竿而起的事业,因陆氏带来的那个为官作宰逞英雄的“念头”得以轰轰烈烈的开展,也因这个“念头”的驱使而慢慢背离初衷。既然以井宗秀为首的涡镇人所要完成的惊天事业起于一个女子的“念头”,一旦该女子从她自己的“念头”觉醒过来,所谓惊天动地的伟业必然烟消云散,就连承载这“念头”、为这“念头”奔波厮杀的无数生命,也要来于尘土,归于尘土,只有“一尽着黛青”的秦岭,永远显现着它无言的存在。
看《山本》,最吃紧的一点是作者毫不吝啬笔墨,巨细无遗地书写无数“念头”的兴起与消散。哪怕短暂如朝露、几分钟后就要奔赴黄泉的芸芸众生,只要各各显示其“念头”,都会恭恭敬敬一笔一画写下他们的名和姓。
但作者怎样静心静气认真繁复地书写这一切,最后也要怎样无情而迅捷地将它们一笔勾销。涡镇“世界”建造的用心与毁灭的随意对比越强烈,人生和历史的况味也就越是深厚。
四
英雄如何在红颜知己的注视中兴起于草莽,创下功业,最后又如何在红颜知己的注视中无可奈何走向失败,这种叙事模式在中外文学史上屡见不鲜。
已婚女子不在乎自己的丈夫,心心念念系于另一个已婚男人,却又并不发生肉体接触,甚至并无一般男女私情,而仅止于彼此的好感与互相的关切,这种现象过去也有不少作家写过,比如李劼人《死水微澜》里天回镇杂货铺老板蔡兴盛的妻子邓幺姑(蔡大嫂)与袍哥小头目罗歪嘴就是这种关系的一个典型。
但陆菊人与井宗秀的关系,和邓幺姑罗歪嘴只是表面相似,内容完全不同。陆菊人井宗秀式的男女关系是贾平凹的独创。一定要为这种独特的男女关系的描写寻找类似的作品,也不必舍近求远。贾平凹1983年创作的中篇小说《鸡窝洼的人家》就有非常近似的男女关系的设置。那个让回回和烟峰、禾禾和麦绒两对乡村年轻夫妇重组家庭的原因也是他们各自所怀的“念头”。烟峰对丈夫回回的发小禾禾的信任,麦绒对丈夫禾禾的发小回回的钦佩,很像陆菊人对井宗秀的情愫,只是《山本》写得更饱满,更酣畅恣肆。
贾平凹还有一个短篇《美穴地》(1990),写风水先生柳子言一生为人找“好穴”,办法也是插根竹子来验证,差别在于《山本》中“赶龙脉的”看竹子冒不冒泡,柳子言则看竹子是否发芽。柳子言、姚掌柜、四姨太和土匪苟百都之间的故事,到了《山本》也被大幅改写,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了。但一人怀着“念头”对另一人寄寓希望,这念头和希望又来自某个不可泄露的天机,仅此而言,《山本》和《美穴地》也可谓一脉相承。
表面的相似也就到此为止。《山本》的可贵在于它显示了作者独特的历史意识,这种独特的历史意识是《鸡窝洼的人家》和《美穴地》所不具备的。因此,最好还是拿同样写历史的《古炉》《老生》跟《山本》比较,才更能看出《山本》的特点。
《山本》书写的历史时间集中于1930年代,空间收缩于秦岭南麓一个虚构的小镇,主体是小镇居民以及他们的子弟组成的地方武装。这就和专写“农村文革”的《古炉》区别开来,也不同于从1930年代陕南(秦岭)游击队写到土改、土改之后以及改革开放直至华南虎事件、“非典”恐慌的《老生》。《老生》展开了“一百十多年”的历史,《山本》则将历史时间压缩为短短的几年。但《山本》和《老生》的内容毕竟有部分的重叠,因此不妨多说几句。
《老生》第一个故事,讲老黑、李得胜、雷布、匡三等陕南(秦岭)游击队员的往事。这些人在残酷战争中都牺牲了,只有匡三活下来,到了延安,官至军区司令,并一直活到非典肆虐的新世纪初。匡三在第二、第三、第四个故事中很少出场,但他在人们传说中的魅力无人能比。匡三(还有十数家与他有关且执掌大权的亲戚下属)发挥着巨大的社会影响,成为革命和后革命时代所有传奇故事的主角和全书的灵魂性人物。
第二个故事讲秦岭南麓岭宁县城一度迁移到方镇,后来败落成一个村子叫老城村,解放后跟匡三有亲戚关系的农民白河的儿子白石做了副乡长,胡乱任命游手好闲的马生做农会副主任,另一个符合“既年轻又穷”这条标准的洪拴劳作了主任,老城村在这两人领导下,上演了一幕幕土改闹剧和惨剧。主角马生劣迹斑斑,胜过《古船》中那个凶狠的赵多多。
第三个故事写三台县过风楼镇(后改公社),由全县闻名、“工作能力强”的“老皮”做书记,他带领酷爱政治动员的宣传干事刘学仁、惟老皮马首是瞻的棋盘村村长冯蟹、变相劳改单位砖窑厂负责人阎立本一干人等,以匡三司令曾率部在本地作战、本地属革命老区、“咱们都是游击队的后代”为名,将过风楼公社统制得严严实实,也上演了十七年至文革许多闹剧和惨剧。
第四个故事讲“当归村”村民祖祖辈辈挖药材为生,都是“半截人”(腿短且罗圈的侏儒),其中有个匡三部下“摆摆”在游击队初期战死,一直未被追认为先烈,儿子“乌龟”做了一辈子皮影戏签手。乌龟的儿子戏生这一辈时来运转,得到匡三司令亲戚、镇干部“老余”的帮助,以“老区”和“革命后代”的名义不断争取政策扶持,千方百计脱贫致富。可惜心术不正,方法不当,屡败屡战,屡战屡败,最后全村毁于一场瘟疫。
相对于《老生》写秦岭“一百十多年”大历史的宏愿,《山本》只写了相当于《老生》“第一个故事”即“陕南(秦岭)游击队”一小部分的故事,主角也从游击队(红军)置换为“涡镇”村民自发组织的预备团(后扩大为预备旅)。历史时段的压缩和历史主体的置换,直接的效果就是大幅度拉开了文学和历史的距离,让文学挣脱历史的牵制,作者因而可以放开手脚,尽情探索历史深处的人性。
《老生》写终成正果的匡三司令员及其庇荫下的革命后代如何坐镇一方,治理一切,好比《史记》写王侯将相发家史的《世家》以及与之连带的《外戚列传》。这样的书写指向明确的历史真实。《山本》则将井宗丞的游击队仅仅作为背景和陪衬,腾出手来主要讲述轰轰烈烈起事最终又无可奈何失败的涡镇“英雄”井宗秀及其同伴们的传奇,类似《史记》记录秦汉之际一个关键的英雄失败故事的《陈涉世家》。《陈涉世家》遭到后世“正史”裁汰,《山本》的书写也不会收入正史,它关注的只是虚构世界那些男女老幼在历史长河中一闪而过的无数“念头”,——恰似陈涉的“鸿鹄之志”及其伙伴们的“燕雀之志”的生与灭。
倘若把历史比作疾驰的列车,《老生》写的是这辆列车的钢铁外形和乘客们的喜怒哀乐,《山本》则不仅写到历史列车的钢铁外形和更多乘客的悲喜故事,还进一步写到这辆列车如何以乘客们无数的“念头”(无数的“鸿鹄之志”与无数的“燕雀之志”)为烧料,日夜焚烧,熊熊烈火驱动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换言之,《山本》不仅描绘了历史的巨大身躯,以及在历史中扮演各种角色的大量旋生旋灭的人物,还为历史发展找到了如黑炭一样燃烧过后即灰飞烟灭的人性与精神的能源。
五
既然由《山本》牵出了《鸡窝洼的人家》《美穴地》《古炉》《老生》这四部作品,不如索性再说说近二十余年来贾平凹基本的创作轨迹,从这个背景再来看《山本》。
1993年《废都》掀起轩然大波,贾平凹本来可以一鼓作气,继续书写他的都市体验。但围绕《废都》的争议使他陷入徘徊和犹豫。《怀念狼》(2000)、《病相报告》(2002)、《高老庄》(2006)就是在这段徘徊犹豫期创作的苦苦纠缠于城乡之间的作品。这以后他似乎摆脱了城与乡的纠葛,不打算再去正面描写自己生活于其中的都市,也不打算再去正面描写自以为居于历史潮头与社会中心的都市人了。
唯一例外的是《高兴》(2005-2007),让拾破烂的故乡“棣花人”走街串巷,登堂入室,一瞥都市的光怪陆离。但也不过一瞥而已,主角不再是都市和都市人,而是偶尔来到都市却又注定要离开都市(或死在都市)的农民。
《高兴》之后,贾平凹终于坚定地将目光转向故乡以及跟故乡一样落后荒僻的中国其他乡村的现实与历史,交错地陆续写出《秦腔》(2003-2004)、《古炉》(2009-2010)、《带灯》(2011-2012)、《老生》(2013-2014)和《极花》(2015)。
在现实题材方面,既有《秦腔》那样直面乡村社会矛盾又注重乡村历史(两代干部政治沿革)的结结实实的“大长篇”,也有本着“不妨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份社会记录”的想法而创作的《高兴》《带灯》《极花》等基本围绕某个单一事件展开、紧贴现实却又简捷轻灵的“小长篇”。
历史题材方面,则一浪高过一浪,连续推出专门叙说“乡村文革”的《古炉》,见证1930年代“陕南(秦岭)游击队”到土改、土改之后以及改革开放以至当下“一百十多年”的《老生》,再就是最近这部《山本》(2016-2017)。
贾平凹《废都》之后上述九部现实题材的长篇和三部历史题材的长篇构成一个巨大的文学存在,读者(包括长期跟踪贾平凹创作的学者批评家)实在不容易将这巨大的存在放进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框架来从容打量。中国当代文学似乎因为贾平凹的存在而发生严重撕裂。面对文化传统与现实生活,历史传说与当下社会,正在消失的穷乡僻壤与似乎凯歌行进的都市,贾平凹执拗地抓住前者,断然无畏地任由后者遗落在视线之外。从这点可以看出,他的性格诚如他本人所说,“不大了解的以为是温顺,其实很犟的”。
贾平凹这种“很犟的”选择意味着什么?
他果真只挂怀于中西部的穷乡僻壤,对“东南沿海”城市现代化漠不关心?
他果真认为商洛、秦岭既是中国的地理中心,也是中国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文化中心?
他果真有“三秦文化”的优越感而鄙视“东南沿海”的时尚文化?
他是否一脚踏进了历史殿堂,沉迷于遥远漫长的古代,不再关心纷杂喧闹的当下?
诸如此类,是任何一个关心贾平凹和中国当代文学的读者都想追问并希望获得答案的问题。
如何解答这些问题?简单地说,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作家什么都写,什么都能写,什么都写得好。任何一个作者,无论他视野多么宽阔,目光多么深邃,也只能看取宇宙人生的一角。关键要研究他所看取的那一角是否能够帮助我们合理地想象宇宙人生的其他部分乃至全部。贾平凹执拗地写商洛农村,现在又由《山本》而拓展到整个秦岭山脉,对“东南沿海”而言,当然都明显偏向“往古”与“落后”,但那不正是客观真实地存在过或存在着的现实中国的一部分吗?
70后、80后、90后作家们专心叩问国人在都市化进程中的生态与心态,绝大多数无暇也无力顾及更广大的乡村和更悠久的历史。这些青年作家甚至对自己身处的都市也并不怎么关心,而一味沉湎于科幻、玄幻、穿越、虚拟的时空。为什么我们对这个现象熟视无睹,视为当然,反过来却对贾平凹历经多年自然形成的创作侧重大惊小怪?是否我们潜意识里也都认定,只有都市化才是真正的现实,而被都市化、全球化、高新技术、虚拟时空抛在后面的广大乡村和悠久历史皆是虚构之物?
说到文化优越感,更是容易迷惑人、欺骗人的一种假象。
贾平凹小说确实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文化和古代文化的气息。不说别的,其纯熟的文言和方言的杂糅,就是这两股气息的显著表征。但贾平凹对乡村和古代一再投去深情的目光,同时不也一再为其中充满的愚昧、落后、野蛮、血腥、嗜杀、冷酷、暴躁、自私、小气、贪婪、肮脏、荒谬而痛心疾首吗?《山本》中大量杀戮的场面,大量算计,阴暗,变态,暴戾,恶毒,仇恨,迷狂,疯癫,不都发生在贾平凹创作所侧重的乡野与往昔吗?他何曾有过什么古代文化或乡野文化的优越感!
他只不过想提醒生活在都市的读者不要忘记,古代文化是我们另一个时间维度上的存在之家,乡村文化则是我们另一个空间维度上的存在之家,这两个“家”发生过或正在或将要上演的一切,无论善恶美丑,都与高速行进着的都市息息相关,它们共同构成了都市文明的根基与底座,至少可以为都市文明提供一面最清晰的镜子。贾平凹的现实题材作品不必说了,他的历史题材的小说,比如历史时段和历史事件都十分明确的《古炉》,见证多个历史时期的《老生》,都很容易和我们的当下对接,而《山本》里无数涡镇人生生灭灭的“念头”,即使从未到过秦岭的“东南沿海”许多都市的读者,不也十分熟悉,而很少感到全然陌生与不适吗?
如果完全遗忘和无视遥远的古代、最近的历史和其实一直近在眼前的广大乡野,当代中国所谓都市文明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就好像一个没有四肢和身躯而只有头颅的怪物,顷刻便会失去起码的真实性。
展示空间的宽阔绵延,见证时间的漫长流逝,强调文明的多层多元,探索人性的丰富深邃,坚持文学的独特个性,这是贾平凹一直努力的方向。读《山本》,我们又一次感受到贾平凹这种坚持不懈的努力。
注释:
①本文引用《山本》原文,皆依据贾平凹著《山本》,作家出版社2018年4月第1版。
②鲁迅:《〈穷人〉小引》,《鲁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第106页。
③贾平凹:《我和高兴》,长篇小说《高兴》的《后记(一)》,作家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440页。
④贾平凹:《序——给责编的信》,散文集《天气》,作家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