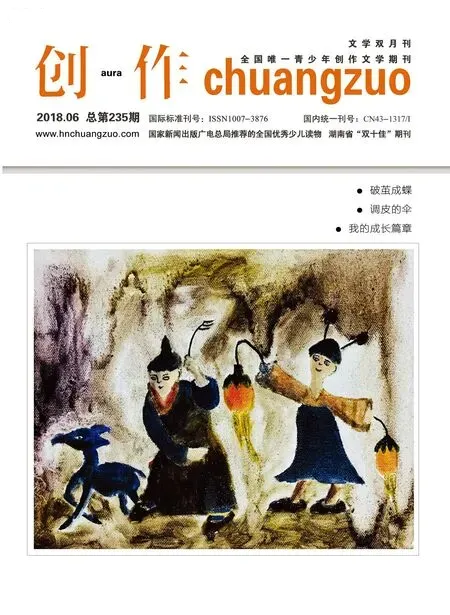行走在消亡中
作者:黄嘉仪
学校:长沙市一中
“你一天做的得了几把伞啊?”
他的手在竹间翩飞,一旁贩卖陶艺的老李看得入神,泥巴吧嗒吧嗒地掉到地上,成了个小小的泥洼。
“三天一把,十五元。”他从布套里掏出卷好的烟草,放在嘴里叼着,风吹过。
“……”
树一定要质地坚硬,竹子一定要老熟,桐油一定要熬一整天,伞衣一定是界头乡的棉纸,粘伞衣的一定要是纯天然的塔枝油,伞骨、伞头和伞眼都要有三十竹签车出来……他执着些许分叉的毫毛笔,自己绘彩花,刷清漆,每个工序都亲自过手,也只能他自己来。
“老人家,您这伞怎么卖?”来了个梳背头的中年人。
他瞥了瞥,拇指摩擦刨下的竹青,从身后取出昨天完工的油纸伞,仰起脑袋把漏在手上的油蹭到裤上,零零星星的油渍落下,“十五元一把,下雨天打出去,执起伞把子,回到家轻轻转一圈,雨水就能飞走。”他摸摸后脑勺,再憋不出话来。
“老人家,您给我套五十把。”肥大的手指朝他晃了几晃。
“哟,俺哪儿找去,你这不耍嘴子呢,先拿五把凑合。”空中浓黑默默的腾生,余晖照得背头脸上的横肉油光溢彩,“那自然是极好的,都拿来,都拿来!”他一层一层的拿报纸包好,颇为缓慢地递过去,沉甸甸的油纸伞—一张百元钞票瘫软在地上“老人家,别找了。”
背头拈着伞把,眉毛轻微地皱了一皱。软绵绵的猩红的钞票。
他弓着身子坐在堂前的木札上,叼着卷起好的烟草,锅里炖着浓郁的桐油,咕噜咕噜炸裂开来,散落的木竹屑,堆积在屋里让人无处落脚,他使劲眯着眼睛,滋滋的火舌潦落地舞动,抵挡不过这席卷的黑暗,索性他闭上眼去,顺着伞架边缘次第将棉线埋下。风穿堂而过。
“老人家,这油纸伞乃中华之瑰丽物也,不如你我二人携手将它发扬光大,您意下如何?”背头大清早的到来让堂内狭小了许多,横梁上悬着大小不一的油纸伞,绽放,延展一篇篇清丽隽永的诗,道是无情却低吟几代人的历史沉浮。他不知道背头在嘀嘀咕咕个啥,拍拍身上的粗布衣,抖抖密匝匝的竹青,“俺以后给你供货可以,不过俺三天才做一把,你要等得。”想再说什么,又憋不出了。桐油翻涌,热气腾升,背头直勾勾地盯着老人,哈着腰,提起嘴角“这都好说,自然依您。”空气回归寂静,风轻悄悄地。
背头买断了他的伞,钱三七分,给他三十,背头的买伞快得很,每每催得紧。可忽地从哪天起,背头来的没那么勤快了,老李还说有个什么高级玩意儿在偏僻的后山头,吵得很,他叼着烟,树窸窸窣窣。
晌午,机器在后山头轰隆作响,像野兽用槽牙碾碎骨头的声音。好家伙,忒大一个铁疙瘩,他还从未见过,来不及惊叹定睛一瞅,这不是油纸伞嘛!“老人家,你听我一劝,这机器伞和手工伞模样无二,成本又低上三倍,说它是手工的,卖价不会低,对你我都有好处,岂不快哉!”背头满脸堆笑,他腮帮子一鼓一鼓的,黝黑的脸涨得赤红“你在这瞎讲个什么玩意儿,就这坨铁疙瘩?做油纸伞?你甭说笑,哼!先别说它不会描花,它熬油都不会,呸!机制伞!”他在空中挥舞着拳头,大声嚷嚷,机器一阵阵的发出巨响,背头也不争论什么,端起茶装模作样的划动着茶盖,笑嘻嘻地看着他,他有时都听不见自己在说什么,感觉声音打在棉花上,沉闷闷地。最后他站起身子往那富丽堂皇的桌子很狠狠地砸去,甩开凳子就走,空气燥热沉闷,迎头就给他来了一棒子,他头也不回就走了。
后晌,他照例从草屋中捣腾出那些做伞的老家伙,每一样都用油墨报纸包好,给捋得服服帖帖。肩胛上挎着旧板凳,斜歪着身子提着没卖完的伞,在拐弯落下脚。他有一声没一声地吆喝着,远处半圆红日散发余热,沉入灰青的老街里,他回到那油黄的长板凳上,吸足了气,振臂一呼,娴熟地架起伞骨,全然忽视了匆匆寥落的行人,一手拉着钻头,一手握住伞骨打眼,双手的力度拿捏得恰到好处,长满老茧的双手并未失去灵巧与协调,孔武有力的臂弯缠绕着棉线,动作之快令人眼花缭乱。不久老人的小摊前,便里三层外三层了,老李常帮着点,两人忙得团团转,一把十五元。
背头这边也还好,还有几只麻雀常来光顾光顾。
后来不知怎的,人们渐渐地也不在他摊前晃悠了,也好,慢工出细活,不用那么赶了,他脚底生风,穿过堂去,把锅底灰和草木料用木椎子凿磨着,灰绿渐渐晕开,浸覆了石碗内槽的老痕。坐了老一会儿,抄起木扎“走咯,去卖伞勒。”走着走着,有些细细碎碎的声音传入耳朵“我说他怎么卖那么便宜,原来是机器伞。”
“就是,看起来没什么两样,可一细看啊,那真正是商场里的别致。那才是纯正的手工伞!”
他坐在那个拐弯的地方,老李也陪着他坐,一下午,再没一个人来。
他从兜里摸出一卷烟草,小口小口地嘬着,自言自语地说着“树一定要质地坚硬,竹子一定要老熟,桐油一定要熬一整天,伞衣一定是界头乡的棉纸,粘伞衣的一定要是纯天然的塔枝油,伞骨、伞头和伞眼都要有三十竹签车出来……”
后来人们再也没有见过他。
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