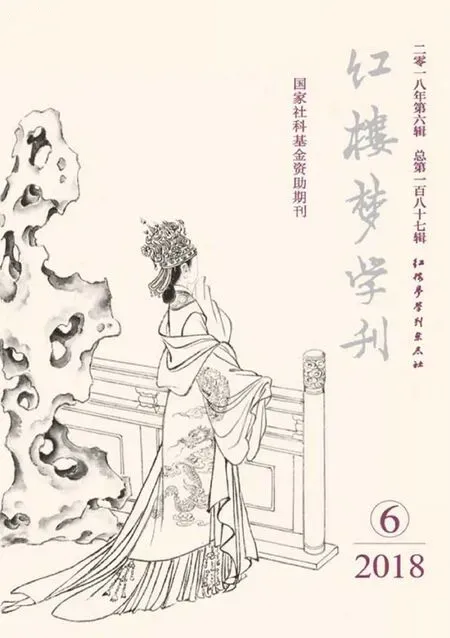《读红楼梦质疑》考论
——兼及民初旧派小说家的《红楼梦》接受问题及相关反思
内容提要:《读红楼梦质疑》初发表于《小京报》及《民国日报》,后易名为《红楼梦质疑录》发表于《小说新报》,撰者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姚民哀,其批评方式接近“评点派”,而又专注发掘《红楼梦》的叙事缺陷,时有独到之见。《读红楼梦质疑》是《民国日报》各种涉红文献中较为完整的一种,也和《民国日报》中普遍的论红观念一样秉持了《红楼梦》的小说解读立场,风格鲜明,尤其对于“索隐”的态度在今日看来可谓清醒,但在“五四”的时代变革大背景下仍是无法做到实现突破、引领潮流。
上海《民国日报》的文艺副刊是中国近代小说研究富矿,荟萃了一大批小说作品以及若干“小说话”,其中与《红楼梦》直接相关又具有一定规模的是《读红楼梦质疑》专栏。迄今为止,《读红楼梦质疑》不见著录于《红楼梦书录》、《红楼梦资料汇编》(一粟编)、《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等资料性质的著作,仅有一篇学位论文因专门研究《民国日报》文艺副刊有对《读红楼梦质疑》一笔带过、未加分析。本文即对《读红楼梦质疑》展开讨论,并试图择取《红楼梦》接受研究的更广阔视角审视其价值。
一、《读红楼梦质疑》的作者问题
《读红楼梦质疑》于1919年1—5月间时断时续地连载于《民国日报》副刊——《民国小说》,其具体刊登日期分别为1 月17、18、21、23、26、27 日,2 月24、26 日,3 月13、14日,5月11日,撰者署名“冷佛”,有时又作“佛冷”。若要经由“冷佛”稽考撰者名氏是比较困难的,单从字面来看,易联想到近代满族作家、创作《珍珠楼》《春阿氏》的王冷佛。王冷佛虽也活跃于报界,然而他作为北方小说家,与南方的《民国日报》似仍有距离,所以王冷佛除去名号相符,并没有其他证据支撑,便无法排除其他作家以“冷佛”为笔名的可能性。同样在1919年上半年,《读红楼梦质疑》亦连载于《京报》附刊——《小京报》,比较同一条目的刊登日期,一般《小京报》比《民国日报》更早几日,知《读红楼梦质疑》应首发于《小京报》,《小京报》中《读红楼梦质疑》又出现“关冷佛”“关璞”等署名,均身份难考。好在其后,《小说新报》1921年第3、4两期刊登了“民哀”的《红楼梦质疑录》。比较《红楼梦质疑录》与《读红楼梦质疑》,可发现其内容大体一致,变易幅度较小,又因《红楼梦质疑录》后出,大可视其为《读红楼梦质疑》的“修订版”。不同于“冷佛”“关璞”,“民哀”身份不难板上钉钉地判定为常熟小说家姚民哀。从《小说新报》方面来看,姚民哀本是其中“高产”的撰稿人,发表了醒世小说《金钱与爱情》、哀情小说《玫瑰花之惨史》、滑稽小说《一梦三千年》、家庭小说《切肤之痛》等各类题材约计可达30篇之数的小说以及其他类型的作品,多数情况下署名“民哀”,有时直接署为“姚民哀”。从《民国日报》方面来看,姚民哀同样在副刊《民国小说》中大量发表作品,“冷佛”即“民哀”并不难解释,如果强调“佛冷”和“民哀”构词方式相似还带有较大程度附会的成分,那么郑逸梅提到的“(姚民哀)笔名很多,且很特殊”,则提供了事实可能性,因此,“冷佛”无疑是姚民哀的笔名。
姚民哀(1894—1938)即姚肖尧,民哀是其号,又有护法军、小妖、老匏、芷卿、灵凤等笔名,江苏常熟人,南社成员。作为文学史视野下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姚民哀擅写会党小说,与“南向北赵”鼎足三立,是民国年间武侠小说开创期的代表人物,历来受到通俗文学史家的关注。他也与《红楼梦》关系密切,在《小说新报》中,《红楼梦质疑录》前有一段引述性的文字(不见于《民国日报》之《读红楼梦质疑》),揭示了姚民哀的红学因缘:
《红楼梦》一书,为旧小说中势力浑厚之作,世之治此书者,不乏俊彦硕士,所以有“红学”名称。然研究红学者夥矣,往古无论,近十年来,王氏为著《索隐》,蔡氏即踵起抉微,未成书者,更不可胜数,大都扬美雪芹,或言题外文章。就原本立论,摘其疏漏者,尚付阙如。不佞亦自附于红学之列,自十一岁迄今,忽忽二十年矣,此二十年中,几无日不治此书。久而有得,笔之于册,败帚自珍,因颜曰“怀疑录”而刊之《新报》。一孔之见,当世幸弗笑我谫陋也。
引文反映姚民哀对《红楼梦》研治颇下过一番功夫,实则他的著述中包含一些零散的红学文献,其中,除了题红诗歌《红楼杂咏》较为常见——《南社诗集》《红楼梦书录》《红楼梦资料汇编》等均有收录或著录,剩余的评红文字则依然深埋于民国报刊中,几乎未见再次转引,如姚民哀在《民国日报》文学副刊“稗屑”栏目连载《息庐小说谈》,漫谈古今小说,即含有评说《红楼梦》及“红楼续书”的片段,又如他在文学期刊《红玫瑰》发表《花萼楼小说羼评》,以二十来种明清小说为对象,各题一诗并附评论,也即包括一首题红诗歌及相关解说,兹录如下:
文笔高庳漫细论,如斯哀艳足销魂。
神龙见首悠然逝,不落寻常科臼痕。
右咏《红楼梦》。此书妙在宝玉、黛玉不成婚,同《水浒》一样结局,致令后世读者,牵肠罣肚,放不下去。或者曹雪芹当日,即瓣香施耐庵,移写草莽英雄之笔,以绘闺阃儿女私情,粗豪细腻,各擅胜场,实则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后之“续梦”、“圆梦”、“绮梦”、“重梦”、“复梦”等作,又被圣叹当年道着,所谓“咬人矢橛,不是好狗”。即索隐辨正之类,活文死注,虚事实做,其亦可以已乎。
作为掩于故纸的“红楼梦稀见资料”,纵是只言片语,却可从中发现姚民哀对《红楼梦》的观照始终秉持“小说家”的立场。所谓“小说家”的立场,不仅是从小说写作的正反、同异等视角剖析《红楼梦》对《水浒传》的效法与改造,也不仅是对红楼续书落入狗尾续貂的常见指责,更值得玩味的还是他对“索隐派”立场鲜明的批判态度,而在批判之余,“小说家”的立场同样有其特定的“意义”——红学,姚民哀自谦地表示“不佞亦自附于红学之列”。身为一名小说家,从小说写作的角度细解《红楼梦》固乃擅场所在,而姚民哀另一方面的信心则来源于“质疑”《红楼梦》的眼光,他认为“就原本立论,摘其疏漏者,尚付阙如”。“尚付阙如”乃就其同时代而言,如若上溯清世,寻拾《红楼梦》疏漏者不乏其例,王希廉评点《红楼梦》即包含一部分《护花主人摘误》(又名《石头记存疑》),摘出《红楼梦》“脱漏纰缪及未惬人意处”,《读红楼梦质疑》与之立意相仿,由于“三家评”本《红楼梦》流行于民国,姚民哀大有可能从王希廉的评点方式中获得灵感。而就实质而言,即便《读红楼梦质疑》连载于报端,也当属于“评点派”了。有趣的是,“质疑”本身实也掉进同时代人的话头,太冷生在《古今小说评林》中就曾言道:“醉心《红楼梦》者,往往寻疤觅疵,挑剔书中情节,亘二百年而未有已。不知原书经曹雪芹批阅十载,增删五次,曹氏胸罗八斗,心细于发,其纰漏处必有纰漏之所以然者。试问摇笔弄舌诸君,有曹氏之才否,推敲十年否?知乎此,当亦爽然自失矣。”与姚民哀的想法针锋相对。客观来说,问题的关键不在“质疑”之行为,而在“质疑”之内容是否言之成理,换句话说,《读红楼梦质疑》的学术分量如何?
补充说明的是,《红楼梦质疑录》的发表阵地《小说新报》作为“鸳鸯蝴蝶派”期刊,包含了丰富的涉《红楼梦》文献,如朱作霖《红楼文库》、陈秋水《红楼残梦》、李定夷《红楼旧话》、寄恨《王熙凤词》(据考证,“寄恨”名为朱怀沙)以及与《红楼梦》相关的各种谜语、酒令、诗钟,颇有价值,在《红楼梦》接受史上应有一席之地。
二、《读红楼梦质疑》述评
《读红楼梦质疑》名为“质疑”,却有一小部分的内容并非着眼于“质疑”,而是纯粹的解说性质,揭示出《红楼梦》在具体人物设计上的创作意图。如《读红楼梦质疑》一开始即说“甄士隐、贾雨村,人固知其为‘真事隐’、‘假语村’矣。按第一回表明贾雨村之姓氏时,姓贾名化,字时飞,贾化似宜解作‘假话’,贾时飞似宜解作‘假是非’”。简单说明了红楼人物命名的谐音问题,无甚新意可言,而“时飞”,后人常解作“实非”,似更合理。《读红楼梦质疑》包含个别可明确定为沿袭自“三家评”的说法,如其中提到芳官既是黛玉影子又是晴雯影子,来自涂瀛与张新之一脉承传的“影子说”,同时,姚民哀也别具会心地点到《红楼梦》第六十三回宝玉睡醒对芳官的一句玩笑话——“我竟也不知道了,若知道,给你脸上抹些黑墨”,与后文晴雯自述担负虚名,黛玉洁身归去形成呼应,可备一家之言。再如《红楼梦》第五十六回,江南甄家四女人和贾母聊起甄宝玉性格,说到“第一天生下来这一种刁钻古怪的脾气,如何使得”,话音未落就被王夫人进来打断了。“三家评”中一则夹批说:“截住得妙。”究竟妙在哪里,张新之没有更多说明,于是姚民哀提供解释:“雪芹于此等处,非但省去笔墨,且留深味于其间,使后之作小说,得此一条绝妙文路,可谓三面俱到矣。”所谓“节省笔墨”,他认为甄家四女人接下来无非要说“常在女孩儿群内胡混”,是可以了然的;所谓“留深味于其间”,他认为如果不打断甄家四女人的话,则衍生枝蔓。因为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说甄宝玉直如说贾宝玉,而引发贾母误会;所谓“使后之作小说,得此一条绝妙文路”,他认为此种小说笔法可供后人借鉴。所以姚民哀的一些观点在因循传统时亦可散发出个性化的想法和特征。从清代至民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探春受到的评价颇以负面声音占据势力,关键点是探春与赵姨娘在母女关系上的人伦乖舛,因赵国基死后赏银事,母女二人直接冲突。《读红楼梦质疑》同样于此处做文章,姚民哀以为探春的做法“亦太过分”,他引用一则谚语——“娘亲舅大,爷亲叔大”带出问题,主要还是以人情为视角,并由此高度肯定《红楼梦》第一百回关于探春结局的安排,他说:“后之离家远嫁,正彼苍之怒其很厉,亦著者之所以警世也。此等处,皆为雪芹布局缜细,他手所不及。”探春之评价是红学史上一项争议性难题,突出反映宗法制度下礼制对人情的撕裂,当时代由古转今后,在迥然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念下,究竟突出探春治家与改革的一面亦或放大其不近人情的另一面更多取决于读者个人的理解和裁定。姚民哀立场鲜明,用他的民俗观念衡量,远嫁是对小说人物的极大惩罚,也就有异于认为探春避开抄家、结局尚属幸运的另一类解说方式。综合观之,《读红楼梦质疑》在“非质疑”部分实际对小说的笔法情节、人物刻画、语言风格颇多褒扬,充分说明姚民哀本人对《红楼梦》的由衷热爱。
《读红楼梦质疑》的“重头”部分在于“质疑”小说的内容,其中同样触及了一些后来《红楼梦》研究的争议问题。姚民哀发现小说第三十七回回目是“秋爽斋偶结海棠社蘅芜苑夜拟菊花题”,写秋景;该回探春写给宝玉的信中提到“若蒙踏雪而来,敢请扫花以候”,写到雪;贾芸写给宝玉的信里又说“近因天气暑热,恐园中姑娘不便”,写暑热——几处的节候问题产生矛盾。“暑热”与秋天并无龃龉,即有所谓“秋老虎”,关键还是探春信中“踏雪”二字,这是红楼梦版本校勘问题的典型案例,在各本中有“掉雪”“棹雪”“绰云”“造雪”“踏雪”等异文,“踏雪”来源于“东观阁”“三家评”系统的版本,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依舒序本校为“棹雪”,并注释为“乘兴”,则是当下影响较大的说法,可相对妥帖地解决姚民哀的“质疑”,即便至今对于“棹雪”二字学界也间有质疑之声。小说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的座次问题,俞平伯、周绍良、王庆华、邓云乡等先生均有撰文探讨,尤其俞平伯的《“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图说》一文1948年先出,历来颇多引述,实则姚民哀的相关讨论要早上近30年,为此他画了一个圆图计算夜宴诸人的相对位置,其中宝钗十六点至探春、探春十九点至李纨、李纨顺手递给下家黛玉、黛玉十八点至湘云,湘云下家是宝玉,易于算出探春——宝钗——李纨——黛玉——湘云——宝玉的顺次上下手关系。接下来湘云九点至麝月,不难呆算出湘云、麝月隔七人,姚民哀质疑的是接下来的麝月十点至香菱,正确的结果应是宝玉,接下来香菱八点至袭人也便接着有误。一方面,这是个简单的数学游戏,另一方面也是个版本校勘问题,假如按照庚辰本的麝月十九点至香菱,香菱六点至袭人,其间不会产生数学错误,问题无疑仍是出在姚民哀所依据的《红楼梦》版本上。
20世纪初,脂砚斋本刚开始陆续被“发现”,姚民哀的“质疑”如涉及版本问题,从他的时代来看如非全身心投入研究完全不可能获得解决,因而姚民哀判定“十点”“八点”为小说硬伤而徒呼“恨不能起雪芹于地下而一叩之也”,亦可理解。换个方向来说,姚民哀对于《红楼梦》的解读集中落实于文本细节,善于捕捉小说的逻辑缺陷,上文两例犹然可谓一针见血,《读红楼梦质疑》的突出特征乃至于其价值也正表现于此,另外,内中还有一些独到的解读。小说第五十一回,周瑞家的带回消息给凤姐:袭人之母业已停床,凤姐派人去大观园取袭人的铺盖妆奁,而后宝玉看着晴雯、麝月两人打点妥当。依据事理,宝玉应是收到“袭人之母业已停床”的消息,但小说突然接续一段心理活动:“宝玉正坐着纳闷,想袭人之母不知是死是活。”脱离前文逻辑,姚民哀即由此表示质疑。今见王家惠先生《红楼五百问》一书试图从民俗的角度给出解释,他认为依丰润的丧葬习俗,人不得死于炕上,当人将死未死之时要被转移到门板临时搭就的“床”上,所以“袭人之母业已停床”,表示袭人的母亲当时还没死去,引发其后宝玉的疑问。丰润丧俗一说实非满意的回答,姑且搁置关于曹氏祖籍“丰润说”的较大争议,而就“停床”内涵来说,一般定义即如红研所校注本所下:“人刚死停尸于床,尚未入殓。”因为《红楼梦》第一百一十回、第一百一十四回尚有贾母、凤姐的两次“停床”情节,均为死后停床,加之此处并不需要在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作者问题上纠缠,所以就小说言“袭人之母业已停床”自可理解为袭人的母亲已经死去,那么姚民哀的质疑完全成立,《红楼梦》此处确有问题。小说第五十四回,鸳鸯对袭人言道:“你单身在这里,父母在外头。”姚民哀留意到小说第十九回交代袭人父亲已故,第四十六回交代鸳鸯与袭人的莫逆之交,所以鸳鸯当知晓袭人父的情况,其“父母在外头”之说便属曹雪芹笔下的疏漏。
一般而言,小说叙事要保证故事构成的相对完整性,但不是意味着小说定然要记录下情节或人物的每一具体细节,叙事允许一定的留白给予读者想象或者自行填充,《读红楼梦质疑》在此问题上时而钻之太深而留下苛刻之嫌。小说第八回,宝玉入梨香院,其时宝钗坐炕上做针线,宝钗见宝玉进来连忙起身让宝玉在炕沿上坐了。后来林黛玉摇摇摆摆地进屋来了,宝玉等忙起身让坐。姚民哀聚焦于“起身”二字,认为宝钗两次起身只是起身于炕上,并未下炕,论及心理、情理,宝钗无不下炕之理,违背宝钗处事细心的个性。这就显得纠之太过,周汝昌先生指出:“礼节上只能让宝玉炕沿上坐,因主人又不能不让上炕坐,客人又不能同一炕坐(男女亲疏之别),此乃从权之礼。”“下炕”不是礼数要求,退一步说,即使是礼数要求,“起身”也能包含“起身下炕”的潜在意涵。又如小说第四十回贾母在黛玉房中与王夫人等说话,薛姨妈进来,贾母等站起迎接,但小说后来一直没写贾母等坐下与否。姚民哀认为作者用笔过省,然则这样的省略对小说内容并无任何影响。
以上梳理了《读红楼梦质疑》的大部分内容,其他一些“质疑”同样审视于文本“小”处,具有“细”的特征。同时,它和评点派一样,具有“散”的特征。该类文献也许不乏灵光一现的地方,但孤立地就《红楼梦》文本研究来看缺乏提升价值认定的动能,因为格局着实有限,它只能为“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添上锦上添花的一笔,反而其共性层面上的表现与特征更加发人深思,本文即把民初旧派小说家的《红楼梦》接受问题作为进一步探讨的方向。
三、从《读红楼梦质疑》看民初旧派小说家的《红楼梦》接受问题及相关反思
民初(1912—1919)旧派小说家,过往常被称为“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作为新文学史的逆流存在。随着学术观念的转变,他们的正面价值又被不断地发掘。就《红楼梦》接受而言,民初小说家无疑充当主力,贡献尤多,除去浅层次的阅读行为,较深一层的包括直接调用《红楼梦》资源的“同人”书写以及模仿《红楼梦》立意、风格的别开新篇等两方面的写作行为,再者便是对《红楼梦》的评说行为,整合红学相关材料的文献搜辑行为以及介于写作与评说之间的题咏行为。民初旧派小说家对《红楼梦》的评说主要来自于“小说话”中涉及《红楼梦》部分,群体内部真正专门探讨《红楼梦》乃至带有研究性质的评说实属罕见,姚民哀的《读红楼梦质疑》仍具有一定填补空白的价值。民国初年专门探讨《红楼梦》乃至带有研究性质的评说是具体有数的,如野鹤《读红楼梦札记》,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季新《红楼梦新评》,蔡元培《石头记索隐》,钱静方《红楼梦考》,弁山樵子《红楼梦发微》(弁山樵子似为南社文人王均卿),邓狂言《红楼梦释真》,雪岑《红学发微》,李佛声《读红楼札记》等。这群作者虽部分有小说写作履历,但较难像姚民哀一样可冠以职业“小说家”的名号,所以姚民哀凭借“小说家”身份对《红楼梦》叙事的细密把握有其一段时代下的独特之处;同时,民初的这样一系列著述明确以“索隐派”占据主流,所以姚民哀自诩“红学”,实与那段时间的主流红学背道而驰。当然,民国初年反索隐的声音此起彼伏,尤其在带有小说理论的语境里批评十分尖锐,如成之《小说丛话》、叶楚伧《小说杂论》、解弢《小说话》等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小说话轮番指摘索隐之谬。姚民哀《读红楼梦质疑》发表于《民国日报》,与《民国日报》的负责人、同样身为小说家的叶楚伧在观点上桴鼓相应毋庸赘言。叶楚伧在《小说杂论》中提出“读红楼只能作红楼读”,《读红楼梦质疑》大可视为在剖离了其中“小说与社会关系”等陈旧话题后更显文本纯粹性的践行。
上海《民国日报》的小说资源无疑是雄厚的,除了刊载为数众多的各样类型的小说,其撰稿人如叶楚伧、姚鹓雏、成舍我、胡寄尘、姚民哀、张冥飞、王大觉等均为民初海上具有影响力的小说家,同时又囊括了《小说杂论》《小说杂评》《小说闲评》《小说管见》《息庐小说谈》《民国小说谈》《快韵庐读小说》等一批小说理论著述。由于其活跃的时间基本平行于五四新文学革命,在新旧交关的概念前提下,《民国日报》的小说资源便有了浓厚的“旧”的象征意味,却又成为“反思五四”的绝佳窗口。其实,在这样一个“旧”的语境中,思想的动荡和问题的改良是并存的。所谓动荡,有小说领域内的笔战,有小说领域外引起南社分裂的“唐宋诗之争”;所谓改良,有响应通俗教育研究会的政策精神,有古今中西交错反思的理论铺设。不管是持续的动荡激变为革命,又或是迟滞的改良呼唤出革命,“旧派”与“五四”之“新派”之间均没有壁垒森严的隔阂,他们中的一些成员同样也对民初小说有量无质深表不满,同样要求使用白话,同样尝试从西人小说中汲取灵感。因而,被“五四”遮蔽的所谓旧小说及相关小说理论不乏可取之处,甚至包容一些与“五四”理路沟通的面向。如果再进一层“反思之反思”,在“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量与质的考量、拉锯中,就会发现,“五四”仍是不可替代的“质变”,而《民国日报》小说家学习西方深度不足,也未曾掌握时代话语权,根本在于他们的理论资源根底于古,而“古”恰恰又是他们要变革的对象,自然难以凌越自身的知识、视野局限。
“五四”也是红学的分水岭,其中新旧反思当可类推,即便《民国日报》评红文献以《读红楼梦质疑》为主力,其他散见《小说杂论》《小说杂评》等,在规模上几分欠缺,他们在大方向上还是秉持了《红楼梦》的小说解读立场,风格鲜明,尤其对于“索隐”的态度在今日看来可谓清醒。但红学的质变最终是由“五四”以后的“考证派”完成,而《民国日报》的小说家仅聚焦于《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如姚民哀般琐细、叶楚伧般陈旧,自又无法实现突破,引领红学的潮流。“五四”新旧视野之下,《民国日报》小说家在小说变革和红学思路上是殊途同归的,他们的声音虽然被遮蔽了,经由第一重反思不难寻觅到“旧派”声音实际表现出来的部分正面价值,再经第二重反思会发现他们在时代变革前有心无力,“五四”仍是无法逾越的文学史标记。“殊途”则在于红学领域表现得较为极端,如果说小说领域之新旧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红学”之新旧则在方法论上截然凿出一道鸿沟。更为纠葛的是,百年以来,“红学”方法论的争议从未停歇过。
坚持《红楼梦》的小说本位,《民国日报》小说家以《红楼梦》为例强化理论构建,与五四小说变革在间接上达成映照,实乃自然结果,因为当时《红楼梦》基本已被公认为古代小说中的一流作品,是五四小说变革中理所当然的立论素材,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代表性的文章即予以《红楼梦》高度定位。但是新红学的考证一派横空出世,却是另一空间的议题,本应由“《红楼梦》是小说”绾合的小说变革和红学转型明显分道扬镳。诚如当事人胡适自身的态度,对于《红楼梦考证》的开创意义十分自信,对于《红楼梦》小说则模棱两可、由褒转贬。后来关于“红学”概念的扰攘争议,已于此处埋下伏笔,只是民初的诸种观念也许止于象征性的潜在交锋,若干年后就发展成事实上的论争了。
注释
① 杜竹敏《〈民国日报〉文艺副刊研究(1916—1924)》,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② 笔者所见《小京报》并不完整,《读红楼梦质疑》在《小京报》的完整刊载情况一时无法把握,但据部分刊载情况推测,《小京报》中刊载的《读红楼梦质疑》条目较《民国日报》更为丰富。
③ 郑逸梅《清末民初文坛轶事》,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290页。
④ 民哀《红楼梦质疑录》,《小说新报》1921年第3期。
⑤ 如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557页。
⑥ 姚民哀《花萼楼小说羼评》,《红玫瑰》1929年第19期。
⑦ 一粟编著《红楼梦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67页。
⑧ 冥飞等《古今小说评林》,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651页。
⑨ 《〈王熙凤词〉撰者“寄恨”考》:民国年间与《红楼梦》相关的弹词文献《王熙凤词》载于《小说新报》1915年第9期,作者署“寄恨”,孙越《〈小说新报〉所载民国弹词〈王熙凤词〉初考》(发表于《红楼梦学刊》2018年第4期)一文在作者问题上失考,其实“寄恨”之身份,尚可进一步追踪。综观《小说新报》,知“寄恨”是其中高产的撰稿人,尤以游戏文数量居多,同样“寄恨”也是基本同时期的《友声日报》高产的撰稿人,他在两报发表过《黍春室谐墨》《黍春室滑稽谈》《黍春室拉杂话》《黍春室联语》《黍春室艳吟草》等,判断“黍春室”为其室名。1915年第4期《小说新报》刊有“轶池”的《黍春医药室跋》,据其内容知“黍春医药室”为“轶池”的朋友“仰沙”所开,而《友声日报》中有大量“黍春医药室”的宣传广告,介绍内外眼科专家朱仰沙,那么“寄恨”跟朱仰沙是不是同一个人?答案是肯定的。1915年《定夷丛刊》(第二集)序四作者署为朱仰沙寄恨,1918年第4期《青年声》“祝词汇录”中也出现“镇海朱仰沙寄恨甫恭祝”,基本可确定“寄恨”名为朱仰沙。如再进一层验证也易形成证据支撑。如“寄恨”在《小说新报》和《友声新报》发布《记念碑征诗启》,宣传其小说《记念碑》,在晚清民国报刊中曾出现“蛟西颠书生”的《病香阁记念碑序》(见《宁波小说七日报》1909年第3期)、“壮青”的《题记念碑(调寄买陂塘)》(见《小说林》1908年第11期)和“镇海轶池”的《买波塘》(题哀情小说记念碑)(见《繁华杂志》1915年第6期,“蛟西颠书生”和“镇海轶池”均是镇海文人倪轶池的笔名。倪轶池(即倪承灿,字壮青,号轶池)在《病香阁记念碑序》中强调了他与“寄恨主人”的朋友关系,“寄恨主人”撰《宁波小说七日报祝词》中又有“吾宁”的字眼,知“寄恨”是宁波人。以上材料结合,则《王熙凤词》撰者“寄恨”为宁波镇海人朱仰沙确定无疑,当然,虽从民国报刊中容易看到朱仰沙的作品以及了解其职业情况,但其生平事迹尤其包括生卒年等基本问题仍需做进一步探究。
⑩ 冷佛《读红楼梦质疑》,《民国日报》1919年1月17日。
⑪⑬⑭⑰民哀《红楼梦质疑录(续)》,《小说新报》1921 年第4期。
⑫ 曹雪芹、高鹗著,护花主人、大某山民、太平闲人评《红楼梦》(三家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920页。
⑮⑱⑳㉑ 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423、605、605、641 页。
⑯ 俞平伯《“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图说》(见《红楼梦研究》),周绍良《“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图说》(见《红楼梦枝谭》),王庆华《“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坐次新解》(见《红楼梦学刊》1988年第4期),邓云乡(“怡红夜宴图”辩)(见《红楼识小录》)。
⑲ 王家惠《红楼五百问》,河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834—835页。
㉒ 曹雪芹著,周汝昌校订《红楼梦:八十回石头记》,海燕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页。
㉓ 雪岑,姓陈,生平事迹俟考。《红学发微》发表于《四川公报》增刊《娱闲录》,陈雪岑本人声名未彰,却与吴虞、李思纯、李劼人、赵熙等一批近现代知名文士同是《娱闲录》的撰稿人,《吴虞日记》中即记录了一些吴虞与陈雪岑的交游记录。
㉔ 详参李晨《“五四”时期〈民国日报〉作家群体的小说改良策略——从〈九尾龟〉论争说起》,《平顶山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