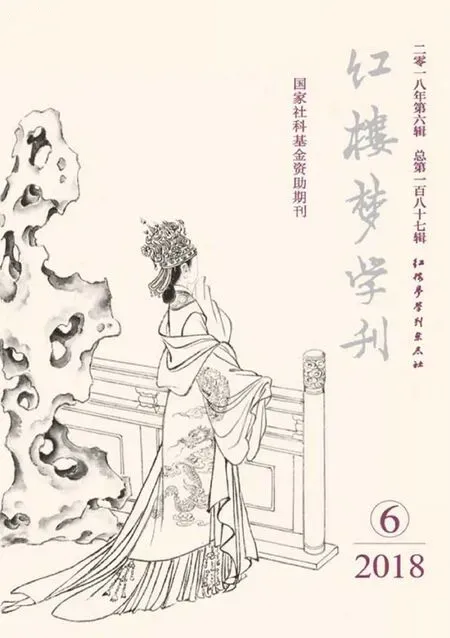从《红楼梦评论》到《人间词话》
——王国维无我之境与人生诗学之书写
内容提要:《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的言说方式不尽相同,但贯穿着王国维关于无我之境与人生诗学的哲学思考与艺术探索,展现出王国维为人生、为艺术的创作主张与审美倾向。源自于诗三百的诗言志、诗言情传统为王国维所承继,并结合叔本华、康德等西学新知,以独有的艺术天赋和对生命的深刻体验,构成《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关于生之有身与有我之境、出之超然与无我之境、形上之思与人生诗学的书写,其思想内容的深邃复杂与艺术形式的丰富多重,彰显着中国美学现代转型路向。
中国近代学界,中西文化交汇。以“人间”自号的王国维,终其一生在探寻生之意义及中国古典文艺现代转型之价值体现。以1904年《教育丛书》刊载的《红楼梦评论》及1908年《国粹学报》刊载的《人间词话》来看,四年之间,王国维关于中西文艺的处理与接受、人生意义与艺术价值的探索与追寻、中国古典诗学的传统承继与现代转型等问题的反思与充实,典型地呈现出中国近代社会的思想剧变与学说分化,不仅展现着中国古典诗学于近代与西学新知接触后所产生的冲击与化合,也预示着中国传统文艺的转型与发展。本文仅就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关于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形上之思与人生诗学的论说,略陈己见。
一、生之有身与有我之境
王国维曾经接受长期、系统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对西学新知也曾做过深入的研究,他既接受了孔子、老子、庄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也接受了叔本华、康德、席勒等的西方学说,写作过《孔子之美育主义》《屈子文学之精神》《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等文章,中西哲人的相关言说曾为王国维引用并体现于《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二书中。中西文化的汇合与交融中,既表现他对生之有身、人生欲望问题的深层思考,又显示他对人生境界书写在诗词构成中核心作用的深切关注。
(一)生之有身与生之苦痛
患有身之说,自先秦典籍即有记载。以老庄二家为例,《老子》尝谓“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庄子》曾曰“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老庄二家思想为王国维所承继,他在《红楼梦评论》开篇即以忧患、劳苦与生之有身对举。同时,他也接受了叔本华关于人受欲望支配、而欲望永远无以满足的观点,认为“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他探研《红楼梦》的悲剧精神,认为“所谓玉者,不过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而《红楼梦》乃“彻头彻尾之悲剧”。在他认为,悲剧分为三种,分别为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者、由于盲目的运命者及“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者(《红楼梦评论》)。《红楼梦》中的苦痛属于第三种,即为普通人物所共有而非极恶极殊之人所有,也为普遍生活境遇所共有而非人生意外变故所致。他也认为人生如钟表之摆,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同时苦痛又与文化程度相关,文化愈进、知识愈广、欲望愈多,则感受的苦痛愈甚。
王国维关于身之苦痛、生之悲剧的体验与主张,与他本人的性情与阅历相关,也与当时社会环境与创作语境相关。中国近代社会忧患深重,士人普遍感到生之苦痛,文学书写中也普遍呈现出生命苦难。例如,梁启超的书写中,大量运用病痛躯体来形容内外交患的中国社会;康有为《大同书》描绘人生十大苦难,并以去类界爱众生、去苦界至极乐等内容展现对大同社会的美好向往。期待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且男有分、女有归,是自《礼记》以来即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传统。西方同样有相关表达,也有乌托邦、社会空想之类的展望。而对美好世界的憧憬,与当时社会的苦难感受俱在。王国维在看到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精神是世间的、乐天的一面的同时,指出中国戏曲小说多始于悲终于欢、始于离终于合、始于困终于亨,就此将《红楼梦》置诸中国传统文化中加以衡量,并认为中国文学中具厌世解脱精神者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但《红楼梦》的厌世解脱之道与《桃花扇》又不尽相同,《桃花扇》所表现的解脱之道非真解脱,是他律的,而《红楼梦》之解脱是自律的。他律非真解脱,自律才是真解脱。但无论他律、自律,归根在于有身、有我。《红楼梦》一书展现了自造苦痛又不得解脱的人生,就在于有身、有我的存在。故而在面对人生欲望及其苦痛不得满足时,王国维倡导解脱并且认为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在他认为,金钏的堕井、司棋的触墙、尤三姐的自刎,均“非解脱也”(《红楼梦评论》)。
有身、有我,既是人人所面临的问题,关于人生之欲、物、我、心的表现与书写,就成为一种必然。在《红楼梦评论》一书中,王国维对人生的欲望、苦痛及其解脱之道进行论析;在《人间词话》一书中,他同样对生之悲欢离合、人之爱恨情欲予以重点关注。生之有身及其中苦痛,成为王国维持续思考的一个严肃问题,并影响着他对艺术与文学的主张。
(二)有我之境与苦之解脱
艺术与文学,成为王国维探索人生问题的重要渠道。在《人间词话》一书中,沿续《红楼梦评论》中关于生之有身的思考,王国维提出有境界与无境界、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一切景语皆情语等关于物、我、心之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关系问题及其处理方式的论说,并表达对于诗词写作与人生诗学的认识与追求。
首先,王国维以境界为目标,表达对艺术与人生书写关系的认识,提出诗词内容以人生情景的书写为重,词要表现境界,而境界不仅要表现客观景物,也要表现人的喜怒哀乐并且具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二种区分。他认为有我之境是以我观物,我为主、物为客,我借物抒怀,物因此染上我的情感色彩,诗词也呈现出有身、有我的客体存在。而在表现与处理情感问题上,他主张要真,要表现真景物、真性情。王国维论境界的有无问题,既包括外在之境的客观世界也包括内在之境的主观情感,并认为表达此二者的关键在处理好“真”与“能”的关系。“真”与“能”决定着境界是否表现及如何表现。基于这样的艺术考量,“红杏枝头春意闹”“云破月来花弄影”之类诗词及其中之“闹”“弄”的使用,被他称许为境界全出之佳作。因为,这一类诗词作品运用通感、比拟等手法,将“情”做了物化转换与文本呈现,展现出情、景之真。
其次,王国维以“一切景语皆情语”,表示艺术创造最终还是作者情志的表现——景语与情语、布景与说情是艺术创造中两大组成部分,“情”的书写大致从二方面进行:或则专作情语,或则情寓于景,前者如“甘作一生拼,尽君今日欢”“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许多烦恼,只为当时,一饷留情”等等,后者如“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绿杨烟外晓云轻,红杏枝头春意闹”“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淮南皓月冷千山”等等。至于境界是否有大小高低的区分,他认为诸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与“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闲挂小银钩”与“雾失楼台,月迷津渡”这一类诗词,所表现的境界有大小的区分却没有高下之别。基于这样的艺术主张,王国维提倡“真”而不喜“游”,他曾借金应硅的话对游词展开批评,认为淫词、鄙词、游词这三大弊病是“词之弊尽是矣”(《人间词话》初刊本第13则)。但正如《红楼梦评论》中强调人不婚宦、情欲失半和饮食之欲强不过男女之欲的主张一样,王国维重视情感的表达诉求,认为淫词、鄙词尚不失表现率真、弥满、生命的一面,游词却因失真、过假、过空而失了生命本原、人生本质。王国维其中所表达的艺术取向,相当明确。
再次,王国维以忧生、忧世来论析事物的层面区分问题,并以之表达对人生和艺术问题的思考。在《人间词话》中,他曾以具体事例说明忧生、忧世之作为一种概念的层面区分。忧生、忧世说是王国维的一个重要创造。把中国数千年的文学概括为忧生、忧世二种类别,也是他的一个重要主张。忧,心动也,从心,尤声。忧生,表示对生命感到忧虑,忧世,则是对时世或世事所生发的忧虑。忧生、忧世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忧生偏重于为己,体现更多一己生命意识,忧世更多为时为世,体现更多现世的关怀以及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思考。忧世随着改朝换代、世事反复而变化,忧生却不带任何特定的时代因素,是一种通古今而观之的纯粹的忧伤之感。论者将忧生看作突破一己感情而进入了人类普遍感情的书写,对人类感情或本性做出了真切的表现,随着人类存在而存在,是亘古不灭的情感表达。王国维自称“人间”,其本意也许就是这种情感的另一种表现。
二、出之超然与无我之境
《人间词话》中关于“一切景语皆情语”的词则,在王国维定稿时被删去。删除原因,与他对人生出之超然及无我之境的倡导有关。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中,王国维提出学术独立问题,主张视学术本身为目的而非将学术视为手段,对于艺术同样当作如是观。艺术创造的出之超然以及关于无我之境的倡导,成为王国维认识身之苦痛、生之悲剧以及解脱之道的方法与途径。
(一)出之超然与美术之慰藉
“诗三百”传统深刻影响着中国数千年文化,风雅颂、赋比兴以及诗言志、诗言情主张,也深刻影响着中国数千年文学。以儒家社会责任与立功立德使命自任的士人,在倡导诗言情的同时更多地发展了诗言志传统,诗言志也承载了士人更深沉的家国情怀。王国维一方面接受着中国传统典籍及诗言志的影响,一方面也接受着西方近代自由、民主、平等浪潮的洗礼。康德、叔本华等人的“审美无利害性”理论为王国维所接受,为人生、为艺术问题为王国维所着重,他曾自陈一度“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故而,佛教自魏晋传入后虽成为中国士人普遍的解脱之道,中国近代佛学虽然也复兴并得到全国上下的普遍信奉,王国维虽然也认为世界之大宗教如佛教、基督教“皆以解脱为唯一之宗旨”(《红楼梦评论》),但他并不迷恋宗教而选择以哲学、艺术为生命寄托,认为“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明确提出“宗教之慰藉,理想的;而美术之慰藉,现实的也。而美术之慰藉中,尤以文学为尤大。”
正是基于对艺术的本质在于超脱利害关系的认识,以艺术、学问为解脱与慰藉之途为王国维所倡导与重视,他从研治哲学转向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他认为,“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红楼梦评论》)由此他也认为,《红楼梦》人物中真正得解脱的只有贾宝玉、惜春、紫鹃,而惜春、紫鹃与贾宝玉的解脱之道又存在本质区别。王国维推崇后一种解脱,认为这是文学的、艺术的、美术的、恒久的。他又将解脱之道与哲学、艺术联结,认为惜春、紫鹃之解脱是超自然的、神明的、平和的、宗教的,贾宝玉的则是自然的、人类的、美术的、悲感的、壮美的、文学的、诗歌的、小说的。
考诸贾宝玉的人生经历及其解脱之法,在于在自己的苦痛循环中使生活之欲不能复起而为之幻影,进而悟得宇宙人生的真相。而悟得宇宙人生的真相,则为王国维主张艺术之既为艺术、美术之既为美术的根本所在。王国维对艺术、美术之美曾做阐释,认为美之为物有二种,一为优美、一为壮美,普通之美皆属优美,而艺术之壮美值得推崇。他认为《红楼梦》一书壮美多于优美,最壮美则为第九十六回宝玉与黛玉最后相见,并认为这样的文字于书中随处可见,感动人心。但是,无论是优美、壮美,“皆使吾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者。若美术中而有眩惑之原质乎,则又使吾人自纯粹之知识出,而复归于生活之欲。”(《红楼梦评论》)王国维将眩惑美与优美、壮美对举,强调自然界客观事物无不与人有利害关系,而艺术在于能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掉物我关系,“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红楼梦评论》)艺术美所以优于自然美,在于使人忘记物我关系,这是王国维对艺术推尊的重要归因,也是他寻求超然现实、解脱心性的重要方式。
(二)无我之境与远离功利的解脱之道
关于有身、有我之境的思考,既而指向关于超然、解脱的追求,无我之境就成为王国维将之与有我之境对举的一个重要美学范畴。他认为,“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人间词话》初刊本第4则)他也提出:“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人间词话》初刊本第3则)王国维所倡导的无我之境,既与庄子“丧我”“忘己”有一定关系,又与叔本华学说有通贯之处,是取径于中西二源而自加熔裁的产物,《人间词话》中的无我之境与以物观物、以天合天互为注脚。而将《人间词话》中关于无我之境的论说与其关于壮美、优美二者的阐释加比分析,可见王国维美学思想的变化。变化的原因,在于对中西学说的选择与扬弃。
与《红楼梦评论》创作时期、王国维的心仪叔本华学说不一样,创作《人间词话》的王国维,对于中西学说有了进一步的理性认识与学理判断。他曾自陈《红楼梦评论》立论全以叔本华学说为立脚地,然于第四章已提出疑问,认为叔本华学说“半出于其主观的气质,而无关于客观的知识”;至1905年,王国维转而折返至研习康德学说;至1907年,他发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一文,将古雅与优美、壮美相关联,认为古雅是优美和崇高得以表现的形式,是“形式美之形式美”,是介于优美、宏壮之间并且存于艺术而不存于自然之美,其中思想受着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理论主张影响;同时,席勒的人本主义美学尤其是素朴的诗、感伤的诗思想也作用于王国维。彭玉平对1903至1907年王国维的哲学研究与文艺思想的形成做过深入研究并指出,王国维撰写了大量中西哲学、美学、教育学等方面的著述,这为他认识社会和人生提供了角度和高度,也为他提倡远离功利的纯文学奠定了基础。
具体就《人间词话》的创作及关于无我之境的倡导来看,王国维的创造性表现在:在接受西方哲学、艺术思想的体系化、理论化影响的同时,结合中国传统文论做进一步的调整与扬弃:从观物的动、静角度论述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以及由此带来的艺术境界之优美、宏壮区别,进而以优美言说无我之境,以宏壮言说有我之境,认为有我之境是在由动到静的过程中得到——由动之静,表示从感情波动中再度回复安静的状态。情绪过于激动,人沉浸于强烈的感情中是无法安静无法创作的,而人激动过后心情平复,所想所感形诸于笔并创造有我之境的作品。而关于优美之境的创造,“惟于静中得之”。此中“静”本意“审”,从青争声,所谓“静言思之,不能奋飞”,呈现宁静思考状态。有我之境的得到需要安静才能创造,但那是“动”之后的静,而无我之境表现的是心灵里外的透彻之静,除情绪平复之外还超越了主观意志与现实功利。
与此前王国维言说造境、写境一样,“无我之境,以物观物”这一则词话以分类方法评判境界,依据创作过程中如何处理物、我关系,以及如何处理由此所出现的物、我组合形态与性质进行的划分,既涉及创造境界的方法,又涉及境界自身的组合。所谓有与无,并非一组互相对立的概念。从境界的创作过程及过程所出现结果来看,有与无也并非互相取代,有你就无我或者有我就无你,而是互相转换、互相融合。“泪眼问花花不语”,其所谓有,乃因在所展现的主客世界中,我仍然占居主导地位,我以自己的角色问花,并希望花应答我,我的意志与情感通过花及其他外物强烈地得以表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当中无我也有我。无我,则无从采菊、无从见南山;而有我,我却与物同化。以物观物,物与我二者处于平等、和谐乃至化合的状态,或者物与我皆为主体,或者物与我皆为客体,其所谓无,乃因我与物处于融合状态,我异化为物,人与物之间,难分彼此,主观的情感与客观的世界化于一体,共同呈现,所以为无。此中展现的,是语言表达上突破隔的要求,也是物与我、我与我之间超越隔而出之超然的艺术追求。这就是无我之境的创造,也是脱离人与人以及人与物之间利害关系,从而真正解脱的实现。
三、形上之思与人生诗学
将真与自然作为形成境界的条件和评价标准,将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作为境界创造的两种表现而加以论说,这是王国维的重要理论构建,但他的文艺思想远不止于此。从《红楼梦评论》到《人间词话》,从有我之境到无我之境,还潜藏着王国维更深层的思考与更复杂的思想——关于形上之思与人生诗学的探索与追求。王国维接受了叔本华关于人是形而上学的动物而有形而上学的需要思想的影响,与中西文化的深层影响密切相关并做了重要融铸与创造,他对人生诗学的思考持续而深沉,他所提出的写实家与理想家、政治家之眼与诗人之眼、诗人之境界与常人之境界、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诸命题,表现了关于人生诗学的审美构建。
(一)写实家与理想家
王国维从写实家、理想家二种角度,讨论文学的书写问题,认为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人间词话》初刊本第5则),故而写实家亦理想家、理想家亦写实家,因虚构之境的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法则。王国维所谓“关系、限制之处”,就是个体或者群体所以存在的条件及其相互关系,“遗其关系、限制之处”就是不考虑利益关系。当然,写实家与理想家并非互相对立而是互相融合、互相转换。观物的立场偏向可能倾向写实或倾向虚构,但高超的作者通过观物的“遗其关系、限制之处”而达致虽写实家亦理想家、虽理想家亦写实家的境界。
基于对写实家、理想家的区别与考衡,王国维重视诗词的忧生、忧世表达,于事物的形下、形上两个层面进行思考并推崇李煜词,引之为典范并认为词发展至李煜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人间词话》初刊本第15则)。伶工之词即教坊乐工创作之词,用以娱宾娱己,士大夫之词为文人、官吏所为,多抒发个人怀抱或表达哲理思考。由伶工之词变而为士大夫之词之所以产生质的变化,乃在于将娱宾遣兴之词变而作抒情言志。李煜词开阔深沉、眼界始大而周济却置于温庭筠、韦庄词之下,王国维认为这是颠倒是非黑白。他将李煜看作划时代的人物,以李煜为分界线,将词体创作划分为二类——伶工之词与士大夫之词,又将词的发展史划分为二期——之前的伶工之词和之后的士大夫之词。这是王国维对李煜词所做的历史定位,也是他对词的发展史所作的历史分期,又是他治词所表现的一种史观与史识。
对于李煜词的推崇,尤其可见王国维心中理想的诗词境界,也可见写实家、理想家二者的本质区别。正因为这一缘故,他在《红楼梦评论》中曾指出,非常之人,“由非常之知力,而洞观宇宙人生之本质,始知生活与苦痛之不能相离,由是求绝其生活之欲,而得解脱之道。”在《人间词话》一书,他也指出:李煜的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人间词话》初刊本第18则)。据徐梵澄译本《苏鲁支语录》所云,尼采认为血乃经义。将作品与经义同等看待,可见王国维对李煜词之推崇似已到无以复加地步。当然,王国维所谓“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重在对词人创作襟抱与人生气度表达的重视与强调,但如果与赵佶《燕山亭》词的意境创造比较,李煜与赵佶所作一个在境内、一个在境外,境界之高下明显可见:在境内,只是着眼于具象的故国与雕栏玉砌,在境外,则着眼于春花秋月以及春花秋月一样美好的人和事,有了普适性意味。因此,联系王国维关于李煜“不失赤子之心”的说法,即可明确得知:写实家与理想家之间,他对于能表现人生真实本原的理想家之赞肯。以之反观《红楼梦》,曹雪芹关于《红楼梦》的书写、关于贾宝玉的形象塑造及情节的设计安排,同样不失赤子之心、非凡能力以及对人生本质的犀利洞穿与真实书写,故而能达到《红楼梦》文本艺术的时空穿透力量与持久审美效果。
(二)政治家之眼与诗人之眼
在关于写实家、理想家论述的同时,王国维对政治家之眼与诗人之眼、诗人之境界与常人之境界也做了阐释。在《红楼梦评论》中,他曾说:“《桃花扇》之作者,但借侯、李之事以写故国之戚,而非以描写人生为事。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他从书写的立场和角度看《桃花扇》与《红楼梦》的区别,借以体现为人生、为艺术的人生观与艺术观。而这一表述,与关于美术(艺术)本质的认识密切关联。王国维认为,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是“人类全体之性质”(《红楼梦评论》)。《红楼梦》的主人公谓之贾宝玉可以,谓之子虚乌有先生也可以,谓之纳兰容若、曹雪芹等等亦无不可,“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为独深,而其希救济也为尤切。”(《红楼梦评论》)人人所有之问题,而人人未能解决之大问题,也成为王国维所关注与重视的。而这,也是诗人之眼所应捕捉与描写的。
进而关于诗人之眼、诗人之境界、诗人之语言,《人间词话》中具体也加以阐释,并以政治家之眼与诗人之眼、诗人之境界与常人之境界两相对比,认为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诗人之眼则“通古今而观之”(《人间词话》删稿第37则),故而词人观物须用诗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诗人之境界,“惟诗人能感之而能写之,故读其诗者,亦高举远慕,有遗世之意”,而像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常人也皆能感之,却惟有诗人能写之,故其“入于人者至深,而行于世也尤广”。因此,“惟诗人能以此须臾之物,镌诸不朽之文字,使读者自得之。遂觉诗人之言,字字为我心中所欲言,而又非我之所能自言,此大诗人之秘妙也。”(《人间词话》附录第16则)从这些论析中可见,在王国维认为,无论是从小说写作还是诗词创作层面来说,政治家之眼、诗人之眼并非是对立的,但两者观察世界、认识世界、反映世界的方式与态度各有差异:是关于域于一人一事和通古今而观之两种对立的观察方法和表现方法的差别。政治家容易局限于具体的人与事,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性与普遍性,不能更深更广地揭示人生普遍意义,而诗人能脱离具象化的人生、脱离关系利害限制乃至超越特定的时空拘限,做艺术概括与典型表现,从而能直指事物的本质性、普遍性,创造出蕴含言外之意的境界。为此,境界往往为诗人而设因诗人而生,世无诗人即无境界的表达与呈现。由此可知,王国维主张观物与创作要有史的认识与史的思考,以超越当下、打通古今。诗人之境界与常人之境界的区分同作如是观,常人所感多不离乎一己遭遇,而诗人独能以超世姿态观照人生万象,写出超脱己身的大格局、大气象之作。《红楼梦》之所以创作成功,之所以能成为哲学的、宇宙的、文学的伟大作品,基于此;中国诗词创作之流传经典,也正基于此。
基于这样的审美体验,除了推崇李煜词之外,王国维对苏轼、辛弃疾词也备加欣赏,认为颇具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风。而相较之下,姜夔的词虽“似蝉蜕尘埃,然终不免局促辕下”(《人间词话》初刊本第45则)。王国维讨论苏轼、辛弃词作时,虽没有具体说明“高致”的内涵所指,但与“胸襟”一样均在于表示内在修炼与气质涵养:苏轼之旷,基于“接受了佛家静达园通、庄子齐物论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深刻影响”;辛弃疾之豪,则“大踏步出来,与眉山同工异曲。“然东坡是衣冠伟人,稼轩则弓刀游侠”语“可引之为注脚”,进而可得知:王国维关于政治家之眼与诗人之眼、诗人之境界与常人之境界,与他关于写实家与理想家的论说一样,均在于重视文本所体现的深刻蕴意与形上之思。
(三)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
王国维有关写实家与理想家、政治家之眼与诗人之眼、诗人之境界与常人之境界诸说,着重于文本表现不一样外,更着重作者观察事物的角度与立场的差异。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轻视外物与重视外物两组概念——他关于境界的言说,以忧生、忧世为理念,以能写真景物、真感情为基点,以能入、能出为标准,相较中国传统的意境说、神韵说,从理论上做了进一步的超越与阐发。忧生、忧世表现于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两种审美思维,忧生念乱的词境迷离惝恍、不可言状,言外之意于可知不可知之间,“是词的‘意内言外’的特性所规定的”。而哲学、文学尤其是诗学,更能表现对宇宙人生根本问题的思索与对忧生情怀的书写,“其所欲解释者,皆宇宙人生根本之问题,不过其解释之方法,一直观的,一思考的;一顿悟的,一合理的耳”。可见,王国维认为诗歌作为文学体裁中的一种,与哲学虽然在表达方式上不尽相同,但有着共同的本质追求:即都能表现人生、反映人生及其根本问题。为此,对于诗人的书写境界,王国维以内与外、入与出、观与写、生气与高致四组言辞加以具体阐释,认为内与外、入与出意味着对人生的了解程度以及由此决定作品是否高于现实。
至于观与写,王国维倡导要联系入与出及其间之关系,来看其能否作“超越‘功利目的’的‘直观’”。在王国维看来,唯有这一种直观,才能穿越“生活之欲”及其感性与理性的局限,达到“势力之悟”的“高致”,悟到人生之真善与人类之美感,即以超越功利目的来解说“观”的问题,由此达致穿越生活之欲及其感性与理性的局限的“写”。就此,所谓内与外、入与出、观与写这三组标准似不难理解,对此则的前三句为此也可大致解说为:诗人必须深入到客观世界,又必须高于客观世界,深入客观世界才能描写客观世界,高于客观世界才能观察并描写客观世界。就此再理解生气与高致问题,王国维所强调的即在于作品的生命力、穿透力,表现生活本质的同时超越生活真实而具有的神韵高致和普遍意义。因此,论者就一“忧”字提出讨论,认为一方面因诗人“忧”思,关爱,故能“入”于对象(人生、人世)之“内”;一方面因诗人对人生、生命之“忧”——“忧生”——本身就是超越了形而下层面“自道身世之戚”的小气、狭隘的心胸欲望,而进入了形而上的对诗人个体的生命、生存状态的忧虑之境;而诗人对人生、人类的“忧”思——“忧世”——则又是超越了对个体生命之“忧”(即忧生)的境界,而进入了对人类的生命生存状态的关爱与忧思,进一步,乃至进入对自然对宇宙的生命生存的关怀。
综上可见,王国维主张以境界为本,就是主张写实与理想、以诗人之眼能入又能出,对宇宙人生要有深入真切的体验又能以自然真实的方式加以描写与表达。对宇宙的生命关怀、对人生普遍意义的书写,始终是王国维所关注的核心。王国维以诗人之眼观物,为此创作的词作寄托遥深,表现对普遍人生、人生普遍问题的悲悯之情,亦为词开拓出新的境界,即:以中西哲理的融入,于创作中作形上之思的表现。这是王国维艺术创作的自觉追求,是《人间词话》阐释人生诗学、创造人生诗学的努力与尝试。同样地,也是《红楼梦评论》中所言说之立脚点与阐释之关键点。在王国维认为,曹雪芹书写之成功,就在于以能入又能出的视域,以对宇宙人生深入真切的体验及生动传神的书写,将贾府及其诸多人生的生命际遇与情感悲戚做了诗化的书写,并展示人生之普遍意义。
余 论
王国维虽自陈《红楼梦评论》立论全在于叔本华之立脚地,但他实际上却将中西文化做了融合与汇通。而从《红楼梦评论》到《人间词话》,是王国维从西方学说向中国传统美学的回归。在中国文学史上,唐代已开始使用境界这一概念来评说诗歌创作,王国维之所发明,乃在于此前集中于情景说及其核心之情景交融,以境界说将诗词文本中的表现再度生命化。而《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二书中的人生化、真实化、情感化,也是王国维人生诗学的具象化,是他表现抽象的哲思学理的文本写作与艺术追求。他关于形上问题的思考,最终归结于人生痛苦的解脱之道,与其哲学、美学上的人生论、价值观具有高度一致性。正是这种一致性,使得王国维在中国美学现代转型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与影响。
注释
① 本文所引《红楼梦》《人间词话》原文,均出自《王国维全集》第1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② 魏源注《老子道德经》,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
③ 王先谦撰、陈凡整理《庄子集解》第2版,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页。
④ 王国维《自序》,《王国维全集》第14卷,第118页。
⑤ 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王国维全集》第3卷,第8页。
⑥ 王国维《去毒篇——雅片烟之根本治疗法及将来教育上之注意》,《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66页。
⑦ 王国维《自序二》,《王国维全集》第14卷,第122页。
⑧ 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52页。
⑨ 王国维《静庵文集》自序,《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3页。
⑩ 彭玉平《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下,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604页。
⑪ 王秀梅译注《诗经》(上),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50页。
⑫ 邓菀莛撰述、施议对审订《百家点评人间词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61页。
⑬ 王水照《论苏轼创作的发展阶段》,《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1期。
⑭ 王国维著,靳德峻笺证、蒲菁补笺《人间词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0页。
⑮ 邱世友《冯煦的词论》,《文学遗产》1986年第6期。
⑯ 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王国维全集》第14卷,第36—37页。
⑰ 蒋永青《从“审美”视域走向“境界”——论王国维的“知力意志”说》,《思想战线》2001年第4期。
⑱ 马正平《生命的空间——〈人间词话〉的当代解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7—98页。
——论《历代闺秀词话》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