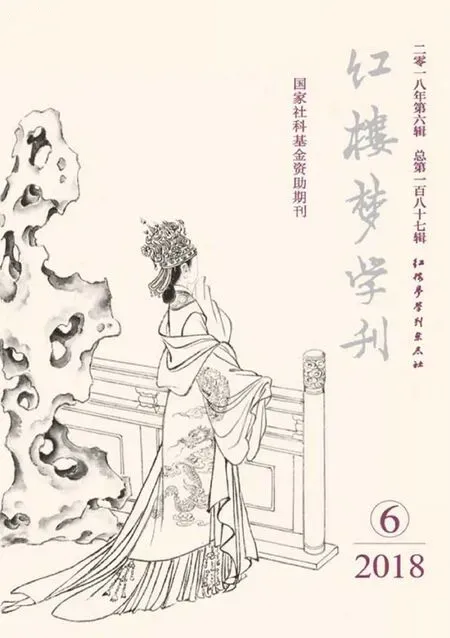宝黛奇缘语境中的“真假”重思
——以理学为视域
内容提要:从《红楼梦》小说的叙事结构以及立意本旨着眼,其与理学思想的关涉,着重体现在宝玉与黛玉以及石草木之关系的叙事上。在理学视域下,宝玉为顽石与神瑛侍者的合体,他和黛玉不仅有“养-报”的先天关系,且有心与所发情意的象征。二人恰以“诚意”的后天工夫以显证先天关系。诚意在于“警幻”,在“假语村言”的幻化中持守诚敬,磨镜自鉴以正身心。重思“真假”还要回到诚敬(成镜)工夫本身。在诗的假言幻化中持存心意诚正,即为诚镜(敬)守玉(心)、因假悟空的理学妙义。
关于《红楼梦》真(甄)假(贾)之说,向来有“自传说”“索隐说”两条解释路径。余英时在两说基础上提出“典范”与“危机”论,并提出了新“典范”——着眼于小说的创作旨趣与有机结构本身,在文本所寓意的理想与现实之间探寻作者的本意。将原著还原为小说本身,从小说的叙事中探索“将真事隐去”、由“假语村言”所建起的“通灵”境域与现实生活的二元结构,“太虚幻境”与“大观园”也就具有了接近理学中“理”“气”划分的关系,而与代表“真事”的外在史料拉开了距离。如果“大观园”可谓小说之“假语”所设置的真实生活,那么“太虚幻境”也同为这套语言所构造的理想境域。鉴于小说所处的明清理学背景,以及书中对“四书”《诗经》等理学经典的推崇,从理学角度看待小说的整体运思,或许可能成为一条可待发掘的阐释途径。
回到小说本身,无论是形而上的“太虚幻境”,还是形而下的“大观园”,都无非是既“真事隐”去之后,就石头的“通灵”为说,借“假语村言”所建构出来的“假象”。然而前者为洁净空廓的“理”,后者是灵动具体的“气”,虽为虚构,荒唐言里又无处不是真实的辛酸痴情。如果因言入象可谓“假作真时”,把“假言”所构建的“真象”当作了“真”,这个“真”未尝不可又成一“假”,仍属可忘之列。若能在宝黛关系的重重假言中,探索作者的真假隐微之辨,得其意而忘其言、象,不失为饶有兴味之选。
一、玉:神妙之心
《红楼梦》中的“玉”被周汝昌称为红楼“三纲”之第一。“玉”是一颗灵石,女娲惟独弃置不用的这块顽石,却“自经煅炼”通了灵性,在青埂峰下昼夜嗟叹。脂批:“妙。自谓落堕情根,故无补天之用。”又夹批道:“煅炼后性方通,甚哉!人生不能学也。”虽自愧无材补天,而也是经过煅炼才通了灵性,即便堕落于“情根”、流连于红尘,也非红尘中“困而不学”的芸芸众生所可比。可见“无材可去补苍天”只是自谦之辞,不然脂批又何笑其“不以此补天,就该去补地”,又称叹“煅炼过,尚与人踮脚,不学者又当如何?”玉之通灵,如人心通过学养而感通性命之理。心的养正在于诚意,而诚意与自谦关联密切。
(一)宝玉:顽石与神瑛的心身合体
自谦其实贯穿在关于“宝玉”的整体叙事当中,谦辞“质蠢”其实暗含“性灵”的意味。然而是否灵石幻化为“美玉”即指此灵性的彰显呢?书中却借僧道之口,对美玉的形态再作嘲讽:“形体倒也是个宝物了”;甲侧:“自愧之语”;蒙侧:“世上人原自据看得见处为凭。”幻化而来的形态美之外并没有实在的好处,这一“假有”在世人眼中还不够显得真实,故此还需再镌刻上几个字,所谓“世上原宜假,不宜真也。”世间崇尚以“假”为“宜”,或者以“假”作“真”,却遗忘了石头的性灵原是自经修炼而来,形态字迹只不过是在“静极思动”、入世应物之后的迹象。这也是“假语村言”的由来。
“静极思动,无中生有”与程朱理学有着深入的渊源。朱熹论静不同于他的老师李侗,对于默坐澄心不甚契合,认为一向静坐容易流于坐禅入定,主张“有父母合当奉养,有事务合当应接”,在日用伦常之间持得八面洞明的“白的虚静”。人心如同落堕于凡间情根的顽石,未曾接触人事之前也有以“静”为主的“未发”工夫,静中涵养通得性理后,接下来就是“幻形入世”。心一旦接于事物,就开始了“已发”工夫,即阴阳二气的屈伸往复,往者屈而为鬼,来者伸而为神。“静极思动”就是在心的未发与已发之间的几微之处,一阳来复、感而遂通,随即在日用酬酢中诚意正心、推仁行恕。所谓“诚”,就是“自慊”而不“自欺”。在心的发动处存诚去伪,便是几微之际向善离恶。
“慊”即通“谦”,唯有做到好善如同喜欢美色、恶恶好似厌恶恶臭一般,才能达到“自慊”,其中包含自我认可的意思,同时也有满而不盈的“自谦”之意。《周易集解》“谦”的序卦辞:“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虞翻注:“天道下济,故‘亨’。”“谦”意味着乾道下济、坤道顺承,阴阳亨通,满而不溢。“谦”卦初六、六二承九三爻,形成内卦“艮”,艮的象为山、为少男,二阴承阳有谦让之意,故有“谦谦君子”,正可联系“青埂峰”以及“宝玉”的意象。此处脂批“就该去补地”也应和了“自贬损以下人”的“谦者”风范。诚悫自谦的功夫多见于宝玉的言行中,如回答代儒有关“好德如好色”的问题时,宝玉无可回避、只好作答的样态就是精彩的一节。
落堕青埂的顽石属于形而下的“气”,太虚幻境则是形而上的“理”。在这套“理”的范畴中,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有一段滋养灌溉与还泪报恩的奇缘。“养”与“报”的关系,可以用孔子的“三年之丧”来表述,而丧服之礼是建立在“三年之爱”的基础上的。出生三年才能“免于父母之怀”,子女服丧三年作为回报,在儒家看来是先天必然的。这种“养-报”关系不仅限于父子,也可推及夫妇。前现代社会里,夫对妇同样有鞠养之恩,妇对夫如同对父一般也服丧三年。在此类推中值得注意,夫妇关系不是先天的,而是男女在相处中体会和证实到的。所谓“称情而立文”,不论“理”还是“礼”的形而上学建构,其基础无非男女、亲子之间的本真情感。如此看来,神瑛与绛珠以及其他入册的“风流冤家”的关系,以判词和图画、或言与象的形式置于“太虚幻境”,也算作其在“大观园”身份的形而上的说明。在形而下的“大观园”里,黛玉的身份是绛珠草的转世,而宝玉是以顽石为心、神瑛侍者转世为身的“心-身”合体。在“理”的领域,神瑛与绛珠存在着“养-报”的先天关系;在“气”的领域,自从黛玉孤身入贾府,宝玉的陪伴呵护、黛玉的温存相依正是“养-报”关系的后天体现;但需要在日用常行中磨练心性,以显证二人的这种关系。这个磨练的工夫,就是顽石逐渐通灵的过程。
(二)宝黛:借由诚意的身心合一
阴阳始交、静极思动的自谦之“心”,随着神瑛侍者的后身一并出场,然而二者之间还存在“心-身”的界限。宝黛相见意味着身体的感通,也是彼此确立心性的开端。黛玉的心和宝玉的心本是一个,然而开始只像“顽石”般跟着宝玉的身体。关于黛玉的心,甄士隐曾梦见僧道携着“通灵宝玉”,正交代这段“风流公案”的起因:“灵河岸上”的“心源”、“三生石畔”的“性本”之间,生着一株“绛珠草”,代表着“心之色”“心之慧”。神瑛对仙草有灌溉滋养之恩,仙草对神瑛则有“缠绵不尽之意”;神瑛与仙草象征着顽石的良知良能,也就是“心”所先天赋有的涵养与立志的能力。只有在神瑛和绛珠的匹配中,顽石才可以“通灵”。从宝黛的相互感通开始,“心”中的意志随之发起,唯有在两人的磨合中,经过谦谦诚意的工夫达到意诚、心正,两心才能融为一个“真”心。
诚意离不开“修辞立其诚”的语言功夫。自从宝黛相遇感通,带有顽石的身体就借着“假语村言”相探,希望在另一个那里找到自己的影像。伴随着屡屡的失败,身体对心没有了信任,表现为“摔玉”的行动。没有玉的也试图从对方的回应中确立自己的心,就像孟子所说的“求其放心”,然而同样未曾得到满意的印证。“你证我证”就是彼此分别的两个身体反复以“假言”相试的痛彻搏斗,如果说顽石可对应于易学“先天图”中“震”的一阳来复,那么与神瑛相应的绛珠则可比“震”的“天根”与“巽”的“月窟”相搏之象。“震”为春雷,“巽”为秋风,在朱熹理学中,雷风相搏跨越了春夏所象征的乾道,直入秋敛冬藏的坤道,坤道的工夫正是格物致知的痛彻搏杀。如果元春的炮仗灯谜可以被视为一盛即衰的隐喻,秋风催折正是转折的起点,“月窟仙人缝缟袂,秋闺怨女拭啼痕”同时喻示了晴雯、黛玉所处的这个关节点。黛玉所占的花名是芙蓉,晴雯被“上帝垂旌”为芙蓉花神,芙蓉盛开在夏季、衰枯在秋天,黛玉喜欢李义山的那句诗“留得残荷听雨声”,是否也表现出对自己时位的把握和预感?
而到了“心证意证”,两人从格致搏杀终于过渡到了“诚意”“知言”,获得心与身、理与气的合一。先天图上已到了“坤”的“冬至”之象,红颜在此时将遇枯骨,黛玉的身体即将面临雪里枯柴般的萎败,两心、两身终合为一,而其中之一也将“无立足境”。这时的坤道工夫益发精微,从已发的戒慎恐惧进入了慎独、诚意的未发持守,“言忠信”的同时伴随“行笃敬”。黛玉善感多愁而精于诗赋,未尝不是在的幻生中守持敬慎,本于心性而用于“警(敬)幻”,在“心证意证”的过程中,“假言”渐渐被忘却,进入“无言”之境,从而能因色悟空、明心见性。然而绵绵之意萦绕于心,又难免多生愁绪,积成玉中的泪痕,或也因此借宝玉之口,“颦颦”成为“黛”的注脚。
黛玉的枯柴之象,似乎隐涉宝钗。“钗黛合一”之说已不再陌生,宝钗虽不为书中之主,也是落笔的实在之处。介于黛玉、宝钗之间的香菱,即甄士隐失散的女儿英莲。香菱比起黛玉,可谓是更“真实”的身体,进大观园随黛玉学诗,也可以作为信言笃行的一例反躬实践。据随本总批,“英莲”“娇杏”分别是黛玉、宝钗的小影。香菱、黛玉都以早夭的身世惹人“应怜”,娇杏(侥幸)偶一回顾便居人上,正合宝钗待时而飞的志向。而“菱花空对雪澌澌”又点出香菱应归于薛,似乎在钗黛之间暗伏隐线。香菱通过“假语村”的就中维持进入薛家,宝钗从而与黛玉比肩出现在大观园中。
“冷”“香”可谓宝钗出场的直感。贾宝玉在可卿房中神游太虚前,看到了唐伯虎的《海棠春睡图》,上有题诗“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袭人是酒香”。张评:“‘虎’为西金,‘寅’为东木,一金一木,所谓‘兼美’。”又在诗后注点出“‘袭人’,是下回‘初试’”以及“金锁、冷香丸方是真正主人翁”。如果与袭人“初试”作为宝钗的前奏,“兼美”又意蕴钗黛二人的合体。与“兼美”成姻仅限于“意淫”幻境,再往前趋就是“迷津”。张评“‘意’乃心之所发”,“诚意”以黛玉为主。而在做工夫的过程中,宝钗又似乎喻指着如谶语迷津一般的结局。
“淫则一理,意则有别”,警幻仙子“速回头”的告诫,似乎是在警示宝玉回到“以情悟道,守理衷情”的“意淫”,也就是本心幻生的痴情蜜意。如果说“警幻”既是本心之用,也有主“敬”、守理的涵义,而守理只有以“色悟”“情悟”才是本旨,回到“诚意”的工夫,达到身心合一、明见心性,是否依然难免红颜枯骨的悲剧呢?也许宝钗的出现,本身就是“回头”的一种隐示;然而四季总是循环再现,工夫只有接续前进,频频回头、抑或偶一回顾,也可以在枯骨之后的生活中继续。茫茫雪地里侥幸的一次回头,或许就像残荷听雨那样,无情、空冷的心境里,也能观照、留下一番灵动生香的记录;只是随着神瑛绛珠的奇缘已尽,这身心虽合为一体,却再也兴不起波澜。香魂已返,此身将逝,唯余石上记录罢了。
二、镜:真假之身
“警”“敬”的另一个代称是“镜”。“菱花镜”首先指代香菱,后又联系到黛玉,“照不见菱花镜里形容瘦”这句唱词,一般被理解为宝玉对黛玉的形容。五十七回,宝玉向紫鹃讨了一个小菱花镜随身带着,这不仅是个定情信物,更是时时提澌“警幻”,只不过“空对雪澌澌”又隐约指向后来的不测结局。无论结果如何,镜子是又一个重要的隐喻。
(一)刘姥姥:镜反诸身
就像“风月宝鉴”“太虚幻境”等无法回避的“镜子”寓意一样,刘姥姥也是《红楼梦》中绕不过的人物。她以其进入大观园的过程,展示出一幅“携蝗大嚼图”的有趣镜像。“母蝗虫”出自黛玉之口。黛玉素以尖酸刻薄著称,因此为刘姥姥起的这个雅号,一般也并未引起注意;然而细想,她平时所着意揶揄的对象,只是有限的核心人物。所谓“着意”其实是一种善意关爱的表示,而对其他人的态度不过是以“目无下尘”掩饰的小心疏远。然而唯独对刘姥姥,林黛玉简直是不错过任何机会进行刻薄。与此有关的是另一个“玉”——妙玉,她的为人也像黛玉一般的疏淡,然而唯一刻意“伤害”的也就是刘姥姥了。如果说这是个巧合的话,那么更巧的事是,这两位“玉”也都用同样的方式对待第三只“玉”——宝玉。
书中名叫“玉”的,除了这三个人之外,还有原名红玉、后因犯忌而改名的小红。周汝昌称“红”为红楼第二纲,与“玉”相比更真实寻常,更有烟火气。宝玉自称“怡红公子”,住在“怡红院”里,其实也有这样一个自谦的涵义在内。宝玉最显著的自谦是“浊物”,而与他同样住过“怡红院”的“浊物”还有性别其实不太明显的“母蝗虫”——刘姥姥。那么,与“红”这条线索相联的宝玉和刘姥姥,与“玉”的线索相联的宝玉、黛玉、妙玉,两者在宝玉身上重合了,“宝玉”其实是个非纯粹的复合体。
常遭到黛玉揶揄的宝玉,在刘姥姥进入大观园的过程中,与刘姥姥有了许多合拍的迹象。比如,刘姥姥被王熙凤用黄杨木根整抠的大杯灌酒,而宝玉则被妙玉用“九曲十环,一百二十节,蟠虬整雕竹根的一个大 ”灌茶;而刘姥姥醉酒后,又阴差阳错地跑进怡红院,在宝玉的床上睡了一觉;并且,二人还由雪下“抽柴禾”的红衣女孩——茗玉联系起来。同被黛玉、妙玉二人贬低的宝玉和刘姥姥,简直如影随形一般合在了一起。值得注意的是,引导着二者合拍的还有一面镜子。
一面巨大的、能照出整个人形的、可反转的镜子,是怡红院里的一个“机关”。宝玉曾对着这面镜子,梦见了另一个“真实的”自己——甄宝玉,同时那个“真”的自己也在梦着这个“假”的自己。“假作真时真亦假”,这仿佛语言学中的经典“说谎者悖论”:“我在做梦”若为真,那么梦中的我所言所行皆为假,因此“我在做梦”本这句话就是假的;而若此命题为假,那么我的言行为真,则我的确在梦中,这又推翻了此命题为假的前提。我是否在做梦既已是非难判,还不如进入“我做梦、梦也做我”的“梦蝶”循环,接受无是无非的相对主义。然而刘姥姥却不一样,她一开始也把在镜子里看到的像当了真,但很快就发现了里面的那个还是自己——一个庄稼人的本色,于是她推开镜子,到镜子的背面睡了一个没做梦的觉就走了。
刘姥姥之所以能打破无是非的镜像循环,在于她无意中推开了镜子、看到了背面,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镜子不就是一个“物”么!这正如语言的逻辑也只是一个“物”,是个有限的存在者;语言里的命题,其确定性不能在其形式逻辑的内部找,而要跳出这个逻辑框架,从“元语言”中去寻找其规定性。这正如理学的这套形而上学语言,如果在红颜枯木、泪尽才竭之后,工夫无法持续,成为了一个绕不过的迷津,那么不如推翻这套“理”的架构。只不过,窥破了镜子迷津的刘姥姥并无意寻找镜子背后的规定性,更无意重建另一套形而上的话语,她只当睡了个没有梦的大觉,就回到了自己“浊物”的本色。由此可见,刘姥姥的闯入,已彻底将流连于高洁的“玉”与寻常的“红”之间的宝玉打回了原形,自己在假语村言中具有的身体无非一个世间的“浊物”,一个并不高雅却又真实纯粹的身体。
(二)香菱:反身成镜
如果说刘姥姥代表着一个不优雅的身体,与之可资比较的是香菱,这个同样卑微渺茫、却向往高雅的身体。就香菱而言,渺渺茫茫、原原本本的身体还远不是尽头,她还抱有着诗的希望。香菱学诗于黛玉,如“同身”“受心”的指引,“行”由“知”来率领。不过这里的“知”并非已经获得的固定知识,而是“致知”“诚意”的工夫本身。意诚而不自欺,自然就会信言笃行。诚意即是一面镜子,主于镜(敬)就是在这面镜子里照影,既照见自己的身体、行为,同样明晰可见的是自己的心性、即天理。易言之,“镜”就是“敬”,通过“格物致知”把心磨成镜子即为“诚敬”(成镜)。敬为守住心性门户,诚为克己自谦,敬是根本,持敬自然会诚。“呆”香菱之“心苦”,其中“心苦”喻指的是“诚意”容易生出愁苦、使玉中留下青黛的痕迹。如果说香菱是一面镜子,从中可照见自己,使自我身心俱正,那么黛玉则以诚敬的工夫将她磨成镜子。
黛玉的“应怜”几乎无人可以否认,其最应怜者当属她的泪水。曾有西园主人作《林黛玉论》,评论她的泪中含有“无言之隐”,他人或许怀疑宝黛两人早有所计,殊不知黛玉“终身以礼自守”,面斥知心婢女的进言筹谋,只将感情保存在心中,偶尔诉诸笔端诗句,与爱人相对却无一句邪言。然而宝玉、黛玉本有意中的姻缘,终于成了水月镜花之“假”;而宝玉、宝钗的姻缘本属“侥幸”,却反而成“真”。这正是镜中照出的影子本是假的,却是“假作真者”;而若将这影子当“真”,却不知被遗忘的“真”本亦是“假”。
宝黛的情意,经“警幻”仙子告诫止步回头,只停留在的“意淫”层面,不敢前趋一步。而宝黛的“真”人本也就是借“假语村言”道出,二人姻缘也只是个“水中月,镜中花”的影像。或许正是明了于此,黛玉才将此情仅保存在心中,听天所付,死生由命,直至泪尽而逝。有感于黛玉的诚敬,宝玉才会向紫鹃要了一面菱花镜藏在身边,时刻提醒自己敬慎、“警幻”。然而“菱花空对雪”又预示了这个虚幻渺茫的结局,香菱归于薛家象征着宝玉终属于宝钗。不论“宝钗”是实在的人物抑或只是一个“迷津”的喻指,心以诚敬自守,不陷入枯寂无为的幻影,就是将自己的心打磨为一面镜子,以“空”对着“假”,不失去本心的工夫,同时赋予假象以生动的意趣,“情不情”可使“无情”者也变得“动人”。守敬(镜),不单如刘姥姥般看到了镜子的反面,而是通过“诚敬”的工夫,使自己的心渐渐修成明镜,既能鉴照外物,又能诚守本己、求其放心。
心的修炼需要身体力行,反躬实践才能自得于心。镜子的寓意在于,身体的修行有助于镜子的打磨,这是明心见性的磨镜工夫;而身体首先需要由镜子照影,才能显现出来。真身与假身的分判就在这里。“身似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指的这是这种“著相”,即著于假象,遗忘真实的身体。刘姥姥推开镜子看到反面以至回到真身,从而生起“蠢”“浊”自谦之意,开始了诚意的工夫。而宝玉、黛玉在“你证我证,心证意证”的已证真身的境域中,尚能以磨镜自诚、反鉴自身的工夫随时相警,不可将此“真身”执为实有,由“无可云证,是立足境”进入“无立足境”。
“无立足境”的一个寓意,是上节所述的“迷津”:一个身体随着泪尽才竭而逝去,身心虽合为一体,理学先天图的工夫过程却只能终止于“冬至”的渺茫空旷,石头所记也只是飞鸿雪泥。如果一切仅止于茫茫雪地,黛玉又为何还要留着“残荷”呢?她所说的“干净”之境,其实还有另一个涵义,那就是境(镜)即自身。自我身心的修为就是镜子本身,镜(敬)就是形而上的“理”,持敬即可成己、成物。以心为镜,持着这面镜子,无论照见自己还是别人,都不再有正与反、现象与本质的区分;现象背后已无本质,而是在时时自我提澌反省中被给出和证实的。黛玉去后,“残荷听雨”与“菱花对雪”,分别可以看作宝玉身心合一之后的生活。他依然可以随时自省“何贵”“何坚”,将“真亦假”的反思贯穿在绵绵不尽的身心工夫当中,将自己的生活进行下去。
有理由相信,正如警幻仙子指出迷津那样,“白茫茫大地”的曲子同样是一种警示,为了避免误入如此迷途,只有借助频频“回头”。也唯有在诚敬工夫的深入精微中,神瑛与绛珠的奇缘才不落于泪尽之后的渺茫幻灭,而是因“情悟”得以“虽死不死”。石头上的文字不仅是偶然回顾的印迹,也不是理学框架下循规蹈矩的叙述,而能在灵动幻化的生生妙用中,重新给出一套即现象即本质、兼于理气的话语系统,身体情意上的“养-报”关系在此系统中可以得到反复的给出和重述。
三、诗:幻化之妙
这个“诚镜”的工夫,最精妙的体现在宝黛的诗论中。诗本是“假语村言”,于“无所云”处别出心裁、巧为字句,而可以言顺事成、成己成物,将“大观园”中天人之间的诸多景象烘托出来。在“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一回,贾政命宝玉题名进门山上的一块“镜面白石”,宝玉回答“这本无可题之处”,不如直书“曲径通幽”。有石如镜,恰是“心”的征象,心中所发的情意从无入有,不可直泄出来,只有从别路曲以应物,才有灵通幽微之效。宝黛二人的诗意,如果没有与周遭事物的接映成趣,就不可能生出分花借柳的“沁芳”妙用。
(一)从真心而守理:黛玉的以诗传意
关于《红楼梦》一书,向来有“借书传诗”之说,其中的诗多为黛玉所作,宝玉的诗尚居其次。黛玉不但善于作诗,更擅长教诗。在教香菱写诗时,黛玉发表了一套诗论。首先是格律工整,然而若有了奇句,也可打破格律;而词句新奇尚且没有立意重要,“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不‘以词害意’”的主张其实并非不修饰词句,只要出于诚心真意,词句自然就会不修而修。
真心诚意表现在诗句中,会出现似俗实雅、意味绵绵的感受。就像香菱读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时,感觉像是含着“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这种感受可以追溯到苏轼的“写诗如食盐梅,味在咸酸之外”,不同于苏诗的是,意境的真实淡远之外别有一层“重”的质感。黛玉的诗不但情真,而且意重,这种重量体现在她看似缠绵凄切、实则意蕴凝重的诗句里。海棠诗以“半卷湘帘半掩门”起首,紧跟着的“冰土玉盆”即突出了质感,门虽虚掩着不拒外物,“玉为盆”却挺立起坚贞笃定的心地,如朱熹的“大开着门,端身正坐以观事物之来”。心意诚正,诗句才有幻化情境的妙用,故能“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诗的语言无论“满纸”还是“片言”,无非自题素怨,不需为众人所知解,这又是菊花诗的“孤标傲世携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心境贞静自守,诗意自会绵密不绝,又无一言不与本心相应;而不至于为物境所牵引,沉迷于“庄生蝶”的梦境假象。
专心守理,不为事物所引,同时又主敬以应接事物,这就会立志于事物之上,随一事一物取其合宜,寄予新意。表现在诗句上,自然能够借景寓情,既述旧典而不失新巧奇趣。黛玉虽自谦其诗有伤于“纤巧”,李纨却称赞“巧”得好。诗最忌一泄而出,唯在行止动静之间随物赋形,才可以随时宜其巧趣。书中称得上“巧”的,除贾母外,只有凤姐、与“心较比干多一窍”的黛玉,香菱则紧随黛玉之后,再就是手艺巧夺天工的晴雯。这几个人心意也似彼此相通,却并不为众人轻易领会。“谁家秋院无风入,何处秋窗无雨声”,外来风雨如刀剑相逼,也是心意“纤巧”似乎难免招致的不幸。黛玉的诗越写越悲,乃至于“冷月葬诗魂”等近似“鬼诗”的句子,也是“巧”易“难人”的无奈悲凉。
(二)致真身而易礼:礼因诗情而损益
上文提到,刘姥姥作为真实的身体,对于镜中假身没有丝毫留恋,可以从容入梦也能从容醒来。黛玉讨厌刘姥姥,就像她不喜李义山的诗那样,对这些一眼窥破迷津、却又能出入惘然了无牵挂的人,她保留着畏恐与排斥。她与香菱的契合,可以追溯到两人及其家庭对和尚道士所说的宿命予以共同抗拒。与此相反,宝钗虽也未必把金玉当作真实的好姻缘,然而却能坦然接受,没有任何情感的牵绊。黛玉与宝钗的最终相知,或许在情感的苦痛上达到了相互的同情,但她终究没有那么淡泊,到底是“意难平”的。这位“诗魔”既不能停止写诗,也不能逍遥于无情,而只会笃定的用作诗去践行心意,直至生命的终结。
大观园迎面的“镜面白石”上,宝玉所题“曲径通幽”点明了诗的主旨,即借物寓意,以达因色悟空的妙用。这里的“空”并非“白茫茫”的彻底空寂,而是即空即假的中道。遵从真心的本源情感,以彻悟的真身去践行中道,在诗语的幻化中“生情”“传情”,由诚敬的信言笃行以达情意相知,才会回归“无立足境”的“空空”之境。那么“空”即是“假”,在“假”的幻生中却能维续真实的情意。礼文制度也是假言所幻化,孔子的“礼有损益”是在履行中道的过程中,在遵从真情实意的基础上,随时进行“理”与“礼”的重构与革新。
以上第一节的叙述是以朱熹工夫过程为奠基的。理学的夫妇伦理中,夫妇各主乾道与坤道,身体虽有两个,心却是唯一的,心的察识作用只在夫的“以知帅人”那里,而作为人妇只需以身力行。这种理学架构的弊端是,妇的身体消亡,意味着夫的另一半工夫也将停滞。在此解释框架下,黛玉逝去后,宝玉只落得雪地枯柴般的空廓寂寥。如果这与警幻所说的“迷津”相去不远,那么“速回头”的告诫,在“理”的叙述模式下,应不是叫他去躲避这个结局,因为它是无法避免的。如果宝黛二人的“养-报”关系是天理,那么即便黛玉如妙玉般躲进尼姑庵,也同样难免“欲洁何曾洁”的命运。“回头”的告诫只能是内心回归本真情感的呼唤,并在以诗传情的叙述中,将工夫持续做下去。但以理学夫妇之伦的默契,若与续娶对象没有这种“养”与“报”的深层契合,失去另一半的工夫是难以为继的。
那么余下的可能包括,依然保留理学的工夫论架构,但把夫妇伦理修正为个体伦理。因此,宝玉在失去黛玉后,身心合一的他选择出家,在对黛玉的留恋与想象中把两人活成一个人,把两个人的诗写成一首诗,就像当年续写探春残阙那样。从家庭的幻灭中走向个体性的独立,同时又将天理的证成凝聚在个体身心的气化融合中,自我涵养的同时也在自我回报。由此推己及人,对他人施以恩养,如果得到回报就共同生活,倘若没有感,那么就回到自己的身心涵养。无论身外境域如何,本心的情感总是“遮不住的青山”、“流不断的绿水”,不会因外界干扰而受到阻碍。黛玉在情悟之后求得了放心,从此不再执意于外物,可以设想,宝玉也在黛玉逝后完成了色悟,而在平和心境中著述立言。从他留下的话语中,他希望得到理解的,会不会正是他所期待去完成的更新与变革呢?
注释
① [美]余英时:“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33页。
② “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说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此处有“[张(新之)评]‘真事隐去’,明明说出,则全部无一真事可见,看者正不必指为某氏某处解。……‘通灵’明德也;说《石头》,‘新民’也。以《大学》评《红楼》,我亦自觉迂阔煞人。”下句“一一细考较去”,又有“[张评]真事既隐,尚何所有;既无所有,尚何‘一一’;既无‘一一’,尚何‘考较’;此即是假语村言之案。”理学的解释宗旨在开篇点明,虽注者也自觉迂阔,却难免为之,这便是“真事隐去”,以“假语村言”解说“通灵”之意。冯其庸辑校《重校八家评批红楼梦》(一),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青岛出版社2011年版,第153页。
③ 从理学视角对《红楼梦》做一以贯之解释的,在清人张新之《太平闲人评石头记》一书有典型体现:“宝玉于《西厢记》回中曾云‘不过大学中庸……’,读此回上半演《大学》,下半演《中庸》,而以一‘善’字串到底,便明此意。”张新之本,妙复轩评本《评注金玉缘》,凤凰出版社1974年版,第三十一回第32页反面。
④⑮ [美]浦安迪(编释)《红楼梦批语偏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⑤ 《论语·季氏》:“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⑥ 俞平伯(评点)《红楼梦》(上),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⑦ “这石凡心已炽,那里听得进这话去,乃复苦求再四。二仙知不可强制,乃叹道:‘此亦静极思动,无中生有之数也。’”俞平伯(评点)《红楼梦》(上),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⑧ 朱熹:“若是在家,有父母合当奉养,有事务合当应接,不成只管静坐休。”(《朱子语类》卷二十六)
⑨ 《周易程氏传》卷一《乾传》:“分而言之,则以形体谓之天,以主宰谓之帝,以功用谓之鬼神,以妙用谓之神,以性情谓之乾。”朱子曰:“功用,言其气也;妙用,言其理也。功用兼精粗而言,妙用言其精者。”叶采解:“功用,造化之有迹者,如日月之往来、万物之屈伸是也。往者为鬼,来者为神;屈者为鬼,而伸者为神也。妙用,造化之无迹者,如运用而无方、变化而莫测是也。”[宋]朱熹、吕祖谦编,叶采等注《近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朱熹又有诗《鬼神》:“鬼神即物以为名,屈则无形伸有形。一屈一伸端莫测,可窥二五运无停。”《朱子全书》第2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⑩ 朱熹:“诚,实也。意者,心之所发也。实其心之所发,欲其必自慊而无自欺也”,(《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
⑪ [清]李道平著,潘雨廷点校《周易集解纂疏》,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93—194页。
⑫ “代儒往前揭了一篇,指给宝玉。宝玉看是‘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宝玉觉得这一章却有些刺心,便陪笑道:‘这句话没有什么讲头。’代儒道:‘胡说!譬如场中出了这个题目,也说没有做头么?’宝玉不得已,讲道:‘是圣人看见人不肯好德,见了色便好的了不得。殊不想德是性中本有的东西,人偏都不肯好他。至于那个色呢,虽也是从先天中带来,无人不好的。但是德乃天理,色是人欲,人那里肯把天理好的象人欲似的。孔子虽是叹息的话,又是望人回转来的意思。并且见得人就有好德的好得终是浮浅,直要象色一样的好起来。那才是真好呢。’代儒道:‘这也讲的罢了。我有句话问你:你既懂得圣人的话,为什么正犯着这两件病?’”冯其庸辑校《重校八家评批红楼梦》(三),第八十二回,“老学究讲义警顽心 病潇湘痴魂惊恶梦”,青岛出版社2011年版,第2005页。
⑬ 《孟子·公孙丑上》:“‘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的“知言养气”意谓着“立心”与“养气”的合一。宝黛从争吵到平静,以至于黛玉不再需要他表白,可谓“知言”。
⑭ “[张评]曰‘空空’,曰‘警幻’,皆作者自命也。 ‘空空’为体,‘警幻’为用。”于“改《石头记》为《情僧录》”,有“[张评]圆明一点本非空。‘僧’,空也。情空则‘性’见,所谓水落石出。”冯其庸辑校《重校八家评批红楼梦》(一),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青岛出版社2011年版,第157、159页。
⑯ 冯其庸辑校《重校八家评批红楼梦》(一),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青岛出版社2011年版,第257页。
⑰ “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下玉粒金莼噎满喉。照不见菱花镜里形容瘦。”此处有张评:“此是黛玉,乃一心所专注也。”冯其庸辑校《重校八家评批红楼梦》(一),第二十八回,“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青岛出版社2011年版,第758页。
⑱ 西园主人:“泪盖有无言之隐矣。际其两小无猜,一身默许,疑早有以计之矣。何以偶入邪言,即行变色,终身以礼自守,卒未闻半语私及同心,其爱之也愈深,其拒之也愈厉,虽知心鹃婢,非特不敢作寄简红娘,而侍疾回馆,镜留菱花之夕,不过明言其事,代为熟筹,且有面斥其疯,欲将其人仍归贾母之言,严以绝之者也。盖以儿女之私,此情只堪自知,不可以告人,并不可以告爱我之人,凭天付予,合则生,不合则死也。”冯其庸辑校《重校八家评批红楼梦》(一),“重议评点派”,青岛出版社 2011年版,第19页。
⑲ “放心”与“不放心”,分别出于第一回僧道口中、第三回王夫人对黛玉不要“沾惹”宝玉的嘱咐中。“只听道人问道:‘你携了此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现有一段风流公案正该了结……(指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的事)’”此处张评:“是‘道’问,是‘僧’答,有‘朝闻道,夕死可’之隐义。”“(王夫人)但我最不放心的却有一件……”此处张评:“叙宝玉于其所自出,而开口用‘不放心’三字,直接首回僧道口中‘你放心’也。”冯其庸辑校《重校八家评批红楼梦》(一),第159、216 页。
⑳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一),卷第十五,中华书局1994年版,卷第十五,第286页。
㉑ 黛玉“菊梦”:“篱畔秋酣一觉清,和云伴月不分明。登仙非慕庄生蝶,忆旧还寻陶令盟。睡去依依随雁断,惊回故故恼蛰鸣。醒时幽怨同谁诉,衰草寒烟无限情。”“菊梦”其实是以“一觉”喝破梦局,回复“陶令”明节,最终以“情”点题。冯其庸辑校:《重校八家评批红楼梦》(二),第10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