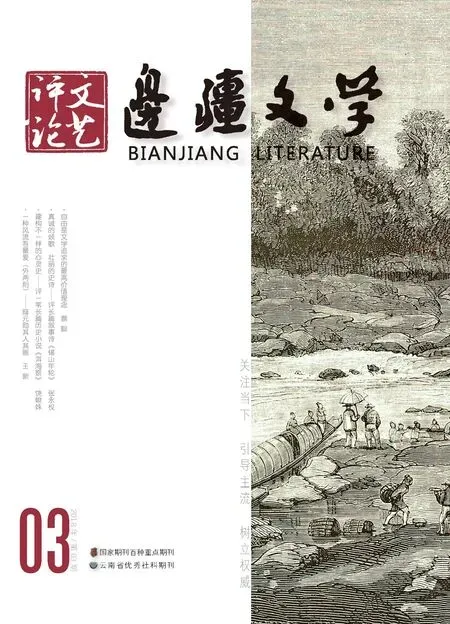彝剧:激腾生命的乐舞
杨荣昌
《毛诗序》云:“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由此可见,人类的情绪勃发,总是通过“手舞足蹈”来表达。千里彝山是一片歌舞的海洋,尤其位于云南腹地的楚雄彝族自治州,这里三山鼎立,二水分流,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这块土地上彝族人崇虎尚黑的精神气质和热情阳刚的民族性格,每逢盛大节日,彝族人围着火塘放歌打跳,表达对生活的热爱。祭祀场、火塘边的吟诵、歌唱等,成为口传文化流播的重要方式。清朝开始流传于双柏大麦地的《阿左分家》和楚雄东华等地的《大王操兵》,或从民间叙事诗演变而来,或脱胎于花灯形式,在歌唱中伴有相对丰富的舞蹈,并已注意塑造人物性格,表现彝族人的生产生活,是彝剧形成的最初雏形。
民间文化有其坚韧的生命力,这源于劳动人民对生命本体的内在自觉。新中国建国前的1947年,正是风雨如晦,文网罗织的年代,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大姚的小学教师罗守仁、李凤章吸纳了彝族群众中流行的民间歌曲和舞蹈,编演出《委员下乡》等剧目,表达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强烈不满,引起了共鸣。新中国建国后,以民间艺术形式来反映人民生活的演出方式受到了极大的欢迎,一种由自发到自觉的创作方式逐渐显现。1958年,由杨森等人集体创作的《半夜羊叫》,把目光投向彝族人日常的生产生活,注重对人物性格的深度把握和形象刻画,在表演上,以彝族的舞蹈、曲调为主要的艺术元素,更加注重表演的生动性和活泼性,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同年底,文化部在大理召开“西南区民族文化工作会议”,《半夜羊叫》受邀演出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受到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著名作家夏衍的高度评价,也正是这次会议上的观摩演出,来自楚雄州的彝族戏剧被正式命名为彝剧,成为中华多民族戏剧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杨森不仅有优秀的创作天赋,还有表演的才能,他将彝族民间的歌曲、舞蹈艺术搬上舞台,从表演的一招一式、一腔一调,到舞台布置的一景一物,都力求传神,使来自民间的“草根”艺术上升为舞台艺术。
新时期以来,党的拨乱反正政策使一大批在极“左”年代受到迫害的知识分子恢复了名誉,焕发了艺术创作的青春。彝剧工作者也一样,在国家和民族走向新的希望的时代背景下,他们将自身对生活的感受融入国家命运的思考之中,与时代同呼吸,和人民共命运,创作演出了一大批饱含深情的优秀剧目。赵星耀的创作在思想艺术上可谓领时代风气之先,他开始彝剧创作的八十年代初期,民族艺术已完成了宣传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而转向反映改革开放带来的人们新旧思想的交锋,由此展现宏阔复杂的社会面貌。《歌场两亲家》描写了当下社会带有普遍性的独生子女婚姻问题,因其题材贴近时代,直面矛盾,有极强的社会性意义,在“云南省1982年现代戏创作节目调演”中荣获优秀剧目奖。他的《银锁》同样直面社会现实,提倡生男生女一个样,诙谐幽默,妙趣横生,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卜其明的《掌火人》,反映彝族山寨中进步与保守思想的交锋,最后代表保守思想的阿举终于认识到自己的落后,选择了进步的生活的方式,紧跟上时代的步伐。该剧于1994年荣获全国“少数民族戏剧创作”铜奖。丁伯廉的《篾独尼闹店》,更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彝族山寨中的反面角色,篾独尼好吃懒做,大队长鱼肉乡民,他俩是“红眼病”的代表,遭到人们的唾弃,酒店的年轻夫妇则是勤劳致富的典型,具有鲜明的时代感。这部剧因触及社会通病之尖锐,人物刻画之形象深刻,是彝剧发展以来的代表性剧目,曾荣获全国“少数民族戏剧创作”铜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戏剧创作,多塑造了带有人格缺点的反面形象,在对其进行批判的同时,极力阐扬一种新的价值观。这也反映了社会风气对艺术创作的包容。可喜的是,这一时期,剧作家们已开始注意挖掘彝族厚重的历史,不仅吸取本民族丰厚的艺术营养,如歌曲、舞蹈等,而且能从历史传说中获取创作的富矿。卜其明、丁伯廉创作的《铜鼓祭》,反映了云南哀牢山区部落之间的纠葛与战争,剧中最重要的器物铜鼓,是一种具有原型意义的美学意象,呼应了楚雄作为“铜鼓之乡”所独有的文化内涵。鲁格创作的《咪依噜》,取材流传于彝剧发祥地大姚昙华山的彝族美女“咪依噜”的凄婉传说,她以身饲虎(土官)、拯救姐妹的悲壮之举,成为千百年来彝族人心中最为圣洁的形象。传说她死后化为洁白的马缨花,又被她爱人悲痛的血泪染红。该剧对咪依噜的故事进行了审美化重构,触及了彝族人民敏感而柔软的心弦。这两部历史传说剧,均表现了一种崇高的壮美。
历史进入新的世纪,彝剧更加蓬勃发展。这一时期的创作更注重与现实的紧密结合,以罗仕祥、冯洁创作的《臧金贵》为代表。这是一部七场大型彝剧,以深圳中国招商银行到楚雄永仁县挂职而去世的臧金贵为原型,表现了这位优秀共产党员心系贫困山区,为彝乡脱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感人故事。同样是讴歌优秀共产党员的,还有大型彝剧《杨善洲》,它讲述了原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退休后扎进故乡大亮山创办林场的感人事迹,生动再现了杨善洲一辈子忠于党的事业,心怀爱民为民之心的赤子情怀。作为戏剧之一种,彝剧创作的成功,在于它紧紧把握了时代的脉搏,传达出人民群众对优秀艺术的强烈期盼,在剧情设置上突出表现矛盾交锋,注重挖掘人性的深度。夏德金的《疯娘》是一出大型无场次彝剧,根据王纪恒小说《我的疯子娘》改编。它紧紧抓住“疯娘”荞子对儿子阿石强烈的爱来表现。在生活琐事的处理上,荞子神志不清,常为家人惹来麻烦,但对儿子的思念和爱护上,却有着超出常人的地方,表现出一种脐带相连的母子情深,尤其最后荞子为了给阿石摘桃子而坠崖身亡,更是将一种崇高之美升华,观众无不潸然泪下。值得肯定的是,《臧金贵》《杨善洲》《疯娘》三部剧,题材的原型均与彝族无关,但是通过创作者的大胆转化,尤其是充分吸收了彝族民间艺术的曲调、唱腔、舞美,以及独具彝族特点的生活环境,使其构成人物活动与心理展示的特殊背景,从而有了浓郁的彝族风味。特别是《疯娘》,将原小说故事中的主角变为彝族的母亲,更生动地展现了天下母亲的感人形象。如此看来,艺术的魅力在于探究并呈现人性的复杂,优秀的作品,可以超越民族、地域与国界。
彝剧是歌、剧、舞三者高度融合的综合舞台艺术,除了灯光、舞美、布景非常重要之外,好剧本是基础,演员是关键。彝剧的发展离不开一批才艺精湛、品德高尚的演员的努力。从杨森扮演的力立颇(《半夜羊叫》),到李光秀扮演的麻纳梅(《银锁》),再到张吉顺扮演的杨善洲(《杨善洲》),高燕扮演的荞子(《疯娘》),张留福扮演的臧金贵(《臧金贵》)等,都已成为彝剧发展史上的经典。此外,老一辈的郭思九、朱柄,中年的冷青、吴甘,年轻一辈的李垠,以及英年早逝的朱晓云等,他们视彝剧为生命,或进行理论探索,或开展艺术创作,或从事舞美设计,都对彝剧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从表演上看,彝族人长于抒情,歌词普遍采用五言、七言和长短句,常用比兴手法来表情达意,唱腔上又充分吸纳民间传统的“梅葛调”“阿塞调”等,曲音婉转,绕梁不息。语言表达上也采用汉语彝腔的方式,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彝族气息,又能让广大的观众所接受。
乌蒙磅礴,哀牢纵横,金沙江浩荡东去,一泻千里,这方水土长歌谣。彝剧植根于广袤的彝山大地,背后有深厚的彝族民间文化作支撑,有能歌善舞、热情奔放且具有鲜明诗性特质的彝族儿女的创造力,作为推动它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相信在今后的艺术变革中,它将继续带着文化母体中的“羊膻味”和“松毛气”,广泛吸收外来艺术的优秀因子,不断丰富、充盈自己,焕发出长青的生命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