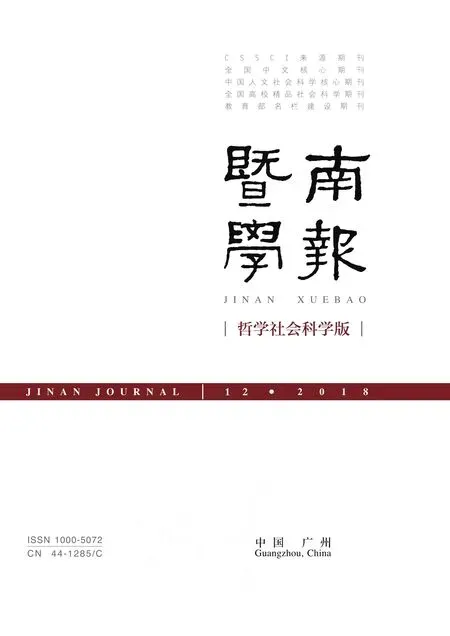《资本论》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一个门径
贺 渊
《资本论》作为马克思的代表作,对于20世纪初叶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是一座难以攀登的理论高峰,因为不同的语言平台、滞后的社会形态,颇有夏虫难以语冰之感。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仍对他们有莫大的吸引力,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党人是马克思主义最初的欣赏者与宣传者,也是《资本论》早期的传播者之一。
1906年,朱执信在《民报》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等文章论及《资本论》。1919—1920年,《建设》杂志第1卷第4期至第3卷第1期,连载以戴传贤署名翻译考茨基著的《马克斯资本论解说》。1927年10月,《资本论解说》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戴季陶(传贤)在该书的序言中说:“这一本书的翻译,我和执信先生两人共同作了二分之一,最后的校稿都是执信先生的工作。和汉俊共同作了二分之一,差不多是汉俊译成初稿,我任校订。最后在今年才由汉民先生全部译完,并且把全书从新校订过。”从《资本论》进入国民党的视线开始到这本通俗读物《资本论解说》出版,共经过二十一个春秋,仅仅是《资本论解说》一书的翻译,前后七年,而且,译者除了李汉俊外,都是国民党重要的理论建设者。戴季陶曾说:“四个译书的人,执信先生是尼采和马克斯的合成人格,汉俊是马克斯主义者,展堂先生是马克斯研究者,我只可以算是一个介绍者罢。”他们怀着怎样的心境接触《资本论》,有什么必要辗转翻译这一在他们看来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的理论呢?他们又是在什么程度上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呢?
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为一个科学研究项目就已经开始。然而,历经百年,研究者较少意识到作为一个群体的国民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及变化,即使有所论及,也只是集中在单个人物研究之上,比如朱执信、戴季陶、胡汉民等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的贡献和努力,因此,更没有人重视多名国民党人参与翻译《资本论解说》这一现象。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以及翻译部门,对以往文本进行研读时,着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此类文章,虽然有一定的思想深度,但缺乏历史背景的分析,他们一般会注意考茨基这本介绍《资本论》的通俗读物,但是,由于在戴氏翻译之前,这部考茨基著、高畠素之译日文版《资本论解说》已经由陈贤溥(署名“渊泉”)转译成中文,以《马氏资本论释义》之名,陆续刊登在1919年6月至11月的《晨报》上,后人自然重视陈译本,忽略戴译本。更何况,国民党后来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也使人们对他们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的所作所为缺乏仔细展开,而对其阶级的属性则急于批判,不过,近年来这种状况有所好转,比较客观地反映国民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真实态度的文章正陆续出现。
本文试图真实反映早期国民党人在思想上对马克思主义由欣赏、吸收到置疑和反对的历程,呈现《资本论》在中国传播的又一途径。虽然,戴季陶、胡汉民以反马克思主义告终,但是,他们曾经的译介毕竟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留下了不应抹去的痕迹。
一、初识《资本论》
同盟会时期,为规划将来的社会,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提出建立一个民生主义国家的设想。他们的观点与梁启超为首的以资本主义为发展方向的改良派发生理论冲突并引起尖锐论争。
朱执信在论战中的表现,显示出他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颇为了解,尤其他对马克思及《资本论》的介绍,达到了当时最高的水平。他说:“顾自马尔克(即马克思,下同,作者注)以来,学说皆变,渐趋实行,世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他指出马克思的代表作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共产党宣言》被“万国共产同盟会(共产主义者同盟,作者注)奉以为金科玉律”,而“学理上之论议尤为世所宗者,则《资本史》及《资本论》也”。无疑,朱执信对马克思的介绍是准确的。
关于《资本论》,朱执信言简意赅地进行了介绍和分析。他说:“马尔克以为:资本家,掠夺者也。其行,盗贼也。其所得者,一出于朘削劳动者以自肥尔。”朱执信在文中对剩余价值理论的解释是:“譬有人日勤十二小时,而其六小时之劳动,已足以增物之价,如其所受之佣钱。余六时者,直无报而程功者也。反而观之,则资本家仅以劳动结果所增价之一部还与劳动者,而乾没其余,标之曰利润,株主(即股东)辈分有之,是非实自劳动者所有中掠夺得之者耶?”他说明工人每日劳动的时间中,包含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所生产出来的是剩余价值,也即朱执信文中的“利润”,这一部分被资本家无偿占有。
朱执信追溯马克思《资本论》的思想来源,以为受李嘉图关于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原理的启发,李嘉图曾说:“凡财产皆从劳动而出,故真为生产者,劳动之阶级也。然则有享有世间财产之权利者,非劳动者而谁乎?……劳心者所受之禀给,百倍劳力者而未止。此何理也?……然而,资本者,本劳动者所应有之一部,遂全归于彼掠夺者,与循其本,吾不知其所以云也。溯而穷之,欲不谓资本为掠夺之结果而劫取自劳动家所当受之庸钱中者,不可得也。”他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在吸收李嘉图思想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
朱执信批判了两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资本起源于积蓄,并不是掠夺。朱执信以为资本之为资本有一个历史的渐进过程,当“孤立经济时代”,此时资本家与劳动者同为一人,最初的资本可能是由积蓄而来;然而,经济发达之后,所谓“交通既繁,借贷之事乃起,而劳动者或用他人之资本矣,既乃有雇佣之制。夫雇佣者,受给而生产益我,故久且不废,然而劳动者之祸于是焉兴。蓄积由庋藏之事益少,而其由掠夺之事渐盛矣。”至于当前“貯蓄者乃无纤毫”,因此,“岁入则大半为赢利,小半为庸钱,虽欲不谓之掠夺盗贼,乌可得哉?”他指出当前资本来源于掠夺。另外有一种观点认为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是契约的关系,而非强占。朱则以为贫富分化,工人“不当权故”,工人和资本家立于不平等地位上签订的契约是“虚伪强迫”的,“故马尔克之谓资本基于掠夺,以论今之资本,真无毫发之不当也”。
朱执信理解到剩余价值的来源,明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资本制度的不公正,体会到造成这一现象的制度性原因,但透彻深入的分析似嫌不足。
国民党早期对社会主义研究颇有心得的人还有胡汉民,他在1906年发表的《告非难民生主义者》一文中,坚持“土地国有”和“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胡汉民文中说:“但论资本国有之问题,则今之最能以资本论警动一世者,莫如马尔喀及烟格尔士(即马克思和恩格斯,作者注)。而二氏不惟认许自用资本之私有,即农夫及手工业者之资本私有,亦认许之。故日本河上学士曰:‘社会主义者,往往慢言,凡资本以为公有,禁其私有,故世人惊之,识者笑之。若夫拘墟之学者,则喋喋其不能实行,以为覆斯主义之根本。’”胡汉民对《资本论》的介绍远不及朱执信,但是,他突出了《资本论》的“警动一世”,并说明社会主义并不完全取消私有制实行完全的公有制。
朱执信所言,涉及资本的原始积累、剩余价值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来源,胡汉民触及到所有制。当时,朱执信、胡汉民等革命党人均在日本,他们显然受到日本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片山潜及河上肇等人的影响。1905年幸德秋水和片山潜翻译了第一部日文本的马克思著作《共产党宣言》。同年,河上肇出版了《新史观》这部译著,原作者是美国经济学家塞利格曼(Edwin Robert Anderson Seligman,1861-1939),所著原名为《历史的经济的说明》,主旨在讨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这样,国民党的历史上,不但出现了介绍《资本论》的文章,并拥有了将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的跳板——日本,以及欣赏马克思主义的人物朱执信、胡汉民等。
二、翻译《资本论解说》收获唯物史观
国民党人头脑中“资本”二字内涵时有差别,比较多的时候,他们将“资本”理解成“本钱”、“资金”,视《资本论》为单纯的经济学说。比如1912年12月,戴季陶在《民国经济不振之原因》一文中说:“论中国之经济现状者,未有不曰中国非贫也,所缺者,流通资本也。”1919年3月,孙中山在演说中讲:“资本问题,是今天世界上最大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兄弟有《实业计划》一书,主张以外资从事于建设生利事业”。孙中山也将资本问题仅仅归属于经济的范畴。戴季陶在《资本论解说》的前言中说:“我对于马克斯的经济学说,很想要用一番切实研究,只可惜不能读他的原书。……所以我译这部书的意思,与其说是介绍,还不如说是学习,因为我对于马克斯的经济学说,本来是毫无门径的。”当然,马克思的《资本论》本来也是一部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专著,但是,如果仅仅当成经济学的书籍来读,肯定是不够的。戴季陶一旦翻译《资本论解说》,便应该能够感受到考茨基这位唯物史观的继承者和宣传者,将《资本论》中的唯物史观作了充分突出的诠释。由此可以肯定,虽然此书翻译得十分艰涩,但戴陶季却深受该书的启发。
《资本论解说》一书中,考茨基参照《资本论》原著,也是以“商品”开篇,为了讲清楚资本主义“商品”的特性,文中简要地梳理了从原始的共产村落到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再至以商品生产为特质的社会的发展过程,并引用了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书中将此文译为《赁银劳动与资本》,作者注)中的关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典型概括。
与此同时,《建设》杂志登载了河上肇著、苏中译的《见于资本论的唯物史观》,河上肇在文章中强调:“马克斯资本论,全体都有唯物史观底血管在里面流通。”他引用马克思《资本论》序言所述:“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他使用语录体的方式摘录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唯物史观的主要观点,说明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一如自然科学寻找规律一样,也试图在人的社会的发展中找到规律。同时,他认为马克思在他的书里,不时地体现“社会组织是进化的东西,而且那社会组织进化底原因是社会组织和生产发展当中底矛盾冲突。这两个主张本是被唯物史观包含的社会组织进化论中两大要素”。他大段地引用马克思《资本论》中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中的“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概括地叙述了关于资本主义诞生、发展到最后资本主义私有制丧钟的敲响的过程,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灭。文中,还引用了《资本论》第三卷第三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等内容。河上肇此文,对于没能看到马克思《资本论》全文的戴季陶、胡汉民有极大的引导作用。
胡汉民在《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一文中,提出《资本论》当然是唯物史观最为成熟的运用。胡汉民归纳唯物史观如下:(1)“人类因社会的生产力而定社会的经济关系。以经济关系为基础,而定法律上政治上的关系,更左右其社会个人的思想感情意见。其间社会一切形式的变化,都属于经济自然行程的变化……”(2)“物质生产的方法变化,一切社会的关系跟着变化。人类所有种种情感、想象、思考以及人生观,其根据都在社会的生活状态之上,即从物质的组织,及跟此发生的关系而起。”可见,胡汉民基本上正确地掌握了马克思社会历史观的精髓。
戴季陶细化物质生产方法的进化,赞成工具的改进是社会不断进化的直接动力。工具的进步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起到决定的作用,所谓“工具是决定经济的组织的,一旦工具发生了大变化,于是生产、分配、交换、交通,一切社会之经济的条件都要随着变化”,“人类社会的一切组织形体没有不随应用工具的变迁以为变迁”。马克思主义认为,创造和使用工具,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生产工具是社会生产力中的主要因素之一。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化和发展开始的。生产力的提高,将最终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戴季陶突出了生产力中的重要要素生产工具的地位,一定程度上承认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戴季陶认为生产与交换是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他曾这样说:“构成社会的基础在哪里?就是:支持人类生活所必需的物品之‘生产’及其生产物的‘交换’”。他的结论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决定了分配方式和社会制度,也就确定了各阶级在社会中的地位,即“在历史上,一切分配财富的方法,一切区分阶级构成秩序的社会制度,都由生产物品的方法和交换生产品的方法如何而定”。“一国一社会经济的组织如何,就是决定一国一社会一切生活的基础。”
可见,译介《资本论解说》,使国民党人得以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并被唯物史观所吸引。当然,孙中山建立同盟会提出三民主义时,民生主义即包含了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防范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双重任务。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根本上突出了生产力对于人类社会的决定力量,更加强有力地证明了发展生产力的至关重要性。同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反资本主义的理论,与民生主义合拍。因此,国民党的民生主义理论,使戴季陶、胡汉民等国民党人能够较快地吸收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原理。
三、运用唯物史观以观中国
对戴季陶、胡汉民而言,唯物史观的魅力在于提供了一种寻找社会发展规律的方法。他们借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1919年8月戴季陶发文说:“胡适之先生著了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我自己却常常在想,哲学史的著作固然是一个极大的工程,经济发展史的著作,更是一个极大极重要的工程。因为人类的一切进行都是从经济的进步来的。一个时代的思想,受那一个时代经济组织的影响很大。”他希望有人写一部“雄大深邃”的经济发展史,把中国几千年来的经济生活状态和变迁显现出来,肯定会对中国思想生活革新起大作用。恰好此时,胡汉民与他不谋而合,想写一篇这类文章,戴季陶听后,“喜欢得了不得”。
胡汉民以《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为名发表了戴季陶期待的文章。胡汉民认为主义的产生是由于“社会的关系和社会的物质的生产不能调和,于是成为问题,拿一种主义理想调和社会的关系,于是发生学说。一切主义理想,皆是历史的生产物,又是移动的生产物”。哲学家的头脑同样受社会生活、社会要求的左右。以上述观点审视中国哲学盛衰的历史,胡汉民满意地得到了以下的结论:他认为春秋战国时代(周朝末年)之所以成为思想盛世,是由于社会经济结构急剧变动,井田制被破坏,从根本上动摇了社会。尤其突出地表现为战乱不休,人民颠沛流离。于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各种思想应运而生,伟大的思想家,如孔子、老子、孟子等纷纷出现。西汉后,中国思想界略起波澜,但杰出人物寥若晨星,关键是井田制废除后,社会在封建制下逐渐稳定,以后社会结构变化甚微。
透过历史以观当前,他看到了新思想的曙光:“最近中国由通商的结果,受世界工业革命的影响,经济的压迫无法抵抗,四万万人起了极大的生活不安的现象,从前一切社会关系都要动摇,求其比例,应该和二千六百年前井田制度变坏的时代,遥遥相对。这真是‘化而欲作’之时,依晚周诸子的陈例,我们对于思想界有很大希望。”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说古论今,很有说服力,且给人们带来了希望。
戴季陶则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革的角度,指出最近四十年来是中国大变动的时代,外国机器制造品大量地输入,其先进的机器生产方式震撼了中国旧有的手工业。由于“工业革命的事实不从本国里面发生,机器力的压迫都从外面输入。这一个极大的压迫加到中国人的身上来,于是乎就引起了一个极大的生活不安的事实来”。改革的要求也就从这生活的不安里生了出来。他总结中国的改革经历了由买外国的枪炮,到自办厂矿,最后是政治改革、主张民权的三个时期,但每一期的改革,都没能阻止外国的货物进入,这一切证明了“中国所有的乱事,根源都是在机器制造品输入一件事上的。所以,说破坏就是经济上的旧物破坏,说建设也就是经济上的新物建设,战争的原因就是在此,一切政治的思想的争斗都是为此。”
依据经济结构的状况,戴季陶清晰地描绘出当时中国社会的结构:“我们中国今天刚刚是在经济组织大变迁的时代。好像在一个花园里,前后不同地下了许多种子。有的已经开花,有的刚刚含苞,有的仅仅抽苗,有的连种仁都没有破。比如上海地方,已经是工业革命盛行的时期,渐次趋向到工业革命完成的时期,资本经济的极致将要快实现了。却在沿江沿海许多地方,有的还是在工业革命的初期,有的还没有梦见新工业是甚么样子,有的地方还完全是一种庄园经济的组织。川、滇、黔等处山间,还留着许多原始共产的小社会。就经济进化史上观察,差不多从上古到现代五六千年所经过的各色各样过程,都完全实现在中国。”他的分析,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中国的社会状况和性质。我们知道对于中国社会性质展开分析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而戴季陶早在1919年前后即有此认识,的确十分超前。
面对社会的巨变,戴季陶说:“中国人现在正在进化的阶段上,好像蛇脱皮一样,里面的新肌肉拼命地生长发达起来,外面这层阻碍新肌肉发达的旧皮又还生在新肌肉的上面,要他脱去,一定要多少的时间。”他表述了新的生产力要在旧社会母体内逐渐成长,强调了这种变化需假以时日,语言中带有稍安勿躁的劝诫,也可以体会到他对于渐进发展的认同。
那么,中国该往何处去呢?戴季陶以十分形象的笔触,描述了当时中国人在世界潮流面前的情景:“大家都在若有识若无识的当中随着世界的新潮走。这个当口,恰被一个向右转的德谟克拉西,向左转的棱霞里士姆,卷到潮流的漩涡里,漩到头昏眼花,究竟向右呢,向左呢?自己也分别不出来。好容易有聪明的人,在自由和平等的交流点上发现出一个社会民主主义来,以为这是一条可以走的路了,谁知刚上了路,就看见了前途横着几条分歧的大路。向哪一条走好呢?法国人向那里去了,英国人向那里去了,德国人俄国人都各有各的路去了。顾得东来顾不得西,可怜这睡眼朦胧的中国人,竟变成了中心无主的迷路儿。”戴季陶明确自己的立场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戴季陶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为何分出诸多派别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这个主义,照我看来并不是一个严格的主义,只是一个世界的时代精神。这个时代精神,是普遍地照住全世界。”他认为其中的原因就是:世界“各民族历史的精神及现代境遇不同”,当“这各民族特殊的性质,在世界的时代精神笼罩下面,都各自自由发展起来,去迎合这世界时代精神。所取的趋向虽是在世界的协同进化,所用的方法——就是进行的途径——却是都现出一种差别的形体。”他以为一个民族,只有在全时代的精神下才能获得向上发展的力量,同时,他呼吁应该回头看看本国的情况,“自己开辟的才是自己的正路”。由此可以看出,戴季陶杜绝了走西方资本主义老路的旧念,肯定了人类社会和发展前景只有一个,这就是社会主义。而所谓的社会主义,并没有一定的模式,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因此也应该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当时,戴季陶作如是说,矛头显然是指向全盘西化的倾向,力图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立场。但是,这其中的民族情结却埋下了以后他的民族本位思想的种子。
戴季陶在翻译《资本论解说》的过程中,与李汉俊、沈玄庐、陈独秀等人密切来往,参与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活动,但当中共正式建立时,戴季陶却脱身而去。他的这一举动,与他在理论上的认识不可分离。他在迎接唯物史观的同时,却与正在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分道扬镳。
四、参照《资本论》解读工人运动
戴季陶对于中国早期工人运动态度上的变化,充分反映了《资本论解说》一文的翻译工作对于他的思想产生了何等重大的影响。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戴季陶抱着指导、规范工人举措的目的关注工人运动。他向孙中山披露了自己的想法:“我受了罢市风潮的感动,觉得用温和的社会思想来指导社会上的多数人,是一桩很要紧的事。”调和劳资关系是这一时段戴季陶努力的方向。
1919年9月以后,戴季陶一改以往对工人运动的态度,发表文章,以生存权、劳动权、劳动所得权作为衡量人权的标准,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所受的非人待遇。戴季陶对于资本主义的揭露,完全是《资本论》式的:劳动者“在这个以私有财产、自由竞争、工银制度为基础的商业的世界经济组织下面,一方面是完成了经济自由人的地位,同时就沉沦到最低的社会阶级里面去了”,他们除了一双手和一身体力外,一无所有,被剥夺了一切作为人所拥有的自然权利,戴季陶将这种自由视为“可以做叫化子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最终就是“把这大多数人都化为少数人服役的机械”,他的结论是:“今天中国所谓的进步是甚么?一句话讲完,就是劳动的商品化,……就是私有财产制下自由竞争的必然结果。”他突显出“产业先进国”所带有的标志:“私有制”、“自由竞争”、“劳动商品化”,揭示出中国正在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路,无产阶级正在形成。
戴季陶一度认为劳资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1920年,他在《新年告商业诸君》中批判胡适的观点,胡适认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使可以互助的劳资两阶级对立起来。戴季陶反驳道:“互助的基础是要站在平等上面的。两个绝对不平等的阶级要他们讲互助,这是个笑话。而且阶级斗争的事实,并不是由马克斯的‘阶级斗争说’而起。不过这历史上的重大事实,被马克斯的灵心炯眼认识了,从一切历史的关系里面抽象了出来”,他批评胡适倒因为果。以“五四”运动时中国的社会实况为例,戴指出运动的发生,是由于生活的不安,这种不安是多方面的。因此,运动爆发以后,无论是工人,还是资本家,出于各自的考虑,投身于运动。“‘五四’运动、‘六五’运动的基调本是在平民生活改造的上面……结果,直接间接地促起中国资本阶级劳动阶级两方面的阶级意识。同时也就促进了工业革命运动——资本家主义的大工业勃兴和劳动阶级团结运动同时并进的新形式来。两个运动各形成一个力的中心,两力的方向成为正反对,不到一个力打消一个力的时候,冲突是无已时的。”他以为中国的阶级已经有了觉悟,阶级斗争将不可避免,最后的归宿是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
戴季陶汲取马克思《资本论》对工人状况的调查研究方法,以统计数字说明由于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厚,中国工人所受压迫比欧洲工人更为深重,上海中外工厂工人劳动时间长达12小时,工资很低,雇佣不满十岁的童工和妇女。他以上海英美香烟厂的女工在罢工时提出增加夜班的要求为例,指出中国工人的罢工,正好与当前世界的工人运动以减少工时为目的的趋向相反,剖析说明“第一,就是资本的生产组织下面劳动机会竞争的结果,使得他们只有走这悲惨的路。第二,就是中国工业不发达,外国直接输入的机器生产品太多,这无业者的增加更使劳动机会的竞争剧烈。第三,就是这些工人自身没有受过智识感情和意志的训练,所以就没有觉悟的能力和机会”。因此,他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失业者太多,解决工人的问题应该分成两部分:一是就业;二是在职工人的生活改善。
时至1920年“五一”,戴季陶关于工人运动的主张,又回到了去年同期。他认为:“倘若真是为劳动运动尽力,就应该暂时不要用甚么‘政治的罢工’来运动工人。……现在上海的工人最要紧的就是生活的改良。离开了改良生活的问题,无论甚么事他们本身都不能享用的。政治的劳动运动,至少都要劳动者本身的生活改善了多少,欲望增进了多少,他们自己感觉到‘由劳动者管理工场’‘由劳动者所有生产机关’的必要,了解了这些意义,然后才能发生,着手运动也才有效果。”随后,他分析当前的运动,就是社会的运动、经济的运动、文化的运动,当前的工作,就是宣传与改良工人的生活条件。
戴季陶对工人运动的态度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前后发生两次转变。从五四运动到1919年9月,他的主张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采取劳动法等一系列缓和劳资冲突的政策影响。1919年9月后,他对劳动运动的激进态度,以及字里行间《资本论》式的观点和方法,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他正在翻译的《资本论解说》。1920年5月以后,他基于对中国国情的分析,以为中国的产业落后,社会发展不均衡,工人阶级不成熟,共产主义运动不适合中国,主张避免阶级斗争,选择渐进的、和平的发展道路,又和他对苏维埃运动存疑有关联。他的理论认识与实际主张相一致,在国民党中具有典型意义。
五、出版《资本论解说》的意图
1927年1月,戴季陶率先主张印行出版1919年翻译的《资本论解说》,得到了胡汉民的积极响应。在戴季陶与胡汉民提出民生史观之后,他们再版这部著作意图何在呢?
戴季陶在书的序言中说:“马克斯的资本论,不是很容易了解的书,更不是读一两篇小论文便可以随便讲马克斯主义是如何如何。要研究马克斯的经济理论,不单要把他的著作,彻底读过,并且至少要懂得亚丹·斯密、李加德、马尔萨斯三家的经济理论和马克斯前后的社会主义思潮梗概,不然,便无赞成反对,都只是道听途说。”他认为在产业落后的中国,经济界同样幼稚,幼稚的中国青年凭着一本书狂热起来,虽是革命狂热初期普遍的现象,并不可取。他希望青年一代,不要人云亦云地讲马克思主义。
接着,戴季陶话锋一转说:“一个人无论读什么书,做什么事,第一不好忘记了自己是人,不好忘记了自己是中国人”,“如果把人的道德抛却,把中国人的信仰丢掉,那便无论研究什么学问,都是有害无益的。这一点尤其是今天在中国革命道途中的青年所千万不可忘记的。”他提醒人们:“中国的革命必须由整个的中山先生的思想和他的主张来指导”,在此过程中,一切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是可利用的材料,“马克斯的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也是我们必须取材的。可是必须要我们去鉴别他,使用他,不好被他鉴别,被他使用。”他认为:“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建国方略,才是指导我们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前进的工作设计”,而“资本论,只是在经济学上,在社会政策上,指示出多少要点来,而没有切实的证明,没有具体的建设。”他以为三民主义比马克思主义更为高明,更适合于落后民族。
胡汉民的意图比较隐晦。他对考茨基相当赞赏,称考茨基“对于马克斯经济学说研究最深,他个人的学术素养,也足以为他制胜的工具”,“对于马克斯经济学的解释,总算是第一个功臣”,考茨基的这本书虽然只是本通俗读物,但却不浅薄,达到了介绍马克思著作本来面目的目的。
胡汉民认为,戴季陶没有译的最后三章:“过剩人口”、“资本制生产方法的曙光”、“资本制生产方法之终结”,“十分重要,断难割弃”。因为在“过剩人口”一章里,介绍了马克思对于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全面批判,包括其来源、作用、错误,“都被这书第五章以下把它完全剖解出来,使我们对于人口论更不必作其他的批判。”与此同时,考茨基的书还开解了人们对马克思的误会,不再把拉萨尔宣传的“工资铁则”说成是马克思的观点。胡汉民的重点落在肯定考茨基对维护马克思主义所作的贡献之上。
戴季陶、胡汉民等选择翻译考茨基的《资本论解说》这一版本也许有一定的偶然性,如前所述,《资本论》来到中国,首先是通过日本这个渠道。日本引进《资本论》所具有的特征,直接影响到了中国,某种程度规范了朱执信、戴季陶等人的眼界,虽然中国的先进分子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引进者和宣传者,相距往往仅有一步之遥。高畠素之所译的考茨基的《马克斯资本论解说》于1919年5月由日本卖文社出版部出版,面世仅仅一个月后,6月2日《晨报》上即开始陆续刊登陈贤溥翻译的中译本。河上肇在自传中说,自己第一次接触唯物史观是1905年,而1906年胡汉民在《非难民生主义者》一文中对他的相关译作有所提及。1919年,河上肇个人办《社会主义研究》杂志,自称“我的开始啃《资本论》大约也是那个时候”,同年戴季陶表达了自己想通读《资本论》的愿望。胡汉民的大作《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开头即引用了若干篇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段落,说明何者为唯物史观,其中两段话,完全取之于河上肇的《见于资本论的唯物史观》。但是,河上肇却明确说自己耗费了二十多年工夫,到五十多岁时,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后,才对唯物史观有了正确的理解。可见,脆弱的日本共产主义运动及其泊来的理论的锢疾和他们思想上对第二国际的偏好,影响到了紧随其后的中国这群译介者。
但是,选择考茨基的版本似乎又有其必然性。曾经是第二国际的负责人,考茨基与恩格斯一起,广泛宣传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继承人,整理完成马克思《资本论》第四卷(即《剩余价值理论史》,作者注)。虽然他曾经被列宁称为“叛徒”,但是无论是恩格斯生前,还是列宁以及苏联共产党,对于他的马克思主义素养不曾完全否定,对他在唯物史观上的贡献普遍认同。他的这本《资本论解说》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入门书籍。
如果仔细地研读考茨基这本《资本论解说》,更可以理解国民党人为何欣赏考茨基。曾经参与翻译《资本论》的哲学家王思华,对考茨基的《资本论解说》有如下的评价:马克思经济学的目的在于研究事物背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阶级的关系,马克思在此文着力于说明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阶级及其矛盾,考茨基没有很好地领会。在方法论上,王思华批评考茨基把“《资本论》第一卷的内容,归纳为三篇:(一)商品、货币、资本;(二)剩余价值;(三)工资与资本收入。在这里,他陷于两重的错误。第一,他把不同质的经济现象——一方面是商品与货币,他方面是资本——混在一起了;第二,他把两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剩余价值与工资——又任意地分割开了。”他对考茨基的批评颇有道理,考茨基此文淡化了阶级斗争的理论。
不仅如此,就《资本论》的目的而言,《资本论解说》是这样写的:“马克斯所研究的,却是一个特定的时代(就是最近数世纪)和特定的国民(就是欧洲及欧系诸国,最近如像日本、印度),特有的‘社会的生产’之发达方法。”这样的表述,很易于让人们感觉到马克思此书只局限于研究欧洲等先进国家,对于落后的中国没有指导意义。事实上,这段话和马克思本人的意思相违,马克思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阁下的事情!……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马克思十分清楚地说明,此文是以英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加以剖析,他不否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因此《资本论》对于其他落后国家有启发和借鉴作用。
联想到1918年列宁所著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显然戴、胡二人通过对考茨基的肯定,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即并不认可苏维埃式的革命。再进一步考虑到以考茨基为首的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放弃了“工人无祖国”的主张,转入民族国家阵线的历史,1927年5月,胡汉民发言批评“工人无祖国”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不懂民族主义,以为“专倡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不能领导世界革命了”,则更可以理解胡汉民为何对考茨基惺惺相惜,更可以理解1927年出版这本《资本论解说》的意图。
从1906年朱执信义正辞严地推崇《资本论》,到1919年戴季陶富于激情地叩响《资本论》的大门,再到1927年戴季陶、胡汉民板着规劝的面孔推出这本考茨基的《资本论解说》一书,可以概括出国民党在政治思想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大致历程。虽然他们对于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解和宣传,仅止于这本考茨基的《资本论解说》,但是,回顾此文的译介,依然可以感受到一百年前《资本论》带来的激烈思想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