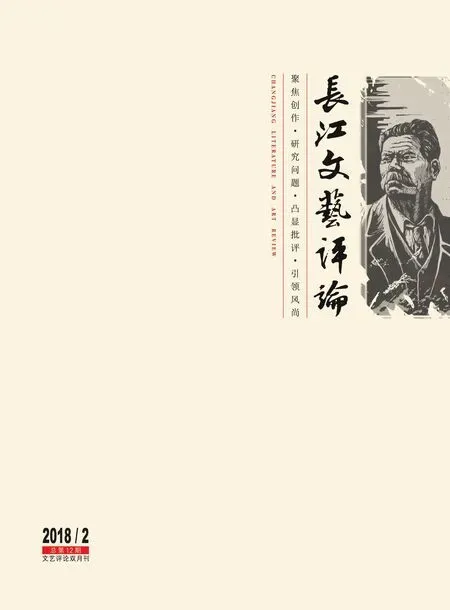时间变形记
——读洪子诚的《材料与注释》
◎李松睿
材料是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必备的资料,是论述与观点的基础和来源,也是检验思想观点是否合理、准确的标准;注释则要么是补充正文的论述,要么是对观点、文献的出处进行说明,既表达对前人学术工作的尊重,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更深入的分析问题的路标。没有一位学者会否认材料与注释在学术工作中的重要性,只是大多数研究者往往更看重自己做出的学术贡献、独特的学术观点,不会过多地在文章或著作中凸显材料与注释。因此,材料与注释一般来说只能不起眼地附在著作的后面或页面的边角处,默默地支撑着学者的整个论述,却很少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不过,洪子诚教授的新书却以“材料与注释”作为书名,而且其中的主体部分,就是诸如1957年毛泽东在颐年堂讲话、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1966年林默涵的检讨书等当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史料,以及洪先生对这些材料所作的注释。这就使得《材料与注释》虽然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著作,但其蕴含的学术价值却又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于是,洪先生也就通过这本书的写作,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学术叙述。
一般来说,文学研究可以分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三个领域。这些领域各自发展出一整套述学方式、学术规范、评价标准、研究传统,这整套研究范式已经发展得如此庞大,使得几乎每一位研究者都只能在满足它的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才能在此基础上做一些有个性的发挥。由此来返观洪先生的《材料与注释》,我们会发现自己遭遇到分类的困难。从表面上看,这本书当然属于文学史研究的范畴,毕竟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如对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评价问题、大连会议关于中间人物问题的讨论等,都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特别是处理十七年文学时无法绕开的话题。如果采用常见的论文或学术著作的讨论方式,对这些话题的分析就很容易落入窠臼,成为文学史研究脉络中的一部分。然而,《材料与注释》的主体部分只是相关史料,洪先生自己的独特分析是以注释的形式出现的,这种灵活、多变的思想表达方式,往往可以绕开论文的论述规范和已有的研究范式,直接对研究者最感兴趣、最受触动的部分发表看法。例如,洪先生的注释常常会超越文学史研究的窠臼,去探讨参与文学活动的具体的人,像林默涵这类文化官员,他们在强大的政治压力面前做出的种种选择背后的心态。特别是收入《材料与注释》中的部分材料,我们能够看到洪先生的写作带有一种自我拷问的性质。也就是说,洪先生的写作一方面是对自己的反思和质疑,另一方面则是带着自己的困惑,进入到当代文学极端的历史语境中去,思考邵荃麟、林默涵、周扬、丁玲、冯雪峰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以及背后的复杂心态。因此,洪先生的《材料与注释》可以说超越了传统的文学研究范式,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具体到研究方法,我觉得可以把洪先生的研究方法称作是“时间变形记”。文学史家在讨论和评价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现象时,他们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时间。因为文学史家非常清楚地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就可以使他相对于当事人来说,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更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对于当事人来说,历史的发展方向是一个未知的、充满了各种陷阱和礁石的凶险海洋。而对于文学史家来说,因为时间赋予他的优势,使得他掌握着非常详尽、清晰的海图,可以让他安全的在一定距离之外品评人物、分析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洪先生在《材料与注释》里显然没有利用自己在时间上的优势,站在道德高点上对当事者指手画脚。他把材料和注释放在一起,制造出一种奇妙的阅读感受。由于洪先生没有直接对材料进行评述,而是把各种材料不加判断地摆在一起,让读者去感受材料和材料之间的联系,以及材料和材料在相互拼接中产生的特殊效果。在书中,一些材料会呈现关于一件事的一种说法,而洪先生会在注释中提供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说法,或者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做出的不同讲述。此外,洪先生在写注释的时候,其语言不像一般的注释那样客观呆板,而是非常文学化的。比如,第52页的注释一开头就说“许广平那个时候可能并不这样想”,接下来继续交代十年之后许广平的看法又有何变化,最后说明周扬、冯雪峰、许广平三人在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下的命运遭际,读来让人唏嘘。再如第123页的注释,指出周扬讲这些话的时候,肯定没有想到,他的看法在一年多之后被推翻。在这些地方,洪先生把不同的时间拼合在一起,让我们看到时间的洪流,以及时间背后隐藏的各种压力,如何深刻地改变着人的思想。于是,所谓人的整体性、思想的统一也就成了一个美好的神话。这种写作方式让时间忽前忽后,使读者在感受时间的变动时,发现人的脆弱与无奈。这样的处理时间的形式,直接让我想到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第一句话:“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的时候,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一定会想起父亲带他去看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所以我把洪先生这种处理时间的方式,理解为“时间变形记”。
事实上,把某个历史人物在不同时间关于同一事件的不同说法罗列出来,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较为常见的写作方式。但是在很多研究者那里,一旦以这种方式来处理其研究对象,他们就会利用自己在时间上所处的优势,对当事人进行某种道德审判,或者指责当事人的虚伪。比如,在今天的郭沫若研究中,研究者经常会提到郭沫若在某个时候怎么说,在另外一个时候又怎么说。用这种手法来论证郭沫若在道德品质上存在的瑕疵。在这类讨论中,研究者呈现出的不是“时间变形记”,而是“时间显形记”。也就是说,研究者直接假定一个人的思想观念应该前后统一,始终保持不变。如果研究对象的思想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所变化,特别是这种变化不符合研究者本人的价值判断时,那么研究者就会把这些不同的观点罗列在一起,指责研究对象是个投机分子,在时间面前显出了自己的原形。而洪先生的研究方法虽然表面上和这类研究类似,但是他没有利用自己在时间上的优势,而是充满了对研究对象、对研究对象所身处的时代的同情与理解。毫不留情的道德审判固然令人读来痛快,但《材料与注释》中那些体贴的分析、温润的论述或许更能勾勒出复杂的历史本相。
当然,在有些时候,我们也能看到洪先生在判断人物时的褒贬。例如,林默涵在1957年亲自修改了冯雪峰为《鲁迅全集》第6卷《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所写的注释。但在80年代初的一次冯雪峰研讨会上,林默涵却站起来指责冯雪峰所写的这条注释歪曲了事实,并进而质疑冯雪峰的人品。这情景在《材料与注释》里出现过多次,应该不是写作上的失误。而是这个场景给洪子诚老师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以至于要在书中不断提到这件事,让人深思文学史中的道德问题。
总之,生活在20世纪50至70年代的人,几乎都处在巨大的压力下,不得不在时间的洪流中发生改变。如何判断这些人的境遇与选择,也就成了今天的道德难题。而洪先生在《材料与注释》中创造的这种全新的学术文体,无疑为我们探索了一条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