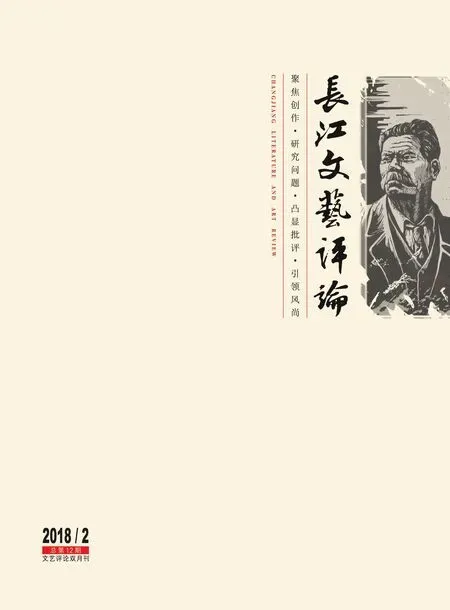是非自我之间
——关于自传的真实性与自由度
◎斯 日
一、“谎言”并不是谎言
本人叙述自我的生平,是自传的核心。自我的生平是真实的存在,叙述一种真实的存在,实际上是再现的过程,因为所要叙述的自我已经是过去式,从过去的时间里经过语言的组织叙述,再现曾经的自我的客观存在,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塑造”另一个自我,这是自传的核心命题。可以说,自传的叙述,如同再现这个词语所内含的意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有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甚至是变动性。由此一来,力求客观和真实这个被要求为自传创作中第一要素的特性,必然会遭遇来自研究者、读者的挑剔和质疑。挑剔、质疑,无一例外都指向经过语言叙述的再现过程,即自我的真实被语言描述的过程,这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所言:“事实是如何被描述,以用来认定某种解释模式而非其他模式。”
关于传记的文类属性,学界的观点从未达成一致,真实性使传记隶属于历史,虚构性使传记隶属于文学。不过在具有真实性与虚构性的统一性这一点上,传记成为一种跨学科的文类,对此学界的观点是一致的。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上面所述关于自传与文学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只能在文学的特定领域里讨论才能够成立,而且必须设定一个前提,即不能超越自传性文学这个范畴。
从自传的虚构性说到与自传性文学之间的关系,其实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就一个,即既然确定自传不可避免地带有文学创作手法中的虚构特征,那么,虚构在自传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围绕这个核心问题,可以讨论更深层的问题,如自传中设置虚构的目的是什么,其在实际文本中存在状态或者所呈现的态势是什么样的,这个存在又引发了什么样的影响,诸如此类。这些问题的提出,不只指涉自传文本,而是整个传记研究领域的问题,自传之外的其他形式的传记,如他传、日记、书信、年谱、墓志铭等无一能够排除这一问题。因为“在书信、日记、笔记中,在任何有意识的自传形式中,作者必定有某些隐瞒,一部自传可能有歪曲,事实可能被修改或省略”,真实与虚构从未能达到楚汉边界、泾渭分明。
在真实与虚构之间,自传表现出不拘一格的形式,从而带来自传文本的无法预测性和不确定性,一部自传在面世之前是无法让人预测或想象的,虽然必然而且必须以自传作者本人真实生平为蓝本,不过关于蓝本被添加、删减或者修饰、润色方面的成分,往往超越了真实生平的蓝本本身。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于2016年3—9月和2017年3—9月在泸州市古蔺县观文镇复兴村进行。试验地土壤类型为黄壤,基本理化性状:有机质26.8 g/kg;pH 6.8,碱解氮118.3 mg/kg,速效磷74.0 mg/kg,阳离子交换量8.5 cmol/kg。
卢梭《忏悔录》的诞生,在传统文学领域带来了崭新的氛围,他要在欧洲以想象为中心的文学创作之外另辟新路:“我在从事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业”,由此开启了一个书写自传的历史时代,“歌德、赫尔岑、托尔斯泰、穆勒、罗斯金、特罗洛普、乔治·穆尔、蒲宁、纪德,只有其中的一些,如果没有卢梭的先例,他们也许不会调转笔锋,回忆过往,推出个人传记”。
在卢梭笔下的自传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琢的,他宣称:“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全部地展示在世人面前:此人便是我。”绝对的真实,是这部自传展现在自传史上最突出的特色,即使是在21世纪的今天这个定位一直未曾改变。然而,这并不掩盖或者不能阻挡其真实性曾经所遭遇的质疑。
解构主义学者保罗·德曼是挑起质疑最多而且影响力最大的学者。他撬开卢梭自传包装严密的真实面目的阿基米德之点,是卢梭第三部自传《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思》里为自己谎言进行辩护这一事件。作为解构主义者,德曼是从语言修辞角度入手解构这个“谎言”。
从《散步》的忏悔直接联想到《忏悔录》中的一次偷窃行为,德曼的联想并不是捕风捉影,而是他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卢梭明明喜欢马里翁,居然能够毫不犹豫地诬陷马里翁,这个事情的发生确实出乎正常人的正常行为。结合《散步》中的忏悔,德曼认为所描述的偷丝带事件是卢梭在虚构事实,“目的是为了写忏悔录,这样,暴露得越多、罪行越严重越好,因为暴露得越多,可以为之感到羞辱的东西就越多,抵制暴露的力量就越大,场面也就越令人满意”。由此可以推算出卢梭在《忏悔录》中讲述的偷丝带那个事件也是不真实的,卢梭在随意地或者是在为了掩盖某个目的而在进行虚构事实。德曼的解构完全符合解构主义的主张,随之引起学界对卢梭自传真实性的质疑。
汉娜·阿伦特1964年圣诞节这天在写给好友玛丽·麦卡锡的信中如此说道:
我刚看完(萨特的)《文字生涯》(LesM ot s),觉得简直恶心,很想写篇文章来批驳一下他的这个弥天大谎。这让我想起最近学术界挖出的卢梭旧事——他根本就没有把五个孩子丢在孤儿院,道理很简单,因为他没有生育能力,我觉得这很有可能。
卢梭的《忏悔录》,曾经被他自己称之为袒露真实的自我,却接二连三遭遇质疑。真实的事实是如何?除了卢梭自己,谁也不可能真正无限接近这个事实。
胡适的《四十自述》,自述的也不是百分百真实的胡适生活,对此胡适自己也承认:“因为第一章只是用小说体追写一个传记,其中写那太子会颇有用想象补充的部分,虽然堇人叔来信指出,我也不去更动了。”
自传的作者是自己,其所拥有的自由度,其他传记文类作者望尘莫及,德里达的“主动自传说”以及麦克莱恩的“生存所需的神话说”,指向的都是自传在写作自由上的特征。不过这个自由是有度的,反过来说,这个自由亦是自传创作与生俱来的局限性或者说是一个美丽的陷阱,即自己叙述自己,自己塑造自己,自己“虚构”自己,其中自我主体意识的干预不可避免。自传是与自我周旋,要把握好周旋的度。
二、目的与“是非自我”之间
阅读自传,我们看到的人都不可能是自传作者在真实人生中的“那个人”,而是经过作家之笔塑造出来的、作家想让人看到的“那个人”。作者在执笔之时早已绘制好了一幅草图,纸和笔是真实的,计划呈现在纸上的景色在各自孤立状态下亦是真实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只是在绘画过程中运用了艺术手法,这里添加了一笔,那里删除了一笔,又在另一处涂抹了一块颜色,增删修饰,目的是为了让“作品”更具真实性,当然,这个真实性是作者心中的那个“真实性”,“事实必须经过处理:有些事实要增加亮色;有些事实要涂暗”。
“处理”真实的创作手法,称之为阐释策略。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说:“阐释就是辨析文本前方展开的此在的型式。”“任何未经符号中介、象征中介和文本中介的自我理解,都是不存在的,理解最终要吻合于对这些中介环节的阐释。”这里所说“自我理解”是对“此在”的阐释,在传记学中指向传记家的“自我理解”,即传记家对所要撰修的传主这个“此在”的理解和阐释,经过符号中介、象征中介和文本中介的范式,即经过“吻合于对这些中介环节的阐释”,辨析、阐明这个“此在”的全貌、特性、意义。这个过程是阐释策略,属于修辞学。
传记需要阐释策略,“传记文学的阐释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解释事实的过程就是一个给事实赋予意义的过程。在传记文学的阐释里,作者的作传目的常常决定他们采取种种不同的阐释策略。”一切的阐释只因为目的,目的性制约着阐释策略。“传记作者和研究者没有把传记的自主性放在首位,常常有意无意地用传记来为某个目的服务。”
自传中为自我的目的而运用阐释策略,有以下几种可以探讨:
第一,对某个时期某个事件进行有目的的阐释。从自我角度对事实进行阐释,目的在于说明事件的真实或者在于掩盖事件的真实,抑或在为另一种事实编织看似真实的面具。马克·萧芮说传记作家“是戴着锁链写作”,那么,自传中的阐释事实是让传主(自我)戴着面具生活。如果,汉娜·阿伦特关于卢梭的质疑成立,那么,卢梭在《忏悔录》中所讲述将五个孩子送去孤儿院抚养这一“事实”属于这一类阐释:阐释事实是为了编织看似真实的面具,为自己所主张“爱弥儿”的教育理念“编织”完美的事实。
第二,在对某段时期或对某个事件回避、语焉不详或者闭口不谈,目的在于有意淡化事实的存在,更在于为另一个目的塑造氛围,当然,一般是在面对有损于或不利于自我形象的事实时采取这一种阐释策略。居里夫人在自传《居里夫人自传》中写祖国波兰,写自己童年,写与丈夫皮埃尔·居里的相识、结婚以及共同为科学事业所做的奋斗,还写了两个女儿的出生、成长等等,但从头到尾只字不提与丈夫的学生和助手保罗·郎之万之间的情感纠葛。这一事实的有意隐去,属于有目的的阐释,忽略一种事实是为了淡化事实的存在。
第三,个别自传中事实失去真实性,不可能排除一种可能性,即自传作者确实记错或者是误记,属于无意的阐释,当然这种情况需要通过与相关人物、事件和文献资料进行核实来证明。西蒙娜·德·波伏瓦在第三部回忆录《事物的力量》中对第二部回忆录《岁月的力量》中存在的“许多小错误,而且有两三处还挺严重的”,作出了“检讨”:“我已经很细心了,但是,百密一疏,我肯定在很多地方给弄错了,不过,我再次声明,我绝没有故意歪曲事实。”
而在一部自传中通篇运用阐释策略的作品为数不多,因为通篇阐释,意味着阐释整个人生,尤其是经过自我的“有意审视”再塑另一个自我,除非别有目的,通常的写作中不可想象。然而,瞿秋白写于1935年狱中的自传作品《多余的话》则属于这一种情况。
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瞿秋白从始至终都真诚而热情地投身革命、忘我工作,甚至为革命献出了全部精力甚至生命。这是瞿秋白真实的历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然而在《多余的话》中,他却否定这些历史事实,说自己没有“治国平天下的大志”“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师’……”“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这样写的目的何在呢?如果不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特定的历史背景,不理解瞿秋白作为党的领袖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经历,就无法真正读懂瞿秋白。通观全文,瞿秋白否定自我,但没有否定党组织;否定自己的能力品质,但没有否定革命信仰,正是通过对自我的否定,袒露真实的自我,向组织证明自己的忠诚。
三、自传与“戴着镣铐跳舞”之间
普鲁斯特曾经说过:“唯美主义注定的命运是以吃掉自己的尾巴结束。”自传的作者无限依赖写作上的自由,再现一个自我,也许这个自我是作者自己在过去的时间里真实的自我,也许是作者自己想要在过去的时间里存在的自我,正如勒热内所说:“关乎自传最深层的真正的问题不是用诚实的方式再现了一段人生时光,而是掌控了一段无法掌控的时光。”掌控了一段曾经无法掌控的时光,其过程中自我主体意识的登场和干预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占领着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为“无法掌控”的一段时光戴上某种面纱同样不可避免。不过,这些与自传所要强调的真实性、史料性、文献性有着原则上的背离。随着在当代社会里自传文类越来越多地呈现,写作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引起相关专家、研究者的高度关注。这些问题是,“如经历与自传中对它的表征这两者关系的实质,以及身份与自传中对它的塑造之间的关系”,诸如此类,核心问题离不开传主是被如何描述,即“自我的虚构”如何实现。
自传中自我叙述的过程是,作者陪伴着自己在那段曾经“无法掌控的时光”里重新出生、成长,这时,自己即便是具有上帝般的全知视觉,也要扮演和履行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陌生人的角色和义务。他传在他人的生命手册上勾勒、涂画、绘制,受限于他人的生平历史的固定尺度,只能“戴着镣铐跳舞”,其实,自传的创作也不例外。
如果将传记写作中必要的必然要素视作为“镣铐”,那么,力求客观、真实描述事实,是自传写作中最重要的“镣铐”。
西蒙娜·德·波伏瓦是一个热情的自传写作者,她接连写了四部回忆录:《端方淑女》(1958)《岁月的力量》(1960)《事物的力量》(1963)《归根到底》(1972)。在第三部回忆录《事物的力量》中,波伏瓦谈了几点自传一定必然带来的问题:一、作者能够讲述所有生平吗?二、在自传这一文本性世界中,“真实”究竟深居何处?自传从来都真正是客观叙述吗?三、如果作者受到文类规则的束缚,要为文本圈定可供核实的经历,那么对美学因素的考虑是否必须屈居次席呢?
其中,第二个问题谈的是自传中的真实性。波伏瓦的回答很明确:“当然,我在叙述我的过去时,总是尽量地做到客观公正。”波伏瓦的自传“尽量地做到客观公正”,即使自己的过往生活中有让“我感到窘迫或尴尬”的事件,那也是由真实的事实编织而成的自己人生“镣铐”中一个零件,不能少,当然也不能多。今天,当我们在研究波伏瓦著作和思想时,在研究波伏瓦所生活的20世纪的时代和事件时,她的这些回忆录作为不可替代的重要文献资料,其价值越来越被重视。
此外,波伏瓦所谈的第三个问题,即美学因素,实质是指自传中通过语言艺术组织的虚构问题,即“自我虚构”,对此,波伏瓦的态度同样是干净利索:“不,我的自传并不是一部艺术作品,而是我激情、失望、激荡的生活。我并不想附庸风雅,我是在叙述自己的生活。”
著名传记研究家保罗·让·埃金在其《自传的指涉美学》一文中探讨过自传美学背后的动机,说探索、创造是自传美学的重要动机。波伏瓦立传的目的不在于探索和创造,她的一生本身是一次成功的探索和创造。与其如此,还不如说,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家,波伏瓦通过自传更想呈现和表达的是对死亡意识的抗拒,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不在此展开。不过需要补充的一点是,试图表达对死亡意识的抗拒,这个目的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波伏瓦的自传依然逃脱不掉采用了阐释策略这个谋划。
自传文本,从诞生的最初就开始参与“虚构人生”的计划,虽然事实的“镣铐”无一刻不存在,但从未能阻止“真实的谎言”随时上演。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自传是一种“最为复杂的令人难以捉摸的文学性文献”。
注释:
[1]杨正润:《现代传记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3页。
[2]【加】艾拉·布鲁斯·奈德尔:《传记与理论:通向诗学之路》,梁庆标选编:《传记家的报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7页。
[3]【美】约翰·豪尔普林:《传记家的报复》,杨正润译,《传记文学》2016年第11期。
[4]【法】卢梭:《忏悔录》,科恩:《英文版导读》,陈筱卿译,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5]昂智慧:《〈忏悔录〉的真实性与语言的物质性》,《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
[6]【美】汉娜·阿伦特、【美】玛丽·麦卡锡著,【美】卡罗尔·布莱曼编辑:《朋友之间——汉娜·阿伦特、玛丽·麦卡锡书信集(1945-1975)》,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273页。
[7][9][10]赵白生:《传记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51页,135页,7页。
[8]朱士群:《作为社会认识论的解释学——利科的阐释策略新探》,《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5期。
[11][15]【法】西蒙娜·德·波伏瓦:《波伏瓦回忆录》第三卷《事物的力量》,陈筱卿译,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2页。
[12][13][14][16]【英】苏珊·本布里奇:《对抗死亡:西蒙娜·德·波伏瓦的自传书写》,李凯平、陈亚斐译,梁庆标选编:《传记家的报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13页,301页。